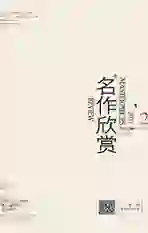《孤独者》中隐含作者声音的实现途径
2021-02-23车文丽
摘 要:小说《孤独者》,以其深邃复杂的思想意蕴备受关注。要理解小说的深层意蕴,离不开对隐含作者声音的探讨。隐含作者的隐而不显虽然为探讨带来难度,但小说中隐含作者的声音是有迹可循的。《孤独者》中,隐含作者通过叙述者、叙述者与人物的裂隙、人物与人物的裂隙发出声音。
关键词:隐含作者 叙述者 人物
创作于1925年的小说《孤独者》,是鲁迅小说集《彷徨》中的名篇。小说以其深邃、复杂的思想意蕴备受关注。然而,小说中隐含着作者声音的探讨,并没有引起学术界的关注。究其原因,正如唐敏所说,一方面是因为隐含作者在讨论中往往“被缺席”,另一方面,隐含作者隐而不显,不像叙述者、人物、情节等元素以显在的方式存在于小说中,读者很容易发现和区别。a在小说《孤独者》中,隐含作者的隐而不显正是作者独特的叙事策略。这样的叙事策略,增加了读者的阅读难度,拓宽了读者的阅读体验,让读者沉浸在小说营造的叙事氛围中的同时,不断追寻隐含作者的声音。
隐含作者作为文本的统一性力量所在,是整个文本中最具权威性的主体。隐含作者的声音是潜在的,虽然没有明显的话语实体,但浸满全文。《孤独者》中,隱含作者作为一个主体性的存在,它的声音的实现途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隐含作者通过叙述者隐含地传达他的声音
通过叙述者和人物隐含地传达隐含作者的声音,这是《孤独者》中隐含作者表达的最重要的途径。《孤独者》从叙述者和人物口中说出的话语,或者是叙述者和人物的感受,往往含有深层意蕴。这些深层意蕴,是叙述者或人物意识不到的。因为,它们不是叙述者或人物的意图,这一深层的声音只能是隐含作者的意图。《孤独者》中大量使用这一手法来使隐含作者的声音得以彰显。
(一)叙述者“我”眼中的“连殳”
小说的叙述从送殓开始,在叙述者“我”的眼中,连殳的本家“仿佛将他当作一个外国人看待”b,村人看来他“确是一个异类”,叙述者认为他“没有家小,家中究竟是非常寂寞”,这些是孤独者连殳的表层显现。从叙述者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的勾勒中,连殳的孤独形象映入读者的眼帘。然而,在族人“全都照旧”的丧葬礼仪的安排下,叙述者眼中的村人“咽着吐沫,新奇地听候消息”,最后,连殳的反应让“沉默充满全厅”,而人们“全数悚然”,这些看似冷静的叙述,叙述者将一个沉默的不被族人理解和接受的孤独者连殳的处境展现在读者的眼前。在叙述者的眼中,连殳在葬礼的最后,“忽然流下泪”,“接着就失声,立刻又变成长嚎,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里嗥叫,惨伤里夹着愤怒和悲哀”。这样的叙述,表面上是叙述者“我”在转述葬礼当天的所见所闻,却在深层发出隐含作者对连殳这样一个“孤独者”命运悲悯的声音。
(二)叙述者“连殳”眼中的祖母
小说在一场遵循旧例的葬礼中开始,小说中魏连殳的祖母的形象,是在叙述者“我”和连殳的建构中完成的。小说的第三章,隐含作者通过魏连殳之口,展示了另一位孤独者。在连殳的眼中,祖母作为父亲的继母,并不是“自己的祖母”,虽然在小时候,连殳认为自己同样爱她。但这份来自年幼的孩子的爱,并没有改变祖母的孤独的命运。连殳的记忆里,祖母是“终日坐在窗下慢慢地做针线”,儿时的连殳无论怎样在她面前玩笑,都不能让祖母快乐。因此,祖母常使连殳“觉得冷冷地,和别人的祖母们有些不同”。祖母和连殳相依为命,却不能互相理解,祖母的生存状态是孤独的:“终日终年的做针线,机器似的。”连殳并不能对祖母的艰辛孤苦感同身受,只是觉得“发烦”。祖母活着的时候“少见笑容”,连含辛茹苦拉扯大的连殳也不能理解和沟通。被世人隔绝的祖母,就连去世后,也是孤独凄凉的。循规蹈矩的葬礼,一切按旧例进行,就连“哭”也是按程式进行,“连先前竭力欺凌她的人们也哭,至少脸上很惨然”,这是多么的讽刺!隐含作者通过连殳的叙述,将一个在文本中缺席的人物展现在读者眼前。作为文本中的人物,祖母始终是没有自己的声音的,她在文本中唯一的一次言语,竟然是临终遗言。她的孤寂,她的苦难落寞的人生,也只是在叙述者的寥寥数语中呈现给读者。作为“孤独者”的“我”和魏连殳,我们能在字里行间寻到他们的声音,他们是有着自我意识的灵魂(尽管叙述者“我”时常隐匿自己的情感)。然而,同样作为“孤独者”的魏连殳的祖母,却是没有主体性的存在,她始终是缺席的,像影子一样存在于小说中。这一位始终缺席的人物的安排,正是隐含作者的匠心所在。
二、隐含作者在叙述者与人物的裂隙中发出声音
在小说中,叙述者“我”是唯一试图理解并尝试帮助连殳的人,在小说一开始连殳祖母的送殓场面中“我”感受到了来自村人们对连殳的敌意。“我”冷静地将其归因于“中国的兴学虽说已经二十年了,寒石山却连小学也没有”。然而,叙述者“我”的内心体验有时又是极其暧昧的。一方面,在小说的第二节和第三节,“我”与魏连殳的几次讨论,又以开放式的结局呈现给读者。
其一是关于孩子问题的讨论。
小说中,魏连殳虽然在身边的人看来行为怪异,为人处世让人难以理解,他也似乎没有与世俗力量和解的愿望。但是,这并不能造成连殳的彻底孤独和绝望。在小说中,隐含作者通过魏连殳和“我”关于孩子的对话,直接而深入地刺痛了魏连殳的内心。这样的对话也直抵读者的内心,带领读者更深入地思考“孩子”作为未来世界的希望,这希望是否渺茫?小说中,连殳起初认为“孩子总是好的,他们全是天真”。而“我”却在怀疑:“如果孩子中没有坏根苗,大起来怎么会有坏花朵?”而对于连殳来说,叙述者“我”不经意的怀疑声,还是让他对心中仅存的那点希望的曙光“孩子”产生了质疑:“想起来真觉得有些奇怪。我到你这里来时,街上看见一个很小的小孩,拿了一片芦叶指着我道:“杀!他还不很能走路……”叙述者“我”将问题抛出来,却并没有做出回答,在小说中,当连殳对孩子的天性质疑后,“我”的态度是含混和纠缠的。“我”一方面质疑连殳对孩子天性的乐观,而当连殳开始对孩子的天性有悲观的看法时,“我”又开始劝慰“这是环境教坏的”,然而“我”“即刻很后悔我的话”。叙述者“我”甚至作为主体性的存在,两次介入讨论,迫使讨论在没有结果的情况下戛然而止。第一次,“我”看到连殳“显出许久不见的冷冷的态度来,默默地连吸了两支烟”,等到他再去取第三支烟时,“我便只好逃走了”,叙述者“我”的“逃走”,让连殳失去了表达的机会。第二次讨论这一话题之后,“我”见连殳“只竭力地喝酒,其间又竭力地吸烟”,“我”又一次中断讨论,“用别的话来支梧”。隐含作者这样的安排,让魏连殳和“我”关于孩子的对话呈开放式的结局,叙述者“我”和魏连殳对于孩子问题的两种不同声音,也会久久盘旋在读者的心中。而这种内心的矛盾困惑,何尝不是隐含作者要让读者去思考的问题?魏连殳在小说中被打断的关于孩子天性问题的认识,又会不会是魏连殳孤独人生最后的曙光破灭的前兆?隐含作者将讨论的答案和结果留白,带给了读者更广阔的思考空间。
其二是关于生活态度的讨论。
小说中,叙述者“我”和魏连殳对于故乡人情的讨论从第二部分开始。魏连殳用冷峭的语气诉说故乡人情的虚伪:“他们知道我不娶的了。但这都没有什么关系。他们其实是要过继给我那一间寒石山的破屋子。我此外一无所有,你是知道的;钱一到手就花完。只有这一间破屋子。他们父子的一生的事业是在逐出那一个借住着的老女工。”魏连殳体会到故乡人情的冷漠虚伪。叙述者“我”劝慰:“我看你的本家也还不至于此。他们不过思想略旧一点罢了。”然而,“我”的劝解并没有得到魏连殳的认同,这次对话在“我”的转移话题和魏连殳的沉默中结束。而这之后,在S城,魏连殳遭遇了小报上的攻击,到春天便被辞退。魏连殳遭辞退后的约三个月,“我”去看望他。小说借叙述者“我”的眼睛,看到“满眼是凄凉和空空洞洞”,“先前曾经常常围绕着忧郁慷慨的青年,怀才不遇的奇士和腌脏吵闹的孩子们的,现在却见得很闲静,只在面上蒙着一层薄薄的灰尘”。面对魏连殳的境况,叙述者“我”劝诫:“我以为你太自寻苦恼了。你看得人间太坏……”“你实在亲手造了独头茧,将自己裹在里面了。你应该将世间看得光明些。”在这段对话中,魏连殳表面上似乎被“我”说服“也许如此罢”。可是,魏连殳再次提出问题:“你说:那丝是怎么来的?”接下来魏连殳借自己祖母的遭遇,说出了自己的看法:“你现在对于我的意见,就是我先前对于她的意见。然而我的那时的意见,其实也不对的。”叙述者“我”似乎没有被魏连殳说服,但是,叙述者“我”在表面平静的叙述中隐藏了主体性的价值判断。隐含作者用这种方法塑造了一个对魏连殳既有理解和同情,又有不同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叙述者“我”。尽管“我”对于魏连殳的理解甚至移情,在小说中往往留有痕迹。然而,当读者追寻到足迹,隐含作者又悄悄地将足迹隐匿,只露出一点点端倪。在这段讨论中,读者看不到叙述者“我”明确的态度转变,却在字里行间品出了叙述者“我”内心的涟漪:“灯火在微微地发抖。”叙述者“我”又一次以主体性的姿态介入讨论并再一次打断讨论“辞别出门”,“我”看到圆月已经升在中天了,“是极静的夜”。关于生活態度的讨论,其结果是不明朗的,是隐含作者设置的两种不同的声音的对话。
第三是关于生存意义的讨论。
叙述者“我”在面对魏连殳深夜来访,迟疑地说出:“便是抄写,一月二三十块钱的也可以的。”“我……,我还得活几天……。”“为什么呢?”叙述者“我”的疑问,是在魏连殳不在场的情况下提出的,这个疑问甚至让叙述者“我”“立刻自己也觉得可笑了”。而隐含作者借叙述者之口抛出这一疑问之后,魏连殳在缺席的情况下(小说第四部分,魏连殳的书信),用书信的形式完成对话。这次对话,是心灵与心灵的碰撞,是两个孤独的灵魂之间对生存意义的探寻。魏连殳在信件中说出自己的心声,他愿意为生活所累,为此求乞、寂寞都不在乎,只要能“有所为”。但是现在却躬行自己先前所憎恶的,所反对的一切,拒斥自己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甚至这“有所为”已经低到仅仅是因为有一个“愿意我活几天”的人。对于魏连殳来说,生存的最后一点希望和意义已经不复存在。魏连殳认为自己是失败的,生存的意义和价值已经失去。面对魏连殳的告白,叙述者“我”却选择了沉默,“忽而又想写一封信回答他,但又觉得没有话说,于是这意思也立即消失了”。“我的确渐渐地在忘却他”,叙述者“我”和魏连殳对于生存意义的讨论到这里,表面上好像停止了,正如魏连殳在信中所说:“我们大概究竟不是一路的。”然而,叙述者“我”的态度是暧昧的,叙述者“我”时而“不知怎地虽然因此记起,但他的面貌却总是逐渐模糊;然而又似乎和我日加密切起来,往往无端感到一种连自己也莫名其妙的不安和极轻微的震颤”;时而觉得自己“其实已经将他忘却了”,这是叙述者“我”竭力从容控制自己内心的挣扎,然而面对可能的同样的宿命,叙述者“我”很难真正轻松。所以,在小说的最后,“我”想要去逃离:“我快步走着,仿佛要从一种沉重的东西中冲出,但是不能够。”而叙事者“我”终究与魏连殳不同,却又有着隐秘而微妙的情感关系,“我”的“耳朵中有什么挣扎着,久之,久之,终于挣扎出来了,隐约像是长嗥,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
三、隐含作者在人物与人物的裂隙中发出声音
在小说的第四部分,隐含作者让人物魏连殳用书信的形式直接展现内心的想法。连殳在书信中称自己已经躬行“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这在连殳看来,是彻底的失败:“先前我自以为是失败者,现在知道那并不,现在才真是失败者了。”生活上的困顿,艰难的生存压力并没有让连殳觉得是真正的失败,而有了每月现洋八十元的薪水,做了杜师长顾问的连殳却认为自己真正失败了。“新的宾客,新的馈赠,新的颂扬”并不能填补连殳的孤独的灵魂,只带来了“新的失眠和吐血”,而与此相对的是大良的祖母对此截然不同的态度和反应。连殳困顿时,她冷眼相对,甚至对来访的客人都不耐烦。然而,在她看来,做了杜师长顾问后,魏大人近来“脸也抬高起来,气昂昂的。对人也不像先前那么迂。你知道,他先前不是像一个哑子,见我是叫老太太的么?后来就叫‘老家伙。唉唉,真是有趣”,她甚至把正屋也让给连殳住了,自己搬在厢房里。在大良的祖母看来,连殳是“走红运”。很明显,隐含作者设置这一组对立是要读者主动去思考:魏连殳果真是失败者吗?他的绝境和自我毁灭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孤独是人的生存状态的本质么?通过这样对立的设置,隐含作者的意图被进一步强化。
a 唐敏:《鲁迅小说符号叙述学研究的思路与方法》,《聊城大学学报》2018年第3期,第54页。
b 鲁迅:《鲁迅小说全编》,漓江出版社2007年第3版,第188—204页(文中相关引文皆出自此版本,故不再一一另注)。
基金项目: 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隐含作者研究》(项目编号:ZGW17205)的阶段性成果;南昌航空大学科研基金项目(项目编号:EA201314082)的支持
作 者: 车文丽,博士,南昌航空大学文法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叙事学、影视美学。
编 辑: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