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在记忆里生长的事物
2021-02-21张发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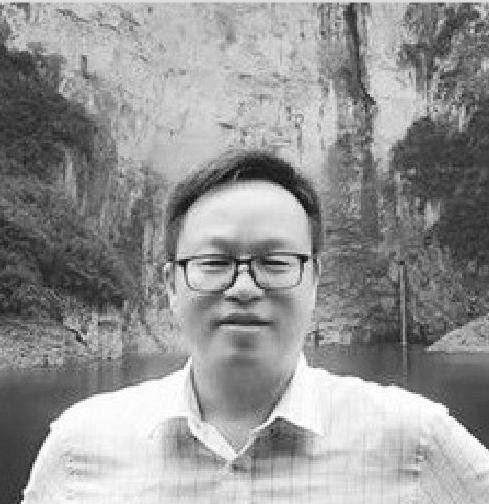

谢宜兴:青年作家张发建这两篇散文,可以说是一组关于闽东的风物画。作者从自己最熟悉的事物与生活入手,写出了对故乡的廊桥之思与对童年的薯米之忆。也许正由于这些都是久已生长在记忆里的事物,作者对廊桥身上所蕴含的人与历史、人与自然、人与神祇及人与人的和谐相处的精神的思考,精辟独到;对番薯收成从刨薯丝、洗薯粉及晒、收薯米的过程的刻画,引人入胜。文中情感内敛,不事张扬,但从行文冷静的叙述中,读者自能感受到作者来自童年、烙在心底的深情。如果是细心的读者,还能从中读出作者深情中的喟叹,一种沧桑感在阅读过后的心头萦绕。
危砖黄:关于古廊桥和番薯米的记忆,在发建这里,首先是来自童年的记忆。他以朴实的笔触,写出了生活和生命对于古廊桥和番薯米的依赖。从童年的记忆出发,或者说“生长”,历史的记忆随之而来。发建以他惯有的理性思考,发掘出古廊桥和番薯米的人文底蕴和精神内涵。这使《古廊桥》具有了某种学术性,使《番薯米》超越了个体体验。散文写作当然需要敏锐的感觉和独特的细节。发建对于古廊桥的“空灵感”和水流声的“压迫感”的描写,对于父母制作番薯米的细节的描写,富有情绪和情感记忆,特别令人赞赏。
古 廊 桥
一
我以为,闽浙边上的廊桥与闽粤赣边上的土楼一样,都是激动人心的工程。
土楼作为客家人引以为豪的建筑形式,是闽粤赣民居中的瑰宝。它产生于宋元,成熟于明清。它的历史就是一部客家人南迁并不断融入当地文明的历史。2008年申遗成功后,土楼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现存的一千多座土楼,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与保护。
但是,在土楼产生的宋元时期,廊桥的建筑技术就已经十分成熟,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里精彩呈现的汴河虹桥,就是一个历史的明证。然而,此后的数百年里,廊桥却神秘失踪了,直到现代,人们才突然在闽浙边上的大山深处发现了它的踪迹。其中现存最古老的一座是位于浙江省庆元县举水乡月山村的如龙桥,至今近四百年历史。不过,由于洪水、火灾以及修建公路、水库等原因,至今全国也只有一百余座木拱廊桥被保存了下来。
可以说廊桥是一个不事炫耀、无所欲求的苦行修士,是一个修建规模宏大、工期约束、一毁即灭的时代刻印,也是一种追求融会贯通、开放交流的生活方式。
这就是廊桥。
二
我与廊桥的结缘,始于很小的时候,因为我老家村边一两公里外的地方就有一座修建于清朝乾隆年间的蛇眉桥。“蛇眉”是当地的土话,我却更愿意唤它为“昨明桥”或“什明桥”,这多少会更增添一些文化或者禅意。
蛇眉桥在蟾溪之上,其位置是明清两代寿宁通往政和、庆元和福安的重要通道。甚至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我爷爷等一班盐客也是经过这里把斜滩挑回来的海盐再挑到政和、庆元等地售卖,只是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个曾经的交通要道渐渐冷清,人迹慢慢稀少。
父母不允许孩子们到那里玩耍,除了人少,还有一个原因是这座桥上的一些怪异现象,比如那么长的一座桥,你居然找不到一个蜘蛛网,按我老家的说法,不见蜘蛛网的地方多半是有未可知之物的。当然,更主要是因为那里地势险要、桥底溪水汹涌。父母越不许可,孩子们就越向往。放学之后,经常三五成群地往桥的方向赶,经过一段乡村公路,再走过两段持续下坡的石板小路,就可以看见若隐若现的桥体了。靠近桥体,耳边是一片嗡嗡作响的水声,让你还没有到达桥面,心里就会产生一种紧张的感觉,不由得加快了脚步。
廊桥是厝桥,桥面上方是屋顶,屋顶之上为瓦楞。廊桥是用大圆木架成的拱桥,两端低,中间高,走在木桥中央,人有浮在空中的感觉。站在中央,从木桥两边风雨板镂空处往外望,上下游的感觉迥然不同。往下游看,蟾溪在不远处拐弯隐入了群山之中,神秘莫测;向上游看,溪水击打两岸石壁激起的一片片浪花,有一种强烈的压迫感,让你并不愿意在桥上做过多的停留。
快速穿过几十米长的桥面后,孩子们迅速抄近路到达了蛇眉桥的木拱正下方。眼前,激流浩荡,响声震动,完全把欢笑声淹没;抬头,几十根圆形巨木整齐排列,相互交织,仿若一个精美的编织,近在眼前,可伸手去摘,却虚无缥缈,反而会有一阵眩晕;不远处,尽是悬崖峭壁,人在其中,好像总有一种气流包围着你,浑身通透,就算是大夏天的正午,也是凉意阵阵。
后来,我到过三峡大坝,也到过葛洲坝,那水势无疑更恢宏更壮观,但我始终无法找到当初在蛇眉桥下那种空灵的感觉。那种空灵,是否更多的是因为叹服祖先们两百多年前就能在绝壁上建出那么飘逸的廊桥呢?
三
随着时间推移,与蛇眉桥一样,多数闽浙边上的廊桥在交通上的作用式微,而且,在现代科技面前,建桥技术也不再神秘,但是,人们对廊桥的热情却是与日俱增。十多年前,我接待过一位来自北京的部委领导,他说来福建最大的愿望就是到闽东去看看神奇的廊桥。眼下,人们热衷的程度已经远遠超出单纯的走走看看,而是深入研究或广泛宣传,甚至还有人筹集巨资重新再建新廊桥。
这并不是一种偶然现象,因为廊桥在闽浙文明发展甚至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都曾经发挥过无可比拟的重要作用,时至今日,它在精神层面上的功效一直未曾衰弱,甚至反而得到了更大的彰显。
这种精神上的功效,便体现为人与历史的和谐统一。
中华民族一直注重向前发展,苦难深重的人民总把美好的希望寄托于未来和子孙,于是比起祖先,人们自然更关注子女后代的发展。向前看不是一件坏事,但时间一长久,人们却发现自己对祖先的忽视造成了某种缺憾,比如孙子未必知道爷爷和奶奶的名字,许多村庄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族系来自哪里,祖先是谁。这反过来,又促使人们开始寻根,开始修订家谱,开始寻找祖先们过往的故事。
闽浙边上的廊桥,是历史钉在这片山水之间的遗迹。看到廊桥,人们就会想起宋代缪蟾“踏破前桥几板霜”奔赴临安考试的情形,就会追寻三百多年前冯梦龙跋山涉水前来寿宁为令的故事,就会感怀闽东浙南乡民的艰辛与劳作。
廊桥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追寻历史与精神皈依的需要。廊桥的价值就在于它的历史,它的久远。在现代技术与财力之下,再建一座、十座廊桥也是很容易的事情,但这没有历史的廊桥,又有什么意义呢?
廊桥在精神上的功效,也体现为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历史越向前发展,人类就越没有“人定胜天”的底气。自然是用来敬畏,而不是征服的,也只有这样,人与自然才能实现和谐的发展。廊桥从建筑选址、建筑形式、建筑材料与环境改造上,都体现了一种人与自然环境的高度融合。
有的廊桥直接利用天然悬崖岩壁加以修凿而成,坚固而且自然;在与村庄位置关系的选择上,多是选择在河流下游方向,既当风水桥,又避免了一旦洪水垮桥对村庄造成伤害。而且多数廊桥建于群山之间,建筑材料就地取材,木头纹理与山间树木并无二致,半掩于茂密的丛林之中,横跨于流水潺潺的溪流之上,自然贴切,充分体现了道法自然、礼让自然的原则,实现了“天人合一”的景致效果。
廊桥在精神上的功效,也体现为人与神祇的和谐统一。
大部分廊桥都结合了桥、亭、庙等建筑功用,桥上设有神龛,供奉着包括观音、关帝爷、文昌帝、赵公明、马仙、临水夫人、黄山公等诸神像,呈现出了儒、释、道的统一。
廊桥还有定期不定期的祭祀活动,人们在桥上求神拜佛、求签问卦、禳关祭神,庆祝一年的收获,祈祷神佛对来年的保佑。
廊桥在精神上的功效,还体现为人与人的和谐统一。
建桥是一项宏大的工程,但自明清以来,绝大多数廊桥的修建却是民间的事情,官府的参与多数只是资助。民间建桥要先推选出几个主事人,并从中择定一个主要负责人,叫“缘头”,由他们负责诸多事宜,在钱款不足时也由他们垫付。而村民们,则是有大钱的出大钱,有小钱的出小钱,没钱者则出力。
人们在建桥的过程中所秉持的行善积德的信念,是一种原始的慈善精神。在这种精神的引导下,人与人的关系重新构建,达到了一个新的和谐。
四
尽管现在闽浙边上各县都加强了对廊桥的保护,但在自然神力面前,有时各种保护都会显得十分苍白无力。几年前的一个夏天,我在电视上目睹了浙江泰顺两座古廊桥被洪水冲垮的画面,心中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最悲哀的是我发现童年时期十分熟悉的蛇眉桥也永远地消失在了那片山水之间,取而代之的是一座随处可见的石拱公路桥,桥边有一碑志,曰《蛇眉桥志》:
……将原厝桥拆改车桥,并将木料出售款贴给建桥凑用。兹为破旧立新之情况,特设此碑,做到不遗忘前人之丰功而树立后人之伟绩,不胜美也,是为志。戊寅年经鉴碑人某某立。
读后我又是一种深深的无力感,很多时候人的悲哀就在于把无知当成丰功伟绩,还以为不胜美也,树碑立传,何其可怜!
然而,历史的脚步谁也无法阻挡,古廊桥作为一种遗迹的存在,数量逐步减少是不可避免的事情,而我们这一代人,最应该做的事情,不仅是要从形态上保护廊桥的存在,更要进一步发扬光大廊桥身上所蕴含的人与历史、人与自然、人与神祇、人与人的和谐相处的精神。
我突然明白,童年时期在蛇眉桥下的那种空灵感,主要还是来源于廊桥本身所具有的文化与精神。
欣喜的是,现在我听到更多的是令人振奋的消息,比如两省数县共商申报世遗,寿宁被授予“木拱廊桥文化之乡”称号,西溪获得创建“寿宁廊桥文旅小镇”的资格。我期待着这些好消息的一一实现,就如我现在看到土楼的良好保护状态一样。
番 薯 米
一
今年春天在乌龙江边觅得一小块菜地,全家热烈讨论该种些什么,母亲一反平常的温和,竭力主张要种一些番薯。大家都很纳闷,这菜市场上天天可见的笨家伙,土里土气的,又便宜得很,有什么好种呢?
长孙几岁,母亲也就离开了闽东老家几年了。在这八九年的光景里,母亲告别打了一辈子交道的番薯,又像番薯一样顽强地适应了城里的生活。我们都以为她早已淡忘了番薯,却不料她只是将心中那颗干瘪的番薯埋藏进了城市坚硬的水泥地里,土壤稍一松动,她心里的番薯就又生根发芽了。
童年时代,在我的家乡,稻米不足以维持一家大小一年的口粮,番薯就责无旁贷地充当起了主粮的角色。特别是漫长的冬季,由于没有十分繁重的体力活,晚餐也总显得可有可无。每天傍晚,母亲从楼上房间的床铺底下取出一盆细小的番薯,洗尽,放入铁锅,中间再放一个小小的搪瓷罐,装着少许白米,众星捧月一般,然后生火蒸煮,直至薯香弥漫了整个屋子,一家人就着简单的青菜、咸菜,填饱肚子。白米饭自然是孩子们的专利,但是晾过半个冬天的小番薯极甜,吸引力更大,大伙都抢着挑走那些个头圆润、皮肤光滑的小番薯,一顿饱餐之后,心满意足地打着充满番薯味的饱嗝,玩儿去了。
能够成为冬天晚餐的小番薯也是不简单的,因为看似平凡的番薯,实际上隐藏着许多有趣的秘密。
番薯个头大小不同。大的产量高,但也多了些笨拙,萌芽的速度慢,而且容易腐烂;中等的萌芽容易,养分也够,自然被留着做番薯种了;只有那些小番薯,因为太小,做番薯种营养不足,但也因为小,不容易腐烂,就被挑回家里存放了。
就这样,中小番薯各就其位各得其安。而大番薯,由于个头太大,挑回家里吃力,且不易存放,就在山里被刨成番薯丝晒成番薯米,开启它颠沛流离的生命历程了。
二
当绿油油的番薯叶色泽开始暗淡,特别是开出或淡紫或乳白色的番薯花时,父亲便开始准备刨番薯米了。
他先在番薯地的附近找到水源,那多是离山地最近的一丘田里,挖出一个小水池,将山泉水引入池中,然后在向阳又通风的山冈上搭好犄角似的架子,接着从家里搬来闲置了几乎一年的番薯楻、番薯笪,带上了番薯篮和番薯刨,开始等待好天气。
刨番薯米是一个盛大的仪式,场面热闹,大人小孩都很忙碌,延续的时间也很长,有时甚至长达到一个半月以上。父亲主重體力的挑番薯洗番薯之类的活,母亲刨番薯丝、收储番薯粉,小孩子们则帮忙捡番薯、收番薯米。
母亲起得最早,天没亮就起床煮饭了,然后叫醒我们,匆忙吃完番薯饭后出发去山上刨番薯米。通常走出家门时天还是黑的,到了场地天才蒙蒙亮,他们便急匆匆地开始刨番薯米了。我们兄弟帮忙把池子里的水打进番薯楻,将他们刨出来的番薯丝倒进去,用锄头或笊篱搅动,洗去薯丝上的番薯粉,然后装入番薯篮,再用清水沥一遍,最后由父亲挑到不远处的山冈上,均匀地撒在番薯笪上,斜架在架子曝晒。
有时我们也学着大人的样子去刨番薯丝,不过速度极慢,粗细不均,留下的番薯头也太大,还要母亲返工,她会很不耐烦地呵斥我们不要添乱。更麻烦的是手指或手掌经常被刨破,皮肉像番薯丝一样,刨出了好几条,样子恐怖,痛得直流泪,而且还要再被责骂一顿。
那个时节,天气寒冷,经常打霜,孩子们冻得脸颊发紫,浑身发抖,经常无助地大哭。邻居们的场子也在附近,情形大抵相近,不时会传出父母打骂孩子的声音。稍大一点后我常想,这也许就是所谓的番薯命吧?
当阳光洒满番薯笪的时候,番薯篮里的番薯全部变成了番薯丝。父亲铺完最后一个番薯笪后,要回学校去上课了,他是村里小学的老师。母亲则带着我们上山去挖番薯,开始一天最难熬的时光。我负责用镰刀割去番薯根茎上的番薯藤,然后拖在一起,捆成一把一把的,待晚上回家时由母亲和我一起挑回家里。
镰刀过处,番薯藤泛出乳白色的汁液,黏黏的,沾得满手满衣服的,又变成了黑乎乎的颜色。傍晚回家,用草木灰搓洗,又打上肥皂,还是无法净除。多天下来,只能用刀子小心地刮,可最终还是刮不掉胶在手掌纹路里的黑色,只好等到来年春天皮肤舒润以后自然脱落了。
母亲用锄头挖番薯,弟弟按大中小把番薯分别挑入三个不同的番薯篮里,等待中午和傍晚放学后,由赶来的父亲挑回刨番薯米的场子。
太阳即将西下的时候,是一天里最愉悦的时光。挖完一天番薯的母亲虚脱般地坐在凳子上,看着父亲用锄头敲开番薯楻底部的软木塞,任洗过番薯丝变成咖啡色的水,缓缓地流到旁边的水沟里。我们好奇地围观番薯楻里的旋涡,盼望尽早看见底部的番薯粉。
终于见底了,母亲会探过头来看看番薯粉有多少,然后发一句或赞扬或牢骚的话,大抵是“还是长乐薯多粉”或“明年不要再种红皮白心”之类的。父亲并不在乎这些,麻木地塞上软木塞,提了两木桶水倒入番薯楻,来回晃动,将楻底的番薯粉倒入一个不大不小的陶缸里沉淀。待第二天早上刨完番薯丝后,母亲用番薯铲将凝结成一整块的番薯粉切成一小块一小块地取出来,削去底层的土渣子,再去掉表层残留的番薯丝,就成了一块块洁白的豆腐块式的“白粉”了。母亲把这些“豆腐块”放在簸箕上,连续曝晒,直至“豆腐块”散发成无数洁白的小颗粒,才算干透,这便是番薯粉了。那些带着土渣子、颜色稍黑的“黑粉”,母亲也舍不得丢弃,而是另外晒起来,留在家里当菜肴。
场子里的最后一道工序是洗番薯。父亲将番薯倾倒进番薯楻发出的轰响,像一阵闷雷,穿透夜色,钻进我的耳朵,仿佛是父亲的责骂声。我惊慌地提起水桶,从池子里打水倒入与我齐胸高的番薯楻里。
那年我七岁,农村人按虚岁算的。
番薯在番薯楻里顺着父亲的锄头翻滚着、碰撞着,一会儿浮在水上,一会儿又沉入水底,最终在来来回回、浮浮沉沉中脱尽表皮,伤痕累累,倒像是洁白的萝卜了。许多年以来,这个镜头一直烙在我的脑海之中,像我这种番薯命的人,奔波忙碌,漂泊沉浮,与这楻里番薯真的没有太大的区别。
父亲洗番薯的同时,母亲带着弟弟去山冈上收番薯米了。她抓起一把番薯米,放在鼻子前嗅了嗅,用手捻了捻,如果干透了,就表扬今天天气真好,如果还是半干不干的,就会牢骚这个鬼天气了,似乎她的喜怒哀乐完全控制在番薯米手里了。但是不管怎么样,番薯米都要收回去的,因为第二天番薯笪还要晾晒新刨出来的番薯米。
母亲在地上铺开一张塑料布,然后半蹲身子,头手并用,把番薯笪托过来,倒下番薯米,再拍拍番薯笪,干番薯米就像雪花一样簌簌地往下掉,煞是好看。更好看的是这个时节山冈上田园中道路旁搭满的架子上,斜排着的连绵不绝的番薯笪,犹如千帆竞发,又似万里雪飘,白茫茫的一片。这种场景比起后来声名鹊起的霞浦近海上的养殖基地,一点也不逊色。
夜色即将来临的时候,忙完所有活儿的一家人终于踏上归途。父亲挑着白天晒出的番薯米和番薯粉,母亲与我挑着刚刚收割的番薯藤,筋疲力尽地回到了家里。母亲开始煮番薯饭,父亲剁番薯藤,那是家里牲畜的饲料。
三
翻晒过后的番薯米颜色白中带暗,堆满了大半个粮仓。母亲进进出出,经常嘀咕稻谷又快吃光了,却对眼前的番薯米熟视无睹。
我曾诧异,明明是番薯做的东西,为什么一定要叫成“米”呢?无论从形状还是从味道来看,叫“番薯丝”“番薯面”甚至“番薯线”,都要形象得多了。后来知道福清人把晒干的番薯片叫成“番薯钱”,终于明白,因为番薯太卑微了,人们就想方设法地让它攀附高枝,蹭了大米和银圆的光。但无论人们的愿望多么美好,都改变不了番薯在人们心中的低贱地位。人们还是不把番薯米当作一回事,年节供奉祖先没有番薯米的份,馈赠亲友没有番薯米的位子,招待客人也不好意思拿出来,就是邻里之间茶余话后的聊天,也不太敢提自己今天吃的是番薯米。
人们对番薯的漠视还远不止于此。在闽东老家,管命不好的叫“番薯命”,嘲笑普通话讲不标准叫“番薯话”,讥讽一个长得太胖的人叫“番薯猪”或“番薯侬”。相反,有人有出息了,终于离开了山村,别人就赞扬他说再也不用吃“番薯饭”了。
我总为番薯受到的这种不公平待遇而愤愤不平,我祖祖辈辈的繁衍都是离不开番薯的,我童年时也是吃番薯过来的。一位已故的邻居长辈告诉我,我的曾祖母建造我家老屋时,一家人唯一的食物就是搁在阁楼上面的烂番薯。不仅我家,在闽东的多数地方,多少年,多少代,人们都是靠番薯滋养长大的。后来,我又发现,不仅闽东,沿海许多地方的生产生活也与番薯息息相关。一位福清的朋友告诉我,他从小也是吃番薯长大的,直到现在看到番薯还感觉胃里作呕。惠安人管番薯叫地瓜,他们自认为自己说的是“地瓜话”,把老乡会命名为“地瓜会”,简直把番薯当成了图腾。
如今,番薯米已经从老家乡亲们的饭碗里淡出,番薯也从田间地头慢慢地消失了。我不知道年轻人是否晓得这东西,但我相信,年纪稍大的人,记忆里一定还驻扎着番薯的影子。
那天我与文友去乌山凭吊,赫然看见矗立着的“先薯亭”,心里一阵激动:人们一直没有忘记最初费尽心机将番薯从吕宋引进中国的长乐人陈振龙!这位先贤“引种一根番薯藤,救活一半中国人”的丰功伟绩,仿佛充盈了整个亭子,令我久久不能释怀。
四
初冬时节,我带母亲到乌龙江边的菜地里挖回了数百斤之多的番薯,她很高兴,可吃过之后,却跟我说,这番薯没有以前家里种的甜,不过低糖倒是适合你们吃。
我有点惶惑,我种的是红心番薯,哪有不甜的道理?细想,应该是母亲觉得少了一場刨番薯米的仪式。
只是,这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责任编辑林东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