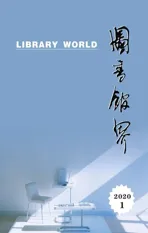文旅融合背景下公共图书馆古籍保护与开发创新策略
——以重庆图书馆为例
2020-11-18谭小华
谭小华
(重庆图书馆,重庆 400037)
当今时代,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已经成为一种重要潮流,其宗旨在于推动文旅产业的深度融合、资源互补,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精神生活的向往[1]。这对公共图书馆古籍保护工作而言,既是发展机遇,也是全新考验。只有抓住机遇,经受挑战,全面突破,才能促进公共图书馆古籍保护事业的跨越式发展。
在新时代条件下,重庆图书馆(以下简称“我馆”)采取多种策略,全力开展古籍文献层级保护,积极探索古籍开发多元策略,取得了阶段性成绩。为此,本文以重庆图书馆古籍保护举措与开发策略为中心,阐述相关经验,以为同业所借镜。
1 重庆图书馆古籍典藏概述
重庆图书馆典藏有古籍文献2.3万余种、近30万册,民国线装书1.5万种、15万册,不仅在藏量规模上处于西部领先,在文献类型和特色内容方面也颇为出彩。其中不仅包括传统的宋元旧椠、珍稀善本,还涵盖明清方志、佛教大藏经、名人稿抄本,以及独具特色的清代殿试卷、巴蜀戏曲唱本、碑帖拓片等,它们共同构建起珍贵古籍的瑰丽宝库。现将我馆的部分特色古籍简述如下。
1.1 宋元珍本
宋元刊本时代久远、存世稀少,具有极高的版本价值和文物价值。我馆藏有元代以前的刻本、写本45种,包括唐写本《大般若波罗密多经》(存一卷)等3种,宋写本《十二缘生祥瑞经》(存一卷)1种,宋刻本《通鉴纪事本末四十二卷》等9种,元刻本《六书统二十卷》等32种。《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共收录我馆珍贵古籍 3 707 种,55 632 册,内有孤本、稀见本424种[2]。近10年来,我馆共有217部珍稀善本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429部善本古籍入选《重庆市珍贵古籍名录》。
1.2 明清方志
方志为一邑之实录,属于地方性百科全书。我馆典藏有历代旧方志 1 464 种,涵盖国内29个省级行政区划,其中四川方志489种、重庆方志84种,巴蜀山水、名胜、祠庙志书及游记33种,其他各省方志858种。该批方志数量庞大、地域广泛、内容宏富,是研究巴蜀历史、地理、民俗的重要文献。尤其是我馆曾收购《刘赞廷藏稿》稿本百余册,其中多属稀见的康藏资料,史料价值极高。2014年,我馆影印出版《重庆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40册),收录馆藏稀见方志64种,其中孤本方志46种,包括《刘赞廷藏稿》中36种康藏图志稿本[3]。
1.3 科举殿试卷
殿试是中国古代科举考试的最高层级,考生所撰殿试对策即是殿试卷。民国时期著名教育家、藏书家傅增湘先生曾收藏有84份清代殿试卷[4],后来辗转交由我馆典藏,它们属于重要的科举档案,具有突出的文献价值。该批殿试卷上起清初顺治、下迄清末光绪,共历八代皇帝、二百余年,地域范围涵盖四川、浙江、江苏等全国15个省份。数量庞大、跨时长久、地域广泛,保存比较完整,是其显著特征。另外,我馆典藏有清末状元骆成骧的殿试卷刻本,朱墨套印,世间流传稀少,版本价值较高[5]。
此外,我馆还藏有佛教大藏经《永乐北藏》《永乐南藏》、巴蜀戏曲唱本、碑帖拓片、稿抄本等,数量丰富,特色鲜明,具有重要的文献史料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
2 构建古籍文献的层级保护体系
古籍文献浩如烟海,价值珍贵,但由于时代久远,历经兵燹、火灾、水患等劫难,部分古籍出现严重破损。近年来,我馆本着尊重历史、保存文献、惠泽后代的原则,采取多种有效措施加强对馆藏珍稀古籍的妥善保护。一方面,注重古籍的文物价值,通过对其整理、修复、登记、建档,完善保存条件,强化安保措施,加强原生性保护;另一方面,发挥古籍的学术价值,通过数字化扫描、拍摄缩微胶卷、开发数据库、影印出版、整理研究等方式,进行再生性保护。另外,我馆还注重古籍的艺术价值,对古籍雕版、印刷、装帧、修复等传统技艺和“非遗”进行传承和保护,旨在构建起分层次、有重点的层级保护体系[6]。
2.1 加强古籍载体的原生性保护
原生性保护是指通过预防历史文献、档案原件的损害和对破损文献的修复,确保其得到长久的保存[7]。由于各种原因,我馆典藏的部分古籍已经出现霉烂、虫蛀、絮化等破损,亟待修复。近年来,我馆通过不断改善存放环境、全面加强古籍修复、系统开展普查登记,大力做好古籍文献的原生性保护措施,以期有效延长古籍寿命,让珍贵文献能够传之久远。
(1)不断改善古籍存放环境。山城空气潮湿,阴冷多雾。我馆已经建立恒温、恒湿的标准化古籍库房,利用红外线检测、温湿度监测、二氧化碳灭火等技术手段,保障库房空气质量和消防安全。同时,为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217部珍贵古籍定制楠木书盒,为善本古籍定制无酸纸盒、樟木板,防止酸化、预防虫蛀,有效改善古籍存放环境。
(2)全面提升古籍修复实力。我馆历来注重古籍修复,七十余年几乎未曾间断,累计修复古籍8万多叶、近 3 000 册。但是相较于破损待修的古籍总量,这还仅是杯水车薪。2007年,我馆设立古籍修复中心,以传统的“师徒相授”模式大力培养古籍修复专业人才,全面提升古籍修复能力。2014年,成立“国家级古籍修复技艺传习中心重庆传习所”,以导师集中培训与日常老带新相结合的方式,着力培养青年人才。2018年,获得重庆市文物局颁发的“可移动文物修复资质证书”,可对外承接古籍、碑帖的修复项目。接下来,我馆将进一步提升修复实力,争取创建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
(3)系统开展古籍普查登记。2008年,重庆市古籍保护中心在我馆挂牌成立,肩负起全市古籍普查与保护的重任。经过近十年的按图索骥、走访普查、全面摸底,该中心终于完成对我馆及全市43家古籍收藏单位的全面摸底、普查登记,陆续出版《重庆图书馆古籍普查登记目录》等系列普查成果,收录古籍4.5万部,63.5万册,建立起准确有序的重庆市古籍总台账。这为下一步开展古籍文献的保护、开发提供了可靠依据。
2.2 注重古籍内容的再生性保护
再生性保护主要是通过对历史文献、档案原件进行载体转换,从而有效地避免原件在使用过程中受到损害。这对于古籍文献的保护开发尤为必要。因为古籍文献比较脆弱,甚至为孤本、残本,不便公开示人,只有通过载体转换,才能尽量地避免损坏原物。其主要措施有:拍摄缩微胶卷,进行物理存放;开展数字化扫描,形成古籍数据库;典籍再造,影印出版;整理特色馆藏,阐释学术价值等。
近年来,我馆以“阅读推广、数字人文”为时代契机,全力做好古籍文献的再生性保护工作。在数字化建设方面。我馆不仅将全部古籍书目数据纳入“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还积极开展数字化扫描工作,先后完成100多种珍贵古籍和地方志的缩微拍摄工作,提供读者查阅使用。同时与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合作,将32部珍贵古籍高清扫描本加入“中华古籍资源库”,真正实现文献资源与数据库的开放共享。接下来,我馆还将继续开展古籍数字化这项重要工作。
在整理出版方面。我馆一直注重对馆藏特色古籍文献的合理开发,先后整理出版《重庆图书馆馆藏珍本图录》《重庆图书馆藏稀见方志丛刊》《清代巴蜀籍考生殿试卷选粹》《重庆图书馆藏戏曲唱本普查目录及要目叙录》等学术著作,不仅揭示了馆藏古籍文献的特色和亮点,也为学术研究者提供了更为丰富、翔实的珍稀文献。其中,《清代巴蜀籍考生殿试卷选粹》以馆藏37本巴蜀殿试卷为整理对象,通过原文过录、标点和文献整理研究的方式,揭示出珍贵的巴蜀科举文献史料,填补了学术界此项研究的空白[8]。
2.3 重视传统技艺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古籍修复、碑刻传拓、古籍装帧等传统技艺与古籍保护事业密切相关,属于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和保护。近年来,我馆通过相关技艺展示和阅读推广活动,大力宣传古籍保护事业,不仅推出“古籍保护进课堂”活动,为高校师生演示雕版印刷、碑刻传拓技艺,讲授古籍修复知识;还注重对外文化交流,将中国的雕版印刷、古籍修复技艺带到俄罗斯、白俄罗斯等地,向当地民众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此外,通过现代技术复制古籍、书画,开发系列文创产品,打造特色文创商店,提升古籍文献的市场价值。同时,充分注重品牌推广,充分利用微博、微信、客户端等自媒体,有针对性地推送专题古籍文献,展现古籍图书的优美装帧和厚重内涵。通过系列措施,古籍文献不再是深藏库房、束之高阁的“秘本”,而是藏用结合、以用为主的“学术公器”,只有让珍贵的历史文献化身千百,服务读者大众,才能充分彰显其时代价值。
除了以上保护举措,我馆还加大专项财政经费投入,完善古籍库房等配套设施;大力推进人才队伍建设,培养古籍管理、修复和保护专业人才;建立古籍典藏单位动态监管与考评制度,促进古籍保护工作规范化、持续化发展。最终形成古籍普查、修复、展示、研究与利用“五位一体”的古籍保护新模式。
通过总结古籍保护的经验得失,结合古籍普查的历史成果,加强古籍典藏单位、出版机构和古籍研究者的合作,共同探索出一条可持续发展道路,努力“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3 开发策略:顶层设计与深度开发
在文旅融合、文化传承背景下,应该调整传统古籍保护“藏而不宣”的理念,从多学科、多路径创新古籍开发策略,解决“藏”“用”矛盾,实现“藏以致用”,充分发挥其时代价值。我馆的主要思路包括:第一,通过文献汇编、丛刊影印和整理出版,大力挖掘古籍文献的学术价值。第二,充分利用大数据、融媒体、数字人文等现代科技,开展古籍数字化,开发智能数据库,实现古籍资源的共建共享与深度开发。第三,通过古籍展览、讲座、数字课堂等多种方式,充分开展古籍阅读推广。第四,通过展示古籍修复、雕版印刷等“非遗”技艺,开发文创产品,充分发挥古籍文献的文物、艺术价值,实现古籍开发与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有机结合。
3.1 进一步夯实古籍普查编目工作
古籍编目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编制各种古籍联合目录。据统计,“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10年以来,全国共有20个省(市、自治区)的 2 000 多家单位完成了古籍普查。截至2018年9月21日,“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累计发布169家单位古籍普查数据 672 467 条、6 541 261 册。
由于计算机技术的迅猛发展,古籍联合目录的编制也显得更加便捷和重要。截至目前,国内最常用的重要古籍联合目录包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国古籍总目》等纸本目录,以及“学苑汲古——高校古文献数据库”(CALIS)、台湾“中文古籍书目数据库”等电子目录。
接下来,全国各地将开展“分省卷”的编纂工作。近两年,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办了两期《中华古籍总目·分省卷》编纂研修班,尤其是天津图书馆率先完成《天津卷》的编写,为推进此项工作提供了前期经验和可行方法。
3.2 注重古籍数字化的顶层设计
古籍数字化是将古籍整理与计算机技术相结合,把文献中的语言文字、图形符号转化为计算机识别的数字符号,形成具备整理、存储、传递和检索功能的电子数据库,用以揭示古籍文献的丰富内涵,实现古籍再生性保护与合理使用的双重功能[9]。中文古籍数字化的探讨始于上世纪80年代,经过30多年的实践发展,无论在学术上、技术上均已取得重大突破和显著成绩,但仍有些问题需要引起足够重视。
该项工作具有强烈的公益文化色彩,关乎国家安全和文化自信,因此需要由国家倡议、政府推动、各方参与、全面协调。国家主管部门首先应该加强顶层设计,做好整体规划,明确数字化的对象、内容、合作分工,制定相关技术标准、行业规范,才能保障整体项目的持续推进。然而,目前该领域并没有宏观规划和具体方案,有关科研单位、图书馆和数字公司都是各自为阵,根据自己的需求和资源,重复、零星、片面地开展古籍数字化工作。同时,由于行业标准的不统一,各大古籍数据库之间难以实现技术兼容,不可避免地造成了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客观上也增加了对古籍文本的损坏。因此,国家主管部门需要制定规划方案、明确行业标准,保障该项工作的合理化开展。
3.3 加强对古籍文献的学术研究和深度开发
古籍的重要属性之一就是学术资料性。公共图书馆作为古籍典藏单位,不仅要在“藏”的层面加强保护,还应该在“用”的层面与时俱进,通过对珍贵历史典籍的学术研究、深度开发,充分揭示其丰富内涵,彰显其人文精神,传承其优秀文化,提升其时代价值。我馆拟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古籍研究与开发工作:
第一,专人研究。可以对与我馆有关的重要藏书家、版本学家进行研究。比如傅增湘、李文衡、王缵绪、郑振铎、刘赞廷等人,他们不仅在古籍收藏、整理、研究领域成就卓越,而且与我馆的古籍事业很有渊源,尤其是刘赞廷、李文衡,二人均曾在我馆工作,慷慨捐赠大量珍贵古籍。通过对其人其事进行研究,既能突显藏书家的历史价值,更是缅怀先辈的君子之风。
第二,专书研究。在我馆典藏的古籍之中,有不少珍稀善本、名家藏本,更有海内孤本,价值及其珍贵,值得深入研究。比如宋元刻本,每部均流传稀少、十分罕见;又如明刻本《永乐北藏》,国内仅存三部,我馆即占其一;又如《琴苑心传全编》二十卷,清康熙九年(1670)刻本,经考证为海内孤本;又如清代殿试卷,每份均为考生手写本,举世无双。这些珍贵文献的学术性强、文物性高,是我们古籍整理研究的首选突破点。
第三,专题研究。除了专人、专书研究,还可以选定某些特色专题,进行综合分析研究:比如从藏书家的角度对郑振铎《纫秋山馆行箧书目》进行探析,从历史文献学的角度对《刘赞廷藏稿》中的“康藏史料”进行研究,从版本学的角度对武英殿刻本、内府刻本、坊刻本等不同版本类型展开研究,从文化地理学的角度对清代巴蜀进士群体进行考察等。
4 结 语
总之,古籍文献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形载体,凝聚了历代先贤的智慧精髓,诠释了华夏文明的内涵和特质,自诞生以来就具有重要的综合性历史价值。它们不仅是珍稀难得的历史文献,也是极具研究价值的学术资料,更是丰厚文化遗产的艺术代表。如何对古籍文献进行有效保护和合理开发,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话题。以上所论,仅为管窥蠡测,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