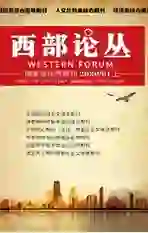周济词体论
2020-10-13黄凯琦
摘 要:周济作为常州词派的重要代表,文学思想颇丰。其中不乏丰富而系统的词体学思想,并较为集中地体现在《介存斋论词杂著》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两本词话中。其词体学思想有如下三个方面:“词亦有史”的尊体观,寄托说与词体抒情特征及通达的词体正变观。
关键词:周济;词体论;尊体;寄托说;正变观
词作为中国特有的古典抒情诗体,自从晚唐、五代发端,于两宋达到巅峰,元、明时代陷入沉寂,后又于清代中兴。在清代诸多词派中,中晚期的常州词派极为重要。不仅承接云间、浙西余韵进一步开拓了词话理论,而且为晚清词学的兴盛完成了重要的积累。张德瀛在《词征》中盛赞其为清词三变之魁首:“茗柯开山采铜,创常州一派,又得恽子居、李申耆诸人以衍其绪,此三变也。”[1](P445)在常州諸家中,周济对常州词学思想有着重要的影响。然学界在对其词学思想的探究中,却鲜有涉及词体思想。本文试对其词体观予以剖析、梳理。
一、“词亦有史”的尊体观
尊体是常州词派中颇为重要的思想之一。叶恭绰就曾在其《广箧中词》中说道:“仲修先生承常州派之绪,力尊词体,上溯风骚,词之门庭,缘是益廓,遂开近三十年之风尚,论清词者,当在不祧之列。”[2](P121)而常州词派宗主张惠言在《词选序》中提出“词者,盖出于唐之诗人,采乐府之音以制新律,因系其词,故曰词……盖诗之比兴,变风之义,骚人之歌,则近之矣。”[3](P1617)即是诗词同源的观点,并以此来尊崇词体的地位。周济经由董士锡而宗张惠言,自是认同其尊体思想。但周济较之张惠言,其自身所发展的尊体思想更为深广。周济并未沿袭前人“词为诗余”的思想,而是从历史和文学本质这两个维度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即“诗有史,词亦有史,庶乎自树一帜矣。若乃离别怀思,感士不遇,陈陈相因,唾渖互拾,便思高揖温、韦,不亦耻乎!”[4](P1630)这一思想被后世称为“词史”说,它从本质上提升了词的地位,并成为常州词派提纲挈领的理论之一。
笔者认为周济的“词史”说有两层含义。其一是指词与诗、文等文体相同,有自身发展演变的历史,故而不能将其简单地视作诗的一部分。文等文体相同,有其自身发展演变的历史,而不能将其简单地视作诗的一部分。自从晚唐五代填词发端伊始,词向来认为是小道,仅为歌舞宴席之上舞风弄月的小技。随着词创作的兴盛,词学理论也逐渐丰富,有前代词论家提出词是诗之余者。虽其旨亦在提升词的地位,却使词成为诗之补充而失去了自身的独立性。周济这一观点正是对诗余说的反驳。周济始终坚持词的独立性,词是与诗相同的抒情文体。无论是创作手法还是发展历史,词都有着独立于诗的特殊性,对于词的研究应该将其置于词的发展脉络之中整体观之。这一点在其对姜夔词作的品评中可探寻一二:“北宋词多就景叙情,故珠圆玉润,四照玲珑。至稼轩、白石,一变而为即事叙景,使深者反浅,曲者反直。吾十年来服膺白石,而以稼轩为外道,由今思之,可谓瞽人扪籥也。稼轩郁勃故情深,白石放旷故情浅。稼轩纵横故才大,白石局促故才小。”[4](P1634)这一段论述,周济虽旨在品评姜夔的词作,没有局限于具体词作的点评和对比,也没有以诗论论词,从意境、风格等方面评价。而是独独选取了北宋词到稼轩词这一历史阶段,通过其间词的发展变化,总结词作的优劣标准。而后又将姜夔词纵向地置于这一历史时期进行论词,以历史空间的深远宏观论述词人词作,充分体现了周济词亦有史的理念。其二是指词的创作与时代兴衰相结合,词同诗一般,也可以反映时代的兴衰变化。周济曾评王沂孙之词“中仙最多故国之感,故著力不多,天分高绝,所谓意能尊体也。”[4](P1635)“意能尊体”即“感慨所寄,不过盛衰,或绸缪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已溺已饥,或独清独醒,随其人之性情学问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4](P1630)正如前人评杜甫诗为“诗史”,周济认为不止诗能存史,词同样能存史。为证其观点,周济列举了四个例子。其中既有表达了对于未来有备无患的“绸缪未雨”,也有贾谊《新书·数宁》中对救亡天下的高声疾呼;既提及了对天子与民同苦、重民轻君的赞许,也说到了对个人高洁品行的讴歌和认同。从个人到国家,由眼下到未来,林林种种皆是对于时代兴衰之反映 。周济以此四方面总述词如何存史,指出了词与诗截然不同的存史路径,充分论证了以词存史的独特性。在此基础上,周济进一步论述以词存史的独到之处,即所得的“由衷之言”会受到性情、学问等因素的影响。不同的词人会因性情、学问、境地各异,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描绘出纷繁真实的社会图景,反映出多样综合的现实特点。因此优秀的词作是时代共性和词人个性的融合,是对历史的真实反映,从而使得词史“独树一帜”。
周济的“词史”说从词亦有史和以词存史两方面,充分论证了词在自身发展和表达功用上的独立性,继而从本质上尊词体。周济的词史论不仅成为了常州词派的纲领,也对后世刘熙载、谢章铤的词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寄托说与词体抒情特征
周济“词史”说的尊体观是从本质上对词体特征的论述。此外,周济还强调从创作上来突出词体特征——寄托说。这是由张惠言的比兴寄托说发展而来的。所谓比兴寄托,实是传统诗文的一种创作手法,可追溯到《诗经》的赋比兴传统,后来被发展成为诗体、文体的特征。而词作为酒宴娱乐,在发端之时并无比兴寄托之意,故多被视为小技。后代词论家为了尊词体,逐渐将比兴寄托纳入词学理论。周济的寄托说既继承了前人尊词体的思想,又没有局限于表面,而是从深处挖掘了词体的独特审美抒情属性。其寄托说可分为有无寄托说和寄托出入说。前者是对于初学者词作提出的词体特征要求,即“初学词求有寄托,有寄托则表里相宣,斐然成章。既成格调,求无寄托,无寄托,则指事类情,仁者见仁,知者见知”[4](P1630)。而寄托出入说,则是从词体特征到词境意趣的总结,即“夫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一物一事,引而伸之,触类多通。驱心若游丝之罥飞英,含毫如郢斤之斫蝇翼,以无厚入有间。”[5](P1643)综合有无寄托说和寄托出入说,可探究周济词体观在词作创作中的体现。
周济有无寄托说既指明了创作的方向,也指出了词体的特征。词作首先要通过表里相宣做到有寄托。何为“表里相宣”?即物情结合。因此词作并非无病呻吟,而是作家把自己的内心情感,通过寄托在外物上加以体现,突出了词体的抒情性。无论是写景词还是咏物词,本质都是情感的寄托。寄托情感是词不同于诗言志、文载道的独特审美属性。词体的抒情特征在周邦彦《苏幕遮》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五月渔郎相忆否?小楫轻舟,梦入芙蓉浦。”他将自己内在的思乡之情,借助鱼郎、轻舟表现得淋漓尽致。将扶摇轻舟的表象同浓烈的思乡之情融合,以一二小物寄托词人浑厚的情思。周济评周邦彦词为“美成思力,独绝千古”[4](P1632),正是出于寄托情思的词体特征。有寄托只是第一步,无寄托是更高的境界。其意并非在创作中放弃寄托,而是指创作过程中应逐渐摆脱技巧的生硬束缚,将自身的情感融入更丰富的艺术形象之中。表现在词体特征上,即是不刻意选取寄托之物表达情思,不故意卖弄技法渲染情感,而是把主观情思浑然融入于客观事物。此时的词作虽然仍有寄托之意,但所寄托情思多重而不确定,达到了含混的艺术境界。正如其所论述:“遇一事,见一物,即能沈思独往,冥然终日,出手自然不平。次则讲片段,次则讲离合,成片段而无离合,一览索然矣。”[4](P1630)周济评易安词“闺秀词惟李清照最优,究若无骨。”[4](P1636)之所以认为其闺秀词最优,正是因李清照《声声慢》中以黄花这普通一物,达到了含混无骨的抒情境界。
此后,周济提出了著名的寄托出入说,其中提及的“浑化”更是成为了常州词派对于词作的标准和要求。“夫词非寄托不入,专寄托不出。一物一事,引而伸之,触类多通。驱心若游丝之罥飞英,含毫如郢斤之斫蝇翼,以无厚入有间。既习已,意感偶生,假类毕达,阅载千百,謦欬弗违,斯入矣。赋情独深,逐境必寤,酝酿日久,冥发妄中。虽铺叙平淡,摹缋浅近,而万感横集,五中无主。读其篇者,临渊窥鱼,意为舫鲤,中有宵惊电,罔识东西。赤子随母笑啼,乡人缘剧喜怒,抑可谓能出矣。”[5](P1643)在这一段完整的论述中,周济将无寄托说,进一步发展为不仅仅是词体的抒情属性,而是词人创作手法与词体艺术特征的统一。周济承接有其无寄托说,把寄托说融入创作过程,即“一物一事,引而伸之,触类多通,驱心若游丝之飞英,含毫如郢斤之斫蝇翼,以无厚入有间。”[5](P1643)周济此处强调的是如何将主观情思与客观物象融合,即“以无厚入有间”。表明词人需要将自己的情思巧妙无痕地融入那些物象之中,通过情感与物象的融合,达到无厚入有间的境界,并进一步升华情感。周济认为这样的词作仅仅完成了寄托入的阶段,那么寄托出的阶段呢?周济表明寄托出的阶段,需要平淡朴素却蕴藉深远,感情丰富却无一明晰,呈现出含混浑化的意境,此时就达到了寄托出的艺术境界。周济关于浑化多有论述,“咏物最争托意隶事处,以意贯串,浑化无痕,碧山胜场也。”[5](P1644)“针缕之密,南宋人始露痕迹,《花间》极有浑厚气象。”[4](P1631)周济所指的“浑化”是词抒情特征的最高标准,不仅要做到有限的物像蕴含无限的情思,还要做到单一的话语寄托多重的幽思。以“浑化”为词作话语的蕴藉属性,以此体现词抒情的独特审美特征。可以看到周济既把浑化无痕视作词体抒情特征的集中体现,更把浑化作为词作抒情最高境界,要求词作全无寄托痕迹,达到主客浑融的境界。
从有无寄托说到寄托出入说,周济从词体特征出发,发掘出词体浑化无痕的抒情特征,从而将抒情作为了词体的独特属性。而实现词体抒情特征,就是要从创作上做到无寄托、寄托出。
三、通达的正变观
正变论原是诗学命题,后被词学家引入词学领域,成为词学史上的经典话题。关于词体风格何为正变的争论,早在两宋时期就有端倪,于明代正式提出,终清一朝的词派、词学家,无一不谈正变论。作为常州词派的重要人物,周济关于词体正变论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而其正变观亦是他词体思想的重要部分。
清初云间词派以婉丽为正,后浙西词派提出以清空为正,清朝的正变论可谓繁杂丰富。常州词派宗主张惠言最早提出了常州词派的正变论,即以雅正为正。张惠言所说的雅正并非是简单的词体风格,更是探源风骚。要以《诗经》风雅为正,并合乎讽谕美刺的文学传统。反之则为变,而变即是失常。面对诸多词体正变观点,周济提出了更为通达的正变观。简言之,以蕴藉深厚为正体,采众家为正体之次。这一思想在其《词辨》中有充分体现。周济依“蕴藉深厚”为词体之正,在卷一“正”中录入了温庭筠、秦观、欧阳修、周邦彦、吴文英等人;而将李煜、苏轼、辛弃疾、姜夔等人收录在卷二“变”中。虽然周济也是以蕴藉深厚为标准区分正变,但其对于“变体”的态度与张惠言的通盘否定截然相反。周济在卷二中将李煜列在首位,并称“南唐后主以下,虽骏快驰骛,豪宕感激,稍稍漓矣;然皆委曲以致其情,未有亢厉剽悍之习,抑亦正声之次也。”[4](P1637)可以看到,周济只是以蕴藉深厚作为区分正体和变体的标准,并未对变体加以过分贬低,对李煜也给予了骏驰豪宕的评价。周济称变体为“正体之次”,即为正体词的补充,可见他对变体词的肯定赞许。
但正如潘曾伟在《周氏词辨序》中所言:“其所选与张氏略有出入,要其大旨,固深恶夫昌狂雕琢之习而不反,而亟思有以厘定之,是固张氏之意也。”[6](P312)周济早年所作《词辨》仍多宗常州词派前人思想,而其后期所作的《宋四家词选》中思想更为成熟。其中言道:“余不喜清真,而晋卿推其沈著拗怒,比之少陵。抵牾者一年,晋卿益厌玉田,而余遂笃好清真。”[4](P1637)由此可知,周济思想的形成亦有一个变化过程。在其《宋四家词选》中,周济进一步突出了词体的现实性和抒情性特征,给予柳永较高的评价。“柳词总以平叙见长,或发端,或结尾,或换头,以一二语勾勒提掇,有千钧之力。”[5](P1651)此时周济在摆脱张惠言的以雅正为正的词体正变观后,逐步形成了自己以蕴藉深厚为正的词体正变观。这一正变观较之张惠言、以及之前浙西竹垞、云间卧子都更为通达,对于向来不受重视、赞许的词人也都能给予客观的评价。除了上文提到的柳永,对于豪放派词人苏轼、辛弃疾周济也都评价颇高。周济认为辛弃疾“然其才情富艳,思力果锐,南北两朝,实无其匹。”[4](P1633)对其词也评为“敛雄心, 抗高调, 变温婉, 成悲凉”[5](P1643),对于李清照等人不以为然的苏轼,周济也高度赞赏“人赏东坡粗豪,吾赏东坡韶秀。韶秀是东坡佳处,粗豪则病也。”[4](P1633)无论词家词作是否符合蕴藉深厚的标准,但凡其词有独到之处,能够存史抒情,那么周济均视为“正声之次”给予相应的评价。由此可以充分辨析周济以蕴藉深厚为正体,采众家为正体之次的词体观的通达豁然之处。
周济的词体正变观与其词史说、寄托说相辅相成,形成了完整的词体思想。周济通过词史说以尊词体的现实性,寄托说强调词体的抒情性,正是建立在词体现实抒情特征之上,才形成了周济通达的词体正变观。
参考文献
[1] 严迪昌.清词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2] 叶恭绰.广箧中词[M].傅宇斌,点校.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3] 张惠言.张惠言论词[M]唐圭璋.词话丛编:第二册[C]//北京:中华书局,1986.
[4] 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M]唐圭璋.词话丛编:第二册[C]//北京:中华书局,1986.
[5] 周济.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M]唐圭璋.词话丛编:第二册[C]//北京:中华书局,1986.
[6] 方智范,邓乔彬.中國词学批评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作者简介:黄凯琦(1993-),女,汉,辽宁本溪,硕士研究生,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