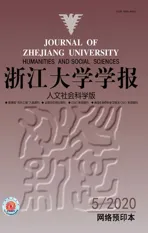中国传统家庭的子女结构与教育产出
——基于清代辽宁人口普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2020-10-12史晋川
史晋川 丁 峰
(浙江大学 经济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27)
一、 引 言
家庭是人类社会最基本和最原始的组织形式,几乎影响了人类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1]。家庭提供了维持人类生活生存所需的最基本的物质资料和精神支持,承担了粮食生产、种族延续、子代教育等职责。经济学对家庭的研究主要以核心家庭为背景,例如研究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投资决策,却忽视了对大家庭的关注。人口学和人类学领域有大量文献考察大家庭与个人的关系[2-3],一般认为,因为大家庭能将资源集中到一起并且成员之间还能在精神上相互提供支持,大家庭应该有利于个人的婚姻、生育和老年保障等[4],但这一观点并没有得到实证研究的一致支持[5]。
本文以中国传统大家庭为研究对象,利用清代辽宁人口普查数据考察未婚姐妹与兄弟教育产出之间的关系,发现未婚姐妹增加了兄弟考取功名的概率。本文应用家庭公共物品理论来解释大家庭促进个人产出的原因,将未婚姐妹视作大家庭公共物品的提供者,父母和兄弟有经济动机对未婚姐妹的无偿劳动搭便车。传统社会中,未婚姐妹只是出生家庭的暂时和边缘成员[6-7]:出嫁前,她们无偿地为家庭提供劳务服务,一方面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另一方面作为婚前的技能培训;出嫁后,她们便从法律上和经济上切断了与出生家庭的联系,不再需要承担出生家庭的任何责任,包括父母的老年保障。因此,生育女儿通常被看作纯粹的家庭经济负担,父母和兄弟都有榨取未婚姐妹无偿劳动的动机,一方面用来收回早期养育她们成人的投资,另一方面用来改善家庭的生活和提高兄弟的个人收益[8-10]。
本文的创新体现在四个方面。首先,本文深入考察了传统家庭结构并应用公共物品理论来解释大家庭对个人产出的影响。尽管家庭公共物品问题及搭便车行为是一个典型的经济学问题,但是只有少数研究应用这个理论来解释家庭成员的行为[11-12]。有别于已有的研究,本文明确将未婚姐妹视作具体的家庭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并结合历史背景和家庭结构来解释父母和兄弟的搭便车动机。其次,本文是对家庭中兄弟姐妹之间手足效应(sibling effects)研究的补充。在核心家庭的背景下,兄弟姐妹之间的手足效应已被广泛研究,然而大家庭下的相关效应尚未得到充分的讨论,本文拓展了手足效应研究的家庭背景并提供基于家庭结构的解释。再次,得益于独特的历史面板数据和计量方法,本文研究了随时间变化的家庭因素对个人教育产出的影响,因为现代人口普查数据一般以截面形式存在,其研究结果只能表明特定家庭因素对孩子未来个人产出的影响而忽略随时间变化的因素。最后,本文的研究表明,未婚姐妹对出生家庭具有无形的和被忽视的贡献,有助于我们理解传统社会中女性在家庭中的真实价值。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传统家庭的特征和维系机理,同时梳理相关文献,指出研究的意义;第三部分是计量模型与实证分析,介绍计量模型、数据,以及报告基本实证结果和讨论内生性问题;第四部分是从未婚姐妹与兄弟生育行为的关系和兄弟之间的相互作用对教育产出的影响两个方面,对计量结果做进一步讨论;最后是全文总结。
二、 传统家庭的特征与维系机理
传统大家庭是指共同生活、工作的亲属团体,为一经济单位,家庭通常只包括两代或三代的人口。普通的中国家庭,特别是农耕家庭,由于农耕土地的限制,一般只包括父母、未婚的儿女、已婚的儿子及儿媳、未婚的孙儿女。父母过世后,则同辈兄弟分居,此时家庭只包括两代人。历史上也有数百人口的大家庭,但这样庞大的家庭只是例外,只有在注重孝悌伦理并且拥有大量田地的极少数仕宦人家才有可能实现,一般情况下,在子女婚嫁前很少有家庭成员的数量超过六人的家庭[13]1-5。
传统中国是一个典型的父系社会,“男尊女卑”是其文化中最为鲜明的一个特征。女人被认为是男人的附属品,始终位于男人的意志和权力之下,无独立意志可言[6]。女人更像是一件物品而不是一个完整意义上的独立人,父亲、兄弟和她的丈夫也可以经常出卖她们以换取金钱[8][14]130。从婚姻角度考虑,当女儿出嫁后,她便从经济上和法律上彻底断开了与出生家庭的关系,从此不再需要承担对出生家庭的任何责任,甚至包括父母的老年保障[6]。因此,生育一个女儿通常被认为是一种纯粹的经济负担[8]。由于家系的传承与父母的老年保障都是由儿子来承担的,为了使儿子获得最大的利益,父母通常希望并且要求女儿加倍地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在出嫁前尽可能为家庭多做贡献。家庭有越多儿子,父母剥削女儿无偿劳动的动机就会越强烈。即使在现代社会,女性已经普遍接受教育和参加工作,但部分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父母仍然希望女儿接受完义务教育就工作,以便快速收回投资来达到资助儿子的目的[10,15]。
为了家庭的利益,或许也为了能嫁个好人家,女孩们在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接受与男孩完全不同的教育和技能培训。女孩从小受到更严格的约束,童年玩乐的时间远少于男孩。女孩需要学习作为女人的礼仪,掌握家务劳动的技能,她们还需要帮助父母料理家务,照顾弟弟妹妹以及她们兄弟的孩子(1)有关女孩童年生活的详细描述可参见林语堂《吾国与吾民》第五章,(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从经济的角度考虑,女孩的产出必须要多于她们的消费,一个未婚女儿创造的“剩余价值”被转移给她的父母和兄弟[8-9]。
传统社会的教育投资具有高投入高回报的特征,成功的教育投资能为家庭和个人带来巨大的收益[16]292。根据Wakeman的研究,清朝政府中高级官员的官方年薪就已经远远超过普通农业家庭全家一年的收入,并且还可以获得权力附带的几十倍甚至几百倍年薪的额外收入[17]26-27。同时,教育投资还可以收获丰厚的社会和政治利益,包括免除劳役、人头税、体罚等。然而,考取功名却是非常困难的。首先,科考的试题出自儒家经典,不仅需要应考者背诵和研习,还需要熟练运用八股文作答;其次,由于朝廷官职数量的限制,只有极少数的考生才能通过科举的层层筛选[18]112-116。因为要达到更高阶层非常难,所以举人和进士具有极高的社会声望。
考试的难度和竞争激烈程度决定了考生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首先,学习和考试基本是考生的全部生活。父母需要在孩子很小的时候就决定是否进行教育投资,相应的正规教育也会在很早开始[19]。一个资质上佳的学生,五岁开始习字,十一岁熟记“四书五经”,十二岁精通作诗并开始学习八股文写作。如果他能坚持不懈,便能在十五岁时首次尝试乡试。大多数情况下,初试会落榜。但经过反复尝试,他或许能在初登弱冠后的二十一岁光耀门楣,获得生员头衔。大多数人二十四岁后才能通过乡试,三十一岁成为举人,三十六岁成为进士。其次,考生需要不菲的资金用于学习和参加考试。一般情况下,一个普通的农业家庭只能支持一个男性后代去考取功名,并且通常还需要一个家族将资金集中到一起来共同承担费用,希望他能考取功名并获得一个官职,为家族带来财富与荣耀[18]209-212。
巨大而持续的成本,需要全体家庭成员共同努力来缓解家庭经济压力,并且承担相应的教育支出。对未婚姐妹来说,由于其临时和边缘的家庭身份,父母和兄弟为了家庭的利益会迫使她们为家庭做出更多的贡献,要求她们创造的价值要多于她们消费的价值。未婚姐妹对家庭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未婚姐妹能为兄弟提供情感上的支持;第二,未婚姐妹的劳动服务能减轻其他家庭成员的劳动负担;第三,未婚姐妹生产的家庭手工产品为家庭成员提供了生活必需品,减轻家庭物质上的负担,并且也可能通过产品交换使家庭获得额外的收入,缓解家庭财务压力。
研究者从父母选择行为、兄弟姐妹的手足效应等方面对影响孩子教育产出的家庭因素进行了广泛且深入的研究。首先,Becker等经济学家提出数量—质量选择模型来解释现实中观察到的家庭收入与家庭规模之间的负向关系。因为家庭预算约束的限制,父母会根据孩子人力资本的边际收益率选择相应的家庭规模,然而该理论并未得到实证研究的一致支持[20-21]。其中只有少数研究关注传统社会,Shiue通过安徽桐城族谱发现,在13至19世纪,中国人口生育也出现了类似西方社会的人口数量与质量相互替代的转换现象[22]。
其次,兄弟姐妹之间的手足效应也会影响个人的教育产出。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兄弟姐妹的性别构成[23],特别是在存在性别偏见的社会中,父母往往会牺牲女儿的利益来换取儿子的利益,即兄弟姐妹之间存在财富转移机制。其中,有关现代中国社会的几项重要研究可以印证。Parish等利用台湾的女性和家庭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在经济条件较差的家庭中,父母对姐姐的教育投资特别少并且迫使姐姐较早地进入劳动力市场,她们的收入被用来资助弟弟妹妹完成学业[10]。Lei等使用CFPS数据的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结论[15]。一般来说,在存在女性偏见的社会中,姐姐通常被当作弟弟妹妹的保姆,帮助父母管理、照料和教育他们[24],有姐姐的孩子往往有更高的存活率、健康和教育水平[25]。
然而,这些研究不能充分解释传统大家庭在提高孩子教育产出上的机制。首先,现有研究主要以核心家庭结构为基础,其中父母是家庭的主要决策者,而在大家庭中,家庭决策是父母、兄弟之间冲突、协商和妥协的结果,需要深入考察家庭结构和子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其次,已有研究一般以现代家庭为基础,就业与教育环境已经完全不同于传统社会。一方面,传统社会的未婚姐妹没有接受教育的权利;另一方面,未婚姐妹没有外出就业的可能性,她的家务劳动也不能直接为家庭创造实际的物质财富来分摊教育投资的巨大成本,未婚姐妹对兄弟教育产出的作用机制就显得非常间接,兄弟姐妹之间的财富转移机制显然无法用来解释传统大家庭未婚姐妹与兄弟教育产出之间的关系。第三,一般的实证研究都以截面数据为基础,其结果只能反映家长在孩子很小的时候的决策环境,而不能反映家长决定对孩子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后,随时间变化的家庭因素对这个孩子教育产出的持续影响。
本文深入考察家庭子女结构并结合传统大家庭的背景,利用家庭公共物品理论来解释未婚姐妹与兄弟教育产出之间的关系。家庭公共物品问题和个人的搭便车行为是一个典型的经济学问题,然而大多数研究都是基于核心家庭结构,考虑的是夫妻双方的公共物品提供及搭便车的问题[26]81-102,只有少数研究考虑到了大家庭中存在于兄弟姐妹之间的这一问题。Botticini等认为大家庭兄弟姐妹之间会产生搭便车行为并导致家庭的生产效率下降,遗产和嫁妆可以在兄弟和姐妹中产生不同的激励,从而有效地减轻搭便车产生的问题[11]。李楠等认为由于大家庭的财富是公有的且产权的界定是模糊的,兄弟会搭大家庭财富的便车来抚养自己的儿女[12]。本文明确将未婚姐妹视作具体的家庭公共物品提供者,利用独特的历史面板数据和计量方法,考察并解释父母和兄弟对未婚姐妹家务劳动的搭便车行为。
三、 计量模型与实证分析
基于上文的讨论,这部分使用经济计量模型来分析家庭子女结构对教育产出的影响。本文的计量模型采用离散时间形式的历史事件分析法[27]9-22[28],该模型仅指定特定事件在固定时间间隔内发生,而未指定事件发生的日期,离散时间模型比连续时间模型(如风险比例模型)更适合本文的数据结构[29]。具体估计模型为logistic固定效应模型:
logit Pr(EXAMijt=1)=β0+β1×SISjt+β2×AGE+Xβ+ui
其中,被解释变量EXAMijt是一个0-1变量,表示事件是否发生,即家庭j中的兄弟i在登记时期t是否考取功名。如果兄弟i在时期t考取了功名,则EXAMijt=1,否则EXAMijt=0。根据计量模型,方程估计结果是预计被解释变量等于1的概率。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SISjt,表示家庭j在时期t是否有未婚姐妹。如果兄弟i在时期t有未婚姐妹,则SISjt=1,否则SISjt=0。历史事件分析中所需要的时间变量由离散形式的年龄来表示。方程中用向量X来表示控制变量,ui表示兄弟i个体固定效应。考虑到数据本身可能存在的序列相关性,本文在报告回归结果时采用了Bootstrap校正的方差。
本文所使用的历史人口数据来自中国辽宁多代人口数据库(The China Multi-Generational Panel Dataset-Liaoning,CMGPD-LN)。CMGPD-LN由清代辽宁省八旗人口每三年一次的人口登记名册转录而成,总共记录了1749年至1909年间生活在辽宁省29个行政区域约26万人150万次的人口普查信息。CMGPD-LN的人口主要是汉族移民的后裔,他们在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从山西省、河北省和山东省迁移到辽东地区[30]120-195。满族、蒙古族和朝鲜族等非汉族人口占CMGPD-LN总人口的比例小于0.5%。尽管CMGPD-LN记录的人口特征可能无法代表整个传统社会的人口特征,但由于CMGPD-LN的人口基本上由汉人的移民及其后裔构成,保留了汉人的文化和生活习俗,至少能反映中国历史人口的部分特征[31]。
CMGPD-LN是历史研究中为数不多的面板数据,由于CMGPD-LN收集的是反映当前条件的人口信息,能确切反映家庭结构随时间而发生的变化,相比于传统的族谱数据,其选择性偏差和生存者偏见是最小的。尽管如此,CMGPD-LN也存在同其他所有历史数据一样的问题,即因为性别偏见等原因,女性的数据质量不如男性。为此,本文采取了多种处理方法:首先,根据Wang等[32]的方法筛选合适的样本,保留了女性记录数量相对完整的19个地区(Daoyitun、Gaizhou、Dami、Chengnei、Feidi、Guosantun、Bakeshu、Daixintun、Nianma、Changzhaizi、Zhaohuatun、Diaopitun、Laojiangbao、Wangzhihuitun、Wangduoluoshu、Waziyu、Wuhu、Subai、Kaidang),同时也删除女孩数量记录不完整的年份。其次,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估计,一方面,在估计方法上尽可能减少遗漏和缺失变量造成的估计偏差;另一方面,也有效地减轻模型的内生性问题。再次,女孩数量记录不足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父母在有多个女儿的情况下更倾向于少报告女儿的数量,考虑到实证分析中系数符号远比系数大小更为重要,因此,本文将核心的数字变量转译成虚拟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本文通过个人编号、父亲编号、记录年份等指标链接祖父、父亲、兄弟和姐妹的相关信息,并且删除了所有基本信息缺失的个体。因为信息登记年代久远,一些原始登记名册被损坏或丢失,或者有些人外出、逃役等,部分个体的记录不是按三年一次连续地出现在数据中,本文删除了这些信息缺失的个体。结合本文分析的问题和数据结构特征,实证研究需要控制个体固定效应,但是由于传统社会中人力资本投资的比例非常低,绝大多数个体的被解释变量始终为0,固定效应模型则会自动剔除这些被解释变量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因此,本文仅保留固定效应模型对应的有效样本作为基准样本。尽管如此,我们认为这样的处理并不会影响本文想要回答的问题,如果被解释变量不随时间变化始终为0,那么家庭内部未婚姐妹对兄弟考取功名的影响也就无从谈起。
本文中历史事件分析法的基本要素分别为:状态(states)——是否有功名;事件(event)——是否考取功名;风险时期(risk period)——考取功名前。因为考取功名事件只能发生一次,根据历史事件分析法,实证研究时期仅限于考取功名前的这段风险时期。经整理,最终得到来自167个家庭的190人的826次观察记录,表1报告了相应的统计信息。

表1 基准样本描述性统计
(一) 计量研究的基本结果
基于以上计量模型,表2报告了未婚姐妹与兄弟教育产出的回归结果。第1列仅控制兄弟的年龄(对数形式)。第2列增加控制变量:兄弟是否已经有孩子。第3列再增加三个控制变量:是否有兄弟、父亲是否在世、母亲是否在世。因为传统农业极易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粮食价格可以反映家庭经济状况的变化,粮食价格上升意味家庭经济变差,因此,第4列加入每年谷物的平均低价来控制家庭的经济波动。这四列回归结果都显示未婚姐妹的系数显著为正,未婚姐妹对兄弟的教育产出具有积极的影响。因为传统社会中女性普遍早婚,而兄弟通常在二十几岁以后才能考取初级功名,有姐姐和有妹妹可能产生不同的效应。第5列根据未婚姐妹相对兄弟的年龄大小,区分了未婚姐姐与未婚妹妹,结果发现未婚妹妹的系数显著而未婚姐姐不显著,表明未婚姐妹对兄弟教育产出的正效应主要由未婚妹妹来驱动。

表2 基准回归:未婚姐妹与兄弟人力资本的关系
(二) 内生性讨论
尽管基准回归结果表明未婚姐妹对兄弟教育产出存在正面影响,但是两者的关系仍然可能存在由反向因果和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虽然固定效应模型能控制部分内生性问题,特别是不随时间变化的遗漏变量问题,但不能充分解决这两类内生性问题。为了使本文的实证结果更有说服力,下面将对这两类内生性问题进行详细的讨论和处理。
(1)反向因果
本文是从家庭公共物品理论的角度来解释未婚姐妹和兄弟教育产出之间的关系,即父母和兄弟有经济动机对未婚姐妹提供的无偿家务劳动搭便车,并以此来改善家庭生活和提高兄弟的教育产出。然而,未婚姐妹与兄弟教育产出的关系仍然可能存在反向因果问题,为了支持兄弟的教育投资和缓解家庭经济压力,父母和兄弟可能阻碍未婚姐妹出嫁。由此可知,只需要证明未婚姐妹的婚姻状态不受兄弟是否接受教育投资或考取功名事件的影响就可以排除反向因果。更进一步讲,如果确实存在父母和兄弟为了缓解家庭经济压力而阻碍未婚姐妹出嫁的现象,那么家庭中其他依赖未婚姐妹劳动的因素也可能会影响未婚姐妹的婚姻状态,例如,需要未婚姐妹照顾、管理和教育的弟弟妹妹、侄子侄女(兄弟的孩子),考察这些家庭成员是否会对未婚姐妹婚姻状态产生影响也可以间接地判断反向因果是否存在。
我们用类似的方法整理原始CMGPD-LN数据,只是现在只保留了女性样本,并将修剪后的样本通过父亲编码与基准样本进行比对,仅保留来自基准样本家庭的女性样本。实证分析仍然是历史事件分析法,表3给出了计量结果。所有回归中都控制了未婚姐妹的年龄和父母是否在世,第1列到5列分别控制了未婚姐妹是否有弟弟、是否有未婚妹妹、是否有侄子或侄女、是否有兄弟考取了地方级功名、是否有兄弟考取了国家级功名。表3的回归结果显示,所有的这些解释变量均不显著,只有未婚姐妹自身的年龄显著为正,表明除了未婚姐妹自己的年龄,其他家庭因素都不会影响她的婚姻状态。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反向因果是不存在的,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未婚姐妹的婚姻状态是外生的。

表3 反向因果内生性检验:未婚姐妹结婚的影响因素

续表3
一般认为父母和兄弟为了自身的利益可能推迟未婚姐妹的结婚年龄,但是表3的分析结果表明,未婚姐妹的结婚年龄不受这些因素的影响。结合历史背景,本文认为这一结果是合理的。首先,传统社会中的女性无法掌控自身的命运,婚姻完全由父母支配,在极其强调伦理的传统社会,父母嫁女的意志受到道德规范的强烈约束。其次,女性出嫁会给家庭带来一笔彩礼,可以用来改善家庭经济,但是彩礼与年龄高度相关,当女性超过一定年龄后,彩礼会快速下降。因此,对父母来说,推迟未婚姐妹的婚姻并不是一个理想的选择。
(2)遗漏变量
以上的分析结果表明,未婚姐妹与兄弟教育产出之间的关系不存在反向因果关系,但是两者之间可能还存在由遗漏变量导致的内生性问题。由于固定效应模型能自动识别不随时间变化的遗漏变量,这里只需考虑随时间变化的遗漏变量,其中,家庭财富是本文最重要的时间遗漏变量。由于历史数据本身的限制,仅粮食价格可以反映家庭经济条件的波动并且已经在模型中得到控制,其估计结果表明,家庭经济条件的变动并没有对兄弟教育产出产生显著影响。除此之外,CMGPD-LN数据中没有合适的家庭财富替代变量或工具变量,为保证本文研究结果的可靠性,需要对这一问题做进一步讨论与检验。
遗漏财富变量可能通过两种方式影响解释变量:第一,遗漏财富变量可能影响未婚姐妹的出生,因为富裕家庭的生育周期可能更长,并且往往也会生育和养活更多的女儿,影响解释变量由0变为1;第二,遗漏财富变量可能影响未婚姐妹的出嫁,因为家庭财富可能影响未婚姐妹的婚姻状态,影响解释变量由1变为0(2)未婚姐妹的去世也会使解释变量由1变为0,但是所占比例比较小,故本文未做考虑。。根据家庭公共物品理论,未婚姐妹与兄弟教育产出之间的作用机制应该是由解释变量从1变为0导致的,因此,为了排除遗漏财富变量的影响,必须否定第一种影响机制并且证明未婚姐妹的婚姻状态是外生的。
首先,考虑第一种影响途径,即遗漏财富变量是否影响解释变量由0变为1的情形。根据现有人口学研究(3)相关文献如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1700—2000)》,(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等。,CMGPD-LN男性人口平均初婚年龄在20到22岁之间,并在34岁左右停止生育,当兄弟考取初级功名时,父母通常已经至少40岁,远高于停止生育的平均年龄,因此,兄弟考取功名前后一般不会有新妹妹出生,即解释变量由0变为1的情形。尽管如此,这些经验证据仍然不能完全排除解释变量由0变为1的情形,家庭财富仍然可能改变父母的生育决策,富裕家庭可以承担教育投资成本,也可能会有更长的生育周期。
为了排除第一种影响机制,从计量模型上看,只需要检验解释变量从0变为1的情形是否会对兄弟教育产出造成影响。检查后发现,基准样本共有19个指标兄弟存在新出生妹妹的情况。我们按照指标兄弟是否有新出生的妹妹将基准样本分为两组,并对解释变量由1变为0和0变为1两种情形分别进行回归估计,相应的结果报告在表4中。第3列是解释变量由0变为1的回归结果,表明解释变量由0变为1的变化对兄弟是否考取功名并没有显著的影响,即表明第一种影响机制不存在。第2列是解释变量由1变为0的回归结果,因为在这一组中不存在解释变量由0变为1的情形,结果意味着当期遗漏家庭财富变量不会影响父母当期的生育决策(或者说父母不存在生育决策),当期的解释变量由父母过去的生育决策所决定。由于过去的生育决策只受过去的家庭财富的影响,并且影响父母生育决策的过去时间超出了基准样本的数据范围,从技术层面讲,固定效应模型已经排除了遗漏过去财富变量的影响。

表4 遗漏变量的两种影响途径
其次,考虑第二种影响机制,即遗漏家庭财富是否影响解释变量由1变为0的情形。家庭财富可能影响未婚姐妹的出嫁,即解释变量由1变为0,但是反向因果的计量结果已经表明,未婚姐妹的婚姻状态只受自身年龄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说,未婚姐妹的婚姻是外生的。综上所述,遗漏财富变量对未婚姐妹的影响途径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被排除,即未婚姐妹对兄弟教育产出的影响是由解释变量外生地由1变为0的变化引起的。
四、 计量结果的进一步讨论
基准回归的结果表明,未婚姐妹对兄弟教育产出有正面影响,本文结合历史背景将未婚姐妹作为家庭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并以此来解释两者之间的关系。下面将从两方面对计量结果做进一步讨论,为本文的解释机制提供更多支持。
(一) 未婚姐妹与兄弟的生育行为
为了进一步支持家庭公共物品的解释,这部分将兄弟的教育产出替换为兄弟的生育行为。生育在传统中社会中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不仅关乎个人的老年保障,还关系到家族的延续。在经济发展缓慢并且谋生渠道匮乏的传统社会,生育数量是衡量绝大多数社会成员个人“终生成就”的最重要标准(4)过去学界一般认为传统中国属于马尔萨斯现实性的生育模式,但是近几十年基于历史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显示,传统社会存在严格的生育控制行为。与西方社会婚外控制的方式不同,中国主要是通过婚内措施来控制人口增长,相关文献可参见刘翠溶《明清时期家族人口与社会经济变迁》,(台北)“中研院”经济研究所1992年版;车群、曹树基《清中叶以降浙南乡村家族人口与家庭经济——兼论非马尔萨斯式的中国生育模式》,《中国人口科学》2011年第3期,第42-51页;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1700—2000)》,(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由于未婚姐妹为家庭提供的如抚养孩子、料理家务等无形服务能减轻兄弟的抚育负担,兄弟在未婚姐妹出嫁前应该具有更高的生育倾向。表5报告了未婚姐妹与兄弟生育行为的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的结果完全一致,即未婚姐妹同样促进了兄弟的生育产出(5)有关未婚姐妹与兄弟生育行为的问题,我们在另一篇英文工作论文“Lucky to Have a Sister! The Effects of Unmarried Sister on Brother Outcomes”中进行了更为详细的研究,有兴趣的读者可自行参阅。。

表5 未婚姐妹与兄弟生育行为
(二) 兄弟手足效应与教育产出
由于年龄和地位的不同,兄弟之间也可能产生与未婚姐妹类似或相反的效应,下面将考察兄弟之间手足效应对教育产出的影响。本文根据相对于实证回归中指标兄弟的年龄大小将男性手足划分为哥哥和弟弟两组。哥哥因为年龄上的优势,更早地进入家庭生产和家庭决策,并帮助家长料理家务、照顾和教育弟弟妹妹,尤其是那些没有未婚姐妹的家庭。这些家庭责任往往使哥哥更具有集体主义精神和利他动机去支持弟弟的教育投资。其中,长兄的身份最为特殊,长兄在家庭中的地位仅次于父亲,往往是大家庭的继承者,也有可能成为家族的族长,负责和主持家庭或家族的日常事务和祭祀仪式[33]。长兄的身份可能使他成为成功的教育投资的最大受益者之一,相应地也会给予弟弟最大的支持。相反,当弟弟出生时,一方面,哥哥可能已经正常地从事家庭生产和管理工作,对家庭资源拥有更多的实际支配权,导致弟弟在财富分配上的劣势;另一方面,弟弟没有长子身份,也没有成为接受教育投资的幸运儿,成功的教育投资带给弟弟的收益是最小的,却要一起承担巨大的教育支出。结合大家庭的集体属性,弟弟很可能因为这种事实的不平等待遇而产生强烈的自利行为,偏离大家庭教育投资的目标。特别地,当家庭中缺少兄弟姐妹时,被选中接受教育投资的哥哥很可能还要承担照顾弟弟的责任。综上所述,哥哥可能部分地扮演了同未婚姐妹一样的角色,他的身份使他成为一个家庭公共物品的提供者,给予被选中的弟弟精神上和物质上的帮助,而弟弟对哥哥却缺乏类似的动机,并且还可能产生负面影响。表6报告了哥哥和弟弟对教育产出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尽管兄弟的系数不显著,但当将兄弟划分为哥哥和弟弟后,哥哥的系数显著为正,弟弟的系数虽然为负但不显著,实证结果符合哥哥和弟弟的家庭身份。

表6 兄弟之间的手足效应与教育产出
五、 结论与讨论
本文深入家庭子女结构,结合历史背景将未婚姐妹视作家庭公共物品的提供者,实证考察了在父母主导下兄弟对未婚姐妹的家庭劳动搭便车以增加教育产出和提高收益的行为,结果表明,未婚姐妹对兄弟的教育产出具有积极的正面影响。同时,本文还发现,哥哥因为家庭责任在某种程度上也扮演着同未婚姐妹一样的角色,对弟弟的教育产出有积极的影响,而弟弟对哥哥则没有类似的效应。
与大多数相关研究一样,本文将女性当作一个完全被动的个体,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们没有追求个人利益的可能性,只是在没有独立人身权利和父母包办婚姻的传统社会,未婚姐妹最好的策略可能是不违背父母和兄弟的要求,无私地为大家庭奉献。首先,未婚姐妹可能产生一些消极的劳动态度,但是这会影响她们的声誉和未来的出嫁。其次,父母可能会给予勤劳的女儿更多的嫁妆以奖励她对家庭的贡献,一个勤奋、熟练掌握家务技能并且伴有一份可观嫁妆的女孩,通常会受到夫家更热烈的欢迎并快速地被接纳成为家庭新成员[34]32-53。最后,未婚姐妹对出生家庭的支持可以加强未婚姐妹与父母、兄弟的感情纽带,在出嫁后成为她们的一种依靠,提升未婚姐妹作为妻子以及她们的儿女在夫家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