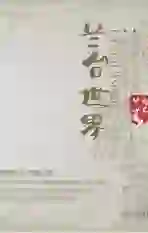清季重商思想新论
2020-08-16张翕喆
张翕喆
摘 要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的洋务运动代表着工业化开始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主题,从这一时期开始,以农为本、重农抑商的思想开始松动,转而出现的是国家机关对商业的关注和精英阶层对西方商业意识形态的学习和接受度。甲午战后随着清政府放宽对民间设厂的限制,重商思想完全取代重农思想,成为社会发展的主流思想。虽然这一时期古典政治经济学已经在西方流行开来,但重商思想在当时的中国仍具有生命力,它的形成和传播对于近代中国来说有着特殊的历史原因,同时也被赋予了特殊的历史使命。
关键词 重商主义 重商思想 郑观应 薛福成
中图分类号 F129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 2019-12-22
Abstract The Westernization Movement started after the second Opium War represented that industrialization began to become the theme of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this period on, the thought of taking agriculture as the foundation and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agriculture and restraining commerce began to decline. Instead, state organs paid attention to commerce and elites learned and accepted western commercial ideology. After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1895, with the Qing government's loosened restrictions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private factories, mercantilism completely replaced the agricultural thought and became the mainstream of social development. Although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had been popular in the West during this period, the thought of mercantilism still had vitality in China at that time. Its formation and dissemination had special historical reasons for modern China, and it was also given a special historical mission.
Keyword mercantilism; mercantilist thought; Zheng Guanying; Xue Fucheng
一、重商主義与重商思想
重商主义诞生于15世纪的西欧,盛行于16、17世纪,17世纪末随着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兴起而衰落。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他的《国富论》中指出:“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不同富裕程度,曾在政治经济学上,引出两个不同的富民主义。其一可以称为重商主义;其他可以称为重农主义。”[1]这说明重商主义是西欧封建经济在向资本主义经济过渡时期的产物,这一思想适应了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需要。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商业资产阶级进行对内对外掠夺的理论依据”[2]。德国历史与经济学家斯莫拉认为重商主义的历史意义在于“国家的建立”[3],瑞典经济学家赫克希尔提到:“重商主义是统一的动因。”[4]即重商主义在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政权建立的过程中发挥着主导因素,适应了建立近代国家的政治、经济乃至军事需要,成为早期资产阶级发展壮大的理论武器。
重商主义者所秉持的信仰为:金钱货币是衡量财富的唯一标准,而财富来源于流通和金银开采。西欧重商主义思想的发展总共经历了两个阶段,分别是“重金主义”和“重工主义”。其中15世纪到16世纪中叶为早期,由于商品经济还不是很发达,人们对货币和流通的关系认识得比较模糊,对于财富的追求仅仅简单表现为对货币始终不渝地渴望,所以“他们认为进口外国商品是非常有害的,尤其是进口本国能制造的商品更是如此”[5]。因此这一时期的重商主义者极为排斥对外贸易,认为这是造成本国财富流失的重要原因。他们主张国家直接干预商业,以行政手段来控制货币,以保持本国货币的有效积累。代表人物是英国的经济学家威廉·斯泰福得。基于这一思想,许多国家都颁布了严苛的法令来防止本国货币流失,如英国在爱德华四世统治时期就曾出现将输出金银定罪的案例。
从16世纪下半叶开始,重商主义进入“重工主义”阶段,这一时期,殖民地经济逐渐建立并走向成熟,国家同国家之间的联系逐渐增强,世界市场开始初步形成,国际贸易成了国与国之间不可或缺的交流手段,同“吝啬鬼”“守财奴”式的眼光来看待货币的早期重商主义者不同,这一时期的重商主义者开始具备了更为开放的目光,学会了用货币去套取更多货币,即强调在贸易中出口总额要大于进口总额,以贸易顺差的方式积累货币。为此他们呼吁国家采取贸易保护政策,同时还需要重视国内生产。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为英国经济学家托马斯·孟。
无论是早期还是晚期的重商主义,货币都是其关注的焦点,以获取更多货币为初衷,进而才逐渐关注因货币问题而产生的金银问题、贸易问题以及工业问题。西欧资产阶级对重商主义的信仰反映出其对于财富的渴望,重商主义因而也成为了殖民者对外扩张和掠夺的思想武器,代表了早期商业资本的意识形态。
晚清的重商思想不同于明末的重商主张,也不等同于西欧重商主义。与西方单纯追求货币财富的重商主义不同,晚清重商思想自产生之日起就带有很强的“御辱”和“救亡”色彩。
1840年以前,以出口瓷器和茶叶为主的中国频频在对外贸易中处于出超地位,这显然不符合西方经济学中“出口总额要大于进口总额”这一原则,因此从19世纪中叶开始,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开始使用军事与经济并行的手段侵略中国,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导致大量白银外流,“此皆中国之利,有往而无来者也,无怪乎今日民穷财尽,有岌岌不终日之势也矣”[6]。面对如此严重的社会问题,一部分地主阶级精英分子从传统的“重农抑商”思想中解放出来,重新看待“农”与“商”的问题,并提出了大量“重商”学说,这一时期,“商务”“商局”“商战”“商政”等新词汇的出现,反映出了他们对“救亡”与“重商”的理解。
王韬提出“商富即国富”,以“恃商为国本”的观点,标志着近代中国重商主义思想的产生。他是第一个看到商业在对外关系中带来巨大红利的人,他在《弢园文录外编》中指出:“泰西诸国以通商为国本,商之所至,兵亦至焉。”[7]他鼓励对外贸易,认为“民间贸易转输,远至数万里外,以贱征贵,以贵征赋,取利于异邦,而纳税于本国,国富民强,率由乎此”[8]。旗帜鲜明地指出:“通商之益有三,工匠之娴于艺术者得以自食其力,游手好闲之徒得有所归,商富即国富,一旦有事,可以供输糈饷,此西国所以恃商为国本欤!”[9]此外,其理论也带有一定的“重工主义”色彩,提倡用机器生产,认为“机器一行,制造益广,一切日用所需,不必取之外而自足”[10]。这也为甲午战后“实业救国”运动的发端提供了理论基础。
总的来说,王韬的思想对近代中国商业有着开天辟地的影响,他敢于打破传统文化中对“商”元素的打压,使人们开始注意到西方国家强大的本质和“商业”作为一项重要社会职能对国家政治经济产生的影响。
与王韬相比,郑观应的重商思想显得更为激进,他直接将“商业”作为武器,首先提出“商战”的口号,称“习兵不如习商战”[11]。他以英国举例,指出“英之君臣,又以商务开疆拓土,辟美洲,占印度,据缅甸,通中国,皆商人为之先导”,对于“商战”的重要性,他强调“彼不患我之练兵武,特患我之奪其利权,凡致其力于商务者,有所必争。”[12]。对于进行商战的具体方法,他认为应该“兴制造”,即“以通商为大径,以制造为本务”[13],发展本国的制造业,使之生产出来的产品能在国际市场上与外国产品进行竞争。
薛福成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性质提出关键认识的人,“工体商用”是他重商思想的核心,他在出使西欧后认识到“泰西风俗,以工商立国,大较恃工为体,恃商为用”[14]。“论西人致富之术,非工不足以开商之源,则工又为基,而商为其用。”[15]此外他还提倡重新界定“士农工商”之间的关系,即“商握四民之纲”,他认为“夫商为中国四民之殿,而西人则恃商为创造国家,开物成务之命脉,迭著神奇之效者,何也?盖有商则士可以行其所学而学益精,农可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可信其所作而作益勤,是握四民之纲者商也”[16]。自薛福成起,晚清重商主义者的目光开始从流通领域转向生产领域,给重商思想的发展带来一丝清风。
除此之外,还有具有明显“重工主义”倾向的陈炯以及具有原教旨重商理论的马建忠、黄遵宪等人,他们思想的立足点都是基于清末社会的大变革,致力于救亡图存,从打破“农本思想”入手,改变商人的社会地位,同时推广以机器大生产为表现的工业化,使国家变得富强,扭转亡国灭种的命运。
二、重商语境下的“重工”与“重利”
近代以来,西方列强频频以“通商”手段为先导,用“贸易”作为侵略和资源掠夺的重要手段,进而导致了被殖民国家“利权”的丧失。晚清重商思想家则通过“重商”来唤起国民的主权意识觉醒,在这一过程中,“重工”与“重利”成为重商思想的理论核心。
宣扬重商就不可避免地考虑到“重利”,宣传重商实际上就是对国民“逐利”行为的一种肯定,与此同时也就肯定了以自给自足为特征的自然经济的落后性,这就对新经济因素的出现提供了理论支撑。同样的,为了更好地“逐利”,就不得不“重工”。“世人皆言外洋以商务立国,此皮毛之论也。不知外洋富民强国之本实在于工”[17],所以“振兴商务为富强之计,必须讲求工艺,设厂制造,始足以保我利权”[18]。机器大生产是实现增加出口,减少进口,挽回利权的根本保证,只有发展机器大生产,才能从根本上变革以家庭手工业为主的传统生产模式,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劳动成本,对内达到利国利民,对外“分洋利”的功效。因此“论商务之源,以制造为急;而制造之法,以机器为先”[19]。
基于此种观点可以看出晚清的重商思想同传统的重商主张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前者所追求的是现代资本主义式的工商业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后者所关注的是封建经济中的农副手工业产品的流通。毫无疑问,重工思想与传统的重商主张相比更加先进和系统,它的着眼点不仅在于流通,还更多地关注制造,力图从根本上改变“抑商”“轻商”的现状。由此观之,“中国近代重商思想的实质内涵是实现工业化”[20]。只有从最根本的制造业入手,才能在变更生产方式的同时将落后的农业观一并变革。
在重商语境下“重利”与“重工”蕴含了丰富的发展内涵。“重利”是“重工”的发展目标,“重工”是“重利”的手段和保障:为了“逐利”就需要“重工”,引进机器、使用机器,才能提高生产率,降低成本,同各国商品竞争以获利。“重利”就是要发展西方式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打开市场,同各国进行贸易,“重工”则是鼓励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制造业,采用机器生产来代替传统的手工业,细化分工,提高生产力。
为保证“重利”和“重工”,需要政府抛弃以往“重农抑商”的思想,开始“重商”,肯定国民的“逐利”行为,对本国商业进行保护,“这在客观上要求国家与政府角色进行重新定位”,从而实现“上下同心,达到官——商关系的最佳契合”[21]。而当“商”元素深入后,无疑会对政府造成一定冲击,因此转变政府职能也成重商思想家关注的焦点。在重商语境下,政府不但不能抑商,而且还要致力于与“商”维持一种微妙的关系。若政府管控过严,则会侵夺商利,造成一定经济损失,市场也因此失去活力。若政府不作为,则商业行为就会不规范,造成欺诈与投机盛行。为此郑观应提出了相应对策,即:“咨取各国商律……颁行天下。……庶几上下交警,官吏不敢剥削,商伙不敢舞弊,举从前积弊一律扫除。”[22]由此使政府不至于束手束脚无所作为,又可以保护合法打击非法,在法律这个框架下加强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晚清至民国的一系列救亡图存运动也大多基于上述思想而展开,从早期致力于推广机器生产的洋务运动,到后来的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都是重商思想在实践过程中的体现。在这过程中政府逐渐放宽对商业的限制,民国建立后颁布的一系列有助于工商业发展的法律也恰恰证明了重商思想的重要性。
三、再论重商思想
清末民初的社会改良、改革、乃至革命,都是在重新探讨“农”“商”的关系和“重商思想”这一大背景下展开的。探究晚清的“重商”思想,不能把它简单地放置于当代的语境下去理解,也不能简单粗暴地把它同西方重商主义进行对比,而是应依据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的时代背景去考察。
晚清思想家所探讨的“商”是广义的商,不局限于商业,而是包括“商事”“商局”“商战”“商务”等一切带有“商”元素的事务。振兴商业在方法论上也具有多重维度,“有国者苟欲攘外,亟须自强;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欲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23]。即在“重商”的话语体系下去试图对国民经济体系进行重新建构,在这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倒逼上层建筑改革,进而影响到意识观念的改变。具体来说,对外表现在贸易上的互通有无,对内表现在发展先进生产力、改良生产关系,在思想上体现为开放性的思维,在政治上表现为简政放权、制定法律、兴商、保商。总的来说,应该是“农、矿、工、商、交通五项中,商居其一。然诸家所言重商之范围,则不限于商务一端,实并五者合而言之,是诸家之视商不啻为其他四事之纲领”[24]。也就是说商为其他四事之纲,是联结各目的总绳。
从时间上来看,西欧重商主义流行的时间为十五、十六世纪,中国重商思想发端的年代,重商早已被推行自由放任政策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所取代。但从阶段上看,欧洲重商主义产生于封建经济向资本主义经济过渡时期,对于中国来说也正是如此,这说明“重商”对于近代中国来讲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重商思想相较于重商主义,理论观点更具理性,更加全面。对于重商主义,无论是早期的重金主义还是晚期的重工主义,其理论的着眼点都只在于对财富的积累,方式简单粗暴,其思想渊源,则是在资本主义谋求政治经济地位时产生的工具性理论。晚清之重商思想是在本国封建势力打压经济,外国列强武力侵略的双重危机下产生的。在这种双重压力的打击下,中国资本原始积累不能顺利进行,中国已不具有容本国资本主义自由发展的土壤,这也说明了重商思想从诞生的那天起就必须有符合本国特点的因素,否则就是不具有生命力的空想。
在重商思想的引领下,洋务派、维新派、改良派、革命派都相继对中国社会的转型进行了伟大的探索。官督商办是这一思想的早期形态,“商战”思潮的产生,是对这一思想的系统性扩展,商部的创立和《钦定大清商律·公司律》的颁布,是这一思想的胜利性实践,中华民国的建立则将重商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潮。
在重商思想发扬壮大的同时,重商论者始终没有迷失自我,在他们看来,“重商”并不代表“轻农”,如郑观应所说“以农为经,以商为纬”[25],在重商論者看来,农业与工业是可以达到协调发展的,发展机器工业,可以提升劳动生产率,大大降低生产成本;发展农业也会连续不断地为工业提供大量的原材料和劳动力。
面对本国的传统文化,重商思想家们认为仍有改造和利用的价值。如薛福成所说:“宜传旧,勿厌旧;宜知新,勿盦新。”[26]他们虽然肯定求利的重要性,但从未忽视求利的正当性,将利和义结合起来,反对人们不择手段地求利。如陈炽所谓:“惟有利而后能知义,亦惟有义而后可以获利。”[27]
除此之外,重商论者对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一对经济学中的基本矛盾的研究也是十分可贵的。他们所认为的“政府和市场要在全新的制度安排下都受到合理的约束”[28],其中就包含了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中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这一核心问题。当然,他们也结合了当时中国远落后于西方的国情,认为政府应该采取积极的干涉,实施“保商”政策,即“任之以领事,卫之以兵轮”[29]。面对当时西方普遍实施的自由放任政策,他们积极回应,梁启超在《干涉与放任》一文中指出:“古今言治术者,不外两主义;一曰干涉,一曰放任。……然则此两种主义者,果孰是孰非邪?孰优孰劣邪?曰,皆是也,各随其地,各随其时,而异其用。用之而适于其时与其地者,则为优;反是则为劣。”[30]
总的来说,自清末以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重商思想,与西欧封建社会末期产生的重商主义有着本质上的区别。首先,后者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近两个世纪,好几代人的传承,才最终形成了完整的体系;而前者是在国门被西方列强以武力叩开后被迫产生的,时间短、观点零碎,但又包罗万象。其次,后者是在相对平和的环境下发展的,无战乱之忧,不需考虑“亡国”问题;前者则从救亡图存的观点出发,把“振兴商务”推到救国的高度加以研究。最后,在某些方面的问题上,前者的认识相较于后者更加广泛而全面。重商论者以“兴商”为契机,所思考的问题却不局限于商。这种独特的着眼点在西欧重商主义已经衰落,古典政治经济学已经成熟的时代是十分宝贵的。
参考文献
[1]亚当·斯密.国富论[M].北京:中华书局1949.
[2]张步先,苏全有.晚清重商主义与西欧重商主义[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1).
[3]参阅斯莫拉.重商制度及其历史意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
[4]赫克希尔.重商主义 英文版第二卷[M],第31页
[5]任晓玲,吴素敏.王韬的重商主义思想及其近代化影响[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3).
[6]薛福成.清末民初文献丛刊·筹洋刍议:商政篇[G].北京:朝华出版社,2017.
[7]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二[M].北京:中华书局,1959:56. [8]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四[M].北京:中华书局,1959:110.
[9]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十[M].北京:中华书局1959:299. [10]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四[M].北京:中华书局,1959:98.
[11]郑观应.盛世危言.初编,卷八,第110页. [12]郑观应.盛世危言.初编,卷八,第9页.
[13]郑观应.盛世危言.初编,卷八,第12页. [14]薛福成.庸庵海外文编.卷八,第16页
[15]薛福成.清末民初文献丛刊.筹洋刍议.商政篇[G].北京:朝华出版社,2017. [16]薛福成.庸庵海外文编.卷三,第1页.
[17]张謇.张謇全集·第一卷[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57-58.
[18]赵树贵,曾丽雅.陈炽集[M].北京:北京中华书局,1997:383.
[19]鄭观应.盛世危言·三编:卷一,第5页.
[20]赵晓雷.近代中国重商思想评析[J].学术月刊,1992(5)
[21]缐文.中国近代经济发展道路的早期探索:清季重商思想再评估[J].思想战线,2012(2)
[22]夏东元.郑观应集(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612-613.
[23]郑观应.盛世危言后编[M].台北:大通书局,1969.
[24]赵丰田.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史[M].北京:哈佛燕京学社,1939:146-147.
[25]夏东元.郑观应集(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738.
[26]薛福成.庸盦海外文编,卷3,光绪二十一年刻本.
[27]赵树贵,曾丽雅.陈炽集[M].北京:北京中华书局1997:273.
[28]缐文.发展经济学的滥觞:晚晴重商思想三题议[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
[29]夏东元.郑观应集(上)[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607.
[30]梁启超.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M].北京:中华书局,198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