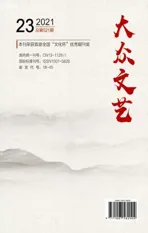刍议土家族摆手舞研究的历程与范式*
2020-07-12
(中南民族大学,湖北武汉 430076;武汉音乐学院,湖北武汉 430060)
摆手,土家语称“舍巴巴”“舍巴日”,也叫“舍巴”,意思为跳摆手,它是土家人民酬神祭祖的一种仪式。自汉晋起,这种称谓源远流长,成为土家族绵延久远的特殊风俗。土家族摆手活动按其祭祀对象与形式内容可分为“大摆手”与“小摆手”,大摆手祭祀民族远祖八部大王,小摆手祭祀溪州土司始祖彭公爵主,和传说中的民族首领向老官人、田好汉。摆手舞作为土家族传统文化的集中显现,是传承土家族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因历史上土家族仅有语言而无文字,由此对土家族摆手舞的研究成为学术界研究土家族文化、社会、艺术的重要旨趣,也成为土家族历史文化研究的重点。
一、土家族摆手舞研究的发展历程
摆手活动是土家族最重要的民俗文化活动,也是土家族精神文明的集中体现。纵观历史文献,摆手活动的相关记载多见于地方县志。自新中国成立初开展民族识别工作,不少学者和民族工作者开始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2001年,中断半个世纪地摆手活动得以恢复,有关摆手舞的保护与传承研究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的开展逐年递增,土家族摆手舞的研究取得了相当丰硕的成果。根据既有研究成果,本文将土家族摆手舞研究的发展历程概要地划分为三个阶段 :1950-1960年、1980-2004年、2005年至今。如此划分主要是基于土家族民族识别的历史原因,及摆手舞研究在理念、范式、方法方面的转型,虽难免疏漏,但也基本反映了土家族摆手舞研究在社会与学术双重因素作用下发展阶段的嬗递。
(一)1950-1960年搜集性调查阶段
20世纪50年代,党和政府为了建立新的民族治理政策,实现民族平等,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调查。那时参与湘西北民族识别工作的学者们在考察中,就土家族摆手活动中的舞蹈进行了初期的记录与研究。潘光旦先生于1955年发表了一篇长文《湘西北的“土家”与古代巴人》,探讨了湘西北土家族与巴人的族源关系,由此为摆手舞的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1958年,彭武一发表《湘西土家族摆手舞的历史来源和活动情况》,着力阐释古代“巴渝舞”与摆手舞的渊源关系,从而认为古代巴人是湘西土家族的先民。此后在党和政府的关心下,曾经历了几次对摆手舞的重要调查。1958年中南民族学院、武汉大学中文系师生在湘鄂西大采风中对摆手歌舞进行了全面搜集整理,并撰写了《土家族文学艺术史》(初稿)。1959年湘西自治州文化部门为了普查民间文艺,对摆手舞进行了专题调查,并写出了《土家族艺术调查报告》(初稿)。但遗憾的是,这些重要的第一手资料没有保存下来。此阶段的调查,由于方法单一,资料不完整,是摆手舞搜集性调查之初级阶段。
(二)1980-2004年断层与接续研究阶段
由于历史的原因,“十年”文化动荡,土家族摆手舞的研究也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此阶段的研究,从纵向时间与研究方法上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20世纪80年代初,随民族识别工作的逐渐恢复,土家族摆手舞研究再次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焦点。1986年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事务委员会出版了《鄂西少数民族史料辑录》[1];1989年岳麓书社出版了《摆手歌》[2];1993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川东酉水土家》[3],以及1997年《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湖南卷)[4]的出版。这一时期摆手舞的研究注重对资料的收集整理,对摆手舞的形态、样式、风格进行记录,为后期的理论研究奠定了基础。此阶段的研究为不可或缺的基础性工作,但在理论建树上稍有欠缺。第二,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部分学者不再满足于民族志资料的收集整理,而将关注点延伸到摆手舞的起源与历史问题,运用历史文献学、文化发生学、考古学等研究方法对摆手舞与巴渝舞、祭祀舞、普舍舞的关系展开激烈的讨论。此阶段的研究,百家争鸣,各抒己见,引起了学术界对土家族文化的极大关注。
(三)2005年至今文化深层次研究阶段
此阶段,学者们从不同学科背景、理论视角、研究范式展开对摆手舞文化的全貌研究。尤其是在土家族摆手舞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抢救性调查研究的重点,对摆手舞的研究呈递进式发展。学者们进一步深入研究摆手舞的文化内涵、价值功能,推动摆手舞研究进入文化内核之深层次的研究阶段。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柏贵喜从象征人类学的“社会结构”范式,阐释摆手祭仪是土家族社会结构,特别是三元结构及其整合的象征表达[5]。此举为后期学者的研究开辟了新的理论范式。与此同时,有学者从历史学、宗教学、艺术学、美学、教育学等不同视角对摆手舞、摆手歌、摆手堂给予了充分关注,也有一些学者面对摆手舞在社会发展中遭遇的时代危机,探讨其文化特质变迁的内在肌理,并提出了如何保护与传承的研究对策。
二、土家族摆手舞研究的主流范式
美国哲学家托马斯·库恩认为范式是“特定的科学共同体从事某一类科学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公认的‘模式’,它包括共有的世界观、基本理论、范例、方法、手段、标准等等与科学研究有关的所有东西。”[6]关于土家族摆手舞的研究发展史不仅呈线性发展过程,也存在不同研究范式之间的转换。在不同的研究范式中,将摆手舞作为研究对象,但所研究的问题、解答问题的方法,以及问题的结论都有所不同。
(一)历史研究范式
历史研究范式的科学性,体现在它的产生基础是客观的史实。有关摆手舞的历史与起源问题,从其进入学者的研究视野起,一直为学者关注的焦点。半个世纪以来,学者们采用历史学、文献学、考古学、文化发生学等历史研究方法,提出了有关摆手舞起源的战争说、劳动说、祭祀说、兴趣说、白虎说等,各抒己见,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与见解,为摆手舞的历史问题研究提供了多重视角。另一方面,学者们也试图溯其源而探其质,通过对摆手舞历史文献的梳理,阐释摆手舞作为土家族重要的文化事象(文化丛),与文化群、文化圈之间的交互作用。
(二)艺术审美研究范式
关于摆手舞的艺术审美研究,学者们首先从舞蹈生态学、舞蹈身体语言学、舞蹈美学等研究视角,关注摆手舞的身体语言、舞蹈形式、舞蹈审美,对其所具有的山地民族膝部屈颤的共性特征,与低重心移动、迈同边脚出同边胯摆同边手的顺边摆动的个性语汇,从艺术审美角度展开了多层次的考究。其次,也有学者认为摆手舞作为土家族一种特殊的精神生产,是为了满足土家人的精神需求,它本身就是土家族审美意识物质形态化的集中体现。学者们从身体美学、民族美学等角度,阐释了摆手舞的审美特质、审美表现、审美意识等,向人们展现了土家人粗犷、朴实、以俗尚丑、以圆为美的美学精神,以期从摆手舞的艺术审美探究其文化形成的内在因子。
(三)多学科交叉下研究范式的转化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摆手舞的研究已不限于历史文献学、文化发生学、考古学、艺术学等研究范畴,部分学者创新研究范式,从不同的研究视域开展对摆手舞的研究。如文化象征范式:运用象征人类学的社会结构研究范式,注重从文化“深描”的角度探讨摆手祭仪的仪式化象征表达,对土家族摆手舞作出了较有深度的理论阐释,创造了摆手舞文化研究的新高度;又如借鉴文化空间理论,对承载土家族身体记忆的摆手舞与构成整个摆手活动赖以生存的文化空间——摆手堂之间的互构关系,并说明“文化空间”是文化事象的诞生母体和生存之源,需建构并保护民族传统文化所属的文化空间;再如民族教育范式:一方面探讨摆手舞特殊的教育场域、教学关系,及摆手舞这一特殊的教育形式,对我国教育的制度化组织,学校教育都有重要的启示;另一方面从教育人类学理论,探析摆手舞所具有的教育功能,更突显了民族文化充实民族教育,民族教育发展民族文化的教育理念。
三、结语
概而言之,摆手舞是土家族文化研究的核心,自潘光旦先生以降,研究学者众多,成就斐然。同时,摆手舞的研究也存在一些深层次的缺失,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其一,长期以来,不少学者对摆手舞研究出现“模式化”与“泛化”的问题,习惯于历史文献方法的梳理,关注摆手舞的历史问题,表层研究过多,深入研究甚少;其二,就学术层面而言,虽有学者综合运用多学科的理论与方法,但缺乏深入翔实的民族志资料,就摆手舞的实证研究仍有隔靴搔痒之嫌;其三,在研究方法上,对摆手舞艺术本体的研究略显单薄,有必要将其置于社会、文化、生态整体框架内予以考察,以提升研究的宽度;其四,在摆手舞的传承保护对策上,多为宏观的、空泛的论句,缺乏系统性、科学性、针对性的具体实施方案,尤其是针对某些地域摆手舞保护的个案分析。因此,我们需要坚定文化自信,担负新的文化使命,不断创新理论研究方法、转换研究范式、加强理论储备,唯其如此,才能开创土家族摆手舞研究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