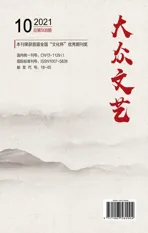契诃夫戏剧《樱桃园》中的喜剧性人物
2020-07-12郑州大学文学院450001
(郑州大学文学院 450001)
《樱桃园》写于1902--1903年,讲述了出身于俄罗斯传统贵族家庭的柳苞芙、加耶夫兄妹因为大笔债务而不得不拍卖祖传的樱桃园的故事。《樱桃园》中人物的喜剧性主要表现在贵族兄妹对悲剧矛盾的消解和次要人物的轻松喜剧因素两方面。其中主要人物柳苞芙和加耶夫兄妹是隐性的具有喜剧本质内涵的喜剧性人物,而次要人物费尔斯、雅莎等人是显性的轻松喜剧性人物。
一、具有喜剧本质内涵的喜剧性人物
柳苞芙和加耶夫兄妹出生于传统的俄罗斯贵族家庭,拥有一座祖传的樱桃园,但柳苞芙长期居于法国,而加耶夫又不善经营,很快便欠下了大笔债务,所以樱桃园面临着即将被拍卖的命运,而樱桃园的买家竟然是樱桃园农奴的儿子、曾做过柳苞芙仆人的陆伯兴。这对兄妹原本应当是悲剧性人物,因为他们失去了祖传的樱桃园,失去了象征他们贵族地位的樱桃园,他们应该是悲怆的。但是,悲剧或来自人物之间的冲突,或来自人物内心的自我冲突,而这两种冲突在兄妹二人身上都未出现。
一方面,这两兄妹身上并未出现人物之间尖锐的不可调和的冲突。《樱桃园》的人物处在典型的转型社会中,19世纪末的俄国,新兴的资产阶级开始兴起,传统的贵族阶级走向衰亡。作为传统贵族的代表,他们本可以因为樱桃园而与作为新兴资产阶级代表的陆伯兴相互对立,构成不可调和的矛盾双方,发生尖锐的矛盾冲突,从而形成悲剧。但在契诃夫笔下,二者之间虽然构成了一定程度上的冲突,但这种冲突却不够尖锐,没有到达不可调和的地步。而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柳苞芙和加耶夫本身具有喜剧性人物的特征,即人物本身对戏剧矛盾冲突或对立的消解和超越。柳苞芙和加耶夫因为樱桃园和陆伯兴构成了矛盾,但在面对这种矛盾时,他们并没有进行过多强烈的抵抗和挣扎,没有把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地步。柳苞芙、加耶夫两兄妹在面对樱桃园被拍卖的厄运时采取了消极抵抗的手段即鸵鸟式的回避,通过一系列地自我的解嘲、弱化与自我消解,解决了关于樱桃园易主的矛盾,从而避免悲剧性的消亡。就像黑格尔所说:“喜剧性一般是主体本身使自己的动作发生矛盾,自己又把这矛盾解决掉,从而感到安慰,建立了自信心”1,他们一边对不幸的到来感到伤感,另一边却通过自我解嘲克服了忧郁和伤感,与生活中的厄运和不幸达成了某种和解。所以最后樱桃园的消失并未使他们走向悲剧性的毁灭,柳苞芙伤感之后回到巴黎去照顾自己的情人,加耶夫也找到了新工作,有了新出路,对未来又充满了自信心。戏剧至此避免了因人物之间的冲突走向悲剧的可能。
另一方面,契诃夫对柳苞芙、加耶夫两兄妹的爱和嘲弄的态度使得二人成为了喜剧性人物。同样塑造身处在不幸之中的人物,契诃夫却并未像美国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在《欲望号街车》中塑造布兰奇一样着重表现人物的优雅和多愁善感,以此来博得读者的同情和怜悯,使得戏剧在布兰奇发疯的结局中走向让人伤感的悲剧。相反,契诃夫在《樱桃园》中并未对柳苞芙、加耶夫兄妹身上的弱点刻意掩饰反而着重表现,使得这两人在有些悲剧性的情境下却带有了喜剧性的色彩。因此,在剧中加耶夫沉溺于打台球、口中念着的台球术语、以及为老书柜开纪念会等等一系列滑稽的言行,柳苞芙对过去以及樱桃园的眷恋与她那不合时宜的伤感并不会引起读者的同情和怜悯,反而具有了滑稽的喜剧性。在作者对他们二人带着嘲弄的态度的弱点描绘中,让读者看清使他们失去樱桃园的那些行为,也是他们失去统治地位的原因。但他们却对此一直不自知,一直在麻醉自己,逃避现实,因此樱桃园的消失以及传统贵族阶级的衰败是不可避免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二人给读者带来的不再是需要仰视崇高感,而是让人嘲笑的滑稽感。契诃夫在《樱桃园》中让读者看清了贵族阶级必然衰败的历史规律和樱桃园终将消失的必然命运,所以读者在最后更多的并不是对樱桃园消失的扼腕叹息,而是对这两兄妹言行和生活状态的嘲笑。因此,柳苞芙和加耶夫二人在契诃夫笔下成为了让人嘲弄的喜剧性人物,而这就是《樱桃园》中契诃夫赋予他们的本质性的喜剧内涵。
虽然从表面看来柳苞芙和加耶夫不是典型的喜剧人物,但契诃夫赋予了他们两个喜剧性人物的本质内涵,这正是《樱桃园》人物喜剧性的决定因素。所以契诃夫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关于柳苞芙的舞台展示中过多的伤感最为失望和不满,契诃夫更想表现的是她身上的喜剧性本质。
二、轻松喜剧性人物
相比较柳苞芙和加耶夫内在的喜剧本质,次要人物是《樱桃园》中十分显在的喜剧性因素,属于典型的轻松喜剧性的人物。他们身上有着时间的错位、空间的错位以及其他的构成不协调的因素,通过这种不协调构成了《樱桃园》次要人物的轻松喜剧因素。
首先,第一种不协调因素是由时间上的错位构成的。最为典型的就是老仆人费尔斯。费尔斯是一位83岁的老仆人,是传统贵族社会的礼仪和制度的最忠实的维护者。从外表上看,他永远都是身穿一件陈旧的仆人制服,头戴一顶高帽;从思想上看,他感叹家庭舞会的来客身份不够高贵、不赞同农奴解放等等。他是所有人中对樱桃园最为眷恋的人,亦是对旧生活最为怀念的人,甚至可以说他是活在过去的人。他经常怀念起四五十年前的日子,在大家讨论樱桃园的未来时,他却想起旧时风干樱桃的秘法;在大家讨论起巴黎时,他想起旧时自家老爷是坐着马车去到的巴黎;听到天边响起的预示着樱桃园消失的声音,他却想起旧时农奴解放的场景。他想的都是过去的事情,而不是现在和未来,他仿佛从来没有从过去中走出,就像在戏剧结尾时他说的那样“生命就要完结了,可我好像还没有生活过”2,他身上有着时间的错位,他的思想和言行都处在旧时代,与现在和现实脱节,这种错位使他经常脱离于戏剧,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从而产生了喜剧效果,使得费尔斯成为了轻松喜剧性的人物形象。
其次,第二种不协调因素是由身份上的错位构成的。其中典型的有女仆杜尼雅莎、大学生彼嘉以及年轻仆人雅沙。女仆杜尼雅莎对自己身份的认知是错位的,明明是女仆却穿衣梳头都学小姐的样子,常常幻想自己贵族小姐,身体十分娇嫩,动不动就要晕倒了,轻浮虚荣,自认为温柔、文雅、高贵。大学生彼嘉亦是有着对自己身份的错位的认知,自认为是永远的大学生,其实是谢了顶的、永远毕不了业的大学生。他说着满口的大道理,有着堂吉诃德式的伟大理想追求,却在被柳苞芙问到恋爱时惊恐的逃开,体现出他缺乏对现实的体验,缺乏为了伟大理想而努力去改变现实的行为。年轻仆人雅沙也是如此,附庸风雅,在巴黎呆了几年,自认为自己是巴黎人,看不起祖国和生活在祖国的母亲。他觉得这里的国家不开化,百姓不文明,饭菜难吃等等,却并未意识到这里就是自己的祖国,自己归根结底是个俄国人,他甚至在最后樱桃园被拍卖后要跟随柳苞芙去巴黎时感到开心。他们对自己的身份的认知都存在的很大的错位,这种错位使得他们经常出现与自身身份不符的言行和思想,从而产生了喜剧效果,使得杜尼雅莎、彼嘉以及雅莎等人成为了轻松喜剧性的人物形象。
最后,除了这两种由错位而构成的轻松喜剧人物,还有一个典型的小丑似的轻松喜剧性的次要人物,那就是新管家叶彼霍多夫。叶彼霍多夫在一出场便充满了十足的喜剧因素,说自己每天都会遭遇一点不幸,但他已经习惯了不会抱怨,但在他说这些话的同时就是在抱怨,这种语言和行为的不协调便产生了喜剧效果。当他碰到一把椅子时,明明是不幸却十分得意,这种心态亦会让人感到可笑。从他开场的一系列语言和行为引出了他的绰号“二十二个不幸”。另一方面,叶彼霍多夫虽然读了很多很多书籍,但却怎么也找不到生活的方向,他每天都在思考生死的大问题,甚至为了自杀身上随时都带着火枪,却对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情包括爱情无能为力,这种发生在叶彼霍多夫身上的强烈的不协调同样产生了巨大的喜剧效果。这些设计使得叶彼霍多夫成了《樱桃园》中典型的轻松喜剧性的人物。
从这些次要的轻松喜剧人物的设计中,我们可以看到契诃夫在创作过程中的良苦用心。一方面,这些次要人物冲淡了由题材带来的伤感色彩,另一方面,这些次要人物从某一方面讲也是柳苞芙和加耶夫性格的体现。他们身上同样有各种不协调因素,只是隐含在其喜剧性本质之后,而契诃夫巧妙的借次要人物从侧面将其表现出来。总之,这几种由不协调构成的轻松喜剧人物是《樱桃园》中的显性的喜剧因素,是人物的喜剧性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作为契诃夫的绝笔,《樱桃园》从第一次被搬上舞台就引起了巨大的争议,尤其是其体裁问题1904年1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将《樱桃园》搬上了莫斯科艺术剧院的舞台上,并将其呈现为一出地地道道的抒情悲剧。这种阐释在获得了大部分的读者认可的同时,却引来了创作者契诃夫本人的不满,契诃夫评价其为“愚蠢的感伤主义”。契诃夫本人从创作开始到创作结束都明确将《樱桃园》定义为“四幕喜剧”。贵族兄妹对悲剧矛盾的消解和次要人物的轻松喜剧因素塑造了具有喜剧本质内涵的喜剧性人物和显性的轻松喜剧性人物的两种人物形象,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创作者本人界定的合理性。
注释:
1.黑格尔.美学(第三册下)[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315.
2.契诃夫.剧本五种[M].童道明,童宁译.北京:线装书局,2014:3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