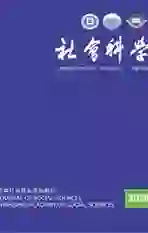《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视角下国际海事安全制度:构成内容与发展面向
2020-06-19陈敬根



摘 要:作为一类与专门的国际海事安全条约共同管控海事风险的并行条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狭义海事的层面就证书相符的适航要求、主体多元的管控责任和避碰导向的海道划设等内容明确了制度构成。而基于海洋宪章和“伞形公约”的属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确立的“二元并存”的立法准据,不仅有效协调了其与专门的国际海事安全条约的关系,而且将缔约国的国内立法基准设定为“一般接受的国际规则和标准”与“可适用的国际规则和标准”,从而实现了上位法的准据统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通过引入区域协同理念,旨在弥补船旗国、沿海国和港口国等国家管辖权配置的空白,以构建一种覆盖全部海域和所有船舶的海事管控体系。
关键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国际海事安全;分道通航制;区域性制度安排;综合安全评估
中图分类号:DF96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20)06-0101-12
作者简介:陈敬根,上海大学法学院教授 (上海 200444)
一、问题的提出
国际海事组织(IMO)制定和颁布了数量巨多、规模庞大的国际海事安全条约,海运界将其归纳为“三公约体系”,即船舶海上航行安全方面的公约体系、防治船源污染海洋方面的公约体系和海员培训、发证和值班标准方面的公约体系①;也有学者将其归纳为“四公约体系”,即在上述公约体系基础上,加上国际劳工组织制定的《国际海事劳工公约》②;还有学者将其归纳为“4+1公约体系”,即在“四公约体系”基础上,加上《极地水域船舶操作国际规则》③。被国际社会尊为“海洋宪章”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其正文共包括17个部分320条,加上9个附件,共计446条,其中涉及了诸多国际海事安全规范。
但是,专门的国际海事安全条约与UNCLOS在法律关系上,却是相互独立的,两者不是母法与子法关系,也不是互为实施性的规则,更不是“优先次序”的存在状态。同一时期的相关公约在其创制过程中明确了彼此之间的关系定位,如UNCLOS第311条“同其他公约和国际协定的关系”第2款明确规定,UNCLOS不改变各缔约国适用的其他公约而产生的权利和义务。MARPOL 73/78第9条“其他的公约及解释”第2款规定,本公约的任何内容,不得影响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对UNCLOS的编纂和制定。
那么,就国际海事安全法治而言,在研究面向上,海事界不仅要研究专门的国际海事安全条约,还要研究UNCLOS关于国际海事安全的规定。而后者目前我国的研究并没有全面系统的开展。在研究方法论上,需要梳理专门的国际海事安全条约和UNCLOS关于同一问题的不同规定,尤其是那些冲突与矛盾的规定。在研究目的上,需要就上述问题进行某种协调或安排,以求全球海事安全法治建设目标的最终实现与和谐共致。上述所涉内容,显然构成海事学界进行相关研究的逻辑起点与最终归宿,而要完成此相关研究,首先须梳理UNCLOS视角下国际海事安全制度的构成内容和发展面向,这即为本文研究所要努力实现的阶段性任务和目标。
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关于“海事”的界定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虽然没有关于“海事”一词的明确表达,但在多个条款中无疑关切和涉及了海事安全的内容调整问题,然就目前我国学界看,“海事”一词并未得到精确的界定。究其原因,一方面,“海事”一詞并非我国本土词语,而是清末修律时的西方舶来品,学界在使用该语汇时囿于观念意识并没有深入探讨其精准的内涵 “我国向守闭关主义,陆以外事,素不闻问,不仅对于海商无法,即于海事,亦何尝有律?”参见王效文《中国海商法论》,上海法学编译社1930年版,第8页。;另一方面,近些年来,随着海运业和海事法治建设的快速发展,尤其是涉海学科的系统和全面研究王赞、赵微、王芳:《海洋强国战略下法学人才培养模式优化——以海洋执法人才培养为视角》,《中国海商法研究》2019年第3期。,学界对“海事”“海商”和“海法”等概念均有不同程序的探讨,在上述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存在交叉、重叠甚至混合的现实情况下比如,在我国某海事院校将海商法学自主设置为二级法学学科的过程中,校内外的专家对“海商法学”“海事法学”的具体所指就存在不同看法。参见李天生《论海商法的概念、调整对象与属性》,《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从而使得学界对“海事”一词的精准界定,变得复杂和困难。概念的界定,既是保证话语体系同一性的根本,又是研究问题得以逻辑性展开的基础。鉴于此,本文首先需要对UNCLOS下“海事”一词的内涵与外延进行科学合理的界定和固化。
(一)UNCLOS下maritime和admiralty之所指
在UNCLOS下,“海事”一词出现在第231条、第303条等,并分别组成“海事当局”(maritime authority)、“海事法”(rules of admiralty)。因此,若精准界定UNCLOS下“海事”一词的内涵,需要对maritime和admiralty进行历时性的界定。
Maritime的前缀“Mari”,表示“有关船舶、航运和海上运输的”意思。据考证,Maritime最早源头是拉丁语Mare[美] 威廉·台特雷:《国际海商法》,张永坚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表示“海”的意思,拉丁语Maritimus、Marīnus等词均源于该词。其中,Maritimus表示“海事的、海运的”;Marīnus表示“在海中的、海运的、海事的、海商的”。随着罗马帝国的扩张,Maritimus、Marīnus被广泛使用在罗马帝国所扩张的地域上David M. Walker:《牛津法律大辞典》,李双元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733页。,其拼写方式与表达内涵也不断演化。其中,Maritimus一词形成了英语、法语以及俄语Maritime、意大利语Marittimo、西班牙语Marítimo等词,表示“航海的、海事的、海商的”等意思。
Admiralty一词最早源于阿拉伯语词根Amīr,指的是“指挥官、司令官”,其经常后缀“al”,表示“管理、控制”的意思。该词随着阿拉伯与欧洲的商贸活动而进入法国,并于9世纪形成了古法语Amiral,表示“海军将军”“舰队司令”的意思。14世纪初,该词进入了英国,形成了古英语Amiral一词,并逐渐演变为英语Admiral一词,其含义不变;后又衍生出Admiralty一词余甬帆:《试探名词“海商法”之源》,《中国海商法研究》2007年第1期。,但Admiralty除了表示“海军将军”“舰队司令”外,还因“海军将军、舰队司令”参与英国在其本土以外设置的Naval Court受理相关海事海商纠纷而被赋予了“海事法庭”“海事法”等意思罗文:《也谈“海事”与“海商”概念的区别》,《世界海运》1998年第5期。。
Naval Court直译为“海军法庭”,但其非“海军军事法院或法庭”。“海军军事法院或法庭”由Naval Martial-court来表示,指的是实施管辖海军的法律规则(naval law)的法院(庭)。Naval Court一词虽也有naval一词,但Naval Court与军事法庭无关,Naval Court实为“海事事故法庭”。英国在其本土以外设置Naval Court,旨在解决发生在公海及国外的海上事故、海上纠纷,专门审理船主或货主及船长、船员提出的紧急调查申诉等诉讼请求或船舶被遗弃、沉没、灭失等意外事故案件的法律问题金秋、魏琼:《主要海运国家海上事故调查及审判制度的比较研究》,《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由此可见,与英国本土的海军军事法庭组成人员不同,Naval Court的组成人员为停泊国外的船舶的船长、海军舰长、英国驻外领事官员。至于naval一词,大概与先前英国的船舶管理均属于准军事化规定有关。在英国本土内,则是由港口城市的地方法庭来兼任审理与船舶、航运及航运贸易有关的法律诉讼,而并未设置类似Naval Court的专门的海事法庭。
无容置疑,在Admiralty被赋予“海事法庭、海事法”等意思时,Admiralty、Maritime两词就趋于同义了。这体现在UNCLOS的英文版本中,便是Maritime、Admiralty都可指“海事”。
(二)UNCLOS下“海事”的外延
在UNCLOS下,“海事”至少包括“船舶海上航行安全”和“防治船源污染海洋”两个方面,UNCLOS第21条、第42条等对此有明确的规定。例如,UNCLOS第42条第1款规定,海峡沿岸国可就航行安全和海上交通管理以及防治海洋污染制定过境通行的法律和规定。
正如前文所述,“海事”一词的外延宽窄并没有达成共识,基于研究的对象同一性和结论可信性的逻辑前提考虑,这里需要探讨的是,UNCLOS所述的“海事”是何种意义的界定。
虽然在英文里,Maritime和Admiralty两词已基本融为一体,但在中文里,两词仍存在不同的含义,即前者被译为“海商”,后者被译为“海事”;相应地,“海商法”和“海事法”分别被译为“maritime law”和“law of admiralty”张湘兰:《海商法》,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因此,在中文语境下,界定“海事”一词,首先要将“海商”与“海事”进行类的范畴的区别。正如有学者指出,从“海商”与“海事”的中国化过程中,以及两者在中国法律体系的表达范式看,“海商”与“海事”分别具有“自己独特的内涵”关正义、李婉:《海商法和海事法的联系与区别——兼论海商法学的建立与发展》,《法学杂志》2012年第6期。。从类的范畴分析,这种区分具有“自己独特的内涵”即为私法与公法的面向区别:一是“海商”为私法面向的概念,包括涉海涉港贸易等一切商业营利行为《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版,第259页。。“海商”一词外延的界定紧紧围绕“海事私法领域之事项”,并很难撼动。这一点缘于清末修律对日本法的广为借鉴。清末修律,师法日本,立法理念自然也会深受日本法影响。日本法将“海商法”列入商法,规范的是涉海涉港私法领域的事项清水澄:《法律经济辞典》,张春涛、郭开文译,上海益群书店1914年版,第317页。。“海商法者,商法之一部,规定关于海事私法上之事项也。”陶懋颐:《商法·海商法》,东京并木活版所1906年版,第1页。民国时期,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立法实践,“海商”一词仍仅限于涉海涉港私法领域的事项。例如,1913年6月,上海科學书局出版的蒋筠专著《商法海商法表解》将海商归于商事行为;1929年12月,国民政府公布了我国首部以“海商法”命名的法律,即《海商法》,规定的也是涉海涉港私法领域的事项,诸如船舶的所有权、运送契约、海上保险等关乃凡:《<六法全书>评介》,《文献》1982年第3期。。二是“海事”为公法面向的概念,其理由是:第一,我国海事法院分设海事审判庭和海商审判庭,分别审理海事案件与海商案件,这两种案件所涉领域、审理依据等,都明显体现出各自不同的特点,从而进一步强化了“海商”谓“海事私法上之事项”而“海事”谓“海事公法上之事项”的认识。第二,从法律调整的全面性看,将“海商”界定为“海事私法上之事项”并通过法律予以调整时,必然使“海事公法上之事项”处于法律调整不足的状态。这一状态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时因我国着重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和私法领域的法律创制而尚未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和行政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海事公法上之事项”成为立法关注的焦点之一。这突出地表现为颁布实施了如《海上交通安全法》、《防止船舶污染海域管理条例》等一些行政性的海事法律、法规和条例等。对这一立法需求的回应,很显然,再不能以“海商”一言以蔽之,势必需要用另外一个词语来涵摄,“海事”一词便由此而生。这其实是一种法治诉求,是对涉海公法上之事项予以法律调整的向往。
将“海商”与“海事”进行类的范畴的区别,仅是一种方向性的指引,为使划分更精准和科学,需要对“海事”进行层的范畴的划分。依外延与所涉范围,“海事”首先为一种最狭义的解释,即指事故层面的一种划分,如海难事故、海上发生的交通事故等胡正良、韩立新:《海事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其次,“海事”为一种狭义的解释,即指“海事公法上之事项”,如海上航行安全、防治船源污染海洋,以及与其紧密相关的船舶及海上设施检查检验、航行保障活动等。最狭义的“海事”是一种最终状态的描述,对确定各类法律责任的承担具有重要价值;狭义的“海事”是一种行为过程的描述,对基于最终状态反推原因视角的海上运输各类主体的行为的失范与相关规范的完善具有重要意义。最后,“海事”为一种广义的解释,包括公法领域事项和私法领域事项,从“新文科”“新工科”等学科发展与创新角度看,广义的解释对于海法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价值。
结合“海事”一词的解读,将UNCLOS下“海事”的外延囊括为两个方面,即海上航行安全与防治船源海洋污染,是精确的。首先,基于研究的对象同一性和结论可信性的逻辑前提考虑,狭义“海事”的相关内涵与外延的界定,符合进行科学研究时应首先确保研究对象的稳定性、一致性的逻辑要求,同时也符合UNCLOS作为公约确立国家义务与责任的宗旨与诉求。其次,与当前海事界的共同目标相一致,即无论是2003年以前的国际海事组织(IMO)的宗旨“航行更安全,海洋更清洁”,抑或2003年IMO第23届大会以A.944(23)决议通过的IMO的战略计划所提出新的宗旨即“清洁海洋上的安全、保安和高效航运”,该国际组织的宗旨始终围绕着海上航行安全与防治船源海洋污染的两个方面的原点并未改变。
三、UNCLOS国际海事安全制度的内容构成
UNCLOS针对海上航行安全和防治船源污染构建了较为系统的制度框架,在一定程度上为专门海事安全条约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确立了方向与指引,也为缔约国或参加国在履行国际海事安全义务上明确了具体规范。综观UNCLOS关于国际海事安全的制度框架,具有鲜明的行业特点和特殊的内容构成,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证书相符的适航制度
适航是确保船舶海上航行安全的根本,包含“船舶适航”、“船员适任”和“船舱适货”三个内容。其中,“船舶适航”是指船舶本身的设计、结构、性能等方面能够应对船舶在航行与营运过程中所面临的风险。“船员适任”是指船舶上所配备的甲板部和轮机部等船员,无论是在配员数量上,还是在配员所获得的职务证书与通过的专业训练要求上,均能契合船舶航行与营运正常开展的需要。“船舱适货”是指船舶各类舱室或载货处所等均适宜且确保用于接受、装载、运输、保管、照料货物。这里需要指出的是,UNCLOS第94条“船旗国的义务”第3款和第4款对“船舶适航”、“船员适任”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但没有对“船舱适货”予以明确规定。
基于海运便利的考虑,以及船舶构造复杂性、技术性的现实,国际社会对适航制度是否得到遵循的判断,是将各项海事安全标准借助船舶的发证系统来实施的,并以船舶構建证书、船舶设施证书、船员证书、特种船舶证书等相关证书记载事项须与实际相符为主要依据的。例如,《1973/78年国际防止船舶造成污染公约》第5条第2款即明确规定,被正式授权的官员对船舶的检查,以核实船上是否备妥有效的证书为限。应确定船舶携带何种证书,也构成UNCLOS下证书相符的适航制度的关键,对此UNCLOS有明确的规定。例如,UNCLOS第23条、第217条第3款等均明确规定,船上应持有国际规则和标准所规定并依据该规则和标准颁发的各种证书,并确保该些证书所载内容与船舶的实际情况相吻合。
近些年来,专门的国际海事安全条约对证书相符的适航制度有了更加明确的规定和完善。例如,《马尼拉修正案》在对STCW 1978公约附则中的规则(Regulations)与STCW Code进行全面回顾与修正时主要是对相关证书的规范,即强调船舶保安员、被指定承担保安职责的海员以及所有海员,必须持有培训合格证书。同时,基于石油工业发展及油化船和液化气船规模的扩大的考虑,调整和细化了液货船船员的货物操作培训证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局:《STCW公约马尼拉修正案履约指南》,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页。。又如,《2004年国际船舶压载水和沉积物控制和管理公约》(BWM 2004)明确要求,所有船舶应持有或备有经船级社批准的压载水管理计划(BWMP)、《压载水记录簿》(BWR)和《国际压载水管理证书》。
(二)主体多元的管控制度
UNCLOS明确了国际海事安全的管控主体,确立了船旗国监督、沿海国监督和港口国监督并存的突出港口国监督的多元主体管控制度。
在1973年第三次海洋法会议之前,针对船舶的海事安全监督,船旗国一直占据着统治地位,即使是1954年国际社会为了应对二战后海上大规模石油运输所带来的海事安全风险而通过的《国际防止海上油污公约》,也只是赋予港口国的有限的检查权,并没有动摇船旗国监督的地位 《国际防止海上油污公约》第10条规定了只有船旗国才有权对海事违法船舶提起司法程序,而第9条规定港口国“可登上任何上述船舶检查遵照本公约各项规定要求船舶备有的油类记录”。。动摇船旗国监督地位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特别是托雷·卡尼翁号(Torrey Canyon)油轮事故发生后,国际社会逐渐构建船旗国监督、沿海国监督和港口国监督的并行模式。1969年通过的《国际干预公海油污事故公约》第1条赋予沿海国基于防治船源海洋污染可在公海对他国船舶采取必要措施进行干预的权力。1972年《防止倾倒废物及其他物质污染海洋的公约》第19条第3款确立了海洋倾废事项上的船旗国监督和港口国监督相结合的原则。真正动摇船旗国监督地位的是1973年《国际防止船舶污染公约》,因为该公约第4条赋予了沿海国对海事违法的他国船舶提起司法程序的权力。UNCLOS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在第十二部分“海洋环境的保护和保全”全面确立了包括海事安全在内的船旗国监督、沿海国监督和港口国监督。
船旗国(flag state)即船舶国籍国,船舶悬挂某一国家的国旗即具有该国国籍,这个国家即该船的船旗国。根据UNCLOS第92条的规定,悬挂某一国旗的船舶,受该船国旗国的属人管辖以及在公海上的受该船国旗国的专属管辖,同时根据UNCLOS第209条至第211条等相关条款的规定,船旗国承担上文所述的狭义上的“海事”安全责任,即船舶海上航行安全和防治船源污染海洋。换言之,船旗国监督仍肩负海事安全的主要责任,或者说旨在保持这一历史延续性,此判断可从UNCLOS第94条和第217条第2款的规定直观得出。
沿海国(coastal state)在UNCLOS下,就其主体构成而言,海峡沿岸国(states bordering the straits)和群岛国(archipelagic states)也可归属于沿海国的范畴,但在专门国际海事安全条约下,后两者的概念并没有提及。UNCLOS关于沿海国、海峡沿岸国和群岛国的海事安全监督在不同海区呈现不同的调整内容。
如表1所示,UNCLOS没有明确规定在毗连区内沿海国有制定相关海事安全法律和规章的权力,其原因在于根据UNCLOS第33条的规定,沿海国在毗连区仅行使海关、财政等必要管制,并不包括狭义海事安全的事项。另外,表1所述群岛国的狭义海事安全事项,针对的是群岛海道(archipelagic sea lane),而根据UNCLOS第53条第4款关于群岛海道“应穿过群岛水域和邻接的领海”的规定,群岛海道本身包括了领海,自无必要再为群岛国就群岛海道所涉领海规定海事安全事项,但群岛海道毕竟是某种“通道”(passage routes)的线的表述,对于群岛国其他领海的面的海事安全事项,则基于群岛国的沿海国身份,自可依据UNCLOS第21条和第211条的规定,就船舶航行安全和防治船源污染海洋进行管控。
港口国(port state)监督是国际社会基于船旗国监督和沿海国监督在海事安全管控中自身固有缺陷的认识而提出的新型管控模式:大部分船旗国缺少担负公海上航行的本国船舶导致的海洋污染的防治责任的动机Daniel Bodansky,“Protecting the Marine Environment from Vessel-Source Pollution:UNCLOS III and Beyond”,Ecology Law Quarterly,Vol.18,1991,p.737.,或者无法对处于流动状态的本国船舶进行有效监管,或者基于本国船队规模的保持等而不愿对本国船舶实施真正监管Ho-Sam Bang,“Port State Jurisdiction and Article 218 of the UN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Sea”,Journal of Maritime Law & Commerce,Vol.40,No.2,April 2009,p.291.;沿海国对于流动性较强的船舶运输,在客观上确实无法有效查明船舶的海事违法行为,而基于沿海国环境的高标准追求,往往会制定严格的海事标准,进而与航行自由产生较明显的冲突江家栋、蒋围等:《港口国应对船舶污染的责任:执行与保障机制》,《中国海洋法学评论》2016年第1期。。港口国监督显然能有效弥补船旗国监督和沿海国监督的自身固有缺陷,即可基于国家主权和属地管辖原则,对自愿抵港的他国船舶,就其海事违法行为,迅速地采取强制措施、开展海事调查和提起司法程序,从而不仅避免了海事违法船舶逃避法律责任,而且避免了对航行自由的妨碍。UNCLOS第218条第1款明确规定了港口国监督的内容,包括对自愿位于其港口或岸外设施的船舶,就其海事违法行为进行调查,以及在证据充分情况下提起司法程序的权力。
(三)避碰导向的海道制度
UNCLOS创新规定的用于国际通行的海峡、群岛水域等区域,使便于船舶航行的海道的权属、使用过程的各相关国的权利与义务等发生了重大变化,也使便于船舶航行的海道成为国际社会平衡各利益集团角力的关键切口,进而催生了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的海道制度、群岛水域的海道制度等曲亚囡:《中美航行自由争议解析》,《中国海商法研究》2019年第3期。。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菲律宾等亚非拉国家提出了群岛国理论,并宣称群岛基线以内的水域为内水,以摆脱西方的殖民主义。这引起了欧美海洋强权国家的不满,认为上述国家干预了海上航行自由原则M. Munavvar,Ocean States:Archipelagic Regimes in the Law of the Sea, Dordrecht:Nijhoff Publ.,1995,p.129.。就群岛水域的海道划设和他国船舶通行权的问题上,经过群岛国家和欧美海洋强权国家的多次谈判,并最终达成了两项妥协,其中一项妥协是群岛国指定海道,所有国家的船舶享有特定情形下的过境的群岛海道通过权屈广清、曲波:《海洋法(第四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84页。。用于国际通行的海峡的海道划设与他国船舶通行权的问题上也面临同样的激烈争论杨显滨:《北极航道航行自由争端及我国的应对策略》,《政法论丛》2019年第6期。,即在联合国海洋法會议确定领海宽度为12海里时,将有宽度不足24海里的百余个海峡因海峡沿岸国主张领海12海里而成为领海海峡,并主张适用无害通过制度薛桂芳、胡增祥:《海洋法理论与实践》,海洋出版社2009年版,第82页。,这与海洋大国所主张的在海峡中享有自由航行的权利产生强烈的冲突。最后的妥协结果是,发展中国家为换取海洋大国和发达国家对专属经济区的承认,作出了接受海峡过境通过制度的让步,即用于国际通行的海峡适用过境通行制,特殊情形时适用无害通行制Kheng-Lian Koh,“Straits in International Navigation:Contemporary Issues”,Oceana,(London and New York), 1982, p.18.。
UNCLOS规定了沿海国、海峡沿岸国、群岛国指定或规定的海道和分道通航制,如第22条“领海内的海道和分道通航制”规定、第41条“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内的海道和分道通航制”规定、第53条“群岛海道通过权”规定等。上述条款均规定了这些国家可指定或规定海道和分道通航制,并应在海图上清楚地标出,以及将该海图妥为公布等内容。其中,UNCLOS所规定的分道通航制,实际上是第21条第1款(a)、第42条第1款(a)等关于狭义“海事”中航行安全在通航领域的具体落实,旨在避免或减少船舶碰撞危险陈敬根:《国际海事安全条约法律问题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81-82页。。
分道通航制因在总流向上确立了在对遇等情形下船舶行进路径,从而在相当程度上避免了船舶碰撞,有力地确保了船舶行进过程中的安全,故自1967年国际社会在多佛尔海峡正式实行世界上首个分道通航制后,其便被《1972年国际海上避碰规则公约》所采纳,并在该公约生效后,成为一个强制性的国际规定。UNCLOS相关条款将海道与分道通航制一并规定,明显体现了以避碰为导向的立法理念。
四、UNCLOS国际海事安全制度的发展面向
作为海洋宪章和“伞形公约”(umbrella convention)的属性Implications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for the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LEG/MISC/4,http://www.imo.org/includes/blastDataOnly.asp/data_id%3D11121/unclosandimolegmisc4.doc.,UNCLOS关于国际海事安全的规定虽然是原则性的、方向性的,但这并不影响UNCLOS对于国际海事安全制度的发展面向所发挥的引领和指示作用。
(一)立法准据的二元并存
UNCLOS关于国际海事安全制度的内容,除了上文归纳的直接规定外,还有相当部分的内容明确要求由船旗国、沿海国等通过国内法的形式加以调整,且国内法的立法准据采“二元并存”模式,即明确为UNCLOS本身和其他国际法规则两大类,如UNCLOS第21条第1款,第211条第2款、第5款、第6款c项等。
UNCLOS关于国际海事安全立法准据的“二元并存”的规定,有利于协调沿海国、港口国和船旗国关于沿海国和港口国海事海洋权益的维护与船旗国海上航行自由原则的冲突,也有利于体现UNCLOS与专门海事安全条约在调整相同问题时作用发挥的平行地位DZIDZORNU D M,“Coastal State Obligations and Powers Respecting EEZ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Under Part XII of the UNCLOS:a Descriptive Analysis”,Colorad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al Law and Policy,Vol.8,1997,pp.285.,更有利于UNCLOS能得到“一揽子”通过。
其中,立法准据的第二类,即其他国际法规则在UNCLOS下具体表述为“一般接受”(general accepted)的国际规则(international regulations)、国际规章(international rules)、标准(standards)、程序(procedures)和惯例(practices)等,统称为“一般接受的国际规则和标准”(Generally Accepted International Rules And Standards,GAIRS),但UNCLOS并没有明确界定内涵模糊的“一般接受”的概念,也没有明确界定外延宽泛的国际规则、国际规章、标准、程序和惯例等的概念。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UNCLOS下,“一般接受的国际规则和标准”(Generally Accepted International Rules And Standards,GAIRS)与“可适用的国际规则和标准”(Applicable International Rules And Standards,AIRS),在准据的构成上虽然具有一致性,但两者适用领域不同。GAIRS适用立法管辖权(prescriptive jurisdiction),如第21条第2款、第41条第3款、第53条第8款、第211条第2款和第5款、第217條等。AIRS适用执法管辖权(enforcement jurisdiction),如第213条、第214条、第216条第1款、第217条第1款、第218条第1款、第219条、220第1款至第3款、第222条等。而且,对于船旗国和沿海国的立法管辖权来说,GAIRS的适用要求完全不同,即对船旗国来说,其构成强制性最低限度,而对沿海国来说,则构成最大限度的容忍袁雪、童凯:《<极地水域船舶作业国际规则>的法律属性析论》,《极地研究》2019年第3期。。
(二)监督机制的区域协同
考查UNCLOS相关条款可知,尽管UNCLOS意图通过国家管辖权的配置构建一种全覆盖的海事管控体系,但仍有部分海域的部分海事风险管控事项并未纳入UNCLOS的覆盖体系内。如果各缔约国均能全面履行相关国际条约的规定,且保证执法能力、执法效果的一致,那么,尚未纳入覆盖体系内的部分海域的部分海事风险管控事项便属于冲突的生成原因,由此也成为协调冲突的关健所在。
UNCLOS从缔约国角度设置了海事安全管控责任,其形式分别为FSC、CSC和PSC,并设定在国家管辖海域的管辖优先性排序为PSC>CSC>FSC,以及设定在非国家管辖海域的FSC专属管辖(UNCLOS第92条)。这种安排协调了国家管辖权冲突,避免了公海的管辖缺位,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国际海事安全Yann-Huei Song,“VII Security in the Strait of Malacca and the Regional Maritime Security Initiative:Responses to the US Proposal”,Intl L.Stud,Vol.83,2007.。但是,根据UNCLOS的相关规定,上述管控形式并未完全覆盖全部海域,或者基于本身的管辖特征而不可能覆盖全部事项(如表2所示)。
首先,在公海区域,UNCLOS只设置了船旗国管辖,且主要实施船源污染管辖事项。在一国港口或岸外设施区域,UNCLOS第210条第1款设置了港口国管辖优先原则,但只限于船源海洋污染管控。换言之,在公海和港口或岸外设施区域内,UNCLOS确立的管控事项没有包括船舶航行安全事项Mark J.Yost,“International Maritime Law & the U.S.Admiralty Lawyer:A Current Assessment”,U.S.F.Mar.L.J,Vol.7,No.1,1995.。其次,对于途经一国的领海、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专属经济区的他国船舶,该沿海国对他国船舶的航行安全和船源污染具有管辖权,但根据UNCLOS第33条的规定,管辖权适用海域并不包括毗连区。
上述不足的情形是从理性角度予以考量,即各缔约国均能全面履行相关国际条约的规定,且保证执法能力、执法效果的一致,然而在具体海事执法实践中,这种理性往往很难实现,由此必然导致一些明显的不足,其表现既有某些国家本身的法律治理能力与水平等主观层面的问题,又有各类国家管辖权本身存在的监管空白、衔接不畅、标准不一等客观层面的问题Tammy M.Sittnick,“State Responsibility and Maritime Terrorism in the Strait of Malacca:Persuading Indonesia and Malaysia to Take Additional Steps to Secure the Strait”,Pac.Rim L.Poly J,Vol.14,No.6,2005.,例如,PSC可能因不同国家的检查力度在客观上的不一致而无法达致UNCLOS的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对船舶的统一海事管控的目的。
综上,仅凭一国之力,在客观上确实难以高效地应对国际海事安全风险,因此,UNCLOS提出监督机制的区域协同理念,如第98条“救助的义务”第2款规定了区域性安排,第197条“在全球性或区域性的基础上的合作”,第199条“对污染的应急计划”,第200条“研究、研究方面及情报和资料的交换”,以及第210条“倾倒造成的污染”等。目前,一些海域沿岸国已经构建了区域性海事安排,建立了数个港口国监督谅解备忘录(MoU)组织刘锟、姜旭阳:《论谅解备忘录的法律效力》,《商务与法律》2002年第2期。。自1982年欧洲14国在巴黎签署了首个区域性海事安排,即“巴黎备忘录组织”(Paris MoU)后,国际社会共建立了地中海区域港口国监控备忘录(1997年)等9个区域性海事安全齐壮、王凤武、刘强,等:《港口国监督中船舶滞留原因》,《航海技术》2014年第6期。。MoU虽不像契约具有完全的约束力,但比传统的“君子协定”更具有效性和正式性。当然,MoU作为对某项事务的相同或高度的兴趣或目的性的联结形式,其对参与或参加的任何一方来说,并不具有法律性质上的义务Ozcayr,Z.Oya,“The Use of Port State Control in Maritime Industry and Application of the Paris MOU”,Ocean and Coastal Law Journal,Vol.14,No.2,2009.。多个港口国监督备忘录协议明确了其本身的非强制约束性,如东京备忘录序文即言明本备忘录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更无意对各成员方当局施加任何法律义务或责任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on Port State Control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Preamble.。当然,区域性海事安排本身所存在的非强制约束性,在客观上决定了其有效实施和预期目标的达成,过多地依赖于备忘录组织成员方的自我约束,故此,如何赋予区域性海事安排的强制执行效力,有待于国际社会开展进一步研究。
(三)风险管理的工具创新
选择何种理念或模型,才能使船舶建造、船舶驾驶、船舶管理的技术标准体现出显著的先进性和广泛的接受性,进而使国际海事安全得到最大程度的保证,成为20世纪中叶国际社会积极解决的一个前置性问题。这一努力在UNCLOS第十一部分“区域”中得到体现,即将“风险管理”纳入其中,并就风险安全评估工具的采用提出一种方向性的指引,如第165条第2款要求法律和技术委员会就“区域”内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准备评价(assesments)李志文、吕琪:《国际海底区域技术转让规则的理想和现實之协调》,《政法论丛》2018年第2期。。“风险管理”和评价的要求,还体现在UNCLOS第206条、第249条、第268条等条款。
所谓的“风险管理”,是指在一个肯定有风险的环境里,对风险进行努力精准的识别、测算和评价,在此基础上选择相关风险管理技术,并加以符合性的优化与组合,实现以最小的成本有效控制和最大程度降低或避免风险所致损失的管理方法和管理过程Neil A.Doherty,“Risk Management,Risk Capital,and the Cost of Capital”,Journal of Applied Corporate Finance,Vol.17,No.3,2005,pp.119-123.。缘起于美国应对1929-1933年世界性经济危机并于20世纪50年代发展成为一门学科的风险管理,在20世纪70年代被法国和日本引进和传播后风靡全球,适用范围也由国内经济领域扩展到国际关系领域。同时,随着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和风险评估精准算法不断出现,基于分析计算、确保风险指数理论型的技术标准体系得以完善和创新,并在绝大部分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的行业广泛实施,如飞机寿命设计、建筑业的可靠性设计等邢丹:《GBS:标准理念的“核裂变”》,《中国船检》2012年第3期。。风险管理的快速发展及显著实践成就,对传统的基于经验型的船舶建造规范提出了挑战,并迅速成为国际社会借此来约束船级社逐利行为、打破船级社垄断船舶建造规范市场、实现船舶建造规范从经验公式向技术标准转变的一个有效切口和法理证成。但是,当时已经建立并广泛实践的诸如运筹学方法、模糊理论、灰色理论、神经网络方法等风险管理均存在通用性和兼容性较差且无法有效匹配海事安全领域等问题,故海事安全领域一直缺乏科学、适切、有效的安全评价工具,而随着海难事故的频繁发生,构建海事安全领域的风险管理成为一种强烈的时代诉求。
UNCLOS通过后,相关国家和国际组织加快推进海事领域风险评估的科学方法(scientific methods)的研究与完善。
1988年7月,北海英国海域发生了“派珀·阿尔法”(Piper Alpha)海上平台连环大爆炸的海难事故,短短一个半小时内,就造成了近170人死亡,控制火势耗时近三个星期全永波:《全球海洋生态环境多层级治理:现实困境与未来走向》,《政法论丛》2019年第3期。。在该海难事故调查过程中,英国大量采用了工业风险分析和风险评价方法秦庭荣、陈伟炯、郝育国,等:《综合安全评价(FSA)方法》,《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05年第4期。,并随后通过法规,明确了所有近岸工程须采用经英国健康与安全管理局(the UK Health and Safety Executive)批准的“安全案例”(Safety Cases)方法,用于预防和应对类似事故的再次发生Rolf Skjong,“Formal Safety Assessment and Goal Based Regulations at IMO-lessons Learned”,Asm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Offshore Mechanics and Arctic Engineering,Halkidiki(Greeceh),2005,p.319-328.。由于“安全案例”方法不仅包括了管控措施、应急预案等内容,而且包括风险识别、风险评估等内容,故其是一种风险控制方法。但是,“安全案例”方法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即该方法的适用对象具有较强的特定性,缺少明显的普遍性,致使不同种类的海上平台须编制各自对应的“安全案例”,故在其基础上创建一种科学的普遍适用于海事安全领域的风险控制方法,就成为国际社会所面临的一项迫切任务佚名:《综合安全评估(FSA)的提出》,《世界海运》2010年第5期。。
在1993年IMO海上安全委员会(MSC)第62届会议上,英国借鉴高危行业的风险管理经验,结合安全评价方法的研究成果,率先提出在海事安全领域引用“综合安全评估”(formal safety assessment,FSA),使其成为IMO的一种战略思想,并逐步应用于国际海事安全公约的制定以及船舶设计、建造和运营管理等领域的议案。所谓的“综合安全评估”(formal safety assessment,FSA),是一种结构化和系统化的方法,旨在通过使用风险分析和成本效益评估,提升包括保护人命、健康、海上环境和财产在内的海事安全参见Revised Guidelines for Formal Safety Assessment(FSA)for Use in the IMO Rule-Making Process,MSC-MEPC.2/Circ.12,London,2013,p.1. 。如前所述,基于國际社会对海事安全领域风险管理的强烈的时代诉求,英国关于FSA的议案一经提出,便被国际社会所立即接受。1997年和2001年分别通过的《FSA应用临时指南》和《FSA指南》,标志着借鉴工业风险管理并结合海运特征的国际海事安全评价工具FSA正式建立并实施。
2001年5月MSC第74届会议和2002年3月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MEPC)第47届会议批准了《在IMO规则制定过程中使用综合安全评估(FSA)指南》(MSC/Circ.1023-MEPC/Circ.392)和《在IMO规则制定过程中使用人为因素分析程序(HEAP)和综合安全评估(FSA)导则》(MSC/Circ.1022-MEPC/Circ.391),标志着FSA作为一种工具,正式与IMO规则的制定过程结合起来,其路径是将FSA作为一种评估手段,对既存的、即将改进或者全新的有关海事安全制度或规定进行比较,力求在各种海事安全技术和操作问题之间达成平衡,或者基于成本——效益考虑实现投入最少、产出更多的目的。同时将FSA的研究成果作为一种的科学性、合理性的证成手段或确信依据,使凭借FSA构建的海事安全制度或规定,更具说服力,更具精准性,进而整体提高国际海事安全制度创制的水平与规范参见Guidelines for Formal Safety Assessment(FSA)for Use in the IMO Rule-Making Process,MSC/Circ.1023-MEPC/Circ.392.。
2002年11月,“目标导向型标准”(Goal Based Standard,GBS)在IMO第89次理事会会议被提出时,FSA又被确立为制定GBS的一种方法论张爽、韩佳霖:《IMO对GBS的审议进展》,《中国海事》2012年第5期。。通过FSA制定GBS的方法被称为“安全水平法”(Safety Level Approach,SLA)。
UNCLOS关于风险管理与评价的规定虽然只规定在第十一部分“区域”,但随着国际海事领域的积极实践,风险管理与评价及其工具不仅会在“区域”得到创新应用,而且会在其他海洋区域以及国际海事安全风险领域得到更为广泛的应用。
结 论
关于“海事”一词的界定,UNCLOS和专门的国际海事安全公约均采狭义的法律界定,不但在法律创制的逻辑前提上达成了明显的一致性,而且在具体的法治实践与理论发展过程中也获得了同样的遵循,从而使UNCLOS和专门的国际海事安全公约均能同轨性的共致海事安全法治建设。UNCLOS虽然不是专门调整国际海事安全的条约,但做为“海洋宪章”的地位,其所规定的证书相符的适航制度、主体多元的管控制度和避碰导向的海道制度,是国际海事安全制度的明确细化的规定,构成海事界的立法基准和行为准则;作为“伞形公约”(umbrella convention)的属性,其所确立的“二元并存”的立法准据,在更高的法律效力上实现了上位法的妥协统一,同时通过引入区域协同理念和提出“风险管理”及其评价工具的创新要求,不但表达了构建一种覆盖全部海域和所有船舶的海事管控体系的强烈诉求,而且在顶层设计和发展面向上助推海事安全管控从单一领域延展至多个领域,以最大程度实现各海洋区划与国际海事安全的完全对接。
(責任编辑:李林华 )
International Maritime Security Regim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Composition and development orientation
Chen Jinggen
Abstract:As a parallel treaty to control maritime risks jointly with special international maritime safety treaties,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defines the institutional composition on the aspects of sea-worthiness requirements,control responsibilities of subject diversity and collision-oriented sea lanes demarcation. In the narrow maritime dimension,while based on the attributes of the Charter of the Sea and the Umbrella Convention,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establishes the“dual element co-existence”legislative criterion,which not only effectively coordinates its relationship with the special international maritime security treaties,but also sets the domestic legislative benchmark of the contracting States as“generally acceptable international rules and standards”and“applicable international rules and standards”,thus the standard unification of the upper law is realized;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introduces the concept of regional coordination and fill the gap in the allocation of national jurisdiction,such as Flag States,Coastal States and port States,in order to construct a maritime control system covering all sea areas and all ships.
Keywords:the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International Maritime Security;Traffic Separation Schemes;Regional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Formal Safety Assess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