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病
2020-03-20姚永涛
姚永涛
一
我小时候常患病,听我母亲说,是因为她在怀我的时候,想吃带着酸味的橘子罐头,家中没钱,父亲便去山中摘了不少野果子给母亲吃,后来在胎里留下了病根。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但我小时候的病,确实不少。
母亲说我小时候爱哭,晚上放不了床,得有人抱着,但不管是怎么抱着,我还是常常发高烧。这对别的小孩都是家常小病,打上一剂退烧药,好好睡一觉,早上起来便可相安无事,照常吃两碗大米饭。而我一烧就烧糊涂了,在床上就手舞足蹈,来回翻腾,能把架在床上的蚊帐全部都撕掉。
我母亲经常在半夜唠叨父亲,催着父亲赶快去找离我们不远的一个医生。医生是我大叔,是个兽医,常做的事情就是给村里每家的公猪结扎,我们小孩都很怕他。我们把他手里的那把能反复使用的铁质注射器,叫作大铁针,总感觉这大铁针是给猪用的,不是给人用的。但村里没有别的医生,去镇上又太远,山路也不方便,只能靠他。
那时候没有专业的医用酒精,父亲就用茶缸灌来自家酿的烈酒,在棉被里抠出几坨好点的棉花,组成简单的消毒医具。
大叔打针的时候,要用钳子敲上两支葡萄糖,吸到注射器里用来调和青霉素。然后让我脱下裤子,用手拍拍我的屁股蛋子,找个肉多的地方,用棉花沾些烈酒涂在上面。他扎我的时候我不敢看他,他一边说着“不疼不疼”一边猛地扎在屁股上,然后就是一阵胀痛,感觉屁股鼓了一个大包。
有时候大叔的针管用,烧了一夜就不少了。有时候大叔的针不管用,母亲就抱着我走十来里的山路,去乡里找医生。
二
乡里的医生只有一个,姓李,按照辈分,我要把他叫哥。李医生个子不高,人也挺和善的,在乡里的街道上租了两间不大的门面房,做了一个简单的卫生室。每次我和母亲去的最早,他才打开卫生室的门,一股青霉素的药味就冲进鼻子,我害怕这种味道,常常待在门口不愿意进去。
李医生也不生气,擦了擦有些年头的凉椅,喊我进来做皮试。我硬着头皮进来,歪着头不敢看他。母亲半抱着我,用身子挡着李医生,扶着我的手,让我把拳头捏紧。
李医生拿出一个大铁盒子,打开后里面有剪刀、酒精、注射器、针头等医用工具,我喜欢他盒子里面那个粗长的黄色皮筋,如果把这个皮筋拿走,做弹弓打鸟,应该很厉害吧。不过,我也只是想想。他用那个黄色皮筋捆住我的手,然后找到我手腕上凸出的青色血管,用小针头慢慢扎进去。
在李医生这看病,除了做皮试和打屁股针疼点,其他的还好。除此之外好像也没有别的治疗方式,就是打吊瓶。那时候的吊瓶是玻璃的,很大,就这样沿着塑料管一点点地滴,一瓶子都得一个半小时,我常常一次是两到三瓶子。那时候他那有没有电视,我就这样傻坐着,似乎能感觉到冰凉的点滴就这样慢慢流进身体,手变得冰凉,脚变得麻木。
在李医生那打完针,一般都到下午了。烧退了,精神稍微好点,母亲又带着我往回走。那时候乡里有没有饭馆,饿了母亲就给我买一包斯美特方便面,我把方便面捏碎,拌着调料,一点点吃。母亲总是什么都不买,也什么都不说,只是带着我往前走。
三
我六岁的时候,受了一场大病,也是自己玩耍找来的病,找来的痛。
那时候我小叔刚初中毕业,我们几个小孩,黏着他去土房的阁楼上,听他放小收音机听。从土房的堂屋到阁楼,有一个木梯,木梯是爷爷自己做的,就用圆木棍组装在一起。下楼的时候,后面有个堂兄催我,我踩着圆木棍梯子,脚一滑,从梯子上摔了下来。
小叔抱起我,看着我流血的嘴,以为是我的嘴摔破了,再看我胳膊时,白色的骨头已经戳破了我胳膊上皮肉,硬生生地伸出了两厘米。
我只记得我一直哭,母亲抱着我往后山梁子上跑,想跑着送我去医院。母亲在哭,接着很多人都在哭,跟着母亲一起哭。最终还是被一个会草医的大妈拦下了来,她说这是骨折,她会接。然后,她拉着我摔伤的手,使劲一拉,生生把露在外面的白骨拉了回去,然后再使劲往上一推。在这一拉一推中,我发出猪叫般的哭声,最后疼晕过去了。
草医大妈说接上了,然后用各种草药,叫父亲捣碎,敷在伤口上面,又给我找了两块竹子做的夹板,把我的胳膊夹住,再用白布缠着。后面的一段时间,我天天喝中药,每次都是一大碗,有时候实在喝不下去了,母亲就给我一颗冰糖含在嘴里。
我常觉得手疼,有时候是痒,懂得的大人都说,痒是生肉呢,快好了。母亲半信半疑,终于在一个月后,把白布和竹板拆开了。原来我的手并没有接好,胳膊上的肉已经开始腐烂了,夹杂着草药,血肉模糊成一片,有的地方还能看到一些白骨。
那时候已经是腊月了,父亲带着我去城里的大医院。走到镇上,然坐那时候为数不多的面包车,再到车站坐火车。
那段时间我一直待在医院,从开始的清理腐肉、重新接骨,再到后面的取钢针,我的胳膊来回缝了三次,现在仍然有疤,像一个蝎子虫一样爬在我的胳膊上。那段时间,我打了很多青霉素,甚至在后面几年里,我出的汗、尿的尿都有一股青霉素的味道。
四
六年级的时候,我肚子上长了一个脓包,别人长脓包可能很小,长到核桃那么大,擦点药就好了。而我肚子上的脓包能长到苹果那么大。
母亲带着我去医院,先是去乡上找李医生,打了几天消炎针不见好,又带着我去镇上找医生。去镇上的路都是山路,我走不成,一走就疼。母亲找来平时背苞谷的背篓,让我坐在背篓,背着我去镇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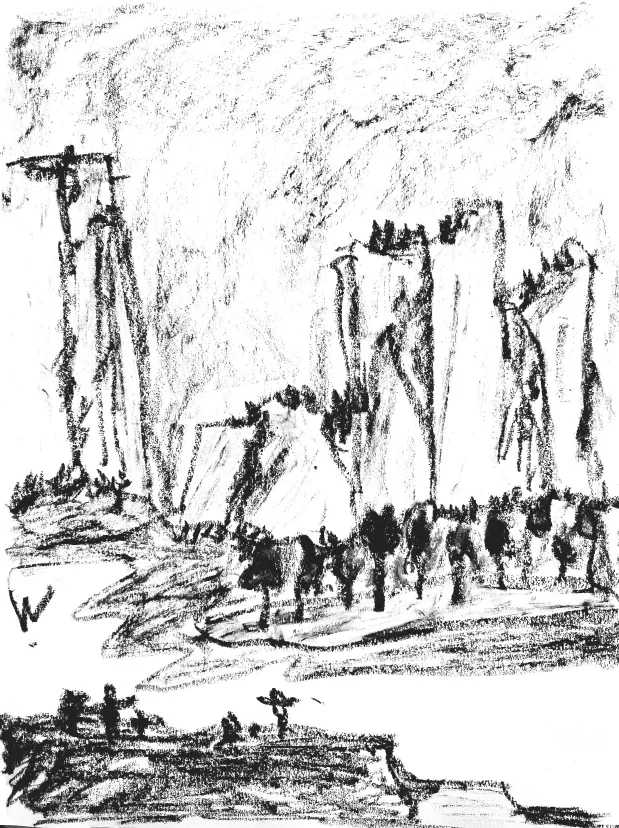
我们那里所谓的山路,就是翻山,去的时候从山尖走到山脚,回来的时候从山脚走到山尖,不管是下坡路还是山坡路,背人都是不好走的。那时候我体会不到母亲的辛苦,就躲在背篓里,不敢把头伸出来,害怕会遇到同学嘲笑我。
就算是这样,来回去镇上打了三天针,肚子上的脓包还是没好。我常在夜里疼着哭。母亲就在夜里去找村子里的大爷,听说大爷那里有“七叶一枝花”,这是灵药,又比较少见,大爷一般都不给别人。母亲求来了一小节“七叶一枝花”的根茎,磨成粉,搅着陈醋,用一根鸡毛沾着,一遍一遍地涂抹在脓包上。
果然有效,脓包在慢慢缩小,也渐渐变软,按照土话说,要化脓了。然后母亲带着我去找李医生,开了刀,清出脓,才慢慢好了。
五
初二的时候,我得了腮腺炎,这是夏季常见的传染病,每人会患上一次,以后就不会再得这个病了。我请假回家,母亲带我去打针,过了两天,快好了。那天下午,我没经得住表弟的诱惑,去河里洗了个澡,当天晚上就开始发烧,高烧到四十度不退。
去乡里、去镇上的医院都不收,母亲带着我坐车去邻镇的医院,医生和母亲想着一切办法给我降温。把我的身上放满夏天常吃的冰袋,灌肠、打退烧针都不见效。晚上我迷糊间,听见医生说,如果今天晚上我再不退烧,就没有任何办法了,建议母亲把我送到县上的大医院去。
母亲焦急,便在夜间跪在地上,求神仙保佑我,求附近寨上的大帝,一边说一边磕头。不知道是神灵的作用,还是药物的作用,第二天我的烧真的退了。
我考大学那一年,母亲凌晨四点的时候喊我起来,放鞭炮,点香烧纸。母亲说我长大了,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她向神灵许了不少愿,也都灵验了,现在是还愿的时候了。我依着母亲,磕头烧香,我知道母亲信仰的是神灵,而我信仰的是母亲每一次的细心关怀。
六
当老师后,讲课很费嗓子,每当天气干旱的时候,咽喉炎就犯了,常常在夜里咳嗽。母亲责怪我,说这都是不喝水的缘故,于是每年在老家摘了不少金银花,蒸过后,再晾干,放在冰箱里,嘱咐我泡水喝,还要加冰糖。
母亲每次唠叨的时候,我总是不说话,脑海里常想起小时候的她。那时候父亲常年外出打工,正月走,腊月回,她一个人顶起家里的天,做农活,种着十几亩地,照顾着我和妹妹上学。
我的顽劣,我的一些病,常让母亲在夜里流下泪水。病在我身,痛在她心,她那操不完的心,似乎并没有因为我的长大而消退,只会变成重复的言语,时常回响在我的耳畔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