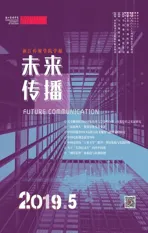“剧界游侠”俞振庭与新潮演剧
2019-12-16刘晓珍
刘晓珍
“新潮演剧”,是当代学者针对清末民初中国戏剧发展的特殊状况做出的概括,它较好地反映了当时“戏剧观念和戏剧意识游弋于古今中外之间”[1]的历史状况。俞振庭,晚清京剧武生俞菊笙的第五个儿子,时人谓其“对戏界,颇有贡献”。[2]喜欢京剧的日本记者波多野乾一也在其专著《京剧二百年历史》中称俞振庭为“剧界游侠”:“先自成前台经理人,招致刘鸿升、梅兰芳等,为其大黑柱,以剧界之游侠而横行”。[3]俞振庭的青壮年时代恰逢清末民初北京剧坛的大变革时期,在思想文化界求新变革与商业竞争等的影响之下,其以罕见的创新愿望、饱满的竞争热情而每每在剧界把握先机,引领剧坛革新风潮,在剧坛男女合演、上演夜戏、时装新戏、新式办班等演剧新潮活动中常常开风气之先,相当引人瞩目。
一、俞振庭与女子观剧、男女合演
清代以前,中国剧坛观演一向男女并重,并无明令禁止女伶演剧或妇女入园观剧的现象。入清以后,由于朝廷干预,北京剧坛上女性迅速退场,戏馆茶楼、台上台下成了清一色男性的天下。然值民初,女角卷土重来,声势浩大,几令男伶无立锥之地,伴随女角登场的还有女观众的大量涌现以及舞台上男旦的凸显,故而张次溪在《近六十年故都梨园之变迁》中总结民国北京剧坛三大变化时,即把“旦行人才勃兴”“坤伶演戏”列为其中两项。[4]而引领这场女性登台风潮的正是俞振庭。
清末民初之际,在梁启超等人“妇女为保种之权舆”[5]的呼吁之下,女子教育问题被提上日程,女学逐渐开禁。戏界也开始大量编演新戏以开启民智。实际上自光绪中叶以降,上海、天津等地男女同观、女角登台则已如火如荼,北京作为政治中心,剧坛偶有违例之举,即遭严禁。直到1906年,一向保守的北京剧坛也编演了几部颇有影响的新戏——《惠兴女士传》《女子爱国》等,并特意安排女性观剧,虽为特例,实女子观剧肇兴之前凑。
到了1907年,以俞振庭为主要经理人的新式戏园——文明茶园,正式开始售票欢迎女观众入园观剧,“楼上专卖女座,楼下专卖男座”,[6]从此彻底打破了北京戏园不卖女座的惯例。这是破天荒的大变局,所以经常被忆及,如《梨园外史·观剧生活素描》中所记:“北京戏馆子照例不卖女座的。堂客看戏很难。自从文明茶园开锣,才有女人买座之事。”[7]当时的《竹枝词》里也咏道:“旧人冷落老何戡,红粉登台倍两三。试向梨园窥坐客,女权真个胜于男。”[8]
据资料记载,女伶入京、男女合演更是直接由俞振庭所开启。罗瘿庵《菊部丛谭》中云:“女伶独盛于天津。庚子联军入京后,津伶乘间入都一演唱,回銮后,复厉禁矣。入民国,俞振庭以营业不振,乃招津中女伶入京,演于文明园。金玉兰、孙一清,皆俞五所罗致也。是为女伶入京之始,并首开男女合演的先例。”[8](797-798)恽毓鼎日记中即有这年四月二十二日“往文明观剧”的记载,观看的即是“男女合演”[9]。2004年出版的《旧京老戏单》中有几张戏单是这一年双庆班男女合演时期的,具体如下:
1912年7月3日,双庆班,广乐茶园,坤角有小月芬、于紫云、小四玉、小月芬、孙一清、金玉兰、马云龙;1912年8月25日,双庆班,文明茶园,坤角有盖毓峰、小月芬、苗素珍、盖樵月、金玉兰;1912年9月1日,双庆班,文明茶园,坤角有冯月娥,小月芬、金玉兰、盖樵月。[10]
从中可见当年双庆班男女合演的具体情况。其他戏班也纷纷邀请女伶参加,一时之间成为风潮。叶龙章《喜(富)连成科班的始末》一文中介绍:“民元之际,坤角大兴,且盛行男女合演。这时本社将改组为富连成,叶社长赴津沪约聘坤角。”[11]可见在民国元年这一年,男女合演可谓风靡一时,这是俞振庭率先行动所产生的影响。
二、俞振庭与文明茶园、义务夜戏
晚清之际,在西方话剧写实观念的冲击下,以写意为主的传统戏曲观念日渐难以站稳脚跟,中国戏剧界开始懵里懵懂地追求西化、写实。尤其是上海新式舞台、新型砌末等方面的先行示范作用,相形之下,“北京戏园,座落一切,实在是太野蛮”[6],这更加刺激了京城一班剧坛维新人士的改良热情。
另外,由于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清末民初的北京城的文明新风也日渐成为时尚,“文明头”“文明脚”等开始流行。伴随文明风尚而来的“追洋逐新”也日益成为一种北京市民生活的风潮,一时之间,洋装洋车、电灯电话成为北京城内居民争相拥有的炫耀资本。当时有《竹枝词》咏写道:“松松辫发裤儿长,天足跚跚海样装。出得风头真十足,露天茶座据中央。”[12]这种风气无疑也促生一种逐新求变的观剧心理,新舞台、新砌末成为招揽观众的法宝。
于是仿照上海式样改建戏园,从上海采办砌末成为当时北京剧坛上的新动向。光绪庚子前,即有福寿班各种服装、砌末“别翻新样,美华鲜妍,均由上海苏杭各省采办”。演剧所在的广兴园也“楼下各廊等座位皆是长椅,均照上海戏馆形式”。[2](585)《申报》也报道此戏园“仿沪上之新式,除京师之旧规,生面别开,匠心独出”。以致于“开张之日虽值大雨,而楼上下坐位全满,后来者竟无从插足”。[9](488)
在此文明新风的浸染之下,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座落于北京西珠市口大街路北的以“文明”命名的戏园——“文明茶园”诞生了。这个命名颇具时代气息的戏园正是由“俞五等集股建造”。[7](403)
据《顺天时报》报道,该戏园“仿照上海戏园办法,池子内一律陈设方桌圆椅,楼上分出一间一间的包厢,所有板墙都是斜的,免得遮断视线。正楼分两层,前边低后边高,规模阔大,形式整齐……园中满装电灯,添演夜戏,进门买票,每天限定卖多少票,卖完便停止,闲人不准乱进”。[6]后又刊载于《文明茶园听戏记》:“北京数百年来,戏班最称第一,戏园内容的野蛮也可称第一。数百年后,到1907年10月间,方才有这文明戏园。园名文明,真是名实相符。”[6]可见这文明茶园改革步子之大,非当时一般戏园所及。
稍后,另一座新式戏园——吉祥茶园也建立起来。而这座戏园也是俞振庭的双庆班经常演出的地方。吉祥茶园于1907年由清宫大公主府的总管太监王德祥出资,在东安市场内东北隅开始建造,1908年2月9日开始营业。“因建立较晚,在结构和设备上有一定革新。”民国以后舞台上也安上了电灯、汽灯。[13]最与其他戏园不同的是“没有台柱子,听戏的没有吃柱子的感觉。”[14]梅兰芳于民国初年搭档俞振庭的双庆班,“排演了各种形式的新戏”,[14](254)如“古装戏《嫦娥奔月》《黛玉葬花》《天女散花》,首次上演都是在东安市场吉祥园”。梅兰芳说:“那几年我在吉祥演戏的时候最多。所以排了新戏总是在那里演第一次。”[14](532)齐如山也说此时“梅所搭之班,为俞振庭所成,永远在东安市场吉祥戏院演唱,后俞又把文明戏院租过来(后之华北戏院),由上海约来林颦卿等成班,与兰芳之班在吉祥、文明轮流演唱。”[15]也即,那时期北京剧坛上的两大新式戏园——文明茶园与吉祥茶园,一个外城一个内城,均为俞振庭戏班的演出场所。由此可见俞振庭对新式剧场的看重。
自文明茶园开业,“添演夜戏”,也成为增进业务的砝码。据说,夜戏在北京剧坛的上演也是由俞振庭一手促成的。
早先北京城是有宵禁的,到了光绪末年宵禁废弛,夜戏便应运而生,成为京城百姓最好的休闲娱乐,也促进了京剧的兴盛。最初的夜戏是借着“义务”之名展开的。清末上海的先进人士受西方演剧筹款的启发,促成演剧筹赈的诞生。京津地区则是在戏剧改良和国民捐运动的作用下,以“惠兴女学事件”为契机,促成了义务戏的出现。[16]
而义务夜戏,则是俞振庭的大胆尝试,他常常借助义务的名义上演夜戏,久而久之,营业性的夜戏也就演起来了。梅兰芳曾回忆,民国二年的五月间,广德楼有一次“义务夜戏”,“俞振庭办的。谭鑫培、刘鸿声、杨小楼……这些好角,都被邀去参加会串,我也在被邀之列。”[14](112)“从义务夜戏唱开了端,才渐渐地把‘不准演夜戏’的旧习惯、旧脑筋改变过来。”[14](114)所以梅兰芳说,俞振庭因“头脑灵活的关系,除了能在台上翻老戏、排新戏以外,北京的开始演夜戏和男女合演,都是创自俞振庭,开风气之先”。[14](102)
三、俞振庭与时装、古装新戏
清末民初的北京剧坛上,与剧场、舞台革新相适应,区别于传统古装的时装、洋装新戏成为追捧对象,表演方式也发生相应改变,过去的听戏、唱戏现在变成了看戏、演戏。新式的服装、新型的表演成为最吸引人眼球的资本,而传统的唱功反倒成为次要的了,《北京竹枝词》中有一首形象的咏写:“歇却梨园管弦声,时行新剧号文明。铃声一振忙开幕,不听歌喉看表情。”[12](429)特别是1910年,剧坛维新人士王钟声自上海来京,在前门外天乐茶园演出,轰动了北京城,“且因钟声重在演说口白,故此向来以池子为靠近台前为最劣等座位的,今一耀(跃)为万人共争的最优等地位,逼近听钟声最亲切有味。”[6]这对北京剧坛改革影响很大。
俞振庭在这方面也不甘落后,早就积极投入到了时装新戏、古装新戏等的排演与推动工作当中。例如,1908年,俞振庭组织排演的时装新戏《杀子报》在文明茶园上演。其时梅兰芳刚登台不久,饰演了其中的小孩金定。[10](9)之后俞振庭又参与排演了《越南亡国惨》等时装新戏,《正宗爱国报》第949期有报道:“本报刊登之《越南亡国惨》新戏,现经梨园俞振庭、瑞德宝、迟小亮儿等排演,唱老旦的麻文子也极力赞成,定于月内开演。现在该梨园又续排演《绿牡丹》,加以电光彩切,必然是可观的了。”[9](155-156)
民初,俞振庭力聘梅兰芳入其双庆社,并一起排演了大量时装新戏与古装新戏。据梅兰芳回忆,从民国四年的四月到民国五年的九月,一面演昆曲戏,一面“排演了各种形式的新戏”。第一类仍旧是穿老戏服的新戏,如“牢狱鸳鸯”;第二类是穿着时装的新戏,如“宦海潮”“邓霞姑”“一缕麻”;第三类是梅兰芳创制的古装新戏,如“嫦娥奔月”“黛玉葬花”“千金一笑”。[14](254)民国六年七八月间,他又一次搭入双庆社,与俞振庭、王凤卿、高庆奎、程继仙、姜妙香、路三宝、姚玉芙等一起演戏……“在吉祥园白天演出,演了十八个月光景。”这期间他们排过两出新戏《天女散花》和《童女斩蛇》。[14](471)由上可见,梅兰芳的古装新戏与时装新戏都是在双庆社期间排演出来的。俞振庭不仅在这些新戏中扮演角色,同时,他作为班主,也经常是新戏的倡导者与组织者。
据齐如山回忆,俞振庭聘请到梅兰芳之后,安排其在东安市场吉祥戏院演唱,后其又由上海约来林颦卿等成班,“与兰芳之班在吉祥、文明轮流演唱。”林颦卿以新戏(《白乳记》《狸猫换太子》)等等为号召,“戏虽没有什么价值,但北京人没见过,大受欢迎。”[15](111)这也激发了俞振庭和梅兰芳创制新戏的愿望。齐如山详细讲述了《嫦娥奔月》这个新戏的产生过程,其中俞振庭的促成作用可以说是非常大的。
齐如山回忆,民国四年八月节前夕,俞振庭找到他说:“八月节第一舞台王瑶卿他们演《天香庆节》,乃宫中的本子,中秋应节戏。我们也应该排一出新的应节戏才好,否则一定要栽给他们。”[15](112)于是就有了古装新戏《嫦娥奔月》的诞生。
他们为这出新戏“特创一件古装”,这些都是旧戏班所没有的,设计上参考古代仕女画像中的服饰,一改戏曲传统服装衣长裙短难以表现女性身材的样式,“于是费尽心思,裙子之尺寸,仍照画中制法,腰带则结于真的腰际,而裙子加长,裙腰则靠上……”,以突出仙女体态的袅娜、轻盈。在发式设计、舞台设计及灯光运用上也有诸多创新之处。[15](113)
演出效果极好,梅兰芳说当时“台下全场观众的眼睛都冲我上下来回不断地打量”。[14](287)足见此戏的吸引力。“大家都叹为得未曾有,连演了四天,天天满座。这在上海算不了什么,北京没有这种习惯,所以是很不容易的,把第一舞台之《天香庆节》,打了个稀溜花拉。”后来在梅兰芳家,俞振庭及几位班中管事特地对齐如山表示谢意,俞振庭说:“这出戏光看本子,实在想不到有这种力量,真是多亏您安排。”[15](114-115)从齐如山的介绍中可以明显感受到俞振庭对这出戏的催生作用,他的大力支持更是直接促成了双庆班之后各种新戏的编演工作。
俞振庭头脑聪明,“点子”颇多,有时候还在戏名上做文章,弄出新花样,来吸引观众。梅兰芳说:“像‘大长坂坡’、‘四白水滩’……等新名目,在北京城里都是他兴出来的。”[14](252-253)有时候又会在戏目的安排上想出新花样。1916年,久未登台的谭鑫培要在东安市场“丹桂戏园”演出,俞振庭就为梅兰芳特意设计了竞争方案,“将《孽海波澜》分四天演出,每天在这新戏里加演一出老戏,如《思凡》《闹学》等”。结果,“四天的成绩,吉祥的观众挤不动,丹桂的座儿,掉下去几成;最后两天,更不行了”。[14](216)足见他的新花样所起的作用。
四、俞振庭与新潮办班、挖取名角
俞振庭还以他敏锐的商业嗅觉、强烈的竞争热情,在此一时期的剧坛竞争中崭露头角。清末,作为重要的通商口岸和租界,上海剧坛的商业化表现已经相当突出,一些到过上海演出的北京名伶开始把这种商业化气息带入北京剧坛,引发剧坛规矩的诸多变化。从前的戏班制度包银、轮转等被迅速打破,剧坛如战场,处处充满商业竞争的气息。俞振庭除了革新剧场、创新剧目而引人瞩目外,在组织戏班与利用名角上,也常常因能力强、魄力大而“称霸”剧界。
善于组织办班,是俞振庭作为一名武生不同于其他演员的本事。他因“少年斲丧过甚,武功退化得很快”,民国十一年以后,就不大上台了,却因“善于组织,而且头脑灵活”,“在清末起就组织了一个双庆社,遍邀各大名伶在他班里演出,自谭鑫培起,杨小楼、余叔岩、四大名旦、王又宸、高庆奎、马连良等,都搭过他的班”。[17]
他办班不止一个,有大班,也有小班;有常规班,还有机动班,可以说是相当丰富了。除了双庆社这个大班外,他还办有斌庆社科班,收些学生和搭班的童伶。他“把成名的大角,安排在双庆社;他的学生和搭班童伶,以及尚未成名而有起色的角儿,安排在斌庆社。有此大小两个班儿在手里,在民国元年到二十年这个阶段,可以说纵横北平剧坛,蔚为一时权威”。[18]
他还办过春合社戏班,据梅兰芳解释,这是一种机动性很强的戏班。由于谭鑫培晚年不常露演,每次演出不过几天时间,所以邀请到他的班主,为了不影响正常戏班的营业,“就就用一个无主的旧班社的名义,先向‘正乐育化会’申报开业。其余的角色,临时再向各方面邀请。春合社就是这种环境之下产生的。”[14](456)而谭鑫培晚年的露演,据说“十回出来总有七八回是俞五的策动。”[2](310)
所以说,俞振庭不仅善于办班,更善于沟通交流,挖取名角。谭鑫培入了民国之后,就不大出来演出了,搬动他当然就不是那么容易了。不过他愈不出台,观众越是盼想,但“无论多难”,俞振庭“也有法可设”,[2](310)真可谓“手眼大”,所以谭鑫培晚年“在文明茶园、吉祥茶园唱的时候多。该二园那时均归俞五主持”。[2](316)
俞振庭邀请梅兰芳也是颇费功夫,充分展现了他的剧坛公关能力。首先是赶几千里路专程邀请,显示诚意。当梅兰芳说“其实这点小事,您又何必老远的跑一趟呢?写封信来,不也就成了吗?”他回答:“那不成,我听说北京有好几处都要邀请您,我得走在他们头里。来晚了,不就让您为难吗?”真可谓来得及时。其次是带有助攻,他不是一个人前来,而是带来了他的嫂子。因为他的嫂子是梅兰芳之妻王明华的姑母,利用亲戚关系做文章。再者是一直陪同,梅兰芳答应之后,俞振庭并没有立即回京,而是选择留在上海,借口多玩几天,其实是想一直陪在梅兰芳左右,等他期满一同回京。[14](248-249)最后是下车后寸步不离。梅兰芳一下火车,就被“翊文社”以及其他几家班社派来的人团团围住。俞振庭早有防备,直接把梅兰芳护送上早已准备好的车子。可以说是步步为营,做足了功夫,足见其长于谋划、考虑周全的性格特点。
五、结 语
俞振庭在清末民初北京剧坛的新潮演剧活动中,可谓时代弄潮儿,成为当时的剧坛风云人物。究其原因,除去变革的时代大背景外,也跟其家庭环境关系密切。正如丁秉燧所说:“一来他是名父之子、梨园世家,大家都有点渊源,他来邀请不好意思不答应。二来,他在台下也是‘小毛包’,颇有点恶势力,又养了一群武行,大家都有点惧怕三分,他来邀也不敢不答应。”[17]武行世家的出身使得他练就一身的霸气胆量,能够做出许多别人敢想不敢做之事。所以梅兰芳说:“俞五的办事,倒是大刀阔斧,能够放手去做,在当时北京城开戏馆的老板里面,是比较有计划有魄力的。”[14](252-253)他以敏锐的商业嗅觉和高超的沟通能力出入于班主、导演、调度、演员等诸多身份之间,如鱼得水、游刃有余,成功地掀起了北京剧坛演剧新潮,虽有急功近利的表现,但对北京剧坛的繁荣与发展也确实功不可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