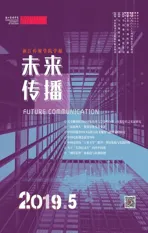共同文化与本土经验中的科幻审美
——基于电影《流浪地球》的情感结构分析
2019-12-16苏东晓
苏东晓
2019年初,由刘慈欣小说改编的科幻电影《流浪地球》风靡全国,上映两周便位居中国电影票房总榜第二,同时刷新了中国电影的海外市场纪录,就连好莱坞著名导演詹姆斯·卡梅隆也在社交媒体上对《流浪地球》发出了祝愿。那么,《流浪地球》的科幻构建对应了怎样的共同文化和本土经验,从而成功地唤起了观众的审美热情,实现了市场佳绩?
一、“惊颤”
科幻的产生与现代科技的发展密切相关,要触及科幻审美的内核,就要从“现代性”入手。什么是“现代性”?周宪教授认为,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现代性总是和现代化过程密不可分,工业化、城市化、科层化、世俗化、民族国家等历史进程,就是现代化的种种指标。作为一个心理学范畴,现代性不仅是再现一个客观的历史巨变,而且也是无数“必须绝对地现代”的男男女女对这一巨变的特定体验。[1]马歇尔·伯曼说,那是一种关于时间和空间、自我和他人、生活的各个可能和危险的经验,我们发现自己身处一种环境之中,这种环境允许我们去历险,去获得权力、快乐和成长,去改变我们自己和世界,但与此同时它又威胁要摧毁我们拥有的一切,摧毁我们所知的一切,摧毁我们表现出来的一切。它将我们所有的人都倒进了一个不断崩溃与更新、斗争与冲突、模棱两可与痛苦的大漩涡,“所谓现代性,也就是成为一个世界的一部分,在这个世界中,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1](15)科幻就是现代性的一种文艺表现,亦或是现代人面对“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巨大崩裂而尝试的一种审美对抗。
从玛丽·雪莱再到凡尔纳、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等声名显赫的科幻作家,一直到21世纪形形色色的科幻小说和科幻影视作品大量出现,他们建构了科幻审美的第一准则,即对工业化的首要动力——科技对人类生活方式的改变展开想象。罗伯茨在《科幻小说史》中粗略勾勒出了科幻作品的四种类型:空间的旅行故事、时间的旅行故事和想象性技术的故事及乌托邦小说。[2]在这几个类型中,故事情节所籍以展开的核心元素都必然依赖于某种科技。首先,科技总是展现出巨大的力量,其次,这种巨大的科技力量总是为人类展开了一个不同于此时此地的“他异性”的故事时空,然后,科幻故事的主人公总是在这个“他异性”的时空里展开一系列的冒险。科幻故事的魅力就在于将科技带给现代人的崩裂感和惊颤,通过“他异性”时空的奇观来舒展和通过冒险历程的紧张来宣泄。
科幻小说和科幻电影作为现代人对科技冲击生活现状的一种审美反应,在早一步进入现代性中的西方已成为一种影响颇大的通俗文艺形式,但由于中国自身的现代性进程在时间与路径上都有异于西方,中国人对科技引发的工业化及其崩裂性后果的感知要相对滞后,因此,科幻文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只是在小范围内发展,只是部分知识精英和耽于科技想象者的审美偏好。但随着中国现代性进程的加快,乡村消亡、互联网+经济、融媒体传播、人工智能、太空竞争、生态危机……与科技、工业化息息相关的议题高频地出现在我们的日常中,科技化和工业化的影响迅速纵深地进入每个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再加上全球化时代国际交流的密切,好莱坞影视文化的滋养,中国人现代性情感结构中的崩裂感和惊颤感也就越来越强烈,因而也越来越显现出对科幻文艺类型的认知和审美需要。于是,在中国科幻类型作品沉寂多时之后,电影《流浪地球》横空出世且恰逢其时。《流浪地球》主体情节圈定在地木危机时刻展开的36小时救援行动之内,是一次危机四伏、紧张急迫的冒险;主要人物形象是一对逃离地下城的兄妹、一支地表救援小分队、一个空间站领航员,由此电影给我们展开了三个叙事空间:地下城的日常生活空间、从地球表面延伸到空间站的秩序空间,地木相吸的危机空间,这三个空间给我们展现了“他异性”的奇观,同时也开启了“乌托邦”的议题,构建起了与西方经典科幻片相似的审美共情。
但《流浪地球》创造了一个更大的惊颤。作为一个空间旅行的故事,《流浪地球》讲述的是科幻文艺中常见的“末日逃亡”主题下人类太空旅行的故事,却不像西方科幻“末日逃亡”时那样只是乘着太空飞船逃离地球,并流亡太空亦或殖民外星,而是试图用一万座高达万米的行星发动机推动地球离开即将毁灭的太阳系到4.2亿光年外的新星系,重建地球的“黄金时代”,这是一个极富新意的太空冒险创设。同时,《流浪地球》里的时空观也是相当恢宏的,它不是部分人的瞬间的时空穿梭,而是将由上百代人所经历的跨越2500年的未知航程。科幻中的“末日逃亡”本就包含两个层面的意象:一个是“末日”的意象,另一个是“逃离”的意象。现代性大崩裂是一种末日,如何逃离?这种逃离是一个多长的时间历程?逃离的结果是什么?《流浪地球》有别于以往的宏阔设想和时空观,构建了新的隐喻,也因为这种新的可能激发出更大的崩裂感和惊颤。
二、“悲欣交集”
科幻表达了现代人面对“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时的崩裂感和惊颤,并尝试一种审美对抗,但这种审美对抗在西方似乎形成了两种不同的传统:从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开始,后承赫伯特·乔治·威尔斯等人的所谓悲悯与反思的科幻正典传统以及凡尔纳为代表的所谓奇幻和浪漫的科幻通俗传统。有评论认为电影《流浪地球》与其说继承了威尔斯一脉对“现代化”的困境意识和精英式的反思批判,不如说沿续了凡尔纳一脉的科技罗曼史建构,但笔者认为《流浪地球》的科幻审美既不算是玛丽·雪莱和威尔斯式的,也不就是凡尔纳式的,它带有浓厚的中国经验的烙印。从其审美形态上看,它是一种“悲欣交集”。
电影《流浪地球》的故事内核里没有人类与科技进步之间的“冲突”这一正典科幻鲜明的主题。它的末日灾难来自于太阳的自然消亡,而不是来自于人类的狂妄自大,相反,人类科技的力量恰恰是故事中人类自我拯救的重要依靠。在危机时刻,人们并没有太多的“to be or not to be”式的犹豫和徬惶,更多的是接受现实,并通过智慧和勇敢最终胜利地走出困境。如,当地木两星球相吸,人工智慧“莫斯”准备执行更“稳妥”的计划:保存沉寂的太空站人类基因信息,等待“弥赛亚”的重生,放弃地球上仍然鲜活的生命最后的机会时,刘培强的反对没有一丝迟疑和挣扎,而人类的“孤注一掷”最终成功也不代表着温暖的人性战胜冰冷的科技理性,而恰恰是人类秉持终极理性的胜利,因为莫斯并没有将太空站的能量计算在内,这与其说是对人类现代困境的展现、反思和批判,不如说是对人类科技理性力量的一种拥抱和歌颂。而以凡尔纳为代表的科幻一脉,在想象科技对人类生活方式产生的影响时,表现出了一种拥抱科技、拥抱未来的热情。另外,葛兰西在评判科幻作品时指出,凡尔纳的主人公掌握的“可能性”,从时间上来说,超越了实际存在的可能性,但并不超越很多,因而,虽然威尔斯更富有幻想力和聪慧的才干,但凡尔纳是更受欢迎的通俗作家。[3]《流浪地球》中那些带着机械重工业色彩的科技器物,似乎离中国当代“大国重器”的愿景较为贴近,展现的不是一种压抑和恐惧,而是一种宏伟和壮观,不是一种不可触碰的冰冷,而有着一种距离现实并不遥远的温暖。所以,某种意义上,凡尔纳的故事少了一些形而上的悲悯与反思,却更能展现出大众的肉身感知与世俗欢乐,从这些层面上看,《流浪地球》确有更接近于凡尔纳的一面,显现出一种欢欣与激扬的风格。
《弗兰肯斯坦》中的科学家僭越人的界限,使自己成为造物主,却创造出了可怕的怪物,而这个怪物原本善良,却被恶意的人们逼迫成了残忍的魔鬼,玛丽·雪莱展现了科技被滥用的可怕后果,也揭示了现代化进程中人类狂妄自大的丑态及危害。《时间机器》中的时间旅行者乘坐时间机器穿梭到未来,看到了可怕的图景:未来的人类进化成机能退化的埃洛伊人和嗜血残忍的莫洛克人,上演了人吃人的惨剧,而在更遥远的未来,地球上再无人类,只剩下一片萧瑟和死寂。威尔斯展现了工业化所形成的阶级对立的极端后果,也对这种进化序列中的人类未来表示出失望,提出了回望过去的反思,于是,他让时间旅行者逃离了未来世界,前往过去,再也没有返回。玛丽·雪莱和威尔斯等人开启的这一类科幻作品,常常在作品的形象建构上描绘发达的机器,展开令人惊诧的冒险,但同时显现出对未来的某种恐惧和失望,因此,凋蔽城市、末日灾难、异变人类也成为这类作品中的常见意象,它们着眼于人类与科技进步之间的“冲突”,主要表达某种警醒、反思和批判,同时也呈现出一种宗教意义上献祭者的无奈又痛苦、谦卑又神圣的情感态度,在美学层面上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悲剧意味。而在电影《流浪地球》中,面对末日灾难,人类坚强乐观,带着地球去“流浪”,整部影片就像一部太空奥德赛,充满了史诗般的美感和浪漫,没有呈现出上述西方悲剧审美中鲜明的情感态度:从恐惧和怜悯中生发出一种终极的超越于世俗功利的人的神圣与崇高,的确不同于玛丽·雪莱和威尔斯。但是,地球的希望却是以百代人的坚持和牺牲为前提,而且谁都无法预测这个希望能否成为现实,尽管如此,人们仍然决定不惜一切,把握当下,“无论最终结果将人类历史导向何处,我们决定,选择希望!”(1)电影《流浪地球》中刘培强在危机时刻所说的话,之后被我国观众口口相传,电影评论争相引用,成为该影片的著名台词。,这里充溢着固执于现世的生命意志和集体战斗豪情,在一种苦痛和绝境中绝不逃向虚无的形而上救赎或个体性的精神抚慰,呈现出一种特有的悲壮和沉静的风格。
浙江大学王杰教授在谈论中国审美现代性时认为,“悲欣交集”正是中国审美现代性的一种表达,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情感结构的直观呈现,这是一种断裂、破碎的人生经验以及激扬的理想在艺术追求中的交集,它们相互冲突撕裂又相互支撑凝聚,呈现出不同于西方的审美经验。[4]上述《流浪地球》中所表现出来的面对科技理性与人类未来的那种欢乐与悲壮、激扬与深静的复杂交合无疑就呈现了这样一种“悲欣交集”,或者说,正是这样一种特有的“悲欣交集”的情感结构,造就了电影《流浪地球》不同于西方传统的科幻审美形态。
三、“革命与乡愁”
科幻审美的形成与现代性的体验和思考密不可分。西方科幻审美所呈现出来的凡尔纳传统亦或威尔斯传统从表面上看确为两个不同的支脉,但归根结底回应的都是西方社会对现代性的体悟,不管是科技罗曼司还是科技悲剧论,实际上都是用资本主义文化的价值核心——自由观念来审视科技理性及其带来的连锁反应。伊格尔顿认为,资本主义体制对于自由观念的诠释与构建形成了一整套庞大的意识形态话语,并将之视为普遍真理,人们以这种自由观念确定主体立场、打造自我身份意识,这种自由体制和意识形态极大地释放了人类潜能,扩展了人类活动空间,同时由于人类自身的有限性,更由于这种自由体制和意识形态存在的诸多不完善,又给人们带来了莫大的精神压抑与痛苦。所以,从本质上看,西方现代精神的各种危机,是自由观念与现实障碍之间的冲突造成的。[5]从这个意义上看,西方科幻中凡尔纳的传统可以说体现的大致是科技理性与人的自由意志相契合的面相,是启蒙精神的积极与昂扬的延续,而威尔斯的传统则是科技理性与自由观念分裂并抵牾的面相,是资本主义体制与意识形态内部无法解脱的结构性困境的艺术表达。但中国现代性的发生并不是从资本主义的自由之思开始,而是从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要获得独立和发展开始,李泽厚说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基本主题之一是“启蒙与救亡的变奏”且有时“救亡压倒启蒙”,因此,中国的科幻审美对科技理性及其后果的审视视角要复杂得多,电影《流浪地球》科幻审美中的“悲欣交集”回应的正是中国社会对本土现代情境多主题复杂变奏的认知和体悟,同时,也以这种独特的认知和体悟为世界的现代性问题提供了另一种体察途径和解题之思。
在《流浪地球》电影中,一些“人设”和情节脉络,如叛逆兄妹的出走、父子情感相依、英雄抗命等,与好莱坞电影的叙事套路并无太大差异,但另一些“人设”和情节设计,如为了保存人类群体的生命延续,可以“心安理得”地以家庭为单位,抽签决定亲人的生死、为了重新点燃地球发动机,可以安然肃穆地面对拯救队员的牺牲等,显然又与好莱坞“政治正确”的情感导向背道而驰。有评论者认为,《流浪地球》电影中的这种叙事呈现挑战了人们普遍认可的情感和价值底线,是其叙事不成熟的表现。但在笔者看来,这恰是中国现代情境多元主题变奏的一种症候。康德在回答什么是启蒙时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要敢于认识!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6]为了启蒙,新文化运动倡导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胡适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7]但正如伊格尔顿所批评的,资本主义体制中自由观念体系存在着诸种悖谬及匮乏,如自由与理性似乎不能等价,建基于理性之上的主体观念难以自明,人道主义价值观也不具有普适性等,故而现实地生产了存在之根本紧张。[5](213)
在中国的现代情境中,这种西式“自由观念”与中国的现实存在之间的根本紧张显然更为强烈,这种个人主义式的主体自由追求在被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同时压迫的现实境遇中似乎更难以实现,要主张个体的自由必先获得民族与国家的自由,孙中山说过,“我们革命党向来主张以三民主义去革命,而不主张以革命争自由……”,“因为实行民族主义就是为国家争自由,……便要为大家牺牲自由。”[8]所以,以集体主义、民族主义为本位的自由观似乎比个体主义为本位的自由观更能适应现实,缓释存在之紧张。在当下,中国崛起,但仍然不得不面对西方构建的现代秩序的禁锢时,民族主义依然是中国当代情感结构中一个强大的结构元素。于是,《流浪地球》既以兄妹的叛逆、刘培强的抗命等情节表达了人们个人主体的觉醒,同时也以似乎有点非人道的安然面对亲人与战友的牺牲等情节,展现了中国现实语境中生发的集体主义精神和民族自强意识。这种从西方自由观出发看似对立的混杂,在中国文化的“中庸”和“实用”传统中却大致可以相安无事。
《流浪地球》的影片中,在地球特殊时期里,人类放弃纷争,在联合政府的领导下,在《流浪地球法》的规约下,集中配置资源,不惜牺牲,按照严密的规程执行拯救地球计划。这是有关地球存亡、人类生死的漫长斗争,人们在这场伟大的斗争中没有小我,只能服从人类共同命运的需要,对西方现代性造就的强烈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而言,这样的情境无疑充满了悲剧性。但《流浪地球》的这种未来想象与常见的好莱坞科幻又是那么的不同。首先,《流浪地球》中的这种高度集约化的未来只是被设定为一个漫长的特殊时期,且是这种非人为灾难造就的特殊时期中最为有效的社会生存模式,是人类共同体深度权衡之后的自主选择,而不是西方科幻中那种非人类自觉的,难以规避又不知其终点所在的异化进程;其次,《流浪地球》还在这个高度集约化的社会运作秩序中设置了一个相对自由和粗放的地下城空间。这里虽然狭小,阳光、白云都是虚拟图景,也随时面临地震和岩浆涌入的威胁,但基本的生存需要都得到联合政府的保障,人们可以保留着黄金时代的大部分生活模式,如核心家庭共居、拥有私人空间,传统的民俗娱乐、街边小吃,甚至还有电子游戏、麻将等私人娱乐,虽然这种私人娱乐似乎属于法外之地,但也似乎只算流氓地痞的行径,还没到联合政府要坚决取缔的地步,总之,地下城中保留了生活百态,气氛祥和且人们充满希望。科幻的类型特征在于创造出一个“他异性”的世界,而这个“他异性”世界的创造不止是引发陌生化的审美感知,还表明对现实的某种否定,对未来某种可能性的拥抱,是“乌托邦”精神的文本实践。电影《流浪地球》中无疑有一个“乌托邦”,而这个“乌托邦”同样是中国现代情境多主题变奏的症候。可以说,《流浪地球》中人类抛弃种族隔阂,压抑个人意志,团结一致,为人类的命运共同奋斗的图景有着鲜明的救亡色彩,统一的配置、集约化的生产又彰显了鲜明的共产主义景观,这是中国现代性过程中,中国社会面对内忧外患而选择的自强道路,是百年来若干次革命背后的乌托邦愿景和精神动力。在这种改天换地、去弊迎新的革命征途中,影片虽然也体现了个体在灾难和集体面前微不足道的悲情,但更表达了个体被“天行健,自强而不息”的崇高所征召后的主动和自觉,同时影片中那种强烈的安土重迁、旧日难忘的家园情怀,那种在逼仄且危机常在的地下城里依然活出百态生姿的现世热情又体现了中国社会一种与自身国族的过去割舍不断的情怀,在不断的回望中矫正现实行动,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理想大同、属于自己的现代性的努力和情感追求。王杰教授曾提出,“乡愁乌托邦”是乌托邦的中国形式及审美表达,[9]《流浪地球》中那种强烈的乡土情怀大致就是一种“乡愁”,而这种乡愁与科幻所特有的乌托邦想象交杂混融正形构了一种极为形象和生动的“乡愁乌托邦”形式,而这种形式应和了科幻审美中普泛的乌托邦情结,同时又突显了当代中国对文化传统的回望和复兴之思。
四、小 结
在美国学者弗雷德里克·詹姆逊看来,“第三世界的文本,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力比多驱力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方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10]综上所述,电影《流浪地球》就是这样一则民族寓言,该片所开启的并不是西方科幻正统里所显现的精英式的、现代性批判的科幻审美,而是面对现代性历程中的西方压迫及“自由”困境,用一个充满中国文化元素和文化自信的拯救地球的科幻故事强烈地投射了当代中国社会基于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的抵抗与反思,呈现了当代中国社会情感结构中的“惊颤”“悲欣交集”以及“革命与乡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