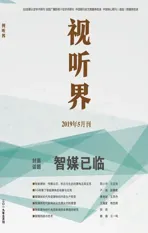嬗变与想象中的“电视之声”
——央视春晚主持人声音体系的意义建构
2019-12-16胡璇董若
胡 璇 董 若
电视作为视听传播的艺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围绕它的讨论大多是基于“视觉文化中心”,而以声音为中心的听觉性因素或被遮蔽,或被搁置。然而,当我们闭上眼睛就可以轻易地躲避影像,可是逃离声音却是一个很复杂的行为。法国学者米歇尔·希翁认为“电视中最重要的就是声音,因为声音永远在屏幕之中,不会被取代,也无须被图像所识别” 。[1]电视由无数的图像构成了一个形象流动体,图像流的特征是碎片化、零散化,我们之所以能够以合理逻辑接受这些图像流,是因为声音在其中起着稳定与平衡的作用,“可闻”填补了“可见”留下的意义空白、弥合了异质的各种片段之间的缝隙——一言以蔽之,是听觉性保证了电视的可理解性,从而赋予其“可看性”。[2]电视的家庭伴随性特征以及新媒体时代的丰富视觉满足,使得“听电视”逐渐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由此,构成听觉文化的声音是讨论电视问题难以绕开的话题。
在神话中,声音尤其是人声被赋予了许多特别的能力,神话与宗教经常将人声当成促使涌现、开创、树立和孕育的力量。[3]基于电视的听觉性本质以及人声在声音范围内的重要地位,这里所要探讨的是对声音的现象学关注,而不是对发声的肉体机制的研究。“春晚”作为中国当代社会重要的政治文化象征仪式,主持人的声音与凝聚某一时刻的总体生成和控制及其背后的文化机制之间形成了一种关系和秩序。央视春晚主持人声音的高识别度,使其建构了一种声音身份,并形成了一套与国家认同和集体记忆相匹配的声音系统,使十几亿观众在一系列规则的声音序列中完成共时性的全民体验。以主持人的声音系统为核心要素的考察,或许能为央视春晚的研究提供新的参照视角。
中国真正意义上的专业主持人概念源于春晚,在这个舞台上,主持人的声音表达走出了播音员语音表达的拘囿,不再是简单的信息传递,而是被赋予了价值与意义。声音总是被一定的文化所建构与重构,由于不断地被注入春晚的文化机制要素,主持人声音在意义增殖的过程中成为春晚最具代表性的象征符号。
一、声音更迭表征:审美范式与内在机制的需求
斯图亚特·霍尔认为,表征是通过语言产生意义,[4]表征系统通过各种各样的符号将事物与概念串联起来。春晚是中国专业主持人的发源地,对于春晚主持人声音流变与更迭的探讨无法悬置于春晚这一方舞台之上。春晚是大众传播时代的文化实践,在大众传播领域,声音是我们认识世界、了解世界的重要途径,承载着传播文化、表达情感等功能,春晚主持人的声音践行着这些功能,成了春晚表征系统中具有强大意指作用的符码。从1983年到2018年,春晚主持人先后呈现出四代格局。伴随主持人格局变化的声音更迭,一方面是其外在审美范式的影响与延展,表征了30多年来文化社会中审美范式的变化;另一方面,声音的更迭也成为春晚不同历史时期内在机制需求的文化隐喻。
(一)语言中流展的欢乐之声
1983年的春节联欢晚会,总导演黄一鹤首次将“节目主持人”概念引入晚会中。相比于之前刻板、单调的报幕员串场,由几位曲艺笑星和电影演员组成的主持人群体受到观众的好评,以至于在整个80年代,一直延续着这种“演员混搭”的组合方式,并未形成固定的主持人阵容。虽然这一阶段主持人的群体“九变十化”,可姜昆却一直将话筒紧握手中,这与该时期春晚的文化定位——“笑的晚会”(以相声演员、相声作品为主)的晚会形式有关,姜昆作为主持人正是这一时期晚会风格的延续,更是整个80年代社会审美风格的一种体现。
声音的附着性与连缀性较强,它往往凭借与声音紧密相连的话语而其形成某种风格与色彩,并内嵌到话语的表达之中。姜昆的声音便是凭借其相声语言的幽默性形成了一种欢乐的风格,同时,相声演员的身份使他对语言的掌握能力较强。索绪尔认为,语言内部存在声音和意义的关系,这些关系有一定的结构规则,从而组成了语言系统。[5]语言的表达无法脱离于声音,并且声音的构成也是语词、语音、语义三者的统一,所以声音是语言的载体。作为80年代现实主义相声的代表,姜昆声音形象的建立侧重于其作品中幽默的语词和带有深刻讽刺意味的语义,由此脱胎成一种轻松欢乐的声音风格。这样的“欢乐之声”在当时的春晚舞台上是一种大胆的突破,更是大众的文化需求。80年代的中国刚刚走出“文革”的桎梏,大众渴望得到精神上的自由,呼唤心灵的抚慰。马季作为1983年春晚的主创人员,曾在筹备会上表示,“咱们春节晚会也别讲太多政治化的词,就是让观众笑痛快了,节过好了,晚会就成功了”。[6]由此可见,春晚在初期秉承的是为观众服务的文化自觉观念,而营造欢乐氛围则是实现这个目标的重要手段,“欢乐”成为这一时期春晚的主题,并且这一主题一直贯穿于整个80年代的春晚之中。所以姜昆的“欢乐之声”既符合春晚构建“欢乐”主题的内在机制,又满足了大众的文化需求。
但是这种“欢乐之声”,并非纯粹的娱乐化,声音的外在表象中仍裹挟着传统播音式的正统与崇高。由此,以姜昆为核心的第一代春晚主持群体也与20世纪80年代的审美范式形成了一种呼应。80年代的中国社会充斥着“文化热”“美学热”的气息,审美与文化的概念开始渐渐渗入日常生活之中。从某种程度上看“美学热”和“文化热”在当时强化了大众的传统审美主义精神。“那时的美学主流认定:审美(包含艺术和其他审美活动)是精神性的甚至是形而上意义的,它指向一种不同于现实世界的‘第二自然’,追求一种超然于日常平庸人生之上的纯粹精神体验;同时,审美活动追求无功利,既不以满足人的实际要求为目的,也不以满足人的欲望本能为归宿。”[7]时间赋予了声音特定的历史标记,姜昆作为春晚主持人的声音形象虽然从内部语义构成上来说是一种通俗化、大众化的状态,但总体上仍具有播音和报幕式声音的正统、崇高风格,符合那个时代对“纯审美”范式的追求。20世纪80年代,电视尚属一种新兴媒介, “三转一响”式生活使得收音机里飘出来的播音腔仍旧是当时大众的美学信仰,这种声音勾勒了当时人们的生存空间与文化空间,对人与人、人与时空的关系起着决定性作用,它是时代的声音符号。因此,姜昆程式化、正统化的主持声音在当时广受好评。但同时值得体味的是,姜昆的声音风格是正统中穿插戏谑,崇高中流露通俗,这种极具个人特色的声音形象背后似乎隐匿着一股与主流审美范式相较量的暗流。这既是80年代文化复杂多元的表征,也是春晚文化机制制衡的需求。
(二)同构调和中的家—国之声
春晚主持人的第二代格局是以赵忠祥、倪萍这对黄金搭档的出现为标志,这也昭示着春晚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固定主持人阵容。赵忠祥和倪萍的时代,是主导话语依靠声音的时代,人们消费或捕捉到的,主要是他们的声音,而不是图像。[8]
麦克卢汉在其“听觉空间”概念的论述中强调了声音的包容性和发散性,声音中所带有的审美特征是对文化内容的一种包含,同时随着其线性的流动也触发了人们的联想。赵忠祥的声音沿袭了80年代电视精英美学的风格特点,将儒雅与庄重注入醇厚与激昂的声音之中,其声音里涌动着的雄性气息为他印上了男性—父亲的标志;江河大川在他的声音中变得具体,触发了人们对于民族、国家的想象。“父亲—国家”的形象在赵忠祥的声音里得到了高度统一,更有人直接将赵忠祥的声音称作是“国声”。较之赵忠祥颇具说服力和引导性的“国声”而言,倪萍的声音充斥着宣泄的“母性”,总是可以撞击到人们内心深处最柔软、最脆弱的地方。她的声音属于唠家常式的平稳音调节奏,建立了一种饱含情感的声音形象。回顾倪萍的春晚主持经历,留有浓墨重彩痕迹的无不是她在舞台上的个人叙述和独白。在她的声音叙述中有器皿里奔腾的黄河水,有全家福中60年变化的家国,有奖杯背后展示中国雄姿的马家军……她的声音里充满了温暖与感性。如果说赵忠祥是“国声”,那么倪萍则可以看作是“家声”,她和赵忠祥的声音配合呈现出了个人叙述方式对那个时代理想和情感的重摹,是同构调和下的家—国之声。
赵、倪组合构建的时代之声是两人声音相互调和、阴阳并举的结果。赵忠祥在春晚中的“国声”形象带有强烈的政治指向,笃定浑厚又颇具说服力的声音充斥着一种强制的力量,而这与90年代后期盛行的大众文化风格显得有些格格不入,“国声”与大众的疏离感逐渐显露出来。实际上,赵、倪二人的时代可以看作是一个声音为主导的话语时代,“家—国之声”之所以能撑起整个90年代的春晚舞台,很大程度上与倪、赵两人的声音调和有关,倪萍柔缓的声音中弥散着抚慰和激励的情感力量,从某种程度上平衡了赵忠祥声音中的强制力量。随着市场经济的转型和发展,90年代开始进入了“泛审美”的阶段,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生活体验成为审美资源,二是日常生活的审美化。“泛审美”最大的特点是世俗化、生活化、平民化成为新的审美倾向,审美趣味从理性沉思步入了感性愉悦的阶段。赵忠祥庄重、崇高的声音仍旧是80年代的“纯审美”特质,而倪萍富有感性色彩的、日常化叙述的声音恰恰是90年代“泛审美”的产物,两者声音的并置与调和也反映了90年代审美范式转向的过渡以及“泛审美”问题在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复杂存在。
在现实中,声音的产生是真实的、自然的,但也是杂乱的、无序的,如果要让声音表达特定的意义、传递特定的情感,就必须将声音转化成为一种有序的、有意味的形式。[9]赵、倪二人的“国—家”声音形象不仅是两人在节目主持领域的成功,更是春晚运行机制的成功。20世纪90年代市场价值观的确立以及消费文化的出现,使得人们在追逐利益的过程中,对个体身份的认同产生了困惑。因此,90年代的春晚已不仅是一台以欢乐为主的综艺晚会,它需要承担起重构家国意识、提供改革合法性证明的责任。赵、倪的声音组合中以赵忠祥的“国声”来强调“国家”的在场性,以倪萍“家声”的文化想象填补了因社会发展带来的种种隔阂与矛盾,同时也掩饰了“国声”传递中意识形态的强制性力量。这样的声音组合既抚慰了民众的焦虑心理,也完成了特定的政治任务,符合人们对于春晚的文化、政治想象,满足了春晚运行的内在需求。赵、倪二人造就了一个时代的“电视之声”。
(三)全球化视域中的崛起之声
进入新世纪以后,朱军、周涛、李咏、董卿接下了赵忠祥和倪萍二人的主持接力棒,并逐步形成了与国家民族发展同构的崛起之声,在全球化的语境之下,以力量、前行、生机与活力为春晚表征新的中国性建构了话语基调。
朱军和周涛在继承赵、倪二人声音体系的基础上弱化了宏大叙事,在“家声”与“国声”之中寻找到平衡点,既呈现出砥砺前行的力量,又流露出温暖亲民的特点。朱军在继承赵忠祥雄浑音色的基础上,弱化了声音中的压迫感、强制性与英雄气势,平稳略带上扬的音调与日常化的叙述使得朱军的声音兼具感召力和亲和力。2005年春晚零点报时环节,当朱军温情说出:“此刻,我们凝望着母亲的白发,抚摸着孩子的笑脸……”时,“想象的共同体”的建构方式已从国家话语逐渐被置换为家庭叙事,在他的声音里,“国家”不再是被强加的一种意识形态认同,“家”才是大国想象的出发点。周涛相较于倪萍,声音中更添一份理性,对于情感的表达不再是倪萍式的肆意挥洒,而是一种收放自如,既有抚慰人心的温暖,也有坚定自信的激励。而主持人李咏则是以相对“欧化”的形象出现,瘦削的脸骨以及一头卷发,成为全球化镜像下中国青年亚文化崛起的一种象征。但李咏绝不仅仅靠视觉上的标新立异就能获得央视春晚重要的主持地位,而是以其欲望化、去节奏化的声音强化了其形象上所代表的青年亚文化中的娱乐和消费元素。主持人董卿声音的最大魅力在于清脆的音质使其声音充满了穿透力和张力,纯净、干脆、优雅、知性、柔缓都能在她的声音中得以协调与融合,这样的声音能连接传统与时尚,沟通本土与国际。她与李咏在春晚舞台上的唱和与配合,诠释了一种新的文化时尚。亲民、自信又富于感召力的声音传递出新世纪的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新地位和崛起的新力量;时尚、欧化又富于知性的声音也让日益强大的青年力量从文化边缘走入中心,为风靡于其间的亚文化、消费文化提供了合法性证明。
“崛起之声”打破了赵、倪二人在春晚舞台的“声音统治”。其中,一方面源于新世纪审美范式的转折。新世纪的中国社会进入了泛审美的后期,也有人称之为“后审美”。所谓后审美,即把传统美学认为割裂的艺术与生活重新联系在一起。[10]“崛起之声”所包含的多元声音折射出审美需求的复杂倾向,主持人的声音在不同程度上对市场、大众、官方等层面都进行了审美观照,逐步呈现出一些后审美风格的特征。但从整体上看,朱军、周涛、董卿三人在承接前一代主持人声音体系基础之上,仍旧呈现出一种较为传统的审美范式,有学者把这种现象看作是后审美语境中对传统审美回归。实际上,这样的观点似乎有些盲目乐观。传统审美范式所指向的崇高与认同是春晚舞台文化机制的内在要求,同时也折射出现象背后对于文化意义的争夺及其审美语境的复杂性。另一方面,“崛起之声”也是春晚从文化重构视域出发对全球化镜像的一种回应。如何应对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强势冲击与渗透,从而保持“中国性”的认同是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面对的最大问题。因此,文化共同体的建构显得刻不容缓。春晚作为联结全球中华儿女的重要文化载体,创建多元文化图景和高度的包容性成为其重要的文化策略,国际化趋向与大国包容成为春晚建构“大国想象”的两个特质,春晚主持人形成的“崛起之声”恰到好处地引导和构建了“大国”的文化自信与文化认同。
(四)“后时代”的喧哗之声
春晚主持人声音系统的再次转折出现在2018年春晚上,朱军、董卿等人的缺位使得表征不同文化意义的个体声音得到了更大程度的自由呈现。只是这样的声音不再执着于与 “春晚”的记忆、仪式或经验发生勾连,从而逐渐消解声音符号之于春晚意义的所指功能。“众声喧哗”的热闹与繁荣冲击着“春晚”原有的文化意味,一定程度上也弱化了其神圣性与唯一性。
文化所塑造的听觉欲望、倾向和想象将反作用于对当代声音的选择和塑造。[11]20世纪90年代末普遍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对文化艺术以及民间生活的影响使得我们进入了一种“后时代”文化——以创新的激情打破陈规俗律,解构一切却又没有重构的力量,“后时代” 的文化症候是无中心意识以及多元价值取向成为新的统领,[12]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实际上,“春晚”自进入21世纪以来,其作为文化领导的中心地位和认同权威在“后网络文化”的冲击下开始出现动摇,“春晚”一直试图在对话、协商、抵制、谈判的文化机制中对抗其危机。听觉空间通过各种汇集在一起的声音形成了一种文化场,在一定意义上成为社会关系或 “文化符号”的载体。[13]春晚试图利用多元的声音形成一种“听觉文化场”,以此来推动必要的对话与协商。在春晚的主持人阵容中,2002年李咏的加入使得其富于动感和跳跃的音律节奏与赵忠祥式的官方话语体系形成鲜明对比,加之其常年主持娱乐类节目,大众消费的色彩充斥着他的声音;2012年撒贝宁的出现也一改往日其在法制节目中的沉稳锐利,开始在“春晚”上“抖包袱”,声音轻松活泼,话语幽默机智,这种声音形象的反差让观众获得了一种听觉上的快感。
2018年春晚主持人群体的声音再次出现新的转折与尝试,呈现出明显的“去主调”特征,是一个没有层次之分的“众声集合”。这样的选择与安排,一定程度上彰显了主流媒体对把握“后时代”文化领导地位的决心。尼格买提和李思思的声音昭示着青年亚文化的动感与活力,康辉将新闻联播式的播音腔带入春晚,“正统”声音的延续是表征“春晚”在场和符号意义的确证,而任鲁豫和朱迅则延续了他们在综艺节目主持中亲民化的声音风格,再次填补了来自大众和民间的文化想象……多元的声音试图满足各阶层的大众对春晚的不同期待与想象,从而找到身份的归属和认同。而实现这种想象或认同的重要手段就是赋权,赋予最广大的受众阶层以话语权,春晚主持人群体各自声音的指向与代言则成为话语权合法性的重要确证。
多元声音体系表征了后时代的审美趋向,但随着朱军和董卿声音的淡出,2018年春晚主持人声音的“个体化”也将春晚另一层面的审美意义完全消解了。个体声音之间的关联性逐渐消减,并游离于春晚文化意味的声音系统,更多的是单一的个体呈现。“后媒介”时代赋予的声音越来越多,富于审美意味的声音已经消散,声音不再成为春晚话语体系中的主导,“听”的意义也逐渐由审美化转变为工具化。随着个体声音力量的突显,其整体失去了与“春晚”的勾连,春晚主持人声音系统的瓦解,也可能逐步消解整个春晚的神话。
二、声音神话的建构:仪式传播和想象认同
春晚不仅自身带有节庆仪式的神圣感,同时也赋予了这个舞台上的一切符号以神话色彩,以声音符号形式存在的主持人群体和春晚内在的文化机制一起共同建构起关于声音的神话。按照罗兰·巴特的理念来说,神话总是被记忆、叙述、媒介图像有选择地建构出来,世界给予神话的是一个历史性的现实,甚至可以人类生产或使用它的方式回溯一会儿;而神话所回报的是这个现实的自然意象,神话将本身的历史掏空,并用自然填充它。[14]春晚的声音神话在建构过程中,抹平了现实生活中的阶层差异,抚慰了现代性带来的焦虑,也将“春节”视域中的神圣与日常事物揉碎、重建、再融,加注到仪式与国族想象认同的熔炉之中,铸成为人所信服的神话。声音神话的建立造就了普天同庆的欢悦,仪式召唤弥补了心灵需求的不足,在天涯共此时的幻象中大众似乎真切地感受到了想象的共同体的存在。声音参与了春晚的仪式传播与国族想象认同的话语叙事,并以强化、延续和重构的方式缔造了关于声音的神话。
(一)延续与重构的声音体系
春晚声音神话的建立是从赵忠祥、倪萍二人在春晚舞台上的合作开始的。赵、倪二人声音的配合,呈现出声音景观中的家—国同构镜像,使“春晚”不再是20世纪80年代普通的节庆欢乐,其背后涌动着凝聚国族人心的巨大声浪,赵、倪的家—国之声也至此被赋予了神性的召唤力量。在那个以声音为主导的时代,赵、倪组合确立了春晚声音神话体系的雏形。
在春晚声音神话范式建立之后,赵、倪组合以长达十年的时间不断强化和延续着家—国同构的声音体系。米歇尔·希翁提出了声音的附加价值功能,即声音赋予了影像意义与价值,通过附加价值,一种声音丰富了给定的图像,从而创造出一种清晰的印象,[15]以至于人们看到赵、倪二人就会自然联想到“春晚”。朱军、周涛的声音组合是全球化语境中的崛起之声,虽然他们的声音和话语叙述方式相较于赵、倪二人有所创新,但依然传承了家—国之声的精髓,在新世纪的全球语境下进行着家—国建构。第二代的声音神话成功延续,并很快如赵、倪二人一般,成为春晚最具代表性的符码。这种延续的声音体系在春晚舞台上积蓄起强大的力量。因此,尽管新生代主持群体的声音都洋溢着鲜明的个性,但他们仍试图极力适应或靠近春晚之声音范式的整体风格,这样才能建立起与春晚的象征性关联,无论他们的这种实践成功与否,我们都需要承认声音神话确实被延续的声音体系建立了起来。
在文化格局与审美需求的不断变化中,春晚在延续声音神话体系的同时,也在进行着声音神话的重构。李咏和董卿颇具“文化符号”意味的时尚之声以全新的动感与活力,将个体的声音神话与大众传媒神话连缀起来,他们的声音不再是将民族国家的大好河山“崇高化”,而是将新千年后如火如荼的消费文化和全球化态势填充在话语的表述之中,凭借外部信息和主观意识的联结,声音为人们构建了一个充满大国想象的“拟态环境”,满足了人们在全球化进程中对国家以及自我的新认知。声音与文化达成了合谋,声音在无形中代替了视觉形象,也成就了大众敏锐的政治文化洞察力。因此,最大限度上满足多元的文化想象也成为春晚再续声音神话的新手段。在这种范式的指引下,声音格局不断被重构,但重构的声音格局是否能延续神话,仍是一个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
(二)声音的仪式传播
在人类学的视域中,关于“仪式”的研究主要围绕两个向度:其一是对古典神话和仪式的诠释,认为仪式与神话之间具有互文、互疏、互动的关系;其二是对仪式的宗教渊源和社会行为的探讨,一方面审视神话—仪式与宗教之间的历史纽带关系,另一方面探索作为宗教化的仪式在社会总体结构和社会组织中的指示性功能。[16]仪式的存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人们对所属群体的想象,在春晚的语境之下则是满足大众对国家与民族的想象。所以,神话的建构需在神圣的仪式召唤之下完成。
仪式化的表达首先是建立在特殊的时间点上。春晚承载的元素包含着春节特定的含义。春节,作为一种节日,是被神圣化了的时间线段,人类在这一时间线段中进行各种有意义的文化填补,以满足某种精神心理的特定需要,[17]而这些“文化填补”则是诸如祭祖、拜年等仪式。改革开放以后,传统家族仪式所连接的天、地、神、人的观念及其实质在现代社会中的衰落,[18]随着大众传媒技术的不断发展,电视拥有了弥补这一空缺的机会与能力。因此,春晚自然而然地成为春节仪式的新组成部分。而声音因其所具有的“时间性”特点,在描述时间流程和营造特殊时间方面有很大的优势。从广义上看,声音在表现“时间性”的时候,可以扩展到不同的“时代”;从狭义上来说,声音在表现 “时间性”的时候,可以表现在生活的各个“具体时刻”。而不论某个时刻还是某个时代,通过“声音流”都能为观众构建一个独一无二的文化场。[19]声音表述的连续性使整个春晚仪式流程顺利进行,零点报时环节的声音表达就是对仪式时间重要性的具体诠释。
零点报时在春晚三十多年的变迁之中,一直占据重要地位,具体时刻的声音现实与屏幕相连接,甚至构成了一个新的视觉空间,观众由声音获得感知,由声音产生的“联觉”效果获得一种“视听”感受,一定程度上将零点报时环节神圣化。为了使其神话色彩更为强烈,主持人还会在其中加入大量的国家、民族叙事,逐渐营造出一种天涯共此时的同质时空感,让全球的华夏儿女感受到想象的共同体的巨大凝聚力。关于春晚的这种仪式呈现,赵忠祥和倪萍的合作是一个颇具说服力的表征元素。在两人合作的整个90年代春晚期间,大多数情况下,赵忠祥承担的是关于政治性的仪式表述,而倪萍则是将日常叙事中的私人空间“家”和个人情感裹挟在声音形象之中。而在零点报时的重要环节,这种重要政治性表述通常是由赵忠祥和倪萍两人配合完成。因此,他们的声音里也自然带上了由政治性置换的仪式神圣色彩。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声音神话的建构离不开神圣的时间基础。也正因如此,掌握了零点报时权力的声音才有可能续写神话。
仪式化表达也离不开特定内容的支撑,每年春晚开场的定场语和“全球贺电”环节也成为一时传播的特定话语。春晚的“直播”特性使其与播客或录音不同,听现场的声音能够让人想象我们正在做什么。每年春晚的开场,主持人都会以极具感召力的声音来刻画全世界中华儿女的在场性,利用民族与国家的隐喻性表述,调动最广大受众的民族感情与文化记忆,通过语义与语词的指引性以及语音上的感化建构由声音带来的神圣仪式,并使每个声音接收者都成为仪式的参与者。贺电环节出现于新千年之后,不可否认,这一流程的设置使仪式的呈现更为具体。声音本身并不具备实体的空间性,它只是具有“时间”上的连续性和运动性,但声音能使得听众在感受声音整体所展示的运动规律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空间想象,[20]当主持人播报着外国大使馆及外国领导人发来的贺电时,人们进入了“万国来朝”的空间想象之中。可以说,这种仪式化的表达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应对全球语境下文化霸权态势的一种软性冲击,让走向世界的中国重新书写了“中国性”。春晚主持人声音的仪式化呈现,似乎承担起了彰显文化软实力的历史重任,无形中强化了神话的色彩。
(三)声音想象与国家民族认同
春晚主持人的声音神话不是凭借某种外在形式便可成就的,其神话叙事的核心内容也是重要的构成因素。春晚主持人声音神话的内核即是对“想象的共同体”的指意。春晚从最初的节日联欢会到今天的“新民俗”,承载的内容已经不仅仅是欢乐。抛开意识形态的因素,春晚已成为一年一度的 “中华民族”“中国” 集体想象的仪式,“春晚”存在的理由,可以看作是为“中华民族”这一“想象的共同体”搭建了一个“心理事实”的虚拟平台。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中对民族界定为:“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21]首先,这个共同体是“想象的”,因为内部成员无法彼此都认识,但是相互联结的意象却存在于每个成员的心中;其次是“有限的”,因为没有任何一个民族会把自己想象等同于全人类。[22]由此可见,“想象的共同体”建立,一方面需要内部成员有相互联系的认知,形成集体想象,另一方面也要强化对本民族与国家的认同感。
春晚的历史政治功能之一就是将无数个“小我”纳入集体的“大我”之中。无论春晚主持人的声音如何更迭,春晚的集体想象功能都不可能被忽视,而且正因为声音的线性流动,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变化,流动的声音已成为生活中的隐喻,每个声音都有能力建构自己的形象和记忆。想象力让我们成为自己身边的人,通过一连串的声音与现在的自我联系在一起,使得大众建立了一种彼此相连的幻象,强化了对于“想象的共同体”的认知。每当主持人发出“全球中华儿女”的召唤时,人们都会自觉地将自己纳入其中,感知到彼此的存在。而这种召唤在四代主持人的声音中从未中断。
对于国家民族认同,声音神话在这方面的实践手段主要是通过话语的修辞转换与隐喻,以及被赋予的声音发出者的权力来实现的。赵、倪二人声音神话的成功建构恰恰是对转喻、隐喻修辞的得当运用,使得人们的认同感由传统的家、故乡、地方等延伸到整个民族和国家,巩固了“想象的共同体”。但根据某种单一的范式来营构公共的声音世界,其模式最初出台时,在一些人眼中固然是新鲜十分,可是很快它就证明自己是一个集团、一种趣味的独裁,也是一种声响意识形态对另一个耳朵的独裁。[23]因此,在春晚的发展过程中,声音的协调搭配与多元呈现也是对整个民族认同意识的考虑,而这种民族认同又常常被转嫁到社会各阶层的文化与身份认同之中,以此来呈现民族共同繁荣的景象。声音表达的目的就是借由声音带来的不同感受和信息,使接受者去领会更多超越“传达”层面之上的主观表达信息,所以诉诸听觉的春晚的声音神话,能让大众体会到形式层面之上的关于国家民族的想象与认同。
三、声音勾连的象征体系:文化场域与意义空间的划分
“场域”这一概念源起于物理学,随后被引入到社会学领域。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认为,“从分析的角度来看,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24]场域是一个充满争斗的空间,布尔迪厄认为场域中存在着积极活动的各种力量,它们之间在不断“博弃”,[25]声音折射出的文化意味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同文化力量的象征与博弈。声音不同于语音的地方在于其拥有语音的所有外在表征,但同时拥有意义与价值,人类世界的各种声音像依据某一种音乐调式和谐地交织排列在一起,以其中一个音为主音(中心音、核心音) ,其余各音围绕主音形成一定的体系,成为某一特定地方人们生活方式、文化样态的折射反映。[26]从春晚主持人声音体系的流变中,可以看到春晚所形成的“文化场域”中力量的多元化与此消彼长。在这种繁荣景象的背后,实则是多方力量在文化场域内意义空间的争夺,但各种力量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制衡关系。
20世纪80年代姜昆所代表的“欢乐之声”在播音腔的一板一眼与相声的幽默中跳进跳出,前一刻他还是手握话筒声音洪亮的报幕员,下一刻他又成为偷吃王景愚道具烧鸡的“泼皮户”,由此引出哑剧小品《吃鸡》。他在看似主流文化允许的范围内说着自己的俏皮话——打趣演员,调侃节目,隐喻着一种来自民间的文化力量,对主流文化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消解。90年代的赵忠祥与倪萍被称作是中国式的声音神话,在商业主义与消费主义日益占据文化空间的背景情况下,他们代表着官方的声音,通过声音的神性来填补现代社会中传统家族仪式所连接的天、地、神、人的观念及其实质的空缺,为主流文化扩展了极大的存在空间。赵忠祥所特有的庄重声音代表的父亲和国家形象是主导意识形态的符号,而倪萍的声音平稳而亲切,使得她可以在各种身份间转换,忽而代表农民,忽而代表工人,忽而代表母亲,忽而代表仪式司仪……在这种转换之中,官方、精英、民间、大众的声音都被带到了春晚之上。进入21世纪后,李咏代表着兴起的消费文化、尼格买提代表着民族文化包裹下的青年亚文化,董卿则在其朗诵语调与谈话语调的自由转换中完成了大众对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的想象,朱军和周涛则以各自的表达策略继续为主流文化发声。“声音”作为文化符号的一部分,在每个时代都参与文化空间和社会空间的营造,由此看来,听觉文化下的春晚不只是国家实现意识形态表达的工具,更是通过声音的意义生产与再生产的完整传播过程,成为国家、大众传媒、商业市场和民间大众等多种力量竞争与协商的文化场域。
声音是协调一致、取得力量平衡的象征,声音文化在意义空间内争夺的目的在于取得文化平衡,而这种文化平衡与隐藏在春晚背后的文化领导权紧密相关。文化领导权是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提出的概念,指的是社会集团通过在社会成员中“发展共同的理念、价值观、信仰和意义——即共享的文化,在此基础上组织赞同”的方式来实现其领导权,葛兰西在论述中强调了“认同”的重要意义,而春晚诞生的最大动因,就是要在新的历史叙事中,为民众创建一种新的认同形式,[27]文化平衡则是实现认同的有效手段。文化领导权的实践不能只看作是国家意识形态的编码策略,事实上还包含着大众对这种编码的认同和抵抗性解码,这是一个复杂的斗争与妥协的过程。
美国著名当代音乐理论家约翰·凯奇称所有的声音都是平等的,但事实上,大众对于多元声音的接受程度完全不同,有人当作乐音,有人则视为噪音,如何对声音表达进行有效编码在春晚主持人声音体系形成过程中不容忽视。从四代主持人声音的更迭中可以看出春晚主持人的声音表达策略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日常生活成了表征的主要内容,国、家、人三种叙事被交织在一起,以提供一种更亲切、轻松的叙述。
沙费曾经将倾听分为源起化倾听和语义倾听(也作编码倾听)两种形式,对于春晚主持人声音的倾听则属于语义倾听。主持人的声音信号被编码,而受众的兴趣就在于对信号的解码。随着大众文化的崛起,商业主义与消费主义逐渐抢夺话语权,大众面对主流化的声音呈现了一种抵抗性的解码态度——赵忠祥的声音过于压抑,倪萍的声音太过煽情。在斯图亚特·霍尔看来,编码和解码没有必然的一致性,所以在第三代主持人的声音形象定位上,如何能在保证文化领导权的基础上削弱大众的抵抗性解码,成为文化领导权实践中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第三代主持人从报幕员、播音员语音中脱离出来,用个体的声音开始对晚会的意义进行把控,对大众进行引导性的解码。2007年春晚舞蹈节目《小城雨巷》结束之后,董卿和李咏的这段串词则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董卿评价舞蹈“美轮美奂,充满诗意”,而李咏则说“让人有一种想起初恋的感觉”。舞蹈通过身体语言来表达意义,但是身体语言在理解上有很大的空间性,或者是模糊性,这就会使得大众在解码时产生与节目预设意义的偏差,主持人在这个时候成了意义的掌控者。但掌控并非绝对控制,而是多种意义的诉诸,从而保持文化平衡。董卿的声音代表了官方、精英文化的审美趣味,而李咏是代表大众的感性愉悦的追求,由此各种文化力量都得到了主流的认可,建立了一种平衡的认同形式。文化领导权的另一种典范式实践就是动情点的设置,这一设置的意图在于创造一种虚拟的人际性关系,通过将大众日常感情与春晚意义相结合,从而形成一种感情认同模式。这一点在20世纪90年代的倪萍的声音中显露无遗,从全家福的讲述、黄河水的采集、北京时间的朗诵再到其最后一次春晚上的国土汇聚,倪萍用声音将大众的日常感情升华为共同的家国感情,升华为对国家的认同。
代表政治符号和话语的声音则是春晚主持人声音体系中实践文化领导权的最直接呈现。春晚三十多年的历史中,新闻播音员曾经七度出现在这个舞台之上,最具有代表性的是白岩松与康辉。白岩松曾两度登上春晚舞台,第一次是在2000年担任嘉宾主持,仅出场一次。但在2009年的春晚中,白岩松占据了主要位置。从站位上来看,代替朱军站到了中心位置;从串词分量上来看,其主持的大部分都是仪式性节目,如对汶川地震的回顾环节等。在春晚的舞台上,新闻主播的声音具有较强的象征意义。2009年对于国人来说是有特殊意义的一年——过去的2008年,中国经历了汶川地震和百年奥运,而即将到来的是新中国的六十华诞。在这种特殊的时刻,需要营造“国家”在场的氛围,因此新闻主播声音的严肃性成为主流文化强调自身在场行为的有力确证。在第四代的春晚主持人声音体系中,虽然声音纷杂,但新闻主播康辉的声音却是清晰而明朗的。充满特定声音的空间就是一个进行文化政治活动的空间,因为其新闻联播播音员的身份使得他的声音自然地成为强势政治文化的符码,虽然在春晚舞台上其声音相对于新闻联播更具感染力,但因其声音较强的既有所指能力,仍会将受众导入主流文化的规训之中。
四、结语
在春晚历经的三十多年时间里,主持人的声音就是春晚的声音,它既是春晚的话语象征体系,也是中国当代社会发展近四十年的政治隐喻和文化镜像,更是建构了一个民族独特的集体记忆。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保证集体记忆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提取该记忆的延续性。[28]声音的呈现方式是线性化、连续的,所以在其构建时间感的过程中也将人们的记忆纳入其中,春晚主持人的声音体验通过表演仪式被赋予集体记忆的意义。
然而,从2018年春晚主持人声音格局的变化来看,集体记忆似乎已不再被春晚视为自救手段,如何维持其巨大的媒介影响力成为现今春晚的主要努力方向。媒介文化的极度膨胀与自我生产消磨着春晚的神圣性与唯一性,而恰是这种博弈和挣扎使得春晚成为中国当代文化格局中一个典型、独到的存在,构成了颇具象征意味的文化寓言。
注释:
[1] Michel Chion. Audio-Vision: Sound on Screen[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4 :157.
[2]朱晓军.电视媒介文化与后现代主义思潮[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9:111.
[3] [15]米歇尔·希翁.声音[M].张艾弓,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178.
[4] Stuart Hall. etc: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 and Signifying Practice[M]. Sage Publications Ltd,1997:16.
[5]项仲平.影视剧的影像叙事研究[D].苏州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8.
[6]王景愚.幕后[M].新世界出版社,1999:35.
[7] 傅守祥.大众文化审美化:从纯审美到泛审美的范式转换[J].天府新论,2006(6).
[8] 师力斌.逐鹿春晚——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和领导权问题[M].中国言实出版社,2014:47.
[9] 刘志新.用声音写作——论电影导演创造性的声音表意[D].上海戏剧学院硕士学位论文,2006.
[10] 耿文婷.融合相同的“后审美”[N].中国文化报, 2000-09-30.
[11] 王敦.“声音”和“听觉”孰为重——听觉文化研究的话语建构[J].学术研究,2015(12).
[12] 谷海慧.“后”文化时代的笑声——也谈《雷雨》“公益场”的笑场事件[J].艺术评论,2014(9).
[13] [19][20]姜燕.城市中的声音与影视创作[J].现代传播,2013(11).
[14] 罗兰·巴特.神话众文化诠释[M].许蔷蔷,许绮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202.
[16] 彭兆荣.人类学仪式研究评述[J].民族研究,2002(2).
[17] 耿文婷.神圣时间的镜像体验——春节联欢晚会的本土文化定位[J].现代传播,2003(1).
[18] 吕新雨.仪式、电视与意识形态[J].读书,2006(8).
[21] [22]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M].吴叡人,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
[23] 沃尔夫冈·韦尔施.重构美学[M].陆扬,张岩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2:5.
[24] 布尔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M].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133.
[25] 毕天云.布尔迪厄的“场域—惯习”论[J].学术探索,2004(1).
[26] 张聪.声音的乌托邦——R. M谢弗自然主义的声音理论及其批评[J].山东社会科学,2018(1).
[27]师力斌.逐鹿春晚——当代中国大众文化和领导权问题[M].中国言实出版社,2014:8.
[28] 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