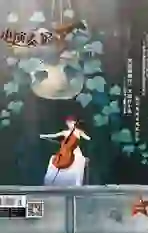云门舞集:生猛舞姿撞开逐日尘封的记忆
2019-11-22默默
默默

“黄帝时,大容作云门,大卷……”《吕氏春秋》如此写道。据说,五千年前的黄帝氏族崇拜云,纪事设官皆以“云”命名,因而产生了一种最古老的舞蹈——云门。只是岁月更迭、沧海桑田,曾经的舞本、舞容均已失传,只留下一个美丽诗意的名字。1973年春,一位年轻的现代舞舞者以“云门”为名创立了现代舞蹈团——云门舞集,他就是国际著名编舞家林怀民。《泰晤士报》曾评价他:“林怀民的舞不只是美丽,而是完美。”三十年后,云门舞集成为世界一流的现代舞团,有许多知名现代舞者自云门舞集发迹,如林秀伟、罗曼菲、刘绍炉等,这些知名舞者有的创办了现代舞剧团,如林秀伟创办了太古踏剧团、刘绍炉创办了光环舞集等。
用一生舞一曲中国魂
林怀民出生于台湾嘉义,少年时代的他是个才华横溢的文坛青年,十四岁时就以小说《儿歌》初绽文坛。也是在那一年,美国荷西·李蒙现代舞团来台湾表演,就此点燃了林怀民对舞蹈的热爱。
上世纪六十年代,舞蹈并不被看好,男生学跳舞更是一件不被家庭和社会认同的事。1969年8月31日,林怀民悄悄在行李箱里带了一双舞鞋飞往美国密苏里大学,1970年又转入爱荷华大学英文系攻读艺术创作硕士学位。在现代舞选修课上,林怀民终于穿上了那双随他漂洋过海的舞鞋,真正开始学习现代舞。
1972年,林怀民从爱荷华大学毕业,第二年毅然回到台湾,创立了云门舞集,那年他二十六岁。林怀民决心从中国本土文化出发编排舞蹈,他说:“中国人作曲,中国人编舞,中国人跳给中国人看。”
林怀民初期的编舞是从经典诗歌、神话中汲取灵感,舞蹈中带有叙事性,如《白蛇传》《薪传》《九歌》等,后来他逐渐发现叙事性有时并没有丰富舞蹈的表现力,于是他决定去除叙事性的舞蹈,更多地发挥舞者肢体的表现力,将观众与舞者的通感最大化。林怀民发现太极一招一式的身体律动很符合自己所寻找的舞蹈形式,于是便有了以太极导引为基础创作舞蹈的想法,为此他创新了一套独特的舞蹈教学方法:练习静坐、气功,舞蹈动作只教最基本的。刚开始,舞者们很不适应,林怀民说:“我鼓励他们尝试让身体跟地板接近,呼吸吐纳,就像写毛笔字,进行了这些训练以后,舞者身上忽然多了很多种语言。”
这项训练的成果就是舞蹈《水月》,两吨多温水漫溢了整个舞台,舞者在水上从容起舞,东方韵味流露于张弛之间。在巨大镜面的映射下,虚与实的距离被弥合。“水光潋滟,对影成三人。”这支被马友友、蒋勋等艺术家激赞的舞蹈《水月》演遍世界舞蹈重镇,被誉为“当代舞蹈的里程碑”,这也是林怀民“为了解救自己”而进行的突破性创作。
除了让舞者通过打坐的方式学会调息,找到平和的舞蹈气息外,林怀民还延聘名师,让云门舞者每周定期练习书法,在横竖撇捺的笔画间感受肢体运动的美妙,之后便有了《行草》《松烟》等以书法投影为背景的舞蹈作品,舞者玄衣舞动,气势庄严。其中,舞蹈《松烟》走上淡雅写意的路子,动作讲究由重到轻到飘逸的层次,追寻毛笔书写中墨分五色的境界,字有多少种写法,舞者的身体就有多少种动法,这是临摹,也是礼赞。舞台上,历代书法家的手迹以君临天下的姿态出现,舞者则以身形舞姿临摹王羲之“永”字破题呼应书法婉转的线条。林怀民形容云门舞蹈的特点是松,跟书法一样,观之让人有一种自在的感觉。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云门舞集拥有两个团,一团负责全球的演出,二团则负责走进校园、乡下,开展舞蹈普及工作。一开始,这种舞蹈普及工作并不被看好,但事实证明好的艺术可以打破所谓精英与普通大众的藩篱,在露天的舞台、学校的操场,云门舞集的舞者们为普通民众演出。林怀民的作品走到户外,与天地融为一体,艺术的灵感来自天地,至高境界就应该回归自然,尽管很多人看不懂,但是一样觉得震撼、感动。林怀民希望能够为大众展现一种不一样的生活方式,也正是由于这一朴实的理想,使云门舞集和民众建立起非常亲密的关系。
2008年春节期间,承载着云门舞集十几年梦想的铁皮屋排练场遭遇火灾,所有的东西都毁于一旦。消息一传出,有四千多家单位和个人向云门舞集捐款,希望他们可以拥有新的排练场继续跳下去。林怀民说:“这是社会给予我们的期望,这个担子是沉甸甸的。”
2014年,新的云门剧场落成,在剧场进门的一面墙上刻着捐款人的名字。为了回报社会,这里除了作为云门舞集的剧场,也供人们观光,并引入其他舞团,邀请其他青年舞者、编导来这里表演,而云門舞集回报社会最好的方式便是拿出更好的作品。
如今,云门舞集已经走向世界,在纽约、巴黎、伦敦、柏林等地巡回演出,同时他们也在社区演出,表演的内容与其他地方一样。林怀民说:“留住那些来看舞蹈的老人、小孩、村民等群众的笑容,这才是我继续做这件事的动力和初心。”或许,这就是艺术最好的归宿。
林怀民成就了云门舞集,云门舞集也成就了林怀民。
反骨的号叫,生猛的街舞
旧时,台湾艋舺街头有位传奇人物,只要他一现身,街坊邻里无不奔走相告,人们将他团团围住,竖起耳朵,摩拳擦掌,只为听他那忽男忽女、幼声老嗓的百变嗓音,每到精彩之处,人们无不拍案叫绝,这位传奇人物就是那个时代最生猛的人,人称“十三声”。
十三声的故事是郑宗龙的母亲讲给他听的,每每忆起,郑宗龙总能想起小时候和父亲在艋舺摆摊卖拖鞋的日子。在那段清贫岁月里,郑宗龙学会了手舞足蹈地叫卖,看街坊邻居嬉闹,看暗夜里的霓虹灯闪烁……这一幕幕生猛的市景始终在他的记忆中骚动。如今四十年过去了,为了找回记忆中那段生猛岁月,郑宗龙想尽办法将这些记忆编织成舞蹈《十三声》。在他看来,这支舞只能生猛着跳,因为越生猛才越鲜活,也越迷人。郑宗龙说:“我不会用文字准确地形容脑海中的一些记忆,所以试着用舞蹈,把水面倒映的景象用身体、用声音呈现出来。”
郑宗龙是谁?林怀民的接班人,云门舞集2的领军人。林怀民说:“云门舞集2是年轻的,他们是吃汉堡、打电动游戏长大的,他们的世界和我们不一样,我的世界没有这么宽广。他们是这个时代的年轻人,作品里没有传统的包袱,没有历史的紧张和内敛,只讲生活,因此很轻松活泼,没那么紧绷。”
云门舞集2是林怀民在1999年云门舞集创立二十六年周年时,为年轻编舞家及舞者提供的舞台。在郑宗龙的带领下,云门舞集2的舞者们敢于探索自己潜藏的能量,他们比云门舞集的舞者反骨,舞姿也更生猛。不仅如此,他们还得学会吟唱,大胆地号叫,他们不再害羞,而是像婴儿般诞生在中国这片土地上,他们是新的,拥有一股与生俱来的纯粹力量。
幕启,十一位舞者舞动着看似荒诞不羁的舞姿,他们的队形有时对称规整,有时又忽然变得无序。他们佝偻着身体,手脚扭曲,时而愤怒地跨步向前,时而静谧地碎步后退。伴着舞者的号叫,街头卖场旋律伴着电音响起,女舞者吟唱起古老的小调,男舞者喃喃地念唱着道坛咒语,极尽所能,毫无保留地释放着体内的能量。这一切就像街头每一个微小的生命,我们努力工作、奔波、打拼,为的不就是更好地活下去吗?这一刻我们仿佛不是坐在剧场,而是置身于一个鲜活的街头。
郑宗龙在舞蹈《十三声》里所要传达的是平凡岁月里人性共通的那部分,每个人都是鲜活的,都是生猛的。
舞蹈是他们的宿命
郑宗龙说:“一开始《十三声》曾让我陷入一种难以名状的情绪,闽南话中的‘见笑带有几分羞耻感,而我的这种羞耻感来自于庶民肢体对比英挺芭蕾的反差呈现。然而,每个人天生就带着某种印记:出生地、喜好、生活习惯……我们生在中国,扎根于这片黄土地,我们最优美的舞姿表达也来源于这片大地,它和西方直线向上的肢体语言不一样,它更包容,也更扎实。”
舞台的背景不断变幻,一条肥大的锦鲤穿梭游走在舞者之间。一开始,舞者一身黑衣,锦鲤身上也只有自己本来的斑点,可当舞者的舞衣从黑色幻化为七彩荧光后,锦鲤身上也开始染上各种颜色,二者你追我赶,关系忽近忽远,直至最后,锦鲤尾巴一甩,舞者身上的七彩荧光也随之被一下子甩掉,只留下自己最初的斑点。
人们身上的标签就像包袱,是岁月留下的痕迹,可无论何时何地,每个人身上最初的印记一直都在。不论生活带给我们多少迷茫和挣扎,不论我们去哪里、有何种经历,只要人还在,我们就和那条锦鲤一样,终将在镜子面前看到那个最真实、最初的自己。
是啊,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去哪里?這亘古不变的问题时刻鞭策着我们。对于郑宗龙来说,云门舞集必须永远年轻,而舞蹈就是他们的宿命。
2020年,郑宗龙将从林怀民手中正式接手云门舞集,很多舞迷都很关心云门舞集的舞蹈会不会继续跳下去,郑宗龙说:“只要有人邀请,当然会继续跳。不过舞蹈与创作者的联系很密切,人在舞在,林怀民老师退休以后,很多云门舞集之前的舞蹈要再现难度很大。”
舞蹈是什么?在很多人看来,它是瞬间的艺术,舞者的一个动作、一个眼神、当时当刻的感悟,只要舞台灯光一熄,人群一散,一切都将停止,稍纵即逝。这就像我们看到某刻月圆、听见某朵花开、遇见某个人时,心中泛起杂绪,有了惦念和感悟,这都是当下的念头。那么,云门舞集会消失吗?郑宗龙说:“没有什么会永存,但只要当下你是年轻的,你是生猛的,舞者不休,云门不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