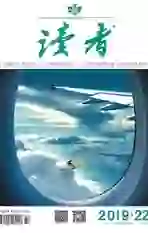二士共谈
2019-10-31张定浩
张定浩

整个二月都在下雨,冷雨不断地把就要来临的春天打回去,春寒料峭,有时比冬天的严寒更令人沮丧。我坐在房间里,会想到年轻时的海明威,这样的早春冷雨,也是巴黎唯一令他觉得悲哀的时刻。他那时待在巴黎一个旅馆的顶层小房间里写作,写不下去的时候,就会坐在炉火边,剥个橘子,把橘子皮里的汁水挤在火焰上,看毕毕剥剥蹿起的蓝色火焰,然后,他会站在窗前眺望千家万户的屋顶,并对自己说:“别着急。你以前一直这样写来着,你现在也会写下去的。你只消写出一个真实的句子就行。写出你心目中最最真实的句子。”
是啊,真实的橘子,真实的句子,它们都毕毕剥剥地引发蓝色的火焰,在火盆上,在稿纸上。我有时写不下去,就会想到这些。
柏拉图在《会饮篇》里曾借阿里斯托芬之口讲过一个关于爱欲的故事:最初的人完整而强大,宙斯因为恐惧,才将一个完整的人劈成两半,但人依旧不死心,从此在世间寻找彼此,结合,力图重新成为一个完整的人。这种不完整的个人在此世对完整的追求,是日后西方人生活的一个重要推动力。
但中国人思想里从来不是这样。中国人似乎从一开始就懂得,妄图把完美集中在单个人身上是危险的,况且,单个人也不堪负担全部的好。譬如挑水,执其两端而用中。中国思想最深处的好,几乎都是由两个人共同担负的,例如尧与舜,孔子与老子,李白与杜甫。
杜甫写给李白的诗里讲,“遇我宿心亲”,这是说遇到一个和自己一般好的人,却不要合二为一,也不要取而代之,你还是你,我还是我,只是心里多了一份没来由的欢喜。
“李供奉、杜拾遗,当时流落俱堪悲”,而自中唐以来,李杜文章,光焰万丈,几近成为中国诗的代名词,进而,对这二人的比较和评断,也成为一代代文人必须要面对的问题。在我看来,这其中的奥秘,并不单归因于这二人诗才的杰出和广大,更重要的,是他们在真实的相遇中所构成的关系,犹如梅列日科夫斯基在形容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关系时所说的,“像是两块对立竖放的镜子,无限地反射对方、深化着对方”。李杜之于我们,并非赛诗会上两个顶着花环的胜利者,只是两个人执手相见,而整个中国诗的光谱,就在这样的相见中,在无限的反射和深化中,完整地呈现出来。
因此,比较和评断他们,也就是认识自己在整个光谱中的位置,这样的比较和评断,并不通往孰优孰劣的终极判断,而只通向个人身心的安放。这一点,其实很多过去的文人都是懂的,比如王安石好杜而欧阳修好李,苏轼好李而苏辙好杜,但这种出自趣味的喜好,并不会让他们就此贬低另一个。再往后,一些更客观细致的分析,譬如严羽所谓“子美不能为太白之飘逸,太白不能为子美之沉郁”,王世贞所谓“五言律、七言歌行,子美神矣,七言律,圣矣;五七言绝者,太白神矣,七言歌行,圣矣”,刘世教所谓“陇西(李)趋《风》,襄陽(杜)趋《雅》”,与其说是在细辩优劣,不如说是在传递他们对中国诗的认识。
至于二人之间相互的毁誉,被编排最多的就是杜甫写给李白的那句“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有以为杜甫在讥刺李白,也有替杜甫遮挡解脱的,我都只当好玩的八卦看,心里喜欢的是洪迈《容斋随笔》里的光明洒然:“《维摩诘经》言,文殊从佛所将诣维摩丈室问疾,菩萨随之者以万亿计,曰:‘二士共谈,必说妙法。予观杜少陵寄李太白诗云:‘何时一樽酒,重与细论文。使二公真践此言,时得洒扫撰杖屦于其侧,所谓不二法门,不传之妙,启聪击蒙,出肤寸之泽以润千里者,可胜道哉!”
(厝 山摘自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既见君子》一书,康永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