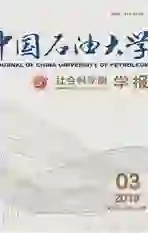仲裁时效期间可约定性问题研究
2019-10-10濮云涛
濮云涛
摘要:仲裁时效和诉讼时效的立法价值存在差异,仲裁时效涉及的公共利益范围较窄,更注重维护当事人意思自治。约定仲裁时效期间的性质不属于附期限的仲裁协议,而是当事人对相对权的处分,这表明约定仲裁时效期间并没有超越权利行使的合理范围。约定仲裁时效期间能够克服时效法定性的瑕疵,有利于推动仲裁的高效进行。应允许当事人在一定范围内约定较短或较长的时效期间。在较短时效期间届满后,当事人仍然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
关键词:仲裁时效;诉讼时效;时效期间的法定性;公共政策;意思自治
中图分类号:D9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9)03-0045-07
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仲裁法》第74条规定:“法律对仲裁时效有规定的,适用该规定。法律对仲裁时效没有规定的,适用诉讼时效的规定。”由于我国法律对仲裁时效没有特别规定,现行法制背景下具体案件中出现的仲裁时效争议应当适用我国法律中诉讼时效的规定。对于诉讼时效的期间,我国民法界占主导性的观点是诉讼时效的期间具有法定性和强制性,当事人约定诉讼时效期间的行为无效。这种约定包括当事人约定延长或者缩短诉讼时效期间。以此为理论基础,从我国的《民法通则》到最近颁布实施的《民法总则》,均体现了时效期间的法定性和时效利益的不可放弃性。在制定《民法总则》的过程中,部分学者对诉讼时效的法定性提出了质疑,因很多国家的立法允许当事人约定时效期间。尽管最终《民法总则》不允许约定时效期间,但时效期间的可约定性问题在学术界仍然存在争议。
虽然我国《仲裁法》目前对仲裁时效没有规定与诉讼时效不同的内容,但是“仲裁时效”这一概念本身与诉讼时效就有概念和价值方面的差异。我国修订《仲裁法》时对仲裁时效的可约定性问题做出与《民法总则》不同的规定具有立法上的可能性。仲裁作为兼具一定强制性和社会性的争端解决方式,其在国际争端解决中的独特性越来越明显。随着临时仲裁、友好仲裁等国际通行仲裁制度在我国逐渐得到承认或默许,仲裁的非诉讼化是我国国际商事仲裁的重要发展趋势,当事人意思自治也得到充分尊重。因此,从立法目的、学术理论、比较法研究、仲裁独立性等角度出发,有必要对仲裁时效的可约定性问题进行专门讨论,以进一步提升我国仲裁法制的国际化,为“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建设提供有力的制度保障。
二、仲裁时效的立法价值特性
明确仲裁时效的立法价值是建立和完善具体时效规则的基础。仲裁时效和诉讼时效在立法价值方面具有共性:其一,维护现有的交易秩序和公共利益,避免“不公正的惊吓和陈腐的请求”[1];其二,避免由于时间过于久远而使举证更加困难,减少证据保存负担;其三,促使权利人积极行使权利,避免权利滥用。虽然仲裁时效和诉讼时效具有立法价值上的共性,由于二者的载体不同,其立法价值不无差异。本文着重分析仲裁时效在立法价值方面的特性。
(一)涉及公共利益的范围较窄
相较于诉讼时效,仲裁时效制度涉及公共利益的范围较窄、程度较低。就立法功能而言,诉讼是国家公权力对私人权利的最后防线,注重维护国家的司法管辖权和当事人的基本权利;商事仲裁是基于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争端解决机制,目的是便捷、高效和秘密地解决纠纷。诉讼注重“定分”而仲裁注重“止争”。[2]“定分”对未来发生的同类案件具有或多或少的影响力,而“止争”的效力仅涉及该案。因此,诉讼涉及的公共利益在功能范围上宽于仲裁涉及的公共利益。
就受案范围而言,民事诉讼涉及的领域较广,既包括财产权益纠纷,又包括人身权益纠纷和混合类纠纷(如知识产权纠纷),其中的人身权益纠纷往往与人的基本权利相关,具有较低的处分性,与社会公共利益关联度较高。商事仲裁处理是基于商事合同的履行而引起的纠纷,不涉及婚姻、继承等人身权益纠纷,回避了与社会公共利益关系密切的案由。值得注意的是,仲裁中的国际投资仲裁①
与一般的商事仲裁相比,由于东道国可能承担巨额赔偿责任,因而其具有一定的公共利益属性。与此同时,国际文化遗产交易纠纷仲裁涉及国家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因而在该问题上国家更注重法律规则的强制性以维护文化遗产的社会效益。各國立法对可仲裁性的限制更宽容,因而原本不允许仲裁的领域也在逐渐突破,例如消费者纠纷、劳资纠纷、反垄断争议等。如果允许当事人就这些争议约定时效期间,可能存在对与公共利益相关的债权债务稳定性的干扰。
① 本文涉及的国际投资仲裁是指东道国和投资者之间的纠纷提交的仲裁。
“诉讼时效关乎公共利益和法律秩序的统一”[3],商事仲裁时效更侧重于当事人微观权利的保护。诉讼时效经常涉及公序良俗和当事人的人身权益,例如人身伤害损害赔偿。法律为了防止具有优势地位的当事人滥用权利,不允许当事人约定诉讼时效期间,以维护基本的法律秩序。再如排除妨害请求权不适用诉讼时效制度,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公共秩序的考量。相比之下,商事仲裁以民商事主体的自愿和平等原则为基础,仲裁裁决的效力仅涉及当事人,影响社会公共利益的可能性较小,不太可能出现一方利用其优势地位迫使对方接受较短仲裁时效的情形。公共利益是仲裁时效制度的最后防线,仲裁时效立法只需保证最低限度的公序良俗。公共利益体现的安全价值,其在仲裁时效立法中的价值位阶较低。
(二)更注重维护当事人意思自治
仲裁和诉讼维护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程度不同。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包含处分原则,强调一方当事人的单方自主选择,而非双方合意。民事诉讼法的调解原则虽然是双方当事人合意的体现,但是意思自治仅仅是民事诉讼的补充。就仲裁而言,维护当事人意思自治是商事仲裁的首要价值,契约性是仲裁的本质属性。仲裁裁决的执行以法院强制执行为保障,也是由其契约性衍生而来。因此,民事诉讼以国家强制力为基础,以意思自治为补充;商事仲裁以意思自治为基础,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
在明确意思自治在诉讼与仲裁的主从关系的基础上,诉讼时效和仲裁时效在维护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程度上有显著差别。诉讼中法院可依据职权调取证据,如果距离法律事实发生的时间已过很久,则法院面临取证困难,增加司法负担。商事仲裁中仲裁庭调查取证的职权较小,一般依据当事人提供证据,仲裁员不必审查每个证据;如果缺乏证据,仲裁员可以依据公平原则作出裁决,没有必要拘泥于严格的举证责任规则。[4]时效的传统价值——防止证据湮灭在商事仲裁中并不突出。与此同时,商事仲裁中当事人可能对仲裁时效有不同的期待:一方面,仲裁的重要目的是快速解决纠纷,尽快明确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因此当事人可能期待较短的仲裁时效;另一方面,在商事领域,商主体十分注重维护商事合作关系,可能不会在短期内提起仲裁,双方期待较长的仲裁时效。这些都是商事仲裁特有的价值,因此,维护当事人意思自治体现的自由价值,其在仲裁时效立法中价值位阶较高。
综上所述,相较于诉讼时效,从整体上分析,仲裁时效的立法价值更注重维护当事人意思自治(自由价值),重视公共利益(安全价值)的程度较低,这是由商事仲裁的契约性本质决定的。尽管如此,不能忽视仲裁时效在少数领域确实涉及一定程度的社会公共利益。仲裁时效与诉讼时效在立法价值上的差异源于二者的目的、功能、争议主体、受案范围、证据规则和实际作用的差异,这些差异构成了对仲裁时效期间法定性的法理基础的挑战。
三、约定仲裁时效期间的性质
仲裁时效的立法价值为约定仲裁时效期间提供了积极的理论基础,但是有学者对约定仲裁时效期间的性质提出质疑,认为其属于附期限的仲裁协议。其理由是:各国诉讼时效期间均为法定期间,所以对仲裁协议中申请仲裁的时间进行约定不属于对时效期间的约定。如果当事人不在特定的期限内申请仲裁,当事人仅仅丧失了通过仲裁进行索赔的权利,其仍然可以通过诉讼解决争议。[5]由于“附期限的仲裁协议”从性质上应当被归为附期限的民事行为,为了避免混淆,有必要对这种观点进行特别分析。下面通过对权利性质的分析,进一步探寻约定仲裁时效期间的合理性。
(一)约定仲裁时效期间不属于附期限的仲裁协议
从仲裁时效性质、与诉讼时效的关系、附期限民事行为的构成要件等角度分析,约定仲裁时效期间不属于附期限的仲裁协议。
其一,不是所有国家的时效均为法定期间,时效期间的法定性不是其固有属性,而是可探讨的问题。法国、德国等国均有条件接受当事人约定缩短或延长时效期间。①
时效期间并不当然是法定期间,源于其立法目的多元性。时效制度直接影响当事人能否通过诉讼或仲裁等具有强制性或半强制性的方式行使权利,而对第三人的公示效力仅为时效制度的间接作用,因而本文認为法定性是时效制度的固有属性的观点缺乏理论和实践方面的严谨性。
① 《德国民法典》第202条和《法国民法典》第2254条规定了当事人约定变更时效期间的条件。
② 参见Broom v. Morgan Stanley DW Inc., 236 P. 3d 182, 183 (Wash. 2010)。
其二,诉讼时效并不当然适用于仲裁,因而将诉讼时效期间的法定性适用于仲裁是不妥的。美国华盛顿州最高法院在Broom v. Morgan Stanley案中指出,由于违反州法,仲裁员无权将消灭时效制度适用于仲裁中。②我国《仲裁法》第74条的规定实际上也保留了对诉讼时效和仲裁时效作不同处理的可能性。诉讼时效不当然适用于仲裁的原因,在于司法裁判权和仲裁权的来源不同。司法裁判权来源于国家对民商事案件具有的司法主权,因而当事人不能随意约定寻求司法救济的期间。就仲裁权而言,虽然仲裁也有一定司法性,但其本质上是依托当事人之间的协议,具有较强的契约性和自治性。[6]对时效期间届满的法律后果,目前理论界和实务界的通说是债权人并不丧失其自然债权。当事人通过契约性质的仲裁解决纠纷,与行使自然债权具有一定的相通性,因而诉讼时效制度并不当然适用于仲裁。
其三,约定仲裁时效期间不满足附期限的民事行为的构成要件。附期限的民事行为是民事行为的种概念,民事行为是民事主体确立、变更、消灭民事法律关系的行为。民事法律关系是受民事法律调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当事人约定时效的行为既不是为了产生特定财产关系,也不是为了产生特定人身关系,因为时效经过与否并不影响当事人之间的自然债权债务,只影响强制力的保护,因而约定时效不符合附期限的民事行为的构成要件。
(二)约定仲裁时效期间属于当事人对相对权的处分
约定仲裁时效期间并没有改变仲裁时效的性质,它既不是附期限的仲裁协议,又不是除斥期间,仍然属于仲裁时效期间的一种,与法定的时效期间相对。约定仲裁时效期间本质上属于当事人对实体权利义务的处分。如果当事人约定缩短仲裁时效,则这种约定属于债权人对权利的处分;如果当事人约定延长仲裁时效,则这种约定属于债务人对权利的处分。
约定仲裁时效期间是当事人对权利的处分,这种权利的性质对债权人和债务人而言是不同的。对债权人而言,这种权利的处分是对行使债权请求权的处分;对债务人而言,这种权利的处分是对行使永久不履行抗辩权的处分。债权人和债务人之间的权利具有互补性,无论是请求权还是抗辩权,都属于相对权而非绝对权。相比之下,物权等支配权属于绝对权,这种对世性的权利具有直接的公示公信效力,因而立法更侧重于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利益。就时效制度而言,约定仲裁时效属于对人权的处分,对第三人交易安全的保护是间接的。因而,时效制度对第三人交易安全保护的价值低于物权制度对第三人交易安全保护的价值。
综上所述,约定仲裁时效期间没有改变仲裁时效的性质,其属于当事人对相对权的处分。从权利的性质角度,约定仲裁时效期间并没有超越权利行使的合理范围,不会直接损害第三人的利益和交易安全。
四、约定仲裁时效期间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由于允许约定仲裁时效突破了我国时效制度法定性,因而必须对约定仲裁时效期间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分别探讨,比较落实这一制度所带来的益处和可能的风险,以提升制度设计的严谨性。
(一)约定仲裁时效期间的必要性
约定仲裁时效期间的必要性主要包括理论方面的需求——克服时效法定性的逻辑缺陷,以及实践方面的要求——提升仲裁的效率的需求。
理论方面,法定时效期间存在逻辑上的矛盾。法定时效期间的理论基础是时效的公益性,即加速债权债务流转,维护第三人对交易的期待。我国现行法对时效的效力采用的是“抗辩权发生说”,即享有时效利益的当事人有权决定是否援引时效进行抗辩。如果债务人进行时效抗辩,则在此期间其有权不履行债务。如果债务人未在合理期限内提出时效抗辩,或者基于商业信誉的考虑放弃提出时效抗辩,则诉争债务在满足其他条件的情况下仍然需要履行。在这种情况下,时效制度所追求的交易安全的目标无法实现。因而,以维护交易安全为由,允许当事人在诉讼或仲裁中放弃时效利益,而不允许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约定时效期间,存在逻辑上的矛盾。[7] [8]30因此,以时效的公益性为由坚持其法定性,存在制度上的不统一性,时效的公益性不应排除当事人意思自治。
实践方面,允许约定仲裁时效将减轻当事人的举证负担,提升仲裁庭审理的效率和当事人对仲裁结果的可预见性。我国仲裁实践中出现过很多仲裁时效起算点和仲裁时效中断事由的争议。①
出现这些问题的重要原因在于我国法律规定的时效期间过短,不能满足商事交往的实际需要。如果允许当事人约定仲裁时效期间,就能从很大程度上减少当事人在仲裁中的争议,提升当事人争议解决的效率。我国现行《民法总则》规定的普通时效期间为3年,但是特别法对时效期间有十几种不同的规定[9];而且有些规定在适用中存在争议,例如“出售不合格产品未声明”。如果允许当事人约定时效期间,则能够提升当事人对合同权利义务的可预期性。当事人对仲裁时效期间的约定一般是具体到期限的长度。在国际商事仲裁中,如果实体问题的准据法不确定,约定仲裁时效期间将有助于当事人对行使权利的时间有明确的认知。
① 涉及仲裁时效起算点和仲裁时效中断争议的案件包括:滁仲裁字〔2016〕第29号仲裁裁决,〔2017〕皖11民特4号法院裁定,〔2014〕京仲裁字第0396号仲裁裁决,〔2014〕浙杭执裁字第20号法院裁定,〔2014〕庆仲裁字第13号仲裁裁决,〔2014〕庆中民特字第2号法院裁定,〔2013〕济仲裁字第1359号仲裁裁决,〔2014〕济中立初字第20号法院裁定,〔2012〕穗仲案字第1958号仲裁裁决,〔2013〕穗中法仲审字第16号法院裁定,〔2011〕济仲裁字第0568号仲裁裁决,〔2014〕济中立初字第20号法院裁定,〔2010〕株仲裁字第012号仲裁裁决,〔2010〕株中法民特字第29号法院裁定。
② 参见Arbitration Law Amendment Law, DIFC Law No. 6 of 2013, Art. 14(2)。
(二)约定仲裁时效期间的可行性
不可否认的是,我国现行时效制度在维护法律统一性方面是值得肯定的,如果允许当事人约定时效期间,则其在某些领域可能存在不适应性。本文第二部分已述,由于可仲裁性的范围有扩大化趋势,文化遗产仲裁、消费者仲裁逐渐成为可能,这些仲裁由于涉及公民基本权益或者国家利益,因而立法在决定与之有关的制度时就会非常慎重,传统的国际投资仲裁亦同。那么能否因此就否认约定仲裁时效期间的可行性,或者允许当事人约定一般商事仲裁时效期间而不允许约定特殊类型的仲裁时效期间?本文认为,普遍允许约定仲裁时效期间具有可行性。
一方面,允许当事人约定仲裁时效期间并不会损害国家或社会公共利益。因为约定仲裁时效期间必须双方当事人达成合意。虽然当事人之间存在谈判能力的差异,但是约定仲裁时效期间有一定的限度,不会导致当事人即使积极寻求权利救济还罹于时效的后果。与此同时,我国《民法总则》虽然将普通诉讼时效期间由2年提升为3年,但是相对于外国诸多立法例,仍然处于较短的水平。即使约定时效期间,由于国际投资等业务周期较长,成本回收较慢,当事人一般更倾向于约定较长的时效期间。在消费者纠纷等非传统商事领域,一些国家即使允许当事人选择仲裁为争端解决方式,也规定了严格的条件。例如迪拜国际金融中心(DIFC)《仲裁法》规定,消费者争议只有在以下三种情况之一时才可提交仲裁:争议发生后消费者签字同意提交争议至仲裁;消费者提起仲裁;法院认为通过仲裁解决争议不会损害消费者的利益。②这类规定保障了消费者等弱势群体的谈判权,避免了因为格式条款而不得不接受较短期限的仲裁时效的约定。
另一方面,如果不允许对特定事项约定仲裁时效期间,而允许一般商事约定仲裁时效期间,会导致立法内容过于复杂,在实践中难以区分。本文在约定仲裁时效的必要性部分提出,允许约定时效的理由之一是避免时效制度过于繁杂。如果在一些事项上允许约定而在另一些事项上不允许约定时效期间,则与“化繁为简”的立法目的不相容。与此同时,不同类型的争议可能存在重合性,在实践中可能出现确定分类的情形,不利于为当事人提供确定的指引。因此,鉴于允许在特定领域约定仲裁时效期间不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当事人的基本权利,没有必要禁止特定事项的仲裁时效约定,允许当事人约定仲裁时效具有立法上的可行性。
五、约定仲裁时效期间的具体方式
约定仲裁时效期间的具体方式包括约定长于法定时效期间的仲裁时效期间和约定短于法定时效期间的仲裁时效期间。无论采用何种方式,都必须确保仲裁时效期间约定的合理性。美国第二上诉法院在Son Shipping Co. v. De Fosse & Tanghe案中表示,只有当事人明确约定時效期间,并且合理的情况下,仲裁庭才受该约定的约束。①本文认为,合理的标准是约定时效期间不损害时效制度的目的,并且能确保当事人的权利得到合理的救济。下面就约定较长仲裁时效期间和约定较短仲裁时效期间分别进行讨论。
(一)约定较长仲裁时效期间
就各国的立法例而言,允许约定缩短时效的国家不一定允许延长时效,而允许延长时效的国家一般都允许缩短时效,[8]29这体现出大多数国家倾向于限制当事人约定延长时效期间,这也与不同国家的立法政策有关。有的国家倾向对民事时效规定最为宽限的期间,当事人可以根据具体事项约定缩短;我国诉讼时效短于大多数国家的时效期间。在这种情况下,不能认为允许约定缩短而不允许约定延长时效期间是一种国际通行做法,也不一定适合我国的实际需要。
① 参见Son Shipping Co. v. De Fosse & Tanghe, 199 F. 2d 687, 689 (2d Cir. 1952)。
② 由于我国《仲裁法》适用于国内仲裁和国际仲裁,并且仲裁本身具有较弱的司法性特征,因而在考虑公共政策的定义时应当更倾向于国际公共政策而非国内公共政策。
反对约定较长诉讼时效期间的理由主要是公共政策因素和当事人无法获得公正审理。就公共政策因素而言,本文已经论述了仲裁时效涉及公共政策的范围较窄、程度较低。除此之外,就公共政策本身的性质而言,其也是指对国家、社会具有全局性、根本性的利益,以及根本性的法律制度和观念。①
如果公共政策遭受破坏,那么任何普通公民将感受到极端不正义。[10]我国历史上素有“欠债还钱,天经地义”的传统观念,在当今社会亦提倡发扬社会主义诚实信用理念。与此同时,我国现行法制中时效的届满不会导致当事人之间的自然债权消灭,债务人履行后不得请求返还。当事人约定延长时效期间,从普通人朴素的价值观角度看是符合自然正义标准的。在各国收紧对公共政策适用的趋势下,约定延长时效期间所可能导致的对经济流转的影响、对第三人交易安全的影响都属于间接性的影响而非直接性的损害,远远不足以达到损害公共政策的程度。因此,约定延长时效期间不仅不会有道德方面的瑕疵,在法理上也具有公共政策角度的合理性。
就当事人是否得到公正审理而言,约定较长时效期间不会剥夺当事人获得公正审理的权利。一方面,当事人在决定是否接受对方当事人提出的约定较长时效期间的要约时,会对相关情况作出判断,这种约定是当事人自愿对其权利进行的处分。需要注意的是,在格式合同中如果存在约定较长时效期间的格式合同条款,则应按照格式合同的规则处理,与约定延长时效期间本身的合理性并不相关。另一方面,如果不允许当事人约定较长的仲裁时效期间,那么这种规定很容易被规避,权利人定期向义务人发出债权请求,时效会屡次中断,义务人需要在较长的期间后接受诉讼或仲裁。以上理由体现出约定较长的仲裁时效期间是义务人对权利的合理处分,使义务人对履行期间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不会导致其遭受不合理的打扰,不会损害其获得公正审理的权利。
允许当事人约定较长的时效期间,有利于当事人采取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避免诉讼或仲裁资源的浪费。仲裁实践中,在很多涉及时效的案例中权利人都提出了时效中断的抗辩。虽然法律规定了诸多时效抗辩的因素,但是不通过诉讼或仲裁的方式经常会出现无法送达的情形,因而短期的时效期间将迫使权利人提起诉讼或仲裁。[11]如果能夠允许当事人延长时效期间,则义务人有更多资金周转的期限,权利人也不会轻易起诉或仲裁。这样既节约了诉讼或仲裁资源,又有利于当事人通过和解、调解等方式解决争议,提升争端解决的效率。
允许当事人约定较长的时效期间,有利于当事人维护商事关系,形成诚信的商业氛围,避免当事人利用时效制度不履行债务。我国实践中一些债务人通过改变住所等方式逃避债务,与我国长期以来实行较短的时效制度不无关系。国有银行每年因超过时效而损失的债权额度十分高昂,造成国有资产流失。这些情形都有悖于时效制度设立的初衷,说明我国法定时效期间还不完善。在这种背景下,我国一些学者建议将时效制度延长至20年。[8]29,[12]这种大幅度改变我国时效期间的建议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时效期间相差甚远。从谨慎的角度出发,允许当事人约定时效期间,一方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醒当事人及时行使权利,另一方面也有助于特定行业延长时效期间以维护当事人之间的商事关系,确保债务的有效履行,促进社会和谐。
① 普通诉讼时效期间为10年的国家有意大利、瑞士、瑞典、芬兰、比利时、波兰、土库曼斯坦、日本(债权)等。
当事人为了维护商事合作关系而作出达成的较长仲裁时效期间的协议,符合正当性原则。国际商事仲裁中,有些国家的时效期间较长(如葡萄牙法律规定的时效期间为20年)。允许约定较长的仲裁时效期间,我国当事人和外方当事人进行商事交易的过程中,当事人对时效期间容易形成共同的期待。如果在实践中当事人经常约定延长仲裁时效期间,在我国将来的法律修订中,时效期间的延长就可能会被再次提上议事日程。这种情况下,我国的时效立法就能够更精确地反映商事交往的实际需求,其具体规定也能与国际一般时效规定更加契合,我国仲裁制度的国际化也得以提升。
为了维护时效制度的严肃性,仲裁时效期间也不应过度延长,这是为了提升民商事主体债权债务关系的透明度,保护第三人的交易安全,加快市场经济的流转。较多国家将普通时效期间定为10年①,[8]29,本文认为,10年的时效期间应当作为时效期间的上限。这也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最长时效期间20年的制度相互配合,避免二者重合而无法发挥普通时效制度的实际作用。
(二)约定较短仲裁时效期间
就各国的立法例而言,各国对约定较短时效期间比较长时效期间更为宽容,但是大多数就时效期间的下限进行了规定。值得注意的是,《德国民法典》第202条规定:“因故意而发生的责任,不得预先以法律行为减轻消灭时效。”这一规定突出了对案件实体问题和当事人主观因素的考量,是维护公共利益的重要表征。
当事人的目的是为了尽快确定权利义务关系,符合商事仲裁的目的和特征,然而缩短仲裁时效不利于债权人权利的主张。如果时效过短,就存在一方利用优势地位使对方接受不合理条件的可能性,因此有必要对约定仲裁时效期间的下限作出规定。实践中一些格式条款均有对申诉期限的限制,体现出部分商事交易对较短期间内行使权利的期待。尽管如此,这种行使权利的期限约定在先行法制下不具有时效的效力,而仅为一方当事人受理另一方当事人提出磋商、和解、调解的期限。这种期限通常较短,如果以此为仲裁时效,容易对处于弱势一方当事人的利益造成损害。由于时效制度的目的并不在于限制当事人合理行使诉权,而是对长期怠于行使权利的人予以规制,因而有必要规定约定时效期间的下限。这种规定应当以在复杂情况下,当事人尽合理注意为准备仲裁所需的最长时间为准。
参考我国现行短期诉讼时效的立法和海事海商国际公约中对时效的规定,本文认为我国立法将约定仲裁时效期间的下限定为1年为宜,即不低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的短期诉讼时效。结合时效的中止制度,1年的时效期间对及时行使权利的当事人权利而言是足够的。我国是否可以借鉴《德国民法典》202条的规定对时效的缩短结合具体案情进行规制,本文认为我国法律没有必要对时效的缩短结合主观因素进行限制。因为在规定1年约定时效期间下限的情况下,当事人即使有故意的侵权或违约责任,对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也是有合理保障的,并且我国《民法通则》中规定的人身伤害责任的时效期间为1年,其中包含了故意和过失的情形。如果借鉴《德国民法典》进行特别规定,会导致立法过于繁琐,而且在实践中容易出现争议情形(如故意和过失的认定、侵权和违约的区分),增加仲裁或司法机关的负担。
如果当事人约定较短的仲裁时效期间,在时效届满之后,需要分析当事人是否有权向法院起诉。本文认为,当事人仲裁时效经过后,在诉讼时效期间内仍然有权获得司法救济。虽然仲裁协议具有排除诉讼的效果,但这是以仲裁时效和诉讼时效的期间相同和均不可协议变更为前提的,如果某项请求已经超过仲裁时效,则也超过诉讼时效。在诉讼时效不可约定变更而仲裁时效可约定变更的情况下,诉讼时效期间具有保障当事人寻求救济的最后一道防线的功能。从维护实质正义的角度,纠纷快速解决的法益在通常情况下小于债权人实体债权的法益。在我国诉讼时效期间较短的现行法背景下,允许较短仲裁时效届满的诉讼保护具有维护实质正义的效用。与此同时,仲裁和诉讼的功能具有差异,仲裁具有秘密性、快速性、契约性,而诉讼具有公开性、程序全面性、公共利益性。这种功能上的差异决定了当事人在无法采取高效和秘密地解决纠纷的情况下,仍然有权通过普通司法救济的方式解决纠纷,符合诉讼和仲裁的功能和目的。
六、结语
允许当事人约定仲裁时效期间,能够更好地适应不同情形所需的时效期间,兼顾了时效制度在立法形式上的统一性和当事人对行使权利的期待,能够体现仲裁时效在立法价值与诉讼时效的不同之处。约定时效期间中权利的性质也体现了约定时效期间行为的合理性。约定时效期间具有理论和实践上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有利于弥补时效法定性的缺憾,提升仲裁的效率。允许约定较短时效期间和较长时效期间都具有法理上的合理性,但是应当在立法上规定约定时效期间的上限和下限。
仲裁时效的可约定性受两方面因素影响,一方面是仲裁时效与诉讼时效的差异(根源是仲裁与诉讼的差异),另一方面是时效制度本身的法定性存疑。事实上,约定缩短和延长仲裁时效期间的理由和约定缩短和延长诉讼时效期间的理由具有相近之处。如果在立法上允许当事人约定仲裁时效期间,这对我国诉讼时效的改革也有一定的推动作用。这种规定还有利于发挥仲裁的灵活性,提升多元化争端解决机制的互补性。
参考文献:
[1] Lara K Richards, Jason W Burge. Analyzing the Applicability of Statutes of Limitations in Arbitration [J]. Gonzaga Law Review, 2014,49:244-247.
[2] 杨玲.国际商事仲裁程序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196-197.
[3] 梁慧星.民法总则立法的若干理论问题[J].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1):40.
[4] Craig P Miller, Laura Danysh. The Enforceability and Applicability of a Statute of Limitations in Arbitration [J]. Franchise Law Journal, 2012, 32: 26.
[5] 杨玲.论国际商事仲裁程序的开始——兼评中国仲裁机构的实践[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90.
[6] 李双元,谢石松,欧福永.国际民商事诉讼法概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6:519.
[7] 金印.诉讼时效强制性之反思——兼论时效利益自由处分的边界[J].法学,2016(7):125.
[8] 高圣平.诉讼时效立法中的几个问题[J].法学论坛,2015(2).
[9] 杨巍.民法时效制度的理论反思与案例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36.
[10] 肖永平.法理学视野下的冲突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224.
[11] 赵德勇,李永锋.诉讼时效期间可约定性问题研究——兼评最高院《诉讼时效解释》第2条[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5(6):96.
[12] 刘应民.当事人约定诉讼时效的效力分析——兼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總则》第197条[J].江汉论坛,2017(8):126.
责任编辑:张岩林、康雷闪
Abstract: The legal value of arbitration limitation is different from that of limitation of action. The scope of public interest involved in arbitration limitation is narrower and more emphasis is laid on party autonomy. The nature of agreement on limitation period of arbitration is disposal of relative right, instead of arbitration agreement with a time limitation, which indicates that agreement on limitation period of arbitration is not abuse of rights. Agreement on limitation period can overcome the side effect of non-variability of period of limitation and is beneficial to arbitration efficiency. The parties shall be allowed to have agreement of a longer or a shorter limitation period within a certain range. After the expiration of the shorter limitation period, the parties still have the right to file suits in courts.
Key words: time limitation of arbitration; limitation of action; non-variability of period of limitation; public policy; party autono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