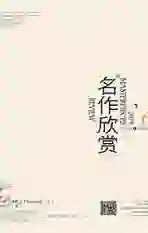女性批评主义视角下解读《永远的幽会》
2019-07-22史华威
史华威
摘要:何立伟《永远的幽会》以神似女性的笔法,诗意的语言,与现实微妙的关系成为小小说经典读物,作者用简短的语言率先从梦境入手,细腻温柔的笔触像初恋时娇羞的姑娘,梦中的白纱裙姑娘成为男人毕生的幻想甚至是死的寄托。梦中的女人表现微妙,细节之处却可见作者对男女个体及关系的思想二重性,对女人“绝对他者”的肯定,同时透露出对女性特有的偏爱。男人追求女人的过程是“双性同体”微妙变化的过程。《永远的幽会》中关于女性主义批评思想的二重性,对男女个人及关系的解读具有现实性和研究性。
关键词:女性主义批评 何立伟 《永远的幽会》
一、女人是男人的必需品,是“绝对他者”的存在
法国著名女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是杰出的存在主义者及女权主义倡导者,她的著作《第二性》内容覆盖面宽泛,涉及文学、历史、哲学、生物学等方面,从历史神话到生理条件,将女性的处境及未来破除他者地位的方法逐一呈现,为女性主义批评解读方法树立一整套完整的话语结构。波伏娃最为著名的观点即为“女性是形成的”,她认为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在传统社会的要求与男权社会的需要所造就的。男人始终是社会的主体,而女性是为标榜男性的地位和权利而创造的参照物,是“绝对他者”的存在。女人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没有自主性和独立性,甚至在金钱的权利方面依附于男人,这迫使女性不得不在现实中按照男人规划的和安排的角色去担当,社会需要女人承担“贤妻良母”,女人就必须做到温柔贤惠;男人需要女人呵护顺从,女人就必须成为男人发泄的工具和生活的调味剂。男人和女人之间从来不是处于平等的地位,两者之间有主体和客体,依附与被依附,第一性和第二性的本质区别。
这种地位和角色的不对等,首先是神话所赋予。在人类文明的远古时期,上帝创造亚当,并用亚当身体最柔软的肋骨做成夏娃。这就说明女人是男人的附属品,是身体和肋骨的区别,上帝为了区别男人而创造女人,为了男人的泄欲而创造女人。男女分工不同,男人负责狩猎和部族生存,女人只需要操持家务和繁衍子孙。女人只是家庭生活维持的附属品,只有男人的外出获得食物等生命必需品才能使部族生存下去,甚至女人过多的生育是部族生活的负担,这种历史条件促使女人必需依附男人。其次是历史环境,中国是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伟大古国,孔子曾在《论语》中表达对女人的态度:“唯女子和小人难养也”以及古代对女子的要求“女子无才便是德”.三纲五常和《女德》《女戒》的约束,甚至在古代寻常人家妻妾成群的现实,便可知女人在历史中扮演着的是男人泄欲的工具及附属品。再是男女生理的不同,女孩成长为女人经历青春期的巨大变化和生理期的痛苦反应,女人更加容易处于“绝对他者的地位,月经的出现并不是个人意愿所能操控,只能默默承受月经腰酸背痛甚至晕厥的痛苦,毫无反抗和选择能力,女人承受的是男人永远无法体会的痛苦。生育期更是女人沉痛的折磨期,过分的消耗与哺乳新生儿,是女人比男人衰老的速度更快,女人怀孕只有顺从和接受,没有选择的权利,只有生儿育女才是女人头等的大事”。“女人对物种的屈从,她的个人能力的局限,是极其重要的事实。女人的身体是她在世界上所占处境的基本因素之一”。女人身体中的特有的“孔”以及男人的“阳物”使得男女之间的性交流始终以男人为主体,女人则是被动地接受。
《永远的幽会》中作者对女人的描写“拖地的白纱裙”“一朵不知名但很馨香的花”,从装扮上呈现的是社会约定俗成的美人该有的模样,素净美丽,似乎女人的装扮本就是为与男人的邂逅而精心打扮;“低眉地说了一句”“她如约而至”细微的动作描写,并非刻意地去描写女人的性格,但在文中不难发现,女人温柔可人,符合男人期望中女人的顺从乖巧,男人的主动恰好凸显出女人的被动;在梦的幽会中,女人从未明确地拒绝过男人的请求,每一天的等待和准时,是男人视角下对于现代女性的观照,这也意味着男人理想的婚姻生活也因是男主外女主内,女人负责等待和操持家务。文章以男人的一切思考为主线,男人的寻找,男人的倾诉,男人的拥吻,男人的死,女人是男人生活的调剂品,是“绝对他者”的存在。男人梦境的缘由归于对现实生活及妻子的不满,随后开始梦到温柔乖巧的女人,梦是对愿望进行合理加工的表现,通过装饰锻炼营造出对现实的替代性满足,生活中的女人不能满足,就通过梦的形式改装后满足;男女之间关系的升温也是得益于男人的主动,在两人的相处中,男人始终作为倾诉者,喋喋不休地诉说自己的伤心烦恼,而女人需要做的只是倾听,没有权利诉说自己的生活苦恼,唯一的作用就是倾听和当作被泄欲的工具。在此方面,作者作为“第一性”的创作者在无形中透露出对“第二性”的禁钢和束缚,用男性的角度诠释女性的“绝对他者”。
二、男人以女人为中介,才能找到生存的正当性
法国著名女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中,认为女人以男人为中介,只要女人依附于男人,顺从男人才能找到生存的正当性。女人不具备独立生活的环境条件,在古代社会,女人成年未嫁则是对父母的大不敬,女人未成年时只能依靠父亲,在父亲的处所和精神的庇佑下成年,成年后女人必须且是社会赋予女人的义务和责任,必须找到一个男人顺从他,依附他,只有女人寄存在男人的身体上,同男人绑成利益和生理的共同体,女人才是被社会接受的女人,才是“正常的女人”。假使女人成为独立的个体,不与男人结合,就会被男权社会的质疑和否定而淹没。“婚姻对于女人和男人,想来都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两性彼此必不可少,但这种需要从未曾在他们之间产生相互性”。女人的选择是十分有限的,只有当女人可以选择不进入婚姻或者是选择与同性结婚等一系列看似违反正常社会对女人的规划时,女人才是真正自由的女人。很少有女人决定出嫁时兴奋高兴,她们通常是失落、纠结,甚至是痛苦,门当户对仍然是女人选择婚姻首要的条件,如果女人到适婚的年龄还未出嫁,那么家庭的逼迫和社会的压力也终究会让女人妥协,被迫放弃自己的身价委身于不爱的男人。只有婚姻才是女人得以生存和维系社会声誉最好的方式。婚后的女人一如既往地选择被动地融入男人生活的圈子,被迫放弃自己的理想和生活习惯,完全按照男人规划的路线一步步向前走,服从男人的命令和信仰,尊重男人的习惯和爱好,在男人孤独时为他解闷,在男人成功时藏在身后为他鼓掌,女人所有的一切,声誉、身体和理想全部送给男人,连同自己的名字都将变成泡沫化为尘土。“婚姻的悲剧性,不在于它向女人保障它许诺过的幸福——没有幸福是可以保障的——而是婚姻摧殘了她,使她注定要过上重复和千篇一律的生活”。而男人可以选择晚婚和不结婚,社会对男人是宽容的,因为社会就是男人构成的,他们在自己创建的国度中自由生活,对另一半的选择允许他们挑挑拣拣,男人四十一枝花,女人四十基本面临被出轨和黄脸婆的命运。
《永远的幽会》中作者在细节处表现对女人的偏爱。首先题材的整体框架是以男人追求女人并最终为梦境中的女人而死。小说的内容选择打破长期的男权压榨和女人甘愿奉献的主题,而是大胆选择以男追女为主线,并且是梦中的女人,梦中的相遇。其次是男人的性格突破以往单一的大男人人设,开始拥有一种男女混合的性格气质,在文中,男人也有自己的柔情和胆怯,“他感到他的手和他的语言都像月光下的树影一样婆娑颤抖”,“难言的惆怅、忧伤,甚至痛苦”,男人也具有女人的怯懦和欢喜,喜形于色,激动时也会双手颤抖,难过时也会想找人倾诉,男人具有“双性同体”的思想和性格,这也是促使他最终放弃生命只为寻求梦境的女人。
“双性同体”的观点最初是由英国现代史上最著名的女性作家、西方女权运动和女性主义思潮的先驱者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她的著作《一间自己的屋子》中提出:“在我们之中每个人都有两个力量支配一切,一个男性的力量,一个女性的力量。在男人的脑子里男性胜过女性,在女人的脑子里女性胜过男性。最正常、最适宜的境况就是在这两个力量在一起和谐地生活、精神合作的时候。”伍尔夫的思想中并不是完全否定男性,相反她看到男性的思考方式和性格方面的优势,在追求男女平等的同时,追求两性的和睦相处,甚至是共荣共存。这对于女性主义初期两性相斥的现状有一定的改善。《永远的幽会》中,男人在不断追求女人的过程也是男人逐渐达到“双性同体”的过程。经历寻找、相遇、倾吐、相爱到义无反顾去寻找梦中的女人。寻找这一持续性动作的发展,以温柔的女人为终极目标,男人在现实中的遭遇使他言不由衷地选择在梦中实现自己的愿望。男人的生存不再是统治世界的“第一性”存在,作為世界的“弱者”,需要女人的保护和爱抚,也只有女人才能使男人重新获取生存的正当性。女人在男人的视线中担当起“天使”的角色,且是男人需要排忧解难的唯一渠道,在此种情况来看,男人需要女人,只有与女人绑成共同体才能实现自己的愿望。由此来看,作者对女性的偏爱油然而生。
男人的结局从本质上论述,也是意料之中。作者巧妙地树立女人的形象,过于理想化,同时也暗示现实中几乎很少有完美女性的存在,致使男人放弃生命去寻找与梦中女人的一生一世。男人的结局虽是生命的终止,但从永恒的世界观去看,男人的死是“双性同体”的终极变体。决定死的过程是漫长的,“就这样,这个人每天等待着是进入令人心驰神往的梦乡中”。过程中男人的女性特征逐渐压制男性本质成为精神上的主导性格,女性柔弱的力量超过男性刚强的力量占据生命的主导,弱压强的局面难以控制,最终导致死亡,也是“双性同体”的终极变体。
三、反观男人出轨的合理性及“第三者”形象
梦中女人典型的性格“不但美丽而且性格很好”,“毕生想遇见的女子不是别人正是她”,这些强有力的“女性标签”贴在这位“第三者”脸庞上,与现实中“庸俗老婆”的明显对比,带给男性读者最强烈的感受是男人出轨的合理性,跳出道德的高度,反而开始同情男人在现实的遭遇,联想自我的实际,在心理上绝大多数男性读者会认同男人的出轨,不仅正当合理,且具有浪漫主义特质。“滔滔不绝地倾吐着仍然是很不逻辑但又很诗意的话”,“那些语言熠熠生辉,就像天上的流星”,男人心中都有一个诗意浪漫的梦,这也是“双性同体”的体现,男人渴望女人能拥有一颗完全理解自我的心,那些话不需要符合社会大众的理解,也不需要符合现代汉语语法的要求,这些话要有诗意和一种只要心心相印的两个人才能交流的“暗号”,一种“诗意的暗号”。反观现实中存在的夫妻关系,这种随心自由的言语似乎只存在于同自我的交流,自言自语或是心灵的自我沟通,意识流的话语呈现,只要是接触到除自己以外人的交流,都不可避免地存在服从现实的倾向。可想而知,梦中的女人是男人的另外一半自己,是女儿身的另一个男人,完全按照自己意愿的另一半在现实中不存在,这在根本上为男人的出轨找到无法反驳的合理理由。
同时为女性读者创造出在男性作家笔下,也是最能代表男性视角的理想女人形象,简言之是服从于男人的另一个自我。男人的死不仅是“双性同体”的变体,同时也是追求另一个隐形自我的表现。过于崇高和伟大的理想女人形象迫使大多数女性读者甘愿放弃自我,去逐渐逼近理想的疯癫的男人需要的另一个自我,“第三者”的形象语言虽浅显易懂,仔细琢磨不难透露出难以超越和实现的幻想性。
四、结语
女权主义者西蒙娜·德·波伏娃的著作《第二性》一度尊为西方妇女的“圣经”,同时对于男女关系,女女关系的深刻分析打破了固有的传统观点。《永远的幽会》以男性作家的笔触描绘出男女之间微妙的关系,既有对女人“绝对他者”的肯定,同时又认为男人生存的正当性只有与女人结合才具有合理性。英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女性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她的著作《一间自己的屋子》中化解男女对立的冰川,提出著名的“双性同体”的观点。《永远的幽会》男人的追求过程体现着“双性同体”的细微变化,不合逻辑但充满诗意的语言是男人将另一半化身为理想中的女性自我,反观现实不难发现男性作家有意维护男性出轨的合理性,同时又为广大女性树立了完美的“第三者”形象,致使女性在家庭生活中难以控制生活的力度,作品思想的二重性具有独到的理想性和生活的见解性,是小小说中的经典之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