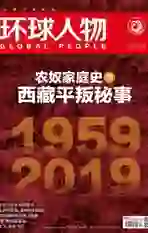王小帅:商业和我,无解
2019-04-12余驰疆
余驰疆

2019年3月18日,王小帅在北京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本刊记者 侯欣颖 / 摄)
王小帅
1966年生于上海,1989年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1993年以处女作影片《冬春的日子》成名,之后因《十七岁的单车》《青红》《闯入者》等电影获诸多国际大奖。2019年3月22日,其新作《地久天长》上映,该片曾在第六十九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包揽最佳男演员、最佳女演员两项银熊奖,备受瞩目。
王小帅很少把自己逼到这样的状态:电影《地久天长》上映前的某一天,他在工作室安排了密集的采访,媒体以“车轮战”的形式一家接着一家。和时下一些进退自如的导演相比,王小帅的确不太精于应对采访,他的回答要么太实诚直白,要么太抽象艰涩——前一种情况容易引发舆论危机,后一种则会让记者无从下手。
不过,也有一些记者选择迎难而上。有位网络媒体记者,专门挑了微博和豆瓣上许多恶评念给王小帅听,想让这位以“爱惜羽毛”著称的导演逐一回复。这些恶评包括:“结尾真是画蛇添足”“无聊,很多冲着史诗去的导演最后都拍成了历史教科书”“最后半小时完全塞满了令人尴尬而虚情假意的各式‘和解”……
一开始,王小帅还能心平气和地解释两句,可评论一多,他便有些着急,只是不断地重复:“他一定没有超过22岁。”这个采访结束后,王小帅坐到了阳台边的书桌旁,人瘫靠在椅背上,两腿交叉架在桌上,点了一根烟,闭上了眼。
“因为现在高科技啊,我觉得门槛就降得好低,而且观众批评电影是最容易的。”王小帅对《环球人物》记者说,“看一个画,听一个古典音乐,他搞不清楚,不敢随便说,只有电影,任何人都可以批评,这个不好,那个好。”
他有些无奈。
“我只是个补漏的人”
《地久天长》是一部未映先火的電影。2019年2月16日,该片在第六十九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同时拿下最佳男女演员奖,这是华语电影在“三大”(戛纳、柏林、威尼斯电影节)上史无前例的成绩。
那天晚上,男主角王景春、女主角咏梅相继上台,两人都有些激动。王小帅也很满足:“你坐在下面,看着你创造的两个人物在聚光灯下获得如此高的荣誉,特别好。”
颁奖结束后,王小帅看到有媒体写道:“从来没有见过一对演员演夫妻,能这么天衣无缝,这么让你相信这是一对真夫妻,在命运里缺一不可、相依为命地走下来。太感人了,所以就把这俩都给他们。”
有时候演员和电影,是互相的运气,有微妙的缘分。《地久天长》本来定了另一位男演员,但临时出了问题,王小帅情急之下半夜给好友王景春连发3条短信。王景春对记者说:“我早上醒来一看,估计他那边有状况。聊了一下,就说行,没事儿,我来。”当时,王景春甚至连剧本都还没看到。
咏梅是王小帅看电视时定下的。《地久天长》剧本创作时,咏梅参演的电视剧《悬崖》正在播出,王小帅看后觉得她的东方女性特质和剧本契合,表演状态也对。本子完成后,王小帅就首先想到了她。
咏梅收到剧组短信是在吃午饭时,一个小时后,标有“咏梅专阅”的剧本送到,她从中午看到了天黑,“眼泪都流干了”。第二天,咏梅约了王小帅,说:“我拍。”
让咏梅流干泪的剧本,讲的是一对平凡夫妻——耀军和丽云的故事。40年里,他们经历下岗、丧子、流浪、逃离,一生都在和失独的痛苦对抗,也在和过去的人、事、记忆纠缠。两个小人物,成了时间的载体,被时代裹挟着、推搡着。许多影响了一代中国人的事件在这对夫妻身上聚焦,让电影带上了纪录片的意味。
“我是60年代生的,经历了中国发展巨变的几十年,感触良多。”谈到创作初衷,王小帅说,“2015年,国家实行新的生育政策。那时给我的触动就是,过去的几十年,中国形成了独特的家庭结构和社会结构,而到这时候,我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要开始了。”
所以,王小帅决定讲述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特殊的“一家三口”的故事。它可能会面对争议,可能也不适合市场,甚至会在口碑和票房上双双折戟。“我一直没有想去改变大家的看法,或形成某种共识。只是有个别的地方被时代遗漏了,而我就是那个补漏的人。”
他说,这个故事没有原型,但它确确实实发生过。
忍受不了凑合的假东西
开拍之前,王景春和咏梅没有交集,咏梅甚至连王景春的脸都没有印象,而当王小帅把两人凑在一起,火花就来了。
“我拍到中间的时候,就说一切都有了,一切都是自然生成。像泥土里的种子,你把水浇完了以后就自己在长。”有一场戏,失去孩子的两人躲在房间里,拉着窗帘。“外面过小年、放鞭炮,小茉莉(剧中角色)来探望,他们招待她,每一个动作都是从生活里长出来的。”王小帅不说话,不给指令,机器开着慢慢拍,突然,鞭炮停了,瞬间安静下来,王景春叹气说了一句:“小年了。”那种失落和沧桑,让王小帅起了鸡皮疙瘩。
在片场,王小帅常常提醒演员克制,不要哭。故事和情绪很浓,但表演要克制,这种反差会让触动更强烈。往往遇到这种戏份,演员在镜头前拼命不哭,王小帅就在监视器后泪流满面。
因为学美术出身,对于场景真实,王小帅有强烈执念。“现在好多电视剧拍年代戏,都希望主角穿得干净、鲜艳,要做旧的话就简单涂下,这样其实缺乏生活的质感。”所以,当一些道具师按照电视剧的工作模式操作,王小帅就会不断提醒,让他们警觉起来。
这样的执念是一种习惯。2003年拍《青红》,故事发生地的贵州老区已经被新楼盘包围,服装也搜集得不理想,于是王小帅决定重新找场地、搭景,挨家挨户搜集老面料,服装全部自制。“但即便这样,也不能百分之百复原过去,那些童年记忆里的山水花鸟,包括空气里的泥土香味都已经消失殆尽了。”2011年拍《我11》,取景难度更大,他只能自己掏出部分资金重修了楼房、街道,“这一切做完后,居然吸引了十里八乡的人前来参观,很多已经迁出去的厂里的老职工拖家带口地赶回来,说看到这一切仿佛穿越了时空一样”。
到《地久天长》,更是找不到七八十年代的景了,王小帅只能从废地里一点点搭出景来。“我们在废墟里面费了很大的劲,找了无数道具,然后去组成需要的场景。”
咏梅记得一场戏,她戴着发套、化着老年妆,拍完过了很久,王小帅越看越不对劲,实在不能接受,就要求咏梅把真头发漂白,全剧组回去再拍一遍。“导演就是没有办法忍受那种凑合的假东西。”咏梅说。
“这是黑泽明都没办法解决的问题”
《地久天长》很长,初剪4小时,成片3小时,投资、宣发都很有顾虑,王小帅却说,一刀也不能多剪了。“有一些电影是需要慢慢看的,如果没有过程,上来就嘁里喀嚓的,就没意思了。”
“可是,3小时真的很长。”《环球人物》记者又重复了一遍。
“长吗?《复仇者联盟4》也有3个小时。”
“那是个商业片,它可能就需要这个时间。”
“我的片子也确实需要这个时间。”
曾有人问王小帅,为什么老是做和市场相反的东西,他回答:“我觉得自己只能闷头做自己喜欢的电影。之前我看黑泽明的访谈,有人让他赶快拍个商业片,黑泽明说没办法,我就喜欢这么做电影。连大师都没有解决的问题,我也没法过分要求自己。我和黑泽明一样,面对商业,是无解的。”
对于拍片,王小帅的确很少妥协。1990年,刚刚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王小帅被分配到福州电影制片厂,“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感觉23岁的自己就要永远离开北京,离开朋友了”。
在福州两年,王小帅写了五六个剧本,引起不小震动,同事都希望厂里能走出一个自己的导演——当时福州厂的片子都是把厂名借给外面的人去拍。那时是“计划时代”,每年摄制都有指标,福州厂一年一个名额,所以外借厂名最保险。于是,在一次次希望和失望中,王小帅还是没能拍到片子。

《地久天长》剧照。该片在第六十九届柏林国际电影节包揽最佳男演员、最佳女演员两项银熊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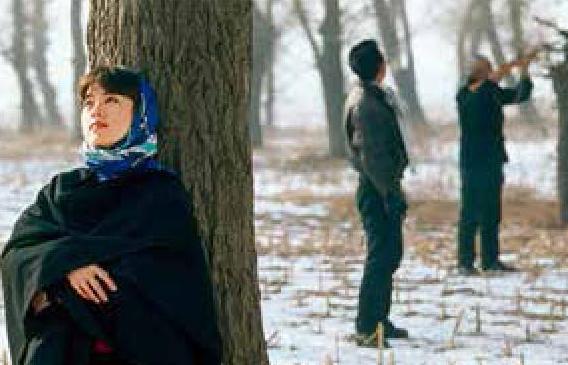
王小帅的首部电影《冬春的日子》剧照。

《青红》剧照。
1992年,北京电影资料馆领导到福州厂视察,说有个叫王小帅的年轻人不错,应该多拍电影。厂里领导回答:“我们这大学生还年轻,想要独立工作还得锻炼5年。”王小帅也在现场,听到领导回复后没过两分钟就站了起来,走出会议室,上楼收拾行李,打包回北京。“我从听到‘5年到踏出厂门,用时不到15分钟。”回京后,王小帅找到中央美院附中的老同学刘小东、喻红,拍了他的第一部电影。全剧组七八个人,拍摄地是美院附中4楼办公室,耗时5个月。
1993年底,这部名为《冬春的日子》的处女作被香港影评人介绍到温哥华电影节,之后又去了柏林、鹿特丹,王小帅一举成名。之后10年,王小帅又拍了聚焦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的《十七岁的单车》、讲述偷渡客故事的《二弟》等,在戛纳等电影节上拿下大奖,却也因“未经审核擅自参展”等原因被禁止拍片。
2003年,王小帅被通知参加一场针对所谓“地下导演”的会议,参会的还包括贾樟柯、张元、娄烨等。那场会议,王小帅得到两个信号:一、他能继续拍片了;二、中国电影要走市场化,以后民营公司也能自主出品了。
会议结束后,王小帅、娄烨和贾樟柯,找了一个酒吧坐下,没有人欢呼雀跃。“我们知道在新的市场化、商业化之后‘应该做什么,但心里的声音一直告诉自己,真正想做的是什么。”酒吧里的小会上,3个人各自做了决定。不久后,王小帅把《青红》提上了日程。
“埋下的种子多了,破土的几率还会少吗”
2003年后的中国电影,高歌猛进,15年总票房翻了20倍。王小帅却没有赶趟儿,依然拍着私人化、带纪录色彩的文艺片。中国第五代导演集体转型时,有记者问第六代的王小帅怎么看,他回答:“你们已经失去了一个张艺谋,还想再失去一个王小帅吗?”
“很多人说我疯了,太不识时务,但我觉得必须有人去走窄道。这条路不会比头一个10年好走,可能会越来越难。可是,埋下的种子多了,破土的几率还会少吗?”
《青红》《我11》《闯入者》,就是王小帅15年间埋下的种子。3部电影,讲的都是三线建设的故事,脱胎于王小帅的童年经历。他生在上海,几个月大就随着父母来到贵州,在贵阳郊区的光学仪器厂生活了13年。那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工业大迁徙,千万工人、解放军和知识分子,从发达城市来到中西部三线地区支援建设。在贵阳,王小帅遇到过押上身家性命带着妻女“逃离工厂,回到都市”的父亲,听说过“严打”期间技校里复杂的男女故事,这两件事合在一起,成了《青红》的框架。《我11》是王小帅的童年自传,《闯入者》则是三线建设的后续,电影中的老太太,早年为了争取“回家”名额出卖朋友,日后在赎罪与惊恐中度过。
3部电影在叙事和表现手法上都异常冷静,带着鲜明的王小帅风格。“我不是人们说的艺术疯子,我也不欣赏要么笑抽了风、要么哭瞎了眼的表意方式,我更不愿用哭和笑来和观众交流,我想在一种相对理性的角度优雅地打动观众。”总有人替王小帅惋惜,说“眼泪刚有就剪掉了,功力还是差一点”。“但我就是不希望煽动别人的感情,达到自己的目的。”王小帅回应。
正因如此,3部电影都在国际上获奖,也都在票房上失利。这让王小帅有了一丝矛盾。一方面,他不愿意为了市场改变自己想拍的东西,“我也试过努着劲儿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比较难坚持”。但另一方面,他又担心票房过于惨淡会让自己陷入困境,“所以每个片子拍出来后,我都会‘不要脸地到电影院宣传,哪怕只能是碎碎叨叨地去传播,我也不放弃”。于是,当新片票房不如预期,他就在微博和豆瓣上写情深意切的“致观众信”,在朋友圈发“撩哥撩妹就去看超长时间的《地久天长》”,反而引发不小争议。最后,王小帅只能悻悻然回应:“我果然还是不适合营销。”
或许,这并不是王小帅一个人的问题,而是中国文艺片导演共同面对的现状。在艺术和市场,自我和商业之间,他们始终没有找到最平衡的解。可是,采访的最后,王小帥说:“即便如此,我还是会继续,像初恋一样地敬畏电影、拍电影,因为这是我最好的生命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