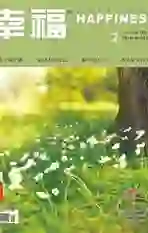我的朋友史铁生
2019-04-10赵泽华
赵泽华
一
说起和铁生的认识与交往,可能还要从我说起——
19岁那年冬天的一个深夜,我从插队的内蒙古赶回北京,探望即将做结肠癌手術的母亲,中途被火车轧伤。由于头部受到重创,我昏迷了七天七夜。死神到底还是放过了我,而代价是我的左腿,被黑暗吞没。
1998年底,我经人推荐,到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主办的《三月风》杂志做了一名文学编辑。杂志决定为残疾作者专门开设一个文学栏目“维纳斯星座”,由我负责。部主任提示我说:“你可以去看看史铁生,请他写一篇点评。”我便拿起手里的稿件,按地址找到史铁生的家。
我跨进屋门,见房子共有两间,外间有几件陈旧的家具,靠里还支着一个木板床。很多年过去了,我已经记不清楚房间的格局和具体陈设,只记得光线很暗,这是给我最深的印象,一直挥之不去。
二
里间紧靠着玻璃窗有一张床,铁生就躺在那里,被子下面露出一个由导尿管连接着的吊瓶。他看上去很憔悴,满脸倦容,但目光温暖安详。我拘谨地问候他,做了简单的自我介绍并说明来意,然后从书包里掏出作者的稿件递到铁生的手里。
他看稿子的时候,我有些紧张地坐在他床边的椅子上。路上我就想好了,如果他不愿意写,我就说……想了好几种自认为可以说服他的理由。他专注地看完稿件,又细心地折叠好,把稿件放回到原来的信封里,然后和气地说:“行,你给个期限吧,大约需要什么时候交稿?”
这么顺利?真没想到。他连一点儿假装的矜持都没有,更没有以正在生病为借口婉拒,尽管那对于他来说是一个最可信手拈来的理由。我松了一口气,掩饰不住内心的惊喜,连声说:“谢谢你啊,我还以为……还以为……真是太谢谢你了。”他笑了,说:“别,干吗那么客气呀?”他的语气就像对一个认识多年的朋友,十分亲切。
临走前,我问起铁生的病,可能不该问,可似乎也不该不问。
说起那些往事的时候,铁生的手里拿着一支烟卷,我赶紧找到打火机递过去。铁生摇摇头,不点着火,也并不吸,说:“戒烟了,医生特意嘱咐的。”他不时将烟卷放到鼻子下面,闻闻那烟草的香味儿,拿起又放下,拿起又放下。沉默了一会儿,我冒出一句很不得体的话:“我能看看吗?我看看……行吗?”说完我就后悔了,没有一个人愿意把自己的伤口裸露给别人看,尤其是一个与自己年龄相仿的异性。
铁生默默地揭开被子的一角,露出了他萎缩的双腿。如果可以站起来,他的个子一定很高,怎么也得有1米8左右。我心里难过得要命,泪水在眼眶里旋转着,旋转着……我低下头,为他盖上被子,又细心地掖好被角,泪水终于一大滴一大滴地落在被子上。“别哭啊。这其实,嗨,也没什么。”他反倒过来安慰我,还递过来一张擦眼泪的纸巾。铁生说:“哎,别光说我了,说说你自己吧。”我便对铁生说到自己19岁受伤的经过。
我说自己曾经试图自杀过……铁生静静地听着,并以宽厚慈悯的目光注视我,温和地说:“残疾者,尤其像咱们这样本来健康的人,绝大多数都有过自杀的念头。其实这也没什么,死亡迟早都会来,这是一件不必太着急的事,真的。”
他似乎轻而易举,轻描淡写地就把一个绝望变成了希望。
三
在一次命名为“我的梦想”的全国性征文大赛中,我和铁生并列获得一等奖。
当时,新任主编找到我,让我陪他一起去看铁生,顺带把获奖证书给他。在铁生的家里,他留我们吃饭。
那是我第一次和铁生一起吃饭。饭菜上桌后,铁生把轮椅摇过来,我们围坐在圆桌旁,宾主尽欢。记得席间,谈起在家里做饭的事情,我说:“我常常觉得做饭是一件特别麻烦的事,要买要做要收拾,要是天天像这样吃现成饭多好啊。”
铁生听了我的话,开心得直笑。笑过之后,他一本正经地说:“在吃饭和做饭的问题上,人大致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是喜欢吃又喜欢做的;第二类是喜欢吃但不喜欢做的;第三类是既不喜欢吃又不喜欢做的。”我们都表示赞成。铁生问我:“那你属于哪一类啊?”我说:“我属于最后一类啊,就是那不喜欢吃也不喜欢做的。”他慢条斯理地说:“嗯,这大概是最不可救药的一类。”我们都一起笑了起来。
曾经,在铁生的家里,我遇见过一个身体健康的女孩子。她有一双大眼睛和长长的发辫,但是眼睛里流露出来的失落和忧伤,让我看出了她的情感秘密。我单独问过铁生:“你干吗不同意呢?”他坦率地说:“我让她以后别来看我了……”我一下就明白了,铁生是对的。后来铁生找到了心仪的对象,还搬离了雍和宫大街。
四
那之后,我在人民大会堂又见过铁生一次。我们是在台阶下偶然碰到的。铁生看见我和编辑部的其他同事,就摇着轮椅过来,脸上挂着我所熟悉的温暖真诚的笑容。但是,我们几乎同时注意到他的脸,黯黑、憔悴、皮肤没有一点儿光泽。
铁生说:“一直做透析,每天整整一上午都要耗在医院。不仅费时间,费用还特别贵,所以很多患尿毒症的患者都自动放弃了。透析的时候,哪天哪个人没再来,是常有的事。”他抬头看看头顶的蓝天,眼睛里掠过一种悲天悯人的忧愁。他忧心的绝不仅仅是自己(北京作协每年特别为铁生拨出专款用做他透析的费用),还有那些没有条件做透析的普通患者。一个人,对于自己忧心的事无奈,那也是一种折磨。
他没怎么说自己,只是说精神不行了,写得很少。告别时,大家都对他说保重,再见!自从在人民大会堂见到铁生之后,虽然和朋友们几次相约去看看铁生,但终于没有去成。谁也没想到,那次会面,竟是最后一面了。
现在想来很是遗憾,但是我并不后悔。给铁生省下了一些写作的时间,我以此宽慰自己。有的人,也许天天见面,转身就可能不再记起。而有的人,即使不再见面,也永远都不会忘记。
2010年最后一天。清晨,我像往常一样,上网浏览各网站的新闻。
一条关于铁生逝世的消息,如乌云一样飘过来。我惊呆了,怀疑自己看错了。前不久,还传出他因肺部感染住院又出院的消息,听说朋友们还策划给他过生日呢。我揉揉眼睛,贴近了计算机屏幕:“2010年12月31日凌晨3点46分,著名作家史铁生因突发脑溢血逝世。”
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失声地哭了。再过几个小时,新一年的太阳就要升起来了,可是,铁生他没有等到。再过四天,就是铁生的生日了,他也没有等到。
其实,多少年来,铁生都生活在死亡的阴影里。
好多年前,他还住在雍和宫大街26号的时候,我去看铁生,他正病着,嘴唇干裂,形容枯槁,躺在床上有气无力地对我说:“高烧好几天不退了,这回怕是真的不行了。”我知道,对于一个肾功能几近衰竭的病人来说,这种来势凶猛的高烧是最致命的。
我故作镇定地安慰他:“你不会的,救护车一会儿就到了,我们送你去医院,医生肯定是有办法的。”救护车呼啸而来,停在院子外的路边。其他几位朋友用担架把铁生抬上去,我跟在担架旁边,把铁生护送到医院。
在医院,医生安排了一系列抢救措施,当别的朋友去办理各种缴费手续的时候,我在担架旁边守着他。铁生睁开眼睛,疲惫地笑了笑,说:“多亏大伙儿,差点儿就交代了。”还对我说:“你回去吧,这儿有这么多人。你们主编也知道了,他派的人也正往这儿赶呢。嗨,惊动了那么多人。”他满脸的歉意和不安。
五
铁生时时刻刻都感受到了死亡威胁,所以,他从来不回避生死的问题。
在一篇散文中,铁生写道:“现在我常有这样的感觉。死神就坐在门外的过道里,坐在幽暗处、凡人看不见的地方,一夜一夜耐心地等我。不知什么时候,它就会站起来,对我说,嘿,走吧。我想那必是不由分说。但不管是什么时候,我想我大概仍会觉得有些仓促,但不会犹豫,不会拖延。”
人的最后一个令人恐懼的敌人就是死神。而铁生早已和那个坐在门外过道里,一夜一夜耐心等待他的死神对视了多年。没有人能够战胜死神,但是,对于那些微笑面对死神的人,死神不过是一个引渡者和黑衣使者。它带走的仅仅是铁生千疮百孔的身体,而带不走铁生的精神和他在亲人、朋友心中的怀念与记忆。
在写这篇稿件的时候,我曾经梦见过铁生一次。我梦见到他的家里去约稿,铁生的家里依然宾朋满座,他就坐在朋友们的中间,笑容生动温暖,一如生前。
铁生写过一篇小说叫《命若琴弦》。铁生去世的那个晚上,被朋友们沉痛地命名为“弦断之夜”。
铁生捐献了自己的大脑、脊髓和肝脏。在他去世9个小时后,他的肝脏在另一人的身体内苏醒……
摘自《文摘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