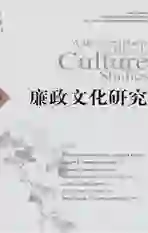软法视野下乡村微腐败治理研究
2019-02-10刘宁
刘宁
摘 要:“微腐败”治理既是完成反腐倡廉工作的必然要求,也是破解腐败治理难题的关键之举。尤其是乡村“微腐败”,因其量大面广、隐蔽性强等特点成为“微腐败”治理的痼疾所在。传统硬法虽承担着法治反腐的重任,但全然依靠硬法并不能实现乡村“微腐败”的全方位治理。公共治理的兴起为软法反腐奠定了逻辑基础。立足功能主义分析框架,软法在弥补单一法规制不足、道德义务规范化表达和发挥乡村治理民主性等方面有着硬法无法比拟的功能和优势。以党内法规、村规民约等为代表的软法资源运用也为乡村“微腐败”治理提供了可行的路径与方案。不过单靠任何一种法的形式都无法完成乡村“微腐败”治理任务,“软硬共治”将是乡村“微腐败”治理的最优模式。
关键词:乡村“微腐败”;法治反腐;软法
中图分类号:D63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170(2019)05-0052-10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提出,“微腐败”也可能成为“大祸害”。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明确指出:“要坚持反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定不移‘打虎‘拍蝇”,这里的“拍蝇”即指“微腐败”。毋庸讳言,我国反腐败工作已取得了阶段性胜利,贪腐之风得到有效遏制。但同时也应看到,“微腐败”仍然是腐败治理工作的“重灾区”。尤其是乡村“微腐败”,因其量大面广、隐蔽性强等特点,成为阻碍精准扶贫和乡村治理现代化的痼疾所在。当前学界对“微腐败”治理的研究乏善可陈①,且多从政治学、管理学等视角探究“微腐败”的治理进路。如有学者立足乡村社会差序格局,以成本-收益为突破口,从文化、制度、经济等方面构建“微腐败”防治的长效机制。[1]还有学者从“微腐败”滋生的政治文化根源出发提出治理对策。[2]总之,上述研究虽从不同角度提出富有价值的“微腐败”治理建议,却鲜有从法学视域下探索“微腐败”的治理道路,从而导致对“微腐败”治理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法治反腐是当代世界反腐的主流,也是我国建设廉洁政治的根本方向。[3]在法治反腐工作中,硬法反腐虽起到健全反腐败法制体系的积极作用,但全然依靠硬法难以有效周延腐败现象的各种难题,且单一制下的腐败治理极易造成公民权益的恣意侵犯,不利于反腐工作的良性开展。软法为腐败治理提供了全新的模式,该模式虽已广泛运用,但学界始终未曾系统总结软法在反腐败尤其是乡村“微腐败”防治中的可能贡献与应然路径。有鉴于此,本文拟就此展开叙述。
一、乡村“微腐败”的概念及其治理必要性
基于对“微腐败”概念的理解偏差,难免会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陷入治理误区。这需要准确廓清“微腐败”的内涵及外延,只有从概念上厘清语境和含义,才能在实践中明确对策有别,实现治理创新。此外,还需明确乡村“微腐败”亟需治理的现实缘由,要从我国当前乡村社会背景、反腐倡廉推进程度等方面入手进行必要性论证。
(一)何为“微腐败”?
要理解“微腐败”的内涵,首先应准确界定“腐败”的概念。《现代汉语词典》对“腐败”的界定是政治、社会风气等腐化败坏。将其置于法学的学科语境下,腐败是指掌握一定权力的公职人员,不合目的地行使权力谋取私益的行为。[4]从这一定义可以看出,腐败的主体是享有公权力的人员——国家公职人员。腐败行为是不合目的地使用公权力以谋取自身利益的过程。腐败的本质是一种以权谋私的行为,即权力的异化。对“腐败”概念的精准捕捉,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厘清“微腐败”的内涵及外延。从逻辑上看,腐败和“微腐败”应当是共性与个性、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微腐败”是腐败的一个类别,其无论是参与主体还是涉及领域较之于腐败的范围都狭窄很多。所以,“微腐败”是指县级及以下基层工作人员滥用公权力所导致的腐败现象。[5]“微腐败”虽在腐败层次和腐败程度上远低于巨腐,但本质上仍属于以权谋私的行为。
对“微腐败”内涵的厘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界定其外延,即“微腐败”的适用范围及表现形式,这也是寻找治理路径的前提性要件。从“微腐败”的行为主体来看,腐败与“微腐败”的行为主体并非完全一致,有必要对二者的主体作进一步廓清。从上文“腐败”的定义中可以看出,腐败的主体主要是从事公职的人员,既包括党政机关中的公职人员,也包括准公共部门、群众自治组织等社会公共机构中的公职人员。但对“微腐败”行为主体的范围界定,学界长期以来却颇具争议。有学者认为“微腐败”治理应将所有从事公务的人员(包括群众自治组织中从事管理的人员)囊括在内。[6]笔者认为此种观点失之偏颇,对主体范围的盲目扩张势必会陷入“微腐败”的监管泛化,甚至会让“微腐败”异化为“口袋罪”的可能性。因此,应当理性甄别“微腐败”的行为主体,对其主体范围的把握不宜扩展至社会治理的各个领域。习近平总书记也曾明确指出:“‘微腐败也可能会成为‘大祸害,它损害的是老百姓的切身利益,挥霍的是基层群众对党的信任。”[7]有鉴于此,“微腐败”的主體范围应更为特定,仅限于基层工作人员,这也与“微腐败”的小微性、直接性等特征不谋而合。可以说,“微腐败”的行为后果都较为轻微,但祸患常积于忽微,微权力的腐化所直面的是普通群众的利益诉求,侵害的也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同时,“微腐败”的隐蔽性强、社会容忍度高等特点也消耗着政府的公信力和权威性,长此以往,将使政府在权力场域中陷入“塔西佗陷阱”。纵观近年来“微腐败”的整治情况,乡村“微腐败”占据着“微腐败”治理案件的大多数,也成为“微腐败”治理的症结所在。①乡村“微腐败”案件呈现出以下特点:一是腐败案件的村级化明显。从公开数据不难发现,乡村组织属于“微腐败”的易发、高发和频发的“重灾区”。究其原因,同村级社会的“圈子文化”有着莫大的关系。在熟人社会里,“请托帮忙”成为领导干部工作的常态,从而模糊了形式权力与实质权力的关系界限,也为腐败文化的生成埋下了隐患。以制度化代替人治化,将是未来乡村“微腐败”治理的价值目标。二是集体“微腐败”现象突出。由于乡村社会宗族文化明显,村民往往借助宗族势力进行腐败犯罪。同时,宗族的人情和互助文化也让集体贪腐成为可能。这种合谋动机下的权力联合演变为集体贪腐行动,不仅导致“微腐败”的集团化现象明显,也增加了乡村“微腐败”的治理难度。三是贪污等职务型犯罪占比较大。同样依据中纪委监察委2018年通报的典型案例,乡村“微腐败”中贪污行为占比为30%,索受贿赂行为占比为18%。仅此两种职务型犯罪就占据了乡村“微腐败”案件的近半比例,对此类行为的专项整治将是下一阶段政策制定的重点所在。四是贪腐手段形式多样、隐蔽性强。乡村“微腐败”的特点即小而多,小是指腐败所涉金额较小,多就是贪腐手段繁多。贪腐手段从以往的截留挪用、虚报冒领等直接占有到间接参股分红、共同承包建设等变相贪腐形式。如云南禄劝县纪委总结了村组干部扶贫领域“回扣式”“巧取式”“蒙骗式”三种“微腐败”新变种类型。[8]这些新型贪腐行为隐蔽性极强,无形中增加了腐败的治理难度。
(二)乡村“微腐败”治理的必要性
1.反腐倡廉建设有序推进的现实要求。腐败的所有形式都体现着侵蚀性,破坏和消弭着自由、正义、公平等民主元素。一个国家的腐败程度会使得改革变得步履维艰并让公众对政府产生合法化质疑,由此走向恶性循环。腐败是一种信号,显示一个国家的治理出了问题。[9]腐败的存在会弱化行政机关在连接国家与民众之间内在关系的作用,从而丧失公共服务的价值基础,使之成为侵蚀公共利益的工具媒介。而轻微的腐败行为即“微腐败”,更易被社会公众知晓或察觉,也就更易成为侵蚀政府公信力的隐形蛀虫。此外,“微腐败”如果不能及时被制止,会在潜意识里加剧公职人员变本加厉地从事贪腐活动,“小官巨贪”由此产生。无论是“微腐败”本身的侵蚀性还是可能演变的“小官巨贪”危机,都体现出反腐倡廉建设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当前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基本框架已初步形成,未来将朝着体系化、导向化和统筹兼顾的方向发展,这其中对腐败“零容忍”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腐倡廉工作的新常态。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要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10]对腐败“零容忍”的治理着力点就应当是对“微腐败”的治理,唯有此才能彻底扫清反腐败盲区,建立全方位、无死角的腐败治理体系。
2.乡村社会多维治理的制度保障。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社会发生重大变化,但生产生活方式的碎片化与村民自治体系的民主化之间的巨大张力,既消解着改革带来的各项福利,也让乡村社会和村民自治产生难以逾越的隔阂,过往的一元治理模式显得难以为继。多维治理时代的到来为乡村治理提供了可行方案。从乡村社会的治理主体出发,主要由政府机构、民间组织和公民个人三部分组成,分别代表着国家主体、社会主体和行动主体。三方共同参与可以充分发挥多元主体与行为规范的交互作用,以确保乡村治理的有序运行。但不容忽视的是,在多维治理框架下任何一个组成部分的缺失或异化都会使乡村治理走向治理僵局,而乡村“微腐败”正是让治理主体丧失本来意义的重要元素。权利服务的目标不是公共利益而是个人私益,腐败在这一过程中就形成了。[11]乡村“微腐败”的存在不仅直接侵害着贫困农民的切身利益,也会导致乡村治理结构失衡,多元治理的活力损失殆尽。腐败以牺牲广大弱势群体的利益为代价来使一小部分特权人士获利,或是牺牲未参加者的利益使所有参与者获利。[12]5因此,权力扩张下的腐败行为导致民主性和公共性异化为自利性与非正义性,公民的合法化权利也将逐步被侵蚀。不过腐败虽具有涉权性,即腐败来源于权力,但并不意味着权力必然会产生腐败。权力孕育着腐败产生的可能性,但尚只是停留在可能阶段,只要有规则和制度的及时保障,腐败就无法转为现实。因此,乡村“微腐败”的治理不仅可以让公权力保留公共属性,而且是乡村社会多维治理的应有之义。以治理乡村“微腐败”来实现公权力在乡村治理的良性运行,可以激发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公共精神,最终推动乡村治理的现代化转型。
二、软法介入的正当性审视——一种功能主义的分析框架
功能主义分析方法主张以功能的眼光来解释一切在发展水准上的人类事实,强调将社会事实置于其所处的特定环境中去考察和分析,研究其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与联系。[13]作为一种较为重要的社会科学研究范式,功能主义原则将法学研究的关注点转向法律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即法律在解决社会问题中有什么作用,发挥着什么样的功能。毫无疑问,功能主义的分析视角强调法律实施的社会规范性基础,并以其内在的合理性价值重塑着社会理想化变迁。
软法是与硬法相对应的概念,起源于国家法语境下的软法概念。所谓“软法”,是指那些效力结构未必完整,无须依靠国家强制保障实施,但能够产生社会实效的法律规范。实际上,软法在我国早已存在,本土社会中亦存在着大量的软法资源,但受制于部分学者对软法理论的怀疑和批判,始终未能系统全面地总结软法在社会治理中的应有功能。事实上,软法的嵌入机制契合乡土社会的法律传统,同时功能主义的“实质合法观”也是软法制定公共性目标的集中体现。功能主义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是社会问题和社会需要,有助于摆脱传统法律概念和思维方式的桎梏。[14]本文从功能主义视角出发,意将软法置于乡村社会的特定文化环境中去考察,分析其在“微腐败”治理中的正当性基础和合理性依据,从而为后文提出乡村“微腐败”治理的软法路径创设前提性条件。
(一)弥补单一法规制之不足
硬法规制是治理“微腐败”的一种基本方式,也是一种传统的治理模式。在治理“微腐败”的法律体系中,宪法位居最基础性地位,也是最核心地位。《宪法》第十二条规定:“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用任何手段侵占或者破坏国家的和集体的财产。”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監察委员会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监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些都为我国反腐倡廉建设提供了立法之基和根本保障。此外我国虽未建立专门的反腐败法律,但在《刑法》《刑事诉讼法》《监察法》以及《审计法》等多个部门法中都有关于查处腐败犯罪的规定。①应当说,我国已基本建成了规范化、多维化、常态化的反腐败法律规范体系。
但也应看到,硬法的滞后性、反复性、片面性等缺陷使得反腐败工作远未达到预期效果。一方面,现有法律并未形成完整的腐败治理体系。以《宪法》为例,虽间接体现了腐败治理的相关内容,但并未直接规定廉政建设的条款表述,使得腐败治理与廉政建设的规范过于模糊化,从而缺乏腐败治理的基本法指导。另一方面,“微腐败”是一种极为特殊的腐败形式。从犯罪数额来看,“微腐败”的涉案金额是三万元以下,而根据《最高院、最高检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三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才能被认定为贪污数额较大。”②贪污不足三万元的虽违反贪污或受贿罪,但通常可罚性较低。这就使得“微腐败”治理难以涵摄至现行刑法体系下,也让腐败分子产生侥幸心理。此时只能依赖于党内法规对“微腐败”治理作更为细致的规定。不过党内法规一般被视为软法的表现形式,硬法规制的局限性也由此可见。反腐工作必须补充一种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合作、政府与非政府合作、强制与自愿合作的全新模式。[15]软法契合民主本意和自律原旨,对弥补硬法规制之不足有着无法替代的作用。可以说软法的参与填补了单一僵化的硬法规制的不足,实现了由管制到共治的“微腐败”治理转型,对多元社会治理结构的建立和良法善治行动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
(二)道德义务规范化的内在表达
道德是软法规范的现实表征,也是软法规范发展的重要来源。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现代软法是指“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可能产生实际效果的行为规则”。在此需要厘清“软法亦法”与“软法非法”的关系问题。依据哈特的法律概念定义,法是由约束力、正义和规则三个基本要素组成。[16]就这一定义而言,软法因其正当性基础、现实约束力和规范体系等特性符合“软法亦法”的标准。但是,法的本质特征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而软法是基于全体成员的道德服从而非强制施行,从这个角度而言,软法又不具有法的根本属性,亦即“软法非法”。需要指出的是,软法是否姓“法”的区分意义在于揭示软法的本质属性,从而明确道德义务能否成为软法的逻辑前提。对此,有的学者主张软法效力来源于人的内心服从,道德规范即是软法。也有学者认为道德与软法尽管都具有约束力特征,但道德并不是软法。笔者认为上述两种观点都过于绝对,道德准则是软法的订立来源,软法是道德义务的规范表达,即道德是软法的来源形式之一。理由在于,“规范”一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是指“约定俗成或明文规定的标准”,而“规则”是指“运行、运作规律所遵循的法则”。从字面意思不难看出,“规范”更贴合软法的内心遵守并加以约束的行为准则的内涵。因此,软法是道德义务规范化的内在表达,意在表明道德义务以明文规定的形式上升为软法规范,并依靠成员自身的合意成为一种标准从而达到自我约束的目的。可见,道德可以成为软法的逻辑力量,绝对的肯定道德就是软法或盲目的否定道德是软法都是不准确的。不过还需要进一步界定“微腐败”与道德之间的内在联系,即“微腐败”的不道德性。如果“微腐败”行为是违反道德准则或道德义务,就可以采用软法的形式加以规制,那么软法治理“微腐败”的正当性也就不言而喻。
在任何国家、任何时期和任何阶段,腐败都被视为一种不道德现象。诚如杰拉尔德·E·凯登所言:“腐败包含了自私、特殊主义、利用弱点和漏洞、不择手段地利用弱者以及黑幕交易等所有方式。”[12]360腐败的出现是公职人员利用自身职权以丑陋卑鄙的方式获得那些不应得、不公正、不道德的利益,这也是对民主制下公众利益堂而皇之地侵夺。尤其是“微腐败”的出现,侵犯的是最底層、最弱势、最手无寸铁的群体的切身利益,并且“微腐败”的传染性和渗透性远超一般腐败行为。而一旦腐败行为被暴露,破坏的将是政府权威和信誉。基层腐败是违反了人们广为接受的道德准则而不能被组织其他成员所接受的行为。[17]所以,个人的不道德性会让他们借助包括腐败在内的一切手段达到追求个人欲望的目的,这也是腐败的道德观想要表明的:越是信仰腐败的好处和威力,越有可能腐败。美国曾在“水门事件”后专门制定政府道德法对公职人员的从政道德行为予以法律规制。笔者认为,以道德准则上升为法律强制,无疑是道德硬法化的另一种说法,这将模糊强制性的道德观念与非强制性的道德观念之间的界限,因此并不能成为解决腐败问题的最佳方案。而道德义务的软法表达恰好可以回应腐败的不道德性和腐败治理缺乏威慑力等现实难题,也在道德反腐向法治反腐的转变过程中建立了缓冲带,不失为一种可供选择的理想方案。
(三)乡村治理民主性的充分发挥
如前所述,“微腐败”现象多发生于基层尤其是乡村地区,而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趋势下,民主性将成为影响现代化进程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村民自治的核心是公民依法直接行使各项民主权利,应当说民主性是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内在要求。法治与民主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两个核心要素。[18]不过,要把握好民主性原则,需要正确处理乡村治理与村民自治之间的关系。以“微腐败”为例,差序格局下的“微腐败”现象使得治理道路偏向内卷化风险,表现在乡村治理中的自治环节,自治主体即可能是腐败主体,自治权的异化导致权力过于集中,再加上乡村社会监管措施不到位,很容易导致“微腐败”愈发严重。因此,乡村自治的本意是民主性的充分发挥,但不受监督且过分集中的权力会诱发腐败产生的风险,结果反而会使基层民主沦为镜花水月的幻想。不过,软法可以在民主自治和乡村“微腐败”治理之间架构起新的认识视野。软法介入乡村“微腐败”治理可以实现民主性与自治权的内在统一。根据哈贝马斯的商谈理论,民主立法需要以有效性、参与性和合理性商谈为前提。[19]这种基于沟通理性形成的决策程序可以让公民权利、国家权力及合法之法三者之间互为表里、同步同构,这其中合法之法也成为连接各种关系和要素的中枢及纽带。而这里的合法之法正是与软法理念不谋而合。软法的回应型法要素同样以民主商谈为必备程序,软法的制定必须以充分的磋商为前提。就本质而言,软法机制体现为一种程序民主的商谈政治,这种商谈范式下的程序主义民主成为基层社会自治的重要表现形式。因此,软法不仅以民主性为前提,还可以反过来拓展民主制的边界范围,提升社会的民主化水平。以商谈为过程的软法制定程序,可以达成社会共识,不仅保障了公民的参与权、监督权等民主性权利,也让乡村治理现代化得以真正实现。
三、软法资源在乡村微腐败治理中的应用
现阶段乡村微腐败治理虽面临着重重困境,但是软法理念的提出为解决治理难题提供了可行方案。不过摆在乡村微腐败治理面前最大的障碍就是软法模式如何落地的问题。本文无意从纵向角度,也就是软法制定的各阶段与实施的全过程搭建治理框架,而是力图以横向界面为切入点,以现行几种主要的软法资源在乡村“微腐败”治理中的应用为脉络,勾勒出腐败治理蓝图。
(一)党内法规
十八大以来,党内法规已成为腐败治理的重要形式。尤其对于微腐败现象的治理,因其涉案数额较小、情节较为轻微等特点,现行《刑法》等法律规范难以对其做到有效规制。而一般软法资源由于惩戒力不足,也无法对腐败分子起到威慑作用。此时,党内法规作为一种特殊的软法形式承担着不可替代的“微腐败”治理功能。虽然学界对党内法规是否属于软法众说纷纭①,但笔者倾向于罗豪才教授的观点,将党内法规视为软法的一种重要资源。
现行的廉政建设党内法规文件有《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几十部法律文件,这其中既有约束性条款和惩治性条款,也有激励性内容和倡导性内容,可以说这些党内法规已经形成了多样化、规范化和长效化的反腐倡廉监管体系。尤其在“微腐败”治理方面,党内法规发挥着独特的作用:一方面,“微腐败”的轻微性和频发性使得传统硬法难以对其有效规制;另一方面,“微腐败”的社会容忍度高和传染性强等特征又呼唤着法治反腐时代的到来。此时,党内法规以其制定程序简便、兼容性强、威慑力大等优势成为腐败治理的有力武器。不过,现阶段党内法规在“微腐败”治理方面还存在亟待解决的困境:一是党内法规的精细化治理程度有待提高,表现为党内立规语言表述的模糊性。语言表述的模糊性是指党内法规的文本中出现大量的模糊词语和语句,使得在理解和适用党内立规时会形成很大的弹性空间,在判定行为是否合规时会遇到边界不清晰的困难。[20]以2018年刚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为例,该条例将十八大以来从严治党成果转化为纪律要求,实现了党内纪律处分制度新的跨越式发展。不过该条例仍存在着语焉不详的情况,例如该处分条例有着大量的“情节轻微”“情节较重”“情节严重”等表示程度的词眼②,那么对轻微、较重和严重的划定标准究竟是什么?这有待于对违纪行为划定更为细致的量化标准。此外,党内法规还存在着较多表性质、表心理的词句,如《处分条例》中有“清正廉洁”“贪图享乐”等表性质的词,也有“表里不一”“阳奉阴违”“自省自警”等表心理活动的词。③这些词句难以采用程式化的标准执行,也无法通过计量化的形式督查,一定程度上不具有可适用性。[21]类似于上述条款中的表程度、表性质和表心理的词句并不占少数,这些模糊性的词句会弱化党内法规的规范属性,也会让党内法规的权威性和执行力大打折扣。二是对腐败预防和激励教育性条款的忽视。“微腐败”治理的未来转向应是以腐败预防为支撑,激励教育为保障的新型治理体系。腐败预防制度是中国腐败治理体系中最为薄弱的部分,加快推进反腐预防法是重中之重。[22]我国的反腐败工作长期依赖于“压制型”惩治,而预防型反腐体系的优势即在于对回应型法治要求和贪婪人性本源的双重兼顾,实现积极治理主义下的腐败治理理念转型。除了健全预防腐败体系外,激勵教育机制也是必不可少的环节。党内法规除了具有惩戒、威慑的功能外,还发挥着教育、激励的作用。党内法规的激励规范有助于激发党员向上向善的动力,教育规范可以培养党员清风正气的意识。同时,预防腐败和激励教育条款也与软法的主体行为导向性理念一脉相承,有着极强的适格性。在乡村“微腐败”治理中,受村干部法治意识淡薄、薪酬待遇较低、监督机制不完善等因素的影响,更容易发生贪腐风险,此时在硬法规制尚未及时跟进的情况下,党内法规更应注重发挥预防腐败和激励教育的规范引领作用,构建源头化和全过程的乡村“微腐败”治理体系。三是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协调与衔接仍存在障碍。把握好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对表主要包括“衔接”和“协调”这两个具体要求。[23]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是中国特色反腐体系的两大基石,二者间的良性互动可以发挥腐败治理效果的最大化。现阶段,随着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纵深推进,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职能重叠冲突引起的重复工作问题,党纪与国法衔接不畅、各自为政的现象得到了有效缓解。[24]但是,二者在实践中仍存在一些不协调、不衔接甚至不一致的问题,主要表现在纪法边界模糊、衔接断裂和程序交错并用等方面。要实现二者的并行不悖与良性互动,需要从实体和程序两方面入手解决适用障碍问题。具体到乡村“微腐败”治理领域,实体层面上要推进反腐败立法体系的无缝衔接。为避免党规与国法的规范冲突,应规定应当由法律法规调整的事项,党内法规不再另作规定。[25]申言之,对犯罪数额较大的贪腐行为由《刑法》等进行硬法规制,而“小微腐败”行为则由党内法规作出规范。程序维度上,要推动党内监察和司法审查协调配合。对待乡村“微腐败”案件,原则上交由党纪监察处理,但监察过程中发现的情节严重或有其他违法情节的,应主动移送至司法机关处理。同时,双方还可建立反腐败信息共享机制和证据交互制度,实现乡村“微腐败”治理的良性互动。应当指出的是,党内法规在乡村“微腐败”治理中除了存在上述问题外,还面临着执纪手段刚性与柔性失衡、党内程序民主仍需完善等难题,这都需要进一步廓清和解决。不过,党内法规作为中国特色反腐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正当性毋庸置疑,以党内法规推进乡村“微腐败”的治理也将是建立民主法治国家下多元反腐体系的必然路径和选择。
(二)村规民约
村规民约无疑是一种极为特殊的治理乡村“微腐败”的软法形式。所谓“村规民约”,是指“村民在生产、生活中产生和形成的,并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利用道德约束机制,进行自我管理的民间行为规范的总称”[26]。从这一定义可将村规民约的基本属性概括为三部分:其一,村规民约是一种民间行为规范;其二,村规民约是生产、生活或习俗中产生和形成的行为规范;其三,村规民约是一种村民自治规范。这三部分属性也决定了村规民约是以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约束为前提和依托。可以说,以村规民约为代表的社会规范逐步成为乡村社会治理的主要制度资源。村规民约的民间法性质和契约本质,决定了其立法资源来自于乡土社会,同时制定过程中的民主协商也让规范的内容更贴合乡村治理实际,这种良法善治过程中的产物可以最大程度地让村民信任和服从,也因此成为乡村治理的主要制度资源。不过,当前村规民约在我国不同地区间形成了两极化的发展态势,一种是虚无主义文本形态。有的农村地区为应付上级政府的村民自治要求,在未经村民合意的情况下照搬照抄其他乡村的村规民约文本,导致制定出来的内容大致相同,村规民约的本旨追求也就荡然无存。还有一种就是结合地方实际的村规民约形态。在我国很多地方,尤其是民族自治地区,往往在不违反上位法的前提下,结合本土习惯和风俗制定具有村域特色的村规民约。例如黔东南阳芳村寨村规民约就是在政府指导下,既体现了民族习惯法,又利用村规民约维护旅游开发的村寨秩序,实现传统民族习惯法和现实经济发展需要的两者兼顾。[27]简言之,村规民约不仅有助于村民民主自治目标的实现,也对我国法治社会建设有着积极的推动意义。
具体到乡村“微腐败”治理环节,我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发挥村规民约的积极作用:首先是村务公开的推行。乡村“微腐败”的治理难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导致的,对“微腐败”监督主要由上级监督、同级监督和村民监督三部分组成。通过村务公开不仅让村干部实现自查自纠,保证村民自治的顺利开展,还能强化同级和村民对村干部的监督,让村干部的权力晒在阳光下。可见,村务公开制度的推行,可以提高信息透明度,拓宽公众监督渠道,明晰公权力的运行空间,实现乡村“微腐败”的精细化治理。其次,以村规民约弘扬反腐倡廉的社会风气。村规民约的制定应当打破传统的教条式范本内容,以新时代的新要求不断丰富村规民约的内容和形式。例如四川省古宋镇桃子坪村为厉行节约,制止铺张浪费,减少大操大办,通过了《桃子坪村移风易俗村民公约》。[28]这种以村规民约的形式弘扬反腐倡廉的社会风气,让村规民约不再沦为搁置一旁的虚无文本,成为乡村“微腐败”治理的又一利器。最后是村规民约惩戒力的合理运用。软法虽不具有国家强制力,但依靠内心自律、社会强制等方式产生社会实效,从而有着不亚于硬法的约束力。村规民约本质上属于软法,因此也具有一定的约束力和惩戒性。传统的村规民约以其严酷的惩戒机制使人产生恐惧心理,让村民服从村规族规的管制,但在现代民主制国家背景下,自然不允许超越上位法的惩戒条款存在。过往的剥夺自由、生命或者没收财产、驱逐出村的处罚方式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现行的村规民约主要有批评教育、道歉、罚款、取消或减少福利政策、移送司法机关等处罚方式。具体到乡村“微腐败”治理方面,对涉嫌轻微腐败的人员,可采取批评教育、写悔过书、罚款等方式让其意识到贪腐行为的后果。对情节严重者,可移送至纪检司法机关处理。这种社会强制力可以让村民产生自律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形成对腐败行为的内在阻力,也成为乡村“微腐败”治理的新范式机制。总之,以保障村民权利和整合乡村自治为核心的村规民约,有助于形成民主化与法治化的规范体系。就此而言,村规民约治理乡村“微腐败”的合理性和正当性毋庸置疑。
(三)其他软法反腐形式
除了党内法规和村规民约成为反腐倡廉软法资源外,还有大量软法形式亟待发掘。如前所述,根据能否运用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为内涵划分,可以将软法分为以下四类:一是国家立法中的宣示性、鼓励性和号召性软法规范,即柔性规范。二是国家机关制订的大量规范性文件。三是以党内法规为代表的各类政党、政治组织制定的自律性规范。四是社会组织创设的自律规范,例如社区、协会等自律公约。从以上分类可知,乡村“微腐败”仍留有很大的软法治理空间。因本文已对党内法规和村规民约的“微腐败”治理价值作类型分析,下面将着重论述前两种软法资源的可能贡献。
首先是国家立法中的柔性规范。以《刑法》为例,第二条规定:“刑法的任务就是同一切犯罪行为作斗争,以保卫国家安全、政权和社会主义制度,保护国有财产和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的财产。”第四条也规定:“对任何人犯罪,在适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权。”除了《刑法》外,《监察法》《法官法》《检察官法》中亦存在着许多柔性规范。这些宣示性、号召性和指导性条款意在揭示立法的任务及功能,表明国家在打击包括“微腐败”在內的一切违法行为的信心和决心,逐渐成为拓展国家法领域新的发力点。其次是规范性文件的运用。目前存在大量的规范性文件对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有着一定的影响。就乡村“微腐败”而言,中央层面的有《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工作规划》《关于推进廉洁乡村建设的实施意见》《关于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的指导意见》等等;地方规范性文件,例如《锦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系统廉政建设的实施意见》《云南省关于贯彻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意见》等等,都对乡村“微腐败”治理起着积极作用。除了国家直接订立的规范性文件外,司法政策作为一种特殊的软法实践成为时常被学界忽视的空白领域。司法政策是在立法缺位和司法能动主义下实现社会公平治理的必然选择。例如,最高院出台的《关于贪污受贿量刑指导意见》就是为打击贪腐行为而作出的政策考量。可以说,这些规范性文件存在能够快速回应社会发展的新要求、规范权力行使的边界,一定程度上打开了乡村“微腐败”治理的新格局。
在现代法治国家的多元治理语境下,软法概念的廓清并设计巧妙的适用机制不仅可以走出传统单向管制法范式的“围城”,还可以为公共治理崛起中治理手段变革贡献新的时代智慧。可以说,软法之治既是一种国家治理模式,也是国家间的世界秩序模式,既是我国传统政治智慧的现代重述,也是当代国家治理的特有之意。[29]本文受篇幅限制着重论述了软法在乡村“微腐败”治理的应然贡献,但是徒硬法不足于自行,徒软法亦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乡村“微腐败”治理的最优模式应当是建立软硬并存的共同治理模式。这种混同法治理模式既能矫正单一法的治理偏差,也能消解因立法漏洞未及时填补和社会发展对法律规制需要产生的紧张关系。具体在处理乡村“微腐败”问题时,一方面,要制定专门的反腐败立法,尤其是乡村“微腐败”治理方面的立法;另一方面,针对硬法反腐过剩而软法反腐不足的现实困境,应积极探索软法治理乡村“微腐败”的可能路径,构建起多层次、多维度、综合化的乡村“微腐败”治理体系。硬法和软法是法治反腐的一体两翼,法治反腐必须要软硬结合,即不仅需要作为硬法的国家法,更离不开作为软法的社会法。[30]展望未来,在进行具体制度设计时应通过软法与硬法相互配合,形成良性互动的双重规制体系,这才是乡村“微腐败”治理最理想的模式。
参考文献:
[1] 吴光芸,田雪森.差序格局下的村镇干部微腐败及其治理[J].长白学刊,2018(4):56-60.
[2] 卜万红.“微腐败”滋生的政治文化根源及治理对策[J].河南社会科学,2017(6):63-69.
[3] 赵秉志,彭新林.习近平反腐倡廉思想研究[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122-133.
[4] 李晓明,张长梅.腐败概念的泛化与界定[J].当代法学,2008(3):52-57.
[5] 任中平,马忠鹏.从严整治“微腐败”净化基层政治生态——以四川省基层党风廉政建设为例[J].理论与改革,2018(2):49-58.
[6] 余雅洁,陈文权.治理“微腐败”的理论逻辑、现实困境与有效路径[J].中国行政管理,2018(9):105-110.
[7]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EB/OL].(2016-05-03)[2019-08-05].http://www.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03/c_128951516.htm.
[8] 禄劝:村组干部扶贫领域“微腐败”新变种类型分析[EB/OL].(2017-09-06)[2019-08-10].http://www.jw.km.gov.cn/c/2017-09-06/2072874.shtml.
[9] (美)苏珊·罗丝·阿克曼,邦尼·J·帕利夫卡.腐败与政府:根源、后果与改革[M].郑澜,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8:52.
[10]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18(1).
[11] 李晓明,等.控制腐败法律机制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28.
[12] (美)杰拉尔德·E·凯登,等.腐败:权利与制约[M].王云燕,译.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7.
[13] 夏建中.文化人类学理论学派[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132.
[14] 雷安军.比较法研究中的功能主义原则、法律文化和法律移植[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169.
[15] 罗豪才,等.软法与公共治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90.
[16] (美)哈特.法律的概念[M].许家馨,李冠宜,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73.
[17] 谭亚莉,廖建桥,李骥.管理者非伦理行为到组织腐败的衍变过程、机制与干预:基于心理社会微观视角的分析[J].管理世界,2011(12):68-77.
[18] 齊卫平.乡村治理:问题与对策(笔谈)——乡村现代治理要求基层党组织再造凝聚力[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6(1):1-12,169.
[19] 哈贝马斯.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关于法律和民主法治国的商谈理论[M].童世骏,译.上海:三联书店,2003:120.
[20] 陈光.论党内立规语言的模糊性及其平衡[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8(1):29-36.
[21] 苏绍龙,秦前红.论党内法规的适用规则[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1):124-140,191-192.
[22] 刘艳红.中国反腐败立法的战略转型及其体系化构建[J].中国法学,2016(4):218-244.
[23] 宋功德.坚持依规治党[J].中国法学,2018(2):5-27.
[24] 冯铁拴.中国监察体制改革论析:过去、现在与未来[J].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8(2):15-25.
[25] 秦前红,苏绍龙.中国政党法治的逻辑建构与现实困境[J].人民论坛,2015(20):14-21.
[26] 蒋传光,张彧,张文友.中国农村民主与法制进程[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6:199.
[27] 孙韡.黔东南苗族村寨村规民约研究[M].西安: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73.
[28] 古宋镇桃子坪村村支部书发话了,反对铺张浪费大操大办[EB/OL].(2018-03-29)[2019-08-10].http://www.sina.com.cn/article_6425378112_17efb7d40001004hi9.html.
[29] 張龔.软法与常态化的国家治理[J].中外法学,2016(2):316-331.
[30] 刘长秋.我国法律反腐的问题与对策研究[J].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101-108,148.
责任编校 陈 瑶
Abstract: “Micro-corruption” treatment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the completion of anti-corruption work, and also a key task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corruption. In particular, rural “micro-corruption” has become a chronic disease because of its large number and hidden nature. Traditional hard laws bear the responsibility of cracking corruption with the principle of rule of law as they do, relying entirely on hard laws does not help much in the wholesale treatment of “micro-corruption.” The rise of public treatment has laid a logical foundation for soft law to play a part against corruption. Based on the functionalist analysis framework, the soft law has the function and advantage unparalleled by the hard law in making up for the defects of the single legal system, in the standardized expression of moral obligations, and the democratic treatment of rural areas. The use of soft law resources represented by Party regulations and village regulations also provide a feasible means for rural “micro-corruption” treatment. However, it is impossible to fulfill the rural “micro-corruption” treatment task with any single legal system. Coordinated “soft and hard treatment” will be the most ideal model for rural “micro-corruption” treatment.
Keywords: rural micro corruption; anti-corruption by legal means; soft la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