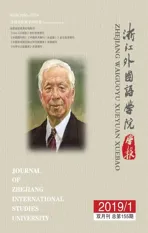后灵魂美学与《地下铁道》的生命叙事
2019-01-30谌晓明
谌晓明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国际商务外语学院,上海 201620)
自成名作《直觉主义者》(The Intuitionist,1999)以来,科尔森·怀特黑德(Colson Whitehead,1969— )一直追求着文学实验和雅俗共赏间的微妙平衡。在创作形式上,他奉行乔伊斯式的“焦土原则”(Joyce 1966:129),坚持用创作革新来挑战自我;而在创作题材上,他在深挖非裔叙事的民族之根和文化之魂的同时,主张摆脱民权运动以来的叙事规约,用后灵魂时代的编史元小说来表征新的时代风貌。基于这一创作理念,他的近作《地下铁道》(The Underground Railroad,2016)接连斩获国家图书奖和普利策文学奖,成为美国文坛近年来不多见的“双黄蛋”。该小说通过对科拉逃亡历程中的语象和声景叙事来表征新媒体时代的生命政治。它将历史与现实融为一体,在虚构和真实之间建构文本化的生命;将资本帝国的剥削巨网置于全球化的语境之下,在利用与反利用的斗争中批判经济化的生命;让种族歧视的斑斑劣迹与“黑命贵运动”(Black Lives Matter)和特朗普主义互文,在控制与反控制中反思种族化的生命。
一、文本化的生命:后灵魂美学和编史元叙事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生代的非裔作家开始逐渐摆脱对传统叙事的依赖,从后民权现实和后现代主义思潮中找寻灵感,希望用新的内容和形式来展现自己对历史和现实的理解。从哈佛大学毕业后,怀特黑德便积极投身于这股新黑人叙事的浪潮中。在《地下铁道》这部作品中,他结合后灵魂美学和编史元小说技巧来展现文本化的生命,在虚构和真实间建构新的黑人生命政治观。
(一)后灵魂美学下的生命
“后灵魂”一词为纳尔逊·乔治于1992年率先提出,起因是《公告牌》杂志对黑人音乐的归类问题。1982年,Run-D.M.C 乐队开创了说唱音乐形式,“灵魂音乐”(soul music)和“黑人音乐”(black music)二词都无法描述这一新的艺术现象,最后只好以“不合时宜的规避策略”选择了“节奏和蓝调”的命名。乔治认为,放弃“灵魂”的命名不可取,因为它失去了“灵魂”一词所代表的“黑色精髓”和“黑人精神”。他认为“后灵魂”兼具传承和创新之意。民权运动之后,黑白分明的隔阂依旧存在,传承黑人精神和灵魂音乐有益于启发后人。20世纪60年代以来,黑人音乐经历了从乐观的乡村福音和蓝调向“虚无主义、黑人中心主义和消费主义”的城市意识的转变(George 1992:7),“后灵魂”一词更能准确传达新民族意识下黑人流行文化的现实蕴含。在文学领域,后灵魂意识给科尔森·怀特黑德、保罗·贝蒂等新生代作家提供了重要的创作美学指导。
在《灵魂宝贝:黑人流行文化和后灵魂美学》一书中,尼尔进一步明确了后灵魂状态和后灵魂美学的内涵。他指出,后灵魂一代寻求“与(民权斗争)胜利关联的怀旧情结分手,秉持一种传统民权领导既不愿意也不能够采纳的客观立场,对运动的遗产进行批判性地接受”(Neal 2002:103)。他认为,后灵魂指的是后民权运动人士对文学与政治先驱者的矛盾心态。灵魂思想主张的灵魂、精神和文化真理是一种对时代精神的天真和简单认识。在后灵魂的状态下,作家们倾向于用反讽、怀疑的眼光来看待黑人民族文化,扬弃宽泛笼统的“黑人性”概念。新灵魂美学具有强大的感召力,新世纪以来,怀特黑德、贝蒂等新生代作家经常将主人公置于后灵魂语境之中,让其在与集体的对话中充分表露自身对不同族群文化的复杂反应。
在《地下铁道》中,怀特黑德借助后灵魂隐喻对黑人生命体验加以表述,突显现实语境与经典历史的断裂性和异化感。在怀特黑德的笔下,灵魂叙事中的千人一面、万众一心的族群身份意识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若即若离、游走在族群边缘的角色,用个人独特的话语对历史和现实中的阶级、种族、性别等体验作出反应、评述和反抗。小说描述了自外祖母阿贾里从非洲被贩卖到美国后,三代黑人女性的悲惨遭遇和数次逃亡经历。在艰辛和残酷的现实中,阿贾里、梅布尔和科拉展现出令人感佩的人性力量。作品放弃了经典的慈母视角,用冷峻得近乎残忍的口吻呈现了生存极限状态下的母亲形象。在主人公科拉的记忆中,外祖母和母亲在给予她生命的同时,也时常流露出一丝的不近人情。外祖母阿贾里生过五个孩子,她经常指着木屋的破板床教训不听话的孩子,威胁要把他们塞回那里。而对于母亲梅布尔,科拉感受更多的则是那种割裂的亲情。为了独自逃亡,梅布尔抛弃了年幼的科拉。母亲出逃那天,科拉只记得自己是“依偎在妈妈肚子上进入梦乡,此后再也没有见到她了”(Whitehead 2016:47)①为方便起见,后文引用Whitehead(2016)时只标注页码。。母亲只存在于灰色的记忆中:她寡言少语,性格倔强,在黑人社区吃不开,她走之后留给科拉的是更加恶劣的生存环境。等到科拉自己长大逃亡在外时,她依然对妈妈抛弃自己的选择不能理解。在北卡罗来纳的一间阁楼上躲避猎奴者的追击时,她幻想着自己的理想生活:铺着雪白被单的床,两个孩子和她一起在床上打滚。她还假想在街头偶遇沦为乞丐的母亲,一气之下,用脚踢翻了她的讨钱罐,转身去市场为儿子买做蛋糕的面粉(207)。亲情关系在蓄奴制下的断裂和异化让梅布尔背负着巨大的负罪感,在《地下铁道》的倒数第二章,怀特黑德安排了梅布尔的自述。文中她充满悔意,“她给女儿的第一件和最后一件东西都是道歉”,她为带她来到这个世界而道歉,为让她在十岁那年成为没爹没娘的孩子而道歉(349)。在逃亡的过程中,她害怕想起科拉稚嫩的脸蛋儿,也动摇了前行的信念,想再次回到女儿身边。她希望科拉足够坚强,终有一天能像她一样越过已知的一切,拥抱新的生命。很显然,作品通过对梅布尔所隐喻的灵魂时代母亲形象的批判和扬弃,彰显了后灵魂美学下的叙事自由和话语自信。
怀特黑德将三代黑人女性形象并置,借用科拉这个后灵魂叙事的传声筒,既控诉了黑人生命所遭受的世代苦痛,又展现出21世纪当下的生命叙事美学。对怀特黑德来说,科拉与母亲和外祖母之间对于生命认知的代际差异具有重要的时代隐喻意义。作为后灵魂的代言人,科拉对母亲生而不养心怀怨言,她认为梅布尔若沦为乞丐是“恶有恶报”。而母亲梅布尔则将自身的悲剧归咎于环境,相信“人初本善,世使人恶;世始于恶,日久愈恶”(351),源自外祖母阿贾里身上的原初亲和力逐渐消失,梅布尔成为亲情断层的代名词。质言之,在科拉眼中,她的外祖母和母亲就像霍奇对民权运动人士的评论那样“老派、不近人情、高高在上、喜欢妄下结论”(Hodge 2010:62)。而反过来,阿贾里、梅布尔认为自己对于后代的失责和苛求是时代使然,她们的付出没有得到足够的尊重,新生一代过于“失德、失敬和世俗”(ibid)。
《地下铁道》的后灵魂生命叙事还体现在新黑人美学(New Black Aesthetics)上。新黑人美学是作家特雷·艾里斯对“文化穆拉托”(cultural mulattoes)社会批判思想的概括,最早出现在1989年出版的杂志Callalloo中的同名论文里。“文化穆拉托”本义是指“成长在白人、中产郊区的,经常被白、黑两个世界误解的非裔美国人”,艾里斯认为当代黑人作家要勇做“文化穆拉托”,自由地去创造能体现多重影响力的艺术作品,借此确立一种“跨越种族和阶级界限的,大胆借鉴和重新组合的开放性新黑人美学”(Ellis 1989:234)。新黑人美学继承了上一代人的抗争精神,并将其移植到新的时代语境中,在叙事立场上远离陈腐平庸的仇恨叙事,敢于对黑人组织的刻板官方路线发起挑战。在怀特黑德看来,新黑人叙事美学是一种代际互动性的反讽视角,年轻一代对民族认知的不同理解是造就这一视角的直接原因。他们不认可灵魂文化中的权威和正面形象,追求“在偶然和多样的黑人性中狂欢”(Taylor 2007:631),乐见作品中的经典形象被颠覆、戏仿和曲用。
具体到《地下铁道》中,生命形式在饱受种族歧视和残忍对待的同时,黑人族群内部问题也昭然若揭。怀特黑德放弃了对黑人文化浪漫化的表述,作品对邻里矛盾不是讳莫如深,而是用反讽和嘲弄的语气和盘托出。梅布尔出逃之后,小科拉落难伶仃屋,为了守护外祖母遗留下来的三码见方的自留地,她先后受到黑人邻居的多重欺压。在这块“法律每天都在重写”的地方,种族欺压已经令人不堪忍受(19),年仅十岁的科拉却挺起胸膛抵御了阿娃的百般刁难,拿起板斧赶走了恶人布莱克和他的党羽。面对顽强且不可战胜的科拉,他们便散布谣言来污损她的名声,使她最终被他们合伙凌辱。这种小女斗群恶的场面充满着讽刺意味,黑奴社区中的炎凉世态更让人心寒。当布莱克一伙搬弄是非的时候,周围没有一个人为她撑腰。在被人凌辱时,即使“有人看见或者听见,也没有加以干涉”(25)。在此,怀特黑德用辛辣的话语批判了这种族群内外的压榨行为,并希望借此与传统的黑白世界决裂,抛弃单一的、宽泛的黑人性,用“文化穆拉托”的理想重构新的世界。
(二)编史元小说中的生命
从哈佛大学毕业之后,怀特黑德开始了自己的艺术探索之旅,《地下铁道》是他在编史元小说创作上的新成就。1999年,他的《直觉主义者》运用电梯这一垂直运载工具来讽喻现代都市中的空间、建筑、种族等社会问题。《约翰·亨利的岁月》(John Henry Days)运用元小说叙事将14个不同的版本并置,叙述了非裔铁路工人坚强而悲怆的人生经历。而《地下铁道》则完美地结合了这两部作品中的叙事技巧,普利策小说奖评论该作品将“现实主义和讽喻巧妙地融为一体,结合暴力的蓄奴制和戏剧性的逃亡历程,在传说中观照当代美国生活”(Pulitzer 2017)。国家图书奖的授奖词更加明确地指出:“《地下铁道》是对科尔森·怀特黑德这位被誉为最敢于创新作家之一的认可。作为一个关于逃亡和追击的充满悬念的故事,它将幻想和反事实的元素与大胆、真切的美国奴隶制描写结合起来。”(National 2016)
《地下铁道》中的编史元小说技巧之一就是模糊历史和虚构的边界,用质朴冷静的叙事风格观照历史、情感和现实中的生命。作品中最主要的历史和虚构便是关于地下铁道的传说。怀特黑德通过科拉、西泽、萨姆、伦布里、马丁等虚构的亲历者转述关于地下铁道的各种细节,让“既被使用又被滥用,既被安插又被颠覆,既被宣扬又被否定”(Hutcheon 1988:3)的虚构历史图景展现在21世纪的读者面前。出于同情,科拉宁愿作为肉盾代替切斯特挨打,死去活来之后,她开始关注传说中的逃亡通道。此时,科拉的视角不仅有着明显的自我意识,还弥漫着强烈的虚构色彩:在詹姆斯去世后,特伦斯接管了种植园,科拉意识到“她过去不是他的人,现在是他的了。或者说,她过去一直是他的,只是她现在才知道这一点”(56)。科拉的思绪开始超越自己和同样在种植园受难的奴隶兄弟,文中写道:“她通过见过它(地下铁道)的奴隶的叙述,努力地从一个个故事当中给它填入细节。”(57)视野里的一切就像一条鱼,自由蜿蜒地前行,转瞬就跑掉了。怀特黑德巧妙地借科拉之口,对作品的虚构特性予以交代。然而,随着故事情节的深入发展,当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用真情实感诉说着“亲身经历”时,作品的现实性愈发强烈,其激发的史观和情感已经超越了对小说虚构本身的怀疑,正如科拉所言:“如果她想留住它,就必须亲眼看到它。”(57)
作品中有关地下铁道的传说从梅布尔逃亡便开始了。奴隶们相信有“秘密的干道和神秘的线路”,从“某个不可思议的源头出发,通往一个难以置信的终点”(80),但对奴隶主而言这些都不足为信。比如当老兰德尔听到猎奴者转述地下铁道新支线的流言时,他“一笑了之”(49)。而当科拉第一次踏入地下铁道的时候,她认为“赞叹二字已不足以形容眼前的景象了”(80)。其实,怀特黑德对于地下铁道的描述并没有超越普通的认知,那景象只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小站罢了,窄小的月台伴着一股酸臭的味道。它延续了《约翰·亨利的岁月》中寄托于地下铁道的非裔美国人的话题,借此传达黑人们追求自由解放的奋斗历程。作为传说,它是一个通道隐喻,它存在与否并不重要,历史的真假和答案的虚实也非重点。比如作品中当科拉问列车去哪儿时,得到的回答是“离开这儿”(81)。只有等你到了站,才知道前面等待你的是什么。因此,某种意义上讲,怀特黑德此书的目的就是:乘坐一段虚构的历史列车亲历历史。当科拉和西泽乘上列车出发的时候,地下铁道站长伦布里说道:“如果想看看这个国家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你们得坐火车。跑起来以后,你们往外看,就能看见美国的真面貌。”(83)而在小说中,地下铁道又超越了虚构隐喻的成分,它伸手可及的现实性又将历史拉回到了21世纪的今天,历史不单单是沉渣泛起,更多的是它的现实意义。作品的结尾处,阴险狡诈的猎奴者里奇韦再次将科拉捕获在手,这一次他要亲自见见大名鼎鼎的地下铁道。他说道:“地下铁道,大部分人以为这只是个比喻。我可没那么愚蠢。秘密就在我们脚底下,一直都在。今晚一过,我们就会让一切都大白于天下,每条线路,每个参与者。”(359)面对看见地下铁道的第一个敌人,科拉拼死抱住里奇韦,双双滚落地下铁道,顽强的科拉保守住了地下铁道的秘密,成功逃亡到北方。此时的科拉想象着黑人铁路工人,挥舞铁镐,劈石凿道,抡起大锤,敲击道钉。建设者们的经历同逃亡者一样,在经历一番艰辛旅程之后,重新迈进阳光里便焕然一新了(362)。地下铁道的秘密是珍藏于黑奴和其同情者心底里的历史宝藏,它量子力学般的神秘力量激励着非裔美国人奋斗不息,即使在21世纪的今天也是一条引向自由平等的光明通道。
《地下铁道》中的编史元小说技巧之二体现在其对史料的采集和处理上。在作品的构思过程中,怀特黑德参考了北卡罗来纳大学收藏的逃奴缉拿广告。在行文中,他巧妙地将它们穿插在作品的六个章节里,让这些真实的生命个体与作品的虚构情节相互照应,使得文本游走在“听和讲、叙和表、拼和拆”的动态过程之中(谌晓明2016:4)。科拉的母亲梅布尔是生活在浓厚谣传氛围中的一个悲剧角色。在科拉的想象中,母亲收拾了简单的行囊,毫无征兆地趁着满月从兰德尔种植园出走,并最终成为第一个成功逃脱的黑奴。对于梅布尔的不辞而别,科拉在心怀怨恨的同时,又期待能了解其中的真相,在自己的逃亡路途上也曾多次打听母亲的下落,然而每次都是徒劳。最终,怀特黑德在作品的结尾处让梅布尔亲自叙述了自己的悲惨遭遇。事实上,在成功走出黑水沼泽之后,梅布尔欣喜若狂,然而因为无法与爱女科拉分享这一美妙时刻,此时的她最终被懊悔和歉意战胜,决定返回科拉身边。踏上返程不久的梅布尔被水蛇咬伤,最终消失在黑水沼泽之中。这种传言在作品中还先后发生在科拉的外祖母阿贾里和西泽身上。阿贾里被贩卖到美国后,听闻家族中的其他表亲随后也被贩运过来了。即使在自己最不堪的奴隶生涯中,她还经常想象着依赛、西多等人成功地赎了身,在宾夕法尼亚过着自由人的生活。殊不知,狭窄肮脏的运奴船上瘟疫流行,当局因害怕疫病传开,下令放火烧船,阿贾里的表亲早已离开人世。另外,在逃亡到北卡罗来纳之后,科拉也曾多次假想同伴西泽在经历多重波折后最终脱险,并过上了自由幸福的生活。残酷的事实却是,西泽在南卡罗来纳逃往地下铁道的途中被截,惨死在奴隶主手中。作品中,叙述者在彼此分隔的时空下诠释过往,历史在虚构和事实之间游走,“真相就是商店橱窗里不断变换的商品,在你看不到的时候任人摆弄,看上去很美,可你永远够不着”(139)。尽管如此,怀特黑德依然坚信历史书写的力量,因为对于经历诸多磨难的非裔美国人来说,“一个有用的妄想要好过无用的真相”(285),科拉这句话恰恰是《地下铁道》中历史元叙事的用意所在。
《地下铁道》中的编史元小说技巧之三是其话语自反性,作品的语言符号中弥漫着戏仿和嘲讽,黑人生命在文字的矛盾嬉戏中超越了传统的阈限,突显出后灵魂时代的种族生态观。迪克森-卡尔指出后灵魂叙事善于将讽刺和戏仿与元小说技巧结合,通过刺破传统叙事中的愚钝、荒谬、表里不一的话语核心,破除道德、文化和灵魂中的偶像崇拜,在不可言说中开讲,在伤口最深处去伪求真(Dickson-Carr 2001:18)。作品中关于黑人识字的叙述具有独特的表现力。在南方种植园,一方面,白人奴隶主用尽各种办法阻止黑人读书识字,将妄图接触书本的奴隶挖去双眼,认为“黑鬼拿书比黑鬼拿枪更危险”(326);而另一方面,在佐治亚的种植园,奴隶主们又时常把记忆能力超常的黑奴当作玩物戏耍。比如,迈克尔并不识字,在被转卖给兰德尔兄弟之前却学到了背诵长文的能力。他的前主人因对南美鹦鹉着迷,因此便推断,如果能教会一只鹦鹉学会打油诗,那么让黑奴背点东西也应在情理之中,因为他认为“黑鬼的脑子毕竟比鸟的大”(37)。于是,他便开始教迈克尔背诵《独立宣言》,虽然对游手好闲的奴隶主自己来说,理解和背诵它都十分吃力,但主仆二人最终创造了奇迹,目不识丁的迈克尔背诵《独立宣言》也成为奴隶庄园里的一大奇闻。怀特黑德在叙事视角上冷静犀利,深入黑白两种话语的内核,在批判嘲讽中讲述人生。迈克尔的超常能力在博宾客一乐的同时,从未超越鹦鹉学舌般的低智表演的实质,他最终被喜新厌旧的主人转手卖到兰德尔庄园。在这里,正当特伦斯想见识迈克尔的背诵水平的时候,却被告知他因劳动不力而被监工康奈利鞭打至死。让不识字的黑奴背诵《独立宣言》是对经典叙事的莫大讽刺,它在炫耀白人奴隶主“文治武功”的同时,揭露了《独立宣言》文本在历史时空上表现出的矛盾性和荒谬性。在南卡罗来纳的博物馆里,科拉幸运地成为展演蓄奴制历史的馆员。此时通过识字训练的她已经开始深入了解美国的历史,虽然对《独立宣言》中的“生而平等”理念一知半解,但质疑始终萦绕在她的脑际:“如果所有人(生而平等)并非真正指的是每个人的话,那么撰写它的白人们也并不真正理解它。”(139)众多类似迈克尔这样的生命不能得到公平对待,“生而平等”对他们而言只是文字游戏而已,承载于《独立宣言》上的丰功伟绩充其量只是白人炫耀的话语资本,其实质是在宣扬“一部反复重演的伤天害理和巧取豪夺的历史”(38)。
二、经济化的生命:资本帝国下的平等幻象
生命在经济视域中首先应当与价值相关。在世界发展的历史上,人一直是经济生活中最具经济价值和充满创造性的力量。随着资本主义的深入推进,资本家开始给不同人口贴上差异化的标签,生命在价值面前被商品化、物化和异化。墨菲在《生命经济化》一书中将价值化的生命分为值得生存的生命、值得不死的生命、值得投资的生命和不值得出生的生命(Murphy 2017:7)。在经济化的生命理论坐标中,横轴是种族标签,它是人口的“语法和幽灵”(135),为物化和非人性化的歧视话语提供理论框架;纵轴是生命价值,它是资本逐利性在人口类型上的直接表现。种族认知决定了生命经济化的对象群体,如非裔族群、原住族群、亚裔人群等;价值认知为资本在生命形式面前的抉择提供了便利,如生产性优于非生产性,男优于女,少优于老等。在《地下铁道》中,白人资本在掠夺和压榨非裔生命的同时,还在乔基身上创造了一种“值得不死”的平等幻象,为生命经济化注入了一针麻醉剂。
《地下铁道》中,驱动南方蓄奴制的原动力是经济,黑奴被贩卖至美洲正是缘于依附在他们身上的经济价值。马丁是北卡罗来纳的一个地下铁道站长。作为白人的他,阴差阳错地成为了一名废奴主义者。在他看来,棉花种植业是整个蓄奴制无情的发动机,它需要非洲的躯体燃料来驱动。在非洲海岸,黑奴作为“人货”(cargo)被数以万计地装船起运;到达美洲海岸后,他们被一一标价拍卖,随后便进入种植园的工人名册中。在这里,“每个名字都是财产,是能呼吸的资本,是血肉创造的利润”(215)。整个过程中,蓄奴制发动机的活塞毫不留情地运转,源源不断的黑奴生命供给着美国这个巨大的经济怪兽。在佐治亚,黑奴被称为“动产”(chattel),他们被打上各种烙印以示区别(255)。科拉在多人身上见过X 形、T 形、马蹄形、三叶草形的印痕。在兰德尔的种植园里,科拉虽然被免除了烙印之苦,但特伦斯给她留下的手杖创伤却更刻骨铭心。失去自主性的黑奴躯体被人偷走,他们的子孙后代也成为奴隶主的财产,世世代代耕作在白人偷来的土地上。而在南卡罗来纳,对奴隶生命的剥削和利用表现出新的形式:黑奴被政府集中买断所有权,他们可以在州内各地自由工作,结婚生子,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科拉在形式上获得了自由,也受到白人的“尊重”。在这里她不仅有了自己的新名字,还开始识字读书,先在安德森家里做帮工,后来又进入博物馆成为特型展演工。然而,在这种表面平等正义的社会下,资本依然无孔不入,他们辛苦劳作之后的工资极为微薄,这点仅有的收入其实是当局在扣除膳宿费、教育教材费、宿舍维护费之后的一点小意思。政府作为集体资本家对于有色人种的盘剥还表现在物价上。黑人商店的物价是白人商店的两到三倍,一条薄薄的蓝裙子就要花去科拉一周的工钱,无奈之下她还使用了代币券——一种政府为黑人发行的赊欠支付工具。这充分表明,资本剥削的恶手正从现实伸向未来。
《地下铁道》中资本的巨网在控制经济命脉的同时,还用自己一套独特的语象来掩盖其剥削逻辑。乔基年过半百,是种植园里最老的奴隶。奴隶主兰德尔对他不闻不问,任由他随意选择自己的生日。对于大家伙来说,乔基每年一到两次的生日聚会成为缓解悲苦生活的调味剂。再者,乔基极会察言观色,他总是挑选恰当的日子来为同伴们提供难得的喘息机会。其实,对于奴隶主来讲,乔基早已失去了经济利用价值:在熬过了白人施加的各种折磨之后,他双眼模糊,只有一条腿和一只手能够正常活动,年过半百便成为一个活动的废人了。他虚构的101 岁和任意选择的生日都无关紧要,因为他已经没有能够可供这个世界观瞻的东西,“只是残虐恶性的最后一块活化石罢了”(29)。乔基的自由选择是张贴在其剩余生命上的一面招魂幡,它表面上泛着迷人的自由光晕,实际上是嗜血资本饱胀之后的午后小睡。詹姆斯对于奴隶的管束从表面上看是其鹦鹉螺般的个性使然,但从根本上来看,他与弟弟特伦斯并无二致,他们的经济大厦都是建立在黑色的劳动力和白色的棉花两种元素构成的经济根基之上的。难得的一丁点儿自由给了风烛残年的乔基和辛苦劳作的同伴一丝饮鸩止渴般的慰藉,而在资本价值的天平上,这种自由又是对被吸干剩余价值、只有剩余生命的乔基的莫大嘲讽和狠毒惩罚。
再者,当资本的触须无孔不入时,乔基的生日聚会便成了阿多诺笔下文化工业的代名词。作为一种隐喻符号,它表征的不仅是资本文化麻醉下的半晌欢乐,更是这种幸福幻象裹挟下的虚伪平等。在乔基生日聚会的前半段,奴隶们尽情狂欢,美好的灵魂传统似又重见天日,他们一个个迷失在短暂自由的漩涡之中。然而,兰德尔兄弟甫一出现,快乐便戛然而止。尽管二人口头上表现出与民同乐的姿态,奴隶们也为讨好主子倾力表演。但当年少的切斯特不慎将一滴酒洒在特伦斯的袖口上时,科拉和切斯特就大难临头了,美好的灵魂瞬间转化为后灵魂的嗜血现实。在《地下铁道》中,经历了血雨腥风的科拉对于选择生日的虚妄自由表现出了出奇的冷静,可以说,科拉是怀特黑德后灵魂叙事的出色代言人。小说中,小可爱问她若是可能,她会如何选择自己生日的时候,科拉的回答干脆利落:“没的选,又不是你能决定的。”(14)对她的耿直率真小可爱固然无可奈何,但从事实上来讲,何时出生确实不为自己所左右。选择生日一方面如同在资本帝国之下选择工作一样,无论如何你都无法改变现实的经济框架,无法逃离被盘剥的命运;而另一方面,奴隶们选择生日反映了一个悲惨的现实——据西泽叙述,由于恶劣的生活环境,再加上频繁的奴隶买卖,很多黑奴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也不知道自己的生日,因此编造自己的生日便成为一个饱含心酸的传统(278)。
三、政治化的生命:生死控制与自治乌托邦下的赤裸生命
“生命政治”的概念始于福柯,随后在德勒兹和阿甘本的演绎下加深拓展,走过了从“捕获生命的权力”到“生命自身的权力”,再到“生命之形式”的理论发展历程(吴冠军 2014:77)。《地下铁道》将生命政治的历史浓缩在科拉的逃亡历程之中,从佐治亚、北卡罗来纳的血腥惩戒到南卡罗来纳的生育控制,从“让你死”(let die)的吊索存在到“使你活”(make live)的战略绝育,从白人的掠夺扼杀到黑人自治乌托邦的失败,既控诉了南方蓄奴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对黑奴的双重压榨,又对黑人自身的问题作出了深刻的反思。
生命政治是关于生命的出生、存续和死亡的管理、调节与决断的观念和执行系统。自奴隶社会以来,生杀大权逐渐从绝对走向相对,从号令走向法理。福柯认为,文艺复兴以来,生命政治开始主张通过“捕获生命的权力”(power over life)对生命进行规训、监视、调节和矫正,并就此训练出数量庞大的顺从而富有生产力的“驯服身体”(2005:100-101),他们是日后西方经济快速成长的重要社会能量。在福柯看来,从奴隶社会的“让你死”到通过干预人的生活形式来致力于如何“使你活”是一种进步(吴冠军 2014:78),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不可少的要素。由此可见,生命政治的历史演变与政治组织形式密不可分。而在《地下铁道》中,生命所经历的不同境遇也是与不同的地域和权力组织形式密切相关的。
第一,佐治亚和北卡罗来纳都属于典型的“让你死”的生命掠夺政治:前者是奴隶主通过压迫性与否定性的力量来限制、剥夺奴隶的人身自由,使他们为己所用;后者是政府通过发动民间力量来集体摧毁和阻碍黑奴在社会上的存在,以行使规范化和规则性的“生命管理”职能。在佐治亚的种植园中,死亡是家常便饭,特伦斯通过监工康奈利来操控一切,对奴隶动辄使用九尾鞭抽打。科拉转述的死亡场景令人心惊胆战:“她见过男人被吊在树上,任由秃鹰和乌鸦啄食。女人被九尾鞭打到露出骨头。活的身体,死的尸首,统统在火葬的柴堆上受着烧灼。双脚砍去了,以防止逃跑;双手斩断了,以阻遏偷盗。”(40)科拉在被特伦斯用狼头棍暴打后,第二天还要依照规矩用辣椒水搓洗伤口。在这里,科拉看清楚了一切,“白人每天都在置你于死地,只是速度时快时慢而已”(32)。而在北卡罗来纳,“让你死”的规训逻辑呈现出的是另一番景象:在通往城中的名为“自由小道”的两侧的树上,挂满了具具尸首,他们中不论男女老幼个个都被折磨致死,死者中甚至还包括废奴分子、窝藏奴隶者和奴隶同情者。躲在阁楼中的科拉窥见了北卡罗来纳最独特的现象——熙熙攘攘的公园里竟然没有一个黑人。原来,北卡罗来纳对待奴隶制的政策就是赶尽杀绝,逢黑必杀。他们可以“骄傲”地对外宣布:“在北卡罗来纳,黑人种族是不存在的,除非吊在绳子上。”(187)
第二,南卡罗来纳走出了“如果控制不了它,就要毁灭它”的“让你死”逻辑(334),转而实行“让你活”的控制模式。在经过佐治亚的血雨腥风后,科拉通过地下铁道逃亡到南卡罗来纳。在这里,科拉改头换面,一切似乎以天堂般的幻象出现在读者面前。她可以自由出入不同场所,与西泽还能每周约会见面。他们获得了德勒兹所谓的具有内在生命力的“生命本身的权力”(power of life)(Deleuze 2006:384)。酷刑、种植园、伶仃屋、死亡威胁等禁锢手段被医院、工厂和学校替代。但最终这一自由幻象因一个“疯女人”的出场而被刺破。一天,在参加完周末联欢会之后,科拉面前突然出现一个疯癫的女人,她衣衫不整,在草地上大声哭闹,口中歇斯底里地叫道:“我的宝宝们,他们要夺走我的宝宝们啊!”(126)后经打听,那个女人因医院强制给她做节育手术而精神失常,最终被关进疯人院。经了解,科拉发现了背后的真相。由于大量涌入的逃奴及其强大的生育能力,南卡罗来纳的白人已经渐成少数。为了降低黑人翻身之后报复的风险,白人们决定对全体黑人进行战略性绝育。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他们以优生优育为幌子,以医院检查为名反复灌输节育观念。对于拒不就范的,他们便拿逃奴和罪犯身份相威胁。此时的科拉终于认清了博物馆、学校、医院、宿舍的控制本性:这里的自由只不过是一种新的控制形式,它表面上的不封闭掩盖不了其“连续的、不断变化的、自动变形的”控制网络的实质。他们不像从前那样是纯粹的商品,而是家畜:按需繁殖,任人阉割。对此,就连猎奴者里奇韦都承认南卡罗来纳“整天谈论什么提高黑人的水平啦,让野蛮人走向文明啦,那儿就是个同样嗜血如命的地方,一直都是”(263)。佐治亚用偷来的身体耕种偷来的土地,而南卡罗来纳通过对黑人的定向节育,偷走的却是有色人种的未来。在这里,“自由的、超快捷的控制形式”正在取代封闭的规训体制,“连续的、不断变化的、自动变形的”控制网络对于生命的管理更为有效(Deleuze 1992:4)。
第三,逃奴们在印第安纳瓦伦丁农场的自治乌托邦的大胆实验,既是对现存政治现实的批判,也是对“黑命贵”等社会现象的现实观照。瓦伦丁农场是科拉等众多黑奴的理想家园,在这里,黑人们有了自己的学校、图书馆和教堂,他们缝制传统的拼布被子,参加剥玉米大赛。女人们再也不用担心南卡罗来纳的手术刀了,“自由使人丰产”(294),男女老幼享受着天伦之乐。科拉也获得了真正的爱情,罗亚尔是个坚定的黑人自由活动者。然而,被白人居民包围的农场与政治共同体相分隔,它所赡养的赤裸生命因为无法与周边的大环境相融合,注定无法摆脱乌托邦的失败命运。如果从阿甘本的视角来看,《地下铁道》中的瓦伦丁农场将自然生命(zoē)和政治共同体生活(bios)割裂开来,没有能够让生命个体在共同体中去实现潜在价值,这是其失败的根本原因(Agamben 1998:1)。在福柯和德勒兹的基础上,阿甘本提出“生命之形式”(form-of-life)一词,即一种“完全不能同其形式分割开来的生命”(ibid:188)。他拒绝对生命的扼杀、捕获和控制,不赞同古典城邦式的排除共同体生活的“赤裸生命”(bare life)形式(ibid:4)。小说中黑人自治实验的失败一方面印证了赤裸生命理论;另一方面,明戈和兰德关于农场未来的辩论也是对黑人生命的深刻思考。明戈的观点是希望清理族群内部的堕落和不理智因素,停止一切激怒邻人的行动,用克制和革新与邻人达成和解。兰德认为,白人不会主动放弃奴役制度,黑人必须团结起来,携手同心实现族群解放。他希望黑人族群在思想上更开放一些,行动上更坚决一点。然而,黑人领袖们的乌托邦理想未能抵挡住奴隶主们的疯狂进攻。兰德在枪声中应声倒下,这场早期黑人生命政治探索最终以悲剧收场。兰德这一人物形象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他身上凝聚了早期黑人抵抗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和“黑命贵运动”以来典型的非裔英雄气质,是族裔不屈的抗争精神在后灵魂语象和声景下的生动再现。兰德及其同胞的遭遇带给读者的不只是数声悲叹唏嘘,更是对白人控制下美国少数族裔命运的深刻思考以及对当下特朗普主义政治秩序的强烈反抗。
四、结语
恰如国家图书奖对《地下铁道》的评论,“为了与我们休戚与共的自由和尊严,怀特黑德带领我们重温了那段扭曲的野蛮历史。他给我们讲述的触目惊心的过往,也激荡着深刻的现实回响”(National 2016),《地下铁道》传达给读者的强烈信息就是,在争取黑人真正平等地位的过程中,流淌着热血的伤口依然鲜红,地下铁道里的摸索依然在行进。与灵魂传统不同的是,后灵魂时代的非裔族群需要更多地关注种族的融合问题,不能在“享受着这个地方的馈赠的同时,却不能融入其中”(338);后灵魂的生命需要更多冷静的思考,如果再像只顾唱圣歌而不珍惜生命的贾斯帕那样“吃一堑,不长一智”,到头来,只能绝望地面对一道道无情冷酷的种族藩篱,悲叹命运给自己开了一个苦涩的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