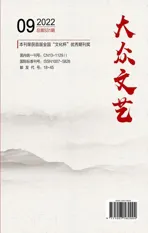清唱剧《长恨歌》音乐美学价值研究
2019-01-28中山大学南方学院510970
(中山大学南方学院 510970)
黄自(1904—1938),我国著名的作曲家、音乐教育家、音乐理论家,于1930年发表的《音乐的欣赏》一文中,提出欣赏音乐有三条路:知觉欣赏、情感欣赏及理智欣赏。其中,知觉欣赏及情感欣赏与罗小平在《音乐美的寻觅》中提出的“形态美”及“情态美”在内涵上是相互对应的,而黄氏在理智欣赏方面的论述商不够清晰全面,而罗小平提出的“意态美”对其起到补充完善的作用。此外,茵伽尔顿曾提出“视界融合”的观点,即创作者与欣赏者的融合。黄自作为清唱剧《长恨歌》的创作者,与其在《音乐的欣赏》一文所阐述的有关情感欣赏的举措是否达成一致,是否符合自身的审美欣赏要求,从而达到“视界融合”。笔者将尝试从形态美、情态美及意态美三方面对作品进行美学价值的探究。
一、形式美的体现
1.曲式过程中体现出均衡、和谐、对比、统一的自然美法则
笔者对作品七个乐章进行整体分析后发现:前四个乐章皆为三段体,后三个乐章皆为二段体,各具个性,并无完全一致的曲式构架,相互之间安排井然有序,层次清晰简洁,犹如稳稳搭建起的楼层。各乐章内部的乐段多由相同规模的乐句构成,建造一种对称的结构模式,使作品在整体的曲式过程中达到均衡、统一的效果。
另外,均衡、和谐的音乐组织形式在作品的局部也得到体现。第十乐章A段中,歌词采用七字句与四字句相结合的形式,但带重复性质的编排却让看似气息缺乏一致的歌词潜藏着某种规律性,为塑造音乐发展的匀称性提供了空间。作曲家在旋律声部的写作上充分利用歌词的可塑空间,采用以模仿为主的手段发展旋律,而第三乐句则以截然不同的旋律形态呈现以求得变化,并与前后形成强烈对比。四个乐句的伴奏织体皆以三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描绘性音乐语言贯穿始终,而在和声音响的厚重程度上有所区别。纵向结构的四声部复调音乐形式的组织更使四个乐句之间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而变化音及色彩和声的运用,又致使它们在衔接过程中的微妙变化紧紧地牵动着听众的心弦。一切因素都促使乐句之间以“起承转合”的逻辑结构完好地呈现出来,音乐的气质得以交融和统一。在规模长度上已经基本一致的四个乐句既能发展个性,同时又被统一在一个无法割裂的整体中,使音乐旋律的发展更具趋向性,大大加强了音乐的均衡感及和谐感,也成就了音乐的自然美法则,给予审美主体以听觉美感的愉悦。
2.旋律的千姿百态
作品旋律以级进为主,跳进经常贯穿其中,旋律线时而和缓,时而跌宕起伏。各种节奏的灵活组合使各乐章的旋律线条疏密有致、长短有序,音乐语言气息的停顿与衔接得到更为灵活、合理的控制。而更换节拍的频繁运用更使音乐行进过程的急缓安排自然得当,歌词的情感表达得到进一步的紧密配合。可见,各种音乐因素的灵活组合使整个作品的旋律形态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如第十乐章《此恨绵绵无绝期》乐段中,其旋律形态在节奏的组合上得到较大的丰富,附点节奏占据颇大的比重,旋律线的起伏较大。其中2/4拍子的加入而带来的四次节拍转换,加快了旋律强拍循环的频率,音乐不安的律动气氛得到强化;另外,作曲家在其中设置了五度及八度跳进,术语“p”与“rit”的标示,配合歌词哀婉情绪的先扬后抑的情感抒发。歌词“只一声,愁万种”,无奈的叹息语调,旋律的走向与审美主体的情感逻辑产生共鸣,这种情态传递给听众的是一种切肤之痛的体验。部分伴奏织体较切近旋律声部的节奏律动,旋律线条的律动进而得到强调,丰富了旋律织体;而另一部分伴奏织体则主要采用分解和弦的形式,以规整的连续的四分音符、八分音符、十六分音符或三十二分音符组织起来,或以震音及琶音的形式出现,这种规整的伴奏织体更加衬托出旋律形态的多姿。
多样化的旋律形态勾勒出一幅幅柔美的曲线图,给审美主体带来视觉上的满足,同时旋律流畅性及其所具有的逻辑性,与审美主体的听觉习惯相吻合,从而产生共鸣,使审美主体在听觉上也得到美的享受。
3.音色的变化无穷
纵观作品整体的调性布局,转调是其发展音乐的重要技术手段之一,转调的形式以关系大小调或同名大小调居多。第一乐章的调性布局为:G-e-D-bB-a-F-g-G,仅80小节的长度便有7次转调。在和声序进上采取疏密结合的方式进行,以主和弦或属和弦贯穿几个小节,或在一个小节中容纳4个和声序进,其中还使用离调和弦及临时变化音,进一步丰富音乐的调性色彩。作曲家在作品中运用大量的音乐术语,音乐在整个行进过程中的强弱、快慢处理得到非常细致而有效的控制,让作品在流动的过程中更赋予表现力和感染力,更有利于突出情感的细腻表达。
作品七个乐章在演唱形式上各不相同,主调与复调两种织体形式的结合与分配,丰富了各具特点的演唱形式,为音色的变化提供更多的可能性。音色的变化旨在营造各种氛围,渲染各种情感,给审美主体提供广阔的遐想空间。
作品旋律的千姿百态、和声的丰富多彩、音色的变化无穷以及曲式过程中体现出的均衡、和谐、对比、统一的自然美法则,使音乐“不仅可以给人听觉审美的愉快,还能使人的幻想力、逻辑力的发挥上得到满足,在情感的张弛、焦虑与解脱上得以激活并在把握结构的生命形态上能得到充分的审美体验”1,展现出音乐的形态美。
二、情态美的体现
纵观作品的歌词,以歌舞升平的景象引出。歌词的写作条理清晰,衔接自然,富于逻辑。押韵灵活、自然,长短有序的歌词富于顿挫感,贴近内心情感的波动,华丽、凄美的语言表达使歌词充满强烈的抒情气息。作品总体以多声合唱的歌唱形式为主,而第二、第六及第十乐章则以独唱占主要地位,将李杨爱情故事的发展线索很好地贯穿起来,使七个乐章之间成为紧密联系并富于逻辑性的整体,歌词的合理安排及强烈的抒情气息让作品细腻的情感表达充满美感。
黄自在《音乐的欣赏》一文中认为作曲家往往从以下几个方面表达作品的各种情感:大音阶表达雄沉而响亮,小音阶表达抑郁而幽暗;节奏的快慢、音的强弱、和声的协和不协和表示情感的激烈与和平;用长而宛转的乐句表爱情或其它和缓的情感,用断而短的乐句表急怒的情感;以音色的配合表情感。在该作品的创作上,作曲家是否坚持以上所述的立场和观点,笔者将对这个疑问进行解答。
作品围绕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展开,在作曲家的笔下,李杨的爱情悲剧始终渗透着优美与凄美的气质。在第十乐章中,小调式贯穿始终,全曲力度很轻,和声非常稳定,主和弦占据绝对地位,功能性很弱。词曲结合方面基本采用一字对四分音符或二分音符时值音符的形式,节奏缓慢,旋律以级进进行为主,连线的大量使用让音乐气息非常连贯、柔和,音色飘渺、悠扬,此起彼伏的复调织体使音乐更显缠绵,均衡的结构形式构成了优美的基本表现特征,其中传达出来的哀怨及伤痛之情为审美主体所深深触动;同样,第二乐章中,长而宛转的前奏,均衡、连贯而轻盈的六连音伴奏织体的衬托下,气氛恬美,主人公的情感表达也尤为细腻,给予审美主体深刻的印象。这两个乐章使音乐寄托在形态美上的各种情思得到美的呈现,展现音乐的情态美。此外,通过以上的分析可见,作品中所运用的体现情态美的相关技术手段与作曲家本人在《音乐欣赏》一文中所总结的表达作品各种情感的相关手段相吻合,这体现了茵伽尔顿“视界融合”理论的效果。
黄自在《音乐的欣赏》一文中提到:“作曲家作一曲,必定有所感于心,故发为音。同时在他作品中,他必定无意中将自己的个性和盘托出2”。唐明皇与杨贵妃之间的爱情固然让人感慨万千,而词作家与作曲家在作品中所赋予的爱国主义情怀同样也无法被掩盖。作品中,第三乐章及第五乐章是最先出现的两个悲剧性曲子,也是最为直接抒发爱国主义情怀的两个乐章。歌词刚劲有力,“不爱江山,只爱美人醇酒”,“可恨的杨贵妃,可杀的杨丞相”,字里行间透出强烈的批判语气,充满悲叹与愤恨。作品摆脱世俗对这一题材大团圆结局的创作习惯,以“料天上人间再也难逢”作为李杨爱情故事的终结。作曲家并非把创作主题单纯地寄托在李杨的爱情故事上,并对这场政治悲剧导致的爱情悲剧表现出打击的态度。可见,处于民族危难时期,作者在创作中融进了自身的主观情感,表达其爱国情怀,体现出一种崇高感。
第三乐章《渔阳鼙鼓动地来》及第五乐章《六军不发无奈何》在曲式结构上相似,都是三段式、变奏曲和分节歌的结合,男声四部合唱的歌唱形式,并贯穿着力度的发展,表现激愤情绪的逐渐增加。两个乐章皆以小调作为主调,音乐在整个行进过程中笼罩在非常抑郁、沉重的气氛当中。附点节奏的使用占有较大的比例,增强了重拍的出现频率,歌词“可恨的杨贵妃,可杀的杨丞相”中,两个带有浓厚感情色彩的“恨”字及“杀”字,每次出现都以附点节奏形式落在强拍强位上,由此得到突出和强调。还有休止符的大量运用,致使音乐气息短促、顿挫,构造断而短的乐句。音响亦抑亦扬,悲痛、愤恨、抑郁的情绪交集在一起,这是作曲家内心的呐喊,试图唤起“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民族觉醒,体现了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怀。
“音乐所具有的影响人的精神世界的巨大力量,在崇高美中得到充分的体现。音乐崇高美总是和精神内涵密切相关,并且和祖国、英雄、正义、理想、信仰等不平凡的对象相联系”3。该作品正深刻地反映着有关祖国的命运、理想、信念之间相互撞击、相互挣扎等问题,表达了作曲家的爱国主义情感,展现了音乐的崇高美。
三、意态美的体现
诗人海涅有句名言:语言终,音乐始。本作品的词作措辞雅致,情感表达细腻、深刻,富于诗意,但不足以道尽作品的神韵。黄自的音乐创作表达了词中所不能表达的,巧妙的词曲结合让作品具有鲜明的动感及强烈的意境塑造能力,其内在的表达也因此更加清晰自然,作品的意态美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
作品最具烂漫唯美色调的第二乐章,悠扬的旋律带出甜蜜的前奏,持续的六连音伴奏清澈晶莹,衬托出飘渺、梦幻的仙境,辽阔而神秘的天宇给予人们无限美的遐想,同时渗透着对牛郎织女真爱的满满赞许。合唱部分柔和、舒缓,审美主体似乎听到摆脱世俗功名利禄的劝告,那是对纯净乐土的真诚渴望,传达出与世无争的祥和。
在对第十乐章词曲结合的分析中,同样可见作曲家灵活运用多种作曲技法,渲染了荒芜、死寂、凄惨的气氛,表达了主人公悲痛欲绝的情感。该乐章合唱部分的伴奏织体,持续重复的八分音符模拟雨滴声,重复多次并呈下行走向的三音列音型仿佛沉重的脚步声,旋律以级进为主,并多处同音反复,小调式的贯穿更让音乐笼罩在十分凝重、阴郁的气氛当中。审美主体似乎听到音乐在哀叹,乐章的最后一个句读的旋律气息长并起伏大,上八度的大跳进刚劲有力,那是明皇高亢且沉痛的呐喊,满载哀怨、无奈和愤恨,唯有留下绵绵不绝的思念,点明作品“长恨”的爱情主题。
作品展现了一幅幅生动、真实的画卷,潜藏着层层耐人寻味的意蕴。它能触动审美主体的心灵深处,在沉醉中不断得到熏陶和抚慰,充分体现出作品的意态美。纵观以上对作品美学价值的探讨可见,黄自把自身的审美思维运用在《长恨歌》的创作上,并贯穿、体现在整个音乐创作过程当中,让作品在形态、情态及意态上均得到美的呈现。
四、结语
通过对黄自的清唱剧《长恨歌》美学价值的分析,作曲家全面而细致地理解歌词的语义,密切配合歌词的节律,竭力营造符合歌词的意境。在变换节拍、跳进、力度变换、弱起等各种技术手段的巧妙运用下,人物情感的起伏及人物形象的微妙刻画都得到了十分灵活的发挥;旋律的多样化及伴奏织体的固定性与灵动性结合,使得整个乐章非常富于个性;阴郁、凝重的气氛及甜蜜、哀愁、无奈、激昂等情绪在作品中都得到充分的展现,成功表达出作品的深层意蕴,作曲家为我们勾勒了一幅幅哀怨、凄美且感人的爱情画卷。《长恨歌》作为中国的第一部清唱剧作品,作为中国近现代音乐的奠基者之一黄自的杰出作品,笔者认为对其进行孜孜不倦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它对后人的音乐创作及理论研究当具指导与借鉴意义。
注释:
1.罗小平.《音乐美的寻觅》.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5年,第142页.
2.张静蔚.《搜索历史》.上海音乐出版社,2004年9月第一版,第164页.
3.张前,王次炤.《音乐美学基础》.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年,第3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