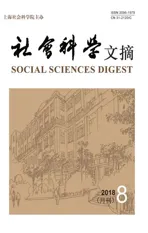近四十年来大陆宋明理学研究的几条线索
2018-11-18
改革开放以来,宋明理学研究以10年为一个阶段,四个阶段各有其研究的重点。第一阶段,理学研究关注的重点是气学,并初步开展以地域为主体的关学、浙学、闽学和洛学等理学学派的研究。第二阶段理学人物的研究得到大大推进,研究更加深入到理学思想内部,社会、政治和经济等外在因素与理学的交织分析淡出。第三阶段,大陆宋明理学研究与港台新儒学、东亚儒学乃至西方哲学的互动频繁,宋明理学的思想史研究成为这一时期研究的热点之一。第四阶段,学界反思现代新儒家和西学对宋明理学研究的影响,经学与理学的交叉研究兴盛。此外,理学学派研究得到更细致的延伸,与地域传统学术相结合,徽学、关学、浙学、北学、黔学、闽学、洛学等研究都有丰富的成果呈现。这四个阶段前后相续,存在着内在发展的线索。本文认为,贯穿于4个10年之中有几条线索,有些可能会持续影响到未来理学的研究。
“反理学”研究
40年的理学研究中同时伴随着一条在内部或者外部与理学对立的研究线索,即反理学研究的线索,这条线索在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表现方式。
在理学内部,最主要的反对者是气学一派。20世纪80年代初期,学界对于宋明理学的评价逐渐由之前的全盘否定到有所扬弃,对理学家的肯定和宣扬正是从理学中气论一派开始的。从唯物主义的立场看,气学一派可以对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客观唯心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学说有所对治。主张气论的理学家因而成为研究的热点人物。理学之中的气学学派因而很悖论地作为理学之中义理之学的对立者,保护了理学的整体地位。
20世纪80年代中期,大陆学界援引朝鲜儒学学派的“实学”一词,批判空谈心性的朱子学,提倡对生活有益的经世致用的新学风。顾炎武、黄宗羲、颜元等明清学者经世致用的思想作为实学得到表彰。陈鼓应、辛冠洁和葛荣晋等认为实学思潮从对整个宋明理学的批判中产生,在当时受到不少质疑。后来“实学”提倡者修正了原有的提法,肯定实学对理学有继承有排斥,在理学家朱子、象山和阳明等的思想中都有体现,亦是对理学的一种和解。“实学”研究在此后20余年仍发挥着影响。然而,实学强调了理学之有,所谓实理论、实性论、实功论和实践论,而否定其超越性的一面,必然会落入功利主义。
20世纪以来,从早期启蒙的视域看待明清之际的思想,认为明清之际是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型的发端和结合点,同样可以梳理出一条明中期至清代的反理学线索。明清之际思想家的思想具有现代性的某些元素和特质,可以很好地结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实践论,呼应西方启蒙思想家的思想,被视为中国现代性的开端。启蒙学说之间虽各有分歧,但总体上,启蒙学说对明清之际思想与宋明理学关系的看法还是断裂多于连续。当我们现在将明清之际思想纳入理学延续的脉络下考察时,“早期启蒙”可以被视为明清之际理学研究的独特视角和方法,也可以被看作是理学自身内部调整和反省的一个角度。
如果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关于气学、实学和启蒙学说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东亚儒学和西方哲学的启示,那么,2000年以后学界乃着眼理学内部的气学问题,确实源于理学自身形而下的面向,是理学研究主体意识的体现。通过反理学的视角研究理学家,其本质上与理学内部警惕空疏虚寂以及纠正形而上脱离形而下、体用相分等弊病的目标一致。但如果因此忽略理学对于坚持德性理想和伦理生活实践的意义,乃至蕴于其中的人性天然的自尊、平等和主体性发挥等价值,则会因噎废食。
西学影响与中西对话
理学研究中的中西对话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直接比较理学家和西方哲学家的思想系统或者具体观点;一种是在理学研究中援引、融合西方哲学思潮或者思想家的观点。前一种情况中,随着大陆学者对中西方思想的深入研究和中国哲学主体意识和文化自信的增强,双方对话越来越平等,对于理学人物和思想的评价也有所提高。后一种情况涉及理学研究中对西方哲学的自觉吸收和运用。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学概念与问题带入宋明理学研究的情况颇为普遍。从概念上说,理、气、心一元论的探究,理性和意志问题的提出,宇宙论、人生论、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框架,先验论和唯理论的定位等在大陆比较盛行,都属于此类。随着宋明理学研究的发展和深入,这些概念和问题意识被带入理学,西学与理学形同自然一体,一转而成为理学自身的问题,西方哲学深入宋明理学研究的肌肤与骨骼之中,令人浑然不觉。40年宋明理学研究脉络中,西方哲学概念与框架的影响决不可小视。如果说反理学研究对于理学研究的区分属于外部路径, 那么西方哲学的范畴、系统、视角、方法乃至话语之于宋明理学的研究就是出乎其外、入乎其内的。
20世纪90年代以来,语言哲学、存在主义、解释学、现象学等在宋明理学研究中都有运用,诠释学的影响尤大。然而,一方面,一些成果只是再次成为西方诠释学在中国文献中的运用,另一方面,零星的解释原则无法构成可以被称为“中国诠释学”的体系。对于理学而言,真正的损失在于虽有大量成果的产生却没有推动或者触及理学的内在问题,相反,因为误读理学,经典注释本身有时被视为主观任意解释的结果。研究者往往强调对经典语义的释义,或将解释结果的差异归结为客观的思想史脉络和个人的主观经历经验,违背了对经典涵义本身的理解而难以尊重经典意义的客观性;将之推到历史,则取消了历史的客观性而走向相对主义,将之推到哲学,则纠缠于经典的外部世界,消解或忽视了经典呈现的价值与意义。诠释学在实际研究中意义大大被泛化,其中问题颇令人担忧。
近年来,现象学与理学的研究颇值得关注。有趣的是,关于现象学与理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阳明心学的研究上。大致可分为从现象学的视角研究心学和进行阳明心学与现象学的比较两种路径。前者延续了瑞士现象学家耿宁所运用的方法,后者则是传统的中西比较方法。基于现象学的描述运用于基于实践和修养的理学工夫论,能否避免肢解,这确实是一个问题。中西真正意义上的对话和交融,仍在探索之中。
哲学史与思想史路径的分野与融合
1949年以后,中国哲学史研究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关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对象和范围的问题。周继旨认为,如果哲学史内容过于泛化,则不免混同一般思想史,而如果一概排除了不属于哲学范畴的内容,则纯化以后的哲学史只剩下唯物论和唯心论,哲学家思想体系的个性被埋没,整个中国哲学的特点和规律因而也变得模糊不清。萧萐父先生进一步谈到哲学史研究中的纯化和泛化,他提出要净化哲学概念,把一些伦理、道德、宗教、政法等非哲学思想资料筛选出去,使哲学史纯化为哲学认识史。同时,他也主张哲学史研究可以泛化为哲学文化史,这样更能充分反映人的智慧创造和不断自我解放的历程。他提到,在哲学史的研究中,或由博返约,或由约返博,或纯化,或泛化,只有经过这样的两端互补和循环往复中的反复加深,才能不断开拓新的思路。萧萐父先生的由博返约和由约返博论预先揭示了1978年以来中国哲学史研究在哲学史和思想史之间循环往复的动态发展过程。
1950年代,任继愈先生认为,“中国哲学史的对象应当是,关于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的认识过程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其《中国哲学发展史》和侯外庐先生的《中国思想通史》等都贯彻了这一总结。这一泛化的哲学史研究的思路一直延续到1978年以后的10年。从1988年开始,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纯化趋势越发明显,反映在宋明理学领域,是廓清了政治、经济、社会等缭绕的论说方式。纯粹演绎理学家思想系统、观念、学说和概念成为一种全新的范式,逐渐成为理学研究中的主流,大大推进了理学内在问题的展开和探讨。宏观上关于理学学派的分系问题,微观上关于理学家个案中的理气心性等问题都展开了恰如其分的言说,理学研究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与此同时,历史与逻辑相结合的方法在理学史研究中继续发挥作用。事实上,思想史在理学研究中的作用和影响从来都没有间断过,主要受到内外几方面的影响和作用。1975年余英时提出“内在理路”说,强调思想史的内在发展;2000年以后,葛兆光的《中国思想史》借鉴法国年鉴学派学说,针对以政治、经济、文化为主线的精英和经典的思想史写法,试图实践“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历史”的写法。前者实际上源于西学知识论的外部挑战,后者在宋元章节中并没有贯彻区隔精英的一般知识的写法。但二者对于思想史的理解和示范客观上对学界产生了深远影响,推动了明清思想史研究的热潮。宋明时期的士人生活与交往、书院讲学、政治活动等方面确实通过思想史的再现得到深入研究,研究成果很多。哲学史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纯化与泛化多元共存、互相促进的新的发展阶段。可以说,近40年的哲学史研究正是在思想史研究范围的拓展和深化中深入的。然而,我们也不能不考虑到理学因其独特的生命经验,其思想的内核和内在问题的推进并非思想史的外缘研究所能完全触及,理学研究的相对独立性也应该得到维护。
理学与经学的互动
经学与理学之间的联系往往表现为历史上的联系和思想上的联系。历史上的联系指汉唐经学主导转向宋明理学发生,和宋明理学主导转向清代经学复兴之间的联系。学界关于后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前文所说的反理学批评和历史学、经学的转向,反理学批评是理学内在的研究路径,历史学和经学的转向则更多涉及思想史的研究。由汉唐经学向宋明理学的转变,也是学界研究的热点之一。
经学与理学在思想上的联系主要体现在宋明理学和经学之中。2000年以前,理学与经学的互动体现在理学研究中,主要是以理学为主导,理学家的思想系统中往往使经学从属于理学的解释,经学成为理学的一种经典表达。2000年以后,随着经学研究的呼声渐高,理学中的经学研究开出了一个新的发展面向。相比于传统看法,学界比较倾向于接受理学作为经学史中的一种形态,认为是经学发展的一种必然方向。以经典为主线,将理学视为经学史中的一段历程,亦是一种新的思考角度。在此视角下,宋明理学与宋明经学共同构成了一种形态,是儒学在宋明时期的新发展。从目前的研究成果看,以易学与理学的关系阐释最多,春秋学与理学的关系研究最少,面向社会思想史研究的礼学近来也成为理学研究中的热点,四书学是研究的重中之重。源于经学与理学的视角,宋元明时期,朱熹是诗学、礼学、易学大家,因而也是经学与理学研究的重点人物。其他围绕理学家的经学,学界已经展开一些初步研究,值得进一步拓展,如蔡沈、金履祥、魏了翁等的书学,宋程颐、邵雍、张栻、朱震、杨简,明黄道周、胡居仁、马理等的易学,宋胡安国、魏了翁、吕祖谦,元郑玉、吴澄等的春秋学等。然而,理学与经学阐发儒学精义有同有异,理学原则和经学原则之间的扞格问题,解释经典和理学表达之间不一致的问题不断彰显,对这些问题的解决亟须经学与理学两方面的深入研究。
经学与理学的交叉研究之悖论在于,无论是五经还是四书学的研究必然主要集中在文献整理和思想史的梳理,一旦涉及理学问题的分析,就会回到理学家的思想系统中加以理解,这时经学研究的独立性就被取消而服从理学的解释,而所谓的经学研究仍然只是加深理学研究的一个阶段或者一项工具而已。或者,在同一理学家的著作中,经学和理学解释不一致,往往被归因于理学家思想前后变化,这仍然是思想史过程论的一项解释;如果按照义理深究,当理学系统服从于经学脉络,结果要么是理学系统不圆融,要么是经学主导,理学研究独立性也无从谈起。因而,经学与理学的交叉研究意味着必有一方为主导,而理学家的思想研究往往是以理学为主导的,以经学为线索并不利于理学结构本身的呈现。
理学内在研究的进路
以上反理学、中西哲学比较与互释、思想史和经学的研究路径对于当前理学研究而言,推动与挑战并存。经学的深入理解、理学思想产生的环境和外部关联、西方哲学的观念和方法以及来自理学内部不同派别的反思与批评,对于理学的研究无疑都有着重要意义。同时,这几种路径往往交互作用,互相支持。比如,经学研究的兴起涉及反理学思潮的研究,经学与理学的互动则不少是在诠释学的背景和框架下进行的,思想史的研究借助了西方哲学的方法,经学与思想史的研究存在着交集,等等。然而,以上对于贯穿40年来大陆宋明理学研究的几条线索,都是外部路径。所谓外部路径,是指这些方法没有充分遵循理学的本来脉络,没有揭示理学的根本精神来推进、解决理学的内在问题。如果能够直指理学的核心,那么反理学的方法、思想史的进路、西学的视角和经学的研究都不是问题。但是,如果方法和进路过于执著于自身的反理学、思想史、西学和经学的目标,那么,它们作为外部路径则无疑义。
我们不得不正视一点,思想本身的深度和广度才应该是哲学研究的主要目的和任务。外在的探索和研究都具有它们自身的研究价值或者成为它们自我研究的目的,也有助于更为精确地捕捉到思想发展的线索或者外缘,却始终不可替代对于理学思想本身的研究和探索。
相反,理学研究中执著于以上外部路径会构成对宋明理学研究的挑战。比如,在诠释学的视野下,哲学问题往往被转化为思想史的问题而被消解。理学本体论或许可以借助西方哲学加以解说,理学工夫论则在西方哲学中找不到完全的对应,对于知的部分易陷入理学家所忌的口耳之说,知解和语言游戏之中,无法真正进入理学的世界。经学与理学不仅仅只有结合,在研究中,结合的背后经学立场与理学立场主导不同,评价和结论也会随之不同,也可谓是新的汉宋之争。反理学对于理学的反思既可以是内部的,也可以是外部的,外部的反思给理学研究带来的不仅是促进,也可能是误解。思想史在西风的助力下,更是占据了理学史研究的大半江山,表面上成果丰硕,对于理学问题的探索却可能只是浅尝辄止。
近年来,不少著作试图顺沿理学自身的脉络和体系庖丁解牛,提出和解决理学内在的问题从而避免西方哲学对理学问题的支离和分裂。这些都是宋明理学主体性的自省与自觉的表现。在具体的理学人物、学派思想、理学概念和问题的研究上,近一二十年来的研究在理学人物、学派方面有新的拓展,也有新问题的提出与发现,使得理气心性和工夫论的诸多问题在理学研究中得到更精微深入的展开和探讨。由于知行合一、涵养体贴是理学研究的内在要求,本体论与工夫论的研究结合工夫的践履和体认,可能是未来理学研究不可回避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