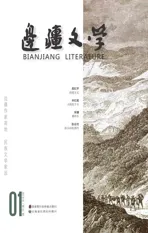入云南记
2018-11-12
高原的阳光干净而冰凉,打在黄土和荒石上,总给人一种无边的荒凉感。两个坐在长满荒草的土地上的人,像两颗裸露在乌蒙山上的岩石,我听到他们这样的对话:
“为什么不迁出去呢?”
“我们祖祖辈辈都活在这里,山上埋着我们的祖先,地里长着我们的苞谷、红苕……”
高处,云雾缭绕的山顶,一只鹰在盘旋,抓拍几张,却发现相片里空空如也,倒也没什么遗憾。在这里,我开始相信一切都是神赐。
的士在开,一会儿上来一个人,一会儿又上来一个人。在狭窄的空间里,我被挤来挤去,似乎要整成什么样子就能成什么样子。我抖了抖衣服,坐正,拿出手机,立即买了一张去云南的火车票。中午,准备出发时,跟一位大哥打了个招呼,说去云南。他说那我也去。我说好,那我们回去准备一下。他说不用了,开车去。就这样,我们出发了。
高速上,大哥接了个电话,对方说明天有事。大哥说,我们已经在高速上了。对方又说,第二个高速路口下。大哥说,我们既然出发了,就不会再回头。
车上刚好播放那首歌: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如今你四海为家……莫名的,一种感动慢慢荡漾开来。车一路往西南方向奔驰,群山远去,村庄远去,我们像两只决绝的鹰,往云贵高原方向飞翔。不知道谁说的那句话:人的一生至少要有两次冲动,一次奋不顾身的爱情,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在我三十一年的生命中,奋不顾身的爱情早已经历,说走就走的旅行倒还是第一次。
车上,我们谈及故乡,谈及《额尔古纳河右岸》《人生》《悲惨世界》,聊到文学作品中的人类意识……聊着聊着,就到了贵州梵净山下,看到山顶上的积雪,寂冷而苍茫。一个诗人写道:那静坐在我心底的佛/寂冷而苍茫。一直记得这句话。那梵净山上的雪,是不是人世的另一尊佛呢?
我深信所有的存在必有拯救。庄稼保佑田野;菩萨保佑村庄;鹰保佑雪山……一句诗是这样写的:张铁匠女儿的碑和海拔6656米的冈仁波齐/共同撑起了/越来越重的天空。反复默念这样的句子,心竟获得了一些安慰。
贵阳是我们的第一站,安排接待的是同行大哥的朋友,非常热情。我是比较喜欢独处的人,吃点东西后,就一个人走到外面,夜色中的贵阳,细雨蒙蒙,在城市的尽头,我看到了起伏的群山和冰凉如水的苍天……
车在云贵高原上奔驰,看着延绵起伏的莽莽群山,我们停下车,大声地呼喊,一次一次。累了,躺在荒草地里,大风吹拂,阳光热烈。突然念及:我愿是倒伏路边的一粒草籽/我愿是覆着积雪的一颗荒石/我愿是一个穿着破旧的牧羊人啊,赶着白云去山上/至死都不再回头……
想着有一天,真想就这样,一个人,一根拐杖,像一个小黑点一样缓慢走在苍莽的群山之中。没有目的,也无所谓方向。就这样走,直到把群山走进胸怀,把心融入大地。
一路上,看到很多村庄,难以想象,在这样的高原,人是怎么生存下来的。房屋如鸟巢,土地如巴掌。从不写诗的大哥脱口而出:把石头搬出去,垒成土坎/把土积累起来,筑成田园/种子洒进去,石头就开始消退……我们一次次下车,一次次向高原靠近,向土地靠近。在一户农家旁边,看到金灿灿的苞谷,一层层往上堆积,这是对劳动的赞美、对丰收的赞美。犹如某种致敬,或某种祭坛。
再往高原上走,更是无尽的荒凉,山顶裸露,除了石头和雪,再无其它。不知为何,大哥突然谈及他的命运,说到五次被招用,五次被辞退,最后一次下着大雪,他一个人往麻力场方向走,大风在吹,大雪在下,他一言不发,两个肩膀积满厚厚的雪,当走到一个岔道口,看到来接他的姐姐,两个人无言对视的刹那,他终于忍不住大哭出来。我聊及我在外打工漂泊的八年,经历各种挫折磨难,有一年冬天,我在天门山默默走着,风霜落满我的肩膀。那时候我写下:不知这落在我肩膀上的,是多少年的风霜。我想,这大抵也有相似的心境吧。
谈这些的时候,车在雨蒙蒙雾蒙蒙的山上穿行,两个人,都怀着一种难以言说的情绪。这时,车进入一个长长的隧道,我们都没有说话。到出口的时候,铺天盖地的阳光突然迎面铺洒下来,温暖、明亮,带着无尽的喜悦。那一刻,真让人恍若隔世,仿佛穿越了两个世界。突然想,这不正是人生吗。我们经历多少风霜和痛苦,只要坚持下来,默默努力,就一定能守到豁然开朗的一天。有个写诗的朋友,一年前过得浑浑噩噩,迷茫、无助,每天不知道自己在干啥,作品里面充满了各种情绪,仿佛全世界都欠他一样。一年后,他遇到了一个女孩,相爱,结婚,他发给我的诗歌里面有这样的句子:
我的身后坐着我的妻子
她的怀里抱着果子
路边的槐花落了一整个夏天
开始结槐角了
都有结局,空茫而宁静
但遇见是值得的,陪伴是值得的
忠贞是值得的。比如此刻
我的心是满的,有地久天长
有天荒地老。此刻,时间带不走我
它走它的,我是静止的
然后他说:兄弟,你是对的,时间是个好东西,它会慢慢成全所有付出的人。我相信他说这句话时的那种真情和感动,我也相信,当遇到挫折痛苦的时候,宽恕的力量永远大于对抗的力量。
抵达曲靖已是下午,阳光暖和,万物生长,一切宛若春天。云霞和她爱人接待我们,饭前,我在外面走,在某个地方,我坐着晒太阳。旁边的一个木牌上写着:发呆、做梦、免费。落日西沉时,看到远处山上的塔和寺庙,在光芒的笼罩下,像某种宿命。夜晚,大哥指着远处高空第一颗出现的明亮的星星说:它那么早出现,是为了窥视人世的秘密吗?
一夜安睡,第二天,经过4个小时的奔波,我们抵达了四季如春的昆明,阳光温暖、明亮,走在滇池边,看着水,看着阳光在水上推出一层层光辉。一个人坐在水边,就想听《假行僧》,把声音开到最大。当熟悉的旋律响起来的时候,我真得不想再动了,就想一生都坐在那里。
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
我要人们都看到我,却不知我是谁
假如你看我有点累,就请你给我倒碗水
假如你已经爱上我,就请你吻我的嘴
入夜,在彩云之南的某个宾馆里,凌晨两点半醒来,世界一片寂静。我不知道生命中有一天能说走就走,也不知道有一天会来到这里,而起因仅仅是因为在车上被人挤得难受,我当时就一念头:难道我真得就这样了吗?难道我飞不出去了吗?前面几周有一个朋友跟我出去,沿着酉水走20公里,又从吉首骑车到凤凰。他跟我说:这么多年来,我都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这是我第一次觉得自己活过。后来,他重新拿起了笔,并写出很好的作品。
整夜,我没有再睡,夜晚的昆明异常安静,在无边的寂静中,我一次次触摸到了自己的内心,一次次和自己对话。许久,我爬起来,翻箱倒柜地找纸和笔,最后把能找到的所有纸都写完了,才倒头睡去,我写下了这样的句子:
我向往有一条人迹罕至的道路
除了我走,没有别人
是的,没有别人,每个人的人生,其实都是一个人走,都是孤独的。这些年,经过不断行走,越来越发现,走着走着,人越来越少;走着走着,路就越来越难行;走着走着,身边就没有人了。突然理解沈从文在给三三的信中为什么说觉得自己像一个受难者了。
天刚蒙蒙亮,再次醒来。看着凌乱的稿纸,想着身在云南。突然有恍若隔世的感觉。我知道自己真正要的是什么,或许不是云南,或许不是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当穿行在云贵高原,倒伏在荒草丛中的时候;当静坐在滇池边,听《假行僧》的时候。我知道,那些东西正在走来,源源不断地向我靠拢。每当这样的时刻,我常常说不出话,记得那次骑车去凤凰的路上,我们看到了山水之上,万物生长。我对朋友说了一句话:山水无言,才能承载万物。在云南,听万物发声,也是同样的心境。
车子刚驶出花垣,我发了一条朋友圈。结果电话就没停过。微信圈了,更是热火朝天。开始出现“抢人”的局面。长沙的朋友说:书正西南巡,引云南群雄起干戈。当然,这是说笑。但感受到那种纯粹的兄弟情谊。杨勇、云霞,郭明、尹马、芒原、李顺星、张雁超……跟同行的大哥说,云南是诗歌高地,列出来的这些人都是诗界名人。
昆明,滇池边,郭明等朋友都打来了电话,像滇池的水一样,热情、干净,内心涌满温情。
昭通,喝了正宗的云南苞谷烧,走的时候,带走了十斤白酒和一生的情谊。龙云故居旁边,看到了自由绽放的菜花,一直连绵到天边。
水富,拦截金沙江,构筑大坝,淹了两座县城。朋友说有些动物来不及跑,有些坟没来及迁。他说:水淹了,让死了的人,再死一次。站在山上,两个卖橘子的人。他说:买那个老人的吧。看着寒风吹拂着的她的白发,他想到了她的母亲。
……
11月28日,凌晨6点20醒来,窗外还是雾蒙蒙的,不知从哪里来,又将去往哪里的火车,一声长鸣之后,就哐当哐当都驶进县城。想到原计划去厦门的云霞,退掉飞机票,跟我们一起奔赴昆明看望她的老父亲;想到雁超下午提前告别,回去带生病的女儿;想到一路上,同行大哥的儿子不时打来电话,问爸爸在哪里,什么时候回来?想到在遥远的湘西,此刻,我的亲人们在开始煮饭烧菜,屋顶升起缕缕炊烟……我坐起来,写下这么一段话:此刻,房间里灯盏温馨,外面,天还不是很亮,金沙江边,水流奔走,伴随一声长鸣,火车哐当哐当地奔跑……我突然有点想哭,早安,水富,这座生在金沙江边的小城。感谢你接纳一个浪子的疲惫、灰茫和荒芜。我就要回家了……哦,我就要回家了……张楚的那首歌:姐姐,我要回家啊,牵着我的手,你不用害怕……
冲凉的时候带着手机,反复单曲循环这首歌,当温暖的热水淋遍全身,我感觉到有温热的东西从眼眶奔涌而出,已分不清是热水还是泪水。我在《致故乡》里面写道:
我赞美它们:司马坡,洲上坪,和尚山
从那里,我取得了粮食、水源和爱情
也获得了保护和庇佑
我一生都走在上面,活在上面
我如果笑了,野菊花就是我的笑脸
我如果哭了,整条古苗河,都是我的泪水
雁超和季风主席在楼下等我们,出门时,谈及诗歌,说要把句子写得短一点,要安静,要让让每一个文字都有归宿,像每一个人都要有归宿一样。
是的,每个人都要有归宿,我们离开故乡,也是为了寻找故乡。在广东的八年,每年回村都有人不见了。问及母亲,母亲就指着山那边说:“都到山上去了。”忽然想,年前回来才好好的,再回来就不见了。此后每次回家乡,都认真地跟每个人打招呼。因为有可能见的每一面都是最后一面,问及的“吃饭了吗”“去哪里”,都可能是临终遗言。又谈及我的奶奶,那时候在广东,家里打来电话说人变了很多,估计也就是十天半月的事情。我知道,但是我不能请假回去等她过世。所以我这样写:现在,对于那个一手把我们带大的老人/我们终于要做这最后一件事/她在家等死/我们在远方/等着她死。而如今,我们身在故乡,故乡却正在远去。我们的粮食多起来,我们的田野荒芜了;我们的楼房修起来了,我们的神龛不见了……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我们正在丢失几千年来保留的传统文化,我们在丢失我们的根。最令人痛心的是,现在,我们很多人在为这种失去而欢欣鼓舞……
那么,我们的归宿在哪里呢?我不知道,也许,就在贵阳那灯火辉煌的街头;也许,就在曲靖那个可以发呆做梦的地方;也许,就在滇池上那一艘古老的木船;也许,就在昭通我们歪歪斜斜地拎着那十斤白酒的路口;也许,就在水富奔流的金沙江边;也许,就在乌蒙山上那两个人谈及祖祖辈辈都生存在那里的那块小土地;也许,就在积雪的山顶,那只鹰盘旋的地方……大哥在《寻找诗人夏天》里写道父亲在临终前在他耳边吐了一口气,他父亲想说些什么?想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追问,一直在耳边回响……
归来的路上,我们从高高的乌蒙山俯冲到金沙江边,从云贵高原冲入四川盆地,再穿越武陵山脉,一路奔驰……
哦,我们回家,马不停蹄。
哦,我们回家,走在天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