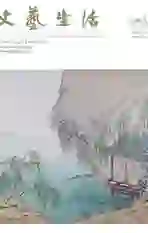弗拉哈迪风格在中国的本土化
2018-09-28孙雨
摘要:纪录片之父弗拉哈迪终其一生都在纪录即将消失的古老文化,其作品《北方的纳努克》在中国得到肯定。而他作品所形成的风格影响了中国纪录片,如《最后的山神》就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与发展了弗拉哈迪风格。
关键词:弗拉哈迪;记录理念;《最后的山神》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8)20-0093-01
一、弗拉哈迪的《北方的纳努克》
《北方的纳努克》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纪录片,在90年代的中国,该作品曾引起高度关注,从而奠定了弗拉哈迪风格在中国的地位。
(一)弗拉哈迪的创作动机
弗拉哈迪开创了有关人类的新型记录题材,其作品始终沿用一个主题:人与自然。他试图摆脱来自工商业方面的干预,超越时间限制,打破人类之间的成见,揭露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在弗拉哈迪眼中,现代工业文明是“丑”的,像一把镰刀割走了人类心底的真善美,他更加青睐于去拍摄那些淳朴自在的原始生活,通过作品去揭示人与自然之间最简单的联系并将其呈现给受众。
(二)弗拉哈迪的记录理念
随物赋形——《北方的纳努克》的创作是利用已有的素材去构思作品的框架,代替了以往先梳理好框架再拍摄的流程。弗拉哈迪拍摄的镜头是真实自然的,事物没有精心安排的痕迹,呈现着其该有的形态。在工作过程中,作者力图还原真实生活,避免在作品中表明个人观点。作品《北方的纳努克》成片之前,弗拉哈迪与爱斯基摩人相处了8年之久,二者之间是相互信任的,也因为这样,他才能清楚地把握爱斯基摩人特有的感染力,并将其地域文化进行提炼加工,通过镜头得以具体表现。
悬念与戏剧性的把握——《北方的纳努克》利用故事来构建戏剧冲突,故事本身生动诙谐且衔接紧凑。无论是故事本身,还是剪辑所构成的戏剧性与悬念性,都充实与完善了作品本身。如纳努克与伙伴们一起捕杀海豹的拉锯战,作者使用长镜头记录,一方面利用事件本身的戏剧性,另一方面用于表现人与动物的较量,体现了爱斯基摩人生存不易与人与自然的矛盾。细节的刻画——纳努克好奇的咬着唱片、艾力无忧无虑滑雪以及纳努克教艾力箭术时的温情,大量的细节描写使影片更加真实可信,令观众喜其所喜、悲其所悲。
摇镜头以及长镜头的運用——弗拉哈迪在《北方的纳努克》中对镜头运作进行大胆尝试,多次使用摇镜头,如猎狗撕咬在一起时,镜头来回摆动,在暴风雪即将到来的晚上,主人的心焦与猎狗的混乱交织起来,相辅相成。长镜头运用较为常见且不繁复,片尾通过较长的固定镜头表现回家的艰辛,人物渐渐消失在镜头里,只剩被风吹起的雪尘,表现了他们生活的艰辛困苦与人作者简介:孙雨,山西师范大学戏剧与影视学院,戏剧与影视学专业。在大自然面前的渺小。
二、孙曾田的《最后的山神》
(一)《最后的山神》内涵
《最后的山神》通过对孟金福夫妇进行实地跟踪拍摄,讲述作为中国最后一个萨满在人们远离山林后心底流露出无助与哀痛,通过萨满文化即将不复存在的事实来引起更多的人去关注那些正在消失的文化。不仅是“最后的山神”,该作品是在呼吁与警醒大众,那些肉眼看不到的东西正在流逝,我们不应该仿若处在梦魇中的人,假装看不到。那些传统文化,是中华上下五千年的证明,是历史长河沉淀下的精华,是我们人类的财富。
(二)人与自然的关系
“孟金福这一辈子眼看着树林越来越稀,野兽越来越少,常常感到山神正在离他远去,感到一种无可依托的孤独”。孟金福的惆怅是因为山林的远去、山神的远去以及文化的远去。在新的生活方式之下,越来越少的人再靠近山林、崇敬山林,这是孟金福心底的哀叹,亦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悲哀。
三、弗拉哈迪风格在中国的本土化
(一)对弗拉哈迪风格的继承
即将消失的古老文明——包括《北方的纳努克》在内,弗拉哈迪的所有作品都在记录即将消失的文明。中国的记录片《最后的山神》亦是如此,通过影片向观众表现正在消失的萨满文化。每一种文化都是经过岁月的沉淀,都曾有过辉煌、引起尊崇,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与文化传递者的减少,那些曾经的辉煌开始走向灭亡,我们能做的就是对其进行记录与保存。
表现美而回避丑——在弗拉哈迪到达北极的时候,现代工业文明已经渗透到了人们的生活中,但弗拉哈迪有意识的去避开带有现代标签的事物,尽量去展现原始淳朴的生活。在孙曾田到达兴安岭的时候,那里的人们已经开始定居生活,孙曾田却不去规避那些“丑”的事物,反倒在片中穿插定居生活的片段,通过生活模式的变化突出山林文化的消失以及人与自然的日渐冷漠。
故事化——《北方的纳努克》按时间顺序将故事链接成段落式的叙事结构,作品中的矛盾冲突以及高潮都是事件本身所有,段落之间紧凑且有节奏感。《最后的山神》按照冬一夏一冬的时间顺序进行故事化的叙事,作品中的矛盾冲突以及高潮都是由人物关系进行构建。孟金福夫妇与郭宝林全家、儿子之间的冲突属于新老一辈鄂伦春人的矛盾。孟金福作为中国境内最后一位萨满代表即将消失的文化,而郭宝林作为第一批过上定居生活的鄂伦春人,他代表现代社会生活对原始生活的渗透,而孟金福祭拜山神时的虔诚庄重与儿子的心不在焉形成对比,深化古老的文明正在消失的主题。
戏剧性——《北方的纳努克》中有很多戏剧性的经典镜头,通过事件本身来展现给观众。纳努克捕捉海象时不放弃,在冰块上直打趔趄,这样戏剧性的镜头向观众传达的不仅是欢乐,还有纯洁的心灵与天真朴实的品格。《最后的山神》中的孟金福坐在被砍掉的山神树旁,一言不发的样子透漏着些许的无奈。在该固定镜头中,刻有山神像的木桩占据画面的较大部分,孟金福全身缩在画面的左下角被木桩包围着,暗示孟金福最后的依靠即将消失。
真实——纪录片的核心宗旨就是真实。人物真实是纪录片的条件,事件真实是纪录片的基本。无论是《北方的纳努克》中的纳努克,还是《最后的山神》中的孟金福,他们都是真实存在的人物,而影片内容全部都是导演跟踪拍摄时记录的,当然二者中都有一部分是导演要求对现实生活的演绎。环境真实是纪录片的保障,弗拉哈迪所记录的北极爱斯基摩人的生活是弗拉哈迪几次前往北极进行拍摄的,《最后的山神》中已经过上了定居生活的孟金福夫妇还是习惯山林生活,他们住的是树枝与兽皮搭成的仙人住,喝的是冰块煮化的水,吃饭用的工具都是孟金福用树枝削好的……内涵真实是纪录片的核心,弗拉哈迪的作品大多表现人与自然的关系、人性的美以及对即将消失文化的眷恋。而孟金福夫妇定居之后还长期生活在山林中,他们对山林的眷恋以及对神灵的信奉是我们理解不了的。
(二)对弗拉哈迪风格的突破
选题的拓宽——《北方的纳努克》,弗拉哈迪用猎奇的眼光深入爱斯基摩人的生活,力图向观众展示接近原始人类的生存状态。作品一方面将爱斯基摩人的优良品格传达给观众,另一方面通过对原始生活的记录,表达对古老文明的敬仰与对现代工业文明社会的不满。由于地域文化的不同,中国的纪录片不局限于即将消失的文化与人性的真善美,更多的着眼于普通人群、弱势群体以及边缘人物。在《最后的山神》中,作者不仅是在表达对即将消失的文化的惋惜与哀叹,还表明人与自然之间的疏离与无奈。
内涵的拓宽——弗拉哈迪的作品在赞扬人性与文化的美,而中国的纪录片在此基础上,还包含着人类的无奈及无助。《北方的纳努力克》中作者有意的过滤消极镜头,从而净化观赏者的心灵。而孙曾田并不避讳“丑”,反而将现实呈现在观众面前。孟金福坐在被砍伐掉的山神树旁,“仿佛自己被砍伐掉一样”,正是这些“丑”的描绘让观众印象深刻,更加了解老一辈鄂伦春人的无奈与无助。
表现形式的拓宽——由于技术带来的局限性,弗拉哈迪的作品较少使用现场同期声,但其音乐有张有弛,字幕语言简洁凝炼,使观众思绪更加清晰且有身临其境之感。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现场同期声大量应用于纪录片,使片中人物形象更加饱满生动。在《最后的山神》中,孟金福的祈福声虔诚敬重,山林间的虫鸣鸟叫真实灵动,篝火噼啪的爆裂声热闹淳朴,萨满“跳神”时,鼓声、铃铛声相互交织,令人怔怔颤动。音乐的运用也较为贴切的,日出日落的平淡宁静,春夏的活泼昂扬,秋冬的悠远深邃,无时不刻透露着孟金福夫妇的心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