诡异世界的坐标系
2018-08-09郑若麟
郑若麟
《新民周刊》在这场新的认识西方的启蒙运动中正在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
最愿意合作的刊物之一
我已经记不得第一次为新民周刊撰稿是何年何月何日何时了;亦记不得是什么主题、什么题材、什么体裁、是哪篇文章了。
我为不少杂志撰稿。但我却非常明确一点:《新民周刊》是我最愿意合作的刊物之一。因为我在《新民周刊》上发表了大量在其他主流媒体上可能无法发表的文章,以及大量其他主流媒体很可能不愿意发表、而我却非常想表述的观点。从《新民周刊》创刊伊始,我一直为其长年撰稿,甚至一直到我结束在法国巴黎常驻记者任职后,我继续在为《新民周刊》撰稿,直至今朝。
我与《新民周刊》的友谊,是建立在真正的相互理解和彼此认可的基础之上的。
我在法国时,也经常为法国媒体、法国杂志撰稿。比如我曾经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是法国周刊《青年非洲》的特邀作者,为该周刊撰写了不少有关中国客观现实(而非如其他法国杂志经常发表的那类千篇一律的“负面中国文章”)的稿子。我也曾为一本题为《月刊》的杂志撰稿,是这本杂志上有关中国方面的文章的主要作者。在法国的汉学界有一定的影响。我甚至曾在法国一本非常著名的月刊《两个世界》(larevue des Deux Mondes)发表过文章。很多法国同行告诉我,能够在这份杂志上发文是作者们的一个“荣幸”。因为这是法国资格最老的杂志之一。《两个世界》创刊于1829年,是法国最严肃的文学性综合月刊之一。很多法国著名作家如大仲马、巴尔扎克、圣·波夫、波德莱尔、乔治·桑等都曾在该杂志上发表文章。不少法国作家听我说曾在这本刊物上发表过文章,都对我刮目相看:因为在法国,凡擅长舞文弄墨者,无不以有缘在该杂志上发表文章为荣。
有一个细节颇能说明问题:我在为《两个世界》杂志撰写第一篇有关中国如何看待欧盟的文章时,开始曾引用了不少国内名家的话语,以此来证明我之所言不虚。杂志总编米歇尔·克雷布把我的稿子退给我,让我去掉引言:“我们的杂志是让其他人来引用我们的,而不是我们去引用他人。”“我需要的就是你的观点。”后来文章发表后果然是他人来引用我的文章……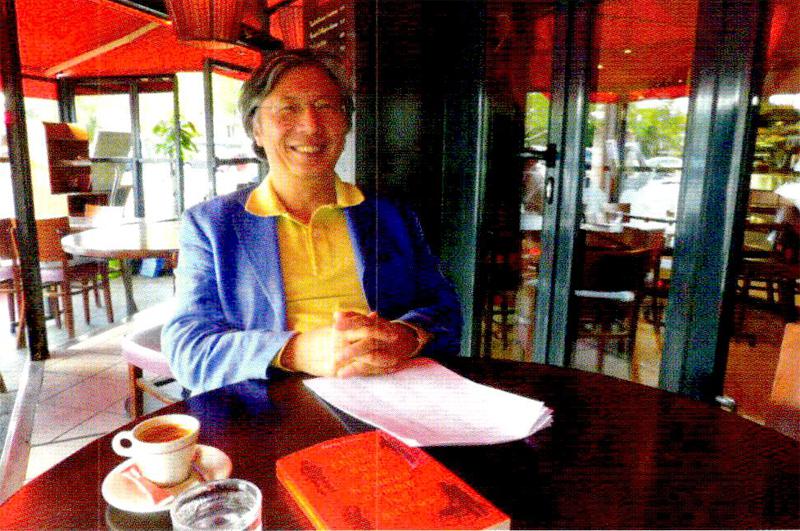

我感觉,《新民周刊》也是这样一份杂志。
我不知道针砭时弊是否应该成为一份伟大杂志的主要个性。但无论从哪个意义上来说,传递信息,总归是一份杂志的首要任务。而我所做的,就是在传递信息。与《新民周刊》合作的体会,就是周刊的同仁们能够接受我所传递的某些非常态的、非常规的、甚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有着某种非“理性的”(对于不理解我的人而言)、打破所谓“常识”但却绝对真实、只是国内尚未了解的信息,这些信息以及我的评论都能够在周刊上一一发表,这是非常不容易的。要知道,一般读者都是保守的、不易接受真正新的、特别是与自己固有观念相悖的信息的。在网络时代,人们获得信息是那么的容易,人云亦云是那么普遍的现象,对于一份杂志来说,要争取尽可能多的读者,就不能总是“逆”着读者的心思而行。所以大多数杂志都是平庸的、随大流的。但《新民周刊》独具慧眼。
我相信,《新民周刊》的读者是认同和支持这一点的。
《新民周刊》在今天這个矛盾的、复杂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相当诡异的时代,正在起着一种坐标系的作用。要知道,今天这个时代,要获得人人皆知的信息实在是太容易了。只要打开手机,一切都在掌中。然而与此同时,想要获得真实的、深刻的、能够经得起历史考验的信息,又是难乎其难。而且随着每天铺天盖地而来、塞满了我们头脑的种种新闻越来越多,我们对真正有意义的信息的鉴别能力却在日益下降。我们获得的信息越多,世界就变得越复杂;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理解不是越来越深入,而是越来越肤浅。信息爆炸时代使我们越来越有一种迈入对世界的“感知迷宫”的感觉。今天我们白问一句:我们真的认识我们生活其中的这个现实世界吗?恐怕很多人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是会犹豫的。
然而,认识和了解这个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却是我们不可回避的一个历史性使命。“知彼”,更确切地说就是“知西方”,是正在伟大复兴征途上的中国所迫切需要的。
因为,只有“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我们应该认识到,我们对西方的认识极其有限。我们有必要发起一场重新认识西方的新启蒙运动。而《新民周刊》虽然不是一份专门介绍外国的杂志,但却很有可能在其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
中国自1840年被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国门后,我们却很少真正去追求“知彼”。我们更多的是努力去“知己”;我们更多的是去反省自身,去研究“为什么我们会输”,而很少去研究“为什么他们会赢”。多少年来,尽管我们在“知己”方面不断地取得越来越深刻的进步(也许是退步,我不得而知),但我们在对西方的认识方面,也就是在“知彼”的领域,几十年甚至可以说近百年来却几乎没有“质”的改变。
对此,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看法。有人会说,我们翻译了那么多的外国文学和学术作品、我们在国外派驻了那么多的记者、我们的学者跑遍了全世界……怎么你还说我们在“知彼”领域存在不足?我这么说当然是有着我自己的切身体验的。我自己就是驻外记者,而且常驻法同长达二十多年。我当然不是轻易下这个结论的。
我们对西方的认知缺口
我们对西方的认知,无论是从理论还是从实践来看,都有着非常大的缺口。
比如我们到今天也不明白犹太、基督和伊斯兰三大一神教对整个西方文明、西方历史和西方精神的深刻的、绝对性的影响。因为我们从来都是对与中国没有直接关系、特别是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东西和事务不感兴趣。最近我们开始讨论是否存在着一个“中国学派”的问题。所谓“中国学派”,广义而言,就是从中国人的视角来解释发生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事物,与中国没有太大关系的事物。为什么今天会提出“中国学派”问题呢?因为过去我们对“与中国没有太大关系的、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事务”,我们一点儿也没有兴趣。今天才刚刚出现一点儿变化。这是我们对“知彼”方面所存在的第一个缺口。
其次,我们对与我们不同的东西也不感兴趣。西方有一种说法,“上帝是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的”。这句话的含义,就是人总是“以己度人”的,总是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来理解他人的。中华文明是人类文明中惟一的一个真正的无神论的世俗化文明。我们的世俗化曾经为深陷宗教困境的欧洲文明、特别是法国大革命带来过伟大的精神解放启蒙。但反过来,正是因为我们不信仰上帝造人说,所以我们对西方文明的核心即“一神教”不太感兴趣。比如我们从来不会关注,为什么美国总统宣誓就职时手是放在《圣经》上,而非放在宪法之上。对与我们不同、不一样的东西不感兴趣,是我们对“知彼”的第二个缺口。
第三,我们对“知彼”一直是浅尝则止。因为我们不明白,西方才是一个真正的复杂体。中国其实并不复杂,而是庞杂。因为中国太大、人口太多、民族太杂、历史太长、地区差异太悬殊……所以中国非常庞杂。研究中国需要的是耐心。而西方则是一个真正的复杂体。因为西方是多层次、多结构、不透明的。尤其是西方理论与实践往往不是一回事。我们过多地去研究西方的理论,特别是他们专门向我们推荐和介绍的理论(比如法国文化部每年都要向国外译介法国某些书籍提供资金赞助,原因就是这些书籍往往是西方希望输入中国,来影响中国思想的),而未能从西方的实践中去认识西方行为的真实内涵。我曾经反反复复地介绍过西方的一句名言,叫做“照我说的去做,不要照我做的去做”。就是说,你要理解西方,不能照他说的去理解,而要看他如何行动、从他的实践中去理解。西方的“言”与“行”是不一致的。
今天美国、欧洲针对中国的许多做法,我们都可以发现西方“言”与“行”之间的不符。“言”往往是道德高尚的、具有某种西方口中的“普世价值”的意义,而“行”则是对西方利益的绝对维护。西方学术界的本事,就是把两者完美地结合起来,就是能够为最自私的行为找到最美丽的辞汇。所以他们能够把以贩卖鸦片为目的的战争,说成是为了“自由贸易”、把遏制中国“2025”科技创新计划,说成是“中国不遵守贸易规则”……美国总统特朗普眼下正在给我们上课。我们只要细细观察今天美国的各种声明、宣言和他们具体执行的各项政策,我们就可以理解这一点。这是我们认识西方的第三个缺口。
第四,我们过度相信西方的蓄意传递给我们的信息、相信西方自己从理论上对西方自己的解释,是我们无法认识真正的西方的第四个缺口。
比如西方告诉我们,他们的政治体制是一个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体制,是他们社会稳定、国家强大的根本原因。然而我在法国二十多年的深入研究,发现行政、立法、司法这三个权力不仅并不那么“分立”,而且从实践上看也无法“相互制衡”。更重要的是,这三大权力绝对无法真实地反映西方社會现实权力结构的构成。统治西方国家的,是资本、政权和大众传媒这三个真实的、处处可见、无处不在的真正的三大权力。我在法国生活了二十多年后认识到,一个普通的法国人,一个遵纪守法的法国人,可能一辈子不会与政权打交道,顶多去投个票,满足一下“统治我的人是我选出来的”这样一种心态;但他却每天每时每刻都会处于资本(财团)和大众传媒这两大权力的控制之下。对此,当我告诉国人时,很多学者的疑问是:我们从来没有从西方的理论书上看到资本、政权和大众传媒三大权力之说呀!《新民周刊》多次发表了我的有关这方面论述的文章,为中国读者认识西方提供了另外一个角度。
最后第五点:因为我们无法做到真正的“知彼”,同时我们又缺少自知之明,不知道自己对西方实际上并不了解,但却自以为自己已经对西方有了充分的认识,特别是对西方蓄意传递给我们的理论上的西方已经了如指掌,甚至能够背诵很多西方的名流名言,因此我们便在自己的心目中,“塑造”出一个理想化的西方,一个几乎是完美无缺的西方,并把这个理想化的、完美无缺的西方树立成我们学习、模仿的标准;更为荒唐的是,把这个理想化的、完美无缺的西方当作衡量我们自己一切的坐标系。这就是为什么近百年来出现一股又一股对中国进行自我否定的浪潮的深层次原因。
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台湾作家柏杨。一部《丑陋的中国人》实际上把柏杨自己钉在“丑陋”的耻辱柱上。因为从书中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柏杨笔下的“西方”,完全是他对西方的表面观察而形成的一个“西方印象”,加上自己纯臆想的部分,进而构成了一个“十全十美”的“虚拟西方”,然后以这个“虚拟西方”来批判现实中的中国。说句难听的话,就是把西方的臭脚想象成芳香美妙,进而批判我们自己的脚太臭……
正因为我们“只知己”而“不知彼”,所以我们在与西方打交道时,很难真正做到“百战不殆”。更进一步说,认识“彼”,才能更好地理解“己”。在“不知彼”的情况下,我们的“知己”也是有缺陷的、片面的。因此,今天,我们已经提出了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那么,“知彼”,从真正意义上认识、了解和理解西方,便成为我们当今思想界的一个当务之急。因而我今天提出,我们需要发起一场新的“启蒙”运动,就是要重新认识西方。
《新民周刊》在这场新的认识西方的启蒙运动中正在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
希望《新民周刊》能够坚持这一角色,直至我们国家的伟大复兴成为现实的那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