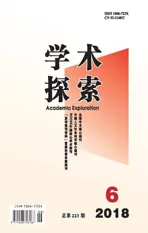云南汉语的历史地理分布及相关问题试探
2018-07-03牟成刚
牟成刚
(文山学院 人文学院,云南 文山 663099)
云南汉语成为地域性方言一般认为是在明代,可汉语在当时的影响并没有遍布滇域全境;宋元之前,特别是南诏大理时期,云南曾长期处于相对隔离的自治状态,一般认为汉语这一时期在滇地已接近消失,但实际上这是一种误解,汉语其实仍以与夷语相融的方式焕发生机并积极产生影响。此前,学界对汉语在云南自汉晋以来的历史地理分布及相关问题关注有限,以致大家对云南汉语的生存环境及演变情况难以整体客观把握。文章将根据移民史实,结合历史韵书及文献资料,辅以语言接触等理论,对云南汉语的历史地理分布及语言来源等相关问题试做探讨,以便人们更深入地把握云南汉语的历史演变脉络并解释差异原因。
一、宋元及之前的南北向移民与云南汉语的生存格局
(一)汉晋驿道汉语的分布与“夷化”
云南有汉族移民的最早记录当为战国末期的庄蹻王滇。据《史记》之“西南夷列传”记载,楚威王时,命将军庄蹻西征,蹻至滇池便以兵威定之属楚,可庄蹻入滇不久,便逢秦夺巴黔,以致滇楚隔绝,故庄蹻无奈便变服从夷俗,且以其众王滇。故一般认为“云南至汉武帝以前是‘西南夷’聚居的‘化外之地’”,[1](P106)庄蹻入滇这次移民带来的汉语在当时并没有其生存的环境。秦并巴蜀后,蜀郡太守李冰即在今川滇交界的僰道(今四川宜宾地区)修筑通往滇东北的道路,秦始皇统一全国时又将该道延伸至今曲靖一带,因道宽五尺,故俗称“五尺道”。秦开五尺道沟通川滇,而且还在云南设置郡县,这“标志着中央王朝对云南正式统治的开始”,[2](P33)这为此后宋元之前南北移民及汉语进入云南奠定了基础。
汉晋时期,随着南北向驿道的开发和维护,四川等北方汉族逐渐迁入云南。因地理毗邻和行政管辖隶属的关系,四川此时迁入云南的汉族主要集中在滇东的味县(曲靖)和滇东北的朱提(昭通)一带,汉语也随之在这一带开始存在并传播。云南今滇东的曲靖和滇东北的昭通,是云南临近川南宜宾(时称“僰道”)的大坝子,两地可由横水相连,汉扩展延伸了秦五尺道至今滇池一带,后人又称“朱提道”,[3](P323)这进一步强化了滇东北经由宜宾而至川陕内地的往来紧密关系。同时,西汉王朝为招抚滇中偏西一带的部落,仿秦置郡县而治,并于公元前129年疏通成都经雅安、西昌而至今滇西的大姚、永仁、姚安的大道(东可至滇池,西可达洱海),史称“零关道”或“西夷道”。此外,西汉孝武帝元封六年,汉军开通了从大理向西经保山过腾冲而至印度的永昌道(又称“博南山道”),此道向东可过姚安(与零关道相通)至昆明达曲靖,最后连接朱提道而至成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蜀身毒道”。朱提道、灵关道、蜀身毒道的开通,强化了汉晋时期中原与云南的联系,汉语也随汉族移民在云南驿道和滇东北一带得以使用,但范围比较有限,因为根据历史记载,驿道的通畅性和使用率并不如人意,只有朱提道一段靠近蜀地郡治僰道,尚基本能维持正常沟通。
语言与民族一般都是相互依存的,滇域的汉语主要是随汉族移民而带来,云南在汉晋时期就有汉族从驿道移民进入。汉开通永昌道后,即“派遣大批汉族进入永昌,并在这里设置了不韦等六个县”,[2](P36)随后又征服滇池东的劳浸、靡莫等部落,并驻兵屯田镇戍。汉晋迁入的这些汉族移民主要沿驿道分布于滇东北的昭通地区、滇中的滇池沿岸和滇西保山一带,并在日后的三国两晋时期逐渐形成地方豪族大姓而影响决定着云南的统治。但总体来看,汉晋时期在云南的汉族移民,其数量比较有限,而且在地域分布上也不平衡。当时,朱提道开通较早,故“中原汉族劳动人民进入云南,多半集中在滇东北和滇东一带”,[2](P66)汉语自然也就在这一带最先得以使用并演化。汉字是汉语的视觉体现,而“汉文字自西汉起便在云南开始使用”,[2](P46)滇东曲靖出土的东晋《爨宝子碑》和陆良出土的南朝《爨龙颜碑》,其文体书法得汉晋正传,而昭通出土的汉《孟孝琚碑》记载,孟孝琚“十二随官受韩诗,兼通孝经二卷,博览(群书)”。据此,汉晋时期汉语在滇东趋北一带已经有一定的使用范围和影响力了。其实,滇西的永昌郡一带,汉语随吕氏及后来的永昌道开发者也很早就进入了该地区,可因该地远离巴蜀,地方部落各自为政,交通时有阻隔,故汉语在滇西和滇中一带的生存发展空间在当时比较有限。只有滇东趋北的曲靖、昭通一带,因地域毗邻四川僰道,受蜀地汉文化的影响较深,汉语方才在滇东趋北地区具有一定的使用影响力度。
云南汉族移民在汉晋时期,主要是沿驿道呈点状式移民,相互之间相隔较远,且数量非常有限,因此汉晋时期的汉语“夷化”现象比较严重。当时,中原政权在云南主要依靠早期少量落藉云南的移民大姓,组成“夷汉部曲”治理云南,但这些汉族大姓为扩大生存和管理的空间,一般都主动融入当地少数民族,以致夷汉主从甚至难以分清。因此,“在三国两晋时的南中地区,各民族间的融合,主要表现为汉族的‘夷化’,即汉族人民逐步融合于‘夷’族人民”,[2](P68)因此,汉语在当时自然也就随之呈现出被“夷语”同化的趋势。
(二)唐宋元汉语在云南的生存与融合
云南在唐宋时期较长一段时间里依靠地方的夷帅酋长进行统治,特别是自唐天宝战争至元蒙灭大理前,云南近六百多年处于相对独立的局面,汉语在这段时间随汉族移民的减少难以形成聚居态势而萎缩,但南诏大理政权主动吸收融汇汉文化,而使得汉语与夷语融合,出现利用汉字改造而形成夷族文字的情况,呈现出部分先进夷族的语言混用汉语的格局。
中原政权在汉晋晚期通过地方夷汉大姓治理西南夷,至隋初云南一带已“实际上为大姓贵族爨氏所割据”,[2](P70)不服朝廷招抚。隋代于云南虽置南宁州总管,但朝廷基本不问政事和民生,滇夷这种部落支离而不相役属的格局一直延续至唐初。唐太宗之后至天宝战争前,中央王朝在云南的管理主要采用的是羁縻政策,虽然开设姚州都督府协调指挥云南各部落抗御吐蕃南侵,但每年仅派蜀地汉兵五百人轮戍姚州,故汉族军事移民数量几可忽略。唐天宝年间,南诏占据爨地并乘势坐大,引起中央朝廷的警惕,于是发动了“天宝战争”,但以失败告终。自此,唐天宝战争到有宋一代,云南有近600余年的时间相对独立于中央王朝的有效管辖之外,以致有学者认为“到元代初年重新统治云南之前,这里已没有汉语的地位”,[4](P614)此说虽显绝对,但内地移民的中断和管理的缺失必然会导致汉语的萎缩。
汉语在云南于唐宋时期,虽因官方规模化移民的阻断而趋于萎缩,可因夷民对汉文化的推崇和向往,加之阻隔不断的地缘联系及民间百姓的交流,*马曜指出:“南(诏)、唐关系时断时续,时密时疏,并未改变南诏对唐王朝的臣属关系。而人民之间的联系,则从未中断。”(参见《云南简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8页)使得汉语和夷语得到了融合的空间和时间,这一点在今白族使用的白语和白文上体现得尤为突出。汉晋时期的滇东白蛮聚居地毗邻蜀地,与内地关系最为紧密,且其民族成分不乏汉族,故受汉文化的影响最深。唐天宝四年,滇东爨氏反叛,滇西南诏地方势力以助唐平叛为由,率军东进滇中、滇东趋北一带,并在迫降西爨白蛮后完全统治了这一地区。南诏为分化西爨的势力,强迫西爨白蛮“徙二十万户于永昌城”,[5](P48)这些受汉文化影响较深的白蛮徙至落后滇西,便与洱海周边一带的土著河蛮(亦属“白蛮”)相融合,改变了洱海一带的主体民族结构,历经南诏大理国五百余年的经营,洱海成为云南的统治中心,当地以白蛮为主体的人民,逐渐融合周边民族而使得语言和风俗习惯渐趋一致,至迟到宋大理国时期“白族共同体至此形成”。[6](P28)既然白蛮是后来白族的主体,那么其原西爨时期融收“夷化”的汉语和汉字,自然也就深深地影响着以大理为中心的民族沟通与交流。天宝战争后,南诏在异牟寻的带领下重归于唐,并主动派贵族子弟到成都求学,使用汉语汉字,学习史诗书数,业成则归。异牟寻死后,南诏于公元829年毁盟,率兵攻掠成都,抢夺子女百工数万人及无数财物而去,随后又“四次打越嶲、成都,掳掠数十万人”。[2](P77)可见,唐代时期,南诏一方面主动学习汉文化,使用汉语汉字;另一方面迫使大量的蜀地汉民移入云南,这又进一步强化了汉语和汉文化的存在。但唐宋时期,云南均相对独立,其以白蛮为主体的地方统治集团,客观上决定了他们不会也没有空间被决然汉化,但因有西爨历史的“汉化”根基以及汉文化自身的优越性,辅以唇齿相依的滇蜀地缘关系,促使南诏至大理时期的夷民主体对汉文化怀有较高崇尚的心理,他们把说汉语和识汉字看成是一种有身份的象征*杨应新指出:“大理白族在日常交际和书写白文时,喜欢使用汉语借词,传统习惯上有一种心理状态,认为借用汉语多的人文化水平高。所以民间艺人常常恰当地在唱词中插入汉语借词,以此显示自己有‘文采’”。(参见:《白族本族祭文》,载《民族语文》,1992年第6期第72~74页。)。因此,“白族人民一向乐于借用汉语词来丰富本民族的语言”[7](P115),并至迟到唐代在“借用汉字的推动下创造了白文”。[2](P96)白族不只从汉语里借用本民族语不能表达的概念,甚至其能表达的概念“白语也往往吸收汉语借词和本民族词更换使用”,[7](P113)白语对汉语的这种借用相融情况至今仍在延续,据统计研究,白语和汉语的同源词占七成以上,汉语和白语彼此之间融合之深便由此可见一斑。
唐宋之后,元蒙出于在蛮夷腹地“制兵屯旅以控扼”的目的,历史上第一次有计划地在云南大规模进行军民屯田。然而,在元代的军民屯田中,绝大多数是云南本地少数民族,据史料统计,汉族因军屯迁至云南的人数最多也就是六千左右。鉴于元代汉族迁入云南的人数有限,加之这些有限的汉军还多与蒙古军、爨僰军等共同屯田戍守,故汉语在元代不可能成为云南大范围内各民族的通用语言。但元代因军事需要,于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首开东西走向的普安大道(或称“滇黔驿道”),这从根本上改变了过去北南移民走向,它对明代及之后的云南汉族移民及当地汉语方言的形成和分布格局,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三)宋元及之前云南汉语的分布特点与川蜀方言的影响
云南汉语在宋元之前,主要呈点状分布于交通沿线的管辖要地,可因这一时期“夷多汉少”,故汉语多被夷化或融合,其中又以融合为主,汉语正是以融入夷语的方式保证了自身的存在,并维持其在云南主体语言中的影响力。滇东偏北一带(今曲靖、昭通)是受汉文化影响比较早也是比较集中的地区之一,由此向西的滇池(昆明)是一个据点,楚雄、大理和永昌(今保山)又各是一个点,这些相互隔离的点受到汉文化的影响较深,汉语也在这些地方得以小范围使用,可夷人在当地一般都是割地“分而治之”,以致点状分布的弱势汉语在当时难以连片,汉语的扩张势头被限制;此外,中央在这一时期,针对云南的政策主要是保障蜀地后方安全,让云南“治而不乱”即可,故汉族在这一时期的移民人数非常有限,少量的汉族移民进入云南多被夷化,处于弱势地位的汉语也多与夷语融合,这样一来,汉语在当地的内源扩张力就受到限制,但却以此保护了自身的存在并维持其必要的影响力。
汉语在云南于宋元之前虽多被当地少数民族夷化或融合,但并没有消失,甚至可以说,汉语正是以夷化融入少数民族语言为载体,保证了汉语在云南的存在并焕发出另一种生机,而得以继续扩大其影响,这一点在白语中体现得非常明显。白族“语言中有百分之七十是古汉语词汇”,[8](P22)可以看出汉语词汇在白语中已占主流,这其实已经不再是夷语融合汉语这么简单的事情了,罗常培就认为白语是“夷汉混合语”,[9](P216)郑张尚芳更是指出“白语是汉白语族的一支独立语言”。[10](P19)如“古无舌上音”“古无轻唇音”“尖团音分两类”等中古以前的语音现象在近现代汉语官话中已很少见,但在白语中仍大量存在,至于“鸟雀曰隹、蛇曰它、牛羊之属曰特、睡曰寝”等则属于古语词的遗留。据此看来,云南于宋元之前的汉语不是没有地位,而是通过与白语等夷语融合隐藏来继续发挥自己的影响力。
中原王朝在宋元之前,主要是以川蜀为据点而治滇,南北向交通路线的构筑,决定了云南在这一时期内的移民原籍主要为四川人,故古蜀语在这一时期对云南汉语的影响最大。如水富、绥江等方言点的入声调为独立的中平调,这是元前四川南路话的典型特点。*四川南路话是元末以前四川本地汉语方言的后裔,主要分布于岷江以西以南,保留独立入声调是南路话的共同语音特征之一。(参见周及徐:《南路话和湖广话的语音特点》,载《语言研究》,2012年第3期第65~77页。)大理洱海周边如大理、下关、鹤庆、剑川、云龙、洱源等地存在入声调,黄宗谷称之为“土著汉话”而与“云南官话”相别,他明确指出“洱海地区的土著汉话,就是南诏、大理国时期白蛮鸟蛮、汉人等各族人民交际的工具”,[11](P60)这无论在时间和特点上都与四川南路话基本相符。根据以上语言例证,辅以交通移民的历史事实,可以看出在宋元之前,中原王朝主要越秦岭经巴蜀而治滇,所以,受其影响,云南当时土著汉语的来源主要是古川蜀汉语。
二、明清及之后的东西向移民与云南官话的分布格局
(一)明代云南官话的语源基础及其地理分布特征
云南夷汉民族结构的改变是在明代。元代及其之前云南的民族是“夷多汉少”,汉语在云南主要体现为夷化与融合;明代及其之后,内地大规模移民入滇,云南自此“夷少汉多”,汉语成为强势语言,并在与夷语及方言的接触影响中,逐渐形成具有地域特征的云南官话。
明在云南基本沿袭元代的交通格局,鉴于都城的南移和北迁,进一步强化了“普安大道”的西东向沟通作用,此道“从昆明往东至曲靖,东行入贵州普安,经贵阳出湖南转内地各省”,[12](P148)其自元明始即为云南进出内地的咽喉要道。普安大道的开通和地位的强化,改变了宋及之前朝廷越秦岭过蜀入滇的“北南向”移民和管理路线,使云南自此与内地呈现出“西东向”的交通管理格局,以致有明一代,因军事屯戍的需要,以湖广江南籍为主的汉族沿此道大量移入云南,而这批移民所带来的汉语即为今云南官话形成的语源基础。
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派出30万大军自南京出发征滇,明军以绝对的兵力优势进入云南,至洪武十五年(1382年),就基本平定了云南全境。此后,明王朝为有效控制云南,推行“以夏变夷”的政策,于是在交通要道和行政主要地区,实行了以卫所留戍为主的“军屯”制度,要求军事屯田的士兵,必须有家室同行,成为军户,这样就使得内地汉军携同其家属在明代随军大批量移入云南并定居下来,家庭及集体驻军的形式,削弱了汉族被“夷化”(如通婚等)的概率,强化了汉族群体及其文化的影响力。据统计,明代“从中原迁徙了近200万汉族人口进入云南”,[13](P265)汉族至迟到明末已“超过了所有土著民族的总和”,[1](P111)已成为当时云南的第一大民族,这对云南地方官话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据研究,明中后期反映云南本地方音的两本韵书,即兰茂《韵略易通》(1442年)和本悟《韵略易通》(1586年)的出现,标志着具有地域方言特征的云南官话已渐趋成型。[14](P3)
根据记载,明代的云南移民来源并不一致,五方杂处,语言也必然各异,云南官话的形成势必以某种强势的汉语官话方言为基础。云南“元末明初的移民主要来自陕西、四川、湖广、江西以及南京等地,沐英部队中还有相当的山西、河北、河南士兵”,[15](P77)如洪武十四(1381年)年平定云南时的30万军队主要来自南京,多为江南湖广藉移民,洪武十九年(1386年)迁湖广长沙卫13000人充实北胜州(永胜县)并设置为澜沧卫;据《明太祖洪武实录》记载,洪武二十年(1387年)曾多次调集各地军民迁入云南:八月调四川都指挥司2500人到云南品甸(今祥云)屯种,九月调湖广官军71560人征戍云南,十月要求湖广常德、辰州二府军民家庭以“三丁抽一”的方式往屯云南,并调山西、陕西8900人到云南屯戍,并于次年(1388年)发河南祥符等十四卫步骑军15000人往征云南;[16](P16);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再“征湖南辰阳兵5000人到平夷卫(今富源)屯田”[2](P138)等。从这些移民记载可知,明代云南有多个移民来源,但来自官话方言地区的主要是两个,其一是黄河流域的中原官话区(如山西和陕西等),另一个是长江流域的江淮官话区(如江南湖广一带)。鉴于明初的政治中心在南京,江南湖广一带与云南因长江而体现出“一衣带水”的关系,而普安连接湖广的大道从元代就已开通,成为内地移民云南的主要交通要道,故东西向的交通极为便利,同时结合移民数量来看,以南京为中心的江南湖广一带的移民数量显然在云南的移民中占据绝对优势,因此,云南官话的语源基础应是江淮官话,这一点辅以语音对比可以得到很好的证明。语音对应规律是判定方言之间是否同源的有效方法之一,江淮官话与云南的官话的入声调均不分清浊合为一类(如“释石”二字,昆明话同读阳平31,南京话同读s5;中原官话则会因声母的清浊而分化),中古精知庄章组的分合格局同属“南京型”(中原官话则属“济南型”),*南京型是“庄组三等(除止摄合口和宕摄)、精组与庄二知组(除梗摄)章组二分”,济南型是“知庄章组与精组二分”,以昆明话为代表的云南官话属南京型。(牟成刚《中古精知庄章组声母在西南官话中的今读类型与层次演变》[J].中国语文研究,2010(2):11-22,第16页)前后鼻音in/i和n/彼此混同(如“音英”二字,昆明话读í44,南京话读i31,而中原官话则是分读不同的音)等等,这些语音对应情况显示云南官话和中原官话相去较远,而与江淮官话则十分近似,故依移民和语音对应规律来看,云南官话形成的语源基础应是以南京话为代表的江淮官话。当然了,明代移民中也有江西、四川等地的移民,可与江南湖广的移民在量上不能相比,加之四川南下的少量移民也是明代入川的军队或当时“湖广填四川”辗转而来的江南人,仍属湖广江南方言区,故内地其他地区的移民方言并不会影响江淮官话方言对云南官话形成的源头主导作用。云南官话的形成源头是江淮官话,它是以南京为代表的江淮方言向西“移民”云南后继续演变的结果。
云南官话在明代于云南的分布并不平衡。明代,中央朝廷大规模移民云南的目的是“镇戍军镇重地、控扼交通干线和加强边疆防务”,[15](P75)故朝廷会因交通要冲差异、地理环境优劣以及民族政治关系等予以有侧重点的移民屯置,从而使得云南的外来汉族移民呈现出“空间上分布不平衡、时间上不同步的特点”。[17](P171)明廷为更有效地控制云南,结合滇地实际,明初就采取“改土归流”和土官制度并存的治理格局,明令“三江(澜沧江、怒江、元江)之内宜流不宜土,三江之外宜土不宜流”,在这一政策的引导下,按万历《云南通志》(卷七“兵食志”)的记载,到“明代中后期云南都司领有20卫、3御、17个直隶千户所,共有131个千户所建制”,[15](P75)以汉军屯置镇戍的形式分布于控扼重地及各坝区城市。滇东是东西向的普安大道和南北向的乌撤道交汇要冲,且有曲靖、陆良、昭通等坝子的分布,军事位置极其重要,朝廷安置了曲靖、平夷、越州、陆凉共4个卫、17个千户所(含1个直隶千户所)镇戍,汉族移民基本覆盖了滇东一带;滇中是政治经济中心,设有云南左右前后中和广南共6个卫、46个千户所(含7个直隶千户所),以滇池为中心的滇中地区是当时汉族移民人口最多、分布最密集的区域;滇西地广人疏,散布有楚雄、大理、大罗、洱海、蒙化、永昌、腾冲、澜沧、景东共9个卫(另有鹤庆和永平2御)、67个千户所(含7个直隶千户所),洱海周边是其分布中心,控扼大理、永昌至腾冲的交通要道,澜沧卫、鹤庆御深入滇西北;滇南仅有临安1卫(另有通海1御)、9个千户所(含2个直隶千户所),军屯移民仅至建水、蒙自区域。综合卫所的分布情况来看,滇中、滇东基本覆盖汉民族,滇西的汉民族主要分布于以楚雄坝子、永昌坝子(延伸至腾冲)和洱海为中心的地区,滇南集中于临安府的中西部和广西府的西部一带。据此可以看出,明代云南“汉族移民区主要分布于云南靠内的19府2州中的12府1州”,[15](P76)其驻军大体分布于“北部和中部,即保山、顺宁(今凤庆)、云州(今云县)以东,元江、建水以北,乌蒙东川以南的地区”,[18](P164)可推知在这些汉族移民屯田聚居靠内的府(州)区域里,通行的语言自然是汉语。其中,滇中的汉族分布密度最大,汉语也是最早在这一带产生影响并辐射开来的,当时五方杂处,汉族移民方言不一,形成共同的地域性官话方言成为客观需要,政府开办教育,习取文化礼教、追逐科举功名是为内动力,因此,滇中这一区域在明代最早出现学习官话的韵书,如嵩明人兰茂的《韵略易通》(1442年)、通海人葛中选《泰律篇》(1618年)等均出现在这一区域,云南官话即以滇中这一带为中心而混融形成,其成型后迅速向其他汉族聚居屯戍区辐射扩展,而最终成为云南区域性通用语言。明代,汉语在云南随移民主要分布于云南靠内的屯戍地区,当时“云南布政使司二分之一的面积上有汉族移民分布”,*明代靠内十九府是“云南、武定、寻甸、曲靖、临安、楚雄、姚安、大理、鹤庆、蒙化、景东、澄江、广南、广西、永宁、顺宁、丽江、镇沅、元江”,两州是“北胜州、兴化州”,当时汉族移民聚居于除后七府之外的其他十二府和北胜州。但这里所说的汉族聚居其实是相对的说法,因为靠近“三江”的边府(或外府)有些下辖有夷治的土司,如临安府的汉族就主要聚居于建水趋北至通海靠近滇中一带,其下所辖九个偏南和偏东的长官司仍是土司自治,故当时今蒙自以南和文山所辖地带仍是夷人聚居区域。故相应的这些区域的通用语言已不可能是当地某一夷语,而应该是融合形成的地域性云南官话。

(二)清代的边地移民与汉语的扩散分布格局
清代的汉族移民和汉语分布主要体现为向边地扩散的特点。明代汉语在云南主要分布于靠内的州府,它是朝廷有意识地移民分布屯戍而促成,至清代,后续移民入滇和云南内部人口的流动,主要是向边地迁移,汉语也因此而体现出“由内而外”的扩散式分布格局。
云南在有清一代并未发生波及全省的大战争,地方性局部叛乱也很快就被镇压,故明代已有的汉语核心分布格局并未受到影响,清代在此基础上通过镇压和深入推行“改土归流”等政策,使移民不断向夷蛮顽固边地推进,汉语的影响范围也在不断扩大。滇东南地区,广南府在顺治十八年(1661年)、开化府于康熙六年(1667年)、土富州于雍正八年(1730年)分别设置了流官,以致楚蜀黔粤等地的汉族移民涌入,“视瘴乡如乐土”,据道光年间的统计,当时这里半数左右的人口均属汉族移民,[22](P327)彻底改变了过去“不过蛮獠沙侬耳”的夷地民族的格局。滇南的元江和普洱两府,清初尚“俱系夷户”,元江府在清兵入滇时曾率夷部抗清,朝廷镇压后即于顺治十六年(1659年)废除元江土司而设置流官治理,随后宁州(今华宁)、习峨(今峨山)和蒙自于康熙四年(1665年)、阿迷州(今开远)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威远(今景谷)于雍正二年(1724年)、普洱于雍正七年(1729年)也“改土归流”成功,在云贵总督鄂尔泰的建议下,在“滇南的元江、镇沅、普洱、威远、茶山、车里等地,分汛防守”,[1](P112)故汉族移民也就随即迁入这些地方,百数十年之后,汉族已与夷人相当甚至超过夷人,以致原滇南夷地“风俗人情,居然中土”。根据清《普洱府志》记录的统计,普洱地区的汉族移民占全部人口的54%,超过土著夷户;清《元江府志》指出元江地区,江左、黔、川、楚、陕各省居民“家于斯焉,于是人口稠密,田地渐开,户习诗书”;清《威远厅志》说当时威远汉族移入较多,以致“夷人渐染华风,亦知诵读”。清代把明洪武时期分给四川管辖的滇东北东川、乌蒙、镇雄重新划归云南,在东川、乌蒙设府,芒部设州,废除沾益土司,设置流官,并在乌蒙派总兵镇守,为填实夷地、变易倮习,“迁徙云南、曲靖二府之民至昭填籍”《昭通县志稿》(卷六氏族),强化了中央对滇东北一带的实际统治。滇西地区,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剑川和鹤庆废土设流,丽江也在雍正元年(1723年)设置了流官,结束元代以来的木府土司统治,同时改设流官的还有姚安,后永平于雍正二年(1724年)、镇沅于雍正五年(1727年)也改设流官治理,随后于雍正七年(1729年)把澜沧江下游以东思茅等江内六版纳归流普洱府。至此,除澜沧江以西的江外六版纳仍归土司管理外,云南其他地方的改土归流已基本完成。清代的改土归流和“迁汉填实、以易夷习”同时进行,故汉语和汉文化在清代不断向边地扩散,影响较为深远。
清代的“改土归流”与明代不同,清代变明代的“屯田制”和“庄田制”为“私田制”,汉族大量移居边地,进一步改变了边地的民族结构,扩大了汉语的交际范围。明代是屯军镇戍,集团移驻,世袭首领在各地拥有大量庄田,土地为世袭首领和田庄主所有,汉民多依附首领土地,人固其地,不能随意迁徙。清代废除明代所遗屯戍田和庄田为私田,规定“凡过去耕种庄田的汉、白、彝族农奴,交出一定的地价之后,便获得土地的私有权,自身也就成了自由农民,直接对官府负担田赋和徭役”,[2](P171)明代以来落籍云南的汉族由此变为自由身。清代改土归流的同时,让“汉族移民随即迁入,他们也应在各营讯、哨卡从事农业生产”,[18](P169)鉴于历经明代屯田以来,坝区和交通要道已被汉族占据且人口膨胀,故清代汉族以自身的文化和技术优势大量向边地迁移,购置边地夷民土地而落籍。据《清宣宗实录》记载,乾隆二十年(1757年)至嘉庆元年(1796年),原边地各土司庄园土地“有典出十分之七八者,有典出十分之三四者,夷人无田可耕”,以致永北(今华坪)傈僳族提出“驱逐汉民地主,夺回夷人土地”的暴动反抗,汉族移入边地的人数和规模由此可见一斑。清代移民“随改土归流的进行,向云南东北、西北和南部的山区推进”,[18](P170)据统计,至清嘉庆、道光之际,移入云南开化、临安、元江、广南、普洱、景东、镇沅、丽江、昭通等边地的汉族人口总计约230万,丽江、普洱等多数边地移民人口超过土著,过去元代汉人住城市,明代主要住在坝区,至清代这些靠内的地区已难以容纳且人口膨胀,故清代则山险荒僻之处多有汉人居住,且边境莫不有汉人踪迹,至此,云南基本上整体汇入了汉文化的发展主流,汉语自然也就随着汉民族向边地的迁移而不断向边地扩散,汉语从此成为云南区域内的共同语。
清代的移民以内源式移民为主,外源式移民为辅,这保证了云南官话的延续性和一致性。据研究,清初绿营兵从外地募兵进入云南比较有限,连家属算在内不超15万,移入边地的外省流民共约45万,[18](P170)以黔、川、湖广、赣、浙等籍为主,如广西州(今泸西)接纳湖广和黔民,普洱府多四川人等,合计外籍移民占不到移民总人数22%,加之移入的黔川楚籍移民,其语言本就属西南官话,其他外省移民较少,故对明代业已形成的云南官话影响不大,即便有少量粤赣籍移民进入,也很快被云南官话所同化,如广南的杨柳树“客家话”,除称呼外语音已与云南官话趋同。云南在清代近80%的边地移民是滇域的内源式移民,因随明至清的发展,云南并未发生波及全省的大战争和严重天灾,故明代屯兵以来的坝区和交通沿线的人口饱和且膨胀,故随着清代改土归流的深入推行和对移民政策的放松,大批汉族便移入边地,如滇西的临沧地区在雍正年间就有楚雄、石屏人迁入,据《元江府志》(卷九)记载,滇西南的元江、普洱两府系收黔、安、建水、石屏、新兴及川、广流寓入籍,滇南地区的“汉族也多在清代中后期迁入”,[23](P46)移民主要来自石屏、通海、墨江、元阳等,滇东北昭通的移民主要来自曲靖和陆良等,甚至清廷设置的营讯、哨卡以及派镇各地的官兵也都基本是在云南就地招募。因此,清代的移民主要是内源式移民,少量的外省移民也多以西南官话和江淮官话籍为主,故云南官话在清代一直延续着明代的语源和特点,这在清代边地移民的背景下,从源头上保证了云南官话系统的历史延续性和稳定性。
(三)民国至今江外边地移民与汉语的推广普及
民国时期,云南军都督府为强化对边地的控制,在李根源等人的建议和推行下,对清代于滇西澜沧江以西的江外六版纳、怒江一带尚保留土司制度的地区进行“改土归流”,通过积极开办学校,构筑打通邮道,传播汉文化,为扩散汉语在边地的影响提供了空间。
20世纪中前期,国民政府采取强制激进和怀柔融合两种不同的差异性措施,对边地土司进行改土归流。怒江上游和独龙江地区时称怒俅,清末民初,高黎贡山西部发生英军入侵片马的事件,1912年李根源受命经营怒江,他随即把怒江分为知子罗、上帕、菖蒲桶三个殖边公署,并“以兵威迫令改土”,[24](P491)以致有“少量汉人因仕宦、戍守陆续进入怒江”,[23](P49)同时协调分化当地土司,争取民心,以致政局日渐稳定,针对怒江的设流用的是强制激进措施。澜沧江以西的怒江下游、德宏、西双版纳一带实施怀柔融合政策,即“不遽设县治,改行土流”,兴教育,抚土民,以达到“举内政而敷布之,不必改土司之名,而已举郡县之制”的效果。[24](P491)德宏边地和怒江中下游由李根源负责,西双版纳由柯树勋协调,他们在地方兴办学校,鼓励汉夷通婚,“无论汉民夷族,均需平等看待”,[25](P491)民国政府为强化沟通融合,“在车里、怒江等地修筑交通,沟通边疆与内地往来”,[26](P56)开通保山至怒江的邮路,在西双版纳的车里和倚邦等地增设邮局等,促进了民族融合和汉文化的传播。民国对云南边地的“改土归流”是明清“消除土司制度”政策的延续,并贯穿了整个民国时期,但因内存纷争外有侵略的国内外环境局限,民国时期的改土归流进行得并不彻底,为共同的利益,土流相依,以致“最终形成土流并治的局面”。[26](P57)民国改土归流的目的是稳定对边疆的统治,明清以来一直实行“迁汉填夷地”的政策暂居其次,故当时汉族移民边地的数量有限,也正因如此当局才鼓励边地汉夷通婚。民国改土归流的政策虽然执行得并不彻底,但其削弱了土司的影响力,“为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根除土司制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6](P58)特别是民国当局在边地开办学校,以优惠的政策吸引少数民族入校学习,组织夷民赴昆参观,开其眼界以渐进文明,设置邮政并开通邮路,以加强与内地的沟通联系等,民国政府的这些措施从客观上宣传了汉文化,无形中促进了汉语在边地的扩散与影响。
云南在1949年12月解放以后,汉语在云南边地因移民而扩散的因素降低,但通过入学教育以习取汉语的力度在增大,至今汉语的影响已遍布全省,成为滇域各民族交流的共通语言。云南解放以后,20世纪50至80年代,随着国家对户口的管理加强,“使内地汉族人口特别是汉族移民自发迁入边疆的活动处于停滞状态”,[23](P64)有限的移民主要是因应云南经济建设的需要,由政府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1953年初,林业部决定在云南红河、西双版纳、德宏等热带区域进行橡胶引种试验,先后接收转业军人、垦荒青年、下放的干部居民、湖南等内地支边移民近10万余人,由于移民和人口的自然增长,到20世纪80年代初,这些地区的人口有了较大增长。据1953年人口普查,德宏40.2万,西双版纳22.61万,红河州170万,到1982年人口倍增,德宏州74.99万,西双版纳64.64万,红河332.05万;[27](P118)民族构成上,“许多传统的民族自治地方,汉族的人口比例有了较大提高”,[23](P68)例如西双版纳的汉族人口在1952年仅1.7万人,仅占总人口的2.6%,1983年增加到19.17万人,已占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一。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因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实施,农民可以自由安排时间和行动,特别是身份证的使用,为人口的流动创造了条件,但因云南地处边疆,这一时期移民进入云南的汉族常住人口不多。大体上,云南自新中国成立至今,汉族移民边地的数量相对来说比较有限,但汉语在云南却基本上得到了普及,究其原因是国家在保障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的同时,提倡推广使用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使得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在云南相得益彰,彻底变过去历代的强制汉化为如今的少数民族主动习得,滇地各民族学习汉语以追求自身素质的提升已成为内在共识,以致在云南普及了汉语。
据以上分析可知,汉语自民国至今在云南的普及,移民显然已不是主要因素,教育的普及和少数民族主动习取汉语以提高知识文化水平才是其内在的主要动力。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在云南边地设置学堂,利用减免学费、免除户捐等系列优惠条件,吸引少数民族学生入学,期待通过学堂教育渐进式引导边地文化的变迁,但“由于多种因素限制,教育并未收到预期效果”。[26](P56)新中国成立以后,云南包括边地在内的民族聚居区,以民族自治州(县、乡镇)的形式纳入国家统一行政管理,并积极兴建学校,普及义务教育,根据国家政策,不断修订和完善符合云南地方实情的语言文字工作条例,在保障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本民族语言的同时,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在教育教学活动中应当以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为基本教学语言文字”。*云南根据国家政策,2004年通过《云南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条例》,2013年通过《云南省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条例》,从而使少数民族语和汉语相得益彰,让其各自得到应有的使用和发展空间。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政府组织各族人民历经超过半个世纪的努力,云南边地在教育方面基本普及了普通话,汉语方言也在普通话的教育普及中,以地缘渗透的形式扩散进入边地,故今云南边地各民族日常主要交流语言已是云南官话。
(四)明清以来云南官话的边地扩散与地域特色的凝练
明清以来,朝廷一改过去对云南以“羁縻”为主的政策,采取了更为积极主动的方式经营云南。普安连接湖广大道的开通和维护,使得汉族在明代以驻军为主的形式大批量进入云南屯垦,至明中后期汉族人口在云南已超过土著少数民族,汉语随移民被带入云南并成为主要的交流沟通工具,迁入的移民汉语方言在相互影响(甚至和少数民族语言也有接触融合)中,至迟于明中后期形成了较为通行的云南官话。因东西向普安大道的开通,云南在明代以来的移民原籍主要为湖广江南一带,故以南京话为代表的江淮官话对云南官话的影响最大,这已得到学界的证明和认可,因此,可以说云南官话是江淮官话方言在滇域的延伸演变类型。经明清至民国时期的改土归流,汉语在云南逐步向边地扩散,新中国成立以来,云南纳入统一的行政管理范畴,在实行民族平等和区域自治的政策下,认真开办学校,积极推行并普及教育,追求更好的生活成为人民的主动需求,故汉语基本普及到了云南边地区域。
值得一提的是,云南官话在清代进一步凸显了自身的特征,即其以能分中古泥母(n)和来母(l) 为特点,而显示了自身在西南官话中的特色。有意思的是,云南官话的这一特点并不是自身演变突显出来的,而是泥来母在清末民初,在同属西南官话的蜀黔鄂等地区演变而合流,以致其两分的特点在云南官话中被凸显出来。明代反映云南官话音系的《韵略易通》(1442年)中泥来母就是两分的,这一两分型的格局至今延续。明末郝敬《读书通》(1623年)反映的湖北京山话,其“泥来母不分,不论洪细全部混同”,[28](P10)清初美国传教士英格尔(J.A.Ingle)记录武汉话的《汉音集字》中泥来母也是不分的,属全混型;明末清初李实《蜀语》(1674年)记载当时的四川遂宁话“[-l]与[-n]为两类不同的声母”,[29](P29)但如“攮音朗”等少数例子表明这两个声母在四川话中已开始出现混同的端倪,据清末英国传教士钟秀芝(Adam Grainger)著的《西蜀方言》(1900年)和民初加拿大传教士启尔德(Omar L.Kilborn)著的《华西初级汉语教程》(1917年)记录的是成都音,二者均反映了清末民初的四川话“中古泥娘母和来母的洪音字已经没有区别”,[30](P56)细音仍读母,属半混型。据研究,“中古泥来母在西南官话中自西(如云南等)向东(如湖北等)呈现出由分到混的地理分配格局和演变态势,中部的四川、陕南等半混型属于过渡区域”,[31](P88)即四川主要为半混型,贵州和湖北主要为全混型(鄂地混为n,黔地混为l),云南官话则自明代伊始泥来母就是两分型。因此,自中古泥来母至迟到清末在四川、贵州演变合流以后,云南官话就以泥来母两分而在西南官话中别具一格,成为名副其实的云南地域性官话。
三、结语
汉语在云南的历史地理分布,大体可以宋元为界分为前后两段。宋元及之前是汉语和夷语的融合时期,汉语主要以融入夷语的方式而借助产生影响,地理上呈点状分布,语源上主要受川蜀汉语的影响;明清以来,因占绝对数量的汉族移民进入云南,汉语具有了独立发挥影响力的地位,随着朝廷对云南边地的重视,汉语和汉文化逐渐扩散至云南全境。
宋元及其之前汉语在滇域主要沿交通驿站呈现点状分布,其中滇东偏北一带(今昭通、曲靖地区)因地域毗邻川南僰道(今宜宾),连接彼此的五尺道(及其之后的朱提道)开通较早,受汉族移民及汉文化影响较深,故汉语在这一带于宋元之前具有一定的使用影响力,并沿“蜀身毒道”一线,汉语随少量汉族移民散布至以滇池、大理、保山为中心的驿道要塞,只因地域民族政权割据的关系,驿道常常被地方势力分而治之,少量点状分布的汉语,在这一时期并不能连线成片,故汉语尚不能依靠自身的影响而成为当地的通用语。但因地缘关系及滇夷对汉文化的推崇,汉语及汉文化在云南夷民及地方部落政权中均具有一定的影响力,汉语借此与夷语相融合,并以一种近乎汉夷“混合语”的形式一直维系着自身在云南的存在与影响,例如白语就是这种汉夷混合语的典型代表,汉语的词汇在白语中所占比例超过七成,很能显示这一时期汉语自身在特殊环境下的变通生存及其生命力和影响力的强大。元代之前,朝廷多以川蜀为据点治理云南,交通也多为连接蜀滇的北南向驿道,汉族移民及汉文化的影响多经川蜀而来,故宋元之前的云南汉语主要来源于古巴蜀汉语,如今白语中的汉语借词及川滇相连的部分方言点,仍可以看出当时古巴蜀汉语的残留影响。
明清及之后,朝廷对云南高度重视并采取“改土归流”等措施,主动积极经营并管理云南,汉族以军事移民屯戍的方式得以大量进入云南,明代移民主要沿交通要道及战略重地连线分布,汉族数量在明中期就已超越云南土著,汉语从此成为云南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的主要交流工具,并在相互影响与融合中形成了云南官话。清代至民国时期,汉语随汉族向云南三江之外的边地扩散,这一时期,云南官话在明中后期业已形成的西南官话大环境中,以中古泥来母两分为特点进一步彰显了自身的地域方言特色。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在尊重少数民族语言习惯及文化的基础上,积极开办学校,普及义务教育。学习语言文化以提升自身素质,成为地方少数民族的内在需求,汉语在云南基本得到了普及。明清以来,随着中央政治中心的转移和东西向普安连接湖广大道的开通,云南移民的来源,主要是以江南湖广一带为主体,故云南官话受当时以南京话为代表的江淮官话方言的影响较深,甚至可以说,云南官话是以江淮官话为主体的汉语方言,在西南滇域的延伸性地域演变方言类型。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云南汉语的历史地理分布具有时间上的不同步性和地理上的不平衡性。汉语早在战国时期就已进入云南,但在宋元及之前因汉族移民数量有限且分布较散,故汉语主要沿驿站重地呈点状分布,影响上以与夷语融合影响为主;明代以来,因汉族移民的数量较大且分布相对集中,因此汉语在云南以坝子和交通要道呈连线分布的格局,后进一步向“江外”边地扩散,以致分布全境。但值得注意的是,汉语在云南内部至今仍还存在不同程度的地域差异,如以蒙自为代表的滇南方言其上声为中平调,滇东南的富宁一带存在十个声调的蔗园汉话,滇西保山至腾冲一带声母分尖团音、施甸及相邻地区存在三声调方言现象,怒江地区的阳声韵尾弱化等等,这些语言现象也都是云南汉语分布不平衡性的体现,至于这些差异与土著夷语乃至具体语源方面的关系,还需要后续的进一步探索研究。
[参考文献]
[1]林超民.汉族移民与云南统一[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
[2] 马曜.云南简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3.
[3] 方国瑜.云南民族史讲义[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3.
[4] 葛剑雄,曹树基,吴松弟.简明中国移民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
[5] 木芹.云南志补注[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
[6] 徐琳、赵衍荪.白语简志[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4.
[7] 周祜.从白族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看汉白民族的融合[J].下关师专学报,1982,(1).
[8] 罗常培.语言与文化[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9] 郑张尚芳.白语是汉白语族的一支独立语言[A].中国语言学的新拓展[C].香港: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1999.
[10]《白族简史》编写组.白族简史[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
[11] 黄宗谷.洱海地区入声考[J].下关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1).
[12] 杨永福.中国西南边疆古代交通格局变迁研究[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14.
[13] 段红云.明代云南民族发展论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14] 云南省地方志编委会.云南省志(卷五十八)[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
[15] 陆韧.明代云南汉族移民定居区的分布与拓展[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6,(3).
[16] 陆韧.变迁与交融:明代汉族移民研究[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
[17] 杨永福.边疆民族史专题研究[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1.
[18] 曹树基.中国移民史(第六卷)[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
[19] 娄自昌,李君明.《开化府志》点校[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
[20] 杨磊.《广南府志》点校[M].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4.
[21] 徐霞客.徐霞客游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5.
[22] 林超民.方国瑜文集(第三集)[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3.
[23] 仓铭.云南边地移民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24] 张肇兴.云南辛亥革命资料(迤西篇)[Z].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1.
[25] 宋恩常.西双版纳历代设治的汉文献辑录[Z].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13.
[26] 马亚辉.民国时期云南改土归流述略[J].文山学院学报,2012,(2).
[27] 邹启宇.中国人口(云南分册)[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
[28] 忌浮.明末湖北京山方言音系[J].语言研究,2005,(4).
[29] 甄尚灵,张一舟.《蜀语》词语的记录方式与《蜀语》音注所反映的音类[J].方言,1992,(1).
[30] 范长喜,刘羽佳.《华西初级汉语教程》音系初探[J].方言,2016,(1).
[31] 牟成刚.西南官话中古泥来母的今读类型与演变层次 [J].文山学院学报,201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