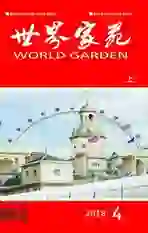《活着》中的叙述者与人物关系分析
2018-05-21赵启文
赵启文
摘 要:叙述者与人物的关系,总的来说就是叙述与被叙述的关系,不过有时叙述者可以充当故事中的人物,有时则不充当故事中的人物。在余华的小说《活着》中,叙述者与人物的关系属于叙述者充当故事中的人物这一种关系,这种关系使得余华的《活着》更加真实,并且叙述者所叙述的故事,带有了人物自己的情感。
关键词:《活着》;叙述者;人物;关系
一、《活着》中的叙述者与人物的关系
《活着》这部小说在叙述上很有特点,在小说开头,是以第一人称叙述者“我”展开叙述的,“我”是一个乡间采集民间歌谣的人,在乡间听到了老人福贵的吆喝声,于是认识了老人福贵,听老人讲述了他自己的故事。小说之后的内容则大部分都是福贵老人在讲述自己过去的故事,但是此时的叙述者依旧是用的第一人称的“我”,虽然这个“我”已经由采集歌谣的人转变为了老人福贵。
(一)《活着》中的叙述者
《活着》这部小说有两个叙述者,一个是叙述整个作品的故事的“我”,即乡间采诗人,另一个则是“我”所遇见的老人,老人福贵。“我”和福贵两人都是故事的讲述者,都讲述的是自己的故事,不过他们所在的层次不同。“我”所在的層次为外部层次,是包容整个作品的故事的层次,而老人福贵所在的层次则是内部层次,是故事中的故事那一层次,这一次层次包括由故事中的人物讲述的故事、回忆、梦等。相应的,“我”就成为了故事的外叙述者,而老人福贵则成为了故事的内叙述者。外叙述者在故事中可以居支配地位,也可以仅起框架作用,而《活着》中的外叙述者“我”,叙述的是自己在乡间遇到老人福贵的故事,不是作品的主要故事,作品中的主要故事则是由故事中人物,即老人福贵,所讲的故事支撑,外叙述者“我”所叙述的故事仅起框架作用,作为作品中主要故事的背景而存在于文本中。内叙述者在作品中往往具有交代和解说的功能,并且地位举足轻重,主要的故事都由内叙述者叙述。《活着》中的老人福贵就是故事的内叙述者,《活着》的主要故事由他来叙述,他讲述了自己的过去,并对自己的过去进行了评价和解说。
外叙述者与内叙述者由于处于同一作品之中,他们之间往往存在着一定的联系。①作为外叙述者的“我”与作为内叙述者的老人福贵之间存在着一种因果关系,正是因为“我”在乡间进行采集民间歌谣的工作才遇见了老人福贵,老人福贵才能够有机会叙述自己的故事。
《活着》开篇,外叙述者“我”在叙述的时候,他清楚的告诉人们,接下来内叙述者福贵所叙述的故事,只是一个故事:“这位老人后来和我一起坐在了那棵茂盛的树下,在那个充满阳光的下午,他向我讲述了自己。”②此处叙述者已经向人们提示,接下来福贵所叙述的故事,仅仅只是他所听到的一个故事。并且内叙述者福贵在讲述自己的故事的时候,并不是从开始到结束直接说完,而是出现了四次停顿,在这四次停顿中,外叙述者又继续展开叙述,叙述“那个充满阳光的下午”发生的事情。这几次停顿让故事又回到了第一层叙述,提醒着人们福贵的故事仅仅只是他自己叙述的故事,这使得人们在对待福贵的故事时,会更加理性。
(二)《活着》中的人物
小说《活着》中主要人物是福贵,即比现在年轻的福贵和年老的福贵,另一个人物是“我”,即比现在年轻大约十岁的我。他们不是人,但他类似于人,他作为虚构作品中的人物只生活在文本的语言世界之中。他们都是被叙述的对象,在被叙述的时候,他们为叙述者提供了视角。
在叙述的外部层次中,叙述者是“我”,而叙述者所叙述的故事中的人物则
是比现在年轻十岁的时候的自己。年轻的“我”为现在的“我”提供了视角,叙述者“我”根据年轻的我所看到的东西来叙述故事,并且对自己当时的某些事情做出评价。此时故事的视角聚焦在年轻的“我”的身上,他只能看到自己所看到的东西,并且只能感受到自己心里所感受的内心活动。
在叙述的内部层次中,叙述者是老人福贵,而叙述者所叙述的故事中的人物则是比现在年轻的福贵,此时故事的视角也是由人物提供,故事的聚焦仍旧是内聚焦。
(三)《活着》中叙述者与人物的关系
《活着》中的外叙述者“我”叙述的是与自己相关的故事,“我”即是故事的叙述者,也是故事中的人物。同样的,《活着》中的内叙述者老人福贵,他所叙述的也是与自己有关的故事,并且他自己也是故事中的人物。不同的是,他们都不是现在的自己,他们之间存在着时间的差异。
外叙述者“我”叙述的自己采集诗歌的故事,给整个故事提供了一个背景。外叙述者“我”叙述的故事中,年轻的“我”听到了老人福贵讲述自己的故事,这个时候,内叙述者本来可以换成是年轻的“我”以此来代替原本的内叙述者老人福贵,将叙述者与人物的关系换成第一种关系,即叙述者不作为人物出现在故事中,他所叙述的故事与自己不相关。如果将此处的叙述者与人物的关系转换,那么故事的内叙述者就变成了年轻的“我”,相应的,内叙述者年轻的“我”在叙述的时候,便不会采用第一人称进行叙述,他叙述的是别人的故事,他会采用第三人称进行叙述。而这样做之后,叙述者只是转述福贵的故事,我们听见的是内叙述者年轻的“我”的声音,我们从中并不能够看出福贵他本人的任何态度。如果以年轻的“我”去叙述福贵的故事,那么福贵的故事可以说是非常悲惨的,因为单凭故事本身来看,福贵的故事非常的不幸。但是在《活着》中,福贵却以一种非常轻松的,带有一丝骄傲的语气来叙述自己的故事,让人在他的叙述中感觉不到他的悲伤。因为福贵作为故事中的人物,他有着自己的视角,他经历过自己的人生,这人生中虽然有苦,但更多的是没有说出口的快乐,他不停的在失去,失去财富、失去家人,在别人眼中他是不幸的,可是在他自己眼中却未必如此。
首先,福贵在叙述自己故事的时候,他的视角是四十年前的视角,而叙述的声音则是四十年后的声音。被叙述的是年轻的福贵,他观察着整个故事,而叙述故事的则是四十年后的福贵。如果故事由年轻的福贵来叙述,那么整个故事可能会悲苦得多,因为他所感受到的痛苦是存在的、还没有消失的。而老年的福贵来叙述故事则会不同:福贵的不幸已经过去,这使得老年福贵在叙述的时候,他自身的感受比当时要淡很多,因此他的情绪也不会像不幸刚发生的时候那样悲痛。
此外,在《活着》中,老人福贵叙述自己的故事的时候,对苦难的叙述往往是简短的帶过,不着重叙述苦难。老人福贵在叙述自己身边的亲人死亡的时候,都比较简短,比如福贵的娘死的时候叙述者这么叙述“我离家两个月多一点,我娘就死了。”①将死亡简短的带过,不着重去表现死亡。对于福贵自己面对苦难时候的悲伤情绪也是简短的带过,不做过多的叙述,比如在福贵的儿子友庆死的时候,叙述者这样叙述:“我怎么想都想不通,这怎么也应该是两个人,我看看友庆,摸摸他的额肩膀,又真是我的儿子。我哭了又哭,都不知道友庆的体育老师也过来了。”②福贵对于友庆的死,他的反应先是哭了又哭,而他自己内心当时是怎样的悲苦并没有进行叙述。到故事的最后,福贵身边最后一个亲人苦根也死了,可是叙述者对于苦根的死依旧不做过多的叙述。
最后,叙述者在对这些不幸进行叙述的时候,他的语言是平静的,不带有悲情色彩。比如在叙述福贵的爹的死的时候,“老爷像是熟了”③;在叙述女儿凤霞死的时候,“凤霞生下孩子后大出血,天黑前断了气。我的一双儿女都是生孩子上死的,友庆死是别人生孩子,凤霞死在自己生孩子。”④;在叙述女婿二喜死的时候,“二喜是被两排水泥板夹死的。”⑤。叙述者在叙述这些死亡的时候,语言都非常平静,没有悲情色彩,只是陈述事件。
总的来说,《活着》中的叙述者与人物的关系,属于叙述者充当人物出现在故事中并且参与故事。用外叙述者叙述的叙述作为故事的第一层,介绍主要故事的发生背景,使得人们能理性对待福贵的故事。并且,叙述者以人物的视角来叙述故事,也使得叙述者的声音带有人物的情感色彩,老人福贵在讲述自己故事的时候,不显得那么悲苦。
参考文献
[1] 胡亚敏:《叙事学》,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第2版
[2] [荷]米克·巴尔:《叙事学:叙事理论导论》,谭君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1月第1版
[3] 陈慧娟:《论小说叙述者和叙述对象的五种关系》,《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3月
[4] [法]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王文融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11月第一版
[5] 余华:《活着》,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8月第3版
注:
①胡亚敏:《叙事学》,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第2版,第44页。
②余华:《活着》,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8月第3版,第6页。
③余华:《活着》,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8月第3版,第65页
④余华:《活着》,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8月第3版,第120页。
⑤余华:《活着》,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8月第3版,第30页
⑥余华:《活着》,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8月第3版,第162页
⑦余华:《活着》,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8月第3版,第171页
(作者单位: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 2015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