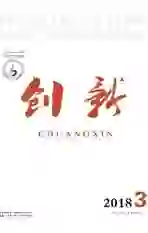世界观的历史形式和哲学发展的相应阶段
2018-05-14刘宗碧
刘宗碧
[摘 要] 哲学是世界观的理论体系。任何哲学研究,在根本上都要回到世界观的把握上来。历来,哲学研究是承认有不同世界观的,但是这种“承认”所包含的逻辑,一般只是在“本体论”上呈现出“物质”和“精神”的立场选择并归结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划分。这样的划分没有披露哲学历史形式的复杂性以及促进问题探讨向纵深层面的把握。关于哲学史,如果没有世界观的历史形式的梳理,那么哲学就不过是一种简单的平面化结构解析。基于世界观历史形式的观察,哲学经历了古代“自然哲学”和本体论的世界观,近代对“自然哲学”的批判和哲学世界观的变革,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变革和“生活世界”的新世界观重建。这三种形式的基本构筑和变革,使哲学的发展相应地呈现为三个基本的阶段和论域。
[关键词] 世界观的历史形式; 哲学发展的相应阶段; 马克思; 哲学变革
[中图分类号] B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616(2018)03-0038-11
哲学是世界观的理论体系。因此,任何哲学研究,在根本上都要回到世界观的把握上来。这样说,是指有什么样的世界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哲学。问题是会有不一样的世界观吗?何以影响哲学呢?笔者认为回答应是肯定的。
历来,哲学研究是承认有不同世界观的,但是这种“承认”所包含的逻辑,一般只是在“本体论”上呈现出“物质”和“精神”的立场选择并归结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划分。这样的划分不是没有意义,只是没有披露哲学历史形式的复杂性以及不能促进问题探讨向纵深层面的把握。因此,在哲学史的研究中,如果没有世界观的历史形式的梳理,那么哲学就不过是一种简单的平面化结构解析。基于此来观察西方哲学的发展,笔者认为从古到今,其在世界观的表达上经历了三种形式的基本构筑和变革,从而西方哲学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三个相应的基本阶段和论域,并认为把握这些世界观的变革及其发展的相应阶段和特征,是深入理解哲学理论尤其马克思变革近代哲学的关键。
一、古代“自然哲学”和本体论的世界观
西方哲学起源于古希腊,古希腊哲学是古代哲学的代表。因此,研究西方古代哲学,古希腊哲学具有代表性。然而,古希腊哲学的特点是什么?笔者认为就是其“自然哲学”的属性。这里的“自然”二字,已经暴露了古代希腊哲学在世界观上的历史形式,这个形式就是问题的设置和反思指向“世界本源”统一于“绝对自然整体”的确定性追问并形成相应的事物解释路线和逻辑立场。
古希腊哲学包括从泰勒斯到巴门尼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形而上学哲学。它们包括的全部问题可以归纳为“世界是什么”“它由什么构成的”问题。然后,每个哲学家都按照自己的立场来回答这一问题并根据回答来解释具体自然和社会生活现象,形成逻辑原则,构成哲学理论。
这里,先从泰勒斯来分析。泰勒斯是古希腊哲学的鼻祖,在公元前六世纪提出了“万物之源是水” [1 ]5的命题,这是哲学的开端,也是本体论的开端。泰勒斯的这个命题所包含的基本问题就是“世界是什么?” 和“世界由什么构成的?”而在“万物之源是水”的答案中,他的解答逻辑是:世间万物归结为“水”,“水”被理解为 “万物之源”。在泰勒斯提出“水”作为万物之源的“本原判断”时,就形成了作为基始的普遍的“水”与它自己演化出来的特殊的“万物”之间的关系。在“水”是万物之源这个命题中必然包含这样的问题,即“水如何演化为万物?”“万物又如何蕴含着‘水的性质?”从“水”到“万物”,就是从 “一”到“多”的过渡并内在地包含差异的对立关系;而“万物”归结为“水”来解释则又在逻辑上指认了“多”蕴含着“一”的统一关系。事实上,“水”与“万物”的划分设定了“本原”与“现象”之间包含“一”与“多”的关系。泰勒斯就本体论的“一”的设置构筑了本体论发端的世界观的基因,特点是追求事物统一于“自然”的确定性把握。之后的古希腊哲学都受之影响,“一”与“多”的逻辑设置在形式上没有改变,只是在“一”与“多”的关系的内容上出现了变化。
赫拉克利特提出世界本原为永不停息的“火”,事物的生灭源于“火的燃烧和熄灭”时,就“事物”与“火”的关系及其“转化”的理论设计中,实际上也包含了上述“一”与“多”的关系意涵,力图把“众多事物”的由来归结为“一”的自然本原理解。这也属于本体论的世界观。巴门尼德把“本原”设定为抽象的唯一不动的“存在”,“存在”寓于表现“存在”本身的各种现实现象之中时,这个不变的内质则被指为事物的真正“存在”本身。这里,作为“本原”的 “存在”,具有唯一性和确定性,无疑体现了追求“自然整体”的统一性规定及其世界观思维。接下来的柏拉图吸收了巴门尼德、芝诺等人的思想,建立了以“理念”为本原的哲学思想。这里,“理念”作为“本原”范畴,它不仅具有万物“源头”的含义,而且还有包罗万象的“全体”的含义,具有作为“一”包含着“多”的统一性,把“多”当作了是对“一”的“分有”。柏拉图的“一”的理念设计,实质是把万物归结为客观的“理念”的统一性设定的本体理解,逻辑上与传统一致。
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不同于柏拉图,其哲学出发点是“实体”。他反对抽象的理念,把认识的起点归结为具体的实体。关于实体,可以根据界定而形成为外延不同的范畴,而如何说明这些范畴及其关系则是“实体”哲学在认识论上需要解决的基础性问题。对此,亚里士多德提出了“种属关系”的范畴论和定义方法,把“种”归结为“属”进行解释的命题方式,从而制定了把“属”当作“种”的本质的揭示原则。“本质”即“本原”,对“本质”的确认就是关于事物本原的把握。亚里士多德的“种属关系”,实际上也包含着“一”与“多”的关系,也是其解决“一”与“多”关系问题的思路与方法。按照形式逻辑的原则,对“实体”的认识,就是它作为“种”范畴放到“属”范畴中来进行种差比较并由此规定内涵来完成,这里“属”范畴就被当作“种”的“一”并表达出“统一性”的功能,即归结为“属”的说明就是实现了把具体的实体(事物)还原为“本原”的把握。当然,亚里士多德的“属种关系”又因实体的多元性及其联系的多样性(如“四因说”),而不能自圆其说。为此,他又提出把“实体”划分为“可感实体”与“永恒实体”或“最初实体”与“日常实体”两类。“永恒实体”即“最初实体”,被解释为无体积、不可分、不改变、独立的“神”;而“可感实体”即“日常实体”,则被解释为就是自然界中的以一定質料为基础的各种个别事物 [2 ]。这里,他在“可感实体”和“日常实体”之外,提出“永恒实体”和“最初实体”,意图在于解决关于世界本原的“统一性”问题。因此,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仍然属于追求“自然统一性”的本体论世界观。
纵观古希腊哲学,其哲学形成了以下基本特征:一是在关于世界的认知上指向了绝对整体的自然统一性追问和把握;二是在绝对的自然界中,人被统一于自然界获得解释,人和自然界中的具体物质一样被当作其中的实体内容;三是哲学在关于世界的自然统一性追问中构筑了“本原”与“万物”的关系,并以因果关系设定了一切事物还原为“本原”把握和确立为认识上其获得确定性认知的原则;四是基于“本原”与“万物”的因果关系构造了认识上“本质”与“现象”的逻辑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主客观的同一性”的反思的证明论题,以此形成了哲学的基本理论范式。
诚然,“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才是哲学的真正问题,这种“人与世界的关系”包括人的自然关系和人的社会关系,哲学作为“智慧”的内涵就在于知道如何处理这种关系。在处理的过程中,在形式上又包含“认知域”和“实践域”的不同方面。“认知域”的“人与世界的关系”,在形式上反映的就是哲学之世界观。世界观的建构就意味着如何在思维形式上设置这种关系并形成哲学的理论模型。而就古希腊的哲学看,“自然统一性”的本体论追问和指认,蕴含了把“人”即主体归结为客体即“自然世界”来理解的,这里关于人的理解无疑是把它当作自然世界的一部分了。其世界观所包含的“智慧”——在“人与世界的关系”的协调上,则是让“人”去适应大自然,而不是让“大自然”来适应“人”或主体。这一点也充分地反映在古希腊人们的实际生活经验之中。如古代人们对自然界或自然物的崇拜并由此产生宗教,这是人们对自然界(神)绝对服从的表现,这种心态及其价值观与古代人们的世界观是同构的,即“人”归结于自然界获得理解的,这是古希腊自然哲学的特点。
古希腊自然哲学之后,西方哲学发展进入中世纪经院哲学阶段。这时,基督教的兴起,社会生活笼罩在神学之下,形成了一个“黑暗的时代”,哲学在神学的卵翼下生存,开展了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和唯名论与唯实论的长期论争,这似乎是一个“新的时代”。其实不然,奥古斯丁基于信仰提出的“灵魂的自我确然性” [3 ]作为所有经验的基础的论证,以及安瑟伦、阿奎那“上帝之存在的证明” [1 ]160-161,都不过是传统自然本体论哲学的延续和变种。而唯名论与唯实论的争论,缘于共相论题的讨论,这是关于“存在”规定的“一”与“多”的归结证明,唯名论认为事物都是个别和具体的,在心灵之外没有一般的对象,所谓共相不过是对个别事物抽象而存在于心灵中的概念。而唯实论则认为,共相既是心灵中的一般概念,也是心灵概念应对的外部实在,这种实在是与个别根本不同的更高级的存在。基于此,中世纪经院哲学在本质上仍在传统自然哲学之内,只是把人归结于自然界的解释的“本体”换为另一个“本体”即“上帝”而已,其所蕴含的方法论是一致的。
二、对“自然哲学”的批判和近代哲学的世界观变革
近代西方哲学对古代希腊哲学的批判,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对其“自然哲学”的世界观批判,从而带来了近代哲学的世界观变革,这种范式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康德以及后来延续这种批判的维特根斯坦。
近代哲学发端于“认识论转向”,即近代哲学属于认识论哲学,它包括了一个“主体论转向”的哲学萌芽。笛卡尔提出“我思故我在”的命题时,把哲学“确定性”的追问从“自然界”转到了“人的思维”上来了。“我思”就是“确定性”的基础。这个“主体论转向”在康德那里深化为所谓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并形成哲学世界观的近代变革,表达为“整体不可经验性” [4 ]和“不可知论”的世界观。
就康德的“主体论转向”的理解,需要从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说起。我们知道,在传统上康德属于理性主义学派人物,不过对他的理论产生重大影响的却是休谟这个经验主义学派的人物。休谟对传统怀疑地提出所谓知识所依赖的“因果关系”规律不是来源于事物对象本身,而是人的感觉联想及其习惯,继而就摧毁了传统的知识理论基础。就此,他有著名的例证,即“太阳照在石头上,石头变热了”的现象,过去理论证明是自然现象本身所包含的因果关系,即“太阳照”为因,“石头变热”为果,知识就是这种因果关系在头脑中形成了感觉印象,即客体的感觉经验构成了知识的来源。对此,休谟怀疑地提出,我们何以要用因果关系来解释认知现象,把因果关系当作知识的逻辑呢?过去人们有没有追问“因果关系”的逻辑从何而来?由此提出“因果关系”属于抽象概念,它不等于自然客体本身,但过去人们把它们相等了,予以相等在于人们经长期观察形成联想,是这种习惯性的联想构建了对象之间的“因果关系”,事实上,“因果关系”来于人类的主观性。由此得出,以往作为规律的“因果关系”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即非必然性,属偶然性。这样,经过休谟的怀疑论证,原有的知识论就失去了可靠的基础。
因果关系的理论包含了西方还原论的学理,是西方学术研究的基本范式。还原论就事物的认识指向本质把握,方法就是把结果当作现象还原为它的本质即原因。哲学上的本原理论也是如此,实际上,“本原”就是“本质”,“本质”就是“原因”。休谟的批判使“因果关系”被怀疑了,实际上是被消解了,这样必然发生传统理论知识系统的坍塌,显然对当时学界予以了挑战。康德哲学就是从回答休谟的问题和挑战开始的,他在十年的沉思中写出了《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批判力批判》的“三大批判”来进行回答。康德的回答提出:一切思维都是具有先验的一种必然结构,即宇宙本身就存在着一种客观的思维结构,这种思维结构作为理性的客观存在是知识本身所固有的,不属于人的主观范畴以及由人主观决定,当然这种客观的理性与自然界并列存在。
这样,他把知识的来源当作了理性的自我构造。其认识论把物质客体世界排除在外,并把它称之为“物自体”。另外,他认为人类因有“意识”,是知识的呈现者和运用者,通过人的呈现和运用使之变成一种现实的形态,同时也可以通过人的认识活动来揭示知识问题。在本质上,知识不过是依据于“理性结构”组织出来的“感觉的现象”一种体系。显然,这里康德给予了知识范畴的先验唯心主义解释,把人们关于知识(真理)的发现当作是回到“先验的知识结构”里。他指出人是负载意识的存在物,人类本身就具有“先验的知识结构”,以致人的认识不过是用这种“先验结构”去把握对象(感觉现象)而已。这就是所谓的“人为自然立法”,对自然客体的认识只不过是人以理性规范自然现象而建立起来的。这样,在康德这里,知识问题所蕴含的解释原则就是把以往“人的主观服从自然界”变成了“自然界服从人的主观” [4 ],改变过去以“自然”为中心为以“人”为中心。这种变换就是康德的所謂“哥白尼式的革命”。康德的这个“革命”具有重大意义,主要在于:客体归结于主体解释,哲学形成了新的坐标。显然,把“人归结到自然”转到“自然归结于人”的解释原则,意味着一种新世界观的确立和构成为德国哲学的传统,我们称之为“主体论转向”。
康德提出他的“主体论转向”后,认为知识来于主体——理性的自我构造,而非自然界的把握,自然界作为自在之物是不能认识的,认识仅仅是来于人对具体对象的直观表象的把握(直观形式如时间、空间)。这样,“物自体”是不能认识的,而“物自体”当作世界整体来指认时,具有对象整体的规定,表达为三种形式:一是主观上的最高统一体,即灵魂;二是客观上的最高统一体,即世界或宇宙;三是主客观的最高统一体,即上帝。这些无条件的对象是超验的,不能用知性范畴去认识的(不能界定并定义);知性范畴即实在性、实体性、因果关系、必然性等范畴,可以用于具体事物,但不能用于整体事物。如果要对“世界整体”进行知性认识,那么必然要站在“世界整体”之外,即关于世界整体认识的依据在世界之外。但人不在世界之外,因此,世界不可认识,视为“物自体”或“自在之物”,能认识的是现实有条件限制的“现象” [4 ]。总之,康德以“世界整体的不可经验性” [4 ]对古希腊的“自然哲学”的世界观进行了批判,基于此对哲学理解就必然出现“哲学是世界观的理论体系”不成立的结论。
后来的哲学家中,与康德类似的主要有维特根斯坦,他提出了“部分不能在整体之外”和“部分不能解释整体”以及“具体事物才可知”的世界观 [3 ],这是其哲学的延续。维特根斯坦是现代哲学家,后于马克思,这里把维特根斯坦放在近代哲学来讲,主要在于他的哲学思想在世界观的学理上沿袭了近代哲学传统,可视为康德世界观的延伸。
维特根斯坦哲学尤其是前期哲学属于逻辑实证主义传统。逻辑实证主义反对形而上学,把过去宏观的本体论或本质主义、基础主义所追求的确定性下降为微观事实的语言真值情况分析。这样一种“下降”包含着一种判断,即所谓的整体不可知。认为人类知识的客观基础不是“本体”世界,而是可直接认识的具体事物本身,因此,哲学不是去研究宏大叙事的问题,而是具体事物的主体判断方式。于是,哲学的逻辑构造由过去演绎的方式转变为归纳的方式。而具体的科学命题——作为真理,需要语言陈述出来。语言是真理表达的中介,与实在具有一一对应的关系。追求真理,其确定性可以通过分析语言与事实的对应关系揭示出来。他指出哲学的任务就是梳理語言命题是否符合事实,即确定判断是否“真值”,为确定“真理”判断找到“语言范式”,并企图构造人工语言,为科学命题奠定基础。
维特根斯坦把哲学所包含的确定性追求下降为微观事实的语言真值问题分析,其前提就是认为世界整体不可知。提出世界具有整体性的,总和由部分构成,而作为整体解释者永远处于部分之中(时空),无言面对整体世界。我们不能跳出这个世界来看这个世界,而当人一旦跳出这个世界来观察的这个世界又不是整体的世界了,整体世界是不能被我们言说的,只有不是整体世界时,世界作为具体之物才可被认识。即世界整体大于部分,人作为世界中的一部分只能认识具体事物,不能把握整体世界。维特根斯坦以“部分不能在整体之外”和“部分不能解释整体”对旧哲学的批判,能认知的仅仅是具体事物。因此,哲学关于认识上确定性的证明就走向了对具体客体命名和命题真值与否的判断和梳理的语言工作。
维特根斯坦放弃了整体的出发点,从归纳出发,研究具体事物中认识予以判断建立命题的真值可能性。分析哲学就是语言分析,即所谓语言论转向。在维特根斯坦这里,哲学也不能理解为“世界观的理论体系”了。
从康德到维特根斯坦的例子来看,关于“哲学”的理解,实际上不能说哲学是什么,只能说“哲学不是什么”,这是“世界作为绝对的自然统一性”批判引出来的结论。它使哲学从客体转向主体,从整体转向部分、具体。这完全不同于古代哲学,否定了形而上学。但是,没有了世界观的哲学还是哲学吗?下面来谈马克思的变革和世界观的重建。
三、马克思的变革和“生活世界”的新世界观重建
马克思哲学是包含世界观的,但不是古希腊自然哲学的那种世界观,也不是近代哲学把物质世界丢掉,或者只关注具体事物而放弃了整体的把握或说明。马克思有一个世界观,即“生活世界”的世界观。但是,这个立场来源于对德国古典哲学的扬弃。德国古典哲学从古代本体论世界观的批判和实现“主体论转向”对马克思具有重要意义。
学界就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传统表述为“吸收了黑格尔、费尔巴哈的合理内核”,这个“合理内核”指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费尔巴哈的唯物论和黑格尔的辩证法。因此,关于马克思对近代哲学的变革有一个基本判断,即实现了唯物论与辩证法的统一以及历史观与自然观的统一。以上两个变革的“统一”理论当然也是正确的,不过若仅仅局限于此则是不够的。笔者认为,马克思对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其关键还在于对德国古典哲学关于古代“自然哲学”的批判和“主体论转向”的扬弃。
“自然哲学”的批判和“主体论转向”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德国古典哲学关于“自然哲学”的批判,就是讲世界整体的不可经验性,否认的哲学作为世界观的理解。而什么是“主体论转向”?上面也已经论证了,就是康德的 “哥白尼式的革命”及其形成的传统,其实质是:客体归结于主体解释,即把过去“人归结于自然”转到“自然归结于人”来构筑事物理解之坐标。马克思扬弃地继承了德国哲学这个传统。这就是为什么早期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提出“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和“人是人的最高本质”之命题的缘故 [5 ]9。有的人批评为马克思接受费尔巴哈人本学的使然,其实不是,我们进一步分析后期著述就明白了。
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一节,马克思批判黑格尔道:“被抽象地理解的,自为的,被确定为与人分隔的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 [6 ]116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在康德那里,自然界被以“物自体”排除去了,而黑格尔提出“实体即主体”,把意识理解为实体的能动性并规定为主体和表现为主体的自我发展,并通过主体的“异化”及其克服的设定,自然界被理解为主体否定性发展的中介。这里,自然界被拿了进来,但是这个自然界是被抽象直观地理解的,并不理解为人类活动的本身,即人类活动不被理解为主体物质实践。这样,实际上自然界就是“被确定为与人分隔的”,因此,这个自然界“对人来说也是无”。这里,黑格尔讲到自然界了,但不把它理解为主体的规定导致存在缺陷。那么,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不是反对从“主体”来理解世界和建构哲学世界观的这个维度,而在于指出“主体”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意识”,否则“主体”就失去了客观的物质基础,从而陷入唯心主义。马克思说道:“如果没有人,那么人的本质表现也不可能是人的,因此思维也不能被看作是人的本质表现,即在社会、世界和自然界生活的有眼睛、耳朵等的人的和自然的主体的本质表现。” [6 ]116显然,马克思提出,“主体”首先是“自然的主体”的人,即具有物质规定的人。这是马克思立足“主体论转向”来重新规定“人”或“人的本质”,这里也包含了“主体论转向”的批判继承。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第一条就阐述道:“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因此,和唯物主义相反,能动的方面却被唯心主义抽象地发展了,当然唯心主义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 [5 ]54在这里,马克思论述的是哲学作为世界观的理论出发点,不是过去旧唯物主义的物质客体,提出是“感性的人的活动”,即“主体”及其实践。关于“主体”及其实践作为出发点,早期马克思对黑格尔、费尔巴哈的批判都在于完成这个规定。十分明显,这里马克思扬弃地承继了德国哲学的“主体论转向”。就“这种承继”的论证,马克思的著述延续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关于唯物史观历史前提,即“现实的个人”的阐述。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论述唯物史观的历史前提说道:“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 “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 “人们用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 [5 ]67“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 [5 ]68“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前一种方法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人。后一种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则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 [5 ]73这里,马克思关于“历史前提”就是指“现实的个人及其活动”。人的“活动”就是生产,即实践。当然,生产是社会性的,因此理解历史应从人的社会生产开始。这个关于历史前提的命题,实际包括了“主体论转向”扬弃及其世界观的设定。也就是说,马克思在扬弃“主体论转向”并用于“历史前提”的表述时包含了新世界观的构筑。这个世界观是什么呢?就是指向历史领域的“生活世界”的世界观。
关于马克思“生活世界”的世界观来源,它与“第二自然”的思想相关。对此,卢卡奇认为受到17世纪意大利哲学家维科的影响。维科在《新科学》中提出了第二自然的思想,认为世界在人的实践中划分为“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自在自然”是第一自然,第一自然在整体上人类是不能周全认识的,人类能够认识的仅仅是“人化自然”,即第二自然,第二自然即人类实践关涉的自然对象和范围。或许马克思受到维科的影响,但是笔者认为,马克思的人化自然思想直接与德国古典哲学的“主体论转向”有关,事实上是这一传统的新构制。我们知道,“主体论转向”的理论范式的学理核心在于以“人”为坐标,把自然界归结为“人”来理解,而不是相反。马克思坚持人的中心地位,由人去看自然界,在“人”的坐标上,被理解的自然界只能是“人化自然”。
就此,可以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进行例证。马克思在“手稿”中说道:“从主体方面来看……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就是说,它只能像我的本质力量作为一种主体能力自为地存在着那样才对我存在,因为任何一个对象对我的意义恰好都以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因为,不仅五官感觉,而且连所谓精神感觉、实践感觉(意志、爱等等),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 [6 ]87“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 [6 ]90显然,马克思明确指出,自然界作为主体的对象出现在于它因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才发生,否则不会构成为主体(人)的对象,这样,世界能真正构成为人的对象是人化自然,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因此,马克思关于世界观中的“世界”仅指“人化自然”,即第二自然。“人化自然”的哲学对象提出,使哲学的对象不再是古典哲学的纯粹“自然界”,也不是近代哲学所认为的世界“整体的不可经验性”的世界观论域。马克思的世界观仅仅指“生活世界”的世界观。“生活世界”的世界观的提出,是马克思变革近代哲学的重要方面,构成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内容,是对哲学产生了重大影響。
第一,在世界观的示度关系上形成了新坐标,提出认识对象的自然是人化自然并只能在人的历史活动中才被理解,哲学不能从自然界来理解人或人类社会,而应是从人或人类社会来理解转为客体发生的自然界。诚然,马克思承接了德国古典哲学的“主体论转向”,因此,客体归结于主体来解释,或“自然界归结于人”来解释。但是,这种“归结”中的“人”或“主体”的理解,马克思与德国古典哲学有了完全不同的主张,即主体不再是“意识主体”或“自然的人”,而是“实践主体”。正因如此,马克思哲学中人的出发点就变成了现实的“感性的人的活动”。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对象、现实、感性”,应“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 [5 ]54“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 [5 ]55“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解释。” [5 ]77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费尔巴哈比‘纯粹的唯物主义者有很大的优点,他承认人也是‘感性对象。但是,他把人只看作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他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 “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或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 [5 ]75。必须“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 [5 ]92。这些言论都是其观点的证明。
以上的立论表达了马克思对近代哲学变革的突破。过去,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发点,强调了物质论,以世界统一于物质性视为基本立场。笔者认为,局限于此的解释纯属误解。马克思是坚持物质观的,但是马克思没有停留于此,而是把物质范畴提升为实践范畴,同时又根据实践的历史展开而拓展为历史范畴,最终把世界观确立为历史观。实质上,马克思是从人类实践的历史活动来理解世界,这才是马克思哲学的出发点及其高度。
第二,从实体论到关系论,形成了以实践为基础的“主客体关系”来解释认识论上的“主客观关系”的路线,真正解决了“真理”的来源依据和检验标准。在前文中已有论述,哲学的真正问题不是离开了人的世界问题,是“人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即哲学的对象是“人与世界的关系”,它探讨的是人如何协调自己与世界的关系,这个关系在内容上包括人的自然关系和人的社会关系;在形式上包括活动过程的“认识关系”和“实践关系”。这里,人的自然关系指人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人的社会关系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尤其是劳动互换;而活动上的“认识关系”是指人通过意识形成的对人与世界及其关系的观念把握,“实践关系”是指人对客观世界和人自身的改造、加工、利用与发展。哲学作为世界观的构筑,就是通过实践把握“人与世界的关系”并上升为观念的原则表达和用于指导生活。马克思哲学是第一次真正直接地指向了哲学作为世界观的这个内容。但是,过去传统哲学尤其古代哲学不是这样的,因为他们把哲学的对象规定为宇宙的世界,其反思中所提出的问题是“世界什么?”和“世界由什么构成的?”,而不是“人与世界的关系如何?”。由此而回答就把哲学的对象指向“自然世界”,并在其“统一性”的追问中形成了“本体论”和以此对宇宙万物解释的路线。“本体论”使哲学引向了形而上学,它的局限性或错误被近代哲学揭开出来,但没有解决。事实上,哲学的对象不是实体的自然界,实体的自然界属于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哲学的对象是人的活动,即人的实践关系,也就是人与世界的关系。
马克思正是以此超越了以往的哲学。马克思哲学以实践作为哲学出发点是以“关系”为内涵的。就此,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讲“语言是实践的”论断时,有一段关于“关系”的论述说出了这个意涵。他说:“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 [5 ]81这里讲的“关系”即实践关系,因为人才通过实践改变对象时也改变人自身,使人自己变成了自己活动的对象,使人类从自然界分化出来并形成人类社会;而动物没有实践,其活动仅仅是本能适应环境,因此它们永远只能是自然界的一部分。马克思从“现实的个人及其活动”作为历史前提引申到实践关系的论述,在于强调哲学不仅要指向“人”,而且要把“人”理解为“实践关系”的存在。正是这样,马克思“在现实上”,才把人的本质规定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5 ]66,而人的发展就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全面性。显然,马克思的哲学出发点是关系论,而不再是实体论。当然,马克思的这个超越包括了对黑格尔的扬弃,因为黑格尔关于意识的发展设定为意识的外化、异化以及对这个外化、异化的扬弃的回归的辩证发展关系。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扬弃在于把他以“意识”作为内容的历史发展还原为人的实践发展,同时在这个基础上来解释意识的发展。
关于这个原则,马克思不是简单地进行了“存在”与“思维”的关系论证,而是归结为人的“实践”存在并构成了双层关系:一是主体的物质活动与客观世界之间构成的主客体关系;二是主体的意识活动与主体物质实践之间构成的主客观关系。主客观关系应归结为主客体关系获得解释,即从物质实践来解释观念的形成。因此,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反射和反响的发展……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 [5 ]73
哲学是世界观。因此,关于人与世界关系的把握会上升为意识的理性形态,表达为一定的观念形式。而哲学作为方法论的智慧之学,作为真理确定性的依据追问,在理论范式上就是“主客观同一”的证明,即恩格斯说的“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但传统哲学就同一性的证明,直观地进行“思维”与“存在”的论证,只有马克思在实践论的基础上把主客观关系归结为主客体关系的解释,使意识内在于实践,使“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在主客体的辩证法关系上得到说明。这就是马克思关于认识来于实践和服务于实践,以及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辩证发展的规律,由此克服了近代哲学的不可知論和重构世界观。
总之,马克思在扬弃德国古典哲学“主体论转向”的基础上,转入实践论的论证,使近代哲学真正发生了变革,把世界观转为实践意义上的人的劳动生成及其发展规律的历史把握,使哲学的“爱智慧”内涵真正得到体现。“生活世界”的世界观表达了哲学发展的新阶段和先进性。走向“生活世界”的世界观才是哲学的出路。德国当代哲学大师胡塞尔在其现象学的论证中把“科学世界”与“生活世界”关联起来了,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也同样如此。现象学的胡塞尔和存在主义的海德格尔,他们的哲学都有了“生活世界”为内容的转向,这是马克思哲学影响的延续。
至于尼采和德里达等这些后现代主义人物,他们作为现代主义的反对者,思想核心在于反对形而上学,但是他们的批判与康德、黑格尔的普遍性逻辑重建(批判)不同,基于追求特殊性的立场,以摧毁基础主义、中心主义、逻辑主义,摒弃一元论、中心论、确定性,倡导多元论、边缘化、模糊性,提出“怎么都行”的理论主张,反映了对传统进行解构的理论旨趣,属非建构性。实际上,也属于没有世界观的哲学,仅仅是一种方法论和立场的批判。如尼采,他是后现代主义思想的源头,反对传统形而上学,高呼“上帝死了”,并以虚幻的超人取而代之并推崇权力意志论,并宣称要“重估一切价值”;同时,赞赏有创意的文学、艺术创作,反对追求逻辑的科学。他的思想属于欧洲哲学的大陆学派,呈现了人文主义的反形而上学之路,不同于分析哲学的科学主义。而德里达作为解构主义大师,以文本诠释为机理,通过强调文本在阅读中的异延和播撒的意义生成与多元化,宣称:“当完成写作时,作者就应当死去,以免堵塞文本之路。” [7 ]把文本理解为主体化了的“自我运动”,以这种多元化和非确定性来解构现代性,推进对形而上学的反动等。
总之,尼采和德里达等后现代主义理论只是一种诠释文本的批判逻辑手段,没有真正面对历史现实本身,因而并未在世界观上掀起革命性变革。这是后马克思欧洲大陆人本主义哲学的状况,限于篇幅,不再过多论述。
参考文献:
[1] G·希爾贝克,N·希耶.西方哲学史——从古希腊到二十世纪[M].童世骏,郁振华,刘进,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2]张志平.西方哲学十二讲[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66-68.
[3]倪梁康.自识与反思——近现代西方哲学的基本问题[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36.
[4]俞吾金.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吗[J].哲学研究,2013(8).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中共中央编译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7]U·艾柯.玫瑰的名字的附言[M].美国:奥兰多,1983:7.
[责任编辑:丁浩芮]
Abstract: Philosophy is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world view. Any research on philosophy should fundamentally come back to the world view. Since then, philosophical research acknowledges different world views, yet this "acknowledgement" entailing logic presents the stance choice of "material" and "spiri" on "ontology" and ends up with the division of materialism and idealism. Yet this division does not reveal the complexity of historical form of philosophy. As far as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it would be nothing but a simple and planar structural explanation without organizing the historical form of world view. In terms of historical form of world view, philosophy has experienced three stages, namely, world view of ancient "natural philosophy" and ontology, criticism of "natural philosophy" and revolution of philosophical world view, and the revolution of Marx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rebuilding of new world view on "life world". The basic formation and revolution of these three forms makes the development of philosophy present three corresponding stages and fields.
Key words: Historical Form of World View; Corresponding Stage of Philosophical Development; Marx; Philosophical Revolu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