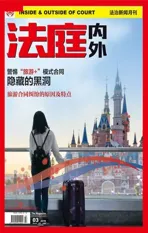入伙需谨慎退伙莫大意
2018-05-07袁楠
袁楠
律师退伙多年后接到法院传票
葛某曾为某律所的合伙人,2012年就已申请退出了律所。2017年的一天,葛某突然接到法院的传票,告知其被某公司申请追加为一起执行案件的被执行人。葛某匆忙赶往法院,得知其原来所在的律所与某公司因房屋租赁产生了纠纷,法院最终判决某律所支付某公司房屋租金、滞纳金、垫付物业费、电费、车位费等费用共计44万余元。某律所没能按判决内容履行判决义务,某公司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法院立案执行后,查明某律所名下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某公司于是向法院提出了追加被执行人的申请,要求追加葛某及律所的另两名合伙人程某、刘某为案件的被执行人。某公司认为,被执行人是普通合伙企业,现在没有财产可供执行,程某、刘某、葛某作为合伙人,应当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所欠债务应当由合伙人来清偿。
合伙人均不同意被追加说辞不一
葛某认为,自己早已经退伙,入伙时虽然约定以劳务出资1%比例,但实际上根本没有出资,不应当追加为被执行人。况且某律所并没有被注销,主体仍然存在,可以承担债务。退一步来说,即使要追加被执行人,也应当追加律所现在的实际出资人和管理人侯某。
合伙人程某认为,某律所的出资人和实际管理人是侯某,应由侯某承担债务,而且律所财产没有彻底清算,不同意追加为被执行人。
合伙人刘某认为,自己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合伙人,当年是因为葛某要退伙,律所缺少一名合伙人,所以才被律所安排入的伙,但都是由律所一手操控,自己对入伙的事压根不知道,入伙协议上的签字不是自己签的,完全被蒙在鼓里,不同意追加为被执行人。
法院查明事情真相
在案件审查过程中,法院查清楚了以下事实。被执行人某律所是北京市司法局于2008年批准成立的合伙企业。成立时,律所的合伙人有3名,分别是程某、李某和胡某。2011年4月30日,某律所召开了合伙人会议,并做出了会议决议,决定增加该律所的律师葛某为合伙人。同时约定葛某以劳务方式出资,占全体合伙人出资总额的1%;发生合伙债务时先由合伙财产进行清偿,合伙财产不足以清偿的,以合伙人的出资比例承担。2011年7月15日,某律所再次召开合伙人会议,并做出会议决议,决定增加刘某入伙。双方约定,刘某出资占全体合伙人出资总额的30%;发生合伙债务时先由合伙财产进行清偿,合伙财产不足以清偿的,以各合伙人的出资比例承担。2012年2月20日,某律所召开合伙人会议,同意葛某退出律所。本案债务发生时间在2011年5月1日至2012年7月30日之间。
历经二审法院做出最终裁决
执行法院审查后认为:某律所为普通合伙组织,程某、刘某作为该所合伙人,在某律所没有能力履行生效判决所确定债务情况下,可以追加为被执行人。某律所对某公司所负的债务是在葛某入伙期间发生的,葛某作为当时的合伙人,应当对该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刘某虽然主张对入伙不知情,但北京市司法局对外公示的档案材料中已经明确了其合伙人地位,因此该主张不能对抗他人。2016年3月15日,执行法院做出了一审裁定,追加程某、葛某、刘某为案件的被执行人,以判决确定的某律所应承担而未履行的债务为限,对某公司承担清偿责任。一审裁定做出后,某律所、程某、葛某、刘某都表示不服,向上一级法院提起了复议。2016年8月22日,二审法院做出最终裁决,裁定驳回复议人的复议申请。
法官说法追加律所合伙人的法律依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77条规定,“被执行人为个人合伙组织或合伙型联营企业,无能力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可以裁定追加该合伙组织的合伙人或参加该联营企业的法人为被执行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4条规定,“作为被执行人的合伙企业,不能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普通合伙人为被执行人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作为被执行人的有限合伙企业,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未按期足额缴纳出资的有限合伙人为被执行人,在未足额缴纳出资的范围内承担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据此,作为被执行人的个人合伙组织、合伙型联营企业或合伙企业,在符合法定情形时,可以追加其合伙人为被执行人。个人合伙是指两个以上公民按照协议,各自提供资金、实物、技术等,合伙经营、共同劳动;合伙型联营企业是指,参与联营各方,在经核准或协商的生产经营范围内,按照合同约定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并以各自投入的财产承担连带责任的合伙型组织;合伙企业是指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依照《合伙企业法》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普通合伙企业和有限合伙企业。本案中,某律所的组织形式为“普通合伙”,不能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可以追加其合伙人为被执行人。

退伙人葛某对其在入伙期间的债务仍应承担责任
《合伙企业法》第53条规定,“退伙人对基于其退伙前的原因发生的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据此,葛某虽然已经退伙,但本案执行依据所涉债务系在葛某入伙期间发生,应当对该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葛某与刘某未实际出资仍应承担责任
根据《民法通则》第35条“合伙的债务,由合伙人按照出资比例或者协议的约定,以各自的财产承担清偿责任。合伙人对合伙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偿还合伙债务超过自己应当承担数额的合伙人,有权向其他合伙人追偿”、《合伙企业法》第2条第2款“普通合伙企业由普通合伙人组成,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第40条“合伙人由于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清偿数额超过本法第33条第1款规定的其亏损分担比例的,有权向其他合伙人追偿”的规定,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是否实际出资、出资比例多少等情况只是区分内部责任,对外均需承担连带责任。因此,即使葛某与刘某未实际出资,仍应对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合伙人刘某主张入伙不知情是否仍应承担责任
《律师事务所登记管理办法》第4条规定,“律师事务所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以上司法行政机关审核登记后设立。”《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第18条规定,“律师事务所的设立许可,由设区的市级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受理设立申请并进行初审,报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进行审核,做出是否准予设立的决定。”据此,律师事务所的设立审核机关是司法行政机关,即所在地的司法局。虽然刘某主张对入伙不知情,不认为是法律意义上的合伙人,但北京市司法局对外公示的资料中明确了其合伙人地位,具有对外公示效力,其抗辩不能对抗第三人,仍应对律所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