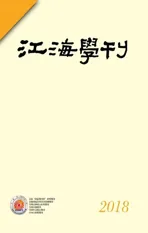清末礼法之争的焦点再探*
2018-04-14彭凤莲
彭凤莲
内容提要 在晚清十年法律改革中,《大清新刑律草案》引起了空前激烈的礼法之争。学界通说认为,义关伦常的罪名是清末礼法之争的焦点。而从清末礼法之争的场域与载体看,比附援引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废立之争异常激烈。从能较全面揭示清末礼法之争的史料《刑律草案笺注》与《修正刑律案语》来看,其争论的激烈程度和争论内容本身的地位与作用都不亚于对于义关伦常的具体罪名的争论。因此,比附制度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废立是清末礼法之争的另一焦点,与义关伦常具体罪名的争论相较,更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清末礼法之争对今天认识和落实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原则有启发意义。
清末礼法之争是个历久弥新的话题,2015年4月17日在北京大学法学院举行的“文化沙龙·中国的法律与社会变迁暨《法辨》《清代习惯法》《礼教与法律》发布会”上,梁治平与周濂就此进行了热烈的“商榷”与“回应”。①清末礼法之争主要围绕《大清新刑律草案》展开,关于争论的焦点似有定论,即义关伦常之罪名。本文试图勾勒清末礼法之争中关于比附与罪刑法定废立之争的概貌,对争论焦点之通说酌做修正。而且,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细细品味这段历史,对贯彻落实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原则不无启发意义。
归纳清末礼法之争焦点范围之确定
自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清廷统治不断陷入危机。迫于内外交困的局势,为稳定统治,清廷于1901年下诏变法。1902年,清廷颁示谕旨着派沈家本、伍廷芳从有俾治理出发,将一切现行律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1904年,修订法律馆开馆,修法工作步伐加快。由沈家本主持修订的《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于1906年告成,其第76条规定:“凡裁判均须遵照定律,若律无正条,不论何项行为,不得判为有罪。”这从程序法上规定了罪刑法定原则,与同年开始起草的新刑律从实体法上确立罪刑法定原则相呼应。但该诉讼法草案交发各大臣讨论时,遭各督抚激烈反对,遂被搁置。其后的注意力便集中在新刑律上。1906年开始起草新刑律,1907年沈家本上奏《大清新刑律草案》,草案采用西方刑法体例,分总则、分则,共57章387条。其第10条规定,“凡律例无正条者不论何种行为不得为罪”。1907年8月和12月,《大清新刑律草案》及其案语由修订法律馆上奏,皇帝下谕着各将军、督抚、都统等文武官员签注。该草案因引进罪刑法定、删除义关伦常罪条而引起了空前激烈的“世纪礼法之争”。集中记录礼教派与法理派关于新刑律争论意见与主张的是《刑律草案笺注》与《修正刑律案语》,两书详细记载了对《大清新刑律草案》第10条罪刑法定原则的签注与辩驳。根据“修订法律办法”,“签注”是制定《大清新刑律》的必经程序——修订法律馆上奏《大清新刑律草案》后,朝廷命宪政编查馆交各中央部院堂官、地方各省督抚、将军都统签注意见。②从1908年到1910年,京内外各衙门陆续上奏对《大清新刑律草案》的意见,这些意见被称为“签注”。对于上奏的“签注”,朝廷先后在十多份奏折上做了硃批,足见朝廷对“签注”的重视。1910年2月修订法律馆会同法部上奏《修正刑律草案》后,将“修正刑律案语”排印成书,定书名为《修正刑律案语》,其内容是对签注的逐条逐项反馈意见:“于草案中详列中外各衙门签注,持平抉择以定从违。并于有关伦纪各条,恪遵谕旨加重一等。”③随后宪政编查馆也将签注意见进行整理,成《刑律草案笺注》一书,以备审核草案时参考。因此《刑律草案笺注》与《修正刑律案语》能较全面揭示清末礼法之争的内容,是研究清末礼法之争的重要文献。
一般认为,清末礼法之争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其一,以沈家本和张之洞为代表,对《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和《大清新刑律草案》进行争论,都涉及比附援引与罪刑法定之存废;其二,以沈家本和劳乃宣为代表,对《大清新刑律草案》及《附则》展开争论,主要集中在旧律礼教条文要不要入律,是入正文还是附则,其中对犯奸和子孙违犯教令的争论最烈;其三,以杨度和劳乃宣为代表,在资政院关于《大清新刑律草案》立法宗旨是国家主义还是家族主义展开激辩,其间亦涉及无夫奸和尊亲属有犯是否适用正当防卫的争论。④“该法自光绪三十三年提出草案,至宣统二年十二月颁布,迭经修改,其间的纷扰攘争,牵动朝野,激动人心。清末著名的礼法之争,便主要围绕这部法律展开。”⑤
综观已有研究成果,对清末礼法之争的焦点看法不一。这主要是由于归纳焦点的范围不同所致。这场世纪之争涉及法律文化、立法宗旨、指导思想、法律原则、法律条文等多个领域,是从所涉全部领域中归纳争议焦点还是从某个方面归纳争议焦点?归纳的范围不同,得出的焦点自然会有差别。比如,自法律文化言之,归纳出的焦点可能是传统礼教与法律的分合问题。是从涉及的诸多领域中归纳还是从涉及的某个领域中归纳,这两种路径只要交代清楚就都可以,只是已有研究在归纳焦点时基本上不作这种前提厘定,所以导致各说各的范围,各提各的焦点。本文以《大清新刑律草案》《刑律草案笺注》与《修正刑律案语》为主要载体,以其增删修订条文本身而不是条文背后的文化规范为寻找争议焦点的依据,并借助清末礼法之争的重要场域——修订法律馆、宪政编查馆、资政院,试图还原历史,从规范主义立场再探清末礼法之争的焦点,为深入研究清末法制变革提供一个观测点。
清末礼法之争焦点之学说
(一)礼法之争焦点通说之奠定
学界通说认为,清末礼法之争的焦点集中在义关伦常的具体罪名上。这与礼教派、法治派强烈交锋后,于1911年公布的《大清新刑律》增加了草案中原本没有的《暂行章程》(原称《附则》)五条直接相关。此五条内容皆是义关伦常行为的罪与罚:第1条,侵犯皇室罪、内乱罪、外患罪、杀害伤害尊亲属罪,处死刑的,仍用斩刑;第2条,损坏、遗弃、盗取尸体者,损坏、遗弃、盗取尊亲属尸体及遗骨、遗发及殓物者,发掘尊亲属坟墓者,发掘尊亲属坟墓而损坏、遗弃、盗取其尸体者,应处二等以上徒刑者,得因其情节仍处死刑;第3条,犯强盗罪得因其情节仍处死刑;第4条,无夫奸之罪与罚;第5条,“对尊亲属有犯,不得适用正当防卫之例”。1936年,杨鸿烈先生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中将以劳乃宣、张之洞为代表的一派称为礼教派,将以沈家本、杨度为代表的一派称为法治派,并对“两派冲突的要点”进行了梳理与阐释:第一,礼教派认为,刑法草案中“内乱罪无纯一死刑”及“无夫奸之无罪”有妨礼教(张之洞);“干名犯义”“犯罪存留养亲”“亲属相奸”“亲属相盗”“亲属相殴”“故杀子孙”“杀有服卑幼”“妻殴夫”“夫殴妻”“无夫奸”“子孙违犯教令”等款,《大清律》皆有特别规定,而《大清新刑律草案》则一笔抹杀,大失明刑弼教之意(劳乃宣)。第二,法治派领袖人物沈家本著《书劳提学新刑律草案说帖后》,对劳乃宣之说一一痛驳。⑥经此,礼法之争的焦点在于义关伦常的罪名之通说基本奠定。在当时他们并不自称或彼此称礼教派、法治派或法理派,而是称为新派与旧派。这从身为资政院法典股《新刑律》审查长的汪荣宝的日记中可以找到记录:“宪政馆同人对于刑律草案分新旧两派,各持一说,争议不已。”⑦
在杨鸿烈《中国法律思想史》出版后,相关教材或论著中关于清末礼法之争的焦点之说大致与之相同。张晋藩教授指出,礼法之争“虽然涉及传统刑法的许多方面,但焦点是新修订的刑律,是否应继续纳入封建礼教的内容”⑧。其将“焦点”概括为“是否应继续纳入封建礼教的内容”,这在杨鸿烈总结的“两派冲突的要点”基础上作了进一步的归纳,实际观点并无不同。史广全博士明确使用“法理派与礼教派争论的焦点”一语,并把“焦点”概括为五个方面:“干名犯义”条的存废、“存留养亲”制度、“无夫奸”及“亲属相奸”、“子孙违犯教令”、子孙卑幼能否对尊长行使正当防卫权。⑨一些年轻学者也基本接受这一观点,认为礼法之争主要是关于中国旧有纲常名教的法律条款⑩,“法理派和礼教派争论的焦点就是传统礼教与法律的分与合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以来,法律史教材中对清末修律焦点的概括都是“无夫奸”与“子孙违犯教令”。梁治平说:“它们之所以牵动人心如此,并非是因为其本身是刑法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内容,而是因为它们所出自的两个范畴,男女和长幼,在传统道德、法律和政治上均有着特殊的重要性,以致针对这些条款的任何修改,都可能触动和改变传统中国的某些核心价值。”这一解释一语中的,揭示了两个重要层面的问题:一是无夫奸、子孙违犯教令不是刑法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内容;二是删除无夫奸、子孙违犯教令严重冲击了男尊女卑、长幼有序的核心价值观。可见,就律典条文内容来说,目前关于清末礼法之争的焦点是封建礼教内容的观点占支配地位,亦即通说。
(二)礼法之争焦点新说之迭起
杨鸿烈是从刑法草案条文出发界定礼法之争的,后世随着研究的深入,把礼法之争放到一个更宏阔的范围中探讨,认为清末礼法之争实质上是清末整个修律的指导思想的一次大争论,争论的过程与内容体现了近代中国如何引进西方法律思想以及中国法律如何由传统向近现代转化演变的轨迹。双方争论的核心是:鉴于当时的国情,应以新的西方法律原理原则还是以中国传统的伦常礼教为指导思想制定新法。“礼法之争的过程中,最大的争论焦点其实就是如何看待和处理西方新法和中国传统法关系问题。”
李贵连教授三十年前将清末礼法之争的核心归纳为三个方面:一是鉴于当时中国的国情,制定新法的主要指导思想是资产阶级法律的原理原则还是封建礼教;二是新法的精神应该是国家主义还是家族主义;三是《大清律例》中维护传统礼教的法律条文如“干名犯义”“犯罪存留养亲”“亲属相奸”“故杀子孙”“杀有服卑幼”“妻殴夫夫殴妻”“犯奸”“子孙违犯教令”等,要不要全部列入新刑律,要列入的又如何列入。在他看来,关于义关伦常罪名之争并不是清末礼法之争的全部核心,而只是核心之一,且将指导思想列为三个核心之首。因此可以推见,他对清末礼法之争焦点之通说并不完全赞同。但如果就条文来归纳焦点,其观点与杨鸿烈又并没有什么不同。
张德美博士指出,礼法之争的焦点“并非是与封建法律截然对立的近代西方刑法原则,而不过是所谓义关伦常的几个罪名的存废问题。究其原因,或许是因为体现近现代西方刑法原则的法律条文,总是能够在传统文化中追本溯源。也许正是因为诸如罪刑法定、罪刑相适应、人道主义等刑法原则都能从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寻根,它们才可以在《大清新刑律草案》引起激烈争论之际毫发未损”。其将刑法原则与义关伦常的罪名相提并论,表明已经注意到刑法原则在新律中的重要性,比通说只关注义关伦常罪名的观点有进展,但对其“与封建法律截然对立的近代西方刑法原则”不是礼法之争焦点之说,考之于史,笔者认为值得商榷。虽然《清史稿》记载了关于干名犯义等罪名的争议,但是《刑律草案笺注》一书更是记载了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签驳“盛况”。
陈新宇博士在其《从比附援引到罪刑法定》一书中把“比附援引与罪刑法定之争”列为专章,但遗憾的是,他并未进一步阐明这场比附援引与罪刑法定之争在清末礼法之争中的位置及重要性。后陈新宇博士又有新的研究,指出清末刑法典的论争“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伦常礼教条款之争,一是比附援引与罪刑法定之争”,把“比附援引与罪刑法定之争”与“伦常礼教条款之争”相提并论。此前,关于礼法之争焦点的主要观点中基本没有比附援引与罪刑法定原则之争论的内容,更不见法学界有比附援引与罪刑法定原则之论争是礼法之争的焦点之说。
本文赞同陈新宇“两个集中”的观点,并认为这就是清末礼法之争的两个焦点。关于义关伦常罪名焦点说得到学界广泛认同,主要集中在义关伦常罪名的存与废、这些罪的刑罚要不要加重一等、是入律典正文还是置于附则三个方面。1907年,沈家本上奏《大清新刑律草案》,光绪帝按程序交由各部院、督抚签注。草案遭到签注全面批驳后,沈家本和修订法律馆迫于压力和能出台的策略考虑,同意“于有关伦纪各条,恪遵谕旨,加重一等”后送交法部,法部尚书廷杰在此稿后面加上附则五条,宣统元年(1909年)以《修正刑律草案》为名由廷杰、沈家本联名上奏。1910年,《修正刑律草案》交宪政编查馆核定更名为《大清新刑律》后,由庆亲王奕劻署名上奏。对此案,劳乃宣要求义关伦常诸条应逐一载入刑律正文,劳沈之间对无夫奸和子孙违犯教令两条争论最为激烈。1910年10月,在资政院议场,杨度与劳乃宣之间就新刑律之立法宗旨是国家主义还是家族主义展开论争,同时对无夫奸和子孙违犯教令再度争议。因此,本文对义关伦常的罪名是礼法之争的焦点之说表示赞同,它的确贯穿了清末修律的所有场域和载体。同时本文认为,比附与罪刑法定之争是礼法之争的另一个焦点。关于前者学界已达成共识,研究成果也相当丰富,而对后者尚无多少深刻之论,故本文重点就此展开论证。
比附存废之争
(一)法治派力主废除比附
首先,细数比附的弊端。《大清新刑律草案》第10条的立法理由指出:“本条所以示一切犯罪须有正条乃为成立,即刑律不准比附援引之大原则也。凡刑律于无正条之行为若许比附援引及类似之解释者,其弊有三:第一,司法之审判官得以己意,于律无正条之行为比附类似之条文,致人于罚,是非司法官直立法官矣?司法立法混而为一,非立宪国之所应有也。第二,法者,与民共信之物,律有明文乃知应为与不应为,若刑律之外参以官吏之意见,则民将无所适从。以律无明文之事,忽援类似之罚,是何异于以机阱杀人也?第三,人心不同亦如其面,若许审判官得据类似之例,科人以刑,即可恣意出入人罪,刑事裁判难期统一也。”其核心意思是:比附援引导致司法者变成了立法者,让民众无法预测自己行为的罪与非罪,导致刑事裁判不能统一。1907年沈家本等在《奏进呈刑律草案折》中再次主张“删除比附”,重申了比附援引的两大弊害:第一,混淆立法与司法。立宪之国立法、司法、行政三权鼎峙,若许司法者以类似之文致人于罚,是司法而兼立法矣。第二,使审判不能统一。“人之严酷慈祥,各随禀赋而异,因律无正条而任其比附,轻重偏畸,转使审判不能统一。”
其次,论证比附不宜存。《大清新刑律草案》第10条的“案语”云:“谨按此条即为不准比附援引而设。原奏理由并臣馆原奏业经剀切言之,乃邮传部并四川、两广、云南、贵州、湖广、湖南、江西、河南、两江等省签注,独于此条驳诘尤力。立论虽互有不同,大致以人情万变,非比附援引不足以资惩创。此盖狃于旧习所致,殊不知于今日情形,比附之制实有不必存、不宜存者。”“案语”又云:“刑法与宪法相为表里,立宪国非据定律不处罚其臣民,此为近世东西各国之通例,故有明定于宪法者,兼有备载于刑法者。光绪三十四年□月钦定宪法大纲业经载入,昭示中外。我皇上寅绍丕基,复叠次儆告朝廷,克成先志,则旧律中之违于宪法者,亟应一体删汰,庶上副缵述之至意,乃于刑律一端忽生异议,实与历次明诏显有背驰。此鉴于立宪比附之不宜存者又一也。”这段论述中,沈家本等运用三段论方法推导出比附不宜存的结论:大前提为东西各立宪国的通例是“非据定律不处罚其臣民”,即不许比附;小前提为我大清国即将实行立宪成为立宪国;结论是实行立宪后的《大清新刑律》中不许比附。
(二)礼教派力主比附不可废
首先,比附乃古之善法。礼教派认为,比附乃古已有之的善法,能预防“情伪无穷科条所不及者”。江苏巡抚陈启泰云:“比附加减之法,三代已有行之,非自秦汉以降始创也。诚以天下事变万端,有非法律所能赅备者,故特设此条为用法之准则,此正执简御繁之善法。”意即罪刑法定不能应对万般情事,比附恰能应变万端。河南巡抚吴重憙云:“比罪之法……我朝益昭慎重,凡援引比附者,均请旨遵行,司法者更无从稍越立法之范围。”即清朝总结前朝比附运用经验教训,规定比附不仅要引律比附,而且要请旨遵行,故司法者不能胡乱比引,不会超越立法范围。军机大臣兼管学部的张之洞说,《大清新刑律草案》《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没有提到比附,是最大的缺点。若因律无正条,不论何项行为,概置而不议,那么只会给刁徒提供“趋避之端”。他们从比附源远流长的历史、执简御繁与预防“情伪无穷科条所不及者”的功效进行论证,认为比附乃古之善法,不可废,否则附会导致“法政废弛”的严重后果。
其次,力陈比附仍属司法而非立法。面对沈家本直指比附援引致司法立法混而为一的责问,一些签注者认为,比附仍属司法,而新律给予审判官酌量轻重的权力,才使立法司法合而为一。江南江苏提刑按察使司签注云:“虽云比附要不能越乎法律之范围,仍是司法之性质,固不得讥为司法立法混而为一。”意即比附属司法性质而不是立法性质。苏抚陈启泰云:“虽曰援引比附仍不越乎正律之范围,犹是司法之向例,与立法迥乎不同,岂得指比附为司法而兼立法,与三权分立之义不符竞可删除不用?况外国法律非无比较参照之办法,即草案内亦尚有准照某条适用之文,乃独于第十条著明‘凡律例无正条者不论何种行为不得为罪’,转似明导人作奸趋避之路。此失于太疏者一。”意即比附向来都属于司法,外国法律也有比附,规定罪刑法定原则似乎在公开教导作奸之人逃避法律惩处。两广总督张人骏签注云:“释文谓比附类似之文致人于罚,则司法立法混而为一,非立宪国所应有。不如无此法而定此例者方为立法,若既有他律而比附定拟则仍属司法而非立法也。如以比附为立法则于本律酌量轻重者,又与立法何异?类似之例不能援以罚人,而轻重之权独可操之问官?诚恐任意出入将较比附为尤甚。”湘抚岑春蓂也不赞同所说比附是司法兼立法,其签注云:“至谓引律比附即为司法而兼立法,恐亦不然。”坚持认为可否比附是立法之权,引律比附是司法之事,比附能以简驭繁,断不可删除。
罪刑法定之争
(一)法治派主张引进罪刑法定
首先,挖掘传统中“罪刑法定”的因子。为驳斥对于刑律草案引进罪刑法定的各种责难,沈家本对中国历代刑法进行考察,从中挖掘出传统法律中所包含的“罪刑法定”因子。《周礼·大司寇》中有“悬刑象于象魏之法”,《小司寇》之宪刑禁、士师之掌五禁、俱徇以木铎等都是“法无正文不处罚之明证”。他还以晋刘颂的“律法断罪,皆当以法律令正文”之疏为例,指出:“今东西国之学说正与之同,可见此理在古人早已言之,特法家之论说无人参究,故称述之者少耳。”并以《金史·刑法志》所载的“自今制无正条者,皆以律文为准”的上谕为例,指出:“金代承用唐、宋刑法,而制无正条者一以律文为准,其不得用他律比附,灼然无疑。是中国本有此法,晋刘颂议之于前,金世宗行之于后,初不始于今东西各国也。”被聘来中国法律学堂主讲刑法、兼任调查员“帮同考订”刑律的日本法学博士冈田朝太郎也认为,“中国向用法定主义,故官吏断狱,必根据于大清律”。这些观点未免牵强附会,但“由此我们能够体察出以沈家本为代表的先进法律精英‘托古改制’的良苦用心和力图使中西法律思想融合的艰难过程。沈家本等人不仅要面对礼教派的诘难,更重要的是还要面对清廷统治层面,使他们接受西方法律的移植”。托古改制或许只是他们应对旧派的一种策略,但在事实上壮大了改革旧制的声势,为改革比附援引旧制奠定了思想基础。
其次,论证罪刑法定具有比较优势。沈家本在“案语”中说,“此条为刑律注重之要端而关系筹备前途尤非鲜浅,是以臣等敬谨统筹全体引伸前说,不敢与众论为苟同也”,意即第10条罪刑法定原则是刑法立法重中之重,关系到筹备立宪的前途。礼教派“谓人情万变,断非科条数百所能赅载者”。对此,沈家本认为,有了罪刑法定,法律之用则简可驭繁,并举例说“谋杀应处死刑,不必问其因奸、因盗,如一事一例,恐非立法家逆臆能尽之也”。《大清新刑律草案》第10条的“案语”云:“旧律毛举细端,几于一事一例,综计大清律例全书不下一千八百余条,然比附定案时有所闻。诚以条文有限,人事无穷,纵极繁密,星漏实多。草案正条一以赅括为主,实无斯弊……昔日本旧刑法采用法国,即以此条弁于篇首,行之数十年,惟窃引电气一案,颇滋疑义,卒以电气具有流质亦物体之一,仍当窃盗之罪。初未闻有巨奸大憝优游法外,何至行之我国反有不便之虞?况草案每条刑名均设数刑,即每等亦有上下之限,司谳者尽可酌情节之重轻,予以相当之惩处,是无比附之名而有加减之实,不过略示制限,不似旧日可以恣意出入其间耳。”此段论述,运用对比方法指出:实行罪刑法定原则有“一以赅括为主”之便利,而无“星漏实多”之弊端;采用罪刑法定原则的日本刑法实行数十年取得了良好效果;新刑律每个罪名有数档刑罚,每档有上下限,司法官可根据情节轻重惩处,能适应复杂情形且不会恣意出入人罪。
(二)礼教派坚决反对罪刑法定
首先,罪刑法定非防卫治安之道。江南江苏提刑按察使司签注云:“若如本条名言律例无正条者不论何种行为不得为罪,恐自此奸狡之徒将百计巧饰为非法之事,殊非防卫治安之道。”邮传部签注云:“迩来人心不古,犯罪者择律例无正条者故意犯之,以难执法之人。自离于罪,俾执法者无所措施。其流弊亦不堪设想,且以一人之心思才力对付千万人之心思才力,非以定法治之不足以为治……后世人心巧诈以致任意枉法,始非治法之过,乃不得治人之过也。按此条,仍不如仍尊旧律引律比附,应加应减,定拟罪名,议定奏闻为妥。”邮传部认为,罪刑法定导致的流弊不堪设想,还不如保留比附制度。江西巡抚冯汝骙签注云:此条立法“所以防承审官吏任意轻重,立法不为不严,若概为罪,则法制有限而人情变幻无穷,刁诈之徒择律无专条者犯之,可在其幸逃法网乎?”意即此条罪刑法定原则的立法是为了防止司法官任意轻重,但一概要求罪有明文,会让刁诈之徒有幸逃脱法网。
其次,不具备实行罪刑法定的条件。一些督抚大臣认为,清政府法制不完备,审判人才缺乏且程度不及,民众文明程度不高,尚不具备实行罪刑法定原则的条件,因此比附不可废。河南巡抚吴重熹签注云:“本条采用日法,凡律无正条不论何种行为不得为罪,范围既狭,疏纵必多,施诸中国,决其不可……东西各国所以能正条之外,概不处罚者,实向于文明程度与中国不同,且于刑法之外有民法、商法、海陆军刑法、海关条例、学堂规则诸类。”湖广总督陈夔龙签注云:“惟审判人才现尚缺乏,各条所载罪名颇多,死刑与徒刑并列之处,设审判官程度不及,援引失当,即难免罪有出入,恐亦不能无弊。”他在复《奏新订刑律与政教难符应详加修改折》中云:“惟是中外风俗不无异宜,人民程度亦多差等,似有不得不就政教民情再加讨论者。如删除比附以杜意为重轻,而情伪万殊,条目不足以赅事变,且审判人才缺乏,如凭审判官就各刑上下之限,临时审定,恐程度不及,亦不免援引失当,出入人罪。”湘抚岑春蓂签注云:“如谓犯应论罪之行为无不赅载于法律之内,是数百科条已能逆臆万变之人情,而无或轶乎其范围之外?恐非立法家所敢自信也。”此乃试图论说立法家制定不出包罗无遗的刑法典。他俩运用简单比较的方法,从中国法制不如外国完备、文明程度不如外国高、审判人才缺乏或不肖等角度,论证实行罪刑法定原则时机不成熟,并认为废除比附后,法官同综合性条款打交道,还要适当处理更多种类的不同情形,因而对罪刑法定这一新事物能否带来如期的效果普遍持怀疑甚至是反对的态度。
结 语
礼教派对《大清新刑律草案》第10条的攻诘较详细地记录于《刑律草案笺注》一书中,法治派对“签注”反对声的回应则集中体现在《修正刑律案语》一书中。围绕《大清新刑律草案》第10条的争论是认识清末礼法之争的重要场域。从其各种攻诘与回应中可以看出,对在立法中是确立罪刑法定原则还是保留比附的论争十分激烈,而此争论是关于刑法基本原则的争论,是刑法总则方面的争论,因而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的意义。从史料来看,其争论的激烈程度和争论内容本身的地位与作用都不亚于义关伦常的具体罪名;从《大清新刑律草案》第10条关于罪刑法定原则的“案语”所云“此条即为不准比附援引而设。原奏理由并臣馆原奏业经剀切言之,乃邮传部并四川、两广、云南、贵州、湖广、湖南、江西、河南、两江等省签注,独于此条驳诘尤力”来看,当时法治派与礼教派关于罪刑法定与比附的争论相当激烈。因此,我们有责任恢复历史真貌,还原比附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废立在这次礼法之争中的真实位置,即比附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废立之争是清末礼法之争的另一个焦点。与“义关伦常的几个罪名”之争相比,无论从争论的内容本身还是从中国法制近代化转型来看,在这场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重大争论中,比附制度与罪刑法定原则的废立之争都更具有根本性的意义。他们的意见分歧只是统治集团内部对于如何推进当时中国法制变革而采取的不同态度,其用意都是想挽清朝统治于即倾,说到底是国家治理模式的选择问题。他们的终点目标是一致的,即收回法外治权,实现富国强兵。但是起点与方法不同,一为要植根于本土文化、国情民意,坚守礼教;一为几乎是在对本土文化、国情民意清零或酌情考虑的基础上,既托古改制又托洋改制,直接接入西洋法律。清末礼法之争虽已属历史陈迹,但这场争论对于今天我们在全面依法治国征程中如何认识、处理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关系依然有启发意义。
①参见金敏《继承晚清谁人遗产?——梁治平先生〈礼教与法律〉读后》,《清华法学》2015年第5期。
②参见高汉成《签注视野下的大清刑律草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③宣统二年十月初四(1910年11月5日)《宪政编查馆大臣奕劻等奏为核定新刑律告竣请旨交议折》,载《钦定大清刑律》书前所附奏折。
④向达:《清末礼法之争述评》,《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
⑥参见杨鸿烈《中国法律思想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98年影印第1版,第324~332页。
⑦转引自陈新宇《〈钦定大清刑律〉新研究》,《法学研究》2011年第2期。
⑧张晋藩:《中国近代社会与法制文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11页。
⑨参见史广全《礼法融合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历史演进》,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539~541页。
⑩参见秦涛、杨柳青《清末法制变革中“礼法之争”的现代启示——以〈大清新刑律〉的制定为视角》,《求索》2009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