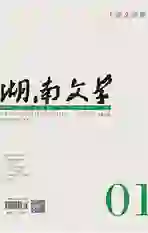曼珠沙华
2018-03-19苏薇
苏薇
一
她醒来的时候,先看见对面楼上十七层的灯光,桔黄色,夜色下透着薄荷的清凉。呆了半天,才想起梦里的情景。梦里,她躺在一根大树枝上,脚下是红得快要破裂的花海,她想翻一下身,可刚一动,就从树枝上掉了下来,撞到了胸口,感到一阵阵的疼。
看了看表,深夜十二点多了。哦,已经过了十二点,也就是说,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从医院回到家后,她经常半夜醒来,渐渐养成了习惯。日子不多了,连睡眠都舍不得。不光是舍不得睡眠,她什么都舍不得。
最近幾天,这种疼痛总是突然来袭,隐隐地由内向外,穿肌透骨。她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可没想到会这么快。出院的时候,医生就告诉她,这种病复发的几率大,要时刻注意。其实医生还有半句话没说出来,就是——一旦复发了,神仙也救不了。当时,她精神很好,天空瓦蓝瓦蓝的,像小时候用过的纯蓝墨水。要怎么注意呢?这种病一旦落到头上,就像掉进了精心设计的圈套,那点渺茫的希望如远去的帆影,摇摇晃晃,若隐若现,随时都会消失。她很坦然地接受了这个事实,就像从别人手里接过一样东西。
丈夫还是没有回来,家里空荡荡的,她算了算,大概又有五六天了吧。她生病花了很多钱,听说他的公司最近遇到了麻烦,他要解决这些麻烦,夜不归宿自然是可以理解的。她出院也好长时间了,完全能照顾好自己。当然,她还听说了他其他方面的麻烦,她不想打听,这对身体不好。病人是要精神愉快的,精神垮了,身体就会立刻响应,否则最后二者只能同归于尽。
她想喝水,双唇太干了,嘴角裂开了口子,不能大声说话,也不能大口吃饭。其实,她用不着大声说话,孩子住校,周末才回来。家里没人,说话的机会也就不多。她能做的也就是边整理整理东西边自言白语——从医院回来她就在整理东西,断断续续的——自己的,孩子的,丈夫的。家不大,东西却不少,孩子小时候的玩具、小衣服、看图识字;自己的书、笔记、随手写下的一两句诗;还有丈夫的——他虽然人不在家,但东西还是在家的。总之,东西多得数不清,要整理好,需要一段时间,更何况她整理得很慢很慢,对每样东西还要说上几句,跟交代后事一样。
昨晚整理衣服时,掉了一粒扣子,她拾起来,虽没有马上缝上去,可还是放在一个小铁盒子里。她知道,快夏天了,这件冬装大概没有再穿的机会了。明年冬天,那一定是很遥远的事情。她觉得自己等不了那么久了。
她给自己倒了杯水,一小口一小口地喝着。她没有开灯。睡觉时,她习惯拉开半个窗帘,躺在床上或靠着被子半坐着,看着对面十七层的窗口。那个窗口永远亮着灯,无论夜里何时醒来,窗口都是亮的,这让她很有些感触。她觉得日子就像剩下的最后一根琴弦,再怎么弹都曲不成调了。只有看见那片灯光,挂在树梢上的心才会落地,才有种还活着的感觉。
她喝得很慢很慢,目光又落在对面的十七层楼那扇窗上。灯光微黄,忽聚忽散,夜色都被晃得轻盈活泼起来。那是一栋新盖的楼房,住户不多,每层零星亮着一两个窗口,十七层只亮着一个窗口,那一定就是他的家了。没错,一定是的。此刻,他在吗?在干什么?
确切地说,她是在问另一个人,在吗?在干什么?这个人是她的初恋男友。他死了,死在十八年前的夏天。当年,她二十三岁,他二十五岁。他开着他那辆宝马,在一个雨夜,车毁人亡。
此后的十八年,她依然活着。她离开了他们的城市,进了工厂。她从没想过这辈子会当工人。当工人也挺好,在她眼里,没什么高低贵贱之分。原来她在研究所,每天和图纸打交道,后来当了工人,每天和机器打交道——都是不需要交流的,这无意中成全了她——男友死后,她就不愿意和任何人交流。她给自己画了个牢,人生崩盘了,连呼吸都是可有可无的。那段时间,她成了孤魂野鬼,轻飘飘的,每天都处在半睡半醒之间。
喝完水,还是感觉干得难受,就找出润唇膏。买唇膏的时候,店家推荐一款浅粉色,说,你的脸太白了,用个带点颜色的吧。她说,好。涂上去,果然不错,像贴了朵桃花,人也精神多了。她来来回回地涂着,极有耐心地,从左到右,从右到左,先下唇后上唇,一种清凉温润的感觉就来了,像下了场小雨。
有风拍打着窗户,对面的灯光变得单薄而惨淡,但仍从容不迫地亮着。这很像那个男人走路的姿势,从容不迫,不紧不慢,每一步都极有底气。
二
第一次见到他,是刚搬到新家不久——出了院,她就将家搬到了东区,是三年前买下的房子,当时四周还是一片荒地。本没打算搬家,偏僻,孩子上学远,买个菜都不方便,可她好清静,原来的家临街,半夜三更还车来车往的,她睡不着。新家本来是想租出去的,简单装修了一下,但现在对她来说,这种简单刚刚好,心没那么堵得慌。
新家在十五层,楼下是个小广场。忘了是搬来新家的第几天,她想下楼走走,她绕过花坛,走过那条石子路,最后坐到停车场旁边的石凳子上,盯着眼前的喷水池发呆。黄昏来了,太阳留恋地从树梢上慢慢西沉,紫色的暮霭轻柔地透过枝叶落在水面上,水柱落处,涟漪中荡出点点金红,像一条条红鲤在恋恋风尘。她就那么一动不动地坐着,水花起落,溅在手上,竟没有一丝感觉。洒水车放着熟悉的曲调从小区门口缓缓驶过,她的目光循着声音,那么耐心,直到听不见为止。现在的她,陌生得连自己都不认识了,曾经的生活遥远得像被丢在了山的那边。
就是在这个时候,她看见了他。他动作流畅地停好车,背对着她在打电话。那个瞬间,她一度停止疼痛的胸腔突然就又开始疼痛不止。那个消失了十八年的背影,就这么无辜地,真实地,完完整整地出现在眼前。这不是梦吧?她问自己。她立刻想起早己稀释了的往事,想起那个叫顾一凡的人。他曾大声地唤她的名字,方蝶,方蝶。方蝶,方蝶……那一刻,她的心被往事给死死地绊住了,直到那个身影走了过去,听见他对着手机说,对,十七层,是的,是十七层……
她看着那个男人,看着他走进对面那栋楼。她突然想哭,却没有哭出来。
她早己习惯了这种感觉。孩子周末回来,放下书包说“妈妈,累死了”时,她有这种感觉;丈夫偶尔回家,不冷不热、不成不淡地问“吃饭了吗?有没有不舒服”时,她有这种感觉;朋友打来电话,“身体怎样?还好吧?”她淡淡地回答,“还好,还好,吃得也多了,还赏了桃花……”简单的对话,这种感觉就来了,从来不打招呼,就那么现成。
这么多年,她尽量不去触碰记忆,像黑夜中绕开一座断桥。那些关于顾一凡的一切,都烹煮成了茶,散落在一板一眼的现实中。偶尔,她也会想起他,特别是丈夫夜不归宿的时候,她就会想,如果当初他们都活得好好的,她嫁给他,是否一定就会幸福呢。她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都过去了。她说。
有段时间,她一想到丈夫,就想笑,控制不住地想笑。他忙,她知道的,但深更半夜的,忙什么呢?他们的关系早己嶙峋成一具风干的白骨,近段日子,越发的冰冷刺目了。她有時也会内疚,但不会内疚太久,怀念一个人有错吗?只是怀念而已啊。
她喜欢一种植物,叫做“忍冬”的,她就喜欢那个“忍”字;她还喜欢一种叫做“彼岸花”的,传说长在冥界,有红白两种,她喜欢红色的。那种血色的花还有个浪漫的名字,叫“曼珠沙华”,花太美,有残阳如血般无与伦比的美,却很凄凉,花叶永不相见,寓意悲凉。
暮色上来了,眼前的喷水池,周围的一切,都变得影影绰绰。突然,十七层有灯亮了,整个十七层,就亮着那一个窗口。她一阵激动,痴痴地盯着微黄的光晕,如隔着玻璃看沐浴的美人,然而,心是干净的,像块无边的草地。
又有几辆车在身边停了下来,有带着孩子的夫妻,也有的只是一个人,提着大包小包的东西,都是匆匆忙忙的样子。她突然羡慕所有的人,包括那些同事们。他们还可以听到机器声,还可以按时上下班,周末也还可以聚在一起,吃火锅,逛大街,采买油盐酱醋,继续过烟熏火燎的日子。
出院后,她就没有再去上班。当时她还傻乎乎地问医生,要休息多久才能上班?医生回答得很简单,先休息。
她是厂里的技术员,也是唯一的女工程师。住院前一天,她还专门去了厂里,她是走路去的。西边天空浅浅的蓝,暮色的黄,火烧的红融在一起,靓丽得像个大舞台。一路上,她边走边看,人民公园、德福超市、丰乐园大酒店、休闲画廊……她感觉那天的街道很美,行人也美,所有的一切都美不胜收。她选的时间很好,到了厂里,工人们都下班了,喧嚣了一天的车间像是沉到了水底。夕阳斜射进来,落在一排加工好的零件上。她拿起一个,对着阳光反复地看。看了会儿,又握在手心里。零件是刚车出来的,还很粗糙,没关系,还要精车,还要清洗,待转到下一个车间,一定是光滑明亮的。她很不舍地将零件放回原处,在厂区慢慢地转着。车间都还没有统一锁门,她看了看表,还差十分钟。十分钟,喝杯茶的时间,她却打算将六个车间转一遍。她走得很快,一排排机器,一个个操作台,都一掠而过,来不及了。是啊,一切都来不及了。
有风吹来,她有些冷,准备回去了。这时,她又看到了那个男人,他从楼上下来了,朝车走去。一会儿,车灯亮了,照着前面的路,一片雪亮。她坐直了身子,他要去干什么?临时有事?或仅仅是出去买盒烟?男人都喜欢吸烟。顾一凡就是,他喜欢站在窗前,开着窗户,将烟圈吐到窗户外面去。高大的身影像棵白杨,沐着夕阳,惊心动魄的暖……唉,今天这是怎么了,不想了,不想了。
她抬起头,十七层依然亮着灯,明朗安静。她摸了摸自己的头,这个假发不好,太短,芦花似的开在头顶。她喜欢长发,明天要戴那个长发才好。
突然间,她的心就那么一沉,感到自己站到了高原上,寒冷,孤寂,还缺氧。她有点想哭,鼻子抽了抽,眼睛眨了眨,但没有眼泪出来。都这么大的人了,灯火这么亮,火树银花地照着,哭了多不好。
三
她没有给任何人打电话。这种病一旦复发了,神仙也救不了。所以早一天晚一天,其实是一样的,殊途同归。而且她还有个秘密,就是想去见见十七层的那个人,一次真正的见面。她甚至想要和他单独见面,身边没有任何人,甚至连风都不要有。她只想看看他,看清楚他的五官。因为他太像顾一凡了,他就是顾一凡的复制品,蜡像,或者,镜子里的影像。
她是不相信轮回的,更不相信死后可以随心所欲地想见谁就见谁。这是她一个小小的愿望,见一面,就好。这么多年过去了,物不再人也非了,只剩下曾经的美好,天苍苍野茫茫地放在心底。她只是想见见,在住院前,或直白一点说,在死之前。就这么简单。
涂完润唇膏,她又躺了下来。这种疼痛只有在梦里才会减轻些。黎明还早,夜太漫长,像条无名无姓的河,不知从哪里来,也不知终归何处。十七层的灯光不再摇晃,被月光染成灰白,像结了层霜。她想,还是再睡一会儿吧。
早晨醒来,就看到孩子老师发来的信息,意思是说,快升高中了,最后一学期最后两个月,是关键中的关键,关系到上哪所高中,进而关系到上哪个档次的大学,再进而关系到整个人生。也就是说,这两个月太重要了。是啊,自生病住院后,对儿子关心就少了。儿子长高了,足足高出她一个头。刚住院那会儿,儿子都是周末来看她。开始时,儿子给她讲学校的事,她有气无力地听着,身体本来就弱,化疗反应让她连看一眼窗外的力气都没有。她感觉自己像放进榨汁机里的水果,只剩下最后一把残渣了。有时她就想,还不如死了算了,受这罪干啥?后来儿子话就不多了,只说,妈妈,你一定会好起来的。她就努力地笑笑,是啊,一定会好起来的。等妈妈出院了,想吃什么,妈给你做。儿子说,我自己会做饭了。她听了一阵心酸,儿子是会做饭了,一个男孩子,能做出什么好饭,还不是泡个方便面、煮几个鸡蛋?
住院的时候,丈夫也是会来的。来了就说,我很忙,想吃什么,让保姆去买。丈夫倒不怕花钱,她的医疗费总是足足的,但每次来都是寥寥几句,感觉还难受吗?吃了什么?或再问一句,需要换洗衣服不,我回家去拿;还需要什么,我去买。
他总是坐在另一张床上。如果那张床也有病人,就坐在旁边的凳子上,不远不近的距离。他从不坐到她床边来,能够让目光不那么辛苦就能彼此交流。也是,他们早就不用目光交流了。她需要什么?她需要一个宽阔的肩膀,一双有力的手臂,还有曾经熟悉的一切。可这些,都被丈夫忽略了,或者说根本就不存在了。他们之间,只剩下正襟危坐,相敬如宾。
老师说的,最后两个月是关键。她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尽量撑吧。她穿好衣服,隔着玻璃看着对面十七层。他也许早就上班走了。她想象着他的样子,一定是换了件新衬衣,理了发,胡子也刮得干干净净。顾一凡就是那样,永远干净整齐,像一块温润的透明皂。
丈夫打来电话,说,你妈妈摔了一下,没伤到骨头。我马上回去接你,等着我。
真的没事吗?她急急地问,那她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刚出院,不是怕吓着你吗。
她放心了,轻轻挂了电话,眼泪却进了出来。虽然丈夫的口气淡淡的,但“等着我”三个字突然让她有种生离死别的凄凉。她很好笑自己的脆弱,丈夫不过是让她别乱跑,他没时间找她,可她宁愿这是一个美丽的误会。有时候,谎言也是美的,就像画有了颜色,怎么看都是鲜亮的。
她又開始整理东西。没时间了,必须得抓紧些。衣服,围巾,各式鞋子,好些衣服都还没有穿过,有的连吊牌都没剪掉。她拿起一件穿在身上,不行,太宽。人瘦了,衣服就大了,穿在身上松松垮垮的,不好看。
她抬头看了眼墙上的表,十点半了,丈夫还没有回来。她给妈妈打了电话,妈妈说,哎呀,没让你们来。不用来的。能走路,就是屁股还有点疼。她被逗笑了,说,妈,那小时候,你打我疼不疼?妈妈不说话了,只是笑。她放下心来,站到窗前,向楼下张望。外面下起了雨,不大,抽丝剥茧一样。她不停地张望,希望看到那辆黑色的车,车上下来那个酷似顾一凡的身影。没有,楼下一片寂静。她又看了眼十七层,窗口静静的,像悬浮在半空中的一段时光,隆重得有些超载。
她一阵恍惚,似看见顾一凡站在那辆车前,斜倚着车门。他还是当年的样子,很年轻,她却老了。没病前,她经常照镜子,感叹“青山常在红颜已殁”,那时,她偶尔也会想起顾一凡,那些最初的美好,总是让人记忆犹新——更何况,他的死也和她有一定的关系。如果她不打那个电话,他是不会临时决定来看她的。出事后,顾一凡还是等到了她,他们见了最后一面,当时的顾一凡,脸白得让人产生幻觉。后来,她真的产生了幻觉,幻想着他去旅游了,或是去国外了。顾一凡不经常这样吗,半个月或一个月,他们才能见上一面。
她有一套首饰,是当年顾一凡送她的。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们肯定会结婚、生子、衰老,再一起走向死亡,像所有夫妻那样。后来结婚时,丈夫也给她买了首饰,她都放了起来,一次也没有戴过。镜子里的自己,还是很年轻的,至少比同龄女人要年轻,她皮肤白,身材小巧,长发披肩。当然,现在是假发了,但反而更柔和靓丽了。
丈夫打来电话,说马上到家,让她准备好。她有点内疚,还有点兴奋。生命快走到尽头了,要笑着才好。出门前,她特地在镜子前站了会儿,镜子里的女人,嘴角轻扬,唇红齿白。她给丈夫发了微信,告诉他,她下楼了。丈夫回了个“好”。
好几天没见丈夫了,他换了件她从没见过的衬衣,深蓝色,很深沉的颜色。
还好吧?他问。
还好。她答。
需要买什么,顺路去买。
不用,家里都有。
还是让保姆来吧,公司太忙,你一个人不行。
我很好,能行的。
这一刻,她很想告诉他,她的病大概复发了。但她没有,她想等见过那个人之后再说。到时候,是生是死只能听天由命了。
雨滴打在车窗上,透着无处寄托的空洞。风此消彼长地吹着,像被动了手脚一样不自然。两个人都沉默不语,彼此都习惯了,似乎一开口,他们的关系就会崩溃,会难以为继,连样子都做不下去。
四
胸口的疼痛时刻在提醒着她,该去见他了。这几天,她觉得每天都能见到他,其实,总共就只见过两次而己。她想象着那个背影,白色的,蓝色带条纹的,暗红色的……她喜欢暗红色,顾一凡最喜欢穿暗红色的衬衣。
从母亲那里回来,雨已经停了,太阳出来,空气湿漉漉的。她发现小区里的花都开了,月季,紫薇,都香喷喷水灵灵的。丈夫把她送到家,说还有事就走了。她拉开窗帘,听到有歌声传来,断断续续的,像埋着一个含苞待放的伏笔。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以及冬天的落阳
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地这么想
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它天天地流转
风花雪月的诗句里我在年年地成长
是罗大佑的《光阴的故事》。这首歌听过无数次,从没有今天这么动听。在书架上,她发现了一个以前的笔记本,打开,扉页上写着自己的名字——“方蝶”。多好听的名字,可惜马上就要刻在墓碑上了;刻在墓碑上也挺好的,如果有人见了,一定会说,这个女人一定很漂亮,名字都这么好听,也一定很温柔。她想着想着,竟有些神往了。
窗外,起风了,风很大。
明天必须去医院检查了,也许,这一去就再也出不来了,就算还能出来,也没有力气去见他了。
她决定立刻去见他。
换上衬衣、牛仔裤,有点内增高的运动鞋,她喜欢这种休闲的打扮,两手闲闲地插在裤袋里,风一样自由;又在脖子上围了条暗红色的丝巾,围上丝巾,就显得郑重多了,像真的要去约会一样。
这很像一个梦,一个红色的梦,一个带着好看花边的红色的梦。她有点紧张了,开始犹豫,还要去吗?她一遍遍问镜子里的人。镜子里,背后就是十七层那个窗口。她感到那个人也站在窗口,正朝她这边冷静地看着。她突然觉得,他们就像两根离得不远的树枝,风一吹,偶尔碰一下,立刻就分开了。
她走出家门,走出小区,走到街上。她看见街道对面一家门店刚开业,门口花团锦簇的,铺着红地毯,地上还有鞭炮的碎屑。她停下脚步,也跟着人家傻傻地欢喜了一会儿。阳光从大楼缝隙间射过来,像跌到了深谷里。她沿着小区门口的和平路一路走下去,穿过向阳路,转到解放大道,最后,站在朝阳路口。她不知自己走了多远,丈夫的公司就在朝阳路的尽头,这条横穿整个城市的主干道,车辆流水一样穿梭。她觉得丈夫的车就在这车流里,可是,他看不见她,她也看不见他。
她站在路边广告牌前,风在耳边痴缠着,不忍分离一样。她呆愣着,茫茫人海,他在哪儿呢?她知道,在这儿不可能见到他,还是在小区门口守株待兔的好。
她又一步步走回去,到小区门口时,已近黄昏。暮色从树根、墙角咕嘟咕嘟地冒出来。她盯着每一辆黑色的车,那个刻在脑子里的车牌号在眼前忽大忽小地变幻着。
那辆车真的开过来了!不快,从容不迫的。
喂,喂,等一下。她鲁莽地挥着手,几乎是冲过去的。
车停了下来,车窗玻璃跟着滑下,她看见他了。
他平静地问,有事吗?
啊?她有些手足无措。她没有事。她就是专门来看他的。我也是这个小区的,她指着不远处的大门口,我……见过你……
他看着她窘迫的样子,居然下了车,又轻声问了句,有事吗?
啊?她继续手足无措,眼睛却很大胆地看着他的脸。
我叫钟辉。他笑了,笑容也有几分像顾一凡。
她没注意听他说了什么,只顾抬着头,直直地盯着他的脸,很认真地盯着。冰山一样凛冽的记忆总是棱角分明,当年的顾一凡,也是这样挺拔的身材,浓黑的眉毛,好看的一张脸。她想,人都快死了,就这样看看吧,看看也无妨。那一刻,她在心里哭得翻江倒海,所有的委屈、疼痛,还有来自另一个女人的羞辱,统统地发泄出来。别装笑脸了,别顾忌这顾忌那的了,做一朵渺小的花吧,春天来了,该开就开吧。
你住在我家对面,十七层,对吧?她看够了,笑着说。
男人微愣了下,抬头看向四周,目光在半空中跳跃着,像是在寻找哪里是十七层,然后冲她笑笑,点头说,是,十七层。
你家夜里总亮着灯,在工作吗?她心里突然一暖,有种子破土而出。
男人又愣了下,有些吞吞吐吐,是,在工作,工作很多。
我经常见到你,还记得吧?她像个小女孩,诚恳又坦率。她确实感到自己又回到了年少时光,那些风雨雷电肆意横行的时光。
他疑惑地看着她,是吗?经常见面……是我太粗心了。
突然,一阵狂风,她的假发像被一只手给抓了起来又扔了出去,飞到了半空中。他们眼睜睁地看着它飞快地转着,落到地上,又被风吹起,旋转着向远处滚去。
啊——她急促地叫了一声,双手抱住头,脸上的表情——惊惧,痛苦,绝望搅在一起,成了一团墨绿。
一切都卡住了,空气不流通了,车轱辘不转了,风不吹了,尘不落了,都不上不下地卡着,只有那个假发依然在随风远去,追都追不上。
没事的……啊,没事的。他说。
这样也很漂亮。他说。
真的没事的。他又说。
挺好看的,一点都不难看……他重复着,像做错了事,不敢去看她的脸。
她几乎要哭了。
她不觉得自己有多难看。她照过镜子,就算光头,眉眼也是精致的,更何况她现在长出了头发,毛茸茸的,像刚出生的小鸭子的羽毛。这一刻,她满脑子都是顾一凡。她想,如果他看见她现在的样子,一定会很难过的。活着真没有死了轻松,但说不定他会后悔,活着的是她,而不是他。他有可能还会落泪,虽然他从不落泪。难过的时候,工作不顺的时候,他就抽烟,一根接一根地抽,抽完了,就没事了。
没事的,真的没事的。她看着他脸上很为难的笑,也浑水摸鱼地笑了下。
接着,两个人都不知道该再说点什么,就都扭过头,看着车来车往。
我想看看你的手。她突然说。说完就后悔了,要死了,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呢,只好纠正偏离了轨道的思绪,说,我会看手相,挺准的。
他将手举到眼前,反复看着,就像看一张纸币到底假不假,看了会儿才大方地伸到她眼前。
对着夕阳,她很认真地看着,他的手大而温暖,她真想握一下,或被它握住,她就会勇敢地走进医院,等待最后的归宿。他低着头,漫不经心地看着她,有点怀疑的样子。
她看了会儿,说,嗯,命挺好的。生命线、爱情线、事业线,都一顺到底,一生顺利,平平安安。
不做那个忧天的杞人,过好当下。他看着自己的手,有点小得意。比如我今天就中了五块钱,他很高兴地说着,刮刮奖,最低五块,我就中了五块。
他那辆车起码几十万,会在乎五块钱?她不懂。
五块?五块也挺好的。她说。发自内心替他高兴。是啊,活着就挺好,更何况还多了五块。
五
该见的都见了,该说的都说了,该收拾的也都收拾了,相当于把后事交代清楚了。水电费的账号,物业的电话,电器售后,车的保养,孩子多长时间要换一下床单被罩枕头套,备用的那套放在了哪里……这些她都整齐地记在一个小本子上。她知道,好多事情,丈夫从来都没有过问过。
她看了眼对面十七层,灯光依然亮着,桔黄色,像一片秋风里的野菊花,孤独顽强地开着。
她坐在书桌前,有种如释重负的轻松。随手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薄薄的,不用看她也知道是美国托马斯·内格尔的《你的第一本哲学书》。这本书她早就看过,讲的是认识、意志、死亡等一些最基本的哲学问题。她翻开,呆呆地盯着一行行的字,悲伤地想,人死后会到哪里呢?会以另外一种形式活着吗?还是就此消亡了呢?消亡了不好,如果以另一种形式活着,就算他们看不见她,她也能照顾他们……
胸口又开始疼了。夜深了,墙上的钟指向十一点,该睡觉了。明天,就要去医院了。
她是一个人去的医院,早已驾轻就熟。检查完她拜托一个熟悉的小护士,请她等结果出来先给自己打个电话。从医院里出来,走在阳光下,她脑子突然不听使唤了,许多杂七杂八的往事一齐冒了出来:小时候妈妈种的向日葵,和丈夫结婚时堵在半路上的婚车,儿子出生时印下的小脚丫……全都历历在目,搅得她一阵头疼。
她是在早晨醒来时接到小护士电话的——方姐,没事的,可能是心理作用……她握着手机的手突然不会动了,整个世界难以置信地冻住,眼前出现大片大片的花海,那种又名曼珠沙华的红色花朵,以不可思议地速度迅速蔓延着,直到天地的尽头。
她来到对面楼下,仰望着十七层。她只想告诉他,她没有事,身体还好,还可以继续活着。
阳光像是从雪山顶升起,透着清凉,空气中还藏着暗香。十七层的灯光不见了,变得和别人家的窗口一个样子。她爬了两层,感觉有些累,只好进了电梯,看着数字嘟嘟地变着,箭头一路向上。十七层到了,她走了出来。第一次离这个窗口那么近,近得像装进了胸腔里。她站在深蓝色的防盗门前,脑子里有片芦苇荡,眼前晃动着人影,还听到了鸟叫声,风声,好像那个叫钟辉的男人,就站在门后,随时都会打开门看见她。
她敲了敲门,听见里面一个老人的声音,来了,来了。似乎还一路小跑。老人打开门,看了看她,说,你找谁?
我找钟辉。他是您儿子吗?她觉得这位老人家很慈祥,也很阳光。对,阳光,充满了正能量。
我们只有个女儿,在国外。老人笑了,冲着卧室大声说,老太婆,我们还有个儿子吗?你藏哪儿了?
卧室里传来一声笑骂,死老头子!谁呀?
她也跟着笑,又不死心地问,你们家是不是每晚都开着灯,夜里也开着?
老人两手一摊,老太婆不让关,关灯睡不着,就整夜都开着。
哦,她说,那我走了。
顺着楼梯,一步一步地下楼。用了好长时间,才下到楼底下。站在清爽透亮的阳光下,她感觉一阵恍惚,像做了一个梦。恍惚中,又突然想起一件事,丈夫说中午是要回家吃饭的。
责任编辑:刘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