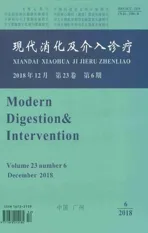3D体外肝纤维化模型
2018-02-10孙启华赵晨玮张迎超
孙启华 赵晨玮 张迎超 陈 晶
【提要】慢性肝病是影响全球疾病发病率和死亡率的重要原因,其特征是慢性炎症和纤维化/瘢痕形成,从而导致终末期肝病及其并发症。迄今为止,肝移植仍是终末期肝病的唯一治愈方式。为了开发有效的抗纤维化治疗,迫切需要稳健且具有代表性的体外模型。尽管通过使用不同复杂性的各种细胞培养模型在二维系统(2D)中进行了重大改进,但尚未开发出有效的抗纤维化疗法。这些再现肝脏微环境的三位系统(3D)体外模型的改进将创造寻找抗纤维化合物的新时代。
肝纤维化由不同病因的慢性肝损伤引起。肝炎病毒感染,某些代谢性肝病如遗传性血色病、卟啉症,重度酒精摄入和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及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都是肝脏疾病,如果不及时治疗,均会导致慢性损伤。如果对病因无动于衷,不及时治疗,将导致肝纤维化,甚至发展为肝硬化[1]。肝纤维化被认为是失调的修复反应,其特征在于肝细胞坏死、炎症、氧化应激和过度的细胞外基质(ECM)沉积,ECM的过度沉积可能最终导致肝硬化。事实上,几乎所有原发性肝癌病例都由肝硬化发展而来[2]。
一、参与肝纤维化的细胞类型
肝细胞的细胞死亡是几乎所有类型的肝脏疾病的驱动因素。在慢性肝损伤中,肝细胞的死亡(或损伤)诱导旨在重新储存肝脏结构和功能的反应,包括通过巨噬细胞清除坏死肝细胞,以及通过产生ECM稳定肝脏结构。
位于Disse窦周间隙的肝星状细胞(HSC)在肝损伤后被激活并且协调修复反应,其主要通过分泌间质纤维胶原发挥作用,特别是I型和III型。 如果损伤是急性的,过量的ECM最终会降解,并且正常的微环境会恢复正常。 如果损伤是慢性的,例如,在慢性乙型或丙型肝炎中,ECM的持续沉积可能最终导致瘢痕基质,扭曲肝脏结构和脉管系统并损害其功能差异。肝损伤后,HSCs“激活”,从静息的维生素A储存的HSC转变为增殖的纤维化肌成纤维细胞样细胞[3]。HSC或门静脉成纤维细胞来源的所有肌成纤维细胞均可基于一组蛋白质进行鉴定,这些蛋白质表明其活化的瘢痕组织形成表型,包括α平滑肌肌动蛋白(αSMA),胶原蛋白(1a1,3a1),波形蛋白,骨桥蛋白,赖氨酰 氧化酶和TIMP1(金属蛋白酶组织抑制剂1)。 这些标记通常用于确定肝组织纤维化或培养细胞中HSC的活化[4]。
HSC活化是由过多的生长因子和细胞因子介导的,这些生长因子和细胞因子是由受损的或垂死的细胞释放的,由浸润的免疫细胞分泌或由已经活化的HSC释放; 例如PDGFbb,TGFβ,IL-1等。此外,HSC吞噬肝细胞凋亡小体也可以诱导HSC活化[5-6]。HSC一旦激活,就不能再回到其初始静止状态;在小鼠中,大约50%的细胞似乎从其活化的肌成纤维细胞状态恢复到静止的失活状态[7-8],而其余细胞很可能发生凋亡或被NKT细胞杀死[9]。在体外,这些“灭活的”或“恢复的”HSC更容易对促纤维化刺激物如TGFβ起反应[7-8],而体内这些恢复的HSCs对新瘢痕形成的贡献比静息HSC更为积极[8]。虽然这种灭活已在小鼠中得到明确证实,但对于人类HSC而言,迄今为止的体外研究只能表明原代人类HSC还具有这种潜力,可以恢复到更加分化的表型[10],但体内数据仍然缺乏。
肝窦内皮细胞(LSEC)在肝损伤期间释放的血管分泌因子似乎决定了瘢痕组织形成的程度[11]。LSEC自身毛细管化(出现基底膜和失去窗孔)并经历血管生成和血管收缩。在急性和慢性肝病中可以并排存在不同的细胞死亡模式,即细胞凋亡,坏死性凋亡和坏死。细胞凋亡导致低炎症状态,坏死性凋亡和坏死导致高水平的炎症[12]。虽然肝细胞死亡可以诱导纤维化,但胆管细胞或肝细胞的损伤也会引起几种肝细胞类型的应激反应,从而导致纤维化[13]。
多年来,动物模型在开发药物化合物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因为动物模型结合了天然ECM微环境,不同细胞类型以及氧气和营养流[14-15]。使用动物模型的局限性很多;例如非人类起源,代谢能力,细胞色素P450同种型活性,种间生理,药物生物利用度和半衰期以及疾病适应机制的显着差异。已证明传统的2D细胞培养系统在研究细胞行为和药物筛选的可能机制方面是有效的,但在维持细胞行为方面存在局限性。一个明显的解决方案是使用三维模型,通过改善细胞的结构支撑,尽可能多地代表人体组织,有助于组织的机械性质(刚性/刚度),并提供灵活的物理环境,以允许重塑响应组织的动态过程。能够反映肝脏ECM的多个方面的唯一3D模型是肝脏ECM本身,除了上述对3D环境的需求之外,已知肝脏的ECM提供生物活性线索以使细胞响应微环境以及作为生长因子的储库。
二、肝纤维化的3D组织培养模型
1. 3D肝球体
目前,3D肝球体的形成在许多实验室中使用多种技术进行,包括使用非粘附材料微粒,这些技术依赖于使用悬滴培养的重力聚集[16],旋转凹96孔细胞驱避板[17],或甚至使用搅拌生物反应器[18]。使用商业上可用的悬滴培养系统(即3D Biomatrix, InSphero)极大地促进了这种培养物的标准化,并且容易获得简单悬滴培养的简易方案[19]。研究人员最近使用超低附着96孔板建立并广泛表征了PHH球状体[17]。蛋白质组学分析显示,这些PHH球状体培养物在表型上保持稳定至少5周,与蛋白质组水平的肝脏相似,甚至保留了个体间的变异性。然而,这些培养物具有一些缺点,例如相对较小(< 200 μm)球状体的繁琐处理和涉及单个球状体染色的劳动密集型分析,需要昂贵的蛋白质组学或mRNA分析以得出适当的结论。
2. 基于微流体的生物反应器培养物
虽然可以通过球体培养或3D生物打印技术(参见肝组织的3D生物打印)部分地重现细胞 - 细胞接触,但使用这些技术不容易建立血管结构和血流。解决方案可能在于微图案化以在结构上组织细胞的接种,而微流体装置可以提供恒定的氧气和新鲜营养物流并且去除产生的代谢废物(作为胆汁的替代)。实际上,由微流体和新兴微加工技术提供的高度受控的生物分子环境可以产生与体内细胞所经历的相当的分子梯度和机械刺激[20]。为了模拟窦周隙,用HUVEC和LX-2细胞接种由两个平板和商业多孔膜组成的生物反应器,设计并通过在LSEC顶部施加流动来受到受控的剪切应力。虽然没有肝细胞掺入该系统,但剪切应力改善了内皮细胞形态并降低了HSC的活化状态,表明流动可能对HSC有益[21]。Frey等人还提出了一种球状培养物和微流体培养物之间的交叉。微流体生物反应器的另一个优势在于它们能够密切监测介质中的氧气,乳酸产生或任何可通过近红外技术测量的参数[22]。
3. 3D生物打印的肝组织
在3D生物打印中,因生物材料,生物化学和活细胞的逐层精确定位,以及功能组件放置的空间控制,可用于制造包括肝样组织的3D结构。从技术上讲,通常使用三种主要类型的印刷:激光引导,基于液滴和挤出生物打印[23]。该组织工程领域主要集中在生物材料的开发,不同的印刷方法和大多数肝细胞细胞系如HepG2的短期表现。最近,使用Insphero板形成的人肝细胞,HSC和库否细胞的基于挤出的3D球体在含有肝脏ECM的水凝胶中生物打印并培养2周。虽然白蛋白和尿素的产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保持相对恒定,但再次没有对HSC存在或活化状态进行表征[24]。生物技术公司Organovo使用了一种稍微不同的方法,该方法优化了最初开发用于制造血管结构的生物打印方法[25]。虽然通过使用这种印刷方法实现的结构不能反映肝脏的细胞结构,但3D生物打印的人肝组织可以长期维持功能性原代肝细胞和静息HSC 。
4. 保留肝脏结构
作为通过使用球状体,生物反应器或使用印刷技术将单独分离的细胞组织组装成有组织结构的替代方案,可以使用另一种方法,其涉及使用精确切割的组织切片或脱细胞组织基质。这个想法使得用这些技术进行肝脏研究或药物筛选的想法变得简单:①精密肝切片(PCLS)是肝脏的最佳代表,维持了细胞间及细胞与细胞外间质的联系,保留了游离肝脏细胞的功能特点和组织的完整性;②脱细胞基质最终可用于在其天然环境中播种人(iPSC衍生的)肝细胞以重建可灌注的肝脏。通过用Krumdieck组织切片机(或任何其他自动化振动切片机)将新鲜肝脏切成200 ~ 250 μm厚的切片来获得PCLS。随后可以在烧瓶或多孔板中在温和旋转下培养肝切片[26]。这种PCLS培养物已经在短期培养中用于模拟16 h CCl4暴露后的HSC活化,并通过基因表达谱分析这些切片对CCl4和对乙酰氨基酚的反应[27]。此外,肝脏和肠切片在微流体装置中的整合允许体外评估组织间相互作用。可通过证明胆汁酸鹅去氧胆酸诱导肠道切片中FGF15的表达,随后导致肝脏切片中CYP7A1的下调[28]。
全器官脱细胞技术允许3D器官生物支架的生产与内在血管网络的保存。这种相对较新的技术基于顺行(通过门静脉)或逆行灌注(通过下腔静脉)通过肝血管系统和脱细胞剂,同时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3D结构。大多数全肝去细胞化技术基于用洗涤剂(例如十二烷基硫酸钠和/或triton X-100或脱氧胆酸钠,与磷脂酶A2[170]脱脂组合),DNase和RNase冲洗肝脏。已经很好地研究了肝脏脱细胞基质(DCM)的产生,并且已经开发了许多产生适合细胞培养的DCM的方案[29-30]。
5. 细胞片堆叠
细胞片工程是一种独特的无支架组织工程方法,使用聚N-异丙基丙烯酰胺(PNIPAAm)接枝,温度响应培养皿(TRCDs)。 可以通过将温度响应性PNIPAAm凝胶植入标准组织培养聚苯乙烯皿中来开发温度响应性培养表面。在低温(20 ℃)下,材料表面变得亲水并且细胞不能附着。 相比之下,在37 ℃时,壳变得疏水,细胞可以附着并在表面上增殖。因此,可以在无酶处理(例如胰蛋白酶)的情况下,仅通过降低温度,获得在表面上扩增的细胞。 同时细胞之间的相互作用仍然保留,并且几层细胞片可以组装在一起,以构建更复杂的3D结构[31-32]。 然而,由于缺乏血管形成并因此缺氧,该系统仅能在短时间内使用。 相比之下,类似的细胞片模型含有脐带血衍生的内皮细胞集落形成细胞(ECFCs),夹在成纤维细胞片之后,在体内移植1周后重建血管前三维细胞密集组织构建体并形成功能性微血管[31]。
三、结论
目前,虽然在体外肝脏培养和3D肝脏培养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但尚无有效的抗纤维化治疗方法。这些体外模型的优化将导致新的目标和寻找抗纤维化合物的新时代。此外,需要研究更接近肝脏微环境的体外培养模型的改进。 因此,研究工作将继续优化由单一和/或共培养平台组成的3D生物系统。诸如HSC的非实质细胞增加了由合成和生物衍生材料制成的3D生物系统中肝细胞的活力和功能。 最终,为学术界和制药行业的研究人员设计常规的3D细胞培养系统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