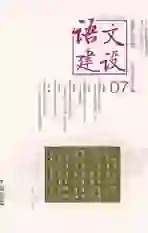亦谐亦庄,情志交融
2018-01-25孙绍振
孙绍振
《我的书斋》全文意趣盎然,文脉之中具有强烈反差,甚至是悖理:明明是一个简陋的场院,根本不是书斋,不但要说成是书斋,而且认为胜过建筑华美的书斋;明明连桌子都没有,只是木板和椅子凑合搭成的勉强可以书写之处,硬说成胜过文人雅士的书桌;明明是半小时就要追随木瓜树影移动方能写作,却乐此不疲,说是比之在书斋更自由;明明是连遮风挡雨的屋顶和墙壁都没有,偏偏要说是世上所有的最雅致的书斋都比不上。这一切,在通常情况下是不可信的,不现实的,但是,读者却能感受到作者抒情的趣味。
其抒情的第一个特点是主观的,不是客观的,不是实用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因为友情深厚,巨大的物理空间距离也会缩短到紧贴身边。“记得绿罗裙,处处怜芳草”,因为所爱之人的裙子是绿色的,故对天下所有青草都生怜爱之情。其抒情的第二个特点是逻辑有极端。“情人眼里出西施”,自己所爱的人,就是最美的。“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杨贵妃回首一笑,再看后宫佳丽,就一个个面色苍白了。极端的,也就是片面的。“月是故乡明”,同样是不全面的。全面了,故乡和他乡月色一样明,很理性、很全面,却没有诗意了。
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说,钟理和把自己只能在木瓜树下写作说成是最美好的,比之“案头有一盆古梅,壁问悬有名人的书画”的雅室还精彩,是抒情的。这种抒情很值得深入分析。
首先,对于一个献身于文学的人来说,连书房、书桌都没有,只好到院子追逐木瓜树影写作,是极其无奈、极其狼狈的,然而,作家却写得怡然自得,美好无比。这说明作家对于物质条件不在乎,超越了物质的实用价值,浸沉于主观的情感价值,在美学上叫作审美价值。按康德的说法,审美的情趣判断,是非实用的、超功利的。正是因为如此,这不是书斋的书斋,使他的心灵获得了超越物欲的自由,发现了精神上最高层次的美:
我极高兴自己的发现,它实在太关了。在那里写东西既写意、又痛快……就是世上所有的建筑得最华关最富丽的书斋,都不会比它更好吧!
特别不可忽略的是,文章写的是“发现”,这里的“发现”,实质上是内心感受的升华。按马斯洛人本主义心理,人的最低需求是生存需求,因而情感是被生存需求压抑的,为了满足于物质的生存需求,人们不得不坚守理性,暂时放弃情感,长期的压抑和放弃就变成潜意识了。但是,一味满足物质需求、绝对理性的人并不是完全的人,或者说只是半边人。故在满足了生理需求以后,人们又通过文学艺术把情感唤醒,既有理性又有情感,二者平衡才是完整的人。钟理和在物质需求还不能基本满足的情况下,却能超越了物欲,获得了情感自由,因而显得特别难能可贵。
值得深究的是,情感是非理性的,能不能一味胡言乱语呢?有没有一定的逻辑呢?有没有某种特殊的因果性呢?有的。四周墙壁的阙如,提供了极其广阔的视野:“壮大的山河,深邃悠远的蓝天,阡陌横斜的田野”尽收眼底,无四壁的场院优越在对大自然欣赏的方便。这显然是片面的,完全忽略了书斋最起码的遮风挡雨功能。“明窗净几,雕金饰玉”的书斋,从实用角度来说,对于写作不但方便,而且高雅舒适,这是现实的实用价值。作家的情感无视于这种现实的实用,把心灵的视野放在生理的实用之上,将情感的享受放在第一位,作家要进入这种审美的境界,就不能不片面,不能不强调其一不及其二了。
因为在山腰,居高临下,前边的山川、田园、村庄、云烟、竹树、人物,尽收眼底,眺望绝佳。你的书斋把你局限在斗室中,使你和外界隔绝;而我的书斋既无屋顶又无墙壁,它就在空旷伟大的天地中,与浩然之气相往来,与自然成一整体。
作家把平日熟视无睹的风光、田野耕作的平凡琐屑,变成了“伟大壮观的图画”,把这一切自然景观和心灵解脱交融起来,变成情感的美的享受。如果有人抬杠说,有了华贵的书斋,只要走到山坡散步,不是一样可以欣赏四周一望无垠的景观吗?在空场地上写作不是有许多不方便吗?比如下雨,等等。那就是不懂得文学的审美情感背后的理念了。在这种极端的、片面的抒情背后,表现了作家不为自己的贫困而自卑、气馁,不以写作为苦,相反,即使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只要能写作,就是快乐的。超越实用性,进入审美境界,表现了作家对于文学使命的执著,哪怕是勉强能写作,哪怕是艰难竭蹶,也乐在其中。这种乐如果仅仅是生理的,那还是低层次的,这里表现的境界是精神的高度。
在作家笔下,这种高度达到了诗的境界:作家说自己从景观中感到的是“一首宇宙的诗”。这不仅仅是外在宇宙的,而且是内在的“浩然之气”,与“伟大的天地”相往来,进入了“与自然成一整体”的境界。
这样的境界,就不完全是情感性质的了,而且有着某种主客观交融的深度,既令人想到孟子的“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又令人想到庄子“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的哲思。这种哲思对于抒情来说是可贵的,缺乏哲思的抒情由于片面化,容易流于肤浅、滥情,有了这样的哲思,情与理就有了某种交融,文章就深沉了。
这种深沉表现为作家对于贫困的、艰难的物质生活的超越,对于精神生活的坚持。“只要有一堆树影,再加上一张藤椅,一方木板,我就有书斋,就可坐下来写字,再不必为阴暗的屋子和摇摆的桌子而伤心了。”本来前文说过,回顾当年的贫困是令他“再伤心不过的”,但有了文学写作的起码条件,他就超越了“伤心”,进入了“与自然成一整体”的精神境界。作家强调,这种境界不是一时的感兴,而是持久的,即使有了挫折,也不会改变。“木瓜树在去年那几阵台风中不是被吹折,便被吹倒,一株不留。但马上我又往回种下几株小的,并且种得更靠近庭子,现在已三尺多高,也许到了明年冬后,它就会给我几堆深厚凉爽的阴影,于是我又将领有我那上好的书斋了。”他的乐观,他的信念,是坚定的,又不是剑拔弩张的,而是恬淡的,即使遭遇挫折,须待以时日方能恢复,他也是宁静的,在宁静中表现了他的坚韧。
然而,本文的趣味,似乎还不仅仅在情思,还有情思不能完全涵盖的趣味,那就是作者反复强调的极端的反差、极端的矛盾。最贫困的向最豪华的转化,最不方便的向最舒适的转化。这似乎是不合逻辑的,但又是很有趣的。这种趣味,就不仅仅是情趣,情趣的诗意是和谐的,而这产生于一系列的不和谐、不统一,在汉语里属于谐趣,在西方叫作“不一致”,英语为“incongmiiy”,属于幽默范畴。
如果文章仅仅是最简陋和最美的不统一,那就是滑稽,层次就低了。文章之所以幽默,是因为在从最简陋向最美好转化时,有一种精神上的条件,那就是他的坚忍不拔、安贫乐道。这应该可能向诗意发展,但是在行文中写到自己的时候,并不一味诗化,反而相当夸张地把自己写得很狼狈。如写他家的旧饭桌:
它在我家已经是四代功臣了;桌面二处破洞大得几乎碗都漏得下;两只桌脚已腐朽得不得不拿木头绑住。
这里语言功力相当可观,一是细节的雄辩性(桌上的破洞,桌腿的腐朽),二是以褒义词写负面事(“四代功臣”),这种语义的“错位”是典型的幽默语言。更幽默的是,夸张自己的穷困,说到自己“发现”了豪华的“书斋”,并不是因为自己“开得金矿,变成大富翁”,而写到在残破的桌子上写作的狼狈:
我便在这上面写东西。姑勿论它给我的不方便有多么大,单说它那像摇篮似的摇摆不定,就够使人难过。你必须时刻留心,稍一疏忽,或撇笔时稍用点劲,它便摇摆得吱吱作响,使你心惊胆战,说不定你的灵感便会因此骇跑得一去不回头,是再伤心不过了。
這里的特点,不仅仅是以细节的雄辩强调设备的不堪,而且是自己心灵效果上的严峻:写作最可贵的灵感因而被骇跑,而且不可挽回。这在幽默学中,叫作自我调侃。这种功夫和抒情相反,不是诗化,而是贬低,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丑”化自己。正是因为这样,文章不但有情趣,而且有智趣和谐趣。三趣合一,亦庄亦谐,情志交融地建构了作家乐观、坚韧、恬淡的精神风貌。作家在开头说:
一个文人大抵都有一间书斋,就像一位将军有他的办公厅,工程师有他的设计室,木匠有他的工作房。那里面的摆设和装潢都按着他的个性、趣味和审美观点加予调剂,一切都配合得十分得体,他在那里面或工作、或休息、或坐下来冥想,都感到自由、舒适和安宁。
整篇文章写的是他的不成书斋的书斋的每个特点,却同样“按着他的个性、趣味和审美观点”“配合得十分得体”。他还说,“如果一个文人没有他的书斋”,“也许他将永远得不到安全和宁静之感吧”,然而,他恰恰是在不成书斋的书斋中“享受着安全宁静之感”。从这里,读者不难感到其中隐含着的缘由:作家高雅的审美趣味和自由的精神风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