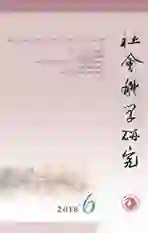农民工的城市经历:改革开放后的茶馆观察
2018-01-22王笛
〔摘要〕 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从农村来城市的“流动人口”的大量增加,经济的飞速发展, 以及“全民经商”浪潮,城市大拆大建等等因素,都影响着人们的日常生活。日渐宽松的经济和公共生活环境,使得茶馆这个成都持久的文化象征,再次得以复兴。 在某种程度上说,茶馆的归来,可以视为改革开放以后私营小商业蓬勃发展最具有代表性的标志。这个研究显示了城市的传统行业是怎样在现代化、商业化、国际化的大潮中发生转变的。本文中的这些故事,说明即使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生了大变动,传统因素仍然会在相当的程度上保存下来。
〔关键词〕 茶馆;流动人口;农民工;算命先生;挖耳匠;擦鞋女;城市生活
〔中图分类号〕K27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769(2018)06-0137-09
①Li Zhang,Strangers in the City:Reconfigurations of Space,Power,and Social Networks within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关于流动人口,还可以参见Michael Robert Dutton,Streetlife China(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John Friedmann,Chinas Urban Transition(Minneapolis: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5).邵勤(Qin Shao)的《上海的消失》是关于上海拆迁和重建的最新研究成果,这本书探索了上海拆迁运动中的家庭和个人经历,见Shao Qin,Shanghai Gone:Domicide and Defiance in a Chinese Megacity(Lanham:Rowman&Littlefield; Publishers,Inc,2013)。
〔作者简介〕王笛,暨南大学客座讲座教授,澳门大学特聘教授,广东广州 510632。
近年来关于改革开放以后城市、城市生活和城乡关系的研究,多是由人类学、政治学和社会学家所完成的。他们考察了城市人口的变化、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以及从社会主义的理想主义到社会契约关系。他们关注工人、公务员、知识分子以及女性,探索女性的工作与生活经历与她们对经济、性别不平等的回应,关注劳资关系、政治参与、公众对变化的反应、女性的工作机会与女性在城市与农村家庭中的地位等等。〔1〕此种取向的另一个重要主题是:他们发现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最突出的变化是大量的流动人口与城市的拆迁和重建。每年一亿多的“流动人口”,加上经济文化与社会网络的飞速发展,以及“全民经商”浪潮,都造成了国家对社会人口的控制逐渐地被削弱。①其实,我认为,这些也是历史研究应该关注的问题,也需要历史研究者做出相应的回答。
在改革开放时代,由于政治环境的变化,国家减少了对小企业和小商业的控制。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在讨论这种转变时写道:“政府现在不再为人们提供道德的指南。当代中国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国家道德权威的削弱和精神上的满足。”〔2〕改革开放以后,地方和国家层面上政治和经济都有一定的变化,1980年代的“全民经商”浪潮,大规模的农民工入城,国有企业的重组,城市大拆大建等等因素,都影响着人们的公共生活。尽管如此,中国商业文化持续发展,市场持续扩张,“市场像是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着人们”。〔3〕
①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研究非常丰富,全面的研究见Hungdah Chiu,“Socialist Legalism:Reform and Continuity in Post Mao Communist China”,Issues and Studies,1981,no.11,pp.45-75;Elizabeth J.Perry,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form in PostMao China(Cambridge,MA: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Harvard University,1985);Tang Tsou,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PostMao Reforms:A Historical Perspective(Chicago,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6);Harry Harding,“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PostMao China”,in A.Doak Barnett and Ralph N.Clough,eds.,Modernizing China:PostMao Reform and Development(Boulder,CO:Westview,1986),pp.13-37;Vera Schwarcz,“Behind a Partiallyopen Door: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PostMao Reform Process”,Pacific Affairs,1986-1987,no.4,pp.577-604;Paul Cohen,“The PostMao Reform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88,no.3,pp.518-540;Nina P.Halpern,“Economic Reform,Social Mobilization,and Democratization in PostMao China”,in Richard Baum ed.,Reform and Reaction in PostMao China:The Road to Tiananmen(London:Routledge,1991),pp.38-59;Merle Goldman and Roderick MacFarquhar,The Paradox of Chinas PostMao Reforms(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关于经济改革,见Dorothy J.Solinger,From Lathes to Looms:Chinas Industrial Polic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1979-1984(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Dorothy J.Solinger,Chinas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Statist Legacies and Market Reforms,1980-1990(Armonk,NY:M E Sharpe Inc,1993);Jean C.Oi,“The Role of the Local State in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China Quarterly,1995,no.144,pp.1132-1149。關于教育改革,见Mariko Silver,“Higher Education and Science Policy in Chinas PostMao Reform Era”,Harvard Asia Quarterly,2008,no.1,pp.42-53。关于改革开放以后城市的变化,见Carolyn Cartier,“Urban Formation in the Reform Era Chinese City:Landscapes from Shenzhen”,Urban Studies,2002,no.9,pp.1513–1532;Piper Rae Gaubatz,“Urban Transformation in PostMao China:Impacts of the Reform Era on Chinas Urban Form”,in Deborah Davis Richard Kraus,Barry Naughton,and Elizabeth J.Perry eds.,Urban Spaces in Contemporary China:The Potential for Autonomy and Community in PostMao China(New York,N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p.28-60。关于改革开放时代的家庭生活,见Deborah Davis and Stevan Harrell,eds.,Chinese Families in the PostMao Er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对改革开放后成都的研究,见D.J.Dwyer,“Chengdu,Sichuan:The Modernisation of a Chinese City”,Geography,1986,no.3,pp.215-227。
②Dittmer and Gore,“China Builds a Market Culture”,East Asia,2001,no.3,pp.39-40。关于后毛泽东中国的小商业研究,见Thomas B.Gold,“Chinas Private Entrepreneurs:SmallScale Private Business Prospers under Socialism”,China Business Review,1985,no.6,pp.46-50;Martin Lockett,“Small Business and Socialism in Urban China”,Development and Change,1986,no.1,pp.35-68;Mohammad A.Chaichian,“The Development of Small Business and Petty Commodity Productio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Asian Profile,1994,no.4,pp.167-176;Jinglian Wu,“The Key to Chinas Transition:Small and Midsize Enterprises”,Harvard China Review,1999,no.2,pp.7-12;Waisum Siu and Zhichao Liu,“Marketing in Chinese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SMEs):The State of the Art in a Chinese Socialist Economy”,Small Business Economics,2005,no.4,pp.333-346;Thomas C.Head,“Structural Changes in Turbulent Environments:A Study of Small and MidSize Chinese Organizations”,Journal of Leadership&Organizational; Studies,2005,no.2,pp.82-93;Atherton Andrew and Alaric Fairbanks,“Stimulating Private Sector Development in China:The Emergence of Enterprise Development Centres in Liaoning and Sichuan Provinces”,Asia Pacific Business Review,2006,no.3,pp.333-354;Cunningham Li Xue and Chris Rowley,“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in China:A Literature Review,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and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Research”,Asia Pacific Business Review,2010,no.3,pp.319-337.
改革开放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也为茶馆的复苏和行业规模的扩大,提供了适当的经济和社会环境。①许多成都居民和外来者发现,开茶馆可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对于没有太多资本的人来说,他们可以开一个小茶馆为生;对于那些想要大生意的人来说,一个高端茶馆则是更理想的投资。改革鼓励人们“发挥主观能动性去致富”。〔4〕中国最高的政治决策者创造了一种有利于小商业发展的商业环境,1987年出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扫除了鼓励私营经济在意识形态上的障碍;1999年宪法修正案赋予了私营商业与国有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一样的平等合法的地位。这一切的政治和政策上的改变,都进一步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
由于一系列政策的刺激,中国的小商业逐步走向繁荣。1996年,在920万个极小商铺中(即那种只有几个雇员的铺子),大概有780万个属于私营,120万个属于集体所有,占零售行业总销售额的28%。②但是我们应当看到,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形成完全的“市场经济”,正如苏黛瑞(Dorothy Solinger)所指出的,中国经济“还存在着许多类似于计划经济的结构性问题。”〔5〕小商业对计划经济的依赖最小,当计划经济被削弱后,茶馆便抓住了这个机会,得到发展壮大。随着国家对日常生活控制的放松,人们愈加积极地赚钱致富,以提高物质生活的水平。日渐宽松的经济和公共生活环境,使得茶馆这个成都持久的文化象征,再次得以复兴。对改革开放后中国茶馆的研究多为中文,主要是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进行探讨,见吕卓红《川西茶馆:作为公共空间的生成和变迁》,北京:中央民族大学未刊博士论文,2003年;戴利朝《茶馆观察:农村公共空间的复兴与基层社会整合》,《社会》2005年第5期,96-117页;余瑶《茶馆民俗与茶人生活:俗民视野中的成都茶馆》,上海:上海大学未刊硕士论文,2007年,等等。在某种程度上说,茶馆的归来,可以视为改革开放以后私营小商业蓬勃发展的最具有代表性的标志。
一、小商业、茶馆和农民工
在改革开放时代,开茶馆比晚清以来的任何历史阶段都要容易。在民国时期,茶社业公会严格控制着茶馆的总数,以避免恶性竞争,甚至售茶价格的浮动,也必须得到其允许。关于民国时期对茶馆数量的控制,见Di Wang,The Teahouse:Small Business,Everyday Culture,and Public Politics in Chengdu,1900-1950(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chap.2。但在改革开放时期,只要有足够的资本,就能申请营业执照。与其他行业不同,茶馆需要的投资不大:租一间屋,购置一个开水炉、一些桌椅和茶碗便可以开业。在小一些的茶馆,一个人可以身兼数职,既当经理,又当服务员和烧水工。当然,高档茶馆则需要更多的投资。在一个短时期内,成都的茶馆便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比民国时期最高峰还要多得多。民国时期,根据統计,茶馆数量最多的是1934年,总数有748家(Wang,The Teahouse:Small Business,Everyday Culture,and Public Politics in Chengdu,1900-1950,p.30)。当然,这也使茶馆间的竞争变得更加剧烈。
在改革开放时期,街角小茶铺与高档茶楼并存,它们为不同的社会群体提供服务,发挥着各自不同的功能。这时,除了上面没有一个行业公会的控制之外,茶馆的运营与管理与20世纪上半期相比较,几乎没有本质的不同。关于改革开放后政府对社会的控制,见Manoranjan Mohanty,“Party,State,and Modernization in PostMao China”,in Vidya Prakash Dutt ed.,China,the PostMao View(New Delhi:Allied,1981),pp.45-66;Lieberthal Kenneth and David M.Lampton,Bureaucracy,Politics,and Decision Making in PostMao China(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Gordon White,“The Dynamics of Civil Society in PostMao China”,in Brian Hook ed.,The Individual and the State in China(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196-221;Jean C Oi,“Realms of Freedom in PostMao China”,in William C.Kirby ed.,Realms of Freedom in Modern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p.264-284;Minxin Pei,“Political Change in PostMao China:Progress and Challenges”,in Galen Carpenter and James A.Dorn eds.,Chinas Future:Constructive Partner or Emerging Threat(Washington D.C.:Cato Institute,2000),pp.291-315;David Shambaugh,“The Chinese State in the PostMao Era”,in David Shambaugh ed.,The Modern Chinese State(Cambridge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p.161-187。茶馆作为一种小商业,有着自己的一套经营方法。 一方面,它们受到国家整体经济状况的影响;另一方面,它们有着很强的地域性。关于改革开放后对私营商业的管理,见Hill Gates,“Owner,Worker,Mother,Wife:Taibei and Chengdu Family KLBusinesswomen”,in Elizabeth J.Perry ed.,Putting Class in Its Place:Worker Identities in East Asia(Berkeley: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1996),pp.127-165;Hill Gates,Looking for Chengdu:A Womans Adventures in China(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9);WaiSum Siu,“Chinese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A Tentative Theory”,in FrankJürgen Richter ed.,The Dragon Millennium:Chinese Business in the Coming World Economy(Westport,CT:Quorum,2000),pp.149-161;WaiSum Siu,“Small Firm Marketing in China:A Comparative Study”,Small Business Economics,2001,no.4,pp.279-292;Yen Benjamin and Phoebe Ho,“PGL:The Entrepreneur in Chinas Logistics Industry”,in Ali Farhoomand ed.,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Hong Kong:A Casebook(Hong Kong: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05),pp.230-243;Fang Lee Cooke,“Entrepreneurship,Humanistic Management and Business Turnaround:The Case of a Small Chinese Private Firm”,in Ernst Von Kimakowitz,Michael Pirson,Heiko Spitzeck,and Claus Dierksmeier eds.,Humanistic Management in Practice(New York,NY:Palgrave Macmillan,2011),pp.119-130。与民国时期不同,由于没有行会控制成都茶馆的数量,新茶馆的数量大幅度地增加。那些小本生意人,开办一个茶馆几乎没有什么障碍,通过简单的营业执照申请和注册,便可开业。当然他们还需要得到成都不同政府机构的批准,如商业局、工商行政局、卫生局等颁发的各种许可。得到这些许可,他们一般只需要提供一些基本的信息,如住址、经营者姓名、服务类型等。例如,在成都石人南路的清芳茶园,墙上贴了三种许可证书:“消防安全许可证”“税务登记证”和“个体工商户经营执照”。另外,墙上还贴有“成都市门前‘三包责任书”“消防安全要求”以及“成都市爱国卫生‘门内达标责任书”等。作者在石人南路清芳茶园的考察,2000年7月13日。但同時,成都还存在大量未注册的茶馆,它们往往以诸如“社区中心”“俱乐部”“活动室”等名目而存在,提供所谓的“内部服务”,也有许多位于僻静的小街小巷,以及城乡接合部等政府难以监管的地区。总而言之,几乎所有的茶馆都在经济改革的“黄金时期”,搭上了小商业发展的“顺风车”。
茶馆为农民工提供了许多工作机会。从对街头来来往往的人们和这个茶馆主人和客人的活动的观察,我们可以了解许许多多茶馆和人们日常生活的丰富信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小茶铺和邻里、过路人,以及来来往往的小商小贩,都有着某种程度的联系,由此我们看到来自社会各阶层、各行业的人以不同的方式相互联系和依存。我曾经考察过由一对农民工小夫妻经营的茶铺,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工作空间和个人生活空间,是基本没有区分的。茶馆既是他们经营的生意,也是他们日常生活的场所,他们在这里和顾客聊天,做饭和吃饭,一方面则打理生意。他们的家庭生活就展现在顾客的眼前,不过顾客们似乎对这些已经习以为常,很少对他们的日常生活产生特别的兴趣。这样,街道、茶馆和城市里的人联系在一起,在这样的茶铺里,私人生活空间和公共空间的界限十分模糊。这种空间使用功能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无疑使茶馆主人在做生意的同时,家庭的纽带也得到紧密的维系。这生动地展示了城市繁华背后的普通百姓生活。
许多农民工都没有与他们的家庭生活在一起,所以茶馆是他们消磨时光、休闲娱乐的最佳场所。1980年代和1990年代港台电影和电视剧在大陆日益流行起来,特别是武打片很受欢迎,许多小茶馆为了吸引顾客,都提供录像放映服务,甚至成为了这些小茶馆的主业,逐渐演变成为了录像厅。这些录像厅的顾客大都是年轻的外来打工者和农民工,要不就是中小学生。关于农民工的研究,见Dorothy J.Solinger,Contesting Citizenship in Urban China:Peasant Migrants,the State,and the Logic of the Market(Berkeley and Los Ang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 與传统的茶馆不同,这些茶馆的椅子不是围着桌子,而是像影院一样,把竹椅排成行列,方便顾客们观看电视。在晚上,这些录像室里坐满了观众。外来打工者多是单身在城市打拼,晚上无事可做,录像厅便是非常理想的打发时光的去处。1990年代,花几元钱便可以在茶馆录像厅里喝茶和看片,而且没有时间的限制。〔6〕
到2000年,成都仍有许多这样的录像室,成都市档案馆附近的“李小龙录像牌茶”便是其中之一。这个茶馆条件很简陋,竹棚外悬挂着一个大大“茶”字,一个大木板立在门前,上面贴着各种影片和电视剧的封面,顾客可以很方便选择他们想看的片子。一杯茶加上看录像只需1元钱,当然茶是质量很差的低档茶。茶馆里面小且昏暗,椅子有五排,每排六个位子,分两边,中间是过道,共不过容纳30个顾客。 每排两边各有一个小圆凳子,被用作桌子放茶杯。室内的墙上贴满了影碟的封面,大部分都是港台和美国片,如李小龙、成龙、施瓦辛格等主演的动作片。我看到里面只有五六个顾客,都是二三十岁的样子,听他们的口音和衣着,是外来打工者。老板是位中年妇女,看起来很悠闲,和几个人在店门口打麻将。当我到那的时候,这家茶馆正在放映一部喜剧。这部喜剧是关于古代人和现代人以及警察和流氓的冲突的穿越剧。作者在成都市档案馆后门李小龙录像牌茶室的考察,2000年8月8日。
录像厅的出现,反映了随着科技的发展,给人们日常生活和娱乐所带来的改变。电视和录像机逐步取代了茶馆里的地方戏和其他形式的演出,茶馆经营和提供娱乐的方式也与过去大大不同。人们从观看舞台上的演员,到看眼前的电视机。对茶馆而言,成本下降了,放映节目的时间更灵活了,节目也更丰富了。在过去,能提供娱乐演出的往往是场地宽敞、客源充足、且有一定规模的茶馆。但现在,即使是规模最小的茶馆也能为顾客提供丰富的节目。大量的流动人口和城市低收入人群,在快速现代化的城市中,找到了适合他们的廉价的消遣活动。
二、农村来的算命先生
像茶馆中大多数的职业一样,算命与茶馆的互相依存有着长期的历史,并创造了其独特的文化。这种文化在改革开放以后,又有了持续的发展,并适应新的社会和经济的需要,甚至成为一些茶馆中必不可少的点缀物。
①下面关于这个算命先生的信息,基于作者在成都府南河边茶馆的考察,2000年7月10日。
在对茶馆的考察中,我曾多次与算命先生交谈。2000年夏天,我在成都府南河边的一家茶馆考察时,遇到过一个年老的算命先生。①他拿着一把竹签问我算不算命,5元一次,可以相面,也可以根据抽签算命,8元一次。我要他先说说我的过去,“看看你的本事”。他问了我年纪,又看了看我的面和手,说“你95年和98年有凶”,我说“不准”。他说“你要么95年,要么98有凶”,我告诉他“这两年我都有喜事”。他又说:“你眉毛稀散,你一生一定很清闲”,我笑着回答:“错了,我一生都忙得很,你以为我在这里坐茶馆,就是清闲?”我告诉他不用给我算了,讲讲你自己的故事,算命钱照付。他告诉我从湖北来,在这里算命三年。的确,这位老人一口湖北口音。他时年71岁,原是农民,只读过几年私塾,后来自学算命,从1980年代便开始这个营生,说着从包里拿出一本皱巴巴的《神相全书》,系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他表示现在算命生意不好做,不过最好的时候一天可挣40元左右。如果顾客对算命满意,最多给过20元钱。当他正和我交谈时,见一位长发长须、有点道士风度的算命先生走过来,他并不理睬那道士,那道士一转身便慢慢离去。我猜想道士可能避免两人同在一起揽生意,便有意不到这边地盘。
我付了他5元算命钱,告诉他想去揽别的生意随时可去,如果想跟我再聊聊,我也欢迎。他说“看你眼睛有神,像是有学问的人,你一定是从文而非从武”。我说这谁都能看出。我又问他能不能看出我是从事什么职业的,他猜道“老师?”我笑道,“这是你第一次说对了。”聊了一阵,他说要回去拿本书来,大约个把小时回来,书中有些地方不大看得懂,想请我帮忙。我说可以等他回来,说罢他便急匆匆离去。大约一小时后,他又匆匆回来,从包里摸出一本皱巴巴的书,我见封面印着《鲁班全书》,是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他翻到其中一页,上面有图形和文字解释,大意是钉“善牌”在门上可使邻里和睦,并讲了该牌有多大,怎样钉等,钉什么位置等。书页中的解释都是文言文,无标点,印刷十分粗糙,显然是盗版书。文中时称“兽牌”,时称“善牌”,显然“兽”是“善”的误印。我将有关内容,根据我的理解,给他解释了一个大意。由于我下午还有其他事情,不能久留,便告辞离去。那算命先生似乎意犹未尽,问:“还来茶馆坐坐吗?”我答曰“有空时会来的”,但是可惜没有机会再到那家茶馆了。
这些算命先生故事,为我们提供了在茶馆中谋生人群的大量信息。首先,他们多是来自于乡村的农民工。他们利用算命作为谋生的手段,虽然不是很熟练。只要能识字,他们便稍加自学,随后立马开始从业。虽然挣得不多,但至少也能在新的环境中求得生存。其次,男性占据着传统的算命行业,但改革开放后,女性也开始从事这行,反映出社会对女性进入传统男性主导行业的容忍度越来越高。再者,算命先生也有等级,有些名声响,收费高,甚至可以以此致富,但大多数仅仅糊口而已。最后,算命为茶馆顾客提供了娱乐,并非所有付钱的顾客,都相信算命先生所说,他们中不少只是寻求消遣,或希望算命者祝福他们的未来,也就是讨一个吉利。正如司马富(Richard Smith)指出的,“算命渗入了中国社会从皇帝到农民的各个层面。”〔7〕帝制的覆灭没有改变这个传统,虽然在激进的革命年代他们很难生存,但是改革开放以后,他们便很快得到复苏,日子也越发好过起来。
三、老行道进入新时代
挖耳匠(又叫采耳师、挖耳师、掏耳朵师傅、掏耳匠等)是茶馆中一个有悠久历史的职业,从晚清至民国时期,成都几乎每一个茶馆中都有掏耳朵匠。1949年以后,他们也仍然在茶馆谋生,只是和茶馆一样,数量大大减少,“文革”时期跌至谷底。改革开放后,挖耳匠随着茶馆的复苏,也逐渐回到茶馆。他们大多数是农民、手工匠或小贩,他们来自农村,在城市里找不到其他合适的工作,只好以此为生。这是一项技术活,但至少比做重体力劳动要轻松一些。过去这是男性的职业,但在20世纪末,女性也逐渐进入了这个行当。
成都顺兴老茶馆里的掏耳匠大概三十岁左右,来自川南的一个小镇,从事这项营生已经七八年。他1990年代初来到成都,首先是在府南河边的茶馆里为顾客服务,每月挣得大约1000元,交给茶馆200元作为场地使用费。当顺兴老茶馆开业后,老板知道他手艺不错,于是请他来这里服务。他每年要付给茶馆六七千元,虽然他挣得并不比在府南河边的茶馆多,但是他说这里环境比以前好多了,有空调,不受日晒雨淋冷热之苦。他穿着白褂,胸前挂有一牌子,上面写着基本价10元,若用一次性工具20元。他说顾客多是成都本地人,因为外地人不习惯掏耳朵。其中大多数又是中青年,因为老人觉得价钱太贵。这个茶馆与旅游单位有合作联系,有些外国游客也找他掏耳朵。他还会按摩,全套可收取四五十元。①
①作者在成都会展中心顺兴老茶馆的考察,2000年7月22日。
③作者在成都人民公园鹤鸣茶社的考察,2003年6月28日。
据2006年关于成都人民公園鹤鸣茶社的一个考察,李姓挖耳匠在茶馆里已经干了三年了,之前他开了一家装修店,因经营不善而倒闭。尽管刚开始做掏耳朵营生时,生意清淡,但随着他手艺的提高,便有了不少常客。因为这份工作全年都可以做,所以只要够勤奋,每天去茶馆,每次收费10元,每天可轻松挣一两百元。这与我六年前的考察相比,他们的收入已经大大提高,但是基本价格(每次10元)没有变,可能是客源增加了。据这个考察,一般来说,一位掏耳朵匠只在一家茶馆揽客,要给茶馆交费(李先生是60元一个月,720元一年)。为了避免冲突,保护自己的生意,掏耳朵匠不可以进入他人的地盘。周末和节假日的生意很好。在春节的那一个月里,他便挣了3900元。〔8〕
鹤鸣茶社里至少有四个挖耳匠,其中一位问我是否需要挖耳。当我表示他的工具似乎不太卫生时,他说工具没有问题。然后,他去为一位年轻的女士服务了,那位女士与她的家庭成员一起坐在邻桌。大概因为那位女士体验愉快,她的一位家人叫了另外一位挖耳匠服务。我发现当茶馆工人忙碌时,其中一位工人叫挖耳匠们帮忙搬椅子。其中一位挖耳匠告诉我,他们会在茶馆需要时帮忙。②
在成都大慈寺的文博大茶园内也有一位住场挖耳匠,看起来四五十岁,他手里拿着一只金属掏耳夹,一边用手弹着清脆的金属声音,一边在桌子间来回揽生意。显然,他与茶馆的工人很熟,当他没有生意时,就和他们坐在一起喝茶。如果顾客付钱时找不开,他便拿着张大票子去找掺茶师傅换小钱。他说之前在理发店干了几年,17岁时跟着父亲学了这门手艺,然后在文博大茶园工作了九年。这位挖耳匠还把手艺传给了他姐夫,现在府南河边的一家茶馆谋生。他说学徒必须学习一年后,方能独立工作。
他住在成都郊区的双流县,每天骑摩托车往返,把车放在二环路他姐姐家,因为外县的摩托不让进城。他和妻子每天中午去大慈寺附近的小餐馆吃饭,只吃稀饭馒头,两人才1.5元。他们进大慈寺也不需要门票(1元钱),门房认得他们。他在文博大茶园从早上9点做到下午,当下午四五点钟,这里生意不好的时候,他会到府南河边的茶馆揽生意。在那里,他不用给茶馆交钱,不过得和其他同行竞争。
他回忆说,9年前他只收1.5元,但现在新客户收4元,回头客收3元。服务时间不超过10分钟。这项工作不需要营业执照,只需每月5号向茶馆交200元即可,他从来都是按时缴纳。他称这个茶馆是他的地盘,如果其他同行想进来,会被茶馆工人赶出去。他每月可挣六七百元,向茶馆交费后还剩四五百元。他的妻子在茶馆里替人擦鞋,一双鞋收费一元,每月也可挣五六百。他有时会遇上蛮横顾客拒绝付钱。有一次,他给三个年轻人掏耳朵,但那三人说对他的服务不满意,拒绝付账,引发了纠纷,还有人受了伤。他当时很生气,掀翻了他们的桌子,打翻了茶碗,在其他茶工的帮助下,把那三个年轻人送到派出所,他们不得不付了12元的服务费和8元的损失费。
他使用五种挖耳工具。大金属夹子是他的招牌,招揽顾客时便弹出声来。一个是细长有柄的刀子,因为耳朵有汗毛挡住视线,先用其去毛。 最重要的工具是“启子”,为一细长的铜片,用来刮内耳壁,给人以舒服的感觉。一个是小夹子,用它来夹出耳屎。最后是一把小毛刷,用鹅毛做成。掏完耳朵后,用这把刷子将残渣清扫干净。他说这一套工具大概值四五十元,有些是他自己做的,有些是找铁匠定制的。
他有两个儿子,一个上小学,一个初中,现在正是暑假,所以他两个儿子都整天待在茶馆里。他说不想让他的孩子学习挖耳这门手艺,而是想送大儿子去学修汽车。他打算钱挣够了,以后在他家乡开一家汽车修理铺,那里位置很好,做修理生意一定不错。 他还谈到了他的农村老家,承包了7亩田,即使是收割农忙季节,也只需3天便干完活了。家里还养了20余只鸡,20余只鸭,20余头猪和一头水牛,鸡鸭蛋经常拿到集市上卖。他们外出时,他父母帮助照看农田和家畜。农田加副业年收入约1万,加上挖耳和擦鞋,整个家庭年收入约1.6万至1.7万。一年总开支约1万元,剩下的存入银行。①
①作者在成都大慈寺文博大茶园的考察,2000年7月5日。
②西方有很多关于中国农民工的研究。关于他们的家庭生活,见Martin King Whyte,“Adaptation of Rural Family Patterns to Urban Life in Chengdu”,in Greg Guldin and Aidan Southall eds.,Urban Anthropology in China(Leiden:Brill,1993),pp.358-380。關于他们的城市经历,见Anita Chan,“The Culture of Survival:Lives of Migrant Workers through the Prism of Private Letters”,in Perry Link,Richard P.Madsen,and Paul G.Pickowicz,Popular China:Unofficial Culture in a Globalizing Society(Lanham:Rowman&Littlefield; Publishing,Inc,2002),pp.163-188;Eric Florence,“Migrant Workers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Discourse and Narratives about Work as Sites of Struggle”,Critical Asian Studies,2007,no.1,pp.121-50;Daming Zhou and Xiaoyun Sun,“Research on‘Job Hoppingby Migrant Workers from the Countryside:A Second Study on Turnover among Migrant Workers Employed by Businesses”,Chinese Sociology and Anthropology,2010,no.2,pp.51-69。关于他们遇到的困难与障碍,见Wenran Jiang,“Prosperity at the Expense of Equality:Migrant Workers Are Falling Behind in Urban Chinas Rise”,in Errol P.Mendes and Sakunthala Srighanthan eds.,Confronting Discrimination and Inequality in China:Chinese and Canadian Perspectives(Ottawa:University of Ottawa Press,2009),pp.16-29;Peilin Li and Wei Li,“The Work Situation and Social Attitudes of Migrant Workers in China under the Crisis”,in Peilin Li and Laurence RoulleauBerger eds.,Chinas Internal and International Migration(London:Routledge,2013),pp.3-25;王笛:《国家控制与社会主义娱乐的形成:1950年代前期对成都茶馆中的曲艺和曲艺艺人的改造和处理》,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当代史研究中心:《中国当代史研究》第一辑,2009年,76-105页;Jiehmin Wu,“Rural Migrant Workers and Chinas Differential Citizenship:A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in Martin King Whyte ed.,One Country,Two Societies:RuralUrban Inequal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0),pp.55-81。国家关于农民工的政策,见Chris KingChi Chan,Ngai Pun,and Jenny Chan,“The Role of the State,Labour Policy and Migrant Workers Struggles in Globalized China”,in Paul Bowles and John Harriss eds.,Globalization and Labour in China and India:Impacts and Responses(London:Palgrave Macmillan,2010),pp.45-63。
许多挖耳匠,像这位男人一样,都来自农村,一边管理着老家的田地,一边在成都打工。整个中国有数以亿计的农民工,他们的工作环境和新的收入渠道深刻影响着中国的经济发展与城市生活。②然而,与其他农民工不同的是,这位挖耳匠充分利用家乡在成都郊区的有利条件,选择仍然住在农村,避免了在成都租房的额外花费以及和家人长期分离的痛苦。此外,他和妻子在同一个茶馆里工作,每天一同来,一同回,一起吃午饭,所以,他的家庭生活基本上是完整的,比那些背井离乡到远方打工的大多数农民工处境要好得多。无疑,农民工进入城市,可以改变自己的经济状况,也可以增加他们的见识,例如,这位挖耳匠便规划了儿子的未来。
当然,他也得为这样的选择付出代价。他的孩子整天待在这种人来人往的地方,充斥着烟味、嘈杂,还有各种粗话,也有各种诱惑,他们不能安下心来做暑期作业。这样的环境对小孩来说是不健康的,缺乏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过早进入熙熙攘攘的社会,可能遇到他们幼小心灵所难以理解的许多事情,可能阻碍孩子接受正常的教育。他们的这种状况反映了在城里工作的农民工的艰辛。纵然我们可以说,社会也是一本教科书,但是这不过是对他们无奈处境的一点心理安慰而已。他儿子缺乏正规的教育,和其他的孩子相比,这是一个劣势,也许有一天,他还是会走他父亲的老路。
四、谋生茶馆的农村妇女
除了前面所讨论的茶馆的掺茶工人、算命先生和挖耳匠,茶馆中还有着许多其他的职业,提供各种服务,如擦鞋匠、理发师和小贩们。一次我在成都西门的清泉茶坊考察时,由于周围街道正在修缮,又下了雨,十分泥泞,给擦鞋匠带来不少生意。她们都是妇女,吆喝着“擦鞋!擦鞋!”一位中年农村妇女模样的人来到茶馆门口,说擦一次鞋一元钱。她带了个小包,里面有刷子、鞋油和布。她给了顾客一双塑料拖鞋穿,然后把顾客沾了泥的鞋提到门外,坐在自带的一个凳子上,先从一个塑料瓶中倒出一些水,沾在刷子上,刷掉鞋上的泥,然后涂鞋油,最后是抛光。她说她来自四川北部的一个乡村,每年冬夏地里事情不多的时候,来成都擦鞋,每月能挣二三百元。如果不是来成都赚点钱,她就无法供孩子读书。她说干这个活,比给老板打工要自由些,她可以随时回家。她估计这片街区大概有五十多个她这样的擦鞋女。她应该没有高估这个数字,因为两个小时内,我身边经过了八九个同样的谋生者。作者在成都石人南路清芳茶园的考察,2000年7月13日。
我在鹤鸣茶社考察时,由于公园环境干净,需要擦鞋的顾客很少,所以只有一位擦鞋女在那里揽活,她提着一双塑料拖鞋走来走去,尋找生意。当她把顾客的鞋拿回她的摊位上擦时,便让顾客穿上那双拖鞋。一些茶馆则禁止她们入内,说是怕茶馆闲杂人员太多,可能丢失财物。一些高端的茶馆,如顺兴老茶楼便不允许擦鞋匠进去,因为他们觉得这有损茶馆的优雅环境。作者在成都人民公园鹤鸣茶社的考察,2003年6月28日;以及作者在成都会展中心顺兴老茶馆的考察,2000年7月22日。
地方报纸有时会报道擦鞋者欺诈顾客的行为,一些茶馆也就是为了防止这样的事件发生,所以才禁止她们入内揽生意。一则故事发生在一个街角茶馆,许多顾客在喝茶、打牌,一位擦鞋女也来这里揽生意,大声吆喝擦鞋价格便宜保证质量。一位时髦的年轻人询问价格,擦鞋女说,5角,只收个鞋油钱。那男人声称他这双鞋是在法国买的,一千多块,对她是否能擦好表示怀疑。那女人说不满意不给钱。于是男人把鞋脱了下来,女人给了他一双拖鞋穿着,然后把鞋带到了树荫下去擦,那年轻人继续悠闲地读报。当他把报纸看完后,感觉有点不对劲,怎么鞋还没有擦好?才发现那女人和鞋都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9〕
小贩在茶馆里也十分活跃,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妇女,她们为顾客提供了便利,也为茶馆增加了活力。2000年夏天,我坐在成都府南河边的一家茶馆,便观察到各种小贩在这里做生意,特别是卖食品的来来往往,这样人们一边坐茶馆品茶,肚子饿了就可以就地买小吃。如一位貌似来自农村的中年妇女,提着两个篮子,里面装着各种佐料瓶,吆喝着,“凉面,凉粉,豆花……” 但因为不是午饭时间,所以没人买。另一位妇女端了一盘白玉兰花卖,花开得饱满,香气扑鼻,可惜也没有人光顾她的生意。几乎每一个茶馆里都有卖报纸的人,而且生意不错,人们喜欢边喝茶,边读报,了解时事。据我观察,这个茶馆里就有十几个人在卖报,有男有女,有老有幼,有骑单车过来的,有走路过来的,都吆喝着,“《早报》”(即《商务早报》)、“《华西报》”(即《华西都市报》),等等。作者在成都府南河边茶馆的考察,2000年7月10日。
上述这些职业,在茶馆里存在已久。尽管这个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都已发生根本性的巨变,但茶馆仍然可以容纳许多人在其中谋生,并进一步展示出传统生活方式和地方文化的活力。尽管小贩重新出现在茶馆中,但这是一个不同的时代,一个不同的社会环境,服务不同的人群,因此并不是所有的茶馆都接纳他们的服务,特别是那些中高档茶馆,那里的顾客更期望安静、有隐私、不被打扰。但在露天和低端茶铺中,他们的服务依然很受欢迎。掺茶工人、算命先生、挖耳匠、擦鞋女、理发匠,以及小贩,都是茶馆和茶馆文化的一部分,继续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但我们无从知晓在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大潮中,他们的未来将是怎样。
结论
流动人口,特别是来自农村的农民工,他们丰富了城市的生活,他们既是城市建设和城市服务的工人,也是城市商业发展的消费者,他们继续为城市的繁荣做出贡献。根据人类学家的调查,农民工主要在建筑工地、饭馆、工厂、家政、环卫以及一些“城市居民不愿干的”行业内谋生。他们不得不“突破户口制度的约束在城市打工和做生意”,还要克服各种来自“农民工、国家与城市社会之间的社会与政治矛盾”。〔10〕
苏黛瑞(Dorothy Solinger)认为判断是否是“流动人口”有三个标准:“他们越过了一些行政管理的边界来到异乡;他们没有能够改变原来的户籍所在地;至少在理论上他们是可以进入和离开城市的。” 他们不能登记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因此“他们不能接受免费的义务教育,在一些国有企业里,他们也没有正常的额外津贴。”因为农民工不具有和城市居民一样的平等权利,而且还面临着歧视,因此苏黛瑞认为:“大都市中的中国农民,不是城市居民”,他们要想在城市里扎下根来,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11〕
我还想指出的是,像任何其他人群一样,农民工也有不同的类型。其中一些人生意做得好,在城市里买了房买了车。成都像其他中国城市一样,许多小企业都是由外来人开办和经营的,诸如餐馆、装修、建筑、小茶馆以及其他许多行业。然而,还有不少人依然挣扎在温饱线上,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茶馆里当掺茶师傅、算命先生、挖耳师、擦鞋匠、小贩或者其他。尽管他们生活艰难,但和以往在乡村相比,生存状况算已经有所改善,他们有了经济上向上奋进的机会。流动人口的存在,帮助了城市日常生活正常运转,对城市的整个经济与公共生活的发展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个研究提供了一个有趣的个案研究,我们看到城市的传统行业,怎样在现代化、商业化、国际化的大潮中发生转变的。在这个巨变中,许多行业被改变了,甚至消失了,但是有些传统行当却幸存下来了。从本文中的这些故事,说明即使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大变动,传统的因素仍然会在相当的程度上保存下来,虽然它们或多或少都将发生一定的变化。而且顽强生存下来的那一部分,经常是看起来没有强大的影响力,但是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那些社会因素。
本文所研究的焦点是当代中国城市的日常生活,茶馆成为观察的窗口。这个课题使我能够从城市史的角度,进入到过去只是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范围——当代中国城市、城市人口和城市生活。其实,我们的城市史学者,不得不试图回答当代城市的许多问题。从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目睹了中国城市的外貌、文化以及日常生活的巨大变化,旧城被新城所取代,历史的面貌已经不在。过去中国古代城市独特的魅力与民俗文化,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消失,中国城市变得越来越千篇一律。同时,大量农民工进入城市,使城市人口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市和城市生活面临新的挑战。因此,怎样理解和认识今天中国的城市,也是研究社会史、文化史和城市史的历史学家们所面临的重要任务。
〔参考文献〕
〔1〕Wenfang Tang ,WilliamParish.Chinese Urban Life under Reform〔M〕.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2〕〔4〕Kenneth Lieberthal.Governing China: From Revolution through Reform〔M〕.New York: W.W. Norton, 2004: 296,190.
〔3〕 Lowell Dittmer,Lance Gore.China Builds a Market Culture〔J〕.East Asia, 2001(3): 23.
〔5〕Dorothy J.Solinger.Chinese Business under Socialism:The Politics of Domestic Commerce in Contemporary China〔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4:108.
〔6〕戴善奎.成都泡茶馆〔N〕.人民日报,1998-07-10;何小竹.成都茶馆记忆〔N〕.华西都市报,2005-12-11.
〔7〕Richard Joseph Smith.Fortunetellers and Philosophers:Divination in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M〕.Boulder,CO:Westview,1991:9.
〔8〕余瑶.茶馆民俗与茶人生活:俗民视野中的成都茶馆〔D〕.上海:上海大学,2007:23.
〔9〕商务早报,2000-07-01.
〔10〕Li Zhang.Strangers in the City:Reconfigurations of Space,Power,and Social Networks within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M〕.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1:1-2.
〔11〕Dorothy J.Solinger.Contesting Citizenship in Urban China:Peasant Migrants,the State,and the Logic of the Market〔M〕Berkeley and Los Ang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9:4,15.
(責任编辑:许丽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