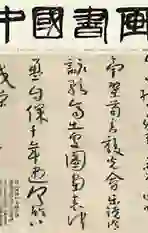论渐江的思想嬗变及对其画风的影响
2018-01-06吕少卿
吕少卿
渐江所处是一个分崩离析、天下大乱、明清易祚的时代。崇祯甲申之变(1644)时渐江年方三十四,他的家乡徽州一带仍然是南明疆域,直到第二年九月才成为大清属土。南明政权从崇祯甲申开始一直持续到清顺治十八年辛丑(1661)。最终以失败告终。其间很多遗民或积极参与抗清。或以各种方式表示了不与清人合作的决心。渐江亦于顺治二年乙酉(1645)避乱入武夷山,并于其后皈依佛门。晚年宗净土宗,发愿往生西方净土世界。应当说,这一朝代的更迭及随之而来的渐江的“逃禅”给渐江的思想变化带来了极大的影响。这里我们来简单分析一下渐江思想变化的脉络。以及这种思想变化带给渐江山水画的影响。
一
早年渐江的思想是“据于儒”。王泰徵《渐江和尚传》中有对渐江年轻时苦学的记载:“少孤贫……其割毡耽学则休映。”休映,指六朝梁江革,大雪天尚敝絮单席耽学不倦,谢眺过访,脱所着襦,并手割半毡给江革充卧席而去。渐江亦苦习若此。所为何哉?王传中亦有陈述:“幼有远志,不入队行,人莫得而器焉。”这个“远志”,当指经天纬地兼济天下了。其挚友程守《故大师渐公碑》中讲得很直白:“(渐江)幼尝应制,徒思帝阙之翱翔:长但佣书,不收儒门之收拾。”他读五经,习举子业。《康熙歙县志》中也有“师汪无涯受五经”的记载。我们知道,这个“五经”乃是明清科举之必修科目,分为《诗》《书》《礼》《易》《春秋》,由乡试至会试、殿试,是科举制度下的必备进身之阶。据石谷风、马道阔先生的研究发现。渐江曾为“杭郡诸生”(周亮工《读画录》、张庚《国朝画征录》《民国歙县志》以及黄宾虹《梅花古衲传》中也有渐江为“明诸生”的记载)。这个“诸生”。也就是俗称的“秀才”。据《明史·选举志》所载。诸生乃是参加乡试(省级考试)的必备资格。明初规定,生员之数,府学四十人,州三十人。县二十人。渐江为杭郡诸生。也就是杭州的四十名諸生之一。按当时规定,诸生通过考试录取,生员专治一经,设科分教。渐江既是诸生,也就是说,他是曾经为参加科举考试作了充分的准备。在他年轻时。和绝大多数读书人一样,受儒家思想熏陶,想着出仕,想着“治国平天下”。
他自杭州奉母返回家乡歙县之后。仍然师从当地名儒汪无涯学习五经,期望能有所作为。后来可能由于生活的压力,他“长但佣书,不收儒门之收拾”,各种渐江传记中也都有他“铅椠膳母”的记叙,如王泰徵《渐江和尚传》中的“尝掌录而舌学,以铅椠膳母”,殷曙《渐江师传》中的“少孤贫,事母以至孝闻。尝藉铅椠养母氏”,程弘志《渐江传》中云“少孤贫,以铅椠膳母”,等等。这个“铅椠”,结合当时徽州刻书业的发达,应当是和刻书业有着很大的关系的营生。后来渐江山水画风中的线条可以明显见到这种木刻版画的影响(当然。这也可能和渐江取法萧云从有着很大关系,萧的线条便和木刻版画关系密切。如《太平山水图》)。渐江一直和刻书业的名人胡日从之子胡致果关系很好。而且。渐江本人曾亲自为木刻版画创作过作品。如《黄山志》中便有渐江等人所作的黄山图。可以看出,渐江此时为了应付家庭的困窘,不得不“不收儒门之收拾”,以佣书为生,以铅椠膳母,生活异常艰辛,诸传记中大都有渐江负米三十里不逮期而欲自沉的记载,如王泰徵《渐江和尚传》中的“一日,负米行三十里,不逮期。欲赴练江死”。“不逮期”便“欲赴练江死”,固然反映出渐江的事母至孝,但亦可见其家是“家无隔宿粮”,“不逮期”,其母便有可能困饿而死,事母至孝的渐江自然万念俱灰,唯有一死了之了。我们无法找到渐江此时再有应举的历史记载,但这一期间,明室处于风雨飘摇之际,宦官专权,党争频繁,朝政极其腐败,不少有识之士也都于仕进一途不抱任何信心了。如当时名士贺贻孙“见战争连年,天下大乱,遂捐弃举业,从此专攻古文词”。相信渐江此时对于应试一事也不会有多大的热情。
其母死后,渐江仍然不婚不宦,这在诸传记中亦多有记载。可见渐江于仕宦一途已然绝念。在他的思想中,与儒学相比,道家的出世思想已经占了上风,正如许楚所云的“长但佣书,不收儒门之收拾”。他自己也说:“瓦缶雷鸣可唱酬,不如归去任扁舟。”后来渐江的偕师入闽。应当不是众学者所云的为投奔唐王政权抗清而去,而应当是“忽念名山神欲往。孤舟系向子陵滩”。他变名韬字六奇为名舫字鸥盟。一变“兵韬六奇”之初衷为“富贵非吾事,归与白鸥盟”,其归隐之心昭然若揭!且当其顺治二年乙酉(1645)七月前入闽之时,武夷山区相对于皖中、浙东、湖南、福建等地来说,俨然是一个尚未被兵燹所触及的世外桃源(按:渐江入闽之时间、目的。另有专文探讨)。他思想中的这种道家出世观念对他的武夷山之行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渐江出世思想的由来之久,还可以从其挚友许楚《渐师归塔文》中略窥一二:“忆楚与师从惠庄之游者,三十年矣,其中天地虚空,物情屯幻,不知几经阅历,而剩此磊岢不群,踽踽凉凉欣然方外之渐公也。”“从惠庄之游者三十年”,算起来,在渐江二十四五岁时,便有了对老庄之学的兴趣了。在渐江的另一位挚友汤燕生笔下亦有“渐江师逃虚人外,积三十年,荡异含真,初不欲自名一长,以与世通”句,算来亦是他二十四五岁时。也就是他开始作画之时,实际上也就是他的出世思想萌发之时(此时,应当是渐江刚刚开始作画,因为饶璟跋渐江《黄山山水册》有“渐师作画三十年,从无一毫画师气习”之记叙。饶为渐江友人。其言当不虚)。他的作画。看来也有点“以画为寄”的意味。对于生存在明末的士人来说,这种思想的产生是异常自然和顺理成章的。正如陈传席先生所说:“国家衰败,党争不已,士人们皆无心国事,各自为是,当李白成率领一批饥民一路杀向北京城时。士人们皆无动于衷。弘仁也依旧在读经作画。”渐江在此时也依旧以佣书、铅椠为生,读书作画,如崇祯七年甲戌(1634),渐江25岁时,为灵运词坛画扇,上题:“甲戌秋写为灵运词坛。江韬。”崇祯十二年己卯(1639)。渐江30岁时。与李永昌、孙逸、汪度、刘上延四人共绘《冈陵图卷》为李生白四十寿辰祝寿。上题:“己卯春日为生白社兄寿。江韬。”此外。还有一件仿黄公望的《天池石壁图》,著录见于容庚《颂斋书画小记》,黄宾虹见过并为之题跋,渐江自题“子久天池石壁遗意。为明老法师写。江韬”。看来也是此时所作。可见渐江此时佣书、铅椠之余,也为人作画,或藉此谋些生活用度也或未可知。endprint
“明王朝灭亡了,许多士人还不知道。当吴三桂降清,打开山海关,满清虎狼之师挥旌南下'江山即将为满清所有时,士人们方惊觉起来,于是纷纷奋起抵抗。”当甲申之变后,顺治二年乙酉(1645)。南明弘光政权成立已近一年,皖中一带抗清烽火迭起。五月问,弘光政权覆灭,清兵自南京开始向安徽进攻,明御史金声、举人江天一在绩溪举兵反抗,皖地已经人心惶惶、战乱纷纷。各种典籍和野史并没有渐江起来反抗、参加抗清斗争的记载。倒是有“乙酉奉其师入闽”、“乌聊既定之明年作幔亭游”的叙述。从渐江的思想中我们可以分析出。此时渐江决定奉其师汪无涯入闽避乱的说法当更为可信。渐江此时至相对安定的武夷山区避乱,其行踪,正如他后来题《武夷岩壑图》云:“武夷岩壑峭拔,实有此境,余曾负一瓢游息其地累年矣。”他在《与程蚀庵》尺牍中也说:“入武夷山,居天游最胜处,不识盐味且一年。”这应当是顺治三年丙戌(1646)隆武帝被杀于武夷山下汀州、清兵骚扰武夷山之后。总之渐江在武夷山的避居生活是异常艰苦的。但他在武夷山仍然坚持画画。查士标跋渐江《黄山山水册》曾有“渐公画入武夷而一变,归黄山而益奇”的评论。说渐江山水入武夷后面目为之“一变”。而归黄山后作品“益奇”,这说明渐江在武夷所作山水,查士标等人是曾有亲见的。陈传席先生说“弘仁在武夷山恐怕没有画画,他当时奔赴战场,为了战斗,画画的条件是很难具备的,目前,尚未见到弘仁在武夷山作画的证据”。显然,陈先生没有仔细分析查士标此跋。
二
虽然艰苦。但渐江在武夷的日子又是过得极其悠闲的,王玄度有《程非二怀予诗见寄,因和原韵奉答。兼忆张蚩蚩、江鸥盟二道友》诗云:“贪云锢石老僧顽,悔逐乌衣故垒还。斗笠已辞天女供,破囊难买道林山。临风觅句秋劳势揽月书怀夜废闲。独有武夷双白鹤,相思路不阻河关。”“白鹤”也是归隐的象征,如倪瓒曾有诗云:“古人与我不并世。鹤思鸥情迥愁绝。”可见渐江与其他抗清志士不同。他如翩然白鹤一样。归隐于武夷山中。避乱于武夷山中的渐江于顺治三年丙戌(1646)间受到了严重的骚扰,这是由于南明隆武帝为清兵所迫,欲往湖南投奔何騰蛟,故向西逃向武夷山区。八月,被清兵俘获于武夷山下的汀州,为了躲避清兵的大肆搜捕、迫害,追随隆武皇帝、鲁王的大批抗清志士或远走肇庆、广州。去依靠南明永历、绍武政权,如恽南田。或于此时避入武夷山等深山,其后更纷纷皈依佛门,如汪沐日、汪蛟、吴霖等人之依古航道舟'陈洪绶之剃发云门寺,熊开元之于南岳祝融峰下削发拜弘储为师等。渐江此时本已身在武夷,亦鼠窜奔逃。如其《与程蚀庵》尺牍所云“居天游最胜处。不识盐味且一年”,最后亦在顺治三年丙戌(1646)、四年丁亥(1647)间皈依古航道舟,师为其取法名弘仁,自取号日无智(然很少用),从而开始了“逃于禅”的后半辈子的佛门生涯。渐江出家前后,友人王玄度也到了武夷山区,渐江时与王玄度、张蚩蚩等啸咏唱和,似乎过着闲云野鹤般的生活。
应当说。刚刚“逃于禅”的渐江,思想是极其复杂的,与早年的“据于儒”及二十四五岁后的“据于老、依于儒”不同,他此时思想中掺杂着道、儒、佛的成分。对于明及南明政权,在其存在时,渐江等一些避世的士人可能并不觉得与自己有多大关系,但俟国家真正灭亡了'他们似乎又是觉得有愧于心,在这些士人心目中,儒家尽忠的思想仍然不可能彻底消除。渐江自取“无智”的号也正是这种思想的反映。但渐江思想中道、佛的成分毕竟占主流,他是一个出世的高人,世事与他的关系是渐走渐远,故而,这个“无智”的号他也并不常用。愈到后来。他愈来愈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虽然遗民的情结并没有能彻底消除,但世间的纷扰已是与己全然无干了,如其自己所云,是“尘壒鸿沟,衣茹桃洞”,即使如楚汉纷争,也已是不关己事的“世外红尘”。他只愿衣茹而居桃洞。这种思想状态和倪瓒是颇为相通的。我想这也是渐江选择取法倪瓒以及他能成功地取法倪瓒的一个重要原因。渐江开始虽属“逃禅”。但他思想中对佛教的喜好究竟有多少。我们也不得而知。陈传席先生在《弘仁》一书中多次说到渐江是不得已才入佛门,如“他出家一半是出于不得已,也有一半是为了清静”,似乎已经确证渐江之出家是和思想中对佛的喜好全然无关。这个论断也略有武断之嫌,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也应当只能作个猜测或存此一疑。但渐江对于禅境其实早有会心。殷曙《渐江师传》中有“师秉性幽贞,绝意婚仕,独嗜读书作画,聊以永日”的叙述。许楚《画偈序》也有云:“独念师道根洪沃,超割尘涅,抚身立命,慨夫婚宦不可以洁身,故寓言于浮屠;浮屠无足与偶处,故纵游于名山:名山每闲于耗日,故托欢于翰墨。”这种记叙应当不是对渐江的一味溢美之词。他的生活,有据可查的是,自入武夷山后就异常简单,“余曾负一瓢游息其地累年矣”。不啻是一种苦行僧的生活。随着渐江逃禅的时日渐长,对佛学的浸淫愈深。他的心灵就变得越来越纯净、越来越澄澈,他也就真正进入了一种禅境:“空山无人,水流花开。”他的生活是简单、无求的,他的心态是、冷、静的,他的精神是孤、寂的,他对外部世界的审美观照是冰冷、净寂的。他心中所追寻的也就是一种“淡而无为”的境界、如许楚所云的“(渐江)因念单道开辟谷罗浮。晓起惟掬泉注钵,吞白石子数枚,淡而无为,心向慕之”。他往来云谷、慈光间十余年,“挂瓢曳杖,憩无恒榻……或长日静坐空潭,或月夜孤啸危岫”(许楚《黄山渐江师外传》)。汤燕生跋渐江《古柯寒筱图轴》中更是具体描绘了渐江的这一生活方式,使人读来如临其境:“渐公登峰(文殊院)之夜,值秋月圆明,山山可数。渐公坐文殊石上吹笛,江允凝倚歌和之。发音嘹亮,上彻云表。俯视下界千万山,皆如侧耳跂足而听者。山中悄绝。惟莲花峰顶老猿亦作数声奇啸。”读此文字,觉渐江真乃神仙中人。再读渐江山水,也就可以明白,其冰冷孤峭恍如藐姑射仙子'并非凭空而来。
较之“四僧”中的其他三僧。渐江是唯一一个能真正“入禅”的人。且不论主动向清廷邀宠、“欲向皇家问赏心。好从宝绘论知遇”的石涛。也不谈同是朱明宗室但时僧时俗又时道的八大山人,即便是终身不与清王朝合作的抗清志士髡残,他的“逃禅”也真正仅仅是个外在形式。他的内心实际上无一日能与佛禅相契合。他的脾气暴躁,佛并没有能让他真正“静”下来。他的遗民情结依然异常强烈。他曾因檗庵正志(熊开元)到钟山未向孝陵行礼而大怒,叱骂不休,直到檗庵认错,复向孝陵磕头方罢。故而,在他们的作品当中,流露的始终是一种波动的美感。浮现着一种“动荡”之气。关于这一点。陈传席先生在《弘仁·静美与动美》一章中有精彩的分析,限于篇幅,在这里不再引述。我们要认清的是,与这些人不同,渐江“生平畏见日边人”,正如王泰徵《渐江和尚传》中说“渐公畏除目中人。所谓‘三朝损道心耶”,他的心中一直是“静”的,这个“静”在他的思想中由来已久。在他“逃禅”之前。他的心态就已经偏向于出世、偏向于隐逸。“明清易代”和“逃禅”只是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思想。渐江思想中的“静”、精神中的“冷”、心灵中的“净”和感情中的“寂”,决定了他山水画风的静、冷、净、寂。endprint
三
但我们说,如此分析渐江的思想,并不是说他就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与人世隔绝的人。我们无意于将他树立为一个遗世独立、卓尔不群的世外高人,这不客观。也不科学。在日常的生活中,渐江也有他的交游、他的追求,他仍然是一个社会的人,对于绘画,他也并不如像对其他诸事一样空寂、淡而无为。在黄宾虹《僧渐江之高行》中有这样一段有趣的记载:“……相传师购倪画数年。苦不得其真迹。一日获观于丰溪吴氏,遂佯疾不归,杜门面壁者三阅月,恍然有得,落笔便觉超逸。”从这个“佯疾不归”,我们可以看出渐江慧黠可爱的一面,亦可看出他对绘画的钻研程度。渐江对绘画的钻研,也是他儒家积极进取的观念在他思想中的一个反映。这也是我们在分析渐江“逃禅入道”的消极思想中必须注意的渐江思想中的积极方面。汤燕生跋渐江《江山无尽图》中有“余从师游最久,见师自壮至老,无问园居刹寓,一日废画与书不观,则郁如负奇疚者”,则渐江之苦学可略窥一斑。也正因为如此。渐江的山水画能够对传统有所传承并发展。从而为自己绘画独特的面目奠定坚实的传统基础。并成为山水画在明清之际传承中的重要一环。
渐江亦曾凭借绘画获得过一些生活上的资助。如程守跋渐江《晓江风便图卷》中有“余与方外交渐公卅年所,颇不获其墨妙。往见吴子不炎卷桢,辄为不平。因思余城居,且穷年鹿鹿。渐公留不炎家特久,有山水之资,兼伊蒲之供,宜其每况益上也”。与丰溪吴氏的关系,在渐江的交游中应当是颇为重要的一环。渐江多次在其家观其家藏书画精品,交谊深笃。如渐江《与吴仅庵》书中云:“去冬曾具只字寄候,想尘几下。仁春来兀坐五明,景况殊寂:兼赢病日增,酬应为懒。所最苦者,故乡松萝,不贴于脾。至涓滴不敢沾啜。极思六安小篓。便问得惠寄一两篓。恂为启脾上药。宴僧感激无量……”可见渐江与他们的关系很是亲密。渐江亦多次为吴家诸人作画,如《为闲止作山水轴》《丰溪山水册》《山水四段卷》《山溪双树图》《江山无尽图》《晓江风便图》《为伯炎画山水轴》等。他客游庐山、阻雪鄱阳吕旦先宅时。闲暇中还曾作画遥寄丰溪吴氏。纵观渐江的画目。不少皆有“为××先生、××居士”的上款。渐江的这种交游和绘画创作。也是他出世思想中的“入世”观念。
另外,他晚年对“性命之学”产生了兴趣,这当中既有佛的因素,也似乎有儒的成分。闵麟嗣《弘仁传》中有“师将省墓界口。并诣鸠兹别汤燕生,然后入山研究性命之学”的记载。“性命”之意,当是如朱熹所云:“物所受为性,天所赋为命。”宋明理学中有专门研究性命之学者,渐江是佛教信徒,后来尤笃信净土宗,相信生死轮回、贵贱寿天之类天命的存在,发愿死后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站在他的角度,这个“性命”,似乎应当和佛有关,但具体指哪些内容。现在也无法考证。但我觉得其中和儒学的关系也不应小觑。陈传席先生在《弘仁》专著中认为渐江的性命之学可能和檗庵正志(熊开元)有关。陈先生认为檗庵是“通性命之学的”,他晚年又曾一度隐居黄山云谷寺,且渐江曾为云谷寺僧书寓安大师塔铭。这个塔铭为檗庵所撰,便认为二人有交往,渐江并受其影响,从而对性命之学产生兴趣。虽然陈先生说关于这一点“尚值得进一步研究和查考”,但于此,我颇不以为然。我觉得渐江对“性命之学”的兴趣比较明显地应当是受王炜的影响。王炜(1626-约1701),又名艮,字雄右,又字无闷,号不庵、广乘樵,晚号鹿田,歙县俞岸人,少渐江十七岁,是渐江好友。二人曾同游黄山(顺治十七年八月。王曾有游记记于汪士《黄山志续编》)和庐山。黄宾虹先生《渐江大师事迹佚闻》云:“(王炜)自其祖龍山及父贯一。世传理学:年二十,读《易》山中,有《易赘》之作:阐发《中庸》《春秋》《周礼》:上自天官地志、玉函金匮之书,骑射击刺之法,靡不毕究:所交皆当世名儒;著《葛巾子内外集》《鸿逸堂稿》。尝自吴归,述昆山顾绛母饿死事,断弃举业,甘于自废。”可见王炜也应当是通“性命之学”的。渐江晚年的出游庐山便是在这个王雄右的策划和支持下进行的。许楚《送渐公游庐山诗序》中说:“岁壬寅冬,渐公由浮溪至郡,将游庐山。友人王雄右自芝山移书为裹鹤粮……”《民国歙县志·江韬传》亦云:“岁壬寅,将游庐山,友人王雄右怂恿其行。”在鄱阳期问。可能因为大雪封山,抑或是缘于主人留客,渐江一直住在王炜的东家、歙县吕村人吕旦先家之且读斋(王在吕家教授其子士鵕、士鹤)。王炜一直陪同着渐江,游匡庐期间,他们一起凭吊宗炳、雷次宗、慧远等人的遗踪,游历白莲社旧迹,宿于雪庵处。然后又下山返吕家,直至癸卯夏六月渐江回到歙县,二人共处大约有半年之久。可谓朝夕相对,渐江受王炜思想的影响是自然而然的事。而且渐江思想中的积极进取的一面一直都存在着。他心灵深处的遗民情结也是他思想中深藏的儒家传统的表征。故而,我们说,渐江晚年的思想应当是“据于佛,依于老,”但仍然有“儒”的因素。
应当说。渐江的心态在皈依佛门前后已经起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依古航道舟之后,随着日渐于佛学禅理的浸淫、于山水自然的娱游、于书画诗文的寄怀。他对佛学的兴趣也与日俱增,对于佛教,他已从最初的或许不得已的“逃禅”而真正“入净”,对佛理产生了真正的信仰与沉迷。尤其对于“净土宗”理论深信不疑。净土缘起于菩萨之本愿。本愿乃菩萨在修行过程中,于将来成佛时,在其所构拟的佛土内要求实现某种状态而先行树立的誓愿。净土东传始于东汉,此后,东晋慧远与大众精修,于庐山结白莲社,诵般若三昧经,期待往生。净土宗与禅宗在一开始冲突颇大。净土宗从末法思想入手,主张通过称名念佛往生极乐净土,主张依靠他力拯救。禅宗则从般若空宗理论出发。反对念佛往生,主张山居、不立寺院,依靠自身力量来寻求发展,主张唯心净土。但宋元之后。净土宗与禅宗逐渐融合。渐江的思想也应是融合禅宗与净土宗的。如他有诗云“为爱山居碧玉围,含毫未识倦和饥”、“几年未遂居山策,瓶笠还如水上飘”。看来他也是主张山居的。
渐江在康熙元年壬寅(1662),他“过匡阜,吊宗、雷之遗事,感刘、竺之微言,觉远公声影犹在”,“乃始毅然著发愿文也”,愿往生佛国净土。成为一个真正寄情于山水、沉湎于禅门佛理的隐逸之士。他心中所怀的已不仅仅是对新王朝的漠然、对山水自然的偏好,而且增加了许多对佛教经典。甚至于性命之学的沉迷与钻研。程弘志《渐江传》中亦有“师尝拟于慈光禁足三年,批阅《大藏》,然后于浮溪丹台之间,结瓢终老”的记载。应当说。随着渐江对佛教义理的日渐钻研,他对于佛门的信仰就愈来愈由衷,愈来愈深沉,他的心灵也便愈来愈澄澈、愈来愈空寂。对山川自然的澄怀体味也就愈来愈澄澈、空寂。虽然不可否认的是他内心深处仍然有怀念朱明王朝的遗民情结,但从心态上说他已经安于这种孤冷萧索的生活,那种激越的胸怀和悲愤的情绪越来越藏之于心底,甚至化之于无形。对于山水林泉,他也以独特的空寂的心灵来观照并形之于绘画。多以冷、空、寂、静发之。如他在《古木竹石图轴》上所题:“‘古木鸣寒鸟,深山闻夜猿,唐句也。余偶抹此,虽无可状其意,而空远寥廓,老干刁调,或庶几似其岑寂耳。”这种“岑寂”已经成为他山水画中所追求的高上境界了。他的心灵,也正如许楚《渐师归塔文》所云:“忆楚与师从惠(施)庄(周)之游者三十年矣。其中天地虚空。物情屯幻,不知几经阅历,而剩此磊岢不群,踽踽凉凉。欣然方外之渐公也。”故而他“不作钱塘江上声”而写“溶溶湖水平如掌”了。这一思想的变化。对于形成和强化他冷、寂的山水画风格来说,是极为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决定性的因素。而越到晚年。随着渐江对净土宗信仰的沉迷,他的生活和思想又略有变化,他的心灵有了真正的寄托。他的画也就随之有了新的变化。
责任编辑:刘光 欧阳逸川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