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示西部散文的神性,文风思骨的天人合一
2017-09-25王克楠
《雪莲》是中国西部的重要的文学阵地,它远离一切媚俗和低级趣味,崇尚高雅高贵,注重人文精神的挖掘,长期以来,吸引着全国散文写作者的目光,尤其是《雪莲》推出“西部散文擂台”栏目,使广大读者感受到了西部优秀散文的魅力。笔者在阅读《雪莲》这个栏目散文的过程中,和作者一起享受着西部的独特天地,西部的元素,西部的经典,西部的粗犷和淳厚,西部的刚烈和温柔……不由从心底里发出了赞叹。
一、西部地理中的文化命脉
中国的西部是浩瀚的,笔者亦以为中国版图遥远的大西北、大西南旷远地带是“西部”不可动摇的坐标圆心。散文家史小溪亦认为,“陕西之西北西南,巴渝、黔地,不过是西部‘概念端边缘地带……”,笔者打开《雪莲》“西部散文擂台”,一篇篇地读下去,深入其中,感到了西部散文的浩瀚:它们领略帕米尔万山之宗,黄河长江之源,西陲长城雄关,茶马古道,雪域的阳光,昆仑长云,蜀道绝壁,苍茫乌鞘岭,黄金蒙古包,布达拉宫;领略野马,牦牛,藏羚羊,北疆鲵;大漠胡杨,戈壁花芷,格桑花,雪莲;还有龟兹乐舞,黔南傩戏,康巴羌笛,陕北信天游,青海花儿……
笔者阅读的《雪莲》第一篇散文是郭保林的《夜雨仄身入成都》,作者是写西南成都的。他以强大的气势,借景入理,思考的是如何为古蜀成都进行定位?郭保林对成都的茶文化有独到发现,“茶馆一度是成都的灵魂,成都的历史是草就的”, 郭保林热情讴歌了成都的“诗城”风范,有诗人之命相:如司马相如、卓文君、杨雄等;有诗境之熏陶“这里多雨多水多江湖,流水的袅娜,流水的清丽,流水的狂放和恣肆,激发了他们的灵性,水的变幻莫测的基因早在童年已注入他们的血脉。”此文再现了唐代李白、杜甫的诗情才艺:李白对蜀地的张扬在于感;杜甫对蜀地,尤其对成都的感觉在于命,是蜀地温厚地包容了他,“杜甫此时才有闲情逸趣,欣赏天然之美”。成都给诗人带来强大气场的人物,不仅有杜甫,还有薛涛以及能歌善舞的花蕊夫人,可以说,如果没有蜀地的青山绿水,就不会有她们的诗歌才情。
作家郭保林深入成都写成都,另一位作家凌鹰则深入历史名城——皖南池州。他的散文《谁让池州如此妩媚风雅》通过地域来揭示李白的命运,李白的率真的个性,无法得到皇帝的喜欢,李白适合出宫游历大自然,因而池州就与诗仙李白有了不解之缘。人们熟悉许多诗人,未必熟悉池州,因而通过诗人李白与两位诗友饮酒作诗,而把九子山更名为——九华山,成为文化营造地理的一个例证。一个地域总是与历史名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名人之人品人格,也融入了地域的文化血脉。为了揭示池州的诗性,作者引入了晚唐诗人杜牧,池州有灵,连接上了李白和杜牧两位诗人的心。因而,凌鹰从时间的长度上,推出了池州的诗性,“让池州很多本不起眼的地方有了沸沸揚扬的文名。”历史文化散文的要点在于——点穴,点穴的关键在于点拨出灵魂的震撼,如作者对池州和杭州两个翠微亭的“点穴”,“翠微亭从此就成了齐山的一个文化符号”,即是。作者还善于主笔侧笔配合,从池州的文脉说,主笔是对李白、杜牧的池州情结;而抒写相对缺乏功名的罗隐,则是侧笔。至于其他在文中匆匆而过的名人们,一样作为侧笔而入文了。主笔和侧笔互相呼应,组成了此文的宽阔,把一个活生生的池州托在读者面前。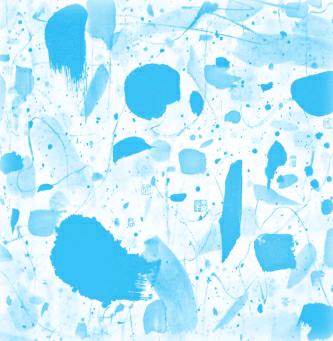
陈拓系藏族,对青藏高原的物象有着深入骨髓的理解,他的《眺望一条黑色的河流》,写的是位于甘青川交界处黄河的一条支流黑河。人有性格,河流也有性格,“它像一条黛青色的飘带,在苍茫辽阔的若尔盖大草原上,自由飘荡,随风蜿蜒……特别是在那天黄昏夕阳的照耀下,更是波光粼粼,如梦似幻。”这条河流具有梦幻美。生活常常会残酷,而河流则浪漫和温存,因而作者心中常常涌起“一种冲动,一种强烈的想直面它、走进它的冲动。”后来作者终于有机会接近这条河,还是失之交臂。最终,作者还是在梦中还是走进了这条黑河,“一种传自天地深处的声音,这种声音轻柔且舒缓,这种声音绵长而亲切,但它切割血肉与骨骼的力量,透过我的肌体”,由此就成了精神图腾。作者清晰地向我们发现了物象和心向之间的联系,证明自然美的同时,还向我们呈现出对草场承包的担忧。人只是大自然的一个物种,大草原上还有牛羊马,它们逐草场而栖,“有人类一种自由生存文化的特殊形式”, 后来实行了“草场承包到户,承包到户的草场实现了围栏化,九曲黄河第一湾两岸广袤的万里大草原,被一片一片铁丝的围栏分割成千千万万的条条块块,将人和牛羊、将自然世界和动物世界分隔开来……一种深深地担忧攫住了我的心”。确实这是一件令人担心的事情。
文化是生活之魂,一个人的文化修养需要修炼,而对历史文化的修炼,很多时候需要“寻找”,黄适远的《寻找大月氏人》,就具有鲜明的“寻找”色彩。大月氏尽管位于西域,却与中华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寻找大月氏人》考证色彩甚浓,对“东大山”地理位置的详尽认定,可见一斑。傅兴奎的《顺着一本书在兰州游走》,解读的是西北重镇兰州,作者用特殊的第二人称——你。虽然字面是“你”,表达完全是作者的兰州情结,考究的是兰州风景。作者对兰州充满了热爱,尤其是文朔阁中的《四库全书》,更是充满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中国的西域,许多游牧民族是消失了的,但作为一个民族。虽然其居住地消失了,并非文化的消失。中华文化洋洋大观,其中就包括游牧文化的元素,比如大月氏,如匈奴。作家马海在《消失在马蹄上的帝国》叙述了匈奴的历史由来,匈奴的战斗特点,匈奴的强大以及消亡。作者认为匈奴是悲情的,因为他们生活在华夏文明和罗马文明、波斯文明这三大文明的夹缝中,而且处于这三大文明的鼎盛期。作家张乃光也在寻根,在西南边地寻出了一个叫做“虎街”的古村,古村位于滇藏茶马古到南线,是一个彝族古村,崇拜老虎,纪年立法“自然被命名为《母虎日历》”。文化可以在血流中奔流,也可以用唱歌的方式表现出来。朱嘉华《丹麻花儿情歌的海洋》,尽情地抒写了丹麻土家族的花儿。endprint
作家淡墨在《我的包格图,我的大青山》中,写的是内蒙古的大青山(古称阴山),写了大青山的骨气以及母亲一般的情怀。大青山少言寡语,“一把将我揽进她的怀里”。淡墨写出了大山的个性:豁达,大气,包容。淡墨的这篇散文是写意的,用意境勾出了大青山的魂魄。另一位来自内蒙古的作家宝音巴图描绘了内蒙古阿拉善盟的旧时物流风景。“与远方拖回的一袋袋粮食、一沓沓料布,一叠叠砖茶和奇闻异事的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去时的剽悍骆驼双峰已经耷拉。”时代在发展,而作者面对未来却怀着淡淡的担忧。中国的西部以自己独特的气质,同化着前来居住的东部人,淡墨就含而不发地写道,“在那些与黄河和大草原朝夕处的日子,我这个南国游子曾让自我的孤独和寂寞,变成东胜的一坨煨碳。把梦想冷藏得就像结冰后看不见奔腾和涌动的黄河”。作家一叶的《腰缠万贯下泸州》,写的是泸州风情以及风情中的历史掌故。“掌故”中有经济由头,也有生活的艰辛。作家孤岛的《七上天山天池》,用的是日记体,七次上天池,是时间的跨度,更是对人、对物的感悟。
二、西部散文的文化内涵及生存哲学
西部散文的内蕴肯定是以它远离现代文明为特征的。当然,西部又从来不是狭隘封闭的,它自有它的文化审美的包容性、开放性和价值取向。西部散文除了它独有的地域色彩特征外,更有自己独具的精神特质:那种张扬的原始自然生命力,不屈的生命激情,雄阔、凝沉的意象,悲凉、悲苦、悲壮的生存意识,无疑是它的质核和根系。在沿海和中原地区被后现代思潮扫荡时,西部散文所展示的自我生命精神因其“超凡的脱俗和纯净”而傲然独立(散文评论家范培松语)。今天,更有许多西部散文正力图跨越地域,探寻其深厚的寓意价值——走向与人类相通的自然、人文精神向度高度。
其实,西部人自强不息的精神早已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液。中华民族需要温良恭俭让,亦需要张扬西部民族那种扬厉刚强、扬厉进击的强悍气质;我们的民族文化需要淡泊致远,也需要那种狂放刚健的文化精神。中华文化脉系问题上,许多学者倾向与南北分界,(以长江为分水岭),却忽视了东部与西部的文化差异。东部的海洋文化与西部的山地、草原文化有着巨大差异,其差异不仅在地理环境上,更重要的是生存方式以及人性彰显上。作家李云的《融入野地》掀开了东西差别的一角,在作者的认知中,西部是“粗粝、杂乱、斑驳、原始、杂草丛生、创世之前的模样、潮湿芬芳、气息迷人、纤尘不染、神圣的净地……”。李云列举了个人融入“野地”之经历,做出了这样的总结:“现在社会,无论男女老少,都需要一块儿野地,至少心中要有这个概念。精致的生活,往往是对人性的摧残和毁灭。”陈有仓在散文《春雪及以外的事》写了一种叫作“地软”的野生藻类植物,其实,是寄托了一种乡愁。周伟在《春望草深》中讴歌了在乡村司空见惯的草——水草,“水草是卑微的,也是坚韧的,水草常被人践踏,它却总是向上生长。”
西部之美是獨特的,却不是永恒的,需要一代代西部人去呵护。作家方建荣以《敦煌的疼痛》,向世人,也向发出保护敦煌的呼唤,“水能载舟,水能颠覆,敦煌这只大船需要水来鼓荡起风帆和魂魄”。对于散文写作来说“写什么”是重要的,“怎样写”同样重要。作家苏世胜写乡愁,不过,他是借助物象来写乡愁,那物象便是北方乡村农人使用的木桶。苏世胜怀着一颗感恩之心,再现了一双木桶的诞生过程。后来,随这时代变迁,这一双木桶进了城里的民俗馆。另一位作家袁海盛从另一个角度讴歌大地的包容,这个角度便是——味觉,“大地不仅是一切生命的母亲,也是天下味道的主人。”优秀的散文是“发现”的结果,这个发现,便包含了“怎样写”。 苏世胜在文中写了土地,写了味觉,思路打开,灵感潮涌,他还写了乡下的苦麻子,写了中医药,写了“慈善是大地的本性”。
同样面对植物,刘艳琴的《乡关何处》表达出另一层担心,“子子孙孙永远眺望着遥远的蔚蓝色,把海的记忆刻进血液。”散文可以可以用白描法去实写,也可以虚写——写臆想中的真实。比如作家李汀写了《风从农谚中吹过》,结构呈流线型,李汀写的是风,首先认定“风首先是从那棵大树上吹过来的。”而后再从意象出发,认为风把一座大山吹得“翻白眼”,风在“扫地”。更有灵气的地方,是李汀呈现了一个13岁的孩子与一位60岁的老人之间的对话,并原彰此显出一些哲理,如 “人在风中,其实也是一张落叶”,“人,就是一阵风”。来自贵州的李天斌的《清明图》,呈现了自己曾经生活的小山村,“水不大,却常年不断,河身不长,只百数百米,却终年不息。”农民在劳作,亦有鲫鱼陪伴,野花朵朵,蝴蝶翩飞,也是一种美境……作者描绘得这幅清明图,是中国农耕社会的美图,与狂燥不安的工业社会形成了鲜明对比。
作家茹孝宏选材水磨,此乃“人类由农耕文明迈向工业文明的驿站”,水磨坊是实用的,也是审美的,“从磨坊飞泻而下的那股粗大的才湍流,冲动着磨轮急速旋转的鸟叫雀唱蝉躁蛙鸣,便组成了一部变一部悠闲而甜美的管弦乐曲”,文中守磨坊人刘三爷的形象尤其感人。作家尹巨龙写了豌豆角,“头顶的白色、紫色的小花,倚靠着阳光,把半片苍翠的画卷在田间慢慢铺开”,碗豆角的样子十分传神。王若冰写了秦岭南坡的独叶草,有着腊梅一样的品质,不畏冬天的寒冷,“在一片寂寥的世界展开它的绿叶,绽放的它的花朵,呈现出与众不同的生命光彩。”这种草的生命力之强,经历了两百万年前的第四季冰川期,这样顽强的生命力非其他植物之所有。独叶草是特立独行的,它可以不借助阳光完成新陈代谢,正如西部人,并不用接受一些条条框框,照样生活得自然而潇洒。除了独叶草,王若冰还写了为西北太白山之独有的红豆杉、太白柳等植物,超凡脱俗也。
刘燕成是贵州苗族作家,虽然定居省会贵阳,依然对家乡农事念念不忘,他的《农事录》就是对家乡农事的审美观照。插秧是南方农民常见的劳动,但在作者笔下,插秧插得好,仿佛是做一件艺术品,“眼光要放远,要盯着前方,看前面已经栽下的秧苗是不是细致而匀称。”还有背粪给稻田施肥,“这个粪儿背得多吗,肥料下得好,秧苗自然喜人”,作者叙述的是人勤和丰收之间的因果关系。拾稻穗是对粮食的珍惜,“将一大把稻穗,捏在掌心,扭过头,小心翼翼地把手掌都谷穗轻轻地揉进了竹篓里。”刘燕成不仅详尽地回忆了拾稻穗的劳动,更有今昔对比,把如今由于打工潮而被从农田引走的农民,被废弃的农田进行对比,蕴含了一种对农业荒芜的担忧。endprint
来自南疆的张钊的《尼雅失落的文明》是追溯文明之源的作品,尼雅废墟的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历史?作者写了英国考古探险家斯坦因雅古址的掠夺,“斯坦因带着从和田沙漠腹地的尼雅,盗掘的满满十二大木箱珍贵文物,从喀什出发,经俄国运回英国伦敦。”斯坦因是卑劣的,而尼雅遗址是鲜活的,尼雅遗址散落南北二十五公里、东西约七公里的范围,“遗址中心有一座佛塔,虽然已破败,但佛韵古风依存。”遗址还有各类树木、有红柳木笔、有六弦琴、玻璃和各类织物……可以想像一千六百年前这里的繁荣。1995年初冬中日两国考古界联合系统考察中,尼雅遗址再次震动了世界:其中在尼雅遗址西北一处古墓群,发掘出大批汉晋时的珍贵文物,三号棺中出土了写有“王侯合婚千秋万代宜子孙”汉字的锦被;五号棺中还出土了写有汉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织锦。“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是我国古代天文学或星占学上的占辞用语,显然为中王朝的赐赠品,有力地证明了汉晋时代,尼雅与中原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密切地关系。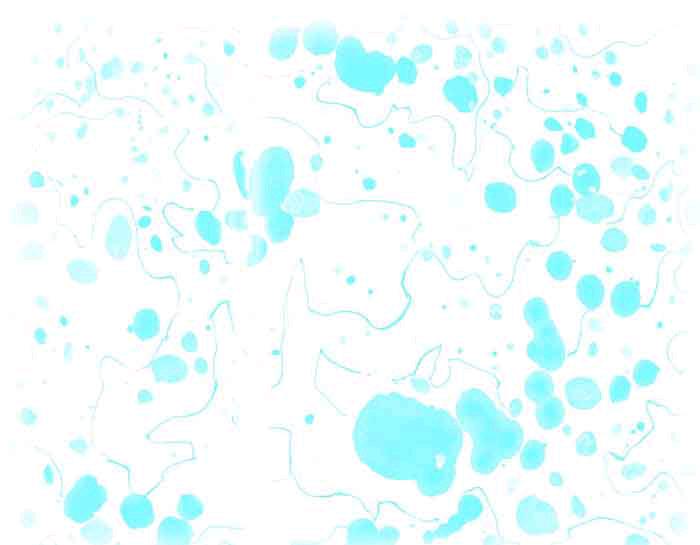
人类和人类文明诞生与地球纪年相比,是微不足道的。作家温国以张扬的笔墨,写了桑干河的历史由来。他的笔墨没有满足于描写现代的现在的桑干河,而是挖掘到唐代的桑干河以及以桑干河为素材的诗人们,作者还不满足,眼界已经穿越时空,抵达几十万年前的桑干河,当时“这里曾经是一个大湖,湖水碧绿,岸边森林茂密,成群的恐龙生活在这片森林里。”当然,这只是作者的想象,但这样的想象可以使人类清醒地明白要敬畏自然,能够决定地球生物走向的,不是人类,而是大自然本身。阅读西部散文,渐渐会被一种强大的气场所熏陶、感悟:人在环境中生活,无不打上深深浅浅的大自然印迹,人类尽管经过努力可以改变大自然一小块,人的生活却无法决定大自然的走向。中国的西部具有西部的野性和骨感,当然由于文化的交流,东西部会沟通,但西部是就是西部,永远成不了东部。作家宋红红的《与高原血气相通》,就彰显了陕北人和黄土高原之间的联系,“生活在陕北高原上的祖祖辈辈,摸爬滚打在陕北大山大河中,吃五谷杂粮,行万里后原土,他们的血气相近,一脉相承。”
三、中国西部自然风情之魅力
自然万象,浩瀚天地,人有人的活法,自然有自然的走势,相对于人类而言,大自然的奥秘总是给人以惊奇。人类文明进步的每一步,都含着向大自然学习的单元。中国西部散文的独特性,首先在于自然风情的独特。自然风情是“物”,物可格致,没有丰富多彩的西部自然风情,就没有西部散文的生长的土壤和肥料。关于西部散文的独特性上,笔者和史小溪先生的认知是相通的:西部散文创造出了独特的西部之美,她所哺育的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艺术;是天山南北民间热瓦普、刀郎木卡姆的艺术;是河西走廊丝路花雨的艺术;是那遥远地方牧羊女的艺术;是陕北粱峁沟壑信天游、腰鼓的艺术;是蜀道难、难以上青天的古栈道艺术;是震撼心弦的侗族大鼓苗寨民间艺术,是悠久的川滇茶马古道的艺术;是天堂一样奇妙的藏歌艺术……“她永远存在,永远都在丰富着我们的情感世界与精神世界。”(史小溪语)或者可以说, 构成了西部散文的神性特质。
西部的山,不仅雄浑还有包容那一面。刘燕成笔下的黔中天台山就是静美地,有禅音,同时也是慈善的,因为她“养育了这个流落的明朝帝王”(明代建文皇帝)。日月星辰是古今人们所司空见惯的,然而在不同的时间、地点、不同的心境下,人们眼中的月亮却不同,作家刘乐牛写了戈壁滩的月亮和星空,作者深入戈壁滩,从没有见过如此壮观的星空,只见“从东北向西南斜贯而去的银河,逶迤而苍茫,浩然而洪荒,就像有不可知的力量在汹涌,在奔腾,在呼啸。”远离城市喧嚣的戈壁滩,“是一片没有被人类足迹踩脏的净土”,给予人的内心一种神圣的庄严感,仰望星空之人,才会怀着敬畏之情去思考人类生活的正途和道德格律。
史小溪先生是西部文学的领头人之一,他具有深厚的西部情结;他多年来甘于寂寞,执著砺练散文。他一直把西部散文视为“遗留胎气的散文,贲张血性的散文”,一直为中国的西部散文呐喊助威。史小溪是一位人文素养积淀很厚实的作家,他写的《延安,历史传说和谜》,记载了他受延安民政部门委托,为延安最宽敞的“二道街”更名为“肤施大街”的过程;这个更名来源于“尸毗王”(传说是释迦摩尼第三世的化身)舍身饲鸽的故事,作者认为,“肤施”更能体现延安的胸襟,是延安的标识,也是延安的德格风骨。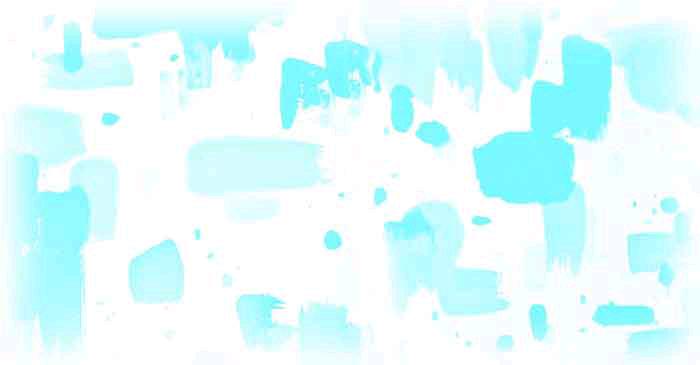
西藏是世界屋脊,当然是中国的屋脊,作家周闻道写的《寻找自己:走向西藏》深情地顿悟西藏。他去西藏寻找的是一方净土,“寻找的是觉悟之门,让灵魂获得清净的栖居。”大凡有大格局的作家,面对“宏伟之风景”,消失得是小我,找到的是大我。去西藏寻找,周闻道找到的是“天人合一”的大我。他在可可西里地区,看到的山,已经不再是山,而是“一尊佛,耸立在泥土、岩石、冰雪、河流、草木、飞云、岁月和藏羚羊的嘴里”,因而,物质的世界化成了人类心灵的世界,而心灵世界则呼应着物质世界。作者在可可西里,看到的天已经不再是“纯粹的天,而是思想!”作家澎湃的《孟溪,青杉的水袖》写的是云贵高原上的梵净山。李文强写的是夏合特库姆沙漠上的“红马群”:马群是红色的,牧羊犬是红色的,一切都是红色的。作家彭殿基写了黔西南的万峰林,“多是有形有貌,俊俏得像模像樣的是山,一座座都很有灵气,或清秀柔润,或枯瘦嶙峋。”山很美,作者并没有止步于赞美,而是把思维涉及“美的社会性”,“在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日子里,谁有半点心思欣赏万峰林崎岖曲折之美呢。”
作家祁建青,也是著名土族作家,他的《黑土白雪之蓝天青稞》,对于青稞的个性有生动的描述:“好倔强的青稞,决不妥协宁折不弯的青稞,‘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一点不给人留什么情面的青稞。”大自然的气候变暖,有自然原因,也有人为原因,青稞就成了气候变暖的牺牲品。作者是有忧患意识的,由青稞北移而联想到冰川消融,进而进一步联想到东西半球的自然灾害,痛心地告诉读者,“一个独立事件,必有内在的因果奥秘。遥望东部和南方连降大暴雨、特大暴雨,城市乡村饱受煎熬,我们身边种下又死亡的青稞,却在风调雨顺中表达怎样的临终独白?”对于高原人来说,青稞不仅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作者强调了青稞的文化符号,“青稞首先以一种文化符号呈现于视野……青稞,这庄稼中的庄稼,麦子之上的麦子,季节的旗帜与领跑者,如高原鸟中猛禽,花中雪莲,林中云杉,就在那里,雪山不是虚设的风景,黑土有黑土的光泽,青稞仅在自己喜欢的山坡之上。”endprint
竹子,在南方是常见的植物,却被文人雅士读出了文化品格。作家汪伟跃写了是自己故乡的斑竹,贯穿了历史传说中的舜帝二妃——娥皇和女英——对爱情忠贞不渝,进而将斑竹“人格化”为忠诚于爱的品格。作家凌鹰的《渠江黑茶》写了茶,从历史的见证看,黑茶穿越了2100年的时空,后人从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杔侯利仓妻子的坟墓中,寻找到了渠江黑茶的踪迹,从渠江黑茶的性格看,“历来就有‘山崖水傍,不种自生的野性,自然就有了一种原汁原味的野味”。此文还插叙了西汉张良的命运,张良作为西汉重臣,帮助刘邦打下了天下,偏偏对官场无趣,“退出大汉政坛后,张良四处云游去了”,可谓是人生智慧也。
如果说“西部”是一个固着的文化符号,土生土长在甘肃的孟澄海,则是一位西部文化的守望者,他的散文《河西苍茫》,以极为宽非常宽厚的西部呼吸向不熟悉西部的读者,推出了一幅幅散文的西部版图。作者笔下的焉支山,洁白,安静,“没有古代民族争斗和厮杀。白雪下,两千年前的烽火狼烟,灰烬不留,剩下的是地衣青苔,层层叠加,斑驳如云。”在作者的笔下,焉支山是灵秀的,内敛的,绝没有祁连山的“霸悍和浩荡”。祁连山下的茫茫大草滩,曾是古代游牧民族驯马的地方,但时光匆匆,盛况不再。孟澄海还描写了明长城(蒙古高原与河西走廊的交界)。“任何高墙堡垒都不可能拯救王朝命运,决定战争胜负的是人民,是民心”。 孟澄海写瞭高山,着重写山顶,“无雪无树,荒旱稀疏凌乱,少葳蕤之势。”山是凝固的,人是成长的,作者在不同年龄段登瞭高山,年龄越大,认知越成熟。
中国的西部,多山,多石,作家许辉就对石头有崇拜感,认为“每一块石头都演绎了一个古老传奇神话,每一块石头都蕴含着一颗纯洁高尚的灵魂。”许辉由石头而发现自我,发现了“感知的温度”,发现了“操守和信仰”。青年作家王信国在《边塞地带》,表现了麦子的神性,发现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幸福感和自豪感。作家余远忠在北纬二十八度以北发现了美——特殊的美。他写了《大美画稿溪》,在画稿溪发现了十二万六千株挱罗树,还有极为罕见的川南金花茶,通过这些罕见的植物向人们讲述做人的道理,“不炫耀,不争春,因而躲过了人们的砍伐”,作品安静的氛围,营造得很好,“身处其中,没有什么名句逼人吟诵,也没有什么悲剧让人感慨,也没有一尊庄严的塑像压抑精神,一切是那么的随意,一切是那么的宁静。”这就向人们呈现出了一种文化精神。
西部是特立独行的,也是开放的,比如西部的葡萄,便是西汉张骞出使西域,从外国带回来的。作家温国写的《葡萄志》,介绍了中国宣化种植葡萄的状况。一种植物和一个地域兴盛息息相关,宣化因葡萄而发达过,葡萄这个植物,也因“现代化”而消失。郭文连通过解读西部古代的龟兹国,向世人传递出做人的哲理。隋炀帝酷爱胡乐,唐太宗喜爱《破阵乐》,他们都爱音乐,一败一兴,并非乐之因也。作家施昱写黔西南的草海,除了写出了美和人文气息,还写出来了人怎样与大自然和谐相处。草海如此之美,也曾在某个错误引导下,出现“草海被放,被破坏,草海逐年缩小”,因而造成了湖水减少,气候恶劣,这样的历史教训,不得不永远记住。
作家张亚宁也是陕北人,他写陕北窑洞,连带叙述了中国的窑洞史,从古代一直叙述到现在。作者对现代窑洞的窗户之美,进行了细致的审美刻画,从居住的角度呈现了 “天人合一”。 作家刘梅花生长在西部甘肃武威,她写的散文《林深人不知》,不是西部山水原生态的素描,而是对画家八大山人画卷的解读。对于一位写作者,可以感受实际的山水,也可以感受画家再创造之山水,不仅解读出山水之灵气,也解读出画家的精神状态,这是一个有难度的精神“相遇”历程,不仅需要把握住画家的心态,还需要具有较高的艺术欣赏力,然而,刘梅花做到了,这实在是一种难得可贵的艺术天赋。李天斌是贵州一位重要散文作家,他有将物象和心象融合的本领,用独特的视角解读了不少云贵高原上的风物。作者在《虚构的风物》中,把心灵的渴望化为普通的神奇;在他的《农历记忆》中,展现了自己对农耕劳动的审美情结,“人的生命,总能从农历中寻到遥远神秘的对应”;他在《水麻柳与何首乌》,咏叹了这两种植物的平民性,“它们是普通的,但作为日常的构成部分,一度融入了我们的生活”。它们是植物,也是药材,正如作者所说,人与植物的相遇,也是需要特定的时间和空间。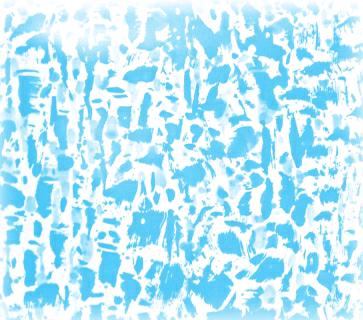
辽西作家袁海胜,在他的散文《庄稼的灵性》,以前所未有的姿态完成了一次反璞归真。准确地说,袁海胜是为我们司空见惯的北方的四种粮食进行画像,它们分别是:玉米、小麦、高粱、小米。袁海胜不仅对四种粮食进行了外表描写,还进行了精神刻画,赋予了四种粮食以性格和品质,比如说高粱是仗义的,“在贫困时代,高粱米立下的功劳要大于其它粮食,它贫瘠的营养更贴近民生。”比如揭示玉米的人文内涵,“玉米粒的黄与白,乃至斑斓都适中,粮食的颜色不需炫耀,任何一种都有亲切感,人的目光触及后变得柔和,心生敬畏。”比如形容小米之伟岸,“小米对自己的名字很负责,小至精微,米至淳朴”。比如点赞麦子之优美,“麦子的优美身姿站在本是贫瘠的辽西朝阳,像天使一样矜持,麦田整整齐齐,全副仪仗,宛若心怀喜庆。”由此而感悟,粮食是大自然衍生出的精华植物,人类籍此才得到生存和繁衍。
文人騷客们解读江南古镇时,常常习惯于小桥流水的温情。在西部,地处滇藏高原有一座丽江古城,也是充溢着河水的温情。作家吴学良的《轮回在丽江古城的水月与时光》,极为宁静地解读了这座高原古城,古城里的玉河九分丽江古城,河滨上有许多石拱桥、条石桥、栗木桥,“古城也因此就具备了旺盛的生命力和动人魅力”,也就是说,没有河水,就没有丽江古城,正如作者所总结的“水是一种般若(佛教语:智慧),一种生命哲学”。作家秦汉写了《西晋的芦苇》,月光照在焉耆七个星寺佛祉,是当年佛教东传必经之路,而现在则“坍塌的废墟,与严冬的气候一样冷清”——这就是时间,时间要超越宗教,但时间无法超越文明。人,作为高级生物,人心向善是一个大趋势,无论是作为宗教人,还是自然人,都需要“超越取舍心,超越爱憎心,超越得失心,便能获得快乐与祥和。”人类社会存在无法跨越的利益,偏偏修养需要我们超越利益,做一个本真的人,这是作者给我们的启示。作家王林先写了一位特殊的猎手,一位有宗教感的猎手,用“梅山之数”狩猎,会咒语,这不仅仅使读者感到新奇,亦可感悟自然与人的关系。王林先写的《末代地主》是以实事求是的勇气写出来的,不是从概念上解读地主,而是写了生活中的“这一个”,一位为村民做事的英雄。
在这个浮躁喧哗的时代,消费文化已成为一股潮流,文坛和文人已被打上深深的商业烙印。理想信仰、艺术良知已不再是他们的心灵依仗,金钱的欲望才是很多人的追求……读毕《雪莲》“西部散文擂台赛”散文,却感到振奋和血脉贲张(由于篇幅所限,只能选取一部分进行评述),笔者深深惊叹于在中国的西部,还有这样一批散文家写着雄浑,苍茫,厚重,开阔,大气的西部散文!笔者感知着西部作家对良知的坚守,他们的博大的人文情怀和可贵清醒,“他们透过纷乱层积的史实,洞悉这些物象的真谛,展示独特新鲜的见解,传达着沧桑而温馨的生存体验,张扬着勃勃的生命激情。”(史小溪语)可以说,西部散文的写作实践代表的是一种精神选择,是一种比生活目标更高的生命追求。
笔者坚信,那些永远不会随时代舆论变迁而沉浮的文字,才是经久不衰的艺术,因此,西部作家和以西部为题材的散文家们,正处在任重而道远的关键时期,所以著文为他们加油助威,并再次感谢《雪莲》的道义坚守和文化选择。
【作者简介】王克楠,本名王克难。内蒙古乌兰察布盟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邯郸学院客座教授。现居贵州。所创作散文、散文评论散见于《散文》《美文》《散文百家》《天涯》《黄河文学》《青年作家》《北方文学》《民族文学》《中华散文》《四川文学》《长城》《山东文学》《奔流》等文学期刊。散文作品被选入《青年文摘》《散文选刊》《中华散文百人百篇》和年度散文年选集数十种。获得中国冰心散文奖。出版散文集《巷子里的阳光》《放飞年轻的梦想》以及诗集等共五部。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