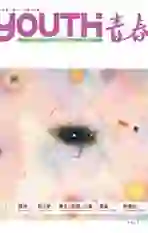迷失的晚餐
2017-09-08周伟
周伟
其实我根本不用回忆,张兰的眼睛从来没离开过我的脑海,但他们还盯着问,非让我眼前浮现出血流如注的画面——沁入泥土的血立刻变为深紫色,而池塘里的血却颜料般的漾开。我眩晕、恶心、浑身虚汗,却不得不一遍遍回答。
我更不愿看到每次提审时父母都在场。我妈坐一会就开始哭,嘤嘤的很烦人,而我爸一进来就握紧拳头,像是要随时冲上来给我一顿暴打。他要是真那么干我倒无所谓,我也觉得自己该挨顿揍,但这与审讯无关,他们在场只会使我吞吞吐吐,谁都明白有些事是不该当着父母面说的。还有就是审讯结束时我妈总要喊“小光”,那声音就使我不敢回头。我觉得他们都希望看到我哭,包括那些穿制服的,似乎我哭了就能使所有人都获益,但我清楚这事该怎么着还得怎么着,哭也没用。
上次提审前我对看守说我不希望把我父母叫来。那家伙把眉毛揚得老高:“怎么?害羞?”我觉得他想笑,他却绷着脸说:“审问未成年犯罪嫌疑人时必须有监护人在场,这是法律。”
每次提审后我都想吐,因为我被掏空了,只剩下一个没人知道的问题:张兰看我时是否还有知觉?黄松当时在我身后,只有我看到张兰的眼珠动了一下。
答案已随她而去,没人能回答,但它一直堵在我喉咙口。被他们问来问去时,我的确有一吐为快的冲动。那是解脱的诱惑。我当然知道这个细节对我的定罪有多重要,所以时时提醒自己:别开口!
翻来覆去的问题使我忘记了提审的次数,但我记得进来才十二天。
那天九点来钟,黄松打电话叫我过去。我到了他却半天不开门,原来他只穿了条三角裤。他冲回床上用毯子掩了下身,又抓起手机摁起来。和往常一样,他的手机连在充电器上。“你还不起?”我说。他嘿嘿一笑:“我和这小妞聊得软不下来,你去烧壶水。嗳,少烧点,我都渴死了!”
这房是邓雪梅的。她家拆迁分了四套房,她有三个哥哥,而当时她已经跟黄松好上了,所以她家人起初没考虑她。她把全家人告上了法庭,拿到了这个单室套。她父母现在跟她大哥过,也在这个小区,两室一厅挤了五口人,成天吵架。邓雪梅看到他们就像看到陌生人一样,她曾对我说:“你还小,你不懂。上过法院了哪还有亲人!”
我知道我爸有一回把欠我家货款的人告上了法院,后来就不跟那人做生意了。亲人上法院会是什么样?
但她对黄松又那么好,装潢买家具没要他一分钱,装好了让他在这儿住,过年前还送了他一部手机。虽说不是名牌,但到底是4核5英寸的,拍照、录像、聊天、打游戏、看外国街景,把我眼馋死了。她自己在脱水蔬菜厂上班,经常加班到半夜,而黄松干任何工作都没超过一星期,大部分时间就在她床上躺着。
大家都以为邓雪梅对黄松好是因为他长得帅,我却发现还有一个原因:她比他大两岁。有几天邓雪梅连续加班,做的全是快餐面里的葱花干,黄松就存心躲着她,说受不了她身上的那股味。邓雪梅大闹一场,并要黄松写保证:今后不管厂里加工什么都不得疏远她,在她上了岁数之后更不能嫌弃她。“要不是我比你大两岁,哪个要签这鸟玩意?”她抹着泪说。因为当时没有别人在场,他们拉我当见证人。我觉得在一张纸上写几句话肯定不管用,不过为了尽早回家,我还是签了字。
黄松上网就为找妞,跟邓雪梅住到一起后还被我瞄见几次。“你不怕惹麻烦?”我说。他瞪着我。我知道自己多嘴了,但我绝没有告发的意思。
他忽然笑了:“你以为男人有一个女人就够了?”在厨房烧水时,我又想起他这句话,但我确实认为有一个女人就够了,因为我还没有女人。
黄松喝了头泡茶,起身钻进厕所。我隔着门问他叫我来有什么事,他说一会和他一起去车站接个人。“是邓姐的亲戚还是你亲戚?”我问。
“你亲戚。”他就是这样回答的,我问了几遍才听清楚。他一般不跟我开玩笑,所以直到他洗漱完出来,我还在厕所门口不知所措。 “我亲戚?我什么亲戚?”
“来。”他用勾成鹰爪般的手让头发蓬松,带我来到床边,拿起手机说:“就是她。”
于是我看到了张兰——名字是我后来知道的。她手机的像素不高,有点模糊,是傻妞玩自拍的标准式样:勒头、向上看、撅嘴。我在网上见的多了,其实她们的眼睛没那么大,人也没那么娇滴滴。
黄松收拾好手机:“今天你带钱没?”他一贯如此。我辍学在家,父母把钱抠得很紧,他明明知道却总要先问一句。不过他并不小气,问过之后吃东西、买饮料就都是他掏钱了。
“妈的,我身上的钱也不多。她跟我吵架了。”他说。
“我陪你接了人就回家吃饭。”
“你不能走。万一她回来撞上了,你得说是你亲戚。她这几天下班没准点。”
天呐,他真的有第二个女人了!我憋到去车站的路上才问:“什么时候搭上的?”他白了我一眼,没绷住,嘿嘿笑了:“最近两星期。”
我跟黄松认识快两年了。我被二中劝退后,跟我爸打了半个月的架。我爸怎么都想不通,一年忙到头都是为了我,而那么多学生中只有我被劝退。说着说着他就打上来,下手很重。我当然要还手,我就是因为打架而被学校劝退的。不过还是我吃亏多些,谁叫我是儿子呢?但反抗还是起了点作用,到后来他也不抬手就打了,更多时候是瞪我两眼,长叹一声,然后揣上香烟去门外继续长叹。一个月后他托人联系到了洪仁中学,那学校很远,在城乡接合部,大门临街,三面被农田包围,但可以住校。我只对最后一点满意,估计我爸也是。
洪仁中学学生很杂,学习刻苦的大多家在农村,像我这样花钱来消磨时间的也不少,而每天往返的都是学习刻苦的,住校的大多是消磨时间的,听上去像是个玩笑。食堂伙食很糟,午饭还能勉强下咽,因为校领导、教师都吃,晚饭就不能看了,一菜一汤。学校规定住校生必须在食堂吃晚饭,但那盘烂糟糟的东西也叫菜?
我只在食堂吃了一顿晚饭,第二天放学就出了校门。附近什么都有,网吧、小吃摊、大排档,做生意的为我们考虑得挺周到。网吧网速很慢,根本不过瘾。走出网吧我吓了一跳,很多住校生都在这儿,而且成双成对。他们靠在一起,还互相喂着吃,旁若无人。跟我同班的一个家伙竟然用左手挑起面条,然后把嘴朝上凑,只为不放开那女生的手。endprint
很快我就盯上了一个有时回家有时住校的胖女生。她叫杜秋丽,嘴巴里总在吃着什么,腿很粗,眼睛像睁不开似的,成天裹着校服,但胸脯还是显得很饱满。有个叫吴岳的胖男生对她有兴趣,但她对吴岳很凶,显然我还有机会。我在这儿还没打过架,所以找她说话时她一点都不凶。这使我很受鼓舞。
机会终于来了。那天像是要下雨,放学时我就盯上了杜秋丽。她果然没回家,在那一排小店里东张西望的挑零食。我进去对老板说:“两卷陈皮。”然后假装吃惊看到了她 :“哇,是你?”她说 :“男生也吃陈皮?”我说:“有规定吗?”她笑了,下巴上的肉粉嘟嘟的。外面人多,我们就在小店里呆了一会。我买了几样东西,都要的双份,但她只接了一小包话梅。她说她讨厌吃饭,从小就讨厌,只想吃零食,上课都忍不住朝嘴里塞点东西。那一刻我真想把身上所有的錢都买成零食装进她的书包,只要她愿意。
后来我们一起去吃饺子,因为是第一次,我只能坐在她对面。她拿筷子的手势很可笑,我是多么想把她的小胖手抓住呀!将近吃完时我说:“下次还一起来吃吧?”她没回答,甚至没抬眼,但蘸醋的手停了一下,害得我整晚都在琢磨她到底是同意了还是没同意。
第二天我想明白了,她是不会直接表态的。我应该在放学时和她一起出校门,她要是回家我就陪她去车站,她要是不走我就买零食给她吃,并找机会碰她的手。那天我的眼睛就没离开过她,而且越来越觉得杜秋丽这个名字很美。我也觉察到了吴岳的目光,那是一种嫉妒的阴冷,但我没工夫顾及他的感受了。下课后我以最快的速度出了教室,不料还没到校门口就遇到了我妈。“小光,这几天怎么样?”她在人群中把一个塑料盒塞给了我。
“什么呀?”
“糖醋小排。”
我急了:“你拿糖醋小排来干嘛?”
“哎呀我不是怕猪蹄在食堂吃不方便嘛!”妈知道我最喜欢吃猪蹄,忙不迭解释,“这是用仔排做的,我把骨头都剔掉了!”她话没说完我就看到杜秋丽出了校门,那感觉别提有多糟了。当晚我把那一盒小排吃了个精光,味道很好,但我心情还是不爽。
吴岳加紧了攻势,有一回我看到她朝杜秋丽的课桌里放了两袋零食。她发现后愣了一下,但并没有回头,两节课后她竟打开吃了,我的感受就别提了。她不知道是谁给的怎么就吃了?她如果知道是吴岳给的怎么还吃?直到我又看见她对吴岳吼“你烦不烦啊”才舒了口气,不过对她的印象也大打折扣。如果再有机会在一起,我肯定不会装腔作势。
事情比我预料的来得快。那天她又没回去,我和她再次在那家小店“巧遇”。我买了几样包装好看的零食说:“今晚我也不吃饭了!”
马路上都是人,我们边走边吃。她讲了因吃饭问题而和她爸闹矛盾的事,我没怎么听进去,只想带她朝农田里去。一对对靠在学校围墙下的景象谁都见过,可是天黑得很慢。
终于天色合适了,我说:“我们朝那边走走吧。”
“上那边干嘛?”她嘴上说着,脚步却已改变了方向。我抓住了她的手,她往后缩了一下,但没挣开。
前面有一对靠墙搂在一道,身后有一对朝这边过来,不能再往前了。我把她朝墙根拉。“干嘛……?”她话没说完我已吻了上去。她有一股奶油的甜味,原来她把舌头伸给了我。我几乎立刻就探到了她的奶子,海绵般的柔软,溢出手掌的满满一握。她喉咙里发出唔唔声,却绝不让我再进一步。
朝回走的时候我们没说话。原先跟在我们后面的一对此刻走在前头,身后是最先到墙边的那一对,他们也没说话。三对人保持着相等的距离,沿白花花的小道返回,除了急促的脚步就没有其他声音。这感觉很怪,我估计是因为大家刚做了相同的事。
不料吴岳在校门口站着,见了我们眼睛眼珠子都快迸出来了。“你去哪了?”他的声音像是卡住了一样。
“要你问?”杜秋丽叫起来,“烦死了你!”
吴岳一把拉住我:“你活得不耐烦了?”
我说:“你放开。”
他放开了。“沈光,我们走着瞧。”
我知道要有架打了,但吴岳不是我对手,当晚也没发生什么事。第二天一进教室我就感到了明显不同——跟吴岳玩得好的那几个不时用眼角瞄我。我明白了,他们要找机会一拥而上,我将吃个大亏而且无法指认谁,因为他们会众口一词。我可以回家,也可以不出校门,但那只能躲一时,而他们的计划会越来越周密,最后在一个神不知鬼不觉的地方把我朝死里揍。
放学后我冲出校门就钻进了一家网吧,平时我嫌它网速慢,但那里地方狭窄,他们没法一起上。一个很帅气的大男孩在跟老板聊天,这正是我希望的。我立刻掏了5块钱给老板。他问:“一小时?”我说:“不要找了,放在这儿以后一起算。”那个帅气大男孩笑了:“蛮大方的嘛?”我赶紧也笑一下:“反正经常来。”
我刚坐到电脑前,吴岳那几个就到了,聚在门外探头探脑。老板招呼他们进来,他们半天不回答。老板不高兴了,“你们进来就进来,不进来就走开,挡在门口我怎么做生意呀?”
吴岳叫起来:“沈光你妈了个逼的有种你出来!”
“嗳,别在我门口闹事哦!”老板说。
“你叫他出来!”
那个帅气的大男孩突然发话。“操你妈你命令谁啊?你想叫他出去?来,别怕!”他拉我走出网吧,“他出来了,你们哪个上?”
他们都愣住了。
“你他妈的长几个脑袋,敢在这个地盘上发号施令?我跟你们说,谁敢动他一指头就下辈子再来上学!”
转眼工夫他们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冲我一笑:“你继续玩吧。”
他就是黄松。那天我没去晚自习,不是怕吴岳,而是要请黄松吃饭。他坐在小摊上喝了4瓶啤酒,然后搂着我的肩膀叫兄弟:“今后你的事都包在我身上了。”
几天后我把杜秋丽指给他看,他做了个鬼脸。“看不出你心还蛮大的,这么肥的女人上起来过瘾吧?”我被他说得不好意思,事后想想杜秋丽确实太胖了点。endprint
认识黄松后,我在学校里火了一阵子。班里就不用说了,吴岳那帮人成天围着我转。后来我带他们揍了一个高年级的家伙,因为他在排队打饭时给了我一肘子。我的手下个个奋勇当先,那回他被收拾得够呛。他用几天时间召集人马,约我在校外农田里决战。谁知走漏了风声,警方都出动了,我被洪仁中学除名。
那次我爸竟没打我。“你以后就每天在家呆着,我回来要是看不到你,看我怎么收拾你!”然后他指着我妈说,“我们的钱已经都花在他身上了。你要是再给他一分钱,我马上跟你离婚!”
拘留所里的夜比白天更难熬,熄灯之后就不准说话了。窄木条钉成的床板很硌人,野猫在附近发了疯似的叫。你躺在这样的夜里等待瞌睡来临,等来的往往是一阵燥热。
我有时也想找回抵着墙使劲揉杜秋丽的感觉,但眼前顿时浮现出张兰的裸体。那非但不能激起我的欲望,反而使我在顷刻间万念俱灰。认识张兰后不到两小时我就看到了她的奶子,不大,却挺挺的。我没碰她,我有机会的,但没那么做。
那天都快到车站了黄松才说:“网上的事没谱,谁知道她发来的照片是真是假。你在出口等着,我在售票处那边。她要是太丑你就直接撤!”
我站到了出口栏杆外,心里憋着气。这些日子我爸每天都在抱怨,说这个季节去收粮简直就是浪费汽油,他很可能中午回家。我冒这么大的风险黄松却不领情,还要处处显他很牛逼,这就不够意思了。再说我不喜欢他搞其他女人,邓雪梅向来对我客客气气,有回看到黄松把我支来支去,她还对他吼了几声。她当着黄松的面对我说:“沈光,他就这么一摊了,你比他小,跟他混个什么劲?”邓雪梅真是个好女人,黄松跟她来这套无论如何说不过去,而我这会儿竟正站在大太阳下帮他欺骗她!我握紧烫手的栏杆,心想是该找机会离开黄松了。
那趟车晚点了一会,我希望它永远晚下去,哪怕被我爸狠揍一顿也值,但它只晚了七八分钟。黄松说的没错,我一眼就认出了张兰。她站在出口处,装模作样踮起脚尖四下打量,还撅着嘴,跟照片上一样做作。那些拎着大包小包的人得从她身边挤出来,她至多闪一闪身子,却没有挪个地方的意思。好一阵子我甚至忘了判断她好不好看,只想晾晾这个俗气的女人。我想好了,只要她走出那扇门的范围,我马上就去对黄松说 :“她没来。我得回家了。”
但她没走,在出口处只剩我们两人之后,她盯着我看了好一会:“你是来接人的?”
我过一会才回答:“你是张兰?”
“啊!”她吓得不轻。
“黄松在那边等你。”说着我就朝售票处走,她迟疑了一下才跟上来。说实在的,她并不难看,但拿腔作调的,显得很俗,这一点就不如邓雪梅,甚至不如杜秋丽。
“怎么这么老半天……”黄松说到一半脸上的表情就变了。那不是笑,而是朝张兰忽闪眼睛。我还没反应过来,张兰就上去搂住了他的胳膊。黄松亲了她一口,在她耳边嘀咕了好一会,再撑住她肩膀盯着她眼睛看,然后又亲她一口。
黄松经常当着我的面亲邓雪梅,有时是她生气,他哄她,有时是邓雪梅撒嬌。我从不把头扭开,他们亲的自然,我看的也自然,但他刚才亲张兰却显得做作。他根本不可能那么爱一个初次见面的女人,深情的注视就是表演。不过张兰显然喜欢这样,在他肩头偎了好一会。
“那我还是回家吧。”我说。
“你不能走!”黄松放开张兰,“我们一起吃饭。”话没说完黄松已迈开了脚步。他速度很快,跟平时完全不一样。张兰一路小跑,但他没有与她并肩走的意思。我不紧不慢跟在后面,琢磨着黄松的心思。他大概是不想在大马路上被人看到和张兰挽着走。
从黄松今早的反应来看,他们聊得肯定很露骨。黄松肯定说了要跟她睡,她就坐长途车来给他睡。天下还真有这样的女人,黄松明明有女人的,偏偏又让他给碰上了。
黄松找了家小饭店,看上去很冷清的那种。老板推荐粉蒸排骨,说老顾客每回都点,但费点火候。黄松问了价,说身上没带多少钱,让老板报几个普通菜。张兰连忙说她有钱,让老板就上粉蒸排骨。
我有点吃惊,因为俗气的女人都是很计较钱的。邓雪梅不跟黄松计较钱,所以她不俗气;杜秋丽跟我还没到计较钱的那一步,但她总是看着我掏钱,连句客气话都不说。那其实就是一种计较,所以离开洪仁中学后我再没去找过她,因为我没钱了。
我想粉蒸排骨的味道一定不错,起码对得起我冒着大太阳跑这一趟,但黄松一个劲反对,说那太费时间。他坚持只要两个简单的菜。
“你今天还有事?”张兰用的是撒娇的口气,但她的嗓门太大。
黄松脸一红,抓住她的手揉捏起来。“想尽快跟你在一道呀!”
又是表演,而且糟糕透顶,连我都看不下去,但我惊讶地发现张兰一下子漂亮多了。这是我第二次正视张兰,她皮肤不白净,额头上甚至还有点汗,可就这么会工夫,她整个人已散发出一种柔和的光。
老板上菜之后我才意识到那是她眼睛的原因。她的眼睛忽闪忽闪的。有人说“女人因爱情而美丽”,我一直觉得那是屁话,一个人生来就那样,除了花钱整容,还有什么能改变容颜?但此刻我真有点疑惑,因为她的确变化不小。
我忽然转过弯来了:她不仅是来让他睡的,而且真的爱他,但问题是他会为了她而抛弃邓雪梅吗?那,睡过之后怎么办?那顿饭我没吃出味。我得走,不管他们怎么收场,反正不会是个好结局。
黄松叫“买单”,张兰赶紧掏钱,黄松争了一会,结果还是张兰买的。我站起来说:“我真得回家,我老爸说不定已经到家了。”
黄松眼一瞪:“干嘛你?你爸要回家早就回了,不差这一会!”
张兰说:“他有事就让他走嘛!他又插不上话,老呆在旁边多没意思呀。”
黄松没理她,把我拽到门外。“你到底想怎么样?我跟你说,今天我的事成不成就看你的了!想想我这几年是怎么对你的!唔?”
我只好点头。
他给我下达了具体任务:跟他们一起回家,进入小区时带张兰走在前头;他们进入卧室后,我得大声说“我走了”,然后把门重重地关一下。但实际上我人不能走,而是去厨房窗口盯着楼下,防止邓雪梅突然回来。endprint
“邓姐要是回来我怎么办?”
“你立刻叫我,然后张兰就是你亲戚。”
“你们说什么呢?”张兰出来了,一脸疑惑。
“没什么。”黄松又搭住我的肩,“沈光最近和家里不开心,我劝劝他。”
张兰的眼睛又亮了。“唔,够朋友。”她可能脑子不太灵,这么多破绽都看不出来。但她比先前更耐看了,这也是事实。我们三人并排走着,我不时偷眼瞄她。她要去跟他睡了,却没有一点害羞的意思。杜秋丽从不拒绝跟我去学校围墙外,但她一踏上田里的小路就不说话,而且我们只是亲一会摸一会。张兰一路神采飞扬,还咯咯地笑,我很难接受这一点。
可我为什么越来越想看她?我想到了性感这个词。这个词被用得很滥,我曾经以为那就是指大奶子和大屁股,杜秋丽奶子屁股都大,可黄松见到她的表情说明她根本不性感。看着张兰眼里的光,我有点开窍了:性感与好看难看无关,它是一种令你想入非非的特质。
晚饭又是冬瓜辣椒烧茄子,这个过去从没听说过的菜我进来后已吃了不下5次。我想大概只有洪仁中学的晚饭才能与之相比,随即我意识到它们无法相比,因为我在这里不能问“今天什么菜”,而且在今后大约十年里都不能问。
我不太想家,但每回吃冬瓜辣椒烧茄子时都想,甚至想起我妈送到洪仁中学的糖醋小排。那一整盒小排里居然连一丁点骨头碴子都没有,我不知还有谁能把骨头剔那么干净并保留肉的咬劲。我妈最拿手的是红烧猪蹄,还在炉子上炖着,路过的街坊就抽着鼻子问:“你买到黑毛猪了?”我妈说:“白毛的哦!现在哪那么容易碰到黑毛的呢?”他们赶紧响应:“是啊、是啊。”彼此口气都很郑重,听上去黑毛猪简直就不是猪。有一回我爸从乡下带回了黑毛猪蹄,一进门就唠叨他如何坐等褪毛,如何为猪蹄与人争执,我却发现躺在案板上的黑毛猪蹄与平时的白毛猪蹄一模一样。那天烧猪蹄时,我妈见人就说:“老头子今天碰上黑毛猪蹄了!”还向人介绍红烧猪蹄的做法:第一次加冷水煮开倒掉,佐料要一次加足、一定要用啤酒和冰糖,千万不要用洋品牌啤酒,本地最便宜的啤酒最好等等,结果那天的晚饭比平时推迟了很久。黑毛猪蹄味道的确不错,但事实上白毛猪蹄的味道也从来不差。
前些日子我妈为了不让我整天闲着,又跟我说起红烧猪蹄的步骤和要点。那天我在家正憋得上火,也不知怎的就朝她叫起来:“你跟我说这些干嘛?现在你做,将来我老婆做,我才不管它怎么做呢!”我妈一愣,随即爆发了:“你还以为你找到的女人会给你做饭?你看看我们这条街还有几个女孩会做饭的?再说我们养你这么大了,你就不能做给你老爸老妈吃?凭什么我就该一直做到死?那我养你干嘛?”我瞪了她半天,因为她从来没对我发这么大的脾气。
和我妈相反,我爸一向对我很凶。小时候我每次闯祸总是被一顿打,我就跑爷爷家去。我爸去领我时奶奶就训他:“就这么一个孩,你还动不动就打,你怎么狠得下这个心?来,你先把我打死,你不是心狠嘛?”我爸就叫声妈,音拖得很长,听上去很不服气。若是我妈来领我,她们就一起抹泪,好像以前从没有过矛盾似的。奶奶每回都拉住我的手说:“小光呀,你爸是急脾气,可他是为你好。你要听话,不能再这么厌了!我跟你爷爷最不放心的就是你!”我妈就说:“小光,奶奶说的你记住了吗?”我点头,然后跟我妈回家。我妈在路上还会埋怨几句,到了大市场却总会问 :“小光,你想吃什么?”我一般会要炸鸡腿,只有一次要了炸鹌鹑,但鹌鹑尽是骨头,后来我就再没要过。我妈自己不吃,只是在我吃完时叮嘱一句 :“小光,要记住这次的教训哦,听到啦?”所以事情基本都是以我吃完炸鸡腿为结束的。
晚饭是我们一家三口面对面的时候,我爸一天跑下来,喝酒是免不了的。过去他边喝边说在外面遇到的事(后来我发现其实很多是他听来的)。我被二中劝退后他就光喝不说了,咂酒的吱吱声也变成了咽酒的咕咚声,好像每一口都很大,而且不怎么吃菜。我也不说话,菜却不少吃,因为我妈中午总说将就点,晚饭我得补回来。
此刻面对冬瓜辣椒烧茄子,我脑子里浮现出我妈为晚饭做的各种各样好吃的,但我想不起案发当天晚饭吃的是什么了,只记得我妈的饭碗掉在了地上,但她没管,瞪着我一动不动。我爸张着嘴,嘴里满是食物。
那顿饭究竟吃的是什么呢?我把我妈拿手的菜过一遍,红烧猪蹄、萝卜炖肉、黄豆煨鸭块、糖醋藕丸、清蒸鳊鱼……都可能是,但似乎又都不是。我的记忆恐怕有问题,很多事我能记很久,真切得如同就在眼前,有些事则立刻就忘,像是从来没发生过。可那是我在家吃的最后一顿饭呀!我们从饭桌上直接去了公安局,下次我再坐上那张饭桌得十年以后,而我妈在这十几天里已经老了几十岁。
我那天脑子比平时好使,很多细节到现在都清清楚楚就是证明,甚至包括我的想法——我先是为黄松担心,生怕他惹麻烦。后来我为张兰担心,觉得她不该就那么跟黄松睡。现在看来,事情就坏在我想得太多,他们反正要睡,我瞎操什么心?在小饭店吃完饭之后我是真想回家的,虽然黄松拦我,我如果坚持要走他也没办法。
问题是我又想跟他们多呆一会,自己都说不清是为什么。张兰笑起来很响,引得路人都朝她看。她发现后赶紧掩住嘴,不是用手掌去捂,而是用手背擋在嘴边,红着脸打量我们,像是犯了错。我喜欢看那个动作,真的很有味。她做了好几次,我都看上瘾了。
到了小区门口,黄松掏出钥匙说:“沈光你先陪她上去,我去买点水果。”这是事先约定好的,但这回他装得很像。“你抓紧呀!”张兰说。
她的口气和眼神提醒了我:他们真要那样了!那一刻我确实有点晕,因为我明知那样不好,却稀里糊涂的跟到了这个关口。我知道一旦他们进了屋,事情就难以挽回,麻烦也不可避免。
“你今天怎么没上学?”
我一愣 :“哦,我辍学了。”
“学不进去了?”
“打架的。”
“可你看上去是读书的料。”她没有开玩笑的意思,我有点感动。我想把黄松的真实情况告诉她,可我怎么开口呢?正犹豫间,我们已到了楼梯口。endprint
上楼的时候,她走在前头,屁股就在我眼前晃,左一下右一下,大小正好,跟杜秋丽的太不一样了。我越发觉得她不该让黄松睡。
我家因为开店,租了沿街的老房子,我每次到黄松这儿来都觉得楼梯太长,唯独那天没怎么走就到了5楼。“哇!这是他自己的房子?”门一开张兰就惊叫起来,我犹豫着该不该说是他女朋友的,她又朝厨房叫 :“东西这么全?他蛮勤快的嘛!”
门没关,好像有人上楼,但无法断定是不是黄松。我忽然想到应该让张兰注意到另一个女人的存在。邓雪梅的东西随处都是,张兰只要看到一件就会产生疑问,那她就不会轻易跟黄松上床了。
我想到了最直接的方法,拉开卫生间的门说:“卫生间在这儿。”
“我现在不用。”她朝卧室探头。我想到床头摊着邓雪梅的东西,赶紧说:“进去坐吧,外面没椅子。”她却站住了,说:“等他来。”然后歪着脑袋听楼梯上的脚步声并把脸转向门口。黄松露面的刹那她笑得光彩夺目,我却感到一股寒气。
“苹果太小,还有斑,我没买。”黄松没笑,瞄了我一眼就朝卧室去,还顺手关上了卫生间的门。他根本没去水果摊,想到屋里有那么多破绽就赶紧回来了。
张兰有点不知所措。我严肃地看着她,希望她能感觉到我的焦虑。她尴尬地匆匆一笑,把目光转开。
黄松从卧室出来直接进了卫生间,里面随即传出收拾东西的声音。我再次看张兰,可她这次没看我。
卫生间里传出冲马桶的声音。黄松出来时已恢复了那种真不真假不假的笑容。“来,我们到里面去坐。”他拉起张兰的手,然后问我,“你也来坐坐?”
我说:“我就不坐了吧。”这也是他安排好的。
“好,那你再烧点水,烧好就放在炉子上吧。”他们进了卧室,半掩了门。
我没烧水,而是竖起耳朵,生怕错过一点声音。黄松刚收拾了卧室,就算他把床头那一堆护肤品都藏起来了,床上还有两条毯子和两个枕头,他那一侧床头的软靠瘪得厉害,有明显的油渍。邓雪梅那一侧只有一点瘪而且很干净……类似的痕迹我闭上眼睛都能列出很多,只要张兰稍加留意,肯定会发现不止一个。如果他们争执起来,我就弄出些动静,那样或许能救张兰。
但他们没有争执,断断续续的低语过后是拉窗帘的声音。我傻眼了,满屋的证据张兰居然没看到一样?她怎么这么笨?我是该走了,她摊上了给黄松白睡的命。
“我走了!”我的声音比预期的低沉得多。“有空来玩!”黄松在卧室里叫。他的声音也不正常,很干。
我在门外站了一秒钟。张兰真那么容易上手然后咯咯笑着上路?我使劲关上门,连自己都愣住了,我竟鬼使神差的站在了门里。
张兰嘟囔了一句,卧室门关死了。不一会我听到了呻吟,旋即演变成嚎叫。我知道他们在干什么,顿时口干舌燥,浑身发热——我每天幻想的事正在轰轰烈烈地进行,与我只隔了一层薄薄的门。
卧室门忽然开了,张兰一丝不挂的跑出来。“啊!”见了我她大叫一声,“他没走!”我还没反应过来她又回去了。
那一刻我真有点晕。我第一次看到全裸的女人,应该说与想象的差别不大,但与我对杜秋丽的想象又完全不同。她身上有一种炫目的挑逗。
“怎么回事?你们搞什么鬼?”张兰在里边叫。
“哎呀他是我朋友,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怎么了?”然后黄松穿着三角裤出来了,“你把她吓着了。”他大声对我说,然后朝卧室一努嘴,做了个手势。
我愣了一下,啊!他叫我去睡张兰?
“没什么!看把你吓的。”
这时他显得很丑,这是我那天第二次注意到人的容貌的迅速变化。“不!”我说,“我不。”
他嘴动了一下,却没出声,看了我一会才说:“那你站到灶台旁边,我让她出来。”
“我还是走吧……”
“不行!”他把我拽回去,“这是你今天第三次要走了,你记住,我从来没叫你帮过什么忙!”他瞪了我一会,然后朝卧室叫,“张兰你出来吧,他看不见的!”
张兰在卫生间时,我们都没说话。黄松一直在看我,我却无法与他对视。他的目光除了压力之外,似乎还有鄙视,我能感覺到。水声清晰无比,似乎显示了张兰的每一个动作……那个裸体哗啦啦的在我脑海里再现。
张兰洗完回到卧室,叫黄松过去。黄松没进屋,手把着门说:“穿起来吧,我们出去走走。”张兰叫起来:“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怪?”黄松没说话,但他的姿势明白无误的宣告事情已经结束。
现在回头想想,如果张兰赖着不走,黄松的麻烦就大了。邓雪梅说不定很快就会回来,她不会相信张兰是我亲戚的,张兰也不会任由黄松那样说。他俩要么同时离开,要么先后离开,反正是永远离开。他们肯定不会结成一对,很可能没走出小区就打起来。就让他们打吧,我则回家跟我爸认真谈一次,我要上技校,学门手艺,什么手艺都行,他会同意的。
当然,如果张兰不肯走,黄松可能会动手,但那也没有生命危险,小区的住户拆迁前就认识,听到动静大家都会过来的。
但张兰出来了。
她没我想象的那么羞怯,不过眼睛也不再放光。“干嘛这会要出去走?我怎么觉得今天好多事不对头?”
“哪有什么不对头?你想多了,就是出去走走,老憋在屋里干嘛?”他对我说,“你跟她先下去,我收拾一下就来。”
门在我们身后关上,我知道张兰这辈子不可能再进这扇门了。
“这不是他的房子?”
我没回答张兰,到这会我已不想回答了。
“是你家的房子?”
我下到楼梯拐弯处,回头与她对视。她到底给他白睡了,我先前的担惊受怕、费尽心思没一点屁用。此刻我鄙视她,甚至恨她。她看着我不知所措,脸忽然红了。这一路我们都没再说话。
小区外的水果摊格外醒目,有葡萄、水蜜桃和巴掌大的西瓜,就是没苹果。张兰却只顾朝小区里张望,根本没注意这些。我从旁边打量她,想找回对她奶子和屁股的回忆,却发现她扭来扭去的样子很蠢。endprint
黄松出来了,一付轻松的样子。“走,带你随便转转,也算是到我们这里来一趟。”
“我不想转,我有话跟你说。”
“那就边走边说吧!”
对我来说,那又是一个离开的机会。
“黄松让你做的事你都做了,他已達到了目的。你如果那时离开他们,今天就不会坐在这里。你为什么没离开?”这个问题他们问过不止一次,刑侦调查时问过,到了移送起诉阶段还问。
其实当时黄松给了我一个眼神,但什么都没说,我自己都说不清怎么就跟了过去。如果照实说,就显得我很主动,到目前为止已有太多的东西显得我主动了。
我说:“是黄松叫我去的。”
“在哪里?他当时怎么说的?”
“他说……沈光你跟我们一起走。”
“这话他在哪里说的?”
“在他们小区门口。”
“你确定?”
“唔。”
“回答‘是或‘不是。”
“是。”
“这和你上次的口供不一样,上次你说:‘他们已经走过了水果摊我才跟上去。这是笔录,有你的签字和手印;这和你对刑侦警察的回答也不一样。你在5月24号的刑侦调查中说:‘我想看黄松怎么打发张兰,就跟着去了。这是那天的笔录,有你的签字和手印。”
我的脸顿时滚烫。我听到了自己的心跳。
“而且,你的陈述与黄松的不一样,你们两人中至少有一个没说实话,也可能两人都在撒谎。你知道对检察官撒谎意味着什么?”
他的口气不重,我却连头皮都麻了。所有的细节都被问过几遍,笔录全在他们那儿,他们翻翻这本再翻翻那本,肯定能找出前后不一样的地方,换了我也会这么做。每次提审结束时我都尽量多记些我说过的话,可哪记得全呢?一旦签了字按了手印,那厚厚的一摞东西中的任何一页都可能成为我的新罪证。
“回答我的问题。”
“要说实话呀小光!”我妈急哭了。
我说:“我是想跟他们同路……黄松可以在我爸妈面前……为我说话。”
“就是说他没叫你?”
“没有。”
“可是你们不是朝你家方向去,这个你怎么解释?”
我被问住了。
“你老实交代!”我爸吼道。不用回头我就知道他的拳头握得紧紧的。
“我好奇……想看他们谈恋爱。”
“你不是对他们做的事很反感吗?而且你连张兰的裸体都看过了,低俗的爱情除了性还有什么?你还想看到什么?”
“我对张兰……还抱有幻想。”
“什么幻想?性幻想?”
我“唔”了一声。
“回答‘是或‘不是。”
“是。”
“是什么?是想和她发生性关系?”
“不是。”
“那你说是什么,你的幻想总该有个具体内容吧?”
我被逼进死胡同,不管怎么回答都不对。我妈的啜泣此刻显得格外刺耳,我爸低声喝道:“哭什么哭?都是被你惯的!”
“请保持安静!”检察官说,但我妈哭得止不住。
“我幻想和她发生性关系……”这话一出口我就想吐,张兰眼珠子的最后一动又出现了,而且有很多她的眼珠子,晃晃悠悠连成了片。
“你像是跟QQ上变了个人,怪怪的。”张兰说,嗓门还是那么大。黄松赶紧四下张望,还朝我使了个眼色。毫无疑问他是要我一起去,但那眼神里还有更多的东西,我又想到了张兰的裸体。
张兰见我过来,扭头对黄松说:“我们该单独说会儿话,他老跟着算什么?”
黄松尴尬地笑着:“他是我最好的兄弟。”
那会我真的想走了,可还没等我开口张兰就说:“你们搞基啊?”
我愣了一下。黄松说了些什么我没听见,只是瞪着张兰。
我打定主意跟着他们,反正黄松没让我走,我要把这个女人从被玩到被甩的过程看全了,也算学门本事。那家小饭店的老板坐在门里喝茶,忽然认出了我们,笑了。我也笑了,我们正在朝车站去。
我从小就有这样的感觉,到一个地方去,去时的路长,回来的路短。可那天我在车站与邓雪梅的房子之间走了三趟,来去就不好界定了,而且我不是担心黄松做出对不起邓雪梅的事,就是只顾看张兰,根本没工夫去感受。此刻我又猜测到车站后黄松会怎么表演,抱一下,亲一口,然后看着张兰走进检票口?如果她哭,他就多亲几口,与她手牵手直到检票口?可能她不哭,却骂开了,那黄松就会憋着,直到她进了检票口再笑……我到这会才觉察他的演技其实不赖,虽然破绽到处有,可毕竟没露馅。
不过事情没那么简单。到了车站广场,黄松刚跟张兰嘀咕一下她就叫起来:“我回去?说什么呢你?我来一趟就这么回去?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她没哭,而是扯着嗓门叫,路人都朝这边看。
黄松说:“别叫别叫,有话好好说。”
“你把我带到这儿就叫我回去,我怎么好好说?”她还叫,“我已经是你的人了,不是妓女。”
黄松的表情很怪,后来我才明白他是想笑却笑不出来。“那我们换个地方谈谈吧,”他说,“24路,我们上。”
“有什么话还要换地方说?我不去我不去!”张兰还没说完,黄松已把我推上了车,用的劲很大。
在车上,张兰问:“你想扔下我?”
黄松把头扭向一旁。我彻底懵了。黄松该跟张兰商量,比如给点钱什么的,而不是跳上公共汽车逃跑。随即我意识到他没钱,看来问题严重了。
24路是朝洪仁中学方向去的,我以前常坐,黄松那时就住那一带。他为什么要把张兰朝那儿带?是想离市中心远点,还是想吵起架来有人帮忙?
车开得很快,我们离邓雪梅的房子越来越远。看着张兰恼怒的样子,我不得不佩服黄松的胆量。把一个女人从外地叫来,在自己女朋友的房子里把她睡了。但那个问题还在,就是我最初担心的问题:他如何让她回去?endprint
经过洪仁中学时,店铺、网吧冷冷清清。我想到了杜秋丽,但眼前的张兰影响了我对她的回忆。只有一点可以肯定:杜秋丽的皮肤比张兰好。
终点站没有房子,只是一截宽出很多的马路。虽说离洪仁中学只有两站,这里我却从没来过。站牌下有两个老人,车刚停下他们就要上。司机叫道:“我下班了!等下一班吧!”车门在我们身后关上,张兰站在劈头盖脸的尘土中问:“我们到这来干嘛?这是地道的农村!”
司机轰着油门去了,黄松这才回答她:“我家就在这儿。我就是地道的农村人。”
张兰愣一下。“你怎么不早说?我先头就觉得那房子不是你的。”但她并没发作,“其实现在农村户口比城市户口值钱,这还要隐瞒?”
黄松蹙着眉看了她好一会:“那我们边走边说。”
他带我们朝一条小路走去。我走在后面,他们的举动都在我眼里。张兰去挽黄松,他躲了一下。“又怎么啦?”她说,还是挽住了他。
我听出张兰是想恢复上午撒娇的语调,但还没恢复到那个程度。我很吃惊,她看到黄松想甩她,怎么还朝上凑?我听说老式女人一旦跟谁睡过,死活就都是他的人了。可张兰大老远的跑来跟一个没见过面的男人睡觉,能算老式女人吗?
张兰到底把黄松挽服帖了,从背后看他俩身材还挺般配。前面是一个光秃秃的山坡,山坡下有一丛树。走近了我才看到树丛里还有个水塘,水质看上去还不错,大概是山坡上流下来的雨水。山和树都映在水塘里,沒想到在这鬼不生蛋的地方竟有这样的景致。要不是张兰在场,我肯定要脱光了下去游一把。
转眼工夫黄松和张兰都严肃了,估计已进入了正题。我想撒尿,但他们站在最粗的那棵树下,我只能到对面的那片矮树丛里去。撒到一半,他们的嗓门就大了起来。
“你怎么知道我不是处女?谁还计较是不是处女?什么年代了?”
“我计较。”
“你在网上聊天时从没说过。”
“废话!我会在聊天时问‘你是不是处女吗?”
“嗬!还想冒充正人君子?你从见面开始的一举一动都表明你是老手。”
“既然话都说到了这个份上,我们还啰嗦什么?我送你到车站,我们好见好散。”
“亏你说得出口。我们聊了两个星期,什么都说好了,我现在请假等于是辞职。噢,给你玩一把我就回去?”
“那你说怎么办?我再说一遍 :我肯定不会跟你好,你回不回去是你自己的事。”黄松冲我喊,“我们走!”
“黄松我跟你说,你到哪我跟到哪,你甩不掉我!”张兰叫道,“先头那个房子的地址我都记住了,找到房东总能找到你。不行我去派出所。”
黄松僵在那里,我也掂出了那句话的分量。“那你说怎么办吧,”黄松说,“我们总不能老在这儿耗着。他还等着回家呢!”
“他早就说要回家,从上午说到现在,先是你不让他走,后来他说走又没走,这会你又拿他要回家当借口,什么回家不回家,都是设好的局!他才16岁,帮你干坏事倒是经验十足。你们这样干过几次了?”
没想到我也被牵进去了。
“你他妈的到底想干嘛?”黄松骂了起来。
“我不能就这么回去,这太侮辱人了!”
“那你说怎么办?”
“我必须得到补偿!”
“那你就说怎么补偿吧?”
张兰斜了我一眼,大概是不想让我听到她为自己的身体开价,但她刚才说的关于我的那些话实在气人。我一直在为她担心,并给过她几次暗示,她自己反应迟钝还血口喷人。我转身走开时想:就该把价钱压得低低的,狠狠教训她一下,让她一辈子都忘不掉。
其实水塘周边就那么大,我走得再远,还是能听到他们讨价还价,何况他们嗓门都那么高。张兰要两千,黄松却只愿出三百,还把口袋都翻给她看了,但张兰一会哭一会喊,咬定两千不松口,理由还是先前的那些,威胁的话也没变,翻来覆去,没完没了。看着太阳一点点斜过去,我急了,就是打死他也拿不出两千块钱呀!
黄松终于朝我走来 :“沈光,你去跟她商量商量吧!”我差点叫起来,他拉我一下,耳语道 :“这呆逼说不通了,得干掉她。”
我吓了一跳。
“否则我们都得倒霉!”他说。
我还愣着,他又说:“你跟她说话时要蹲下,我好下手。你不要看我!”
“蹲下?不看你?”
“对。”
我半天才问:“可我跟她说什么呢?”
“就说我只有三百,她最好还是拿钱走人。”
那一刻我真晕了,既记不得怎么走到了张兰跟前,也记不得自己说了什么,而且说了一会才想起要蹲下。张兰也蹲下了,她在哭诉,我却不敢看她的眼睛,几小时前令我看不够的眼睛这会儿很苍老。
我事先猜到黄松要干什么,但看到他突然窜到张兰身后举起石头,张兰想回头,但已晚了。她“哦”了一声,朝我倒过来,我一下子朝后窜了好几米,却怎么都站不起来了。
好一会我才听到黄松说话 :“你,你起来,起来……”他声音抖得厉害,脸色发青,很吓人。
我拼命咽口水,但就是说不出话,只好指了指张兰。
“你去……去砸她!”
“我不去!”我终于叫出来。
“你必须去。她要是没死,你我都倒霉 ;她要是死了,只有你知我知。”他喘着粗气,眼睛朝上看,“你帮了我一天,我帮了你两年,你去!”
我腿软得站不起来,他拉了我一把 :“石头就在旁边。”
张兰的眼睛是睁着的。她上半身仰卧,两手摊开,两腿却是侧卧的姿势,但我没看到血。“快,我们得赶紧离开!”黄松说。
石头比我预想的重,我拿着它浑身发抖,扭头又看黄松。“快呀!照脑袋上来一下就行。”
我使足全身力气把石头举起来,张兰的眼珠突然动了一下,我浑身汗毛一竖,本能地把石头砸下去。血!我跳开,随即大口呕吐起来。endprint
黄松过一会才说:“好了?把她扔水里去。”他在翻她的包,动作很快。“唔。”他卷了几张一百元递给我,但手抖得厉害。“我不要。”我说。地上的血紫得发黑,我还想吐。
他把钱塞给我:“你搬腿。”
我不敢看张兰血糊糊的脸。她的腰露了出来,然后是胸罩的边缘。先前令我悸动的身体此刻使我踉跄。
黄松在水塘边朝她衣服裤子里塞了几块石头,然后叫“一二三”。没想到张兰几乎落在我们脚下,黄松骂了一句,脱鞋下水,把她朝水塘当中推。血在水里漾成丝丝缕缕,我担心张兰沉不下去,但她还是沉了。
那天回家的路真长,我都不知自己是怎么捱过来的,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感觉。我和黄松都没说话,也都不看对方,上了车就背对背站着,像不认识一样。街景在车窗外模糊成片,我想告诉黄松我晕得厉害,转过身去第一眼就看到他还没干透的裤腿,差点没吐出来。在我下车换乘时,他说:“多保重。”我没回头,也没应答。
打那以后我再没见过他,估计这辈子也见不着了。
我爸那天已经到家,我头昏脑涨的,也不知跟没跟他打招呼。我妈在做饭。她做的是什么?我怎么一点都想不起来了?
我妈叫吃饭时我又想吐,脑子里嗡嗡的,却不得不坐上饭桌,还装模作样朝嘴里塞东西。我妈给我夹了一筷子菜,我使劲憋着不让自己喷出来。我爸开口了,但我没听到他在说什么。
我爸叫起来:“你说话呀!老子在问你话!”
我看着他,仍然无法开口。他忽然扇了我一巴掌 :“今天闯了什么祸?”
“我,我杀人了……”
“哗啦”我妈的碗掉到地上,从那一刻起我有点清醒了。
我判了10年。开庭那天人不多,爸妈请的律师根本没先前说的那么神,公诉人很容易就把他驳倒了。判决书很长,除了案情还有很多“应该”和“不应该”。法官在念到黄松的名字时,总要加上“另案处理”四个字。我站在被告席上,心里估算着黄松还能活多久。
宣判后我媽又哭了,不过没叫“小光”。我没敢朝他们看,那一刻我真的很后悔。
少管所的伙食比拘留所好,当然不能跟家里比,但起码没有冬瓜辣椒烧茄子了。我已不再焦虑,每次吃饭都试着回忆那天的晚餐。我觉得应该想得起来,却一直没成功。
我妈在允许探望的第一时间来看我。少管所离我家一百多公里,她头晚就到了,在附近找了个小旅店住下,几乎一宿没睡,排在了探视家属的第一批。她抓住我的手说不出话,努力透过泪水看我。我怕她失控,东拉西扯说些这里的生活,主要是这里的伙食。我忽然问 :“妈,那天晚饭我们吃的什么菜?”
她一愣,“那天?我想想。”她的目光很空,最后缓慢地摇了摇头。
第二次探视还是我妈一人来的,解释说生意不能没人照看。见面她没哭,我的压力就小了很多。“我爸好吗?”我问。
我妈没回答,眼圈却红了。“你上次问的事,我实在想不起来,就问你爸。他想了几天也想不起来,都想哭了……”
我惊讶得说不出话。上次我随口一问,只为有个话题,没想到竟会引出这样的事。
“你想知道,我们理解,可那天就像天塌下来一样,我们哪记得住?”她低头大口喘息着,我闻到一股老年的气息,忽然有一种万箭穿心的感觉。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