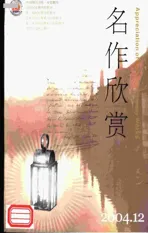女性知识分子在革命浪潮下的不同改造之路
——以《蚀》和《青春之歌》为例
2017-07-13魏铭辉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州350007
⊙魏铭辉[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福州 350007]
女性知识分子在革命浪潮下的不同改造之路——以《蚀》和《青春之歌》为例
⊙魏铭辉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 福州 350007]
女性知识分子身兼女性与知识分子两种身份,在不同时代以及不同作品中,女性知识分子在革命浪潮下往往有不同的表现,即不同的改造之路。本文以《蚀》三部曲和《青春之歌》为例,探索女性知识分子的不同改造之路并关注她们的改造过程、改造方式以及背后所传达出来的时代精神。
女性知识分子 改造 娜拉模式
“五四”运动的首要功绩,是对人的发现,这里面包括对女性的发现。约翰·穆勒在《妇女的屈从地位》一书中说道:“规范两性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原则——其中一个性别法定地从属于另一性别——其本身是错误的,而且现在成了人类进步的主要障碍之一。”女性的发现就是使得女性有“为人”与“为女”的双重身份自觉。波伏娃说:“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
“五四”运动强调自由平等,因此男女关系的不平等自然而然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女性的解放是“五四”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青年》上刊登的易卜生所写的《娜拉》是女性解放的先声。女性要解放,就必须追求女性的人格独立与婚姻自由,而要做到这些,冲出家庭的束缚是第一步。但走出家庭后,又该如何呢?鲁迅的《娜拉走后怎样》给了我们答案:娜拉走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女性在走出家庭后,失去了依附,如何生活,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人们为娜拉的出走感到痛快,实际上也是为女性独立人格的觉醒感到鼓舞。相比而言,鲁迅却冷静深刻。在《伤逝》一文中,子君与涓生的爱情悲剧同样回答了这个问题。相比于娜拉,子君更进一步。子君清楚意识到家庭专制对男女平等造成的不良影响,同时她又热爱文学,有自己的个性,是人们所期待的新女性形象。但这样一个新女性,追求恋爱与婚姻的自由,最后收获的却同样是悲剧。
那么,是否有一条道路能使女性在冲出家门后,在“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这样一种二元结局之外得到解救?于是有了集体主义对个人主义的宣战。集体主义指出女性的个人主义是没有办法使女性得到解放,只有集体的力量才能对抗堕落。从个人主义走向集体主义,就是把个人的命运与社会变革联系在一起,并献身于社会解放运动,从而在集体中获得无限力量。
在女性解放与改造运动中,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展开论述:个性解放与阶级解放。这两个层面也与本文所关注的两部作品有一定程度的契合。《蚀》三部曲中人物形象塑造得最成功的部分是那些时代女性。她们追求官能享受,像章秋柳与孙舞阳等,突破传统对女性的束缚,大胆追求个性解放与性的解放。在大革命失败前后,女性知识分子彷徨无助,颓废感伤。在《青春之歌》中,小说呈现了一个女性知识分子如何经过不断改造,最终成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过程。个人的命运只有与祖国的命运紧紧相联系,才能拥有真正的青春之歌。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从“五四”到“十七年”时期时代精神的变化以及对作家创作的影响。下面本文将逐一分析。
一、革命与性泛滥:时代女性的个性与迷茫
茅盾曾经总结过“革命+恋爱”的小说模式,具体来说有三种:1.当男女双方的恋情阻碍了革命的发展,主人公选择革命而牺牲爱情;2.当主人公有多个可选择对象之时,主人公选择最革命的作为对象;3.男女主人公因为革命而产生爱情。三部小说都有革命也都有恋爱,但在《蚀》中,革命并不是主体。茅盾在《从牯岭到东京》一文中写到《蚀》三部曲主要写的内容是“(1)革命前夕的亢昂兴奋和革命即将到来时的幻灭;(2)革命斗争剧烈时的动摇;(3)幻灭动摇后不甘寂寞尚思作最后之追求”。虽然处处体现革命,但革命在小说中显然是一个“他者”的形象。女性知识分子的恋爱并不是为革命所服务,革命只是促成了她们的恋爱。这些女性知识分子受过新思想的影响,不同于传统女性。但在革命的浪潮下,她们所想的还是自身的愉悦。“既定的道德标准是没用的,能够使自己愉快的倒是道德”;“理想的社会,理想的人生,甚至理想的恋爱都是骗人的勾当”。恋爱给她们带来愉悦,革命促成了她们的恋爱——革命的幻灭使得她们苦闷颓废,借恋爱来消遣。革命的失败使她们找到自我麻痹的理由。无论是孙舞阳还是章秋柳,这些女性知识分子对于男人是带恨的,她们甚至用“性”作为报复男子的手段。赵赤珠和王诗陶这两位女性知识分子的身上显示出性与革命错综复杂的关系。她们投身革命活动但最终因为革命也为了生存下去,从而走上了出卖肉体的道路。这样出卖肉体的行为在革命的幌子之下可以心安理得。《蚀》中的时代女性充满着“中国式的世纪末的苦闷——幻灭的悲哀,向善的焦灼和颓废的冲动”。茅盾在塑造这些女性形象之时,运用了大量的内心独白,让读者清楚明白她们在革命的浪潮中的颓废与悲观,显得真实而动人。作家总是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表现出男权中心主义对女性的想象。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塑造都是以男权中心主义为标准。《蚀》三部曲中的女性,除了作者着力塑造的时代女性之外,还有一部分是传统女性。她们沉溺于日常琐碎生活之中,例如《动摇》里面的方太太。方太太与丈夫方罗兰最后貌合神离,闹到了离婚的地步。这些女性知识分子有意无意地成为男性继续革命的负担,她们似乎在瓦解着男性的革命意志。而在革命的男性眼中,传统女性知识分子是负担,革命女性知识分子不过是其恋爱的对象。
二、堕落与回去:娜拉模式的延续
这些时代女性其实都没有走出“五四”的“娜拉模式”。在出走之后,她们感到迷茫与无助,恰逢革命浪潮的袭来,于是精神上似乎有了寄托,要在革命中振奋精神,做出一番功绩。革命对她们来说只是精神无助之时的一种寄托。如果有他者可以寄托之物,那就不一定是革命了。在《追求》中,当章秋柳等人齐聚一堂成立革命团体之时,这个成立的革命团体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人们的心思也不在革命,革命成了一句空口号。章秋柳在性的享受中麻痹自己。她想拯救史循,但她连自己都拯救不了。《蚀》中的时代女性是“五四”娜拉走出家门后的典型,她们的改造与解放仅仅只是走出了第一步。革命对她们也只有一般的影响,她们的结局不是革命造成的。如果没有革命,她们也会是同样的结局。精神上的空虚与意志的薄弱,让人寻求心灵的寄托与安慰,虽然有进取之心,但往往遇到阻碍便退回原点。自身的局限使得她们囿于个人的小天地。与革命的浪潮相比,个人实在显得渺小。她们没有认清自己的道路,自然也无法选择正确的道路,即使是选择了正确道路也很难坚定地走下去。这些所谓的时代女性,在革命浪潮下便被打回原形,因此她们的改造很不彻底,很不完善,还停留在“五四”的娜拉模式。
茅盾把自己的颓废色彩倾注于人物形象中。茅盾在这一时期受到大革命失败的影响,也处于迷茫颓废阶段。从这些时代女性身上,便可以看到茅盾自身的影子。同时茅盾早期受到自然主义的影响,所以《蚀》是茅盾感性的流露。“五四”运动从1919年的狂飙突进,到1927年的陷入低潮,中间不过短短几年时间,变化却如此之大。而这也投射到《蚀》三部曲中的时代女性身上。
三、集体战胜个人:女性知识分子的终极改造之路
《青春之歌》为读者展现了一个个人主义的女性知识分子如何经过不断改造从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并最终成长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过程。上文提到,女性知识分子的解放与改造之路有二:个性解放与阶级解放。《青春之歌》可以看作是女性知识分子的阶级解放。在阶级解放中,女性知识分子要经历一个自我身份的寻找过程,此过程也可以看作是女性知识分子的改造之路。杨沫为林道静进行人物身份的初步设定:地主家庭的出身背景,父亲是地主,但母亲是佃农。生母早死,父亲与继母并不喜欢林道静。林道静从小受尽虐待与凌辱。因此林道静自己也坦言,身上既有白骨头,也有黑骨头。实际上,虽然林道静有生父与继母,但在其成长过程中这两个人并没有很好地发挥作用,只是使林道静养成了叛逆的性格。因此从林道静冲出家庭后,她便走上了自我身份的寻找过程,此时的她像是一个婴儿。同时,《青春之歌》的叙述模式是“革命+恋爱”。革命置于显性地位,恋爱置于隐性地位,从属于革命。在《青春之歌》中,杨沫特意为林道静安排了与卢嘉川、江华这两段恋情,这两位男性对林道静的改造之路有着不同的意义。
四、革命与爱情:显性文本与隐性文本的相互交流
林道静的改造过程中,革命是显性因素,爱情是隐形因素。为什么杨沫要设置卢嘉川死亡的结局,让江华来带领林道静最终成长为一个共产主义的战士呢?因为林道静与卢嘉川的爱情是真正的爱情,而林道静与江华之间的爱情是革命的爱情,是同志间的爱情。小说写道林道静见到卢嘉川时候的表现,林道静是“立刻被他那爽朗的谈吐和潇洒不羁的风姿吸引得一改平日的矜持和沉默”。第二次见到卢嘉川的时候,卢嘉川的迷人魅力更使林道静沉醉。此时卢嘉川展现出个人渊博的知识以及非凡的谈吐,深深地吸引了林道静。卢嘉川对革命的执着、林道静对卢嘉川的喜爱,使得林道静也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这是一种爱屋及乌式的革命,爱上了卢嘉川,同时爱上了卢嘉川的革命事业。但林道静不能对卢嘉川直接表达自己的爱意,只能在革命的大背景下暗暗表达,所以卢嘉川必须死亡,以保持这爱情的纯洁性。而对于江华的爱意,林道静认为江华是一个革命性十足的进步青年,面对这样的爱意没有理由不接受。如果说与卢嘉川的爱情是理想型的,那与江华的爱情更像是现实性的——与江华的结合是合适的,并不是喜欢的。但不管如何,林道静与众人的爱情显然不能成为小说的主要内容。小说的内容某种程度上也可以概括为林道静与余、卢、江三个人的爱情故事,但革命必须置于主体地位。因此,这些爱情只能置于隐性地位。由于卢嘉川与江华是革命的代表,是党的化身,因此林道静的爱情被简单化、粗俗化。革命必须是主体,置于显性地位,爱情必须置于革命之后。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使爱情简单化,去除浪漫的情感。“革命的原动力是对个性、自由和享乐的憧憬,但这样的憧憬寄予理想之中,革命的实践是禁欲的——这样的憧憬只能求助于禁欲阶段迂回抵达。”林道静与卢嘉川、江华的爱情,事实上都只存在于未来,而不可能是当下。林道静和卢嘉川把对彼此的爱意深藏心中,还来不及告诉对方,卢嘉川就被捕而牺牲了。江华与林道静也是见少离多。这便是革命的叙事伦理——革命大于一切,爱情只能置于其底下。“革命发生在现在……同时革命不知道现在,也不拥有现在,革命是完全指向过去和未来的……”
五、反叛与寻找:自我身份的认同之路
女性知识分子要想完成自身的阶级解放,就必须先找到自身的阶级身份并且认同这个身份。《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最终完成了阶级解放,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离不开一系列革命男性与女性的帮助。他们的言行举止使得林道静身上的阶级解放意识萌发,并最终认同。在这个过程中,由于革命是占据了主导地位,为了更好地让林道静寻找到阶级身份,就必须对她的性别身份做一定的处理与规避。在《蚀》中,茅盾对于时代女性的身体有许多具体的描写,这很符合五四精神。但在“十七年文学”中,女性的形象出现了很大的变化,有别于五四时期。女性这一词更多成为一种符号,作家有意无意地抹掉女性的性别特征,不断地向“男女平等”方向靠近,塑造的是女英雄的形象。而在五四时期,对于女性形象的塑造往往关注其内心独特又细腻的心思,大量采用心理描写。在以革命为大背景的前提下,任何女性的细腻情感都可以被视作是对革命的妨碍,是小资产阶级的软弱表现。因此,“十七年文学”中的女性形象,为了更好地革命,就必须弱化自身的女性特征,显示出对革命的尊敬与协调。因此,《青春之歌》虽然写的是林道静一个人的成长经历,但最终成为女性知识分子最彻底的改造之路。
身份觉醒之后,便是寻找的阶段。卢嘉川唤醒了林道静身上的阶级身份意识。让林道静最终认同这个身份,则离不开一群工农角色的参与,因此在《青春之歌》中,工农兵的形象几乎是理想化的,让林道静感到尊敬和自卑。林道静在定县小学教书时,因为没有识破已经叛变革命的戴愉的诡计,发动了学潮而处境危险,她只好暂时藏匿于学生刘英家里。对于刘母的农民身份,一开始的林道静不以为然。但与刘母接触之后,林道静改变了自身的看法并产生了崇拜。在刘母面前,知识分子的天然自卑感被触碰。曾经的知识分子是时代的先锋者,引领时代的思潮。但很快知识分子发现自身的软弱,缺乏改变世界的力量。在工农大众面前,知识分子是启蒙者,是高高在上的。然而到变革社会之时,知识分子只能退居二线。《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使得这种情况更加严重,工农大众才是主体,知识分子必须依附工农大众,并且要深入工农大众,与工农大众在思想、情感态度等方面打成一片。此时的知识分子从时代的先锋一下子沦为落魄书生,自卑感油然而生。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也是一个有着原罪意识的群体。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言:“这个知识者群,却共有着一个精神特征,即同属一个‘罪感的群体’。”面对工农兵大众,她们要赎罪。小说中特意安排了林道静到河北深泽县农村进行锻炼这一情节。在这里她看到资产阶级如何剥削劳苦大众,更增添自身的罪恶感。林道静看到了她家原来的长工郑德富家破人亡,从前对她很亲热的郑德富现在竟然对她如此冷漠,这让林道静不解。姑母一语道破:“你是小姐,他是佃户。”阶级的对立使她产生了赎罪的想法,而后林道静逃离河北深泽县农村之时,郑德富帮助了林道静。郑德富解释说:“你不是林伯唐的闺女了,你是闹革命的闺女,咱还能再恨你?这是共产党叫我不再恨你啦。”这种天然的罪恶感使得林道静深刻地反省自己,而郑德富的一番解释让林道静更加坚定地走上阶级解放的道路,也促进了自己的阶级解放。
浙江专员办顺应转型趋势,突出管理思维,聚焦事前事中环节,努力在问题研究的深度、政策建议的高度和系统纠偏的广度上下工夫,不断提升财政金融监管的权威性。
在《青春之歌》中,林道静一步步成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一系列作为共产党化身的男性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使得林道静最终完成了女性知识分子的改造之路。林道静的改造之路从反抗封建男权开始,皈依党的男权结束。在卢嘉川、江华等一系列作为党的代表的男性的指引下,林道静一步步皈依党的男权。正如陈顺馨所说:“林道静的解放之路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寻父’,她的最终归宿并不是其最初指望的独立女性的精神家园,而是一个丧失女性自我的集体意识形态。”年长又成熟的卢嘉川与江华,使得林道静产生了“恋父情结”。林道静对他们的崇敬背后是对党的权威的认同。
六、“五四”与“十七年文学”:双重时代精神的喧哗与骚动
从《蚀》到《青春之歌》,我们看到了五四精神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双重话语的喧哗与骚动,作家的叙事空间也随着政治的变化而被不断被压缩。在《蚀》中,茅盾可以大胆地描写作为小资产阶级的女性知识分子的各式情感,并赞同这些情感是自然的、真实的。在五四时期,知识分子是时代的先锋,强调个性张扬,工农兵大众处于被启蒙的状态。到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工农兵大众成了革命的主体,强调集体主义。在“十七年时期”,政治的高压使得作者的叙事越来越规范,叙事空间不断被压缩并且不敢越过雷池。作家们只能严格地遵守规范,并且不断地向主流权威示好以显示自身的革命性与进步性。
《蚀》和《青春之歌》这两部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体现了女性知识分子改造之路的不断深入。《蚀》代表着“五四”的时代精神。封建与家庭专制是束缚和残害女性的牢笼,同时也是阻碍女性知识分子解放的精神枷锁。女性知识分子想要获得独立和自由,想要拥有人格的独立与个人的尊严,就必须冲出家庭走向社会,就必须要有个人独特身份意识的觉醒和性的解放。追求个性解放与性的解放,某种程度上使得女性知识分子沉迷于官能享受,因此《蚀》三部曲也使茅盾备受争议。到了《青春之歌》,它是对特定的权威话语的承载:作为小资产阶级的女性知识分子只有在共产党的引导之下,经受住种种考验与打击,投身于群众运动中去,才能得到真正的、彻底的改造与解放。由此我们可以看到从“五四”到“十七年”时代精神的变化,以及因此产生的作家叙事空间的变化。
两部作品,从作家的叙事层面来看,是“五四”精神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的激烈碰撞与交锋,同时体现了作家身份的多重性。作家时而是启蒙者,时而是革命者,时而又是被拯救的对象。“五四”运动虽然声势浩大,狂飙突进,但说到底只停留在知识分子阶层,广大工农兵群众并未参与其中,某种程度上来说只是知识分子这个小群体的自我高潮与狂欢。随着大革命的失败,作家们一下子成了迷途羔羊。从前意气风发之时,作家们承担着启蒙者的角色,要启蒙工农兵大众。而现在,作家们成为需要被拯救的对象。工农兵大众的革命集体主义拯救作为小资产阶级的作家们的个人主义。《蚀》三部曲是作者个人的苦闷在时代女性身上的投射,也是作者对五四时代女性命运的思考。在女性解放的大背景与口号下,解放的不是女性本身,而恰恰是男性的欲望。女性的悲剧性命运依旧存在并且延续着,所不同的是表现形式。她们从父亲家出走,最后走进了丈夫家,成为丈夫发泄性欲的工具,或是在社会中沦落。《青春之歌》的情节设计以及人物之间的关系,体现了新中国成立后的时代精神对知识分子的规训。作为一部具有自传体色彩的小说,《青春之歌》依稀存留着一些五四时期的时代精神。但在个人欲望与政治规训之间,杨沫很难做到平衡,因此在小说文本中,革命虽然被置于显性地位,但林道静内心情感的描写细腻又真挚,林道静与卢嘉川之间的爱情真实又动人。杨沫为了进入主流,必须与“五四”告别,与过去告别。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知识分子必须老老实实地投入到革命运动中去,成为其中的一员。
① [英]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英]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女权辩护 妇女的屈从地位》,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25页。
②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女人》,桑竹影、南珊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
③ 茅盾:《从牯岭到东京》,见《茅盾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版,第30页。
④⑤ 尼古拉别尔嘉耶夫:《论人的奴役与自由》,中国城市出版社2002年版,第232页,第229页。
⑥ 何向阳:《不对位的人与“人”》,《山东文学》1998年第3期。
⑦ 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5页。
[1] 王宇.性别/政治:《青春之歌》的叙事伦理[J].江苏社会科学,2003(4).
[2]李春梅.周作人女性解放思想的独异性[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1).
[3]聂国心.“五四”新文学关于女性解放的一个悖论性主题[J].天津大学学报,2009(1).
[4]尹旦萍.女性解放是什么——五四时期对女性解放涵义的探讨[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9(5).
[5] 林小叶.革命叙事中的矛盾——论《蚀》三部曲中的女“性”[J].名作欣赏,2013(18).
作 者:魏铭辉,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本科生。
编 辑:赵 斌 E-mail:94874655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