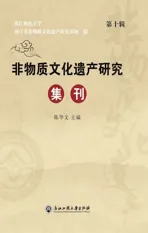电视剧《白鹿原》中自然信仰的文化宿命
2017-04-15陈爱国潘路路
陈爱国 潘路路
(浙江师范大学文化创意与传播学院 浙江金华 321004)
最近热播的电视剧《白鹿原》,改编自陈忠实的同名小说,尽管播出时有所删减,但还是通过讲述白嘉轩的一生历程以及白鹿两家三代的恩怨情仇,侧面性地表现了中国清末至新中国成立初半世纪的历史变迁,同时反映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自然信仰的变迁。自然信仰是某种程度上民间信仰的早期形态,即在先民中广为流行的对天地万物的崇拜,逐渐衍化成对某种超自然的神秘力量的崇拜,对类似的精神观念或实际物体都会予以虔诚的信奉。
“白鹿”作为白鹿原中多次出现的灵物,被原上村民共同信奉、追逐,是“万物有灵”的自然信仰的一种体现,进而与祖训“仁义”相联系,进入村民的祖宗崇拜视野,本质上是中国传统乡村社会土地崇拜的衍化,对自然信仰的丰富。供奉祖宗灵位的祠堂,因此成为传统乡村社会中承载自然信仰的最佳载体。该剧正是通过“白鹿精魂”的反复追认与白鹿村祠堂的历次兴衰,构建了中国乡村社会的自然信仰的演变历史。从乡土劳作、天地敬仰,到自然灾害、土地革命,中国乡村社会的历史变革,同中国传统自然信仰的变迁存在着众多的契合。近现代中国乡村社会形态的沿革,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近现代中国自然信仰的变迁,造成了二者相互纠缠、彼此唱和的局面。
白鹿原半个世纪的发展,是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的缩影,而白鹿原的信仰革命问题,至今影响着所有中国人。信仰是人类生产、生活、心理、灵魂的最高信赖对象。在当代中国,占据主导地位的民间信仰体系,除却宗教层面,仍是传统乡村社会长期延续的自然信仰与儒家思想。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加速,现代社会构建的推进,传统乡土社会日显衰退态势,诸多问题滋生。自然信仰固有的价值追求,既有含混性、歧异性,又有初级性、地域性,如何与法律规则、社会建构相结合,如何找寻一条回家之路,已经成为我们每个人的燃眉之急。
一、白鹿诞生:自然信仰的文化源起
乡土是本乡本土、故乡之意,具有浓厚的地域性、习俗性、自足性,究其寓意,是疆域土地生产所带来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总和。土地是农民全部生活的承载与依赖,播种和耕地是他们人生最大的意义,人可以迁居、变身,土地可以转让、改种,而土地本身固守不动,乡土性也始终流淌于他们的文化血脉之中。
传统农业社会中,小农经济的空间限制和儒家思想的礼俗浸染,致使乡村社会的流动趋于停滞,相对固定的客观环境,使得乡村生活相对趋于稳定,白鹿原上白鹿两家的历史存在,似乎几百年如此。“他生根在他所照料的土地上,人的心灵在乡村中发现了一种心灵,存在着一种新的土地束缚,一种新的情感自行出现了。敌对的自然变成了朋友;土地变成了家乡(Mother Earth)。在播种与生育、收获与死亡、孩子与谷粒之间产生了一种深厚的因缘。”①[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98页。土地不仅是世代黏着的父母之邦,更逐渐被赋予一种“历世不移”的朴素信仰。在变动较小、彼此熟识、安土重迁、生死于斯的乡村社会中,客观环境的相对稳定巩固了主观经验的延续性,自己的生活经验可以信任且传承,其祖辈亦是如此。在“言必尧舜,敏而好古”的乡村社会,文化传统、信仰习俗得到了绝对的巩固,成为乡村社会所累积的基本经验与规约。②费孝通:《乡土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50页。乡村社会的经验积累中,有很多东西不可也无须穷其蕴理,只要诚心照做即可。这些解决问题的办法代代相传,而内涵的价值日益趋于抽象,“灵验”和“魔力”成为此类传统的解释与实证。只要依照传统、恪守章程去做,就会得到庇佑与福气,反之则有相应的惩罚与训导。
信仰圈层之生成,有不同方式与特点,其一便是由传说传奇之传播,从而达成信仰,再至塑偶像、建宫庙,焚香供奉,这是既合乎田野事实,又合乎信仰生成的过程。①庄孔韶:《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1920—1990)》,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67页。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信仰形成大都如此,躬耕土地中感受四时交替、春风秋雨,进而从土地农事中抽象出一种顺天承地的朴素自然信仰。传统乡村社会的信仰习俗中,大量的神明与天地、鬼神、动物、植物有关,如雷公、电母、土地公、土地婆、龙王、神树等,而无处不在的土地公、土地婆、土地庙,是土地崇拜的最佳代表,“土地”这位最近于人性的神,是老夫老妻白首偕老的一对,喻示着永恒与慈悲,他们还管着乡间一切的日常与闲事,因为这些都与土地生产有关。他们象征着可贵的泥土,象征着农民的根本。②费孝通:《乡土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2页。
在电视剧《白鹿原》里,作为灵物的白鹿最初只出现于原上人的传说传奇,即白鹿原最初得名之因由,是期盼能给常年干旱的黄土地带来丰收、安宁与福祉。而白嘉轩一代最初与白鹿的“相遇”,是在大雪地里发现一处无雪之地,长着一株青翠的小蓟,说明此处地下有丰沛的水源,是一块沃土福地,于是白鹿精灵应运而生了。在原著小说里,此处是白嘉轩撒尿时意外发现的,而电视剧中,是其未婚妻仙草寻他而冻卧之处。究其寓意,前者指向白嘉轩的幸运,后者表明土地、水与女人、母性之间的密切联系,也即西方“地母”神话原型的再现。由此可见,流布于白鹿原的“白鹿信仰”诞生于土地,构建于宗祠,统括于白鹿原所有的自然信仰。当干旱威胁白鹿原时,白嘉轩领导全村“伐神取水,每户一升一”;之后为摆脱瘟疫困扰,全村筑塔抵御。在历次灾难里,白嘉轩和村民不断期待“白鹿”显灵,以祭祀仪式沟通神明,消灾祈福,实现愿望。此类朴素的自然敬畏,或许可以溯源至人类早期的某些文化传统,日久逐渐形成令人敬畏的自然信念,传统的自然信念随着信仰仪式的不断重复,得到外在的巩固,更因“灵验”与“惩罚”而获得内在的敬畏,生成一套参差不齐、自圆其说的自然信仰。
传统乡土中国的小农经济是一种生活水平较低、发展前景堪忧的“匮乏经济”。耕地面积有限,居住人口趋多,产业结构单一,技术发展缓慢,导致粮食生产不足,一旦遇上天灾人祸、政策失当,就会出现恶性事件。于是,乡村社会结构趋向于具有原始氏族部落遗存性质的宗法关系,集体应对,步调一致,但等级严明,犹如小小的王国。儒家思想作为影响中国乡村社会交往与礼俗信仰的重要因素,其核心是“中和位育”。“中和”是其目的,不偏不倚,和谐适度;“位育”是其手段,各守本分,适应处境。这种“匮乏经济”因资源有限,其位育方式是“修己以顺天”,严格控制居民的过分欲望,以应付有限的资源。①费孝通:《乡土中国与乡土重建》,台北风云时代出版社1993年版,第115页。能有口饭吃就不错,不可浪费一粒粮食,日常生活其他方面,也大抵如此。勤俭持家,节衣缩食,顺应天命,忍辱负重,成为中国传统农民的典型性格。
与《白鹿原》中的白嘉轩一样,人类学纪录片《无米乐》中的昆滨老伯,自称“末代稻农”,种田对于他而言是一种精神修养。外界的很多人喜欢修禅养性,而台南这里的农民不需要修禅,他们甘心受自然之苦,种田劳作不只是粗重,还要暴晒,遭受风雨,有时候台风来袭,造成农作物损害,无法反抗,怎么抵抗大自然也没有用。如果说禅是教会人无须抵抗,甘心忍受,那么这里的农人都是在学会甘心忍受,就像和尚修禅,因此他们不需要形式上地修禅,种田就是默默地修禅与修行。他们上辈子没有修够,这辈子只好再继续补修禅。《白鹿原》中以白嘉轩为代表的农民,将躬耕陇亩的经验与智慧不断予以抽象,进而上升,通过祠堂这一神圣空间的协调,完成自身对自然信仰的无限敬奉。
从《周易》开始,中国人就将这种源于乡土的“修己以顺天”思想,演变为对“天”与“地”的自然信仰。“天”“天道”被看作是宇宙自然力量和社会人伦秩序的最终依据和最高化身,人世的一切都要问究于天、听命于天。“天意”“天命”“天兆”“天谴”等,是中国自上而下最为敬畏的自然信仰。①李德顺:《论中国人的信仰》,《学术月刊》2012年第3期,第39—40页。这种通过“种地”而得出的、以天地为对象的、夹杂儒释道思想的、多有纰漏且无法像宗教那般建立起体系的价值观念,恰恰呈现了中国人根骨里由乡土性表现出的、对自然天地的终极信仰,似悠悠无尽,也历历分明。这种天理正如《周易·系辞》所言:“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
乡村社会的鬼神大都源于自然天地的感应,是农耕文明的附属物,而红尘俗世的人间烟火缭绕,使得每位乡土神明不仅具有神话味,也具有生活味。乡村社会的自然信仰,内含了一种朴素的人本精神,通过借助各种各样的神明,向大众提供了一个有关人生和世界的解释系统。白鹿原上的凡尘众生正是通过这个价值系统,“试图实现天神人之间关系的整合与心理的适应过程”②庄孔韶:《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1920—1990)》,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366页。,借以尘世香火求得宽慰和告诫,从而在寒来暑往中敬畏天地,在秋收冬藏中返照自身。
二、白鹿隐现:自然信仰的文化歧异
《白鹿原》所处的时代背景,集中于20世纪上半叶中国社会的剧变时期,中国受世界现代化、工业化浪潮的裹挟,开始由近代转向现代的社会变革。白鹿原作为汉唐故地,传统的乡村社会与自然信仰不断受到冲击,文化观念也随着时代发生一些改变,进入多元共存、相互竞争的纷乱状态。
从剪辫、交农、北伐、农运,到清党、抗战、解放、镇反,白鹿原经历了整个近现代中国的大小变革,无疑是“民族秘史”的缩影。巍峨坚挺的白鹿村祠堂无疑是中国民间自然信仰的标识,那里供奉着传说中的白鹿精魂、吃饱肚子的盛世理想。从白鹿两家争夺新族长,翻修祠堂,以宗祠乡约为道德约束,到白孝文念《乡约》,鹿子霖兴风作浪;从白嘉轩在祠堂领导全村抵御天灾人祸,到黑娃闹农协砸祠堂;从政局暂定,拼合乡约碑,祠堂重振威风,到日本战机扔炸弹,炸毁祠堂,先人不佑;从再次建立祠堂,接纳白孝文、黑娃回归,最后到国民党乱抓壮丁、滥派捐税,白嘉轩无能为力。“一方净土”白鹿原从和平宁静的乡土小国,变成了历次斗争、革命与运动的舞台。这舞台主要集中于村里的祠堂和戏台,一切像是演戏一般。乡土社会的失序与崩坏使得白鹿原成了一个“鏊锅”,中国的乡土文化乃至自然信仰开始经受漫长的折腾。历经半个世纪的煎熬与折腾的白鹿原,其社会秩序与自然信仰逐渐衰弱、蜕变,其表征是作为自然信仰神圣载体的宗祠,遭受到一次次的打击与破坏。其间,作为地方神明的白鹿显灵过几次,等白发苍苍的圣人朱先生凄然仙逝,此后再无人提起。
白鹿作为地方神明,并非白鹿原先民自古就有的动物图腾,而是中国自古就有的文化符号,至少包括了三个层面的意义。一是隐士,白鹿代表着一种隐逸人格。如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且放白鹿青崖间。”圣人朱先生长年隐居于白鹿书院,徘徊于出世与入世之间,洞明世事,超然物外。这种凌空高蹈的仙气与白鹿原喧嚣吵闹的俗气形成强烈对照,可看作是对国民劣根性的一种批判精神。二是祥瑞,白鹿的出现意味着吉兆。如《史记·孝武本纪》:“天子苑有白鹿,以其皮为币,以发瑞应,造白金焉。”白鹿神话首次的显灵之处,是鹿子霖的劣质慢坡地,其实是上等的水地,白嘉轩耍计谋夺得,并将祖坟迁移于此,因为它是吉兆,主大运。他和村民每次期望风调雨顺、和平安宁时,大多会“遇见”它的身影。三是贤明,白鹿是拯救苍生的英雄。如《宋书·符瑞志中》:“白鹿,王者明惠及下则至。”这是《白鹿原》中白鹿最主要的符号价值与隐喻意义,与白鹿村的“仁义”祖训相表里。朱先生和白嘉轩是老一辈中的这类人物,一个是《乡约》的制定者,一个是《乡约》的执行者,在白鹿原的几次劫难中,都发挥着运筹帷幄、扭转乾坤的作用。在局势动荡、时代变革的社会环境下,朱先生还将拯救苍生的“白鹿精魂”赋予白鹿原的下一代,在原著小说中给了国民党将领鹿兆海,在电视剧中给了共产党特工白灵,他们都是为了抗战大局,奋不顾身,就像是朱先生和白嘉轩为了地方大局,勇于抗争。朱先生还有一个关门弟子黑娃,从儒家文化的叛逆者转变为儒家文化的皈依者,足见白鹿的神力无边。白鹿的以上三种含义,本身包含了中国传统儒家与道家的文化歧异,但冲突性并不是很显著,也无关紧要。
白鹿原文化观念的分裂与冲突,主要来自与外面世界、现代文明的残酷对照。在白鹿原世界之外,还有滋水县城,还有西安省城,那些闪烁金光的城市空间,代表着现代文明的广阔天地。去而重返的白鹿村人,命运都发生了改变,并带回来一些新东西,如新文明、新思想等。石头带回西装、离婚协议,鹿兆鹏和白灵带回西式教育、革命,黑娃带回自由恋爱、复仇,鹿兆海带回界限、民国理想,白孝文带回法制、政治权谋。这些新东西造成白鹿原乡土理想根基的逐渐松动,以此为据的自然信仰与神明系统,再也无法聚合为一个自圆其说的解释系统,进而导致传统乡土信仰的日渐崩塌。白嘉轩、冷先生等“村一代”,作为自小仍有乡土反哺和天地敬畏精神的一代,对此巨变无法适应,也无法改变,且晚年可以依靠已有的乡土记忆和自然信仰来应对红尘浊世,原生环境的消失和传统信仰的崩塌对其影响不大。但是,白孝文、黑娃等深受乡土文化影响的“村二代”,对乡土环境的反哺缺位,对传统天地的敬畏缺失,其后果是严重的。信仰作为人对人生、世界和价值的把握,其根本作用在于精神寄托和行为指南。失去传统乡土环境,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失去了传统精神信仰的庇护。当乡村社会结构发生重大转型时,白孝文、黑娃他们骨子里的信仰体系便产生一种自我防卫的机制,对于客观环境的改变产生不适感和陌生感,犹豫紧张,惶惑不安。这些不得已而叛逆、出走的人,最后都要求回家祭祖。隐没的白鹿,又重现了。
但是,鹿兆鹏、鹿兆海和白灵等在县城、省城接受过现代文明教育的“村二代”,其文化观念的新异、分裂与冲突,就不可同日而语了。这三个人作为三角恋爱的关系,成为全剧的爱情副线,作为国共两党的关系,成为全剧的斗争副线。他们代表着现代文明与外面世界,与白鹿原祖传的文化观念、自然信仰格格不入,基本都为“村一代”们所不容,他们也坚定信念,绝不回头,不会返回祠堂忏悔,不会在认祖仪式中完成乡土生命的回归。耐人寻味的是,心怀天下的朱先生默认了他们各自的政治信仰和文化选择,并将“白鹿精魂”的题字送给了他们,因为他们心中装着“雪白世界”的盛世理想。白鹿原上的几匹年轻白鹿,到底是跳跃出闭塞的小世界,去了远方的大世界,而大世界本身包含着小世界。
白鹿原文化观念的分裂与冲突,也部分来自乡村社会结构的变迁,这鲜明地体现于乡村基层组织的变迁,其中蕴含着不同的治理观念、社会习俗的价值取向。明清时期的基层管理机构,大多是县一级,尽管有时下设村正、里正,下面各乡村的实际统治者还是族长。天高皇帝远,上下一盘棋,族长在乡村的权力是绝对的,其执行地点是祠堂,其治理思想是孝悌、仁义,儒家的宗法观念与帝制观念是相互一致的。这就是《白鹿原》前半段中白嘉轩作为族长极有威望、呼风唤雨的根本原因。民国建立后,所谓民主政治逐渐下到基层,在乡镇一级设立过渡性的仓,下设保障所,便有了鹿子霖的乡约官职,其基本职能是负责交粮交税,抓住经济命脉。此时节,族长的权力受到一定制约,民主自由的风气开始刮起,出于各自的目的,一些村民开始背井离乡,外出发展,即白嘉轩眼里的人心离散,有些降服不住了。抗日战争结束后,仓改为联保所,下设保公所,鹿子霖变成保长,将各村划分为几个甲,甲长相当于生产队长,族长被彻底架空,乡村的宗法关系被釜底抽薪,连白孝武世袭族长的机会也被杜绝了。
中国社会变迁日趋迅猛,乡村社会迈向现代社会的脚步逐渐变快,乡村社会结构的转换致使整个价值体系发生变化,原始的自然信仰随着族长的失势而被质疑,民主观念与科学精神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但是,社会结构与价值观念的转变是一个缓慢的过程,总是从某一部分开始,并在此过程中与过去传统形成此消彼长的抗衡,这就是多元共存、相互竞争的过渡状态。可见,社会结构和精神体系的冲突最易发生在社会转型发展时期。旧有的乡土礼俗社会已经被打破,但现代社会构架并未完全建成,值此时节,社会乱象与乡土流弊大行其道,这便是“狼来了”,长期被儒家思想压制的“欲望”“人性恶”重新抬头。在这种充满冲突性、竞争性的文化环境下,几乎什么怪事、奇谈、传奇、极端行为都会发生。如美艳性感、温柔善良的田小娥,逃脱了父亲和郭举人的魔掌,却逃不脱白鹿原的魔掌;明明是受害者,差点被村人修庙祭祀,却到底被当成了害人精,被镇压在砖塔之下,为村里因饥荒而引起的瘟疫“买单”;因为她,鹿子霖、白孝文、黑娃的人生命运也发生了几起戏剧性的变化。
现代社会的构建体系源于西方,其基础是“丰裕经济”。“丰裕经济”是指工农业齐步发展,职位众,机会多,经济不断累积和扩展。①费孝通:《乡土中国与乡土重建》,台北风云时代出版社1993年版,第107页。相对于“匮乏经济”的“修己以顺天”,“丰裕经济”是“修天以顺己”,讲究通过改造、控制自然来满足自己的欲望。白鹿原社会的现代化过程,势必与传统乡村社会的一套价值体系形成矛盾,导致旧有的自然信仰日渐凋敝,加深乡土信仰与社会转型之间的冲突。相比起来,中国的传统乡村社会结构是一种等级制的“差序格局”,而西方的传统社会基层结构是组合制的“团体格局”,后者比前者较为自由,容易松动。“团体格局”的基本理念源于宗教信仰,即耶稣称自己是神的儿子,并称神是每个人共同的父亲,也即每个“人子”都是平等的,都是“团体构成分子”。深谙乡土中国的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对此认为,“在私有的父亲外必须有一个更重要的与人相共的是‘天父’,就是团体。——这样每个个人人格上的平等才能确立,每个团体分子和团体的关系是相等的。”①费孝通:《乡土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版,第30页。除却其中的宗教外衣与误读成分,这种宗教伦理中的民主自由平等的现代性观念无疑是值得借鉴的。这就好比白嘉轩家里藏着一架轧花机,明明知道靠它可以发家致富,明明可以兴办乡镇企业,可他偏偏不发展这种“丰裕经济”,因为只有“匮乏经济”才能确保人心不散,他的族长地位才能长期维持下去。
白鹿原在近现代半个世纪的折腾与变迁中,代表着自然信仰和盛世理想的白鹿时隐时现。经历了多次斗争、革命与运动的白鹿原,没有迎来理想中的盛世与福祉,却迎来了动荡、饥荒与瘟疫。究其原因,是文化观念出了问题,以及社会结构出了问题。
三、白鹿涅槃:自然信仰的文化归宿
抛开外面世界时代潮流裹挟的因素,冷静客观地审视白鹿原的自然信仰与文化观念本身,我们不难发现其问题的复杂性,也即其对象与本相的多元性。这可能是原著作者陈忠实借鉴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的结果,而电视剧的编导、演员也都较准确地把握了这一点。自然信仰及其价值的多元,本身形成一个彼此对抗、抵消的复杂格局,那么“白鹿信仰”“雪白世界”就注定是一场空幻。
白鹿原中的“白鹿信仰”,与“白狼禁忌”始终是并行对立的,似乎隐喻着人性的善与恶,惩恶扬善是“白鹿精魂”之所在。其实,白狼的部分寓意与白鹿一样,是祥瑞之物,是北方地区早期的一种动物信仰。《国语·周语》:“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艺文类聚》:“白狼,王者仁德明哲则见。”《后汉书》记载,汉朝时,崇拜白犬的犬戎国的西部析出白狼国,该族以白狼为图腾。白狼作为动物图腾,也被赋予一些北方民族的性格特征,如凶残、彪悍等,在白狼的菜单和美食里,就有各种鹿科动物。电视剧《白鹿原》中的白狼基本是凶残、贪欲、灾难的化身,多次闪现,偷吃家畜,袭击人类,甚至有一个土匪头目叫白狼,四处横行,无恶不作。鹿兆鹏、黑娃为报复地方军阀而火烧白鹿粮仓时,假装是土匪所为,也留下白狼的名字。这叫以恶制恶,可他们闹农协时也闹得人心惶惶,被讥为“痞子革命”,四处打砸抢。以拯救苍生为己任的白灵,被赋予“白鹿精魂”的象征,但她婴儿时被闯入村里的白狼叼走过,长大后野性十足。白鹿与白狼似乎合二为一,难以分辨。
这些都指向一个残酷现实:儒家思想中所谓人性的善与恶,其实不能严格区分,它们都是人性的实在,鹿狼共存,善恶同体,相克相生,此消彼长。这种二元辩证统一的人性始终并存、纠缠于每个人的心里,需要在各种利益的考量与较量中做出选择。多次看见白鹿显灵的白嘉轩,似乎是“白鹿信仰”的执行者,可他早年用计取得鹿子霖的水地,带头种植祸害人的鸦片,就落下不仁不义的把柄。在对待、规训几个“村二代”的问题上,他大多像明代清官海瑞一样以正义杀人。鹿子霖似乎是真人版的白狼,身为白鹿村的“乡约”,屡屡藐视、破坏祠堂里的《乡约》,但他的人性呈现很真实,“实用理性”的一套可圈可点,还养育了国共两党两个高级人才。原著小说中,白嘉轩以撒尿发家,鹿子霖以拉屎终局,他俩似乎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黑娃与白孝文这两个黑白相间的对手,恰似《静静的顿河》里的葛利高里,始终徘徊于黑与白、正与反之间,最后白孝文以“打黑”的方法杀死“变白”的黑娃。“恶之花”田小娥,是蛾子与狐狸的双重化身。傻子二豆是一个隐喻化的、不可或缺的龙套角色,始终能记住《乡约》的关键几句,憨厚正直,没有欲望,最符合白嘉轩的“仁义”精神,但他是个傻子,不是个正常人。由此可见,“白鹿之辩”有点像“白马非马”,但不是逻辑问题,是认识问题。白鹿原传说中的灵异白鹿,在白嘉轩早年发现水地同时发现白鹿的那一刻,就注定该涅槃归天,消隐人间。
我们再来看传统乡村社会的文化形态,一般包含三个层面:农耕文化、实利文化、自然文化。农耕文化以等级化的仁义精神为基础,强调自上而下、和谐共处,代表人物是白嘉轩;实利文化体现为私有制的功利主义,突出个人奋斗、自私自利,代表人物是鹿子霖;自然文化符合童心论的自然人性,偏重天人合一、个性自由,代表人物是白灵。多种文化价值的叠合与冲突,无疑会造成文化的裂隙与尴尬。作品需要倡导,就需要选择,而主导价值是什么,关键在于如何开头,如何结尾。《白鹿原》原著小说的第一章开头,是“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说明白嘉轩早年偏重人性的自然属性。电视剧导演版的第一集开头,是傻子二豆用方言唱民谣“吃饱了喝胀咧跟皇上他大一样了”,突出个人吃喝、个人至上的功利主义。删减版第一集开头,白嘉轩在窑洞求亲,仙草难过哭泣,他看不下去,白送人家粮食就走人,凸显了他的仁义精神。在电视剧的改编中,原著小说的很多情节被删除或改动了,人物被洗白或走样了,为的是压制功利主义、自然人性,凸显仁义精神以及儒家文化背后的主旋律色彩。但是,体现三种文化的人物和情节大多还是被保留下来,白嘉轩逼得长子放浪形骸,逼得女儿负气出走,竭力造塔镇压田小娥,这些以仁义杀人的情节,足以冲毁农耕文化的大堤,让观众质疑儒家文化的合理性,乃至质疑白鹿背后的“雪白世界”。以白鹿为代表的自然信仰,因农耕文化、儒家文化自身的不足,因小农经济、匮乏经济自身的不足,注定成就不了一座世外桃源。原著小说是“新时期”乡土寻根小说的延续,对儒家文化多有批判反省,而同时期莫应丰的《桃源梦》走得更远,其核心人物栀妹善人一手毁灭了世外桃源。
删减版的电视剧《白鹿原》除了对儒家文化略有批评外,也在探索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变革与出路,如将“白鹿精魂”改给白灵,增加鹿兆鹏在结尾的戏,“白鹿”所指不言自明,那头灵异白鹿涅槃之后竟然获得重生。从大势上看,无论国民革命还是人民革命,都指向了一个必经途径:破儒学,引西学。其本质是要由“礼治”“差序格局”的“圈子”转向“法治”“团体格局”的“规矩”。在此过程中,乡村社会的道德律条和自然信仰随之被法律规则、现代精神逐步取代。这一过程产生的社会诟病,并非仅归咎于信仰被法律所代替便可一言而蔽之,更有旧有秩序已被打破而新的社会建构尚未完善等原因存在。乡土重建乃至信仰重构,是中国乡村社会亟待突破的文化困境。
现代社会结构中,法律大多被视为通过厘定权利义务而解决纷争、创造合作的程序纽带,具有自上而下的强制性、传递性;信仰大多被视为一种心灵修行,旨在思考现实物质生活的终极探索和存在意义。将这两种概念进行狭隘定义且二元对立的观点,本身存在很大的纰漏。法律意味着客观社会的秩序指南,而信仰则是主观世界的规则引导,两者任缺其一,势必造成人与当下社会的维系断裂,或是对于精神世界的割裂与逃避。法律不仅来自国家的立法机构,而且出自个人和群体在其日常交往中创造的关系,而这种日常关系往往又是信仰的所在。信仰可以包括宗教,但不一定是宗教。乡土中国的自然信仰是一种非宗教形式的民间信仰,其本质也是人对于自身生命存在和主观精神的控制与把握。对于自然天地的敬畏与信仰,不仅规整乡村社会的伦理道德构建,也影响日后的儒释道三教的理论体系构建。不论是儒家的“四时行焉,百物生焉”,道家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还是佛教的“天地同根,万物一体,法界同融”,都深受自然信仰观念的影响,而传统乡村社会礼俗法规的架构,也大多出自这三教的教法意旨。西方文明源于希伯来文明,其宗教信仰与法律规则也紧密相连,如《摩西五经》言说的不仅是上帝的教诲,也是世间的规则和法律。无论是东方文明还是西方文明,民间信仰与社会规则的构建,乃至与习惯法、民间法的形成都颇有渊源,而且习惯法、民间法是国家法的来源。当社会构建的基本法律规则和民间信仰相隔离,甚至相互联系的纽带断裂并形成二元对立,社会秩序便容易陷于混乱。现存的制度结构和程序失去其神圣性,社会建基其上的神圣价值反而会被视为纯粹的伪善。①[美]哈德罗·伯尔曼:《法律与宗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页。但是,包括自然信仰在内的中国民间信仰必须予以批判的继承,因为它们既具有多元性、歧异性,又具有初级性、地域性,如何在基本法律规则中合理运用与结合民间信仰,这是个较为复杂的观念问题。
白鹿原的“雪白世界”虽然很难实现,甚至不存在,但是具有普世价值的自然信仰或民间信仰对于乡土社会的秩序建构与精神维系依然有可取之处。必须注意的是,人的精神升华或生命转化不应是少数人或个别团体的事,而应是整个社会乃至全部生命体的事。
四、结语
电视剧《白鹿原》借白鹿原半个世纪的恩怨情仇与乡土变迁,展示了中国传统自然信仰的魅力与沿革。因近现代社会变革的冲击,人性本身的复杂性,以及自然信仰的含混性、多元性,白鹿原的“白鹿信仰”出现一些文化歧异与文化悖论,以致一度造成“白鹿涅槃”的文化宿命。如何解决自然信仰或民间信仰与法律规则、社会建构之间的关系,更好地实现传说中的“雪白世界”,或许是中国社会需要重新思考的重大问题。
中国的民间信仰问题并非在于有或没有,而应更多地注重如何保障具有精神需求的民众正确认识精神层面的学习与修行,从而防止信仰的迷失与堕落,减少由此产生的负面社会影响。思想教育、精神修行乃至生命进化不独是局部的、小众的,囿而自居容易产生片面的、狭隘的信仰理念,导致畸形的物质主义价值观,造成一幕幕令人咋舌的人生悲喜剧。人生的转化是大众乃至世界的大事,浊世红尘中每个人都在找寻自己生命中的回家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