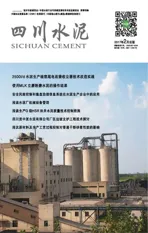城镇化能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吗?
2017-04-11李思玮
李思玮
(上海大学经济学院)
城镇化能推动我国经济增长吗?
李思玮
(上海大学经济学院)
城镇化能否促进经济增长是目前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说明,单靠投资驱动的造城运动只能在短期内推动经济增长,但不具有可持续性。中国的城镇化运动只能通过进一步制度变革、释放制度红利,才能提高经济效率,从而有效地推动经济持续增长。
城镇化;集聚效应;技术进步;制度变革
一、引言
近几年来,中国经济增速开始下降。2010年,GDP增长率为10.4%,2011年为9.3%,2012年下降到7.8%,2013年仅为7.7%。如何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继贸易和投资之后,城镇化被寄予厚望。一些学者和官员表示,“城镇化可以推动中国经济增长20年”( 辜胜阻,2013)。 近期,政府制定《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城镇化,作为一台动力十足的经济引擎,似乎已经呼呼欲出。不过,其他个别学者也提出谨慎的相反意见,告诫“单纯城镇化不是经济增长引擎”( 迈克尔·斯宾塞,2013)。因此,厘定清楚城镇化和经济增长的关系具有理论和实践价值。
二、城镇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分析
实证研究表明,我国经济发展与城镇化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贾云赟,2012)。既然存在均衡关系,那么至少存在一个方向上的“因果关系”。争论在于,到底存在哪个方向上的因果关系。可惜,数据本身很难回答问题。
几乎一致认同的是,城镇化内生于经济增长。技术进步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增长的后果是居民收入增加。根据恩格尔定律,随着居民收入增加,需求结构必然发生变化:对农产品的相对需求下降,对工业品和服务品的相对需求上升。农业生产受制于自然条件,具有分散性的特点;相反,工业生产能够产生集聚效应——为了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工业大多集中于城市。需求创造供给,随着技术进步和需求结构变动,最终从事工业生产的收入大大优于农业,人口便不断向工业和城市转移。推动人口快速城镇化的直接因素是,经济增长导致的居民需求结构变动,而根本因素则是技术进步。
那么,城镇化能否推动经济增长呢?答案是令人满意的。因为城镇化带来的要素集聚,可以产生集聚效应,如知识外溢、规模效应、范围经济等(约翰·奎格利,2010)。该逻辑的问题在于,经济增长导致城市化,经济增长导致的城市化反过来促进经济增长——追根溯源:经济增长导致进一步的经济增长。该思路说明,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具有内生性的特点,城镇化只是传导机制的桥梁,其本身没有贡献任何力量。城镇化的功能在于,将自己从经济增长继承来的能量顺势传递出去。
三、中国城镇化的现实
按照以上逻辑,城镇化是经济增长的结果,也就无所谓政府推动,从而也就无法成为经济增长的引擎。但上文所言乃完全市场化的城镇化路径,政府似乎都不存在过;但对中国而言,该假设很难符合现实。
关于中国城镇化,第一个问题:城镇化水平是超前、协调还是滞后?无论超前还是滞后,都是相对于经济发展水平而言,因为城镇化是内生于经济增长。学者持有各种观点,莫衷一是,原因在于“要跟谁比”?一般研究方法是,控制经济发展等众多因素之后,将我国的城市化率与其他同等发展水平的市场化国家进行对比。由于存在异质性,直接对比没有太大意义。最简单的方法,即观察政府在城镇化进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如果政府是推动力量,更大的可能是超前城镇化;如果相反,那应倾向于滞后城镇化。由于我国政府在计划经济时期设置了大量不利于城镇化的制度障碍,并且至今仍然延续,因此中国城镇化只能是滞后,不可能是超前。该观点也与最新的实证研究结论相符合(熊俊,2009)。
具体而言,中国城镇化滞后,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数量和质量。由于制度设计不合理,农民进城的预期收益被人为降低,导致一部分农村劳动力仍未转移出来,此为数量滞后。质量滞后,是相对于已经被“半城市化”的这部分居民而言。2011年,按常住人口统计的城镇化率达51.27%,而如果按城镇户籍统计,我国城镇化率大概仅为35%——这中间差距体现的全都是利益。
第二个问题:推动城镇化能否促进我国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答案是肯定的。中国城镇化的滞后,是由于制度障碍。如果将这些制度障碍消除,一方面,能直接作用于经济增长;另一方面,消除制度障碍促进城镇化,并通过集聚效应推动经济增长。此处的城镇化具有额外的经济增长效应,原因在于,此时的城镇化非直接源于经济增长,而是一种“补课城镇化”(暂且这样称呼之)。作为“补课”的城镇化具有经济增长效应,不过是经济增长通过城镇化进一步推动经济增长的效果,“滞后”地释放出来。
城镇化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有效,这与其“有效”的原因是一致的,即其性质是“补课城镇化”。等到将缺乏的都补充完好,其进一步发挥效应的空间也便没有了。因此,我们很难指望城镇化能推动经济增长20年。一旦我国城镇化发展至合理水平,也即城镇化的制度障碍全部消除之时,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也便将重回至与经济增长的循环空间。
四、总结性评述
根据以上分析,最终促进经济增长的还是制度变革,城镇化只是经济实现内生增长的一个桥梁。如果制度存在不合理之处,说明制度变革仍大有可为,制度红利还存在进一步挖掘的空间。纯粹的造城运动确实无法提供持续动力,投资只会造成众多的“鬼城”。由于我国目前仍然存在的许多多制度约束,所以仍然具有很大的制度红利有待释放。因此中国经济持续增长,依然只能寄望于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
[1]辜胜阻:《新型城镇化是未来 20年经济增长新引擎新动力》,http://finance.sina.com.cn/hy/20130427/144715303477.shtml
[2]贾云赟:《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城市发展研究》2012年第12期。
[3][美]迈克尔·斯宾塞:单纯城镇化不是经济增长引擎,http://opinion.huanqiu.com/opinion_china/2013-06/4008500.html
[4][美]约翰·奎格利:《城市化、集聚效应与经济增长》,《比较》2010年第2期。
[5]熊俊:《对中国城市化水平国际比较中若干问题的探讨——兼论中国城市化水平的滞后性》,《中国人口科学》2009年第6期。
G322
B
1007-6344(2017)02-0318-01
李思玮(1988-),女,安徽人,上海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硕士专业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金融市场与中国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