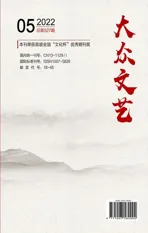当下中国“新民谣”的“南北”意识
2017-04-08李小雨四川大学610065
李小雨 (四川大学 610065)
当下中国“新民谣”的“南北”意识
李小雨 (四川大学 610065)
“新民谣”于2000年走入流行乐坛的视野,至今已经17年之久,它从最初发迹于狭小的圈子到现在成为一种流行,是很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它所具有的一种“南北”意识在近两年更是蔚然成风,但是“新民谣”中对南方和北方的唱词,前人并没有给出太多的关注和理解。这种“南北”意识的形成有其深层的历史和当下的原因,并且和“新民谣”自身的精神内涵有不可分的关联。本文就“新民谣”所具备的“南北”意识的表现方式以及其形成的原因给出简要的分析,并从它所具备的先锋性和危机感去进一步思考“新民谣”在当下所蕴含的理念和其存在的合理性。
新民谣;“南北”意识;先锋性;危机感
在这个千禧年之初,大陆新民谣开始在中国流行音乐界崭露头角。它一方面源自于20世纪90年代大陆城市摇滚音乐,随着摇滚乐队的解散和摇滚市场的低迷,它以自己特有的方式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可以说,在最初新民谣是小众的,而做民谣的人觉得这是难以启齿的,周云蓬说:“2000年,世界末日没有到来,我住在树村。那时不好意思跟人说,我是搞民谣的,在血气方刚的摇滚斗士中,民谣意味着软弱、矫情、不痛不痒。”1但是随着新民谣有异于摇滚金属味道的清新之风从小众刮向市场,如今它的确成为带有大众消费色彩的一种音乐类型。而2105年,一首《南山南》唱遍大江南北,在这之前和之后,都有大量以南北为主题的民谣作品问世。能随口道出的就有好几十首,如:《春末的南方城市》(2004)、《南部小城》(2009)、《南国的孩子》(2009)、《南方的我、北方的你》(2010)、《北方的北方》(2010)、《西北偏北》(2011)、《北上的列车》(2012)《南方姑娘》(2011)、《南方的秋天》(2013)《一个人的北方》(2013)、《北方女王》(2013)、《北方姑娘》(2015)、《远在北方孤独的鬼》(2015)、《北方情歌》(2015)、《南方北方》(2016)、《再见南方》(2016)等等。可以看出,在21世纪初这种“南”“北”的感受便已经呈现在民谣中,到了2010年左右,对“南北”的区别与歌唱在“新民谣”中成为一类,而这种趋势到近两年也是有增无减。
本文将这种体现在“新民谣”中鲜明的南与北的划分定义为一种创作意识,这种意识,使得这些歌曲成为“新民谣”中的一类,而且具有较高的辨识度。不论歌曲本身的优劣高下,单是看这些相似的曲名,便可看出这些歌手心中有着并不鲜明但十分明确的南北界线,更不用说隐藏在歌曲之中的“南北”意识。就仅仅从题目看出“南北”界限是要有的,而且要达到势均力敌。这其中造就的刻意与区别,是如何形成的?而又为何成为了一种集体创作意识?这里明显的南北之分,有何意义,又如何能为听众接受?这些问题都值得深究。
一、“南北意识”的言说方式
1.以城市的书写为标志
在新民谣中,歌唱者或创作者,都会对一个城市作出南北的界定,虽然这种界定并没有明确地不以自然地理的角度去看待城市的南北方位。而在众多新民谣中,以城市名字为歌名的歌曲更是数不胜数,几乎所有省会都成为了歌名或歌唱的对象,而且许多小城成为了热门的选择,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城市民谣”。
虽然,城市的名字并不能直言新民谣的“南北”意识,但是在歌词的行文中,创作者的确有着鲜明的南北之分,的确是将一座城市从南北位置去考虑。如严老板的《无锡》:“想念被河水拉长,多么柔软的南方”;宋冬野《关忆北》:“我正在下着雨的无锡乞讨着生活”“我的一生却再也没有北方”;李晋的《扬州》“南方遥远北方辽阔世界依然是村落”;陈小虎的《兰州故事》:“人们不来偏北的高原,不知道兰州在哪里”;花粥的《西安》:“而你在遥远的北方想起我”;姜博文的《通化》:“想起北方的那座小城一定是大雪漫天”;谣大鹏的《呼和浩特》:“我们这个城市就在北方”;李中玮的《张掖姑娘》:“我在西北悲伤地原野里大声唱”;王胜的《武汉》:“走在南方周末的街头……让我暂时忘了北方的寒冷是否还有”等。
其实,新民谣对城市的关注是有90年代城市民谣或摇滚音乐的影响,而在每一首歌中,创作者力图将对象城市的特色元素融合进音乐里,比如在诉说“兰州”时,多会提到穿城而过的黄河、牛肉拉面、以及“兰州烟”;在与“西安”相关的曲目中,多放入城墙、油泼面、秦腔等元素;在有“南京”的歌中,多刻画南京的雨水等南方潮湿的感觉等。目的是传达出这座城市的独特性,引起与这座城市有关人的情感共鸣。
当然,城市的南北地理位置造就了一个城市独特的气候与人们习性以及相关的情感记忆。有人取了大约30个覆盖大多数人群的民谣歌手和乐队,包括李志、尧十三、赵雷、宋冬野、周云蓬、逃跑计划等等,以及一些其他风格的歌手和乐队,比如老一些的汪峰、窦唯、朴树和新一些的低苦艾、谢天笑、反光镜、草东等。并随机抓取各个歌手和乐队的前50首歌,对所抓取的歌词(约42万字)进行数据分析。在众多城市中,北方城市胜于南方城市,成了在歌词中被唱的最多的地方,尤其是北京,一共出现了81次。2(仅供参考)
每个城市都有其独特之处,但是“南北”成为了最基本的区分项,只有言说了城市南与北的,才能进一步去抒发创作者的情愫和抒写城市的特点。
2.直言“南”“北”的差异与认同
在歌曲中,南北的差异是多方面的:北方和南方;干燥与湿润;寒冷与温暖;直爽与温婉;大雪纷飞与阴雨连绵;大漠孤烟与小桥流水等等。在这些歌曲中,南与北是分明的,但又不局限于具体的哪一个城市与地方。当然,在这些曲目中,并没有明确的南与北的界线,这种界线是十分模糊的,只是一个感性的说法和印象。但是可以肯定,创作者在创作时是有一个自己的参考系的,如果笔下写的是北方,那他心中必定有一个与之相对的南方存在。当然,除了以上的南北差异之外,在诸多区别之间,新民谣表达了一些相似的主题或者说是情绪。
首先,这种南与北的对立,其实是造成了一种心理上的距离感。表达的是一种青春逝去,故乡物是人非而再也回不去的失落,如宋冬野的《关忆北》:“当你装满行李,回到故乡,我的余生却再也没有北方”;张小九的《南方,北方》:“南方,北方,那时候我们正值年华……而时光匆匆让人潸然泪下。”其实在创作者那里,南北是隔膜的,不同的物候加强了南北时空的错落感。
其次,正因为在创作者眼里南北是不同的,所以总有一个与身处当的下迥然不同的南方或者北方。所以,对立的那一个正好成了人们向往或者逃离要去的地方。如好妹妹乐队《北上的列车》:“北上的列车带我离开,我也许不再回来。”;倪健的《北方》:“厌倦了北平的生活……突然看到鸿雁飞向南方……我撑着船儿逃离了故乡。”总之,不论南北是如何的不同,但二者在概念上的确是对立的,是不可能同时兼得,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新民谣中的这种“南北”概念,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南方与北方。
再次,如果不是现实中南方与北方的自然地理位置的相对,那么新民谣中“南北”就成为了不可跨越的心理上的概念。这更是造成了一种无法弥合的无奈。如赵雷《南方姑娘》:“南方姑娘,你是否爱上了北方……南方的果子已熟,那是最简单的理想”;野孩子《眼望着北方》:“我眼望着北方,弹琴把老歌唱,没有人看见,我心里多悲伤”;宋冬野《安河桥》:“让我再尝一口秋天的酒,一直往南方开不会太久”。南方通常是向往的地方,是逃离所向,而相对的北方却是已远离或要归去的故乡。总之两者的对峙将这种地理上的认知强化,而且较传统意义上的地理方位富有时空的张力。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是“南北”的不同,让很多人有了一种错落与无奈,也有了一份离去与归来。但是并没有好坏的区分,也正是如此,才有了可以选择可以言说的空间和可能性。而且,在大数据分析中“南方”稍微高于“北方”,但可以说是不相上下。3
二、新民谣中“南北”意识产生原因
1.历史形成的“南北之争”
会有人说,我国幅员辽阔,东西距离约5200公里,南北距离约5500公里。为什么在我国南北文化差异说得多,而东西文化上的差异则说得较少呢?我想这是有深一层的文化原因的。
在古代“天下观”中,其实是没有明确的地理方位的界限,“我国古文献上的‘中国’一词,或指京师(首都),或指中原地区,或指内地,或指诸夏族和汉族居住的地区,或指中原王朝。”4以“中国”为中心,便形成了“东西南北”四个大的方位,当然我国的历史是国内各个民族共同缔造的,由于历史上政治经济的变动,逐渐形成了南北上的文化差异。
政治上,自秦成为大一统国家之后,不断受到周边少数民族的侵犯。至西汉初,匈奴崛起于北方,不断掠夺汉王朝北部边郡,经过多次战争,匈奴臣服于汉。而到了三国、西晋时期,拓跋鲜卑部落迁徙至现今内蒙古中部,逐渐加强其权势,成为当时我国北方最强大的少数民族。而南北朝时期,五胡内迁,与汉族交流融合,是一次大规模的南北文化的交融。而唐朝也有鲜卑族的血统,经过不断的统一与向北扩展,唐朝疆域向北已到达贝加尔湖畔。到了北宋,北方契丹族建立辽王朝,而后来金灭辽,到了南宋,不得已向江南迁移。又一次大规模促进了南北的交流。之后,北方蒙古族成吉思汗又重新统一中国,建立元朝。而清朝也是由北方的满族建立,其统一蒙古诸部落,又入山海关,至1661年收取江南。总之,在一次又一次民族融合的趋势中,南方与北方也不断地交流碰撞。
在经济上,我国古代的经济中心逐渐从北方转移到南方。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而在西晋之前,南方都属于蛮荒之地,全国的政治经济重心都在北方,而东汉末年,中原地区的战乱使得人口大规模向南迁徙。随着之后的“永嘉之乱”以及“安史之乱”,使得经济重心最终由北方转移到南方。而南方也成了人们心中所向往的地方,由于古代交通不便,从北到南有重重阻碍,而这也加剧了南与北的巨大心理差异。
所以,“文化不只是一批知识与想象的作品而已,从本质上说,文化也是一整个生活方式”5这些北方与南方的差异,自古以来在人们心中逐渐形成,“一部艺术作品被生产出来后,也就包含着那种可以说是世代相传的信息。”6而民谣的内核就是贴近民间,贴近生活,“在回归乡土传统的思路里做音乐”7,所以根植于中国人心中的南北差异也就自然而然可以被放入“新民谣”的理念之中。
2.乡土的变迁和主体性的模糊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大浪潮,并且投身于“全球化”的进程中。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在逐渐瓦解,因此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问题。这也能够理解,为什么90年代,摇滚乐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在震耳欲聋的金属声中,用嘶哑的嗓音吼出自己对时代的不满与批判,用不妥协的姿态去振奋充满迷茫与焦虑的一代。但是,这种声嘶力竭的反抗最终没有抵抗的了时代的大势所趋,摇滚退位给了民谣。
就像前文所说,“民谣”是要回归乡土的,是要根植于民间的。但是“乡土”都消逝了,何谈回归?他们开始了漂泊与寻找。其实作为摇滚的继续,民谣更多的是以其小众的接收方式进入市场,但它的确有着一种对社会整体的失望,只是较为温和和隐蔽,而不像摇滚那样赤裸裸。“这种暧昧莫名的不满情绪和不愿随波逐流的边缘意识使得这个时期的民谣音乐常常与“摇滚”相混同并且分享着大致重叠的表演空间和受众群。”8在乡土社会中,大量的民间百姓虽然没有上层达官贵人的权势与地位,但是在传统的社会中是有着其“主体性”的,而随着现代化的入侵,城市取代了农村,而城市也变得千篇一律。来自底层的大量百姓失去了千百年来的具有的“主体性”,迷失在了巨大的时代转型之中。而民谣的创作者,也正是体验到了“故乡”的失落以及无处可寻的痛苦。
所以,“新民谣人”开始了他们的流浪之路,寻根之路。他们去过大大小小的城市,去过南方,去过北方,他们试图要营造出所到之处的不同,他们一定要找到差别,这样才能找到心之所归。但是不管所到之处有多么的不同,对于这一代人来说都是“他乡”而并非“故乡”。所以他们还在路上,还在痛苦地寻找,前往而又逃离,痛苦地辨别何处才是真正的归程。所以他们是要强调“南北”这样基本的区分,希望是总有一片土地是心灵的归处,而不是所到之处都成为陌生的异乡。
三、如何看待“新民谣”的“南北”意识
1.弱化消逝的先锋性
“新民谣”身上所具有的先锋性是矛盾的,而这种矛盾更加明显地体现在这种“南北”意识之中。
前文已经说过,“新民谣”是另一种方式的摇滚乐,“他们把摇滚的‘呐喊’转换成民谣的‘诉说’后,也把原来的那种愤怒之词转换成了平和的悲音。”9但是,的确具备时代先锋的性质。“先锋”一词来源于法国,最初应用于军事领域,之后有广泛应用于文学,艺术和政治领域。在文学艺术方面,“先锋派是(或应该是)有意识地走在时代前面。这种意识不仅给先锋派的代表人物加上了一种使命感,而且赋予他们以领导者的特权与责任。”10这种“先锋性”在摇滚乐身上体现的得更为明显,而在“新民谣”这里有些弱化,不是用激进和极端的方式去反对。它借用中国本土以及民间的一些资源,去构建自己的乌托邦,以对抗现代性所造成的后果。
其实,在潜意识里,“新民谣”认定自己是具有或应当具有先锋性的,因为“当学者、作家和诗人们操作‘民间’这同一话语符号的时候……有一点共同之处,即凡操作这一语符的人都表达了对某种或主流话语的抵制甚至反抗,而无论支撑这种话语的权利来自政治领域还是文学领域。”11但是来自于底层和民间的创作者,深知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理想”已经成为人们耻笑的对象,而“新民谣”也不再去重复摇滚时代的“荒谬”,只能更多关注现实关注自身。“南北”意识,是一种不盲从不遵从的姿态,南与北的不能等同,不能和解,正是他们先锋意识的体现。“新民谣”中的“南北”意识,很大一部分是有意为之的,开始是作为一种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背离。你有你的“南方姑娘”,我也有我的“北方女王”;你有“南方小城”,我也有“北方小城”;你有“南方的秋天”,我就有“北方的春天”;你有“南方的早晨”,我有“北方的深夜”等。可以说这的确有着一种要表现自己立场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在“南北”意识上的加深,却让其走向了一种相互竞争与游戏化,以至于忘记了最初为什么要寻找差别。然而当它这种有意识的区分,营造一个对象去反对,成为人们消费的对象时,它所要表达的便成为一种陈词滥调,它也走向了自我的瓦解,这种“南北”之分便毫无意义可谈。
2.深刻的危机感
这些弊病,并不能完全归咎于“新民谣”自身,在当下文化市场运行机制下,出身底层的民谣人,需要调试自身才能存活于当代话语之下。他们有着深刻的危机感。
民谣在英语中是folk-song。而“folk这个词是古条顿族语言中,众多拼法之一;在古英文中,它是folc。它具有people的一般意义。”12而“Folk-song(民歌)这个词被收录,最早是在1870年。”13到了20世纪中期,在德国、英国等欧洲国家,有一场“影响普遍的民歌运动:将口语流传的乡村、佛那个也歌曲记录下来并改变成新的作品来表演,仍保有原来的精神及模式。”14此时,的民歌与“流行乐曲(popularsongs)”有了内涵上的重叠与联系,而“popular”这个词同时也有民众的意思,后来演变为“流行的”“大众的”含义。中国“五四”时期的“歌谣运动”受到西方“民歌运动”的影响,而却倾向于从中国本土和民间去寻找构建“传统”的资源,可以说当下“新民谣”的确是有着“歌谣运动”的价值取向和精神内核。
但是,走进民间是不能与大众分离的。而当下中国的现状则意味着,大众审美成为了主流的一种趣味,那么“新民谣”则不自觉地(或者说不得已地)去迎合主流文化。就算最初具有反抗的意识和先锋性,但是也只能在大众的把玩之中走向消亡。而这种“南北”意识,也是在蜂拥而起中趋于缓和,一方面是因为太多相关的作品容易造成审美疲劳,另一方面的确是因为这种“南北”意识的流行导致了其美好愿望的失败。
所以,“新民谣”中的“南北意识”的兴起和最终走向衰落,不仅表现着民谣人对于社会现状产生的危机感,更是他们对于自身如何存在的困惑与焦灼的演绎。在这种潮流中,民谣人甚至不清楚民间是什么,他们只是承袭了“五四”以来的话语方式,“当民间被要求承担近代以来西方市民社会所发挥的功能时”使得folk被移译为汉语“民间”而启蒙化。15以至于现在民谣人想借助民间话语和本土所营造的本土传统表象,被裹挟在了普遍主义现代性原则中,迷失了自己,甚至想要表达,却无从用力。
3.无止境的寻找
“南北”意识,只是“新民谣”前进路上的一个鲜明的方面,至今并没有完全丢弃,甚至还有回春的迹象。但是,就算没有了“南北”的歌唱与言说,“新民谣”还是会继续去寻找“归程”和“故乡”。其实,很多人对“新民谣”抱有很大的信心与期待,“由于‘民族’与“‘世界’之间的中介发生了深刻的转变,民族主体的现代性焦虑始终存在并且随着中国介入全球化程度的深化而不断加剧,因此“新民谣”展现出来的世界想象也是复杂纠结且充满张力的。”16所以,如果“新民谣”的南北意识彻底沦为其所反对对象的欣赏物时,或者当其发现所反抗的对象并不存在时,它也就会走向自身的死亡。由此来看“新民谣”的每一种尝试都是实验性的,而且“大陆新民谣还面临着诸多问题,如民间文化生长土壤的贫乏、新民谣向主流文化的主动示好、民谣音乐人与大众生产机制之间矛盾重重、小众文青对于民谣歌手大众化的反感等。”17但是它的发生和走向还会让它存有直面社会矛盾、反思现代化的后果的批判精神和寻找精神家园的终极目标。
而其“南北”意识,的确在某种程度上为听者拓展了一个不同寻常的音乐世界或者说是感官世界,让身处异乡的游子重温熟悉的地名和物感,在音乐中加深了对对“故乡”的记忆与感受力,这也是“新民谣”中“南北”意识受欢迎的原因之一。它怀着略带伤感的温情脉脉切合了很多人对故土的还念,在急速改变的社会中对乡土的变迁作了必要的记录。当然,我们也不能以我们的标准去要求“新民谣”的发展和走向,毕竟他要生存就“要植根于当下社会生活的新模式,适应当下社会的传播环境和接受机制。”18不论今后其“南北”意识将如何继续,但相信“新民谣”经过尝试与探索,它成为“一种出奇制胜的激活的力量,甚至是革命性力量。”19它依旧在路上,不论寻找还是迷失方向。
四、小结
“新民谣”的发展与走向的确可以作为观察当下中国流行文化的一扇窗口,其自身蕴含的多种表现方式也是在中国巨大的社会转型期下造就的。其中显现的“南北”意识更是尤为突出,它的形成不仅带有历史文化的遗留,还有着现代性的影子。这种“南北”意识在当下深刻的危机中也弱化了应有的先锋性,但其还是通过大大小小的城市抒写以及南与北的言说,在迷茫中继续寻找遗失的“民间”与“乡土”。
注释:
1.周云蓬.春天责备[M].上海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P217
2.我分析了42万字的歌词,为了搞清楚民谣歌手们在唱些什么[DB/ OL].http://mp.weixin.qq.com/s/NfIyGVbzKXkM33zA1Z82gw,2017年2月7日
3.我分析了42万字的歌词,为了搞清楚民谣歌手们在唱些什么[DB/ OL].http://mp.weixin.qq.com/s/NfIyGVbzKXkM33zA1Z82gw,2017年2月7日
4.中国古代史常识:历史地理部分[M].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年10月第一版:P10
5.雷蒙·威廉斯著,吴松江、张文定译.文化与社会[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P403
6.荣格.心理学与文学[A].心理学与文学(冯川等编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P138
7.魏小石.新民谣在中国:谁的幻想?[J].书城,2010年第4期
8.刘斐.日久他乡是故乡:“新民谣”的历史记忆[J].艺术评论,2011年第2期:P50
9.赵勇.从摇滚到民谣“批判现实”的音乐轨迹[J].社会关注:P42
10.马泰·卡林内斯库著,顾爱彬、李瑞华译.现代性的五副面孔[M].译林出版社,2015年2月第1版:P112
11.吕薇.民间:想象中的社会[A].文化研究(第1辑).陶东风,金元浦,高丙中主编.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6月版:P156
12.雷蒙·威廉斯著,刘建基译.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10月北京第2版:P231
13.同上:P232
14.同上:P233
15.吕薇.民间:想象中的社会[A].文化研究(第1辑).陶东风,金元浦,高丙中主编.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年6月版:P165
16.刘斐.日久他乡是故乡:“新民谣”的历史记忆[J].艺术评论,2011年第2期:P51
17.张慧喆.大陆新民谣— —从“大众”到民间”的意义[J].文学与文化,2014年第4期:P137
18.同上:P137
19.王一川.走向文化的多元化生— —以文学艺术为范例[J].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李小雨(1994-),女,陕西省渭南市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