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财政依附性反思中国社会保险
2017-03-09熊伟
熊 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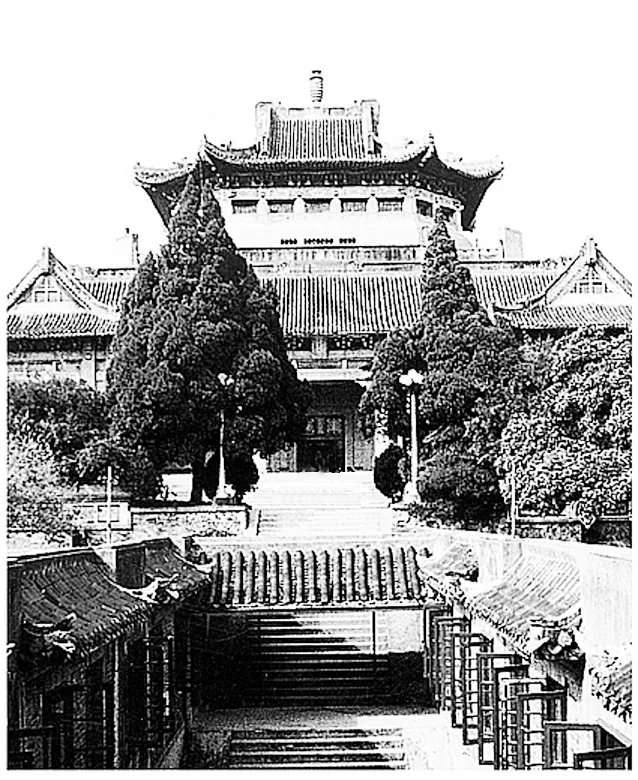
从财政依附性反思中国社会保险
熊 伟
社会保险是一种参保人自我负责的互助共济制度,建立在精算平衡的基础上,其收入和支出都应受法律约束,不宜由政府自由裁量。社会保险与财政应保持相对独立,政府不宜直接干预社会保险财务,社会保险不应依附财政。鉴于此,社会保险基金不宜纳入政府预算,而应该财务独立,自治管理。作为利益主体之一,政府可以参与社会保险的管理,但不能垄断,参保人和公众都有参与权和知情权。基于不同的理由,政府有义务补助社会保险,但补助必须条分缕析,于法有据,不宜将制度转型成本和政策性开支等同于政府的制度担保人责任。
财政依附性; 社会保险; 财务独立; 体制转型
政府对于社会保险从来不能缺位,否则,社会保险制度很难建立及运转。尽管如此,社会保险却不宜依附财政,二者在法律上应保持独立性,遵从不同的理念和原则,防止在主体和权责方面的混同。我国仿效美国和英国的做法,由政府出面充当社会保险人。社会保险甚至被纳入财政管理,其主体、财产、管理、责任等方面都与财政重合。这种严重依附财政的社会保险虽然在获取财政资金、借用政府信用方面颇具优势,但会带来政府责任的无限扩大以及资金管理方面的僵化官僚。一旦将社会保险趋同于国家福利,淡化缴费与享受待遇之间的关联性,社会保险内在的人性尊严、自我负责、社会连带理念也会受到冲击,参保人的权益保护势必难以周全。因此,应重新审视我国财政与社会保险的关系,基于主体区分重构二者之间的法律关系。
一、 社会保险关系与政府的角色定位
社会保险源于大规模工业社会风险分担的需要(察赫,2014:240)。在农业社会中,家庭是基本的生产及生活单位,成员之间的扶养照顾,加上家庭本身的经济积累,基本可以解决健康、养老的问题。养儿防老,积谷防饥,就是这种模式的写照。如果出现更大的风险,基于血缘的家族也可以发挥一定的互助功能。由于当时手工业的规模小,从业人员常常以家庭成员为主,家庭给养仍是主要的保障模式,辅之以行业协会的互助互济,政府一般无须承担社会安全职能。而在工业社会中,城市人口聚居、大家庭的解体、大规模机器生产的引进、高度危险行业的出现,不仅产生了日趋普遍和严重的职业伤害,也让传统的医疗、养老等风险难以继续在家庭内解决(Kaufmann,2006:250)。为缓和劳工阶层与资本家之间日益激化的矛盾,也包括作为对抗社会主义思想传播的措施之一,社会保险在俾斯麦时期的德国首先出现,便不是一件让人意外的事情(Kaufmann,2006:249)。
其实,不管是养老,还是疾病治疗、失业救济、生育保障,都可以通过国家福利方式提供。相对而言,其分担风险的能力甚至会强于社会保险。但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在现代国家中,高福利总是和高税收连在一起。如果国民相对富裕,收入差距小,让政府有机会获得充裕财力,同时保证福利分配大体公平,这种体制也许的确能运作良好。北欧国家的实践就是例证。然而,要想让国家福利覆盖社会的方方面面,运作成本十分高昂,一旦财政汲取能力变弱,就会陷入入不敷出的困境。另一方面,如果地区发展差距、居民收入差距大,居民贡献不一但福利相差无几,公平问题就会凸显。因此,虽然各国都在为国民提供福利,但一般限于急迫性事项或特定人群。至于养老、医疗等,由于其构成可预见的持续性开支,将其纳入福利体系的国家并不多见。
相比国家福利,在解决社会风险方面,社会保险的特点在于:第一,社会保险有别于财政,一般不需要国家提供资金。除非需要特别照顾,否则,所有参保人都必须缴费,才有可能在发生保险事故后享受保险待遇。而国家福利并不以特定个体的纳税作为前提,而是根据需要和可能来提供。第二,社会保险的缴费与享受待遇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一般而言,缴费越多,享受的待遇越高。这种关联性使得保险待遇成为参保人的权利,而不是国家的恩赐。这有助于维护参保人的人格尊严,从心理上摆脱对国家的依赖。而福利标准并不基于纳税数额,是否提供福利,提供多少福利,完全由国家斟酌决定,纳税人没有请求权。第三,国家福利必须以政府名义举办,而在社会保险关系中,政府并不必然成为当事人。即便政府部门承担保险人职责,也可以通过特定的法律构造,让国家与社会保险保持相对独立。
社会保险通常可区分为“福利型”和“保险型”两种形态。在福利型社会保险制度中,社会保险事务基本上由政府负责,社会保险资金通过税收方式征集,社会保险待遇支付也由政府有关部门负责,政府充当社会保险人的角色。这些国家包括北欧国家、一些英语国家以及部分中东欧国家,如瑞典、美国、英国(郑秉文、房连泉,2007:10)。在保险型社会保险模式下,社会保险资金通过社会保险费的方式征集,由雇主和雇员供款,强调风险分摊原则,政府只负责行政费用或者若干赤字弥补(孙迺翊,2008:2)。比如,法国和德国就设有专门的非政府组织经办社会保险事务,或者由私人保险公司经办(贝克尔,2005:1)。然而,无论是哪一种类型,只要坚持风险分担的保险原理,就必须遵循风险、缴费与待遇的关联性,坚持精算平衡原则,确保社会保险与财政的区分,让社会保险依法独立运行。
社会保险的经典模式可以简化为,根据法律设定的条件和标准,参保人缴费,保险人承保。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向参保人支付保险待遇,政府只是履行监管和保障职能,并不直接成为保险关系的一方(察赫,2014:259)。即便根据法律授权,政府在缴费标准、待遇确定、资金管理等方面行使一定的职权,政府仍是社会保险关系之外的主体。保险型社会保险与这种模式高度契合(郑秉文、房连泉,2007:10)。即便是福利型社会保险,虽然政府直接充当社会保险人,财政与社会保险也会适度分离。正如政府对国有资产的所有权职能与对社会事务的管理职能不一样,作为社会保险人的政府与作为公共管理人的政府同样可以区分。通过一定的法律设计,可以创造出公法上的经办主体,如借助信托机制建立基金,代表政府行使保险人权能,免于跟公共管理职能混同。按照这种安排,政府的责任相当于“最后保险人”,它所起到的是支持、保障和兜底作用,而不是替代社会保险人对外承担责任(Pierre Koning,2006:381-389)。
有鉴于此,不管是哪种类型的社会保险,社会保险与政府财政都应当分离,社会保险收入不应混同于财政收入,社会保险支出不应定性为财政支出。虽然政府在社会保险改革方面经常居于主导地位,但这绝不意味着政府替代社会保险。如果将社会保险改造为纯粹的财政行为,社会保险将不再具有保险性,与参保人自我负责、风险分担的原理相冲突,而会变成事实上的国家福利。即便政府充当社会保险人,也应设定专门的法律主体独立负责,财政与社会保险仍然得以分离。也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坚持社会保险的财务独立性,维护社会保险的保险性质,防止社会保险异化,最大程度地维护参保人的利益。
二、 财政扶持与社会保险的财务独立
社会保险财务独立是基金收支平衡的需要,也是参保人自我负责和团体成员之间连带互助的要求,能增强社会主体对社会保险的参与意识和对保险制度的认同感,也可有效减轻国家财政负担。德国社会保险制度基于自治的理念,强调所有社会保险支出、准备金以及行政支出,均应由保费加以支应(孙迺翊,2008:101)。即便在政府主办社会保险的国家,通过设计一定的法律架构,社会保险与财政之间仍可保持恰当距离,以保障社会保险的财务独立性,同时厘清政府的财政责任,避免身份混同和责任泛化。例如,美国联邦政府成立社会保障信托,独立于财政运行,不必遵循政府预算程序。政府征收工资薪金税后,随即信托给社会保险基金,作为基金收入来源,用于社会保险开支(佩塔斯尼克,2009:74)。
尽管如此,财政与社会保险之间的联系仍无法割断,这在各国社会保险实践中不仅客观存在,而且非常普遍。随着福利国家观念的普及,发展社会保险事业成为国家的义务,享受社会保险则成为公民的权利,一些国家的宪法对此都有确认(陈新民,2010:449)。例如,我国《宪法》第四十五条即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年老、疾病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情况下,有从国家和社会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国家发展为公民享受这些权利所需要的社会保险、社会救济和医疗卫生事业。”基于这个背景,国家对于社会保险不能置身事外,而必须通过制度供给、财政扶持和信用担保的方式,发起、推动和支持社会保险事业,也包括对社会保险行为的监管和规范。从这个角度来看,财政介入社会保险是国家责任的体现,是现代国家的宪法义务。
财政对社会保险的扶持有很多方式,大多数体现为资金支持,也可能表现为管理服务或制度借用。在资金支持方面,例如,在社会保险事业刚起步时,由于公众接受度低、参保覆盖面不宽、缴费率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导致社会保险收入不足,难以应对社会保险待遇的支出。此时,政府即有必要提供资金支持,帮助社会保险解决资金困难,引导和鼓励更多的人自愿缴费,提高保险的缴费率。此外,对于经政府特许的缴费减免,或因政策变化而导致的支出标准提高,财政有责任填补费用,使社会保险基金的利益不至受损。再则,对于未来可能出现的支付不能,政府还有必要未雨绸缪,建立社会保险储备基金,维持人们对社会保险事业的信心。万一社会保险发生支付不能,基于“最后保险人”责任,政府有义务投入资金,对社会保险施加救助。在管理服务和制度借用方面,财政也可发挥多种形式的作用。例如,我国将社会保险基金纳入财政预算管理,同时要求将社会保险资金存入财政专户,一些省份的地方政府还委托税务机关征收社会保险费*据笔者统计,自2017年1月1日起,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和5个计划单列市中,由税务机关征收社会保险费的有22个,其余14个由社保经办机构征收。。尽管有些做法可以从法理上商榷,但毫无疑问,这是典型的财政为社会保险提供管理服务。美国等一些国家开征社会保险税,但仍然维持缴税与保险待遇之间的关联性,并通过信托设立社会保险基金,保证社会保险独立运行。在很大程度上,这种社会保险税也是在借用财政资源,形式上是税,事实上就是社会保险费。税收形式所能提供的,是征税的便利和效率,就社会保险而言,其他的并没有发生变化。此外,尽管社会保险基金不同于财政资金,但都属于公共资金,在公众参与和公开透明方面有共性要求,财政经验也可以为社会保险所借鉴。
该如何看待财政与社会保险的联系?是因为其存在就主张取消社会保险的财务独立性,让社会保险依附于政府财政,还是在承认的同时维持社会保险的独立性?笔者认为答案应该是后者。社会保险的财务独立性是由其内在禀性决定的,并不会因为其与财政联系紧密而消除。如果否认社会保险对财政的独立性,将其混同于政府财政行为,社会保险将不再是社会保险,而可能会变成国家福利。这是因为,社会保险是团体成员共同分担风险的机制,缴费形成的保险基金是应对风险的物质基础,缴费与保险待遇之间的关联性是团体成员自愿参保的心理基础,财务独立则是社会保险有效运行的制度基础(张荣芳,2015:3)。如果保险基金没有稳定的资金来源,如果保险事务没有自主的决策机构,如果保险财产不能被免于外在干涉,而是完全遵照政府财政的运行逻辑,社会保险的“社会性”和“保险性”就不复存在,而成为变相的国家福利。
相比社会救济、社会福利等传统的社会保障项目,社会保险的“社会性”体现得最为明显。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仍是国家直接出面解决社会问题,社会本身的主体性并没有体现出来。借助于保险机制,社会保险则在国家与个人之间开创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对于养老、职业伤害、医疗等社会问题,保险团体依据大数法则分摊风险,所有成员共同缴费,共同形成应对风险。在这种机制下,“社会”问题“社会”解决,因此,它是最能体现社会保障特色的领域。尽管国家会对社会保险提供帮助,但这不足以消除社会保险的特性。从法律角度可以说,国家提供物质帮助,只是在履行国家责任。而社会保险事业从国家获取物质帮助,则是公民基本权利的体现。正是由于社会保险在机制上独立于国家财政,才使得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区分在社会保险领域表现最为充分。
三、 中国社会保险依附于财政的具体体现
中国社会保险明显呈现两面性。一方面,它坚持保险原理,强调参保人自我负责,社会保险收支平衡,保险基金专户管理,经办机构与政府相对分离,希望维持社会保险相对于政府和财政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它又将社会保险纳入财政预算,政府在机构设置、内部决策和资金调度方面强力介入,社会保险和财政很大程度上相混淆,主体、财产和职能的独立性变得模糊,社会保险严重依附财政。由于社会保险是现代国家的职能,社会保险必然与财政发生关联,其两面性在任何国家都会存在,但其效果却不一致。相容的配置不会发生法理冲突,在分立的基础上发生联系,在联系的同时承认分立。不相容的配置却会导致一方否定另一方,事物内部呈现尖锐的法理冲突。笔者认为,中国社会保险对财政的依附性,本质上存在着反社会保险的因素,需要基于社会保险原理进行协调。
(一) 社会保险纳入财政预算与保险原理不符
作为全口径预算管理的一个环节,我国自2010年起试行社会保险基金预算,2014年修订的《预算法》对此正式予以确认,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成为政府复式预算体系的组成部分。虽然国家加强社会保险管理的初衷可以理解,但是,严格按照这种方式运作的后果是,预算编制和审批机关对社会保险基金拥有裁量权,可以决定收入和支出的项目、标准和规模,这与社会保险收支法定的要求相冲突,对维护参保人之于社会保险的信赖并无益处。众所周知,预算程序是利益主体争夺资金的渠道,也是社会政策博弈妥协的重要机制。对于社会福利、社会救济而言,政府和预算审批机关每年视情形相机行事,这是理所当然的。但社会保险是一种类似于长期契约的机制,依赖强有力的法律制度予以支撑,否则难以取得参保人和全社会的信任。社会保险资金的收入和支出应该事先通过法律明定,并保持其稳定性。一年一度的资金预算分配机制不适于社会保险资金。而如果形式上被纳入预算,实质上却不能接受任何审查,而且必须批准通过,这样的预算程序难以起到作用,反而会消减预算审批机关的权威,也造成了制度浪费,并且增加行了政成本(张荣芳、熊伟,2015:3)。
(二) 政府包揽一切,参保人自治管理权被剥夺
由于我国未能区分社会保险与财政,社会保险事务完全被当成政府事务,社会保险的自治被政府规制所取代。例如,虽然按照《社会保险法》的规定,统筹地区设立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但其职能仅限于日常业务的经办,不包括社会保险重大事务的决策。在现实中,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形式上独立,是依法成立的事业单位法人,事实上隶属于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人、财、物都无法独立(张荣芳、黎大有,2014:13)。参保人作为社会保险关系的主体,除了作为缴费义务人和待遇请求权人,没有渠道参与保险事务的决策和管理。社会保险的重大事务决定权掌握在政府手中,包括统筹地区的政府,也可能是上级政府乃至国务院。例如,2016年《关于阶段性降低社会保险费率的通知》就是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联合下文的。医疗和工伤保险报销标准的调整则由统筹地方的政府决定。尽管政府负有“最后保险人”责任,必须维护社会保险事业的正常运转,但既然是社会保险,本质上应该“众人之事众人管”,参保人自治的机会不可以被剥夺。否则,当出现政府损害参保人利益的情形时,参保人很难在决策程序中予以制衡,只能事后通过其他渠道争取补正。
(三) 财政补助事由不清晰,侵蚀社会保险的独立性
财政补助是社会保险重要的资金来源。据《2015年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事业统计公报》披露,财政对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补贴为4716亿元,占该项保险全部基金收入的16%;财政对城镇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补贴为2155亿元,占该项保险全部基金收入的75%。不过,在历年的预算、决算或统计报告中,政府都没有列明补贴社会保险的具体事由,而是笼统地将其定性为“促进”“扶持”或“帮助”。事实上,我国上世纪90年代建立社会保险制度时,社会保险替政府承担了大量的转制成本,后期又替政府支付了多种形式的政策性支出,包括减免养老金缴费、提高养老金支付标准等。如果将社会保险理解为独立于政府的主体,基于上述事实,政府对社会保险的补助并不是扶持,而是偿还债务(熊伟、张荣芳,2016:1)。而如果不区分二者的职能,当政府有需要时即命令社会保险配合,事后再以财政补助的形式予以弥补,不利于凸显社会保险的财务独立性,缺乏对社会保险自主意志的尊重,事实上将社会保险作为政府下属主体予以对待。从参保人的角度观察,一旦财政补助在社会保险收入中比重过大,或者补助的频次过高,也很容易淡化自身的权利意识,转而对政府产生心理依赖,社会保险的自主性和自治性都会受到影响。
(四) 过于倚重预算平衡,为政府滥权提供了空间
《社会保险法》第六十五条规定,社会保险基金通过预算实现收支平衡;政府在社会保险基金支付不足时给予补贴。此处所谓的预算,不是指社会保险的内部财务,而应该是指政府预算。由于社会保险收支标准法定,不允许通过预算程序予以调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平衡的方式,只能是从其他政府预算中调入资金*还有一种可能性是,政府在不同险种之间调剂资金,解决特定基金收不抵支的问题。不过,《社会保险法》和《预算法》都强调专款专用,分账核算,说明内部调剂也是违法的。,也就是财政补贴。然而,只要社会保险出现支付不足,政府就给予财政补贴,这种大包大揽与社会保险改革的初衷不相吻合,与已践行多年的社会保险内部收支平衡原则也存在冲突。鉴于现行社会保险法规范过于抽象,社会保险费的征收范围、标准大都由政府规定,对社会保险待遇的给付措施,法律也未完全明确,而是授权国务院主管部门或省级政府决定,一旦确认社会保险通过预算平衡收支,当社会保险基金出现资金缺口时,为了减轻自己的财政负担,政府完全可能利用社会保险管理权,提高缴费标准或降低保险待遇,破坏社会保险的内在统一性。
四、 社会保险与政府财政的归位之策
在充分利用政府信用和支持的同时,如何保持社会保险基金的独立性,破除社会保险对财政的依附,这是中国社会保险必须直面的问题。即便由政府出面主办社会保险,社会保险的财务也应该独立于财政。要做到财务独立,前提在于二者的主体资格不混同。这意味着,社会保险基金在法律上具有独立性,无论是主体资格、基金财产还是决策程序,都应该区别于财政,独立于政府,遵循社会保险自身的逻辑。虽然在现实中,社会保险和财政联系紧密,但这并不能证明二者本身就是一体,更不能证明彼此之间没必要区分。相反,如能将二者在法律上加以区分,反而能更好地解释这种联系。例如,《社会保险法》第65条第2款规定,县级以上政府在社会保险基金出现支付不足时,给予补贴。从行文来看,法律对政府与社会保险基金已经做了区分。不仅如此,从法律属性上分析,“补贴”一般都是指政府对相对人的给付,政府内部的拨款不宜定性为补贴。有鉴于此,笔者认为,我国社会保险制度可从以下方面予以改进:
第一,废除社会保险基金预算,让社会保险脱离财政体系。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本身是内在矛盾的概念,在现实中不具有可操作性。这是因为,社会保险关乎基本人权,是国家的宪法义务,其收入和支出都必须法定,不能通过政府预算斟酌裁量。政府预算的意义在于贯彻财政民主,实现议会对财政的控制。如果缴费义务和保险待遇每年都要预算,并经议会审查批准后才能执行,这可能损害参保人的法定权益,也不利于维护其对社会保险的信心。事实上,在预算程序中,议会无权降低或提高法定的缴费标准,也不可能增删法定的社会保险待遇。因此,将社会保险基金纳入政府预算属多此一举,且会带来权力体系内部的冲突。废除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制度后,尽管基金在收入征收、内部管理、外在监督等方面仍与政府保持紧密联系,但二者已经不具有行政隶属关系,转而成为两个独立的法律主体。这种处理不妨碍继续将社会保险收入纳入财政专户管理,但这只能理解为政府代为管理,因为社会保险基金收入不再是财政资金。这种处理也不妨碍社会社会保险基金编制预算,甚至将预算报送政府、提交人大审议,但其意义只是为争取政府补贴提供论证材料,而不是需要政府或议会审批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第二,坚持社会保险给付的法律保留,减少政府对社会保险的直接干预。
社会保险待遇标准涉及被保障对象的生、老、病、死等社会风险保障,与社会主体的财产保障、甚至生存保障直接相关,需要遵循法律保留原则。 政府通过法律确定社会保险待遇的条件和标准,实际上是政府对参保人的政治承诺。社会保险待遇的标准和条件如果不明确,会导致政府向社会主体征收保险费的对价不确定,社会保险费的征收难度以及社会保险支付中的道德风险会大大提升。我国政府既是社会保险制度的设计者,也是社会保险的组织者和管理者,两种身份存在一定的利益冲突,更应当尽量避免由统筹级别的地方政府制定社会保险给付标准,防止出现全国社会保险待遇标准不统一,也防止地方政府利用保险人与管理者身份的混同限缩参保人利益。
第三,社会保险费应当依据保险精算调整,实现内部收支平衡。
社会保险收入的主要来源是社会保险费。由于社会保险的财务平衡会受到经济发展变化、物价指数调整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在不影响参保主体社会保险权利的条件下,保险费的适时调整必不可少。虽然由于保险费与待遇之间的对应关系明确,保险费的调整不必像税收那样严格遵循法定原则,但也不能完全委托保险人裁量,而应当建立在保险精算基础上。如果按照我国的做法,社会保险基金通过预算实现平衡,或者只要社会保险基金支付不足政府就补贴,由于违背了保险精算平衡的原理,社会保险体系必然难以持续长久*预算平衡的核心是,当社会保险基金支付不足时,政府财政提供补贴。精算平衡则坚持社会保险独立于财政,参考平均寿命、人口增长率、老龄化速度等,定期评估和调整收支标准。二者的联结之处在于,当精算平衡被打破后,如果是由于政府决策造成的,政府有义务通过预算提供补助,帮助社会保险基金恢复平衡。当社会保险出现系统性风险,或因为紧急情况导致支付不能时,政府也有责任帮助其渡过难关。。正因为如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规定,社会保险基金实行精算平衡原则,这是对我国社会保险改革的方向性指引,未来修改《社会保险法》时有必要贯彻(刘志强、白之羽,2015:8)。
第四,社会保险管理应体现公共参与、公开透明。
在我国实践中,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是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的下属机构,接受社会保险行政部门的领导。这种体制源于目前财政与社会保险界限不清的事实,与社会保险财政化的理念一脉相承。一旦废止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将社会保险与财政体系脱钩,社会保险的管理体制就应该随之调整。具体而言,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只行使监管职能,具体的决策和管理交由经办机构处理。笔者主张,经办机构由政府代表、参保人代表和外部专家组成,内部管理遵循自治原则,在法律确定的治理架构下自律管理。政府不能直接对经办机构发号施令,而只能通过自己派出的代表参与决策。参保人代表的选举或遴选方式由法律规定,外部专家的遴选方式和职责也由法律直接规定。在此基础上,为了防止机构滥权,社会保险基金的财务、投资和管理都应该充分向社会公开,接受公众和政府的监督,以此保障全体参保人的利益,提高管理质量,抵制政府的不当干预。
第五,财政补助应与政府职能保持一致,有理有据。
政府对社会保险的财政投入很多,其性质因政府干预的名目存在差异。在政府组织社会保险事务的情形下,政府一般应承担社会保险运行费用,而不是从社会保险基金中提取管理费;如果政府职能与社会保险分立,当社会保险基金出现支付不能时,财政则应当承担资金周转顺畅的担保责任;对国家主导和推动的转制,如果涉及社会保险问题,财政应承担转制的成本;当政府将弱势群体纳入社会保险时,也应当为这些主体缴纳社会保险费。实际上,这些责任范围不仅可以核算清楚,政府也完全有能力承担。每年政府给予社会保险基金的补贴,本身就蕴含了责任补偿的内容。关键问题是,政府的补贴项目、理由应当明确,让各方清楚自己的责任范围。鉴于社会保险是社会主体自助互助、自我负责的方式,应充分发挥社会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如果角色和职责不清,政府投入越多,公众在风险应对方面对政府的依赖性越强,反而会加重政府的政治责任。
[1] [德]乌里奇·贝克尔(2005).德国社会保险的自治权——理念、组织安排和改革.社会保障研究,1.
[2] [德]汉斯·察赫(2014).福利社会的欧洲设计:察赫社会法文集.刘冬梅、杨一帆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3] 陈新民(2010).德国公法学基础理论(增订新版·下卷).北京:法律出版社.
[4] 刘志强、白之羽(2015).财政部长表示,不能把缺口完全留给公共财政,社会保险要坚持精算平衡.人民日报,2015-03-23.
[5] [美]埃里克.M.佩塔斯尼克(2009).美国预算中的信托基金:联邦信托基金和委托代理政治.郭小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6] 孙迺翊(2008).论社会保险制度之财务运作原则——兼评中央与地方政府关于健保保费补助之争议问题.政大法学评论,2.
[7] 熊 伟、张荣芳(2016).财政补助社会保险的法学透析:以二元分立为视角.法学研究,1.
[8] 张荣芳、黎大有(2014).论我国社会保险人的法律地位.珞珈法学论坛(第十三卷).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9] 张荣芳(2015).基于财务独立的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3.
[10] 张荣芳、熊 伟(2015).全口径预算管理之惑:论社会保险基金的异质性.法律科学,3.
[11] 郑秉文、房连泉(2007).社会保障供款征缴体制国际比较与中国的抉择.公共管理学报,10.
[12] Grayson Clarke(2014).Policy Brief on Budget Management for Social Insurance Funds.中国社会保险学会网站,http://www.zgsbxh.org/contents/46/2188.html.
[13] Franz-Xaver Kaufmann(2006).比较福利国家:国际比较中的德国社会国.施世骏译.台北:巨流图书有限公司.[14] Pierre Koning(2006).On Mixed Systems of Public and Private Administration of Social Insurance.EuropeanJournalofSocialSecurity,8(4).
■责任编辑:李 媛
Re-assessment of China’s Social Insurance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ts Reliance on Public Finance
XiongWei
(Wuhan University)
Social insurance is a mechanism of mutual assistance among the insured based on actuarial balance principle where all the rules concerning revenue and expenditure shall be governed by law. Accordingly it is suitable for social insurance to be legally separated from public finance, thus to prevent it from governmental intervention directly. For this purpose, it is not necessary to include social insurance funds into public budget plans. Instead, they should operate on the basis of self-governance. There is no reason to exclude government from decision-making of social insurance affairs. However, public participation and fiscal transparency are needed simultaneously. While state aids are needed to social insurance, they must be out of specific reasons. Normally, social insurance has to maintain a balanced budget by itself.
social insurance; fiscal reliance; public finance; state regulation
10.14086/j.cnki.wujss.2017.04.005
2016-08-0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5AFX021)
DF4;F840.61;F8
A
1672-7320(2017)04-0036-07
■作者地址:熊 伟,武汉大学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