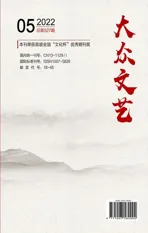《失落》的叙事视角策略探析
2017-01-28西北大学710000
黄 梅 (西北大学 710000)
《失落》的叙事视角策略探析
黄 梅 (西北大学 710000)
印度作家基兰·德赛的长篇小说《失落》中叙事方式传统,在整体上是全知视角,它解构了中心和边缘的对立关系,致力于表达多元并存与融合;而在局部的人物视角上却又体现了多元的难以融合。这两种冲突的观点在隐含作者那里被证明都是真实的,即是说,德赛在这部小说中通过她这传统的叙事方式表达了生活多元的真正所在:融合与冲突对立俱在。
全知视角;人物视角;多元
《失落》是由印度作家基兰·德赛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该书在2006年获得英联邦文学大奖布克奖和美国国家图书评论奖。小说主要以两条明线为发展主线,一方是描写印度本土葛伦堡小镇中的人及其日常生活,其中穿插了大量的回忆与现实,并涉及了本地的暴乱;另一方以贫穷人家的儿子比居到美国谋生的艰难故事为主。两条线最终以比居回到印度小镇在时间与空间上连在一起。由于这部小说在地理上跨越印度、英国与美国,时间上从印度独立前到独立后的80年代,殖民主义、后殖民主义、全球化以及由前者带来的移民身份问题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本篇小说的叙事方式并不复杂,整体上叙述视角与叙述声音一致,即全知视角;在局部片段是隐身叙述+人物视角。这种在传统小说中比较常见而在现代小说中较少用到的叙述方法,在这部小说中没有受到研究者的关注,只是外国研究者有认为小说在叙述中“左转右弯,令人目眩,描写分散而粗略”,批评作者的叙事散漫,国内有研究者认为“散漫叙事”在症候性解读的语境中是作者的叙事策略所在,即在英语叙事中保持个人立场1。可是,本篇论文要探讨的正是由于太常见而被忽视的小说的全知视角及局部的人物视角。
一、整体上的全知视角
关于全知视角,是指作为观察者的全知叙述者处于故事之外,他既说又看,可以从任何角度来观察事件,可以透视任何人物的内心活动,“既在人物之外又在人物之内,知道他们身上所发生的一切但又从不与其中的任何一个人物认同”。热奈特将之描述为“零聚焦”(Narrative Discourse Revisited),徐岱称之为“全聚焦”,申丹认为应名之“全知视角”,因为“我们难以从整体上把全知模式描述为‘全知聚焦’,而把这一模式称为‘全知视角’则问题不大,在西方相关论述中经常出现‘omniscient point of view’这一术语,但尚未见到‘omniscient focalization’这样的用法”。在这里,笔者采用的是申丹的用法。
人们把全知视角也称为上帝视角,因为只有这样一个超越性的存在才能洞悉人生的全貌,因此换一种理解也可以认为“若真从全知即神的角度出发,任何个人其实都不在生活的中心,而任何边缘者也都分毫不少地享有人生的一段旅行2”。在如今大行其道的后殖民语境中,“中心”与“边缘”常被批判为西方对自身与东方之间关系的一种自大定位;而在一个国家内部,发达或首府地区被认为是“中心”,落后地区和偏远地区被认为是“边缘”。正是通过全知的神之视角,德赛对这两种中心与边缘关系进行了消解。
1.异域印度与中心西方
文中写到这些去往西方的印度人,在他们的认知里,中心被描述为拥有财富、有序、理性,但是当他们到了西方之后发现它的破败也无处不在。前往牛津求学的法官杰姆拜伊被惊到了:
在英格兰走过一条条灰暗的街道,四处找房子住,见灰暗的小房子一排排挤在一起,不乏东倒西歪的好似被鼠胶垫给粘住了。他很是吃了一惊,因为这和期许的恢弘气势太不相符了,他可万万没有想到这里也有穷人,也过着毫无美感的生活3。
怀抱着致富梦的比居到了美国只能在餐厅的地下厨房工作,睡在下等街区的某间地下室,它被租给非法移民,街上到处都是流浪汉,冰冻的尿液,成堆的空外卖盒,拉皮条的,贩毒的,抢劫的,以及和他一样过着的卑微生活。
同时这样的一种谈话也随处可见:我们要挺进亚洲,亚洲正在逐渐开放,新的疆域,无数潜在顾客……我们这个国家没戏了,欧洲没戏了,拉丁美洲也差不多了。非洲除了石油,一穷二白;亚洲是下一块开拓地。
亲眼目睹普遍的贫穷和悲哀,是对中心西方固有的认知模式的相对校正。而西方对东方市场的重视可能会使人想起资本主义时代,殖民者从东方掠取资源原材料,又将商品输入东方市场获得巨大利润。但是自80年代以来,印度以及其他亚洲的国家不同程度的开始改革,国内的经济得到发展,在国际上的地位也在不断提升,无条件的商品输入在今天已经不太可能了,那么今天市场饱和的西方寻求亚洲的巨大消费力在某种程度上是对“主导”与“附属”关系的消解。他们需要亚洲,但不能命令亚洲。
2.国家主流与地方发展
小说是以几个廓尔喀青年抢劫法官杰姆拜伊的枪支为开端的,他们是廓尔喀民族解放阵线的成员,这个阵线的游行和活动衍生出了一系列的暴力冲突。廓尔喀人是印度-尼泊尔人,因为印度与尼泊尔接壤,早年就有尼泊尔人越境进入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省生活,由于他们世代繁衍并且非法越境的人数增多,外来人口就对本地人的生存空间造成了挤压。1984年拉吉夫·甘地这个年轻的总理上台开始了较为全面的改革,开放了市场,使得国家整体上获得了发展,但正是这种改革带来的发展将各阶层群众广泛的卷入了市场,由于资源、能力、环境等的问题,贫富不均,地方落后,底层人的生活没有得到改善,这是包括克什米尔、阿萨姆等在内许多邦动乱的主要原因。人民失业或者缺少就业机会、基础教育、卫生保健和其他社会福利问题使人们对政府感到失望,尤其是年轻人,他们产生了一种被国家主流疏远甚至压抑的感觉。
文中的这一群叛乱者,叙述者尤其强调:
人人都看得出来这些叛军还只是孩子,模仿兰博的样子,满脑袋的功夫和空手道的劈砍动作,骑上偷来的摩托车,开着偷来的吉普车,轰鸣着、呼啸着,玩得不亦乐乎。兜里揣着钱和枪,简直生活在电影里。等一切结束,他们的这段经历就不是虚构了,新电影将以它们为蓝本……
叙述者在小说中不厌其烦的重复这群年轻人在模仿电影中的主角,幻想自己正在演戏。这是一个重要的细节,因为电影是一个将故事影像化并通过集中的大荧幕展现给他人的手段,电影中的人和事是被聚焦的,他们被活生生的观看、理解和分析,因此这种幻想将自己被疏离的生活通过电影聚焦的方式进入人们的视野中心,是这群地方上的年轻人试图进入国家主流的愿望,他们渴望被关注,被人理解,渴望获得年轻人应有的发展机会和个体存在的未来性。这场由他们制造的暴乱为他们提供了电影般的聚焦功能,也成功地使叙述者叙述了他们的故事。在这里,暴乱与不平静、地方落后成为主流,国家被隐退到幕后成为背景。
全知视角囊括了跨时空的故事,世间一切的中心该如何确立,边缘又相对谁而言,小说的全知叙述者并不想重新确立一种中心-边缘关系,即东方成为中心,或者地方成为国家的中心,而是力图证明这种关系的彼此相对性、易变性。每个人都处在所谓中心与边缘的不断碰撞中,这样无法由谁来定义什么是中心,而中心的解构也意味着世界发散式的存在,即多元化的存在。这样导致的一种思考就是,印度本身是一个由多民族、多语言、多宗教组成的多元文化融合的国家,而近年来国际上由于人口的流动性增强,包容性的品质倡导全球化的多元融合,鲁西迪就认为流散者不仅失落,同时也创造,不同文化存在不断地分裂交融并组合成新的文化,这是所谓“文化与身份杂交”的良好状态。
可是从一些由印度到西方去谋生的人物身上看,文化融合似乎不怎么应验。
二、局部的人物视角
在小说的某些片段,叙述者选择让人物自己看、想,然后叙述出他们的所见所闻。文中的人物没有一个大人物或者英雄,尤其是到美国去谋生的这些人,都是些生活在卑微处境中的平民。如果说全知视角是上帝般的俯视人间,那人物视角则是从底层仰视着这个世界。罗伯特·J·C·扬有个说法:如果你要学习有关于后殖民的知识,那么你开始的唯一条件是要保证你会仰视而不是俯视这个世界。他认为后殖民是观照底层、少数、边缘人的知识,意味着更真实的状况。这里并非要谈后殖民,而是说这种仰视的人物视角可能会发现一些不同的东西。
比居是法官家里厨子的儿子,父亲对于西方的绝妙想象以及本地的贫穷,促使比居到美国去谋生。在比居工作的甘地咖啡馆里,店主哈利什-哈利白天对美国人笑意逢迎,夜晚醉酒后则对着比居说:
“他们以为我们崇拜他们!”他大笑起来,“一有人来店里我就微笑。”他咧开嘴露出骷髅般的笑容,“‘嗨,好啊您?’其实我只想拧断他们的脖子。我还办不到,没准儿我的儿子能行,这是我最大的希望。”……“看吧,比居,看看这世界是个什么样子。”
在另一间餐厅和比居一起洗盘子的工友阿楚坦说:
“这些白人!妈的!不过这个国家至少比英国强点,”他说,“这里至少还讲究点伪善。他们都觉得自己是好人,你倒能少受点罪。在英国,人们会当众在大街上对你喊:‘滚回老家去!’”在坎特伯雷待了八年的他,每次都喊着骂回去,这骂比居每星期都要听他重复说几遍:“你爹到我的祖国来拿走了的面包,现在轮到我来你的祖国拿回我的面包!”
而比居自己在餐厅打工时见到了许多印度人吃牛排,他总是意味深长的瞪他们一眼,最终比居离开了这家餐厅并一直寻找不吃牛肉的地方。因为比居觉得“人不应该放弃自己的信仰,放弃父母以及祖祖辈辈的信念。不,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这么做。你活着,就必须遵循某些准则。必须寻找你的尊严”。
因为殖民的旧恨和资本全球化时代资本与劳力的不平等交换造成的新仇,因为文化理念的不一样,文化融合在这些人的身上显得异常艰难,因为他们必须首先面对生存,可是又想保持自身的“洁净”,他们没有条件来支撑其所有的愿望与想法。罗伯特·J.C.扬认为“一些后现代主义者曾试图把流浪和移民描述为文化身份最具生产价值的形式,与认为身份源自身体对家庭和土地的附属的观点相反,它强调了身份的创造性作用。这对于四海为家的知识分子也许有好处,但对于有两百五十万阿富汗难民的奎达、贾洛扎和巴基斯坦的其他地方的难民营来说,对于……来说,这种后现代的‘移民’身份又有什么好庆祝的呢?”即所谓身份混杂创造性、文化的多元包容性与这些少数族裔的真实状况之间存在着很深的裂痕。
这样看来,好像叙述者的话语世界与人物视角展现的世界存在冲突,全知叙述者的世界里所谓中心与边缘的文化、认知方式被消解了绝对的对立性,而人物视角的世界里不同种族的文化、世界观和生活方式难以相融,如果一个人要融入另一个社会,他必须改变自己一些或者放弃一些东西,但比居放弃不了,阿楚坦也忘不了。
三、可靠的“多元”
既然叙述者与人物之间存在认知上的冲突,那是否叙述者并非可靠的了?纵然他是全知者。小说的隐含作者——根据布斯对隐含作者的定义:不仅包括所有人物的每一点行动和受难可以推断出的意义,而且还包括它们的道德和情感内容,简言之,它包括对一部完成的艺术整体的直觉理解——在笔者看来,表明了这种文化多样并置的普遍状况。小说中甘地咖啡馆的老板名叫“哈利什-哈利”,他还有两个兄弟“盖瑞什-盖瑞”和“丹苏克-丹尼”,这是些饱含着文化并置意味的名字,他们在多种文化中游移,设法将两者都囊括进来;而诺妮和罗拉她们也存在这样的双重性,内心交战不休。可是在法官的外孙女赛伊和她的数学老师基恩之间的恋情上,他们有一个分手的结局,因为赛伊从小在修道院这个纯西式的环境中被教育长大,而基恩则在纯正的印度环境中长大,从最小的一餐一饭上(赛伊用刀叉吃饭,基恩则急吼吼地用手抓)到庆祝节日(赛伊自然的过圣诞节,基恩则不过)再到冲突爆发(基恩受到廓尔喀民族阵线的影响)骂赛伊是蠢货和模仿者,矛盾与裂痕无处不在。
也就是说,在隐含作者那里,全知叙述者说的都是真的,人物自己看到和感受到的也是真的。今天的多元文化主义者们一直强调不同文化要融合,尊重文化的多样性才能获得共存,流散者的身份也是一个不同文化碰撞建构的存在,可是,难道“融合”与“不融合”的共同存在就不是混杂的状态了吗?马克·柯里就认为“后现代世界总是旧与新的认同过程之间的对话。将身份作为基于籍贯的叙事这种传统身份意识与任何将身份作为不固定的商品附着想象性后现代身份意识4共存于此”。在这部小说里,叙述者与人物共同展现了这种可靠的、真实的多元混杂。那么,因为现在文化融合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赞同它就成为主流了吗?不,在上帝或者生活本身面前,谁都不是主流。
注释:
1.引自蔡隽:“失落”的背后——对基兰·德赛《失落的传承》的症候性解读,载《当代外国文学》,2010年03期。
2.这是作者在论述托比亚斯·斯摩莱特的《汉弗雷·克林克》,小说以一个叙事中最卑微、相对无关紧要的小人物为小说的书名。
3.小说的译文目前有两个版本,这里采用的是韩丽枫译2008年重庆出版社版本.
4.这种观点认为不同文化的符号在超级市场中通过与各种种族的依附关系而组成购物者的身份,好像购物本身就是一个身份建构的过程。大卫·哈维和斯图尔特·霍尔有相关论述。
[1][法]罗兰·巴特.符号学美学·叙事作品结构分析导论[M].董学文,王葵译,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
[2]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3]黄梅.推敲“自我”:小说在18世纪的英国[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4][印]基兰·德赛.失落[M].韩丽枫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
[5][英]罗伯特·J·C.扬.后殖民主义与世界格局[M].容新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
[6][美]韦恩.C.布斯.小说修辞学[M].华明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7][英]马克·柯里.后现代叙事理论[M].宁一中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
黄梅,1994年出生,女,四川省巴中市人,2015级研究生,目前就读于西北大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专业,研究方向主要为印度文学,参加过陕西省外国文学年会,提交论文是关于印度作家阿拉文德·阿迪加的小说《白老虎》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