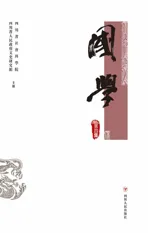張之洞與四川教育
2017-01-26魏紅翎
張之洞(1837~1909)是晚清洋務派中於教育最有作爲者。他早年任四川學政期間,積極籌建尊經書院,大力整頓川省學風,對於四川教育的發展功不可没。可以説在這裏張之洞真正將自己的學術思想、教育理念完整地付諸實現,事無巨細,親力親爲,其投入精力之巨,傾注感情之深,世所共睹。宣統元年(1909)八月,張之洞去世後,四川總督趙爾巽在請求將張之洞的教化之功宣付史館的奏摺中言:“教澤所及,全川化之。迄今學校大興,人材蔚起,文化之程,翹然爲西南各省最。蓋非該大學士陶熔誘掖之力,斷不及此。”[注]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卷首上,中國書店1990年版,第6頁。確非溢美之詞。實際上這也是張氏辭世後,唯一一份單純因其興學之功請求朝廷予以彰顯的奏摺,足見其對四川教育文化影響之深遠。本文將着重論述其在四川興學的舉措。
同治十二年(1873)六月,三十六歲的張之洞奉旨充任四川鄉試副考官。同年奉旨簡放四川學政,至光緒二年(1876)十一月任滿返京,歷時三年。[注]據胡鈞《清張文襄公之洞年譜》卷一,王雲五主編:《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年版,第17、18、44頁。三年裏,張之洞勵精圖治,興利除弊,爲四川的教育發展做出了極大的貢獻。
首先張之洞是一位非常有見識的學官,他對教化之事極爲看重,有一套完整的教育理念。據《大清畿輔先哲傳之張文襄公傳》記載,張之洞年輕時便“究心經世之務,以天下爲己任精研歷代諸儒之學,而以實用爲歸。”[注]《張文襄公全集》卷首下,第15頁。早在同治二年(1863)的《殿試對策》中他便明確提出學問應經世致用,認爲“明體而達用,化民而成俗,此帝王之學所以與小儒異,而不僅訓詁詞章之爲也。”[注]《張文襄公全集》卷二一二,古文一,第742頁。他反復强調讀書的真正目的在於“讀書期於明理,明理歸於致用”[注]《張文襄公全集》卷二〇四,輶軒語一,第611頁。,這種理念伴隨了張之洞一生,任學政便是實施這種理念的絶佳時機,所到之處,他都積極推行自己的主張。入川伊始,他在學政《報到任日期折》中便表示:“(川省)至軍興以還,學額日廣,品行實學尤須極力講求,臣惟有首勵以廉恥,次勉以讀有用之書,至於剔弊摘奸,惟力是視。”[注]苑書義等主編:《張之洞全集》卷一,奏議一.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頁。當時,八股文還非常盛行,書院教育仍然普遍以課時文爲業,張之洞能在此時旗幟鮮明地提出通經致用的主張,强調讀書應有益於現實社會,而不應僅僅追求科舉功名,爲迂腐空洞之學,這是具有相當的現實積極意義和社會價值的,而且因爲張之洞所居地位的不同,其社會影響及實際效果,自然又遠非其他一般文人所能企及。
不僅如此,張之洞還將教育與地方治理、國家興衰之間的關係緊密相聯。他任四川學政,整頓試場積弊時曾言:“士爲民望”,“欲治川省之民,必先治川省之士”。[注]苑書義等主編:《張之洞全集》卷一,奏議一,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8頁。又説:“氣節學術關係國家元氣。”[注]《張文襄公全集》卷二〇,奏議二〇,第404頁。在其《勸學篇》裏也指出:“古來世運之明晦,人才之盛衰,其表在政,其裏在學。”[注]《張文襄公全集》勸學篇序,第544頁。對張之洞的這種觀念,曾在張之洞幕府任職達二十餘年的辜鴻銘有一段精闢評價:“張文襄,儒臣也;曾文正,大臣也,非儒臣也。三公論道,此儒臣事也。計天下之安危,論行政之得失,此大臣事也。國無大臣則無政,國無儒臣則無教。政之有無,關國家之興亡;教之有無,關人類之存滅。且無教之政,終必至於無政也。”[注]辜鴻銘:《張文襄幕府紀聞》,《民國筆記小説大觀》第一輯,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第17頁。張之洞與曾國藩、李鴻章等洋務派大臣最大的區别正在於其絶不“僅計及於政而不計及於教”[注]《張文襄幕府紀聞》,《民國筆記小説大觀》第一輯,第17頁。,而是相當重視文教事業,並且是站在國家治理的高度來關照教育的。他認爲政治、文教乃表裏合一的關係,尤其是在鴉片戰爭之後,清政府內憂外患加劇,作爲一代能臣,張之洞非常强烈地希望通過教育造就可用之才,挽救國家於危亡。
另外,作爲儒臣,張之洞也極其看重文化的傳承、道統的延續。張之洞對於傳統儒學一直充滿着深情,他晚年曾説:“我孔、孟相傳大中至正之聖教,炳然如日月之中天,天理之純,人倫之至,即遠方殊俗亦無有譏議之者。”[注]《張之洞全集》卷二七一,勸學篇二,第9769頁。在當時,他每每以衛道士的身份自居,常常自詡道“惟淡泊所以明志,乃儒臣守道之本,懷而爲學必先治生,亦先儒探源之要論”[注]《張文襄公全集》卷二〇,奏議二〇,第404頁。,“儒之爲道也,平實而拙於勢,懇至而後於機,用中而無獨至,條理明而不省,事志遠而不爲身謀,博愛而不傷,守正而無權,必其並世得位,有數千百儒者與之共修一道,其道乃明,共舉一事,其功乃成。”[注]《張之洞全集》卷二八一,古文二,第10057頁。張之洞重視教育更有保存中國文化、傳承道統的這層良苦用心,其至交陳寶琛所作《張文襄公墓誌銘》對此有透徹解讀:“公之忠規密謨,關係斯文之興壞,非獨天下安危而已。”[注]《張文襄公全集》卷首上,第12頁。四川總督趙爾巽也認爲:“其(張之洞)在粵則設有廣雅書院,在鄂則設有兩湖書院,與蜀中之尊經書院鼎足而三,後先繼美,皆以啓迪新知,保存國粹,爲百年樹人之計正,不徒補苴目前而已。”[注]《張文襄公全集》卷首上,第6頁。
張之洞的這些教育觀念較爲完備成熟,而且在其年輕時便已定型,且堅持終生,之後隨着時代的變化雖然有所發展和豐富,但没有發生實質性的改變。擔任學政期間,張之洞正是秉持着這些理念完成了對四川教育的重建。
其事蹟主要有如下幾方面:
一、奏設尊經書院
張之洞任學政後,同治十三年(1874)四川興文縣在籍侍郎薛焕偕通省薦紳先生十五人,投牒於總督吴棠、學政張之洞,請建書院,張之洞對此大力支持。吴棠是川督,事務繁多,在書院興建上所費心思有限,而書院能在極短的時間建成,於光緒元年(1875)春季投入使用,學政張之洞所作的努力是絶對不能忽視的。
“春,尊經書院成。擇府縣高材生百人,肄業其中。”[注]廖幼平編:《廖季平年譜》,巴蜀書社1985年版,第13頁。張之洞作爲學政,按試省內各地,各州府縣考取的第一二名秀才、貢生可調取入院學習,這百名學子是從當時川省三萬士子中選拔而出的,可謂蜀中翹楚。廖平正是通過這種選拔而被録取的,他於光緒二年(1876)“正月赴成都應科試,以優等食廩餼,調尊經書院肄業。”[注]《廖季平年譜》,第17頁。
張之洞還向吴棠建言聘請江蘇南匯張文虎主持尊經書院,張文虎曾爲此作詩《蜀省新建尊經書院,制軍吴公(棠)奏開書局,以張香濤學使(之洞)言,介李制軍(宗羲)書來欲屬予此席,辭之而副以詩》,雖然此事並未成功,但積極延聘名儒主持書院之心可鑒。
張之洞主張讀書一定要選擇一個適合自己的方向加以研修,而不要一味貪多求全,他告訴尊經學子:“非博不通,非專不精”。[注]張之洞:《四川省城尊經書院記》,沔陽盧氏慎始基齋刻本,《叢書集成續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443~444頁。因而根據師資、經費的情况在書院中設置了經術、辭章兩個專業,分科講授,廖平入書院後,“所課爲經、史、小學、辭章,尤重通經。”[注]《廖季平年譜》,第13頁。這種有所側重的教學方式也爲日後廖平成爲經學大師奠定了基礎。
二、手訂章程及讀書治經之法
尊經書院的學規、制度、章程均爲張之洞親自制定。書院初期的草創人主要是四川總督吴棠、學政張之洞,發起人薛焕。吴和薛功名上都是舉人,因此辦學及學術上的問題,他們都需要向張之洞請教,書院章程實際上也的確是由張之洞負責起草方案,然後與二人商榷定議的。光緒二年(1876)十一月,張之洞學政任滿離蜀前將其寫入《四川省城尊經書院記》以示師生:“建置書院之本義,與學術教條之大端,願得與諸生説之。”[注]《四川省城尊經書院記》,沔陽盧氏慎始基齋刻本,《叢書集成續編》,第443頁。此記被刻在石碑上,立於書院之中,這表明它已然成爲了當時尊經書院奉行的基本規章制度。
該記涵蓋內容甚廣,既有高屋建瓴的方針性、原則性指引,如對書院建院目的的明確闡述,對學子學習方向、志向的諄諄告誡,又有具體而微的實施細則,如招生的辦法、院生學習的方式、考課的內容、言行的要求、師長的職責、書籍的借閲、教職人員的配備等相關工作都給予了詳細規定,對於建立一所具有標杆意義的大型省級書院起到了規範作用。
另外,爲了讓院生擺脱當時較爲盛行的陳腐讀書觀念的束縛,能真正對學習方法、學習要求有正確、清晰、系統的認識和理解,張之洞又撰寫《書目答問》《輶軒語》二書,指示學習路徑。這是張之洞一生之中,唯一一次專門爲書院學生所作學習指導之書,同時也是張氏生平最重要的學術著作。其對尊經書院學生影響立竿見影。據廖宗澤的《六譯先生行述》記載:“先是,文襄未來時,蜀士除時文外,不知讀書,至畢生不見史漢。文襄以紀、阮之學相號召,創立尊經書院,重鋟五經四史,風氣爲之一變。”[注]廖宗澤:《六譯先生行述》,《廖季平年譜》,第85頁。之後二書流播甚廣,影響甚衆。
總之,正是在張之洞的親力親爲之下,這所川省最高書院建立起了基本制度,完成了教職人員配備,端正了學生學習態度和方法,形成了較爲良好的學風。
三、購置圖書,開書局刊行書籍
四川地處西南,交通不便,較爲閉塞。有鑑於此,張之洞積極爲書院購置大量書籍以開啟師生的眼界,曾致信在京的朋友王懿榮請其代爲購書:“代購書籍各種,感甚。惟已有《通鑑紀事本末》,似不宜復出。李燾《通鑑長編》此書擬留以自用,望再尋一書足成之。但須莊雅得體者,不拘何時版本,能兼有陳善進規之義,如《通鑑》等類者尤佳。”[注]《張文襄公全集》卷二一四,書劄一,第789頁。又自捐薪俸從外地購得經史子集各類圖書兩百餘部數千卷贈予書院,“除官發外,使者(張之洞)捐置二百餘部”。[注]《四川省城尊經書院記》。並且在院中建立尊經閣,作藏書之用。張之洞在任期間,先後幫助書院購置書籍多達上萬卷,當時的院生張祥齡在《翰林院庶起士陳君墓誌銘》中記:“(張之洞)購書數萬卷庋於閣,總督吴勤公復助之。”[注]《廖季平年譜》,第16頁。
又安排專人管理書籍,爲圖書整序編目,並制定具體可行的借閲保管制度。從而“穎異之士,如饑渴之得美食,數月文風丕變,遂沛然若决江河。”[注]《廖季平年譜》,第16頁。
張之洞還爲尊經書院擬定有下一步的藏書計劃:“若經費充足,凡切要同看之書,院中須各置十許部,若注疏、經解、正史、《通鑑》《提要》《説文》《玉篇》《廣韻》及考據家最著之書,周秦諸子、大家文集之屬,雖費數千金,其效甚鉅,不足靳也,姑俟異日。正史即坊本亦可。”[注]張之洞:《四川省城尊經書院記》。
張之洞對刻書事業也極爲重視,認爲刻書是“傳先哲之精藴,啟後學之困蒙,亦利濟之先務,積善之雅談。”[注]范希曾編:《書目答問補正》附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342頁。這時雖然還未正式成立尊經書局,但書籍的刻印已經開始了。之前總督吴棠便開有書局,刊行經史小學諸書,張之洞在其基礎上擴大了規模,所刻印書籍流布坊間,數量極大,其中僅是爲尊經書院學生所刻印的教材便已不是小數目。據《四川省城尊經書院記》:“督部吴公初議,入院者人給‘五經’一、《釋文》一、《史記》一、《文選》一、《史記合評》一。如經費能辦,可著爲法。更有《國語》《國策》《兩漢》《三國》《説文》——必須兼《檢字》《歷代帝王年表》《簡明目録》,皆成都有版,價值亦廉,諸生亦須置之。”[注]張之洞:《四川省城尊經書院記》。這些實際爲院生每人需準備的教材,僅就必備的五部書而言:“五經”即《相臺五經》,九十三卷、三十二册,《釋文》即《經典釋文》,三十一卷、十二册,《史記》一百三十卷、二十六册,《文選》即《昭明文選》,六十卷、十二册,《史記合評》六卷,合計三百二十卷。尊經書院首批招生一百名,僅此項便需印製三萬兩千卷,如再加上《國語》等書籍,數量蔚爲可觀。其中《相台五經》《經典釋文》《史記》《昭明文選》均爲尊經書院刻版。
四、調和漢學、宋學之爭
針對清初以來一直持續的漢學、宋學之爭,張之洞竭力加以調和,消弭門户之見所引起的弊端。對這場曠日持久的學術之爭,張之洞有自己清晰的認識:“近代學人,大率兩途,好讀書者宗漢學,講治心者宗宋學。逐本忘源,遂相詬病,大爲惡習。夫聖人之道,讀書治心,誼無偏廢,理取相資。詆娸而求勝,未爲通儒。”[注]《張文襄公全集》卷二〇四,輶軒語一,第608頁。他告知尊經院生:“學術有門徑,學人無黨援。漢學,學也;宋學,亦學也。”兩者各有長短,“漢學豈無所失,然宗之則空疏蔑古之弊除矣。宋學非無所病,然宗之則可以寡過矣。”並且恰如其分地指出兩者各自的優勢:“漢學師法止於實事求是,宋學準繩止於嚴辨義利”,因此彼此爭鬥、互相排斥是没有意義的,張之洞又現身説法表明:“使者於兩家有所慕,而無所黨”,繼而明確告知學子正確的做法是:“惟漢、宋兩家不偏廢,其餘一切學術亦不可廢。”“大要讀書宗漢學,制行宗宋學。”[注]張之洞:《四川省城尊經書院記》。只有發揮兩者各自的優勢,回避各自的不足,取長補短,纔有利於學業的真正進步,學術的長久發展。
張之洞對尊經書院學生的要求正是漢學、宋學並行,但各有側重。讀書强調宜由漢學入門,“讀群書之根柢在通經,讀史之根柢亦在通經,通經之根柢在通小學”,“治經之方,不得不先求諸漢學”[注]張之洞:《四川省城尊經書院記》。,漢學是治學的基礎。而宋學則主要體現在對院生言行舉止的規範上,因爲“宋學貴躬行,不貴虚談,在山長表率之、範圍之,非所能課也”[注]張之洞:《四川省城尊經書院記》。,爲此,張之洞制定了一係列相應規章,要求學生尊敬師長、注重自己品行的培養。
漢學、宋學實爲中國傳統學術發展的兩個階段、兩種路徑,它們各有利弊、各有優劣,清初發生並一直持續到清朝中後期的漢學宋學之爭,本有着特殊的社會時代背景,但一般學人不明就裏,各立門派,互相攻訐,嚴重制約了學術的正常發展。尤其是鴉片戰爭之後,中國面臨着外來文化的强勢挑戰,傳統文化遭遇前所未有的壓力,這時傳統文化必須形成合力應對西方的衝擊,尋找其生存發展之道,紛爭顯然已經非常不合時宜。張之洞正是敏鋭地察覺並順應了這種潮流,自覺地推動着學術力量、學術道路的整合。
五、善於發現、培育人才
張之洞愛才、惜才,所到之處,拜訪名宿,唯恐不及。他發掘人才,獨具慧眼,不拘一格。廖平即爲典型一例。當時廖平前往應試,“初院試題爲《子爲大夫》。先生(廖平)文破題爲三句,已爲閲卷者所棄。學政張之洞檢落卷,見其破題異之。因細加批閲,拔置第一。以後張於先生更屢加拔識,故先生對張知己之感獨深。”[注]《廖季平年譜》,第12頁。廖平因爲文章格式不符合八股文要求,已被淘汰,而張之洞獨賞之,不但將其從落選卷中挑出,且定爲第一名,使其得以後來能順利進入尊經書院學習。《清史稿·張之洞列傳》評曰:“所取士多俊才,遊其門者,皆私自喜得爲學途徑。”[注]《張文襄公全集》卷首上,第13頁。
張之洞對其所發現的人才,非常關愛,“暇日蒞院爲諸生解説”。[注]胡鈞:《清張文襄公之洞年譜》卷一,王雲五主編:《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年版,第42頁。外出按試各地,還會安排尊經書院學生隨行,“召之從行讀書,親與講論,使揅經學”。[注]《張文襄公全集》卷二二五,詩集二,第975頁。光緒二年(1876)張之洞按試眉州嘉定等地,與隨行學生遊覽剛竣工的三蘇祠,作《登眉州三蘇祠雲嶼樓》,喜愛之情溢於言表:“共我登樓有衆賓,毛生楊生詩清新。范生書畫有蘇意,蜀才皆是同鄉人。”[注]《張文襄公全集》卷二二五,詩集二,第975頁。詩中的毛生、楊生、范生分别指仁壽學生毛瀚豐、綿竹學生楊鋭、華陽學生范溶,皆爲尊經書院高材生。
光緒三年(1877)卸任歸京途中,張之洞依然念念不忘這批蜀中才俊,正月初六日於西安致書繼任學政譚宗浚:“蜀才甚勝,一經衡鑒,定入網羅,兹姑就素欣賞者略舉一隅。五少年:楊鋭(綿竹學生。才英邁而品清潔,不染蜀人習氣,穎悟好學,文章雅贍,史事頗熟,於經學小學皆有究心。)、廖登廷(井研學生。天資最高,文筆雄奇拔俗,於經學小學極能揅索,一説即解,實爲僅見,他日必有成就)、張祥齡(漢州學生。敏悟有志,好古不俗,文辭秀髮,獨嗜經學、小學書,篤信古學,不爲俗説所惑)、彭毓嵩(宜賓學生。安雅聰悟,文藻清麗,甚能深索經學小學)、毛瀚豐(仁壽學生。深穩勤學,文筆茂美)。以上五人,皆時文詩賦兼工,皆在書院。美才甚多,好用功者亦不少,但講根柢者,實難其人。此五人未能深造,尚有志耳,已不易矣!此五人皆美質好學,而皆少年,皆有志古學者,實蜀士一時之秀。洞令其結一課,互相砥礪,冀其他日必有成就,幸執事鼓舞而教育之,所成必有可觀。四校官:楊聰(酆都教諭。楊鋭之兄,博雅好學,文章遒麗)、蕭□□(雅安縣教諭。尚屬博洽,好學不倦,讀書細心)、李星根(署茂州訓導。讀書不俗,好古能文,詩才尤佳)、譚焕廷(梁山教諭。風雅善畫,其尊人石門先生是績學)。”[注]《張文襄公全集》卷二一四,書劄一,第792頁。信中不僅一一介紹諸生的特點,而且囑託譚宗浚鼓勵教導之,其情可鑒。
張之洞對自己在蜀網絡人才的效果也感到欣慰,他表示:“通省佳士,豈能蒐拔無遺,就目力所及者言之,大率心賞者,盡在書院。”[注]《張文襄公全集》卷二一四,書劄一,第790頁。時人對此也多有佳評,袁昶《香岩老人六十壽言》稱贊張之洞:“兩爲學政,所至網羅通才宿士教以治經門徑,通知時務。曾文正曾嗟異之。以前輩若洪亮吉之督黔學,朱笥河之視皖學閩學,阮文達之督浙學,無以逾也。”[注]胡鈞:《清張文襄公之洞年譜》卷一,王雲五主編:《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第45頁。
六、多方籌集經費,捐俸助學
辦學需要大量經費,不少書院正是因爲經濟拮据而難以爲繼的。張之洞爲了解决這個難題,在尊經書院成立初期,便積極籌劃經費之事,特“爲文勸當地紳富捐舍學田,優免新生卷費”。[注]胡鈞:《清張文襄公之洞年譜》卷一,王雲五主編:《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第42頁。在他的推動下,籌款取得了顯著的效果,不但保證了書院的正常開支,而且較爲充裕,乃至後來尊經書院改設學堂,所需經費都多取於此。
張之洞不僅勸人助學,自己更是身體力行。先是“以邊省購書不易,捐俸置四部書數千卷”,[注]胡鈞:《清張文襄公之洞年譜》卷一,王雲五主編:《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臺灣商務印書館1978年版,第42頁。所購書籍全部贈送給尊經書院。
然後又裁剪學政的收入。四川學政本爲腴差,爲翰林京官爭相謀取之職,“承平時,京官最稱清苦。翰林仰首望差,閲三年得一試差,可供十年之用;得一學差,儉約者終身用之不盡。”[注]胡思敬:《國聞備乘》卷一,見榮孟源、章伯鋒主編:《近代稗海》第一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13頁。除了薪俸,按試各地,學政都還會收到豐厚的例銀,但張之洞“廉介自矢不許婪索”。[注]許同莘:《張文襄公年譜》卷一,民國二十八年(1939)鉛印本,《晚清名儒年譜》第11册,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年版,第40頁。
他又核定了各項考試録取收取的費用,不准額外索要。在《慎始基齋叢書》中存有張之洞所作《勸置學田》,現已收入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張之洞全集》。文中張之洞説他在四川最爲憂愁的事便是新生覆試需要交納束脩,此項爲川省慣例,且費用不低,“常有一朝進學,毁家太半,負債終身。雖甚孤寒,亦索常例”[注]《張之洞全集》卷二七三,輶軒語二,第9820頁。,而且這又牽扯到考試費用開支,也導致很多試場弊端,因而每到覆試日,他便終日惶惶不安。張之洞認爲唯一解决辦法是:“若得各處紳宦糧民感發,集議公捐一款,置買學田,計其三年收穫之租,足敵兩考束脩之數,(各學豐歉不同,須就本處歷届情况酌議之。)分年勻給,送考時酌加資斧。(如此,則遠郡署事者,即不送考,亦不至困踣難歸。)取進後,限定衹以千錢爲贄,一切書鬥小費、認號、轉案、補廩、幫增、出貢、舉優、報丁、起復、録遺諸費,取辦於此,陋款概爲湔除。士民定議於下,然後禀請長吏,督率行之。(官吏勸捐則滋弊,士民勸籌則可行。)由本州、縣詳明立案、立石,永永不得變革。若不能籌此買田鉅款者,或仿照他項公事之例,酌議定數,按年捐助,或别籌他款取息給用,惟地所宜,不必一轍。”[注]《張之洞全集》卷二七三輶軒語二,第9821頁。在士紳的支持下,張之洞“在四川裁革頂充書吏承差陋規兩萬金”,[注]《張文襄公全集》卷二二八弟子記一,第1021頁。“既裁陋規二萬兩,又核定恩、優、歲貢及録遺諸費不許婪索。”[注]胡鈞:《清張文襄公之洞年譜》卷一,《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第45頁。貧寒學子的負擔也因此减輕了。之前,“川省積習,文武童生取進後,教官書鬥,多方勒索,不遂其意,不送覆試,寒士苦之,公嚴檄督催,苦心曉諭,自是依期送覆,無遲誤者。”[注]胡鈞:《清張文襄公之洞年譜》卷一,《新編中國名人年譜集成》,第41頁。
張之洞以清廉自持,三年學政任滿,離蜀時竟無錢置辦行裝,只得售賣所刻《萬氏拾書經》雕版才得以成行。回京後,生活也非常困窘,過生時甚至需要靠典當纔能勉强支撑,張之洞在懷念亡妻王夫人的詩《永歎》中記:“高車蜀使歸來日,尚藉王家鬥面香。”句下自注:“余還都後窘甚,生日蕭然無辦,夫人典一衣爲置酒。”[注]《張文襄公全集》卷二二五詩集二,中國書店1990年版,第978~979頁。
七、整頓四川科場積弊
欲振興四川文教,除興辦示範性的尊經書院外,還需整肅外部環境,爲師生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這也是張之洞上任之初面臨的主要難題。
張之洞對此是洞若觀火,他一直憂心忡忡:“竊惟考試弊端,各省皆有,然未有如川省今日之甚者。弊竇日巧,盤結日深,幾乎並爲一局,牢不可破。士子以舞弊爲常談,廩保視漁利爲本分,以致寒士短氣,匪徒生心,訟端日多,士習日蔽,於人才、風氣大有關係。”[注]《張之洞全集》卷一奏議一,第3頁。四川當時考場弊端最是嚴重,各種利益糾結、盤根錯節,造成極爲惡劣的社會影響,倘若不嚴加整頓,勢必影響士林風氣,也極不利於尊經書院的健康發展。張之洞經過認真調查、分析,有的放矢地採取了以下措施進行整治:
(一)懲戒鬻販。廩保等人在童試、院試時,杜撰空名,雇傭槍手答卷,然後高價出售。購得者可能又轉賣他人,乃至多次轉手。届時如被發現與原登記人名不符,則謊稱原係過繼云云蒙混過關。張之洞認爲這些人之所以能得逞,主要是四川童試名册上所填寫的考生祖上三代的名字並不一定真實,因而可以任意改變。爲杜絶這類不法行爲,他要求以後必須填寫真實姓名,不可含混,從而使外人難於假借。如發現有姓名含混者,一律不得録送取進。如係販賣者,一旦查實,認真懲辦。
(二)禁止訛詐。訟案中有一類型,看似訴訟,實爲訛詐。這類案件的被告往往爲各級考試被録取者,他們或許有一點身家不清之類的瑕疵。上訴者初則“聯名迭控,勢不兩立”[注]《張之洞全集》卷一奏議一,第4頁。,之後傳訊時卻不到庭或者反悔,甚至銷聲匿跡,這實際是借助訴訟訛詐當事人,欲壑已盈,遂作罷。張之洞於是規定了這類訴訟的上訴人資格、訴訟時效:只允許文武生童呈控,不准放榜多日纔來呈控,也不准院試放榜後再呈控府州縣試前二十名。對於此類訴訟,張之洞還希望上級部門能制定明確條例,以便日後遵照辦理。而當前,他認爲可以主要採取置之不理的態度,如有插訟混擾者,則予治罪。但對於原告所控之事,府州縣暨提調則應認真調查,查明實情,不得包庇回護,否則將受到嚴厲處分。張之洞表示:“公則民服,民服則事少,若地方一味濫收偏袒,而欲禁衆口之沸騰,匪徒之訛詐,不可得也。”[注]《張之洞全集》卷一奏議一,第4頁。
(三)禁止拉搕。拉搕是四川科場尤其令人憂慮的惡習。考生若被疑似有瑕疵,匪徒便會前往勒索,倘不合意就綁架拘押,逼出銀票纔放人,此爲拉搕。而且勒索者往往肆無忌憚,公然敢從轅門內將生童、廩保徑直架走。於是,有瑕疵者爲求自保,也雇傭數十個壯士護衛,前呼後擁而來。因此每至招考日,試院門外,彼此對峙,民衆驚駭。張之洞認爲這必須嚴懲不貸,“親訊拉搕者,飭提調率兵拏辦,每於覆試日放牌後訊之,剖斷公明,或扣除,或坐誣,或勸解,士論翕服,其訟立平,其爭立解,自是學轅無械鬥者。”[注]《張文襄公全集》卷二二八弟子記一,第1021頁。其中松潘武生蘭映太案最爲典型。據記載,蘭生勇健多黨,橫行四川,曾經與駐守省城的旗兵發生爭鬥,結果旗兵大敗,官府對之也束手無策。他在成都參加考試時,將松潘書吏與廩生扣押,松潘考生只有向其交納重金纔能獲取考試資格。同治十三年(1874),張之洞設法調兵擒獲了素行不法的蘭映太,判其永遠監禁,此舉極大震懾了不法之徒,令其收斂不少。但偶爾仍有從寓所綁架生員的案件發生,張之洞主張絶不可寬縱,必須嚴辦,才能遏制此風。
(四)緝拿包攬。在槍替、販賣、詐騙等事件中都有仲介居間包辦,外省稱之爲“槍架”,四川名爲“親家”。仲介來源複雜,有無業遊民、商販、捐官之人等等。這些人平時收養槍手,考試時便鼓惑誘騙他人犯罪,自己從中坐收漁利,還勾結匪徒詐騙謀利。張之洞認爲這類人實爲罪魁禍首,“大抵清試場在幹絶槍架,亦猶治盜賊在於絶窩主,實爲探源之務。”[注]《張之洞全集》卷一奏議一,第5頁。但這種人卻不易緝拿,一是受害人往往在放榜後纔知受騙,難以追查;二是這些人與各衙門相識,耳目甚廣,地方官也常常聽之任之,不加管束;三是此類案件需要槍手、本童、廩保等各方面人證全部齊備,纔能定案,這些人會想方設法拖延、阻撓,最終導致無法立案。科場案發,槍手、本童自會受罰,但這些罪魁卻逍遥法外,實爲不合情理。張之洞上任四川學政後,查訪出其中有名的十多人,登記在册,逐一通緝,使其稍知收斂,但仍有一些新進無名之人繼續爲非作歹。張之洞認爲今後對於包攬舞弊引誘説合者,只要槍手、生童供認確鑿,或者衙門存有案底,那麽不論本案是否完成、人證是否齊全,先懲處包攬引誘説合者,全案再另行詳查。他説:“如此則無所牽制,方能真加懲創。”[注]《張之洞全集》卷一奏議一,第6頁。如果槍手、廩保、本童事發後供出包攬之人,協助抓捕,可以免罪。消滅了包攬,槍替自會消失。
(五)責成廩保。張之洞從屢次辦理科場弊案的經驗總結:廩保對情况最爲熟悉,倘若其能秉持公正,將極大降低弊案的發生。而他們之所以會肆無忌憚,是因爲廩保人選要麽學業優秀,要麽老邁窮困,即便問罪,也往往不宜對其加以重刑,由此得到法外開恩的照顧,不久後猶能請求開復。針對這種現象,張之洞提出在懲處的時候,對於認保廩生舞弊者,先以“濫保”報送上級部門,將其革黜,一旦坐實永遠不准開復。這樣一方面讓廩保有所敬畏,另一方面也解决了官員辦案時的棘手問題,易於推行。
(六)嚴禁滋事。四川武場童生很多,最易生事。嚴重程度超過文場,其藐視法律、蠻橫無禮之處尤甚。張之洞到任後查閲文武童生名册,發現其中一項爲業師。武童的業師即是“教習”,負責平日的操練,考試期間的食宿。童生的所有事情都由教習主使,因此也應責成其加以管束。張之洞責令考試前,教習需率領學生到學政衙門具結,開列所教武童姓名、考試日期,並且經識别查對方可參加考試。如没有教習前來具結的考生,不允許參考。武童如作弊滋事,教習應承擔責任。規定只准填寫本縣武生爲教習,以便約束,其他之人,一概不得填寫。此舉簡單易行,不僅澄清了科場弊端,而且街市也更爲安寧。
(七)杜絶規避。四川文武生總共五萬多,其中不免刁劣生事者。文武生每當犯事將被查辦之時,往往急忙捐置一貢生、監生頭銜,捐局便會來文指此生已結業,生童遂借此逃避追責。張之洞認爲四川捐局太多,各局空白執照亦多,是否有倒填年月的情形,無法查驗,結果導致各級學校衙門不能約束學生。因而要求如是部捐者,收到部文即辦理結業,除此以外,需令生童自行前往學校衙門呈遞執照,得到學臣批准後,纔能辦理畢業。如查出有案在身借此規避或者倒填日期者,將註銷其執照並嚴加追究。張之洞也希望省內各捐局,在文武生報捐時,先行在學政處查明有無事故,再報給上級部門,而且也不要輕易判定其結業。
(八)防止鄉試頂替。四川録遺考試一向有很多代替、假冒者,張之洞表示在最後録取時,確實無法知道考生是否是其本人。他認爲這需要從州縣考試抓起,因爲之前的貢監録科録遺,都在本籍考試,真假易辨,必然是本人前往。那麽,州縣面試卷就可與録科録遺卷核對,以定真僞,之後再層層上報、層層核對,就能查驗是否本人應考,不至於混亂難辨。
張之洞極爲重視科場整肅之事,分别上《川省隨棚録遺片》(光緒元年七月)、《整頓試場積弊折》(光緒二年三月)、《奏請敕議申明嚴飭辦理片》(光緒二年三月)等奏摺,痛陳四川科場弊端範圍之廣、數量之大、危害之重,懇請嚴加辦理,消除惡劣影響,以提振士風。並且他從四川全域治理的高度着眼,在《整頓試場積弊折》中指出:“士爲民望,邊省尤甚。川省人性浮動,獄訟繁多,大凡户業公局唆訟詐財之案,必有文生在內;燒香、結盟、糾衆滋事之案,必有武生在內。激揚之道,固不僅在考試一端,然童試乃士子進身之始,棚場爲萬衆薈萃之時,若此時即專以作奸犯科抗官滋事爲務,通省郡縣相習成風。則異日成名必蹈故轍,愚氓見慣,群思效尤,爲患殆非淺鮮。故欲治川省之民,必先治川省之士。”[注]《張之洞全集》卷一奏議一,第8頁。張之洞認爲生童在考試時舞弊,在試場外又勾結官吏、干擾訴訟,這樣的人今後一旦發達,必定禍患無窮,而且因其社會影響大,其他人群起效仿,造成的危害更加難以估量。因此清理科場積弊、整頓士風是全省治理中的首要切入點,可以起提綱契領的作用,從而事半功倍,“通省士民濯磨振勵,庶幾試事永遠清肅,地方亦少事端,川省幸甚。”[注]《張之洞全集》卷一奏議一,第8頁。
經過幾年嚴格的整治,頗見成效,張之洞學政任滿離蜀時曾感慨:“學政署中,渣穢如山,三年以來,聊效愚翁之移,幸得净盡。”[注]《廖季平年譜》,第18頁。張之洞創辦尊經書院與嚴懲科場弊端,是一枚錢幣的正反兩面,互爲支撑,其出發點和目的是一致的,一方面是爲了政治上實現全省大治,另一方面是爲了文化傳承與振興。政教並舉,相輔相成,是張之洞不同於其他洋務派大臣的重要特點,也是其一生仕途中恪守的爲政之道,其核心正是他一貫宣導的經世致用思想。陳寶琛在爲張之洞所作《墓誌銘》中將這種特色概括爲:“平日論學言政,以法聖崇王爲體,以進夷予霸致國富强爲用。”[注]《張文襄公全集》卷首上.中國書店1990年版,第10頁。
在四川學政任職期間,張之洞殫精竭慮,事必躬親,頗爲辛苦。同治十三年(1874)舊曆除夕,剛上任四個月的張之洞在忠州考棚給友人王懿榮的信中説:在四川“事繁、道遠、弊多”,前往各府州考棚,“山行十餘站,大率荒山絶壁,盤路一綫,險不可言。天氣嚴寒,大雪迷路,不敢投足。舁夫顛踣,從騎隕斃,不知凡幾。此外,水程則處處皆灘,驚心動魄,絶無從容怡曠之地。”而且“生童益多,試事益繁,棚數益多,道遠日促”,因此“終日勞煩,甚於在楚時數倍”,“公事艱難精力日衰,其苦殆有甚於大考者。”[注]張之洞:《張文襄公全集》卷二一四書劄一,中國書店1990年版,第788、789頁。之前同治九年(1870)卸任湖北學政時,張之洞有《送妹亞芬入黔詩》云:“人言爲官樂,哪知爲官苦。我年三十四,白髮已可數。”[注]胡鈞:《清張文襄公之洞年譜》卷一。感嘆其勞累。而在四川張之洞馬不停蹄地按試眉州、嘉定、叙州、瀘州、叙永、重慶、酉陽、忠州、夔州、綏定、順慶、保寧、潼川、龍安、寧遠、雅州、邛州等各地,回成都後又立即主持鄉試録遺等各類考試,三年的春節均在棚場度過,確實公務更爲繁多,辛苦也尤甚。
誠如張之洞自己所言,他在四川是“鞠躬盡瘁”[注]《張文襄公全集》卷二一四書劄一,第788頁。,做了許多實事,尤其是創辦尊經書院,功不可没。光緒二年(1876)十一月離任之際,張之洞對其親力親爲創辦的尊經書院充滿了眷戀,書院學生廖平等送行至新都,在桂湖餞别。到達綿竹,他立即致信繼任學政譚宗浚:“身雖去蜀,獨一尊經書院惓惓不忘,此事建議造端經營規劃,鄙人與焉(根柢淺薄而欲有所建立,誠知其妄)。今日略有規模,未臻堅定,章程學規具在精鑒(章程有稿存案,書院記即學規),斟酌損益,端賴神力。他年院內生徒各讀數百卷書,蜀中通經學古者能得數百人,執事之賜也通省佳士,豈能蒐拔無遺,就目力所及者言之,大率心賞者,盡在書院。”又叮囑其開列院生名單以便考查:“請飭吏將歷年調院者無論正備總開一折,分注籍貫,隨棚驗之(惟涪州陳驤瀚能文通算,因知其處館,未調)。”對於山長人選也挂心不已:“丁稚翁前輩到鎮後必謀山長,或仍舊委員、或定議延聘、或議而未决,敢請馳書相告,幸甚幸甚!”[注]《張文襄公全集》卷二一四書劄一,第790頁。到達西安後又寄書一封告知尊經書院杰出的五少年和四校官情况,拜託譚宗浚教育鼓舞之,稱“所成必有可觀”。[注]《張文襄公全集》卷二一四書劄一,第792頁。應該説,在尊經書院創建的初期,張之洞付出的心血之巨、傾注的感情之深、取得的成績之顯著,無人出其右者。費行簡(沃丘仲子)的《近代名人小傳》對張之洞的評價基本是負面的,但也肯定其在川功績:“川立尊經書院,皆以經術造士。所至恤寒畯,屏饋賄。望冠一時。”[注]沃丘仲子:《近代名人小傳》,中國書店1988年版,第125頁。
張之洞作爲清末一代重臣,一生所成就的大事難以計算,而在其政治生涯中最重要最顯著的一個特點便是政教並舉,所到之處,興教辦學,惠及無數。成都尊經書院便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它爲四川文化教育所帶來的影響恐怕是連張之洞自己都没有預料到的。
書院在很短的時間裏就發展壯大,爲四川文化界帶來了顛覆性的變化。光緒十一年(1885)四川承宣佈政使易佩紳説:“夫文王之化可被江漢,孔子之教豈不能達於巴蜀耶!是以劉氏之興,蜀學比於齊魯國家右文之治超越往古,蜀之文學視各行省未稱極盛。光緒初元,學使張公與督部吴公始立尊經書院,今督部丁公尤加意經營不數年,蜀才蔚起,駸駸乎與兩漢同風矣。”[注]王闓運編:《尊經書院初集》序,尊經書局光緒十一年(1885)刻本,第3頁。四川成綿龍茂兵備道並署四川按察使司按察使王祖源也認爲:“張孝達學使之創建尊經書院也識者謂與詁經學海相頑頡。三年鐙火,成學斐然蜀自漢興,文翁立學,東詣受經,學徒鱗萃,蜀學比於齊魯今之尊經,追隆兩漢鴻生巨儒,接踵而興矣。”[注]王闓運編:《尊經書院初集》序,第5~6頁。二人都將尊經書院於四川的影響與文翁興學相提並論,認爲張之洞創建尊經的貢獻是承繼了西漢文翁的偉業,從而令英才輩出,蜀地文化重獲生機。
書院能在如此短的時間裏取得喜人的成果,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張之洞宣導不課時文,主張應廣泛學習代表中國傳統文化的各種典籍,這無疑將學子從“八股文”的嚴重束縛中解脱出來,極大開闊了他們的視野。這的確是洞察了書院教育的時弊,李國鈞的《中國書院史》明確指出:“清代地方官學的衰敗在於它僅以制藝取士課士,而清代書院的普遍衰敗亦在於它捨去了書院自由講學的傳統,師儒所教率不出‘時文試貼’,書院的掌教已失去了學術帶頭人的作用,一些書院延聘山長更多的是考慮這位山長的時文做得如何,能否使學生多中舉登科甲。”[注]李國鈞:《中國書院史》,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813頁。因此張氏的舉措在今日看來,自然是明智進步之舉。但實際上在當時的情况下,這個政策的推行是有相當的阻力的。因爲科舉考試沿襲已久,成爲衆多讀書人進階的通道,因而也是其一生的夢想所繫,讓其接受不課時文是極爲困難的。
也有人在其他地方曾提出過類似的主張,但收效甚微。如乾隆時期,經學家盧文弨主講南京鍾山書院,便有此號召,然而肄業者數百人只有“一二同志信而從焉”,大多數“漸染俗學已深者,殆終不能變也”[注]盧文弨:《抱經堂文集》卷一八《寄孫楚池師書》,《續修四庫全書》第143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700頁。。同樣,光緒年間,中國首位駐外使節郭嵩燾從歐洲歸來後,意欲在湖南重建湘水校經堂,講求實用之學,孰知招致一片譁然,有人還給郭嵩燾寄來《僞校經堂奇聞》,指責他“不講時文試貼,而講天文算學,其計狡毒”[注]郭嵩燾:《郭嵩燾日記》第三卷,光緒五年(1879)九月初八,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35頁。,純屬漢奸行爲,要士子鼓而攻之。由此可見在當時推行這項教學內容改革難度是非常大的。雖然尊經書院關於這方面的記載並不多,僅在張之洞所作《四川省城尊經書院記》中有專門一項,向學子解釋爲什麽不課時文,希望能消除他們的疑慮。從中我們也可以感知這種抵觸情緒其實在尊經書院也是存在的,但難能可貴的是,張之洞成功化解了這個難題,有力推行了這項正確的决定,從而切實完成了尊經書院這座清末具有改良性質的新書院的歷史定位。
不僅破舊立新,而且張之洞在四川學政任上治理積弊、選拔人才、精心培養,功不可没。他去世後,《諭葬碑文》贊其“萃蜀才歷岷峨而擢秀疇”。《入祀賢良祠論祭文》稱“持尺量才,振文風於巴蜀,歷膺清秩”。[注]《張文襄公全集》卷首上,第3、4頁。四川總督趙爾巽上奏摺請求將張氏在川興學事蹟宣付史館,該摺內容詳實,情真意切,稱贊張之洞四川學政任上成就功不可没,皆爲確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