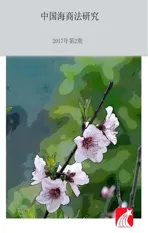船员外派机构法律定位之再考量
2017-01-25王亚男
王亚男
(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辽宁大连 116026)
船员外派机构法律定位之再考量
王亚男
(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辽宁大连 116026)
船员外派机构法律定位之确立是规范船员外派管理,维护外派船员合法权益的重要问题之一。在厘清学界对船员外派机构法律地位所形成的“中介说”“用人主体说”以及“折衷说”三个理论的基础上,分析其不确定性所带来的相应困境及原因。借鉴域外国家的相关立法规范,提出“协商折衷说”理论,确定船员外派机构法律地位要以充分的协商为前提,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员外派管理规定》中规定外派船员获得相应的咨询及建议的权利。
船员外派机构;中介说;用人主体说;协商折衷说
为船员提供对外劳动派遣服务的一个机构,良好的船员外派业务的发展和国际船员劳务市场的开拓有赖于外派船员机构的发展。然而,目前中国相关的法律法规暂未对船员外派机构之法律定位作出明确的界定,这间接地导致船员外派法律关系的复杂化,为损害船员之合法权益带来了新的可能。在这一背景之下,有必要深入剖析船员外派机构的法律定位,对其进行充分的研究。
一、船员外派机构法律定位观点之思辨
(一)学界就船员外派机构法律定位观点之分歧
考量船员外派机构的相应法律定位,首先应该立足于现有的学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分析相应的不足之处,从而为相关的定位思考及法律法规完善建议奠定相应的基础。针对船员外派机构的相应法律定位,学界有以下三种学说。
1.中介说
有学者认为,船员外派机构应该是一种中介机构。所谓中介机构,是指只是为船员和境外船东提供信息,在船员外派法律关系中处于居间人地位的机构。关于居间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简称《合同法》)第424条明确规定,居间人的主要义务是在从事居间活动时,对于有关订立合同的事项,向委托人如实告知*根据《合同法》第424条的规定,居间合同是居间人向委托人报告订立合同的机会或者提供订立合同的媒介服务,委托人支付报酬的合同;这里所说的媒介服务,与外派船员所处的实际情形相类似,故而可以适用相关的法律法规。。赞成中介说的学者认为,船员外派机构本身的媒介作用十分明显,且赋予了外派船员与境外船东订立相关合同的机会,除此之外中国相关的法律法规,如《外派海员类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条例》(简称《船员条例》)等都将船员外派机构界定为提供船员代理服务或者媒介服务的机构*《船员条例》中第44条的规定,船员服务机构为船员用人单位提供船舶配员服务,应当督促船员用人单位与船员依法订立劳动合同。这里体现出的一定的中介性色彩。。据此,认为船员外派机构是一种中介机构不仅符合中国相关立法的要求,同时也符合该机构所发挥的本质性作用,是一种通说性的法律地位。
2.用人主体说
另有学者对中介说提出了质疑,认为船员外派机构本身并不仅仅发挥了中介性质的作用,其程度完全可以达到“参与至船员外派法律关系中的用人单位”之中。[1]据此,船员外派机构可以理解为是一种特殊的用人主体。这是因为:第一,船员外派机构真实地参与到协议以及管理活动中。所谓协议,是船员外派机构与外派船员之间的聘用船员协议,而所谓管理是为用工单位提供符合相关的资质的船员并参与到管理活动中。相比之下,一般的中介性机构难以从事这样复杂的活动;第二,《船员条例》本身的规定。根据《船员条例》第27条的规定:“船员用人单位应当按照劳动合同法律、法规或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加入的有关船员劳动与社会保障国际条约的规定,与船员签订劳动合同”。基于船员外派机构具有用人单位的性质,它与外派船员所签订的是劳动合同,而并非是中介性机构所签订的居间合同。从这一点出发,船员外派机构不应该仅属于中介性机构,而应该是一种用人主体。
3.折衷说
还有学者认为,船员外派机构并不必须只具有一种法律地位,它可以在不同情形下兼有不同的法律地位*两个不同的法律地位之间并不互相矛盾,而是可以兼容。。[2]据此,船员外派机构完全可以被认为是中介服务机构和用人单位机构,只是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应该依据不同的情况适用不同的法律规范,而这些不同法律适用之间并不必然互相排斥,完全可以进行兼容。对于其中一些船员外派机构,如果其确实从事了相应的居间性媒介式活动,那么在调整其相关行为时完全可以依据《合同法》第424条的规定进行。与此同时,如果船员外派机构与外派船员之间建立劳动合同关系,由船员外派机构外派该船员到境外船东的船舶上提供劳务,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完全也可以被视为是一种特殊的用人主体。因此,对船员外派机构法律定位之考量不必拘泥于一种法律地位,而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分类讨论,以适应实务中的相关要求,从而做到灵活地看待船员外派机构的法律地位,避免产生更多的法律问题*参见《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管理办法》第4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船员服务管理规定》第22条。。
(二)就船员外派机构法律定位观点分歧所引发的现实困境
学界对船员外派机构法律定位之观点认识存有诸多不同之处,如何认定这一机构的法律地位在实践中也未形成一致性意见。因而在实践中引发诸多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为船员外派机构获益的非法性提供便捷空间
无论将船员外派机构认定为何种法律地位,有一点可以明确的是:在船员外派过程中,船员外派机构扮演了劳动中介的角色。在这一背景下,船员外派机构既不是劳动力的所有者,也不是船员劳动力的实际所有者,而只是发挥了一种“中间人”的作用,以便可以双向获取两方主体所提供的必要报酬。[3]据此,船员外派机构法律地位之考量的分析就会产生以下两种矛盾式的困境。
第一,认为船员外派机构仅具有一种中介地位,那么作为居间合同一方的主体,其便会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故而产生诸多非法现象。有学者在对相应的案例进行分析的过程中就指出,目前中国的很多船员外派机构为达成交易获得报酬,不惜将不适格的船员外派给境外船东,以获取非法利益*参见王俐君、潘晟、潘弋、屠秀华诉阳春海运有限公司海上人身伤亡损害赔偿案,(2008)沪高民四(海)终字第137号民事判决书。。由于只是单纯作为居间合同一方主体,中介人无需过多顾及外派船员的合法权益,只要符合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协议即可。
第二,船员外派机构不仅被认为具有中介地位,还被视为特殊的用人主体,那么其所承担的义务就远不止其与外派船员所签订相关协议中约定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简称《劳动合同法》)第58条的规定,船员外派机构应当履行用人单位对劳动者的义务,如与外派船员签订劳动合同、按时发放工资、为船员办理社会保险等。据此,一旦船员外派机构被视为是用人单位,那么它就必然受到《劳动合同法》约束,进而承担相应的义务,而这些义务很可能本身在协议中被规避,从而使船员权益无法得到有力的保障。
2.加剧外派船员人身伤亡损害赔偿的困难程度
如果外派船员在外派期间遭受到了人身伤亡等事故,船员外派机构法律定位之分歧同样不利于他们及时获取赔偿,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一方面,如果船员外派机构仅作为一种中介性的机构,双方之间所签订的船员服务协议应被视为是一种民事合同,外派船员和船员外派机构之间的关系也应是横向的。在这样一种关系下,船员外派机构对于船员的人身伤亡事故不负赔偿责任,而只是按照《海外雇主与外派海员合同》的相关规定,承担一定的督促责任。[4]很明显,这种督促责任的履行相比于实际赔偿的履行而言较为简单,实际对外派船员的保护也不充分。
另一方面,如果船员外派机构处于一种特殊用人单位的法律地位,那么双方之间就形成了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的关系。这时当外派船员发生人身伤亡事故时,《劳动合同法》中的相关内容必然就会为外派船员增加一层额外的保护,外派船员在遭遇人身伤亡损害之时能够获偿的概率就会大大增加。
3.模糊外派船员与船员外派机构间的法律关系
船员外派机构法律地位的争议及模糊,直接会影响外派船员与船员外派机构之间法律关系的确定,进而产生模糊化现象。如果船员外派机构扮演的是一种中介性机构的角色,那么船员与船员外派机构之间形成的是居间合同,船员外派机构与境外船东之间形成对外劳务合作关系,真正的劳动关系存在于船员与境外船东之间;如果船员外派机构扮演的是一种特殊的用人主体,那么船员与船员外派机构之间所形成的是一种劳动合同关系,船员外派机构与境外船东之间则是一种劳务合同关系。因此,如果船员外派机构的法律地位不确定,那么外派船员与船员外派机构之间的法律关系就会有多种情况产生,在实践中这种不确定性会使得纠纷发生之时,相关主体的权利义务关系变得更加模糊。
4.无助于推动船员外派机构的进一步发展
船员外派机构法律定位的不确定性使得船员外派机构的地位存在诸多争议,而这种争议反过来会抑制船员外派机构的进一步发展。船员外派机构的发展能够为国家赚取外汇收入,为企业增添效益,而且还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国内船员的就业压力,促进了外派船员较多地区的经济发展。[5]除此之外,船员外派机构的发展还有助于推动中国的对外交流和对外影响,开拓视野,促进中国海运业、航海教育和培训的发展,加快了中国与国际海事通行规则接轨的步伐。然而,这些有益的影响都要依赖于船员外派机构的蓬勃发展,并且这种发展要以纠纷的最小化为必要条件。因此,由于船员外派机构法律地位的争议性,必然会产生这种纠纷,故而船员外派机构的进一步发展便会受到相应的桎梏。
二、对船员外派机构法律定位观点分歧及困境之分析
(一)对船员外派机构法律定位分歧之辨析
通过对船员外派机构法律定位的分歧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现有的研究基本上覆盖了对船员外派机构法律定位认识的可能,对日后认清其法律定位有着积极的意义。同时还缩小了我们认定这一机构之法律定位的视野,在继续研究的进程中具有较强的针对性。然而,现有的研究也存在若干问题。
第一,“中介说”和“用人主体说”两种学说之间的对立性较弱。现有研究中船员外派机构的法律地位形成了“中介说”和“用人主体说”两种情况,并认为这两种地位之间存在一定的区别。然而,这种看法未必正确。笔者认为,两种学说之间并不必然存在对立关系。即使船员外派机构能够被视为一种特殊的用人主体,但最终该机构也并不是为了将船员派遣至自己的工作单位从事工作,而是要将其送至境外船东并服务于他们的船上。从这一点看来,在承认船员外派机构是一种特殊的用人主体时,完全也可以说他们发挥并扮演了“中介”的角色,只是该角色被“用人主体”这一特殊的地位所吸收。
第二,“折衷说”的兼容式表达与中国法律之间存在一定的间隙。由于“中介说”和“用人主体说”之间并不存在完全的对立关系,那么似乎“折衷说”更加符合标准。折衷说的核心在于将船员外派机构既考虑成“中介”,又考虑为“用人主体”,二者并存。然而,笔者认为,尽管“折衷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确立这一观点仍然会产生一定的问题,最重要之处在于“折衷说”本身的提出并没有法律依据作为支撑。与其他两种学说不同的是,现今中国任何一部法律都没有将这种兼容性的法律地位表达至船员外派机构之上,也没有任何一个法律规范明确表示采纳这种双重的法律地位之后,外派船员与船员外派机构之间的权利义务应该如何划分。[6]因此,采纳“折衷说”会面临依据不足,过于理想化的问题。
(二)对船员外派机构定位分歧所引发困境的原因分析
船员外派机构法律定位之所以会存在上述分歧,进而引发现实困境,笔者认为主要是由于以下几点。
1.中国相关法律规定的模糊性
直接调整并规范船员外派机构的法律规范是2011年7月1日开始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员外派管理规定》(简称《外派规定》),其主要实体性规范集中于该规定第三章。针对船员外派机构的法律地位,第24条明确提到了船员外派机构为船员提供外派服务,并且应当保证外派船员与下列单位之一签订有劳动合同:(一)本机构;(二)境外船东;(三)中国的航运公司或者其他相关行业单位。根据该规定,外派船员可以与船员外派机构签订劳动合同,也可以直接跟境外船东签订合同,这种表述本身的意图就在于模糊船员外派机构的法律地位:如果船员与船员外派机构签订劳动合同,那么其主体地位就应该是用人单位,而如果船员外派机构选择了让船员与境外船东签订劳动合同,那么这时其就在扮演中介性机构的角色。因此,《外派规定》本身对于船员外派机构法律地位的确定就采取了一个模糊的、不确定的表达方式,这种模糊的表达方式导致了更为严重的分歧。
2.中国对外派船员保护力度不足
中国对外派船员保护力度的欠缺,是上述困境产生的重要原因。尽管《外派规定》第29条中规定了船员外派机构与外派船员之间在签订协议时必须包括的若干事项,但是在第29条中船员外派机构与外派船员所签订协议的具体要求内容却只有4项。其中,第(一)项与《外派规定》第27条之间属于复制性关系,实际内容几乎相同;第(二)项和第(三)项内容中才明确提到了船员外派机构的相关责任,且责任的内容仅限于管理和服务责任以及紧急情况下的安置责任*参见《外派规定》第29条。。因此,从这一角度出发,外派船员保护力度仍然受到一定的限制。这种限制并不是由于正面保障性条款的缺失,而是在于《外派规定》本身对于船员外派机构责任承担的限制。
3.外派船员维权意识薄弱及处境的艰难性
外派船员维权意识的薄弱和他们本身工作环境的艰难性,一定程度上也为外派船员机构获取非法利益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众所周知,船员是传统的高风险职业,工作强度高、生活环境差、伤病风险大。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和发展,船员与陆上人员的收入差距逐渐缩小。船员收入优势不复存在,船上与陆上的生活条件差距也越来越大。近年来,船舶运营周转加快,靠岸时间越来越短,海上安全和环保的要求进一步提高,船员劳动强度增加。特别是海盗活动猖獗,进一步增加了船员的职业风险。这种处境的艰难性使得船员在发生人身伤亡或权利遭受侵害之时难以及时地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这种情况在外派船员这一主体上体现得更为明显。[7]
三、域外国家对船员外派机构法律定位的认识及理论借鉴
在众多域外国家中,诸多发达国家已经在其相关的法律法规中明确了船员外派机构的法律定位。对这些国家相关立法的研究能够有助于认识中国船员外派机构的法律定位,并在这些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并借鉴相关的经验,以破除所面临的相应困境。
(一)域外国家对船员外派机构的法律定位认识
笔者通过对船员立法相对发达的国家和地区的法规分析发现,域外国家对船员外派机构法律定位的认识比中国现有理论更为丰富,主要集中于以下几点。
1.法律定位限制说
有国家在其相应的立法中表明,无需对外派船员机构进行法律定位,这是因为在这些国家中承担船员劳动中介服务的多为政府部门这种非盈利性机构,船员外派机构本身并没有独立存在或者至少这种存在受到很大程度的限制。例如,《1970年英国商船航运法》第6条就规定:“任何人不得为了报酬而设法为雇佣海员的人寻求海员或为海员去寻找雇主;任何人不应由于为任何他人雇佣了海员而直接或间接地索取或接受任何报酬”。《韩国船员法》也同样认为应该弱化,甚至要限制船员外派机构的作用,尽可能地否定他们的存在。其第101条就规定:“法律不允许任何人根据供应合同提供船员。”综上,英国和韩国两个航运发达国家在其立法中认为,对船员外派机构的法律地位以及所发挥的作用应该予以必要的限制,这种所谓的中介性服务与盈利性服务应该是互斥的,所以在这两国立法看来,承担这种船员劳务中介服务的应该是一种非盈利机构,或者即使是盈利机构,也要对其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严格的限制*关于英国的相关法律法规,参见Rule 3.1 of the P&I Class Rules 2007-2008 of the London Steam-ship Owners’ Mutual Insurance Association Limited。。
2.雇佣主体说
中国台湾地区1991年“船员法”认为,无论与外派船员签订契约的主体为何,都应该称之为“雇佣人雇佣船员”*参见中国台湾地区“船员法”第13条到第17条。。这里的雇佣人,强调是否与外派船员签订了书面的雇佣契约。已经签订了这种契约的,就应该是雇佣人,并且要承担“船员法”第12条至第17条所规定的义务,而不问这种承担义务的主体。根据中国台湾地区1991年“船员法”第13条、第15条和第17条的规定,雇佣人雇佣契约的范本、相关配置标准,乃至工作规则都要报台湾地区“交通部”而定,要受到他们的制约和监督,不得任意而为之。这表明,不管雇佣船员的主体是船员外派机构这样具有模糊性中介色彩的主体,还是直接雇佣船员的船舶所有人,其法律地位都统一为雇佣主体。事实上,中国台湾地区的“船员法”并不像《韩国船员法》和《1970年英国商船航运法》那样规定得较为严格,并对其地位予以根本性的否认,从措辞来看较为缓和。然而,中国台湾地区的“船员法”更希望模糊这一法律地位,将公众的视线从主体的法律地位转移到实质的契约规范内容之上。正因如此,该法才统一使用“雇佣主体”这一措辞。
3.代理责任说
所谓代理责任说,是指间接与船员签订雇佣合同的主体可以是除了雇佣人之外的其他代理人,只是这时雇佣人与代理人之间的责任应需“捆绑”。采纳这一观点的是《希腊海事私法典》,根据该法第53条第1款的规定:“在不违背《海事私法典》第53条的情况下不论雇佣船员的是船员所有人,还是船舶经营人,只要不是永久居住在希腊或为外国航运公司,其代理人为其所有的船舶在希腊与船员签订雇佣合同时,对雇佣合同产生的或基于雇佣合同的责任,应与雇佣人共同承担。在此情况下,代理人应该被认为是雇佣人履行手续的代理人。”[8]根据该法所体现的要求,船员外派机构与境外船舶所有人之间应该形成一种委托代理关系,而与外派船员形成一种中介性的角色和关系。然而,这种中介性关系与中国学界所论述的“中介说”不同的是,船员外派机构作为中介性机构要与境外船东承担一种雇佣合同项下的连带责任,即在该机构未履行雇佣合同项下相应的义务时,其与境外船东之间就赔偿责任问题应承担相应的连带责任。事实上,代理责任说强调船员外派机构名义上扮演“中介性角色”,而实质上却是“连带性角色”。
(二)对域外国家相关立法的分析和借鉴
尽管《外派规定》对船员外派机构的法律地位予以明确,肯定了其扮演中介性的角色,但是这种中介性机构项下的相关规范体系却并未实质上建立起来。因此,需要对域外国家的相关立法进行分析,并去其糟粕而取其精华,择取其中有益的部分对其进行借鉴。笔者认为,三个比较有典型性国家和地区的立法反映出了以下两点共性的内容,值得中国相关立法进行借鉴。
1.船员外派机构不应停留于中介性角色
无论是任何一国的立法,都否认一个单纯的中介性机构的存在,只是在规范之中表达的程度有所差别。英国和韩国直接对这种机构的存在予以否认,而中国台湾地区则对其予以相对淡化。事实上,直接在法律法规之中表达船员外派机构的中介性角色是不被认可的:一方面,这种表述可能会与船员外派机构所额外承担的义务和责任相违背。如果仅将其认定为是一种中介性机构,船员外派机构所承担的其他额外义务和责任就会冲击这一说法,使其法律地位远不限于中介。另一方面,这种中介性的表述可能会引发一定的歧义,在适用法律规范的过程中容易忽略或规避《外派规定》的适用。
2.船员外派机构的法律地位应该通过立法的方式予以明确或推定
除了否定单纯的中介性角色之外,域外国家都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明确了船员外派机构的法律地位。或者即使是这种法律地位不被直接规定,但是通过相关的规定也可以直接推理出它的法律地位。例如,中国台湾地区1991年“船员法”就认为船员外派机构作为与外派船员签订书面契约的主体,应属“雇佣主体”;而英国和韩国的相关法律规范就表达出否认船员外派机构法律地位存在的意思。
四、对中国船员外派机构法律定位的思考与立法完善
通过对中国学界针对船员外派机构法律定位三种学说的探讨和分析,以及对域外国家船员外派机构法律定位的认识,笔者认为,应该从维护船员合法权益的角度出发,结合外派船员的实际情况对中国船员外派机构法律定位加以明确。
(一)中国船员外派机构法律定位的立法表达现状及问题
在《外派规定》之中,唯一涉及到中国船员外派机构法律地位之条文是第24条。除了前文针对该条所分析的船员外派机构的双重法律地位之外,该条事实上还体现了船员外派机构在确定自身法律地位之时的选择权。因此,该法所表达的船员外派机构的法律定位应该与“折衷说”相一致,只是在折衷的过程中,究竟靠向哪一法律地位,其选择权应该交由船员外派机构予以决定,是一种单方意思之下的折衷说。
事实上,根据《外派规定》第24条的规定,船员外派机构可以自行选择让外派船员与本机构,或在本机构确实不方便签订劳动合同时,与境外船东乃至其他相关行业单位签订这一合同。这种规范存在下述两个问题。
第一,船员外派机构可自行选择有利地位而忽略了外派船员之需要。《外派规定》第24条试图通过一种折衷的方式来平衡“中介说”与“特殊劳动主体说”两个理论分支,然而问题在于该条同时表述为“应该由船员外派机构来保证船员与下列单位之一签订劳动合同”。这种表述事实上赋予了船员外派机构一个选择权,其可以根据自身的需要来决定外派船员应该与何种主体签订劳动合同,以使自身的利益得到最大化展现。但是,这一决定是否真的符合外派船员的权益却不得而知。
第二,与域外国家考量船员外派机构法律定位相违背。通过分析域外国家的相关立法可知,这些国家考量船员外派机构法律定位的视角往往十分严格,甚至直接否认。可中国法律规范面对这一问题时,表面上似乎以签订劳动合同的做法为掩盖,但事实上真正与外派船员签订劳动合同的主体是谁仍然要由船员外派机构决定。这种做法与航运发达国家的相关立法不相一致,需要我们至少从条文的设计中予以修正,以维护外派船员的合法权益,避免他们受到船员外派机构所享有的主导性选择权的不正当干扰。
(二)中国船员外派机构法律定位的再考量及相关立法完善
1.船员外派机构法律定位的新思考——协商下的折衷说
基于中国立法的相关问题表现,笔者认为“折衷说”确实是一个符合中国外派船员实践活动的理论学说,只是《外派规定》第24条在赋予船员外派机构这一自主选择权的同时,还应该同时顾及外派船员自身的意志。因此,“协商下的折衷说”是一个更好的出路。所谓“协商下的折衷说”,是指是以顾及外派船员的意志为核心的折衷说,即船员外派机构在保证外派船员与下列单位之一签订劳动合同的同时,还应该与外派船员进行充分的协商,并尊重他们针对这一劳动合同签订主体的选择,而后才能够确定船员外派机构究竟是属于一个中介性机构,还是一个特殊的用人主体。针对这一问题,《外派规定》第24条可以做出如下修改:“海员外派机构为海员提供海员外派服务,应当与外派海员进行充分的协商,在尊重外派海员之意志的基础上保证外派海员与下列单位之一签订有劳动合同:(一)本机构;(二)境外船东;(三)中国的航运公司或者其他相关行业单位。”
将“尊重海员之意志”引入《外派规定》的做法有以下两点好处。
第一,扭转外派船员在签订外派船员劳务合同中的不利局面。如果船员外派机构在促使外派船员与本机构或其他机构签订劳动合同的过程中能够与外派船员进行充分的协商,并且能够尊重外派船员的相关意志,那么此时船员外派机构的法律地位就是一种协商性质的产物。无论是扮演中介性质的机构,还是处于用人单位的法律地位,只要双方主体予以认可,那么此时船员外派机构的法律地位就可以依据《外派规定》进行分类确认,且这种地位对双方当事人都有益处。
第二,有助于解决外派船员所面临的实质性困境。在船员外派机构法律地位的不稳定性所引发的各种问题中,引入“外派海员的意志参与”也能有利于监督船员外派机构的行为,避免其从中谋取不正当利益并进而选择一种合适的法律地位以规避自身的法律责任。这种做法对于外派船员自身合法权益的维护有着积极的作用。
2.其他相关规范的完善性修正
在明确中国船员外派机构法律定位之后,对于《外派规定》的其他相关条文也应作出相应的修正。《外派规定》第24条判定船员外派机构法律地位的连接点在于劳动合同签订的双方主体,然而中国立法如果完全地依靠协商性的规范来确定船员外派机构的法律定位可能会出现协商不成或其他相应的问题。对此,《外派规定》的保护措施在于规范劳动合同中所必须包含的若干事项。笔者认为,中国台湾地区的“船员法”对此可以提供相应的借鉴。该法认为,船员劳动合同的相关内容应该受到相关公权力部门的制约和监督。这一思想可以伴随或跟进于“协商下的折衷说”,无论外派船员机构最后被协商或被确定为何种法律地位,除了《外派规定》对相关劳动合同中所必须包含的若干性事项的要求之外,当外派船员针对劳动合同中的相关内容确有不明或船员对此无法作出正确合理的协商时,有向相关部门进行咨询并获得建议的权利。这一权利能够有助于外派船员进行有效的协商,并作出正确的决定,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具体而言,笔者建议在《外派规定》第五章监督检查部分新增一条置于第40条之前:“外派船员针对劳动合同中的条款有疑问的,可以向有关海事部门或其他劳动性保障机构进行咨询,有关部门收到相应的咨询后,应在合理的期限内给予答复。”
五、结语
船员外派机构的法律地位关系到其与外派船员之间的劳动关系,同时也涉及外派船员相关合法权益的保护问题。《外派规定》应该由原来的以船员外派机构为中心确定其法律地位转向“协商下的折衷说”,通过与外派船员进行充分的协商与沟通,来确定外派船员所签订劳动合同的另一方主体,以切实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同时,《外派规定》也应该肯定并保障外派船员获得相应的咨询和建议的权利,避免他们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1]王亚男,李澜.船员外派法律关系构成之法理分析[J].社会科学辑刊,2011(4):38-40. WANG Ya-nan,LI Lan.Legal analysis of the legal relation of crew assignment[J].Social Science Journal,2011(4):38-40.(in Chinese)
[2]孟红军.海商法修改中关于船员外派的若干法律问题[J].世界海运,2006,29(4):44-46. MENG Hong-jun.Study on seaman output law[J].World Shipping,2006,29(4):44-46.(in Chinese)
[3]蒋跃川.关于我国现行船员劳动中介制度的思考[J].当代法学,2001(6):67-70. JIANG Yue-chuan.Reflections on the system of labor intermediary labor in China[J].Contemporary Law Review,2001(6):67-70.(in Chinese)
[4]张敏.船员人身伤亡工伤赔偿问题研究[J].当代法学,2003(3):145. ZHANG Min.A study on compensation for injury and death of crew[J].Contemporary Law Review,2003(3):145.(in Chinese)
[5]李大泽,于诗卉.船员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的理论解读[J].中国海商法研究,2014,25(1):43-49. LI Da-ze,YU Shi-hui.A theoretical study of seamen’s status in labor relationship and employment relationship[J].Chinese Journal of Maritime Law,2014,25(1):43-49.(in Chinese)
[6]徐俊.从船员劳务合同角度思考《海商法》有关船员规定的修改[J].中国海商法研究,2013,24(3):33-39. XU Jun.Research on modification of theMaritimeCode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in the perspective of service contracts of seaman[J].Chinese Journal of Maritime Law,2013,24(3):33-39.(in Chinese)
[7]周连柏.浅析工伤事故的特点与对策[EB/OL].[2017-05-21].http://www.coscogz.com.cn/gzyy/1gzyy/200501/txt/g1.htm. ZHOU Lian-bo.Analysi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industrial accident[EB/OL].[2017-05-21].http://www.coscogz.com.cn/gzyy/1gzyy/200501/txt/g1.htm.(in Chinese)
[8]韩立新,王秀芬.各国(地区)海商法汇编(下卷)[M].大连:大连海事大学出版社,2003:938. HAN Li-xin,WANG Xiu-fen.Compilation of national (regional) maritime law (Vol. II)[M].Dalian:Dalian Maritime University Press,2003:938.(in Chinese)
Analysisofthelegalstatusofthecrewassignment
WANG Ya-nan
(Law School,Dalian Maritime University,Dalian 116026,China)
The demarcation of the crew assignment is to regulate the current crew export management system and protect the crew’s interests. When learning the three theories which are agent theory, employer theory and agent or employer theory respectively, we should analyze the difficulty in defining the crew assignment and its reason. After learning the regulation from the other countries, the negotiation theory will be promised. It is assumed that sufficient negotiation is required when defining the legal status of the crew assignment institution and that the crew should have the right of consulting and receiving the advice under theProvisions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ontheAdministrationofOverseasAssignmentofSeamen.
crew assignment;agent theory;employer theory;agent or employer theory
2017-05-31
王亚男(1979-),女,黑龙江绥化人,大连海事大学法学院讲师,国际海事法律中心成员,E-mail:applelaw117@163.com。
王亚男.船员外派机构法律定位之再考量[J].中国海商法研究,2017,28(2):12-18
DF961.9
:A
:2096-028X(2017)02-001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