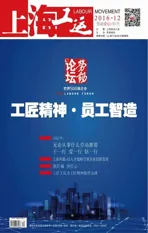呼唤工匠精神正逢其时
——访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施凯
2017-01-17王文怡
文/王文怡
呼唤工匠精神正逢其时
——访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施凯
文/王文怡
工匠精神是专心致志、精益求精、锲而不舍,追求完美与极致的价值观呈现,有普遍意义与时代特色。但它指向的并不全是手工艺人。将匠心与匠人分开来看,或许更能说明问题。施凯认为,“工匠精神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但不是以落后的姿态出现。”
访谈链接

施凯,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长期从事党建、城市法治化建设等多方面研究工作,参与和主持过多项市委重大课题。
记者:在如今现代化进程中,我们为什么要特别强调弘扬工匠精神?
施凯:中国的制造业已经名列世界第一,但是这个第一主要说的是产能和规模,即制造能力,并非品牌与品质,否则中国消费者也不用到日本去买马桶盖了。应该说,这些产品并没有太多的高科技,但人们为什么依然愿意去买外国品牌的东西?原因在于,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的差异。
规模和产量做大了,没换来应该有的经济地位。产能过剩从一定程度上讲也反映了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如今强调发扬工匠精神,并不是要我们回到过去的简单劳动的状态,而是要注重它的专业与恒心、耐得住寂寞与经得起诱惑的内涵。毕竟专注一件事是很枯燥的。
在讨论这一问题时,要持两个角度——精神与产业。工匠精神是提炼出来的。不管什么企业与行业,都应该怀有对产品负责、精益求精与专心致志的职业感。但另一方面,从生产形态来看,工匠确实有它独特的一面,一般以私人定制与小批量生产为特征。但工匠并不完全等同于手工制作,他们也借助机械制造。身怀独特的技艺与技术,这些一般不适用于大批量标准化生产。
进一步说,工匠精神与现代化生产不该割裂开来对待。前者不等于落后产能,它或许最初从作坊间孕育,但这样的精神对任何企业都有指导意义。
将来竞争的也不是产量,而是这个产品的科技或人文含量。我有个朋友去日本拜访了一家生产陶器的铺子,店里的订单来自全世界,但它始终坚守一条,不增加数量,虽然也讲利润但不唯利是图。而在中国,产品好卖,就扩大生产追求批量,然后超出能力范围导致质量陡然下滑的事例太多。我们的一些传统老牌也在扩容中消失不见。但那日本铺子一年只做几样,因为独特精致,虽然量不多,但售价不低,特别受到一些人的青睐。
而在中国,赚一票走人的情况发生不少。在这里,工匠精神里同样蕴含一种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坚守,对社会的责任感。
还有,我们大量的专利发明与实际生产力之间少了那么些环节,这其中需要技术的介入,否则永远停留在纸面上。而工匠精神发扬,也旨在推动创意产业的发展,为此做好技术支撑。
记者:您觉得工匠精神有哪些特点,它的发扬需要怎样的社会文化条件?
施凯:工匠精神,一是指心无旁骛,专心做一件事。我们与国外对于企业大与小的理解不同。国外的企业家专注于一两件力所能及的事,通过做精做优,来扩大市场份额,大企业就是这样来的。而中国的企业喜欢大而全,无法做到专一,很难做到精益求精。
二是对待工作要有足够的耐心与恒心,要忍得住寂寞。比如德国科隆大教堂,造了几百年,不是因为没有财力、人力与物力,大部分原因是在于建造者一丝不苟的精神。
一是积极引进专业投后管理人才,设立独立、专业化的投后管理团队,负责引导基金的投后管理工作。二是建立健全信息监测和信息披露制度,采取信息化管理模式,动态跟踪子基金投资运作情况,强化子基金信息披露,实现全要素、全过程、全流程化管理。三是充分挖掘整合政府、合作机构等各方资源,积极搭建项目库、机构库、专家库,为被投企业在人力资源、运营管理、战略规划、技术研发、市场营销、资本运作、产业资源网络等方面提供有力支持。
另一方面,社会条件与工匠精神能否发扬相关。比如劳动力的价值是不是能得到社会的承认,特别是一些有技术含量的劳动?在日本和德国这些国家,劳动权益保障很充分,真正工匠式的人物,他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准不低。但在中国,技术型劳动虽然比体力劳动要好,但它的社会地位和价值体现得并不充分。
在过去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中国工匠有不错的社会地位,比如八级钳工,当年收入比一个大学教授还高。但现在,这样的岗位是不是还能获得以前的社会认同?
文化观念与风俗也是一个因素。比如日本的家族企业,他的长子不能自由选择其他职业,只能继承父辈的产业,所以文化得以传承。
其实,工匠精神是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其中也有历史的轮回。最早的时候,没有现代化制造业,大家都是工匠;后来因为蒸汽机的发明,社会化大生产建立,当年所谓的工匠变成了作坊里的手艺人。
如今,工匠精神又进入了人们的视野,但绝不是以落后的面貌出现。
记者:我们可以从哪些方面入手呼唤工匠精神,让它成为时代风尚?
施凯:第一,完善相关的制度与政策。保护那些历史品牌与商标,比如一些祖传下来的配方与工艺没有知识产权与专利认证,仿冒抄袭的太多。
事实上相关立法是有,但为什么效果不好?优秀的历史品牌,它的生产时间长,消耗的人才成本高,如果卖出去的产品与背后的劳动得不到社会认可,那么利润持续低迷,行业与产业无法长久生存。这样来看,即便立法,也无法挽救。到最后,还是要通过市场来解决。不像一些遗迹或者文物,可以只依靠公共财政支持来保护,现在说的是生产活动。对于这些老品牌的工匠而言,先要满足他们生存需要,然后是对职业声望与社会地位的需求。但等到整个社会认可需要一个长时间过程。所以在这之前政策就要介入。
第二,收入分配制度要体现工匠的劳动价值。精益求精专注于一件事,在其中倾注劳动力的周期长,那些价值如何体现?我们往往认为工匠劳动的知识含量不多,只是一个习惯动作,但养成过程实际上也是一种劳动创作,它能不能得到社会尊重?
第三,工匠手艺人要得到应有的职业声望。比如瑞士钟表,严格来说它用现代化工业生产也可以,但社会对工匠的劳动十分尊重,我们这里是不是有这样的条件?
另外,现代化的大生产与作坊式个性化生产不一样,前者是协作生产,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连接大多是依靠产销上下游的利益关系。但那些在工匠精神指导下的私人定制或者个性化生产,往往是独立的,一般形态以小微企业为多,不会是几万人的大工厂。这时对他们的权利保护就需要行业协会发挥作用。
第四,职业教育在我们国家一定要大踏步发展,包括教育结构的调整。
我们现在是学历教育,并不是技能教育。但国外从应用的角度更强调技能教育,特别是德国。现在国内的价值观里觉得考大学走学历教育就高人一等,而接受技能教育的人没有前途。我们不应当否定哪方面,要做的是打通技能教育与学历教育这两者。比如,读完职业教育的毕业生同样可以凭借这份学历去考相对应的本科院校;同样,学历教育之后,毕业学生要从事一门非常专业的工作的话,也要补足有关职业教育的经历。不要把界线分得太清楚,这样的办法可能有利于工匠精神的普及。
现在大学生进入企业以后,许多人不适应,还要重返培训班学技能。一些银行或者跨国公司,在员工入职后对他们进行起码半年的专业培训,因为大学里学的是理论。但这样的培训主要由用人单位承担。
比如在一些国家,像社会工作者是一个专业技能岗位,应征者在本科毕业后要继续读社会工作者的专业,目的是掌握技能,不然没有录用的资格。这样的情况在中国也开始兴起,但没有完全定型,也不普遍。
记者:工匠精神未来会更加有力、持续弘扬吗?
施凯:我对此持乐观态度。随着我们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有着大量个体劳动或工匠式劳动的行业、产业会越来越得到社会尊重。因为人们更追求个性,消费趋势已然改变。但所谓的个性化需求几乎是不能批量生产的,它要手工制作。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与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都有助于推动带有工匠精神的行业或产业发展。
还有,社会文明程度在提高,对于文化方面的追求也在剧增。沉淀在产品中曾被忽视的文化因素越发受重视,人们会为情怀埋单。
市场有了细分,一方面是高度科技化与信息化的产品需求,一方面是个性化的消费。中国式产能过剩是一种相对的结构性过剩,不是不需要。如今一些消费者从实物消费转移到文化消费,但供应方还未准备好。
应当说,如今全社会弘扬工匠精神正逢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