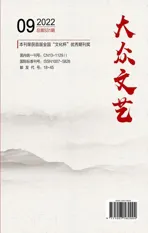“质物本心”
——本人陶艺创作的三个阶段
2017-01-09湖北美术学院430060
张 春 (湖北美术学院 430060)
“质物本心”
——本人陶艺创作的三个阶段
张 春 (湖北美术学院 430060)
“质物”是物质的本源,“本心”是我创作的初心。本文主要围绕“物质”之本源,“我心”之初衷为话题展开自己十年陶瓷创作之路中对现代陶艺创作的理解。也希望通过对自我创作的梳理,总结并归纳出自我创作的方法论,以此继续探寻未来陶艺创作之路的可能性。
物 现代陶艺;创作方法论
20世纪80年代,现代陶艺在中国刚刚萌芽,之后曾有一段相当长的高速发展时期,而在近几年学院背景下的现代陶艺创作开始出现不同的发展方向,一部分创作者开始走向手工艺化,从原本的先锋性慢慢蜕变成大众更能接受的审美倾向;另一方面的创作者越来越注重个人与时代性的表达,用陶瓷创作变成其中但不唯一的表达方式。
面对历史和当下的陶瓷艺术发展现状,回顾本人十年的陶瓷创作经验,发现自身对个人意识的处理与实验性的创作一直贯穿在我的创作之中。本文也是希望通过对自我创作的总结与归纳,寻找到个人陶艺创作的语言与规律,并以此探讨未来创作的可能性。
总的来讲,我的创作思路有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器皿去功能化,追求形式语言的偶发性。其作品以手工成型为主,追求与自然协作。代表作品《皮囊壶》系列等。
第二阶段,从对历史文本的热衷,如魏晋书法和明式家具的审美体验,到人与自我生活空间之间的关注,在矛盾中追求和谐。代表作品《瓷书》系列等。
第三阶段,把人与物的关系进行拓展,回归到“物”的本质,将个人体悟提炼并强调作品体现的观念性。手法上开始试验泥土的“可复印性”。代表作品《自述》《以死印生》等。

图一 皮囊壶1

图二 皮囊壶2
文中所指的“物”大体上可归纳为“自然之物”“历史文本之物”“艺术思维之物”暗合我创作中体现的偶发性、和谐性与观念性之特性。
一
《皮囊壶1》系列如图一,创作于2010年,这是我就读中国美术学院硕士研究生时期的早期作品。在这件作品中,“壶“的功能被关注到最小,其形态也被置换成纯粹的雕塑语言。当创作这件“物”(“自然之物”)时,可以说我已经接受了来自中国美术学院最优质的陶瓷材料训练,这个阶段我非常关注泥巴本身形式语言的产生的多种可能性,利用黑陶“致柔致硬”的特性,有意将偶发状态下产生的质感与记忆一一保留:泥土在湿润状态下柔软且极赋可塑性,而撕裂之后类似疤痕的质感又不禁让人联想起人类身体被伤害后的记忆,但这种记忆的被唤醒是潜在的,更多的是泥巴本身带来的,而非意识的充分发挥。

图三 瓷书
同系列的《皮囊壶2》如图二,在空间形态的处理上,从积蓄膨胀的外形转化为内敛的收缩状态,我利用钢筋将其架空、悬挂,这改变了传统壶的放置方式。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件作品与其最初的形态来源——“蒙古皮囊壶”驰骋沙场的气质更为吻合,某种程度也赋予了这个器物一定的动物性与原始性。
在这个系列中,泥土的偶发效果是我刻意表现的,在看似宛若天成的自然肌理背后其实是我对泥性的有意经营。这个阶段,我和泥巴的关系是若即若离的,一方面放任泥土在造型过程中产生的自然质感,另一方面又紧紧控制这种质感的限度与范围。在这个系列里,泥巴是自然、柔软的,而我的情绪与意识呈现的是一种含蓄,内缩的状态,这种状态更多的是泥巴直接带给我的感受,我的意识其实是伴随泥巴的周折而周折的。
也就是说这个阶段的创作是材料先制作,意识后产生的过程。泥土的偶发是顺和自然的发展而展开的,是呈现泥土自然属性的最好的体现。
而我这阶段的作品似乎更符合和自然合作的概念,这里的“物”是比较单纯的“自然植物”
二
《瓷书》系列如图三作品是我对“物”(“历史文本之物”)的语言的另一种尝试。这是对魏晋书法用笔和明式家具的审美有感而作。在气度上,我试图寻找书法的运笔走势,而在细节的推敲上,又将在明式家具上所感受到的雅致审美、高格调体验移植入作品之中。
《瓷书》系列作品是我将瓷与木的结合首次尝试。瓷与木结合在材料上是一种冒险,这是硬与软的冲撞,冷与暖的交织。但我试图营造出一种视觉上的和谐。在这种和谐中,“保护与抗争”“承载与依附”的悖论情绪一直伴随我创作到最后。

图四 自述

图五 以死印生
对矛盾的事物进行联系,我在第一阶段的创作之前就十分感兴趣。中国古典美学里提到,对常规事物的“反常”理解(即称之为“反常合道”)在表面上是对现事物的扭曲,但却能形成艺术中的新奇效果,但“反常”又必须“合道”,虽意表之外却在情理之中,即生活常理合乎艺术之道。此处的矛盾最后都将化为和谐之力量。
因为有矛盾因素的存在,所以在手法和视觉上我尽可能处理的单纯,和谐:铜红釉和米黄色柏木在色彩上互补,犹如层层青峦。诗意缠绵的瓷和冷静平阔的木形成对比,整个作品体现出一种平和收敛又包容互斥的能量。
而这种冷静表达的背后,支持我的作品完成的最重要的恰恰是对和谐的表达,虽然和谐的同时存在着矛盾与反对,材料的反对,色彩的反对,但我还是试图在反对中寻找和谐,寻找其可以共存的元素。
三
在《皮囊壶》《瓷书》系列作品中,我非常拒绝生涩的表达“观念”的形式,取而代之的是用接近手工艺的处理手法来创作作这些作品。在《瓷书》之后我又很长一段时间沉寂与思考:如果我的《瓷书》继续做下去,文本是否可以继续往前发展,或者瓷书的未来会不会变成只是有简单意义的抽象雕塑?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需要我回到材料的本质来考虑。这种本质不仅仅是对材料本身特点的探寻,也是对背后的文化意义的探寻。
而所谓的文化意义应该是对生活、对文化、对社会的一种个人体悟。《自述》《以死印生》等系列作品就是在这样的思考下产生的,一种来自个人化、观念化的“物”(“艺术思维之物”)的面貌将日渐清晰。
与在《瓷书》系列中瓷与木结合所传达的是“和谐”不同,从《自述》《以死印生》开始,我重新思考了瓷与木的关系——泥土的可复印性——泥土的物理特性之一。复制是为了还原与记忆。出于偶然的生活体验,我对老旧的木制家具产生兴趣,使得我的关注点从历史文本中转移至寻常生活,我想,这恰恰是艺术的本源之地。
在《自述》如图四这件作品中,我将老家具所有突出的边角,用泥土包裹,每块泥土都形成内方外圆的两个形态:内形是家具的结构与纹路,外形是包裹的软体形态。随着泥土干燥、开裂、瓦解,最后我将脱落下来的瓷泥坯置入高温窑炉将之瓷化。在展示时,瓷片被工整的安置在展厅,形成零件集合的场域。这些白色或黑色的瓷片,看上去似乎是物体的皮屑,又有建筑或者工业零件的错感,同时又有很强的书写感。好像一篇生活、环境、亦或是本人“自述”的一种物化方式。
《自述》系列的开始使得我重新考虑我的两种创作材料:木与瓷。不同于《瓷书》中比较简单的将两个材料进行“加法”,《自述》更多的是考虑“减法”,木与瓷的联系更像是一种概念上与空间上的关联。
与此同时,树木的新芽,树皮的脱落,再一次使我体会到了自然的生死合一。我重新思考:木的本来,木与瓷再次结合的可能性。树皮剥离了树木,剥离了时间、剥离了生命,成为了时间与生命的碎片。《以死印生》系列如图五就是在这样的思考下产生的,我认为我所做的就是将这些碎片以一种原始的方式储存。
我将捡来的或大或小几十块树皮一层层地涂上瓷泥浆,累似漆器里脱胎的手法,只是我木头部分我做了保留。最后将之置入窑炉中高温烧制。此时,泥浆化为瓷质而树皮则化为草木灰釉,最终达到瓷(泥浆)与木(树皮)的完全合一。
在我看来,树皮是树死亡的痕迹,正如死皮是人类细胞死亡的证据,记录树皮剥离的状态也是在记录这个生命曾经活着的记忆碎片。记录这样的死也是在回忆这样曾经的生。在创作《以死印生》这件作品,与其说这是创作,不如说这更像是一种对转瞬即逝的祭奠。也许,更难能可贵的,这是“我做为我”对外界事物的全新认知,也是“我”重新发现“我的初心”的一种方式。
而此时对于陶瓷这种材料我有了和之前《皮囊壶》不一样的认识。最初的《皮囊壶》系列是对陶瓷材料最直接的反映,陶瓷在制作过程中的偶发性与空间感是吸引我创作的最大动力。《瓷书》系列中体现的理性中的反作用力是体现和谐的材质之美的最大体现,《自述》开始我慢慢体会陶瓷作为创作材料的的社会层面的意义,第三阶段的《以死印生》是我对人与自然作为生命较深层面的理解。
四
自从2005年第一次接触陶瓷,无论是自然偶发的启示还是历史文本的引导,最终到艺术思维的体悟,给我的最大影响的是这些思维过程给予丰富的感官,心理体验。我个人认为文中的三个阶段即:自然之物,历史文本之物,艺术思维之物内在还是一个递进体悟的过程。但无论怎么样每个阶段都有其自身的特点和经历,而艺术思维的快乐给我感情、认知、生命所带来的微妙变化和碰撞是当下的,我认为对陶瓷材料进行创作,是一个越来越走向思维解放的过程,也是一个在艺术挑战、人生态度上越来越勇敢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