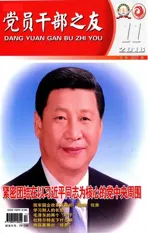学者杨敬年:超越生命长度的力量
2016-11-19王京雪
□ 王京雪
学者杨敬年:超越生命长度的力量
□ 王京雪

2016年9月4日上午11时52分,著名经济学家、教育家、翻译家、南开大学教授杨敬年在天津逝世,享年108岁。不久前,他就读过的牛津大学圣体学院授予其杰出院友的最高级别头衔——“荣誉院士”称号。
37岁留学,86岁退休,88岁写完20多万字的《人性谈》,90岁翻译74万字的亚当·斯密《国富论》,100岁出版27万字的自传《期颐述怀》……一生中命运跌宕起伏,他是流传在几代南开人中的传说。他的个人事迹被收录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澳洲和远东名人录》《21世纪2000个杰出的知识分子》以及美国马奎斯世界名人传记中心《世界名人录》《亚洲名人录》。
“我走的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道路”
1908年,杨敬年生于湖南汨罗。在他出生一周前,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离世。
“我度过了20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20世纪是个不平凡的世纪。”杨敬年说。作为学者,那是最好和最坏的时代。人类以往几代人的遭遇都被紧凑压缩进一代人的命运。新旧交替、中西碰撞,种种翻天覆地的变迁……对于一个家境贫寒、只能找免费学校读,又“没有其他兴趣,棋都不会下,只想求学”的年轻人来说,他的求学之路注定是多舛的。
1927年,19岁的杨敬年考入黄埔军校长沙分校。数月后,“马日事变”爆发,国民党长沙驻军许克祥宣布反共,正醉心于共产主义、准备加入共青团的杨敬年愤而离校。
在贫困中为生计奔走数年,1932年,为免费读书,他考上国民党培养县长的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行政系,毕业后分配在江苏省民政厅,杨敬年没去。1936年,28岁的杨敬年考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成为民国四大经济学家里的两位——何廉、方显廷的得意门生。他打算读完研究生就去考庚款留学,不料入学不足一年,“七七事变”爆发,他不得不中断学业,跟着老师们在国民政府工作了七年,一直做到财政部秘书,相当于现在的司局长。
恩师何廉劝他放弃留学:“敬年,你年纪大了,劝你不必考留学了。如果你想搞银行,我介绍你给周作民;如果你想搞政治,我介绍你给陈辞修。”但他既不想搞银行,也无意搞政治。
1945年,已经37岁的杨敬年从孟买坐上去伦敦的轮船,他考取第八期庚款留英,成为牛津大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专业的新生。
60年后,当杨敬年的学生孟宪刚想要写写自己的老师,他发觉人们对杨敬年的关注多聚焦于他跟命运的搏斗,忽视了他作为学者,一生为求知和自我完善所付出的不屈不挠的努力,“这是他‘夕阳红’的真正原因和内容所在,是他的‘大故事’”。
那是一种“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追求。“我走的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的道路。支配我的唯一动机就是充分发挥自己的天赋和聪明才智。”杨敬年说。
他认为人生就是要追求更多的知识和更大的力量,即使危及生命、牺牲快乐也在所不惜。人类的进化就在于这种追求,它没有止境,“总会有些什么东西,值得为它活着”。
1948年,杨敬年在50%的淘汰率下拿到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研究政府分权问题的论文被认为“对知识有原创性的贡献并适于出版”。同年10月,他放弃去美国工作的机会,应时任南开大学校长何廉的邀约回到南开。当时,天津解放在即,何廉很快就远赴美国。临走前,他给杨敬年留下些钱,说:“你还年轻,要好自为之。”杨敬年的出国护照还在手中,完全可以“说走就走”,但他心中窃喜:“有所作为的时代终于来到了。”
这一年,杨敬年40岁。
“逆境可以予人一种锻炼,况且有些道德价值,非在逆境中不能实现”
1949年,杨敬年主持创办了南开大学财政系,成为该系首位系主任。他觉得,施展才华的时候终于到来了。
可是,谁能想到,迎接杨敬年的,却是长达22年的多舛之途。
1957年,49岁的杨敬年被划为“右派分子”,继而是“历史反革命罪”“牛鬼蛇神”“专政对象”……1974年,他的妻子因脑溢血瘫痪,自此卧床。1976年,他唯一的儿子又因急病离世。到1979年,杨敬年获得平反,重新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大学教授,能名正言顺地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时,他已经71岁。
“能受天磨真铁汉”,杨敬年后来时常提起这句他的同乡左宗棠说过的话。这辈子,他挺过了命运的数番折磨,不是通过高举拳头,而是凭借一种强大的消化力,将苦难咀嚼。
也曾有悲观的念头在他脑海中摇摆,他说那感觉像独行于沙漠,面前不外两条路:要死还是活。他背诵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觉得这么死“若九牛之一毛,与蝼蚁何异”?他靠毛泽东的话恢复心理平衡,“既来之,则安之,自己完全不着急,让体内慢慢生长抵抗力和它做斗争,直至最后战而胜之,这是我对待慢性病的方法”,他把眼前的遭遇也当成一场慢性病。他甚至觉得这20多年的苦难对自己不完全是坏事,因为“逆境可以予人一种锻炼,况且有些道德价值,非在逆境中不能实现”。
在被迫离开讲台的22年里,他做尽了所能做到的一切跟学术相关的事,包括翻译7部经济学著作,校审、定稿180万字的联合国文件翻译。所有这些几乎都不能署名,甚至常常毫无报酬,“无所谓,只要能够工作”。
学生张俊山记得,“文革”后,杨敬年自告奋勇为经济系77级学生开设专业英语课。结课时,他在黑板上写下这样一句话:“The drop hollows the stone,not by its force,but by the frequency of its fall。”意思是,滴水不已,阶石为穿。
这是一种信念。
“一个人的浮沉荣辱和成败得失,在宇宙间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
平反后,年过70的杨敬年决定要再工作20年。
他给学生和青年教师讲专业英语,直到86岁退休;又在国内率先开设发展经济学。当时没有现成教材,杨敬年就一边授课,一边编写教材。历时5年,他编写的54万字的《西方发展经济学概论》终于出版,并获得教育部优秀教材奖。同时,他还编译出版了61万字的《西方发展经济学文献选读》,入选的60篇文章,都由杨敬年“自行翻译”。在这过程中,杨敬年先后培养了20名硕士生。
1983年,我国首招博士研究生,75岁的杨敬年因超龄没有评上。有人为他鸣不平,但他觉得“一个人的浮沉荣辱和成败得失,在宇宙间是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
80岁时,杨敬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有人说这是作秀,他回答“你不了解我”。
“杨先生既非求名,也不求利。他从旧时代过来,受儒家影响较深,他有积极入世的人生观,总是希望以一种积极的心态投入社会做事情。不了解他的人生观则无法理解他的选择。”杨敬年的忘年交、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副教授关永强说。
1998年,还在大学二年级的关永强听了杨敬年的一场讲座。让他印象最深的,是两小时中90岁的杨敬年始终站着,“这是一种老师对学生的尊重”。2004年,为了解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历史,关永强多次拜访杨敬年,“每一回,他都送我们到楼梯口,一直站在那里看我们走下去。那时他都96岁了,而我们只是很普通的学生”。
对于这些,杨敬年的“老门生”们早有感触。南开77级经济系的学生曾在一起交流,许多人都觉得杨敬年对他们十分照顾。现居美国的邹玲,当年因为跟不上专业英语的进度,到杨敬年家中辞课,惊讶地发现70多岁的老师正在学法语,每周两次课,每天背单词。“难道你会输给我这70多岁的老人吗?”杨敬年问,“以后有什么问题,欢迎你来我家,我会给你解答。”
“杨先生70多岁学高等数学时,对我讲的那句‘只要开始,就永远不晚’,不仅是我的,而且已经成为我儿子的座右铭了。”学生赵津说。
晚年的杨敬年一直笔耕不辍,88岁时写完20多万字的《人性谈》,90岁时翻译了74万字的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当时,陕西人民出版社策划出版“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十本书”,其中经济学方面约请杨敬年翻译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杨敬年虽然觉得任务很艰巨,但自认“余勇可贾”,于是“毅然答应”。此后,他每天凌晨3点起床,翻译到7点,得3000字译文。上午休息锻炼身体,下午校对。历时11个月,终于完成书稿,后来又陆续补充了6万字的索引。100岁时,他又出版了27万字的自传《期颐述怀》,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忠实地叙述了自己的百年经历,以生命的体悟启迪后来人。
直到108岁高龄,杨敬年每天早起依然要背几首古诗词,他最爱杜甫,尤爱《秋兴八首》。每天晚上,他坚持听新闻,从《共同关注》到《新闻联播》。若有晚辈来看望,他会与之讨论最近发生的新鲜事。在被问及思考最多的问题时,杨敬年说:“我还是在想,中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