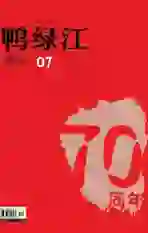紧贴现实 多元探索 厚积薄发
2016-07-27宋文坛周景雷
宋文坛 周景雷
在1980年代中期,随着文学风向的变异,在“马原热”与“寻根文学热”的现实启示下,在传统小说创作成就的影响下,一些辽宁作家们重新审视、考察历史与民间文化,剖析传统文化心理,展现浓郁的关东风情,这便形成了富有辽宁风格和气质特色的地域乡土文化小说创作。90年代后辽宁作家在地域乡土小说写作方面进一步精耕细作,逐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学版图。有人认为,辽宁的文学创作实际上已形成了有明显地域文化特色的创作群体。李惠文、孙春平、白天光、谢友鄞、周建新、李铁等人形成了辽西丘陵文学版图,邓刚、孙惠芬、于德才、张涛、林和平、津子围、于晓威、陈昌平等小说作家构成了辽东半岛文学版图,洪峰、王怀宇、韩志军、韩汝成等则在东科尔沁草原地带构筑了自己的文学版图。这样的划分无疑体现了自然人文地理与文学创作的关联,是十分准确的。[1]当然,从辽宁文学的整体来看,地域差别对文学风格写法的影响虽然巨大,但辽宁地域文学的整体风格趋势仍然趋同,淳厚朴实、扎实细致仍是统一的风格,在基本的写法上,现实主义的创作仍为主体。
一
来自辽东的满族作家于德才具有丰富的生活阅历和积累,对农村生活的熟稔和对自身民族身份的体认使他的创作深深扎根于乡土沃野之中,在80年代的创作中较早贡献出个性化的作品,成为具有鲜明地域文化风格的作家。于德才的创作不断呼应着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变异,体现出敏锐的思想触觉。《解毒》《野血》对“文革”的荒诞和惨痛多有触及,对这场时代闹剧如何伤害、撕裂了正常而健全的人性与道德进行了严肃的审视。《焦大轮子》《土商》写改革之初被物欲催红了眼睛的农村“能人”形象,无论是跑运输的焦炳和还是皮货商人卢老二,他们为求财富不择手段,或勾结官府或掺杂使假,却纷纷暴富。如何面对经济改革之初的物欲膨胀、社会失范以及由此带来的伦理松动是作品中发人深思的主题。于德才小说中的诸多主人公均展现出硬气强悍的生命状态,曹天德、焦炳和等小说人物无不具有粗莽野性、豪强率真的特点。就是一些女性形象如《风流窑主》中的富英玲、《野血》中的宋笑莲、《山里女人》中的陈香草、《土商》中的张秋平等等也均有刚直独立、率性而为的特点,这反映了作家明确的民族文化意识和崇强好胜的生命意识。
同样来自辽东的作家张涛具有自觉的小说风格意识,他的作品追求大气厚重的史诗性品格。早期创作中他曾贡献出《斗牛人》那样极具深度和力度的小说,长篇小说《窑地》的出版标志着作家创作的成熟。这部作品以辽宁农村的一座砖窑为叙事焦点,讲述围绕着它而展开的自清末民初一直到改革开放近百年的历史变迁和前后七代窑主的身世命运。七位窑主各有不同的历史时代际遇及性格特征,但他们的身世命运也构成了前后相关,交叉迭现的共同的历史面影,从而象征性地构成了一种对历史的整体性把握。《窑地》重点表现对历史流脉的追寻,在朴实淳厚的叙述中带有深厚的历史思考,其风格特征比较集中地代表了辽宁地域乡土文学的特色。
于晓威是一位“70后”作家,在小说创作中表现出多方面的潜力和严肃的态度。于晓威的创作具有多变的特点,他的持续努力使他的小说在不同题材、不同思想维度中多方发展,其作品勾勒出他不断前行的轨迹。早期的《九月玉米地》对土地、自然有着深深的依恋,村姑与林子的夫妻之情是温暖的,他们之间的依恋充满了善意的光芒。小说流露出温暖和哀伤的情感。《丧事》同样写农村,却迥异于前作。小说勾勒出一幅北方农村丧事的风俗画,对传统农村社会文化形态进行了批判性的审视,风格节制而冷静,完全不同于早期作品。《L形转弯》《勾引家日记》《弥漫》和《让你猜猜我是谁》中,则对人性有深刻精彩的剖析,体现出作家心理洞察的功力。《北宫山纪旧》又深深地参悟了人生和情感的禅理。《抗联壮士考》《陶琼小姐的1944年夏》《一个好汉》等作品又将历史偶然中的荒诞、吊诡展现得淋漓尽致,在戏谑中暗含对历史本质的嘲弄。《圆形精灵》以一枚钱币为切入视角,通过叙述它的流通经历纵贯百年,从清朝延续到当下,串联起五行八作各色社会人等,展示出与古钱相关的不同的人的各自生命历程,这又是作家想象力的游荡。但不管怎么追求形式的变化和内容创新,于晓威的努力都体现着严肃的态度,为人生而文学,以迎难而上的姿态去探索人心,去创新求变,这无疑是十分可贵的。当然,于晓威的创作还有过分的用力提炼主题,努力抽象达到更高的哲学高度反而使小说显得有些滞涩和勉强的问题。如何在戏谑化写法中处理好历史表现的轻重也是需要作家思考的问题。
马秋芬是一位沈阳作家,但她的小说创作却大都是以黑龙江原始山林中边民的渔猎生活为表现对象。《狼爷·狗奶·杂串儿》《远去的冰排》《雪梦》《阴阳角》《二十九代人杰》等小说都着力表现偏僻原始山林中的边地生活,具有突出的传奇性色彩,彰显出原始、刚强的英雄格调。在对原始渔猎生活的表现中渗透着作家对文明对抗主题的思考。马秋芬的小说语言更接近男性作家,大气、粗犷、豪迈、诙谐、幽默,她灵活运用方言土语,而且不避俗言俗语,但又能有效驾驭,形成了强烈的个人风格,具有鲜明浓郁的关东气息。她在新世纪的小说创作中明显转向,《蚂蚁上树》《朱大琴,请与本台联系》等作品致力于对底层民众生活心态的书写,有别于此前的大气粗犷,这些小说体现出细腻委婉的风格特征,对民工、下岗工人群体的关注表现出作家创作重心向现实的位移。长篇散文《老沈阳》《到东北看二人转》则展现了马秋芬散文创作的个性和实力。可以说,她拥有令人羡慕的多重笔墨和文学潜能。
二
梳理辽宁地域乡土小说的创作,辽西作家的创作是不能不提的。谢友鄞、白天光、孙春平等人为辽宁地域乡土小说贡献出了许多有代表性的文本。谢友鄞的小说始终关注着地域文化现实,其取材主要有两类:煤矿生活和边地生活。他的小说始终充满着一种强健旺盛,放荡不羁的生命活力,具有浓郁的辽西边地生活气息和独特的文化品格。他的创作从80年代一路走来,无论是《马嘶·秋诉》《窑谷》《大山藏不住》,还是较晚的《嘶天》《一车东北人》等作品无不体现出他一以贯之的风格特色和艺术追求。谢友鄞的小说注重对边地生活和热烈的人情人性的表现。蒙汉杂居的生活场景,辽西北独特的民俗风情都在他的笔下得以细致呈现。可贵的是,他的小说语言极为讲究,不仅纯净清晰而且讲求动势、韵味和美感,具有鲜明的画面感,这为他的小说创作赋予了鲜明的个性。《嘶天》为我们描绘了阜蒙边地汉蒙杂居、民族文化交错融合的特殊民族生活。“边地”的多元文化生态,文化的和谐与杂色使小说展现了文化杂交地带的独特风格。谢友鄞擅长书写辽西边地男女粗犷火热的性格气质,无论是《空谷》中的表嫂、还是《大山遮不住》的谷秀,《满山都是情》中的白玉琪,《窑变》中的翎姐,这些边地女人们都有着火辣热烈的性格与生命温度,又有着吃苦耐劳的坚韧和强悍,同时不乏温柔与单纯,这些人物形象无不留给读者深刻的印象,表现出作家对这一片土地和土地上边地儿女的一腔深情。
与谢友鄞不同的是,孙春平的辽西乡土叙事更体现了一种现实的沉重感。《蟹之谣》通过写县委书记雇工养蟹的故事,表现了底层百姓生存的尴尬与艰难。于旺田为摆脱贫困而去跑贷款买蟹苗,最后却不得不屈从于权力,成了当官的养蟹的雇工,名义上为自己养蟹,实际上为官员打工。在不免苍凉无奈的结局中明显感触到一种沉重的现实生存压力。《叹息医巫闾》写三舅一生的命运乖离与坎坷遭际。三舅一生有三次机会走出大山,但阴差阳错,都没能走出去,他逼迫着学无所长的两个儿子走出去闯天地结果落的家破人亡的下场。三舅始终保有对外面世界的幻想,为了告别贫困,他渴望走出大山,却不料世事早已不再单纯,这个残酷的世界并不能给社会底层人公平的机会,只能让他们在贫困中挣扎,找不到挣脱的机会,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这也使小说充满了令人压抑的悲剧感。孙春平以悲悯之心时刻关注苦难的社会底层人的命运,体现了深厚的现实关怀。作家对乡土的关注是和强烈的问题意识、批判精神联系在一起的,情节叙述的同时渗透着强烈的质疑和批判精神,这构成了作家写作的特质。这一特质不仅在乡土文学写作中凸显,他同期写作的许多“校园社会问题小说”如《老师本是解惑人》《老师本是老实人》《怕羞的木头》等也体现了这一特征,对当代知识人的精神堕落和生存的尴尬进行了较为深刻的暴露和审视,也体现了非常强烈的批判精神。孙春平的小说情节性十分突出,具有曲曲折折引人入胜的特点,情节的戏剧性明显是在模拟这个光怪陆离的社会生活的现实性,使小说具有可读性的同时似乎也制约了作家当时的写作向深层次展开的可能。
白天光是又一位有影响的辽西地域乡土小说作家。事实上,他的文学叙述因其个人生活轨迹和思考倾向的不同早已超越了“辽西”“辽宁”的空间范围,题材范围也绝不仅限于乡土的书写。从80年代至今,白天光的小说从多个方面进行创作拓展:有关于关东历史的重新审视与结构的小说,如《雌月季》《行走的鸡毛掸子》《香槐》等,有反映改革开放以来乡村生活种种变化的小说,如《七角猪的悲剧》《冬天里的一把火》《天堂的萝卜》《鬼塘》等,还有对现代人生存状态与尴尬处境的有些哲理化意味的反思与阐释,如《希尔顿烟蒂》《田鼠在城市的红灯区漫步》等。富有智慧,笔带反讽,善于编织故事并体现含而不露的批判是白天光小说的突出个性。这一个性是与作家的智慧和气质紧密相连的,也是作家的学识阅历和生命智性的集中体现。阅读白天光的小说,我们会感到写作智慧所驱遣的灵动、轻松,而种种深刻的思考却往往隐藏在引人入胜的异人奇事之中,在曲折回环的故事编织中渐次呈现,这种举重若轻的能力令人印象深刻。
三
90年代后的中国社会,面临着市场经济大潮剧烈冲击下全面转型的现实压力,急剧的发展变化同时带来了对城乡生存秩序的强力冲击,尤其是乡村伦理秩序和乡村文化秩序产生了急剧的变异。城与乡不再是空间意义上的分割而是在现代化大潮中愈加凸显出的不同的文化空间、不同文明规范之间的冲撞和不协调。城市文化与文明以其强烈的诱惑力冲击着乡村文化,于是生长于斯的乡村男女便有了徘徊于城乡之间的挣扎和困惑。对这一困惑的细致表现和准确拿捏构成了孙惠芬乡土叙述最主要的内容。《歇马山庄》《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上塘书》《吉宽的马车》等地域小说作品使孙惠芬成为了辽宁地域文学写作的杰出代表。孙惠芬十分注意经营自我的精神故乡,如同高密东北乡之于莫言,马孔多小镇之于马尔克斯一样,“歇马山庄”“上塘”这样的辽南乡村成为孙惠芬笔下刻意营造的具有强烈地域文化审美意义的地理存在。在这片土地上寻找、失落、挣扎的男女,他们对现代生活的渴望与激情,他们周遭乡村秩序的变迁,以及在这种变迁中他们强烈的心理律动都在孙惠芬细腻朴实、不急不徐的叙述与描画中表现得充实而饱满。孙惠芬小说经常以针脚细密的心理叙事贴近人物的复杂内心世界,她善于贴着人物的心理流程和逻辑展开叙述,其自然亲切和水到渠成都体现了作家极强的控制能力,带有心理现实主义手法的独特韵味。这种写法或许显得不够灵动,但足够细腻。无论是《歇马山庄》《歇马山庄的两个女人》还是《吉宽的马车》《民工》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看成是不同视角下人物心灵史的细致展现,而综合起来,无疑构成了孙惠芬式的人物叙述群像,他们是生长于辽南农村的“这一群”,同时也反映着现代化大潮下农村的沧桑变化。
陈昌平是一位独具特色的大连作家。他的创作从80年代起步,中间也曾经历了较长时间的积淀和蛰伏,新世纪以来,他以《英雄》《汉奸》《特务》等作品重登文坛,引起广泛关注,随后《国家机密》《复辟》《肾源》等中短篇小说相继问世,获得评论界一致好评。不同于其他辽宁作家致力于乡土地域风情的描述,陈昌平更看重小说表现人与历史的关系这个主题,他将一个个卑微无助的小人物放入过往的历史中,通过个人与国家、个人与历史的交错、龃龉和碰撞展开对历史幽暗之处、人性复杂之处的审视和观察,所以从某种意义上看,他的创作更像是如昆德拉所言的对“存在的勘探”。他的小说致力于叙述充满荒诞性的生存场景。在《英雄》中,退休工人老高在人民广场给百无聊赖的老人们讲战争史,天长日久竟被误当作战斗英雄崇拜,意外的“成功”逼得老高只能假戏真做,冒充“战斗英雄”四处演讲;在《特务》中,儿子遭受政治磨难,为了不让母亲担忧,编造了一个又一个谎言,最后当自己再也无法回家侍奉母亲的时候,又编造了自己是被组织选中到台湾去做卧底的谎言;《国家机密》中的王爱娇能做预言性的梦而且屡屡在“文革”政治大事到来前准确梦见,于是这样一个孩子被政治力量严加看管,梦境竟然成为“国家机密”,禁止外传;《汉奸》里的李徵本来是一介知识分子,在日军守备队长田中敬治强迫下,他作了田中的书法老师,尽管李徵利用特殊身份秘密传送过日军情报,但在抗战胜利后他却对“汉奸”身份百口莫辩,最后被枪毙……身份的错位、际遇的荒唐、历史与现实的互嘲造成了作品中的荒诞感,经常使小说充满内在的反讽和张力。人物诸多不合常情的行为正透露出历史本质的乖违错乱,显然,这是对沉重历史深刻而严肃的思考。而恰到好处的夸张和反讽又往往使叙述具有特殊的间离效果,它使小说叙述具有足够的距离感和分寸感,这便赋予了作品一种智性和从容。在虚与实之间,作家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叙述方式和视角,从而保证了作品在历史纵深和小说组织之间的弹性和平衡。小说是对巨大历史难题和历史处境的深入解剖,但它紧贴着一个个的个体生命展开,避免了对主流话语的背书和演绎;小说叙述的灵动和分寸感又避免了历史叙述中常见的滞重和僵硬,这是对小说能够怎么写的巧妙回答,正如评论家洪治纲所言:“陈昌平以其对历史与生活的特殊审视和理解,使叙事成功地摆脱了对社会表象结构的复制并进入幽暗仄逼的文化记忆深处,以反讽式的话语呈现出个人与历史的荒诞性存在图景。”[2]
通过对以上作家创作的梳理我们看到,辽宁不同地域作家的创作已经形成了较为统一的群体特征,对乡土的关注与表现,对乡土中人情人性、生存状态的细致描摹使辽宁作家的群体风格清晰起来,这标志着辽宁乡土写作板块的整体上升。当然,区域文化风情的描摹作为主流并不能取替不同区域板块作家的个性化、多元化追求,很多作家力图开拓富有个性风格多领域创作能力,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
以上仅就辽宁区域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作了极为粗略的概述。事实上,辽宁作家对区域乡土文化的倾情注力使90年代以来的辽宁文坛涌现出了大批优秀作品,这几乎从群体意义上塑造了辽宁文学的整体形象。如果说80年代的辽宁本土的小说创作还停留在现实的“问题”语境中做反思与批判的话,那么90年代以来辽宁小说创作通过倾力表现关东黑土,通过不同区域作家的不同审美风格的写作实践已经初步确立了辽宁文学的整体风貌,这是坚持文学从生活中来到现实中去的现实主义原则的文学,是与土地与人民情感相系、血肉相连的文学,是风格浑厚、朴实厚重的文学。值得特别指出的是,80-90年代,当辽宁作家致力于地域乡土写作时正是全国小说创作潮流快速变化之时。先锋热潮使小说创作的走向发生了较为明显的方向性转折,小说关注“怎么写”更甚于关注“写什么”。进入90年代之后,新写实、新状态、都市写作、女性写作等不同的创作潮流纷至沓来,新的媒体扩张和网络写作更是显得咄咄逼人,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似乎已成明日黄花。另一方面,文学在市场化、消费化的大潮冲击下日趋边缘化,已不复80年代的话语主流地位,文学的精神导向与思想启蒙作用日渐衰微。此时,辽宁作家也面临着某种确定方向的困惑,是跟随潮流、趋新鹜奇,还是坚持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路子成为辽宁作家必须做出的选择。我们看到,坚持现实主义精神的创作,坚持立足本土,从深厚的文化土壤中挖掘现实的意义,再现人生人性的多重内涵,贴近文学的“人学”根基,仍是辽宁大多数作家的创作选择。正像有的研究者指出的那样:“作家们似乎是说好了的,不动声色,不赶时髦,不怕寂寞,将一篇篇佳作呈现出来。而其中在现实主义精神影响下的作品仍占了绝对的比例。”[3]这个选择当时可能会被看作是“保守”,“缺乏创新”的一种精神疲态,甚至被视为整体性的“缺乏上进”。但事实上,辽宁的中青年作家们,他们都有一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韧性和坚持。尽管文学的追新逐奇、潮起潮落更能引人注目,造成轰动性的一时话题,但文学毕竟是人学,它要回归对高度复杂的人性人生的观照上来,还要与现实的血肉紧密相依。从这个意义上看,90年代辽宁作家们的集体选择更像是一份沉默的宣言,它宣告了与浮华躁动的市场化时尚的远离,宣告与单纯玩弄技巧的形式化写作和操纵注意力的媒体化写作的分野。因此,这样一种沉潜的现实主义写作姿态更像是一种自觉的价值选择而不是自甘鄙陋或敝帚自珍。它立足于辽宁的现实土壤,关注现实的精神问题,直面人生人性的困境,保有独特的辽宁风格和气派。如果说,80年代的辽宁现实主义写作是从“问题”起步并得到多方面的经验拓展而显现出深化成熟的趋势的话,那么90年代后的辽宁文学则是超越了这个单纯的社会学写作模式,努力从精神气质上接近现实主义的精神本质:深刻的批判意识,深厚的悲悯情怀和纯洁的人文理想。正是经历过90年代的沉潜与寂寞,辽宁作家们才纷纷在世纪之交和新世纪到来后拿出了属于自己的“辽宁故事”,从而获得了在中国当代文学地形图上不容忽视的位置。
四
作为工业大省和传统老工业基地,辽宁曾经是全国瞩目的经济“火车头”,辽宁文学界也一直关注工业题材小说的创作,也曾经贡献出草明的《乘风破浪》等经典作品。90年代以来,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入,反映国企改革及其问题的辽宁工业题材小说再一次引起文坛内外的关注,以胡小胡、李铁、孙春平等为代表的作家聚焦国企改革的现实艰难,以全景方式书写90年代以来的经济改革及其面临的问题与冲突,形成了一股颇有影响的创作潮流。辽宁作为老工业基地面临国企改革的困境,企业转型、工人下岗、积弊重重、改革维艰。因此辽宁工业题材小说的大量涌现,是对当时现实困境的反应和思考,是作家现实主义问题意识的自然流露。值得注意的是,与此前曾在全国范围内引起过热烈关注的“现实主义冲击波”等创作相比较,辽宁工业题材创作体现出了自己的性格和深度,这体现为既能精细描写现实的复杂多面性,又能细腻表现国企职工复杂的心理反应;既关注总体转型的艰难和滞重,又渗透着作家对工人大众兄弟般的温情和人性的悲悯。因此,辽宁工业题材作品在叙事表现上既有大刀阔斧的粗线条描写,体现出叙事的力度和厚度,又有客观冷静的现实思考和细致深入的人性体察,表现出思考的深度和情感的温度。在省外的同类创作中,很多作品往往过于纠缠于困境时艰的琐碎描绘,往往忽略人性的维度,缺少思想的深化,“分享艰难”的煽情描绘和道德化取向很容易导向掩盖矛盾,使文学流于苍白和虚假。但纵观辽宁工业题材小说创作,通过有效的开掘与书写无疑在相当程度上避免了这一问题出现。
90年代以来的辽宁工业题材小说最引人注目者是两类创作:胡小胡的《蓝城》《太阳雪》代表着“总体把握”“正面强攻”式的写法,着重对国企改革艰难进程的宏阔表现。李铁“女工系列”小说则是眼光向内,通过对普通工人、下岗工人心态、命运的表现展现出抒情化、“向内挖掘”的特点。
胡小胡的长篇小说《太阳雪》描绘了东建总经理陶兴本雄心勃勃,励精图治,努力带领企业脱困但最终失败的故事。市场环境不规范、企业内部争权夺利、上下级多方掣肘,还有社会多方面的腐败终于使他没能凭借自己的知识和才能将东建这条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搁浅的大船拖出困境,再创辉煌。作品细致描写了在国有企业内部重重横亘的发展困境,对企业积重难返的体制原因做了令人深思的揭示和观察,尤其对社会腐败等问题的揭露令人触目惊心。作家试图赋予主人公鲜明的英雄气质和精神品格,作品也具有明显的抒情浪漫倾向,但严峻的现实问题并不能靠理想主义解决,主人公的身亡更使作品蒙上了浓重的悲剧色彩。显然,作家并不愿意以温情和理想抹平现实的裂隙,并不愿意在世俗的维度上认同现实,这赋予了作品某种冷峻、坚硬的风格。
李铁是另一位擅长书写工业题材小说的作家,不同于胡小胡全景式的细致描摹,李铁的小说更多体现了对人情人性的关照,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他的小说更像是把工业题材推到了幕后,命运与人性、道德与守望等主题被推到前台,这赋予他的创作强烈的人文色彩。李铁自己也说过:“我不太愿意听人把我界定为所谓的工业题材的写作者,其实我的绝大部分小说写的并不是工厂生活。小说是写人的,其他的都是背景,只要把人的喜怒哀乐写出来,把人性和心灵写出来,就会是好小说。”[4]《乔师傅的手艺》《乡间路上的城市女人》《花朵一样的女人》是他最初阶段的作品,发表之后轰动文坛,被称为“女工三部曲”;之后,《冰雪荔枝》《青铜器》等家庭题材的小说显示了作家逐渐开放的眼光;随着人生阅历的进一步拓展,李铁日益显示出进一步开拓多方面创作领域的潜力,《城市里的一棵庄稼》《出轨》《以水为花》等,获得了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在李铁的小说中,女性形象占据着中心位置,这些女性形象明显浸透着作者的情感,为似乎是单调呆板的工业题材的书写注入了柔美和细腻的格调。李铁笔下的这些女性虽然聪慧善良,如花朵般美丽但都不免遭遇现实的悲剧。不论是《纪念于美人的几束玫瑰花》还是《花朵一样的女人》,都涉及到美丽的工厂女性在权力之下的命运,无论是有关家庭与婚姻、情与性,这些女性的命运与权力都脱离不了关系,归根结底她们的生存是被迫压服于权力下的生存。当然,怀着对笔下主人公的偏爱,作家赋予了这些女性坚韧执着的个性特征,女性的生存悲剧和她们对这一命定的悲剧的承担与反抗构成了小说内在的张力,也赋予了小说某种悖论的色彩。
孙春平是一个勇于直面现实的作家,他有极其强烈的社会问题意识,在他的辽西乡土文学和别具一格的“校园社会问题”小说中我们能够发现这一强烈的个性特征。孙春平书写工业题材的小说往往把焦点放在下岗工人身上,忠实地记录下岗转型的社会震荡。《陈焕义》《陌生工友》《拿不准是谁》《太平世界》等小说,传达的正是转型期下岗工人的酸甜苦辣。他对下岗工人有着兄弟般的温情,着力讴歌这些虽挣扎在社会底层但有着纯洁道德的老百姓们。《陈焕义》中的主人公陈焕义、《陌生工友》中的聂家祥、《太平世界》中的赵师傅都是这样仗义疏财、热情主人的道德模范,显然,作家对这些人物有着深厚的偏爱。
辽宁工业题材的创作者很多,上面提到的三位作家仅是其中的代表。众多创作者坚持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坚持关注社会底层,对艰难转型中的辽宁社会百态进行信史般的描摹和书写,在世纪之交的时代留下了文学的印记。但是,从总体上看,辽宁工业题材的创作无论是从挖掘生活的深度上还是从反映生活的广度上还未达到读者期望的水平,并未展现出多元并进、繁荣发展的面貌,这与老工业基地的地位并不相符,多多少少令人遗憾。究其原因,工业题材小说本质上是与现代文明的成长同步的,是与都市文明相伴相生的,而辽宁却并不是都市文明发达的地区,许多书写工业题材的作家更熟悉的创作资源是乡土和农村,无论是在生活感知上、审美倾向上、道德尺度上作家们更熟稔乡土文化而与大工业生产情况下复杂的生存场景仍有隔阂。这某种程度上造成工业大省乡土创作强劲而工业题材偏弱的现象。另外,立足现实的问题意识既是创作的动力也有可能成为创作的束缚,如何摆脱单纯关注现实问题的倾向,赋予作品更深层次的思想把握力、历史洞察力和审美创造力,使作品在厚重沉实、有情感温度的前提下更为灵动多姿仍是作家们应该努力的方向。振兴工业题材,尚需作家的努力。
五
辽宁改革开放以来的小说创作已走过将近四十年的旅程,对它的综合评述是难以用短短的一篇文字加以概括的。本文从现实主义这一具有高度包容性的理论角度出发,力图兼顾多元发展的文学现实,但生机勃勃的创作是永远超越理论的规限与视野的,所以本文不可能对纷繁复杂的小说创作作逐一细致的梳理和归纳,挂一漏万在所难免。许多优秀之作和出色作家,许多值得回味思考的创作趋向也只能割舍,留待别篇。这些优秀作家里面既有紧随马原的脚步具有极强文本个性化实践特征的刁斗,还有对新兴都市中人生百态持续关注的皮皮、津子围,以及在儿童文学创作中展现不俗实力,获得文坛普遍关注的薛涛、常星儿、肖显志、老臣等等。而近十几年来的新世纪文学,辽宁文坛又涌现了新的创作力量,李铭、苏兰朵、鬼金、曾剑、鲍尔金娜等70、80后作家俨然成为未来辽宁文坛的新星。许多已成名的作家也展现了不断拓展的发展态势,孙慧芬、李铁、孙春平、周建新、马秋芬等纷纷拿出了有分量的作品。这一切使得总结辽宁近四十年的小说创作变得极为困难。本文只能从改革开放的文学时代起步,到新世纪之初的时代终结,力图对这几十年的小说创作给出一个视角清晰的透视观察和综述评价,对许多复杂而有难度的文学现象及近年来的文学整体观察,只能留待将来了。
从整体看,改革开放近四十年来辽宁小说的创作历程是一个多元文学观念并进但以现实主义为主导的发展过程,文学创作思想从单一的社会学意识向更为宽宏的现实主义观念转变为辽宁文学的丰富和发展创造了条件。经历了80、90年代的沉潜和积累,辽宁小说创作整体上逐渐找到并形成了“辽宁风格”和“辽宁气派”并贡献出了具有极强文化地域特色的“辽宁故事”。近年来,辽宁的小说在全国范围内屡获奖项,许多作家逐渐具有全国的影响,这充分说明了辽宁小说创作厚积薄发、后劲充足的现实,也有理由让我们为辽宁文学的未来抱有谨慎的乐观。
当然,辽宁文学的问题和痼疾依然存在。首先,作为小说文体最有影响力的长篇小说创作仍显得薄弱,我们还很难说有底气凭借长篇作品与历史积淀厚重的江苏、湖南、陕西、山东等地的文学创作比肩。20年前,前辈作家刘兆林曾经以“辽宁应该是长篇小说的大省”为题对辽宁文坛说了一些“实话”,他认为,辽宁文学还缺扛鼎之作,即使是获奖的辽宁中长篇小说“与大将之作似乎都有一截距离”。[5]这无疑是清醒的。经过近十几年的发展,辽宁文学的长篇创作已有很大改观,但仍然存在明显差距。
其次,正因为有影响力的长篇小说的缺失,辽宁小说创作者众,但有山无峰的情况比较突出。尚缺对某一领域综合集大成的大部头作品,也便同时缺少了这样重量级的人物。
再次,现实主义作为主流的创作精神与原则,既体现了辽宁作家的沉实与厚重,同时也反映出某种保守和执拗的心态。辽宁作家在80、90年代之交时并没有随大流跟着文坛的流行风向转变自己,在90年代直至世纪之交才拿出了一系列颇有分量的作品并形成了群体风格。从后反观,这是得大于失的;但同时也毋庸讳言,辽宁作家对形式创新、新的技巧方法、新的文学观念缺乏敏感,这多少阻碍了更快、更多元发展的可能。表现在创作上,辽宁小说总是在文学新潮中显得“慢半拍”,很多自认为不错的作品也免不了被人视为亦步亦趋之作,缺少独创性和新鲜感。马原是走向全国的辽宁作家,而有意思的是,他很难被视为文化地域意义上的“辽宁作家”,他的创作与反响反而在家乡显得寥落而沉寂,真正跟随他的文本创造方向的辽宁作家寥寥无几,这种情况未免遗憾。所以,关注底层的现实主义精神、朴实和厚重的风格表现与写法既赋予了辽宁作家和辽宁小说某种整体性格,又一定程度上成为辽宁作家进一步开拓、超越自我时面临的规限和必须跨越的界桩。
如何保有辽宁文学已经具备的深厚热烈的人文关怀,在现实主义传统之中融进现代的人生形态、社会形态与语言形态,从而创造一个独有辽宁地域文化韵味的小说形态是摆在辽宁作家面前的难题。我们相信,辽宁作家已经初步具有了自己的风格和气韵,已经奉献了独具特色的“辽宁故事”,在不远的将来,也一定能够凭借自身的努力在中国文坛上推动辽宁文学的崛起,在“中国故事”的讲述中占有不可忽视的显要位置。
参考文献:
[1]韩春燕:《当代东北地域文化小说论》,吉林大学博士论文,2006。
[2]洪治纲:《幽暗深处的历史回响——评陈昌平的小说创作》,《当代作家评论》,2004,6。
[3]张祖立:《新时期辽宁小说创作述略》,《大连大学学报》,2002,3。
[4]李黎 林建法 傅汝新 女真 李铁:《工业大省的工业题材文学为何贫弱?》,《艺术广角》,2009,3。
[5]刘兆林:《辽宁应该是长篇小说的大省》,《艺术广角》,1995,5。